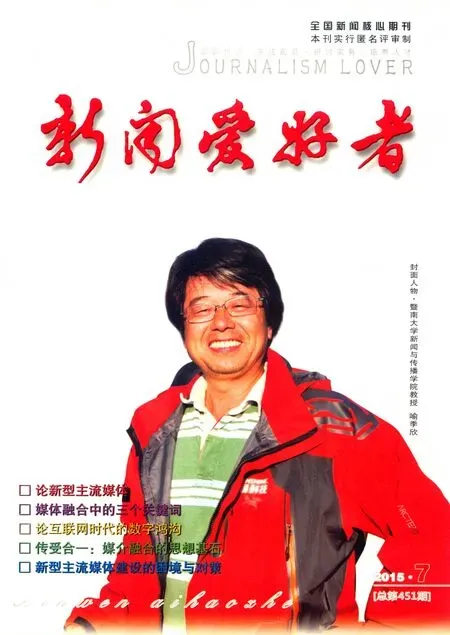新媒介平台与乡村媒介化演进——以农民利用微博售卖农产品现象为例
2015-03-02李凌达
□李凌达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主任科员)
“三农”问题是近些年来中央始终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1]在媒介技术狂飙式发展的今天,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依旧不能被忽视,如何让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任重而道远。施拉姆指出:“各种媒介除非与一个经济的、技术的和有社会支援的计划相配合,它们本身对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是很小的。”[2]根据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32亿,其中农村网民占比28.2%,规模达1.78亿。[3]该报告显示,农村网民的互联网应用情况中,即时通信、网上看新闻等网络应用的使用率远超过其他。根据艾瑞咨询 《中国微博用户行为研究报告》(2014年),截至2014年3月,微博服务在PC端阅读覆盖人数达到2.9亿。而微博用户中47.1%的用户因有相应的购买需求和广告进行互动,44.4%的用户因广告与需求相关而在微博上进行购物。微博已经成为电商网站(尤其是淘宝)的导流入口之一。[4]显然,城市居民所熟知的社交网站和电商类网站并没有出现在农村网民常用的互联网应用之列。但不可否认,新媒介技术正以各种方式渗入乡村,无论是以村村通、户户通为代表的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还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的尝鲜使用,都在形式上反映了乡村社会与媒介更新的关联。
以微博为例,关于农村网民的微博使用情况,鲜有相关的研究和数据。以“微博”“农村”“农民”等为关键词在新闻搜索引擎和报刊数据库检索,结果不多且关注点分散,经过汇总发现最多的是关于农民通过微博平台开展农产品售卖的新闻。农民的概念已经远非传统意义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5],本研究中的农民概念所指广泛,既指传统的农民,也指从事与“三农”相关工作的个人,比如农村工作者、“村官”,还指新兴的“新农人”。除了传统农民、新农人的明确提法,其他并未做严格区分。本文就以农民利用微博售卖农产品现象为例,对新媒介平台和乡村媒介化演进的议题进行研究。
一、微博售卖的传播路径分析
最早引起关注的微博售卖是重庆武隆“微博卖瓜”。2011年5月初,一批“沧沟瓜农”的微博在网上悄然兴起,赢得大批粉丝关注,并连续两天在热点话题中排行首位。随着网友关注和媒体报道量的增多,被称为“西瓜书记”的武隆县沧沟乡党委书记张宏“@武隆张宏”渐渐“浮出”水面。瓜农“微博卖瓜”的想法就是出自这位书记,并由她组织当地的大学生“村官”为瓜农开通了微博。受其影响,陕西延安宜川县的副镇长王涛“@百姓大于天”通过微博“吆喝卖苹果”,与公益活动相结合,同时千里送瓜去海南、进北京超市等制造相应的新闻话题,产生了宣传售卖的一系列活动。各地类似的活动也纷纷推出,从批发市场到超市,从线下到线上,从博客到微博,从微博到微信,农产品营销走出了越来越多的渠道。
(一)微博售卖的传播者是农村掌握新技术手段的意见领袖
由于微博将长篇大论、打字速度、持久上网的限制统统摒弃,因此,低门槛应用下不只是官员、专家、明星和专业媒体人能够引领舆情,大量由普通人组成的意见领袖也因各种机缘被“制造”出来。[6]微博售卖农产品行为起初都是组织传播行为,最有代表性的是2011年9月由人民网人民微博和大学生“村官”园地发起的一场农产品微博展销会,来自北京、重庆、内蒙古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村官”们在这一平台上,争相抢晒当地富有特色的农副土产,吸引了众多网友围观并表达选购意向。[7]参与组织传播的传播主体大都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对传播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具备可行性,这些人都相对较早地接触并使用微博,这些掌握新媒介技术手段的人成为网络售卖的意见领袖。
(二)传播内容都符合自己的身份并遵循网络传播的规律
微博售卖的内容根据传播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层官员,这类微博充当公告板的作用,将自身定位为农民兄弟的代言人,以工作笔记的形式记述下乡过程中看到的农业生产状况,以观察者的角度进行传播;另一类是农民自身,他们学会刷微博之后,每天记录农产品生产的心路历程和销售情况,让网友和买家参与售卖的过程。这两种方式都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手段,运用对农产品或者农作物的特写图片,形成视觉冲击。
(三)传播终端更新换代但使用者并未参与媒介化进程
微博因为随拍随传的功能,催生了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海南土鸡蛋”的运营者除了收集家里的土鸡蛋打包发往海口,每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拍照片并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微博。为了方便上网和拍照,他还特地换了一部智能手机。但是传播终端的更换并不意味着售卖者能够参与到农村媒介化的进程中,笔者在研究10位瓜农的微博时发现,这些微博的内容基本相同,微博的数量基本都在130—250条,其中原创微博数40—60条。转发微博集中转发@武隆张宏的微博内容,而且10个微博账号的转发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农民虽然开通了微博账号,但其并没有主动使用的意识和自主权。智能手机这样的终端使用促进了传播主体的分化,却并没有促进所有的使用者参与媒介化进程。
(四)微博平台的“出村信息”和“入村信息”不对等
农产品售卖虽然在社交媒体上,但作为社交媒体的属性并未得到太大的发挥,而更多的是发挥了公告板的功能。以吆喝卖苹果为例,微博发布信息、公布手机号,却并没有实现网络直接下单购买的产业链,而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来达成购买意向。武隆西瓜的微博也是这样,沧沟瓜农不止一次地表示:“我们不是通过微博来直接销售西瓜,而是通过这个平台来宣传沧沟西瓜。”[8]交易很多都是在线下完成的,即便是通过线上完成交易,微博的作用也是用来宣传导入电商页面,并不再关注微博宣传的后续效果。微博传播只承担对外发布信息,并没有实现对称的反馈信息,未实现完整的传播链条。
(五)传播效果差异显著,社会效益多元化
农产品的售卖者观念差异较大,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结合农产品自身的特点,才能实现有效传播。比如西瓜并不适合网购的物流渠道,因此微博只是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土鸡蛋同样在物流上是短板,即便有网店也只能本地售卖;而核桃从价值到物理特性都适合网购,就催生出当地政府出台政策,促进核桃等农林产品电子商务销售队伍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营销手段的选择会产生特定的传播效果。苹果售卖作为帮助果农的宣传路径,推动了微博公益活动的开展。媒介的力量使得乡村与城市生活有了直接面对的机会,农民的劳动成果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进入了城市,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促进,凸显了新媒介内在的社会力量。购买和销售的公益性质凸显。
二、从新媒介的使用到新媒介平台的形成
(一)新媒介时代乡村媒介使用情况与总体趋势趋同
根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2011年有27%的农村手机用户使用手机上网,他们使用手机上网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在线聊天,有24%的手机用户至少每周使用即时通信软件进行聊天,每周使用手机浏览互联网的用户为22%。[9]而根据笔者2012年在陕西关中地区乡镇所做的农村媒介使用情况的调研来看,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很低,只有三到四成的受众上网,而在这些上网用户中,每周上网一次以上的用户仅占20%,并且一般都是晚间在家上网。在对待新媒体问题上,娱乐消遣是其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2014年,农村新增非学生网民的互联网应用情况是:即时通信、网上看新闻、网上收听或下载音乐的使用率分别为72.2%、61.3%和43.3%,远远超过其他类网络应用。[10]从2011年到2014年,新媒介的发展日新月异,而即时通信作为网民最基础的网络需求,稳居网民使用率第一位,并呈现出使用率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是以本文研究微博平台为例,2014年微博的用户规模是2.75亿,比半年前减少543万,在经历了2011—2012年的快速增长期后,微博市场呈现出了集中化趋势,微博用户规模有一定程度的降低。[11]从大的趋势看,农民对微博的使用也顺应了这一趋势,比如沧沟瓜农的微博集中在2011年和2012年的瓜果种植季和售卖季更新,之后就基本不再更新,直到2013年停止更新。
(二)多元化应用的异军突起推动新媒介平台的形成
微博用户使用成熟度和内容偏好的加深,促进其自身属性的变化。微博成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媒体的信息发布交流平台,随着微博数据的积累,其网络营销的价值得到了发挥。以微博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使其原有以人际交往为目的的社交平台得到了拓展,而以淘宝、天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纷纷进军县域市场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使得微博的平台得以拓展到电子商务网站,实现一站式营销售卖流程。“@海南土鸡蛋”就是以这样的商业思路,从本地配送开始,到微博宣传,再到电商售卖,其微博的背景页面就是海南土鸡蛋的微博网址和二维码扫描入口。微博的使用现在仅仅是销售环节中的一个,对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达到了集成和集约的目标。
(三)县域电子商务模式和新农人群体的加入推动平台化进程
新农人是现今农民中的一个新兴群体,他们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业。新农人的构成是多样化的,有本地农村人口,有外出一段时间的返乡者,也有大量的外来者,他们或来自外乡,或来自城市,其中较多的人具有其他职业背景。在农村从事农产品电子商务经营的网商,就是新农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12]新农人群体逐渐崛起,他们活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成为领域内最具活力的群体,在各类电商平台上积极推动着农产品电商的实践。[13]而政府组织县域电子商务模式,也在各地产生不同的样本。以甘肃成县为例,“微营销”已经成为该县核桃电子商务的一大特色。目前,成县电子商务协会主要通过微博、微信等工具来营销推广,协会会员注册了统一的微博ID,通过与媒体、专家、大V的互动,极大地提升了成县核桃的线上知名度。当地淘宝卖家也在快速扩张中。据阿里研究中心统计,目前注册地在成县的淘宝卖家账号接近200家,核桃成为主打产品之一,其销量逐月提升。[14]微营销作为推动力,促进了传统意义上新媒介的使用和转型,和城市居民热衷于新媒介社交功能和朋友圈功能不同,对于乡村来说,新媒介的商业功能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三、新媒介平台助推乡村媒介化的可能性
(一)乡村媒介和媒介乡村共同构建乡村媒介化
乡村媒介的概念主要指目前仍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拥有的媒介环境发展和媒介使用状况,包括面向共存的媒介传输机构、设备、功率、覆盖情况,同时又指目前农民所拥有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终端情况,包括广播电视接收设备数量、报刊订阅量、图书拥有量,以及目前正在普及中的新媒介,如电脑、互联网、手机等。乡村媒介还包括面向乡村时媒介的运行规则和过程。[15]现有的媒介规则和定位都是由最早接触到媒介的群体制定和使用的,对于参与度和使用率都不高的农村来说,已有的规则可能并不适合乡村实情。传统乡村作为中国熟人社会的代表样本,现实生活就是朋友圈和社交功能的集合体,对新媒介网络社交功能的需求比较低。而新媒介作为新事物,通过掌握新技术的意见领袖传入乡村后,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型和改造,结合了当地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纯粹是本着商业目的去了解和使用的,“酒香也怕巷子深”的观念逐渐在乡村树立起来。
媒介乡村的概念指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大众传播媒介和非官方的各类媒介共同构建的乡村媒介形象,包括媒介传播内容中农村所拥有的份额,其农村内容同农村、农民、农业之实际情况之间的吻合状况,媒介所展现的农村、农民、农业的形象为广大农民所认可的程度。[16]换言之,也就是媒介里展现的乡村。“微营销”作为新鲜事物闯入人们的视野,比较符合都市类媒体的新闻定位,农产品滞销、微博求助、乡镇干部开通微博等关键词本身就能够引发媒体的关注,而当农产品的购买者与公益结合在一起,因为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就更容易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因此媒介乡村就通过新媒介平台得以展现在受众面前。乡村媒介与媒介乡村是彼此互联、相互促进的。
(二)乡村媒介化对农民媒介使用的作用或有限
城市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占有,政府对组织信息的把关,村庄精英对生产信息的垄断,往往会使普通村民在信息接收上感到有巨大的落差,使他们的依附感和被剥夺感持续增强。[17]新媒介技术在农村的传播者,包括开通实名微博的官员、大学生“村官”、在外面求学归来的农二代。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依旧是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获得信息,并听从这些意见领袖的指挥,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习惯。通过微博售卖农产品的创新扩散,并不能达成对新媒介技术本身的认知,而是对销售渠道的认知。农民并没有构建起自己的微博,反倒依旧要借助组织的力量,通过意见领袖实现使用新媒介平台的目的。
(三)知识鸿沟在新媒介平台上或转化为媒介鸿沟
媒介所展现的乡村和农民形象跟人们刻板印象当中落后守旧的农民有所不同,但需要看到,能够使用新媒介平台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上文所述“新农人”的范畴,是区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兴群体,并不能代表广大农村人口。新媒介平台为城乡沟通搭建了桥梁,虽存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是却通过共通的文化符号在新媒介平台上形成共鸣。但是,这样的共鸣只会加深人们对“媒介幻象”的认知,却忽略了多数传统农民并未得到新媒介带来的切实利益的事实。在初步尝到新媒介带来的新奇感之后,广大新农人出现,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资源和平台优势,使得传统农村的经营模式直接进入规范化、品牌化、平台化的转型,这些都是传统农民所不具备的。知识鸿沟在新媒介平台上或转化为媒介鸿沟。
(四)城乡沟通的密切可能带来消费文化在乡村泛滥
在一个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和图像通常都被传遍全球,我们和那些与我们的思维完全不同、生活完全不同的其他人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18]新媒介平台对传统的农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消费文化以农产品为载体影响农民的观念和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其对新媒介的初步认知。新媒介被标上消费媒介的标签,其他如社交功能、公共空间的功能在乡村通过不同的路径被解构或消解。其一,通过公益活动,汇聚社会正能量。海南的滞销香蕉内地援助购买,陕西的滞销苹果海南解急购买。但对于农民,公益只是售卖农产品的形式或者渠道,公益的具体内涵并未得到深入传播,公益是消费的代名词。其二,消费文化先入为主。信息化经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式。[19]接触新媒介的农民在接触到“微营销”之后,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是社交功能,而是销售工具。褚橙、柳桃、潘苹果这些在乡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物品,却因为城市居民对乡土生活的怀旧,成为健康和时尚的代名词。消费文化对传统乡村的侵蚀通过新媒介平台实现,农产品电商的蓬勃发展,新媒介与商业的标签捆绑在一起,通过农产品的载体,实现了对农民消费文化的灌输。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EB/OL].http://cpc.peo 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4.html
[2]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89.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 140721_47437.htm
[4]艾瑞咨询集团.2014年中国微博用户行为研究报告简版[EB/OL].http://report.iresearch.cn/2183.html
[5]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05.
[6]毕宏音.“微博”热潮下的网络意见领袖变化趋势[J].新闻爱好者,2011,8(上).
[7]张卉,等.大学生村官微博争晒特产 创业、帮农两不误[EB/OL].http://cpc.people.com.cn/cunguan/GB/15631906.html
[8]微访谈——乡政府带瓜农微博卖瓜[EB/OL].http://talk.weibo.co m/ft/20110509829?page=6
[9]爱立信消费者研究室.2011年中国农村消费者通信消费报告[E B/OL].http://www.ericsson.com/cn/res/site_CN/docs/2011_suburb_chines e_consumerlab_report.pdf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 140721_47437.htm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7/t20 140721_47437.htm
[12]汪向东.新农人与“新农人现象”[N].河南日报农村版,2014-04-02.
[13]阿里研究院.阿里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2013)[EB/OL].http://www.aliresearch.com/?m-cms-q-view-id-76127.html
[14]焦宏.特色农产品“微营销”很火[N].农民日报,2014-01-12.
[15]段京肃,段雪雯.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的理解[J].现代传播,2010(8).
[16]段京肃,段雪雯.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的理解[J].现代传播,2010(8).
[17]骆正林.农村传播研究的“寂静”与“繁荣”[J].新闻爱好者,2013(9).
[18]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19]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