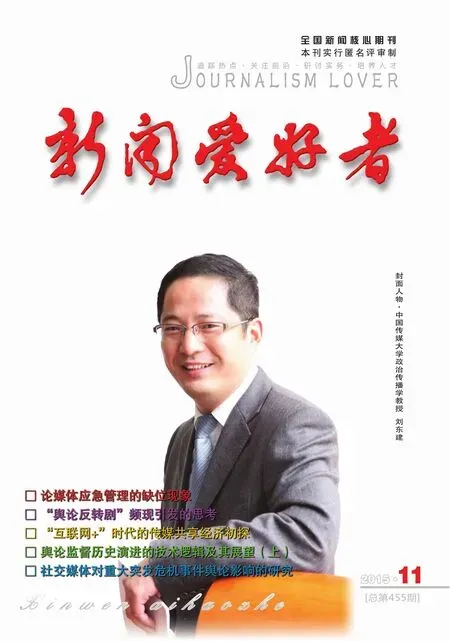社交媒体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影响的研究——从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看社交媒体的“渗透”
2015-03-02王灿发
□邢 祥 王灿发
(邢祥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博士生;王灿发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得到迅速发展, 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We Are Social2015 年8 月发布的《2015 年全球数字、社交和移动调查报告》最新数据,社交媒体用户已达6.59 亿,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中国社交媒体使用量已经处于高水平, 数据显示,99%的中国网民使用社交网络。[1]社交媒体的兴起、发展和壮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我国舆论格局的转变。 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由于公共性和危害性强的危机事件本身就备受关注, 再有大量网民参与使用的社交媒体渗透其中, 会使舆论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因此,探讨社交媒体与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交媒体与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的关联
(一)强弱关系纽带交互作用,多传播形式产生乘积效应
1974 年,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弱连接理论,将人际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强关系带来相互的信任,弱关系带来信息的传递。[2]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关系网络是基于强弱关系交互作用的。《2014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显示,33.7%的网民同时使用社交网站、 微博和即时通信工具这三类产品来满足他们各个层次的需求,用户的重合度高。[3]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不断提升,许多社交媒体用户通过一种社交媒体获知信息之后,可以借助第三方社会化分享组件推送到其他社交媒体中,这就实现了社交媒体作为私人空间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私人化的有效切换。
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并不局限于一种,而是融合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圈子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实现了传播的交互性。 多种传播方式交互作用,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呈现几何式爆炸增长,根据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信息一经传播就能快速到达每一位社交媒体用户。
当发生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 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和重要性, 相关信息在社交媒体中的传递和扩散会更加迅速,扩散效果会更强,这就使得舆论场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二)用户参与意识提升,社会心态多元多变
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广大用户提供了信息表达的畅通渠道,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得到提升,不再甘心做“沉默的螺旋”,而是常常作为舆论场的表达主体和信息发布者,积极参与网络互动,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和评价,表达态度和情绪。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困惑、矛盾和压力交织重叠,社会心理出现震荡和失调。同时全球格局复杂多变,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也愈加频繁,尤其是西方加紧了对我国的文化输出和思想渗透, 使得受众的信息获取量越来越大,思想活动也越来越独立。这些因素使有些人产生质疑、宣泄、焦虑、仇视等不良社会心态。 这些不良心态的持有者会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也容易“感染”其他网民。
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面前, 尤其是涉及公众生命财产的人为性灾难事故,事故爆发的原因、政务工作开展的偏颇、 媒体的报道内容方式等都会唤醒和激起不良社会心态。 持有这些不良心态的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时, 其发布的信息和表达的情绪都会将多元、多变的社会心态映射出来。
二、社交媒体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的影响
(一)“双微”平台反应迅速,成为舆论主阵地
近年来,每当发生突发事件后,微博、微信进行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优势尤为凸显, 遥遥领先于传统媒体。 此次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以下简称“天津‘8·12’爆炸事故”)最早也是由社交媒体爆出。 在大爆炸发生之后,就有网民将事故发生情况发布在微博上,有不少网民将天空出现蘑菇云、家里窗户被震碎、汽车被烧毁、受伤市民跑到街上等大量事故照片和微视频等现场第一手材料传至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中,瞬时引爆社交媒体。 在接下来的6~8 小时内,现场事故情况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
从事故爆发到13 日20 时, 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 共监测到相关舆情总数57,305,153 条,其中新闻689,476 条,微博56,587,458 条,论坛7,394条,博客1,876 条,微信18,949 条。[4]根据艾利艾智库数据统计,截至2015 年8 月19 日17 时,此次事故相关新闻报道及转载共计48.6 万篇, 微博主帖共计292 万条, 微话题#天津塘沽大爆炸#、#天津港爆炸事故#等总阅读量超过40 亿次,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近3 万篇。[5]从不同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来看,此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中,尤其是爆炸最初的24 小时内,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量远高于传统媒体进行新闻发布的总量。可以看出,此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中, 社交媒体形成的舆论场已经不再是传统媒体的辅助和补充,而是成为此次事故的舆论主阵地。
(二)共鸣溢散交互共振,合力引爆舆论场
媒介间存在“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两种互相影响议程设置的流向方式。 “共鸣效果”由1968 年诺埃尔·纽曼等人提出,指由主流媒体引起而在媒介系统中产生一连串报道的连锁反应。[6]在关注信息从主流媒体流向另类媒体或弱势媒体的同时, 学者马西斯等也提出:“媒介议题同样可以从另类媒体流向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媒介),即产生媒介议题的溢散效果。 ”[7]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共鸣效果”是主要议程流向方式;而在新媒体大力发展的今天,“共鸣效果”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与“溢散效果”共同作用。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以媒体为中心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与以用户为中心的社交媒体交互共振,共同推动舆情的生成和演变,合力引爆舆论场。
在天津“8·12”爆炸事故中,虽然信息发布的“第一人”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但是主流媒体也能做到较快较好的信息跟进,除利用官方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和移动客户端进行信息发布外, 多次以头版头条的形式予以突出报道, 其深度优势发挥得较为明显。 这些报道中, 关于事故救援类的文章占据首位,其次是领导工作批示类报道,再次是信息辟谣类报道,还有少量文章谈到救援的消防官兵等情况。 因此,在此次火灾爆炸事故中,社交媒体能与主流媒体形成共振,议题既能在主流媒体得到重视和报道,也能在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等所谓边缘媒体得到共鸣。
(三)正负效应并存,谣言频现引恐慌
刘建明认为:“舆论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 舆论对社会与人影响的客观效果,表现为舆论的社会功能。 舆论给人的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方向,使之呈现良性发展趋势,称作舆论的正功能。 舆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 属于负功能,这样的舆论称作负向舆论。 ”[8]社交媒体对重大突发事件舆论的影响,也存在正负效应。
天津“8·12”爆炸事故发生后,致敬消防官兵、寻人接力和号召爱心捐款等事件彰显正能量, 尤其是许多亲属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 有些张贴在街头的寻人启事也被媒体和网友拍照后转发到社交媒体上,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中发起了寻人接力。 在此次爆炸事故中, 社交媒体舆论场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务信息公开,社交媒体上关于事故责任人、事故原因等方面的问责和发问, 尤其是在几次新闻发布会之后产生的次生舆情,都是网民对事件调查、政务工作的质疑,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务信息公开,提升了事故信息发布的透明度。
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必然会伴随谣言的传播。 作为网民自发生产、传播信息的载体,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这也导致社交媒体中谣言传播的管控变得异常困难。 随着爆炸事故伤亡人数的攀升和信息公开工作的备受质疑,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谣言和舆论质疑,如“方圆一公里无活口”“天津市更换市委书记”等。 通过梳理,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谣言主要有伤亡人数类、爆炸原因类、政治类、环境类、求助救援类、媒体环境类和社会秩序类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还可能引起社会恐慌。虽然针对很多谣言,政府和媒体都专门进行了辟谣,国家网信办对90 多个微博账号、70 多个微信公众号予以永久关闭, 还对200 多个账号采取临时关闭措施,但是其负面效应已经造成,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三、社交媒体中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的应对
(一)政府积极应对,避免“塔西佗陷阱”
移动互联网时代, 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一旦政府在处理政务问题时出现偏差,就会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 偏差也会因为大范围传播而被无限放大,引爆舆论场。 因此,政府在面对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的考问和考验等问题时, 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必须将社交媒体考虑在其中,避免扩大“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9]
此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中,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受到了质疑,尤其是在几次新闻发布会之后,都会生成次生舆情,被评价为此次爆炸事故的“次生灾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妨碍了后续工作的开展。 政府公信力是长久积累形成的,每一次的政务公开、每一次的危机应对,都会影响以后的舆论场,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进一步改革信息发布制度,切实改变“堵”和“删”的治理措施,加强网络的疏导及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对受众提出的疑问及时解答,以提高公共领域信息的透明度。利用好社交媒体,充分发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的功能,提高自身的认可度,为受众塑造一个思辨、理性、人文的信息交流空间;同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媒体正确发声,避免议题断裂
在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舆论时, 媒体应当及时准确发声,履行好信息发布、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共鸣效果”,同时重视社交媒体的“溢散效果”,实现议题共振,避免议题断裂。 所谓断裂,指的是议题在社交媒体受热议而在传统媒体未得到重视, 或者传统媒体进行大量报道而在社交媒体上未受关注。
此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中,主流媒体除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事故报道外,还能够较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主动发声,官方微博发布消息保障时效性,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时评保障报道质量和深度。 但是作为事故发生地的天津媒体的“慢作为”备受质疑,被网民称为“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尽管后来有 《天津媒体又被骂死了,有些地方真的骂错了》之类的文章进行辟谣,但已于事无补。 在此次事故中,有些媒体公众账号甚至成为谣言的发布者和传播者。 所以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传统媒体除了主动发声,更要正确发声,制定并遵守媒体机构的社交媒体使用规范, 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
(三)网民理性看待,提升怀疑性认知能力
李普曼认为,每个公众个体都会受到认知因素、智力水平的局限, 再加上刻板印象造成难以抵消的影响,即使没有媒体的引导和设置,本身也容易形成非理性的观点。[10]尽管这种观点较为悲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每个人辨别信息真伪时都存在局限性。 加之自媒体时代,碎片化的传播使谣言等信息更具迷惑性,人们无从查证信息真伪,加之社交媒体的圈子文化、 广泛的用户基数都制约了公众对谣言的辨别力和批判力。
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 网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训练,采用怀疑性认知方法进行信息辨别,具备怀疑性认知能力。 这种技能能帮助人们避免掉进错觉和安全陷阱,教会人们应该关注什么,从而迅速预见未来,不会因为各种变化而手足无措。[11]这一认知过程包括以下问题:“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3.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提供了什么证据? 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12]在面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网民可以采用怀疑性认知方法,理性看待相关信息,用其分析及辨别信息真伪,并要努力做到“慎独”“自律”,保持个人思想独立性,不要被别人的言论“绑架”,不主动制造不良言论,不主动传播谣言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有害信息。
[1]2015 年全球数字、 社交和移动调查报告[EB/OL]http://www.cbdio.com/html/2015-01/30/content_2376235.htm
[2]预知社会——微媒体、微传播、微动力[EB/OL]http://www.gmw.cn/media/2013-01/07/content_6286580.htm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 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R].2014,7:9.
[4]天津爆炸事故过去24 小时舆情全记录[EB/OL]http://yuqing.cyol.com/content/2015-08/14/content_11547497.htm
[5]http://www.cpd.com.cn/n15737398/n26490099/c30083322/content.html
[6]董天策,陈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134-138.
[7]董天策,陈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7):134-138.
[8]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78.
[9]李季芳.网络时代,如何破解“塔西佗陷阱”舆论怪圈[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3(7):77-79.
[10]Michael Curtis.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action Edition[M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xvi-xix.
[11]科瓦奇·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2.
[12]科瓦奇·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