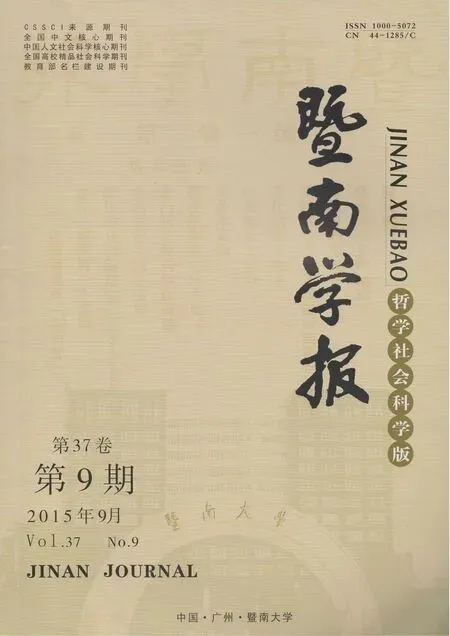论洛夫《漂木》的意象创造及经典意义
2015-03-02熊国华
熊国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论洛夫《漂木》的意象创造及经典意义
熊国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洛夫的长诗《漂木》是诗人70多年生命体验和思想探索的艺术结晶,也是集洛夫一生诗歌创作经验和心血的巅峰之作。《漂木》的经典意义在于:在长诗中成功运用了意象思维;创造了象征性的典型意象;在诗艺和思想上熔铸古今中外。《漂木》是一座蕴藏丰富的诗学宝库,其价值还有待人们深入开发和研究。[关键词]
洛夫;漂木;意象;创造;经典“诗魔”洛夫以72岁高龄,在公元2000年创作了一部3000多行的长诗《漂木》。2001年元旦,台湾《自由时报》副刊开始像连载长篇小说一样连载这部长诗。同年8月,《漂木》由联合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洛夫继《石室之死亡》之后的第二部震撼诗坛的长诗,从其写作和出版的时间来看,可以说是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诗,同时也是新世纪的第一部长诗。《漂木》问世之后,好评如潮。台湾著名诗评家简政珍认为:“没有这一首长诗,他已攀上中国二十世纪诗坛的高峰。有了这一首三千行的长诗,他已在‘空’境的苍穹眺望永恒的向度。”大陆著名诗评家龙彼德指出:“长诗《漂木》,是洛夫一生的总结,是他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精品。”时过13载,笔者重读《漂木》仍然激动不已,深感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穿透时空的艺术魅力。本文仅就《漂木》意象的运用和创造作一粗浅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意象在长诗结构中的作用
长诗的写作不同于短诗,首先要考虑的是结构,如同建造一座宏伟的殿堂,首先必须有坚实独特的结构去支撑。洛夫自言“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长诗,史诗,但是属于精神层次的,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思考做一次总结性的形而上建构,而不是西洋那种叙述英雄事迹的epic”。纵观洛夫的人生经历,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到加拿大,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金门炮战和越南战争,目睹战乱、死亡、饥荒、瘟疫,颠沛流离,漂洋过海,远离故土的漂泊命运伴随了诗人的一生。这部长诗可以说是洛夫70多年生命体验和思想探索的艺术结晶,也是集洛夫一生诗歌创作经验和心血的巅峰之作。
洛夫如何设计他最重要的长诗的结构呢?全诗分为四章:《漂木》、《鲑,垂死的逼视》、《浮瓶中的书札》、《向废墟致敬》,其关键词分别为“漂木”、“鲑鱼”、“浮瓶”和“废墟”。不难发现,《漂木》的结构竟是由4个原创性的意象支撑的,换句话来说,洛夫竟然选择了用4个意象来解构他的长诗。第一章“漂木”与长诗同名,是这部诗集的核心意象,隐喻诗人漂泊流放的命运。第二章通过加拿大的“鲑鱼”洄游到内陆淡水河流产卵、然后死亡的生命历程,展示动物的回归和对死亡的逼视。第三章的“浮瓶”,即漂流瓶,通过瓶中的书信表达了对母亲、对诗人、对时间、对诸神的怀念和思考,仍与漂泊的主题有关。第四章的“废墟”由一个大家族祖屋的荒废,进入到现代人精神漂泊荒诞虚无导致整体文化的“废墟”,蕴含着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思考和终极关怀。这四部分,分而独立成章,合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意象”来解构长诗,既避免了故事性的冗长叙事,也没有抽象议论的空泛虚浮,又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示了诗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思考,极有创意。
另外,每一章的标题,章前的引文(分别引自屈原《哀郢》、洛夫《石室之死亡》、洛夫《血的再版——悼亡母》、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名言,以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与正文形成提纲挈领、相得益彰的互文关系,产生一种诗意弥漫的张力,增强了诗歌文本的艺术感染力。第二章附录的《伟大的流浪者——鲑鱼小史》,亦可作如是观,足见诗人构思的精巧高妙。
二、意象在叙述方式上的运用
诗歌文体长于抒情,短于叙事,但仍然存在一个“说话者”。即便是抒情诗,也是一种不以讲故事为主的“叙述”,仍然有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的问题,只不过因为诗歌一般篇幅短小直抒胸臆,常常被诗人和研究者所忽略,而一旦涉足长诗,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漂木》作为一部3000多行的长诗,承载着抒发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形而上思考的重任,不可能采用小说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讲故事,如果采用作者第一人称抒情议论,又势必显得直白抽象、诗质淡薄。于是诗人经过反复思考,不论在叙述视角,还是在抒情策略方面都选择了“意象”。长诗的第一章《漂木》,其叙述内容是一块漂浮在水上的“木头”。作者通过漂木在大海、加拿大、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之间的漂泊经历,甚至透过漂木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世界的荒诞、混乱和堕落现象,呈现其迷惘、悲凉、痛苦、无奈,在多次失望中仍坚守信念、寻找家园的悲剧命运。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则用第一人称“我们”,以“鲑鱼”的身份来叙述抒情,同样是一个意象。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浮在海上的漂流瓶中的书信,一般为个人的秘密、心里话、愿望,等等。作者以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对话的形式,分别展开了对母亲、对诗人、对时间、对诸神的叙述和思考,其载体仍然是一个意象“浮瓶”。第四章《向废墟致敬》,以作者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叙述的主要内容还是一个巨大的意象。综上所述,长诗在叙述方式上,或者以“漂木”、“废墟”作为叙述的内容和对象,或者以“浮瓶”作为叙述的载体,或者直接以“鲑鱼”作为叙述视角,意象在长诗的叙述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洛夫擅长在长诗中合理变换叙述视角,还根据内容和抒情的需要不时运用视角越界。如:第一章以中性的全知视角叙述,然而“一块木头/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才发现一只空瓶子在一艘远洋渔/船后面张着嘴”,通过木头的视角“发现”空瓶子,已经从“外视角”转移越界到“内视角”了。“木头的梦不断上升/它终于在云端看到/那悲情的/桀骜不驯的岛”,仍是运用视角越位,通过“漂木”的视角看台湾:“凤梨。带刺的亚热带风情/甘蔗。恒春的月琴/香蕉。一篓子的委屈/地瓜。静寂中成熟的深层结构/时间。全城的钟声日渐老去/台风。顽固的癣疮/选举。墙上沾满了带菌的口水/国会的拳头。乌鸦从瞌睡中惊起/两国论。淡水的落日”,一系列蒙太奇的自由组接,句号从中间隔断的互文句式,增强了诗句的内在张力和隐喻效果。加上大量的独白、追忆、梦幻、跳跃、自由联想、时空穿越、立体的多视角叙述,创造了一种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审美情境。个人经验与历史事件、现实场景融为一体,这种蕴含了个人深层意识和复杂内心感受的叙述方式,恰好成为诗人大半个世纪的战争、灾难、流放经历中的生命体验与存在拷问的最佳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叙述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单一的外部的、以再现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命运的叙述方式,而转向现代或后现代的多元的隐匿的、以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和生命体验的叙述方式。洛夫在长诗《漂木》中所运用的现代叙述方式和技巧,并不亚于优秀的现代主义小说。
《漂木》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如何吸引读者阅读并产生审美快感呢?洛夫还是选择了意象,运用核心意象主导的意象群,以意象的演绎和隐喻推进叙述的持续发展。第一章和第二章自不必说,试以第三章的《瓶中书札之一:致母亲》为例略加分析。洛夫的《致母亲》没有像一般悼亡诗那样宣泄情感和伤痛,反而显得比较平静,请看开头:“守着窗台上一株孤挺花,我守着你/一个空空的房间/空得/像你昨天的笑/窗外是一个更空的房间/昨天你的笑/是一树虚构的桃花”。洛夫是在1949年21岁时离别母亲开始放逐生涯,直到1988年才回到故乡,但见到的却是母亲的坟墓。再到2000年洛夫写《漂木》,“空空的房间”也许是追忆首次回乡时的实景,也许是梦幻中想象的情景,也许来源于佛教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心经》)。其丧母的虚空、孤独、思念和内在伤痛,通过空房间、孤挺花等意象透露出来。《致母亲》的核心意象是“空房间”,并衍生出桃花、碎玻璃、壁钟、时间、灰烬等意象。“隔着玻璃触及你,只感到/洪荒的冷/野蛮的冷/冷冷的时间/已把你我压缩成一束白发”。接着,诗人沿着“白发”的意象继续演绎,“我,天涯的一束白发/雪水洗白的,这之前/秋风洗白的/在秋风中流窜的/曳光弹洗白的/战争,那年在梦的回廊拐弯处遇到/我便跟它走了/跟它步入雨淋,踏上险滩/在散落的一页历史中登陆”,意象一环扣一环,推进到台湾,形成母子“一水之隔”的思念与永诀。诗人在极度思念中仿佛听到母亲的“唇语”:“在那病了的年代/贫血,便秘,肾亏,在那/以呼万岁换取粮食的革命岁月中/我唯一遗留下来的是/一条缀了一百多个补丁/其中喂养了八百只虱子的棉袄/和一个伟大而带血腥味的信仰”。意象的纵深延伸与拓展,增加了诗歌的历史厚度和社会内容,使诗人个人家庭的遭遇与国家命运民族灾难交织在一起,发生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的母爱也就有了独特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诚如洛夫所言:“我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与母亲有关联的意象,还有脐带、坟头、墓碑、蚂蚁、狗尾草、蜉蝣、夕阳等,组成一个隐喻着感伤悲愤色彩的意象群,其中“空房间”的意象反复出现,贯穿始终,并寓有深厚的象征意蕴。
三、典型意象的创造
一个成熟的或者伟大的诗人,一般都会创造出最能表现自己的个性特征、时代语境和美学理想的典型意象。庞德甚至认为:“一生中创造出一个‘形象’,胜于创作出无数部作品。”诸如:屈原的香草、陶渊明的菊花、李白的明月、杜甫的悲秋、李商隐的春蚕、苏轼的赤壁,以及艾略特的荒原、叶芝的天鹅、聂鲁达的大地、布罗茨基的黑马、埃利蒂斯的太阳,等等。洛夫在语言策略上极其重视意象的鲜活与精炼,在以往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创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诗歌意象,当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为《石室之死亡》中的“石室”。而长诗《漂木》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漂木”、“废墟”和“鲑鱼”都是意蕴深厚、新颖独特的典型意象。本文仅对“漂木”意象进行解读,其余留待另文探讨。
“漂木”是书名,也是长诗第一章的题目。从语义学来看,漂木指“飘在水上的木头”;从修辞学来看,隐喻着漂泊、漂流、流浪之意;从诗学来看,可视为一种放逐、流放命运的象征。如果说,洛夫1949年跟随几百万人从大陆去台湾是第一次放逐的话,那么1996年从台湾移民加拿大则是第二次放逐。虽然这两次放逐有被迫放逐与自我放逐的不同,但远离故土、漂泊海外的命运却是一样的。因此,“漂木”隐喻着诗人个人的身世与命运,从而具有某种普遍的放逐、流放的象征意义。诗前引用屈原《哀郢》的诗句“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以日远”,可作为长诗最好的注脚。
“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这是长诗的第一句,当诗人面对着自己一生漂泊命运的时候,当他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一块漂木的时候,他能不严肃吗?这种严肃也是出于对诗歌和生命的敬畏。“落日/在海滩上/未留一句遗言/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双双偕亡”,一幅多么凄清感伤、带有死寂色彩的画面,“一块木头/被潮水冲到岸边”,就此出场。伴随木头的,是天涯、海滩、落日、向日葵、远洋渔船。一只空瓶子与烟、天空、木头一起“浮沉沉浮”。漂泊天涯的木头“不见得一直是绝望的木头/它坚持,它梦想/早日抵达另一个梦……/它的信念可能来自/十颗执拗的钉子”。木头而有梦,具有人的灵性、思维和信念。木头的梦是什么呢?诗人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从“被选择的天涯/却让那高洁的月亮和语词/仍悬在/故乡失血的天空”和“究竟什么是那最初的图腾?/那非预知的/亦非后设的/正在全力搜索的/心中的原乡”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为了寻梦,木头“开始起锚,逐浪而行……/这漂泊的魂魄/随着浪花的跃起,观望/日出”。尽管“漂泊是风,是云/是清苦的霜与雪/是惨淡的白与荒凉的黑”,仍不能阻挡木头对梦的追寻。
诗人的诗思随着“漂木”在海上漂流,通过“漂木”的视角展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面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道德、风土民情、生活方式等,诗人用蒙太奇式的意象排列组合呈现出来,其中不乏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而年轮/却是一部纹路错乱伤痕累累/不时在虫蛀火燎中/呼痛的断代史/宝岛林木葱郁/内部藏着日趋膨胀的情欲,和/大量贪婪的沉淀物/红尘,由烟雾编织的神话/流传于国会与棒球之间……/一大早捷运系统/就会有系统地把抗议群众和市长候选人/一一送进了历史的某章某节/电视里议员们以拳头发言/电视外议员们与黑道角头杯酒交欢”。而大陆呢,经过一系列天灾人祸之后,“十年冰雪/一旦解冻小河便一丝不挂/闪着细腰/落花流水送来一群母鱼……/宾馆。五星级的情欲在房门后窥伺/茅台。黄河之水天上来……/龙井掺一滴五粮液。不太成熟的民主程序/普希金的抒情诗。蟋蟀在寂寞中哀鸣/乡镇企业。一个飞上太空却以为到了天国的僧侣”。当然,这也许是期望太高,恨铁不成钢式的反讽与责问。海峡两岸,似乎都与诗人心中理想的“原乡”有一定差距,“大地为何一再怀孕却多为怪胎”。那么,诗人的“原乡”究竟是什么呢?“或许,这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漂泊/一根先验的木头/由此岸浮到彼岸/持续不断地搜寻那/铜质的/神性的声音/持续以雪水浇头/以极度清醒的/超训诂学的方式/寻找一种只有自己可以听懂的语言/埋在心的最深层的/原乡”。由此可见,诗人上下求索的原乡不一定是现实中存在的原乡,“形而上的漂泊”追寻的更多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原乡,即“精神家园”。洛夫一生遭遇两次放逐,这种放逐不仅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放逐。背井离乡,漂泊异国,时间越久思之越勤,空间越远念之越深,且已至落叶归根的老年,对故国乡土、民族文化的回归亦属必然。既然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还不能回归,那么只能在精神上回归,以写作的姿态对抗命运的安排,“漂木”乃是诗人一生漂泊命运的写照和象征。
四、《漂木》的经典意义
文学经典与其他学科的经典一样,需要经过时间和读者的双重检验,才有可能成为或者被确认为经典。洛夫的长诗《漂木》能不能成为经典,尚需后世验证。但是,经典本身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系统,有些历史上曾被认为是经典的作品,到了今天或将来可能被淘汰,而我们今人创作的优秀作品,也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学经典。从这种观点来看,《漂木》或许是一部潜在的有可能成为中国汉语新诗经典的长诗。
不同的文体,因其文体特征不同而有各自的经典。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诗歌的语言与小说、散文、戏剧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诗歌是一种最具有原创性的高级语言艺术。它用充满张力的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重新整合,以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从而获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自由”。也就是说,诗歌主要是一种“意象”语言,诗人将主观的意识、情感、观念投射到客观的物象上去,或者说,客观外界的物象被摄入诗人的心象之中,两者完全契合,主客交融,意象同一,并转化成语言文字写进诗中,意象由是完成。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单位,诗人藉意象与世界对话,向读者展示诗人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发现,引导着读者的思维指向。一首诗就是一个意象的世界,诗歌的思维,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意象思维。
洛夫,对意象炉火纯青的运用和苦心孤诣的创造,在长诗《漂木》中有着令人惊叹的表现:
首先,成功运用了意象思维。从而避免了一般长诗、史诗的通病——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抽象乏味的议论、直白泛滥的抒情,等等。《漂木》在构思上采用了漂木、鲑鱼、浮瓶、废墟等四大意象,支撑了长诗的宏大结构;在叙述方式上采用多元立体的叙述视角,甚至通过鲑鱼、漂木的“眼睛”去观照事物,进行思维,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通过核心意象主导的意象群,用意象的隐喻和演绎拓展来推进叙述的持续发展。这种以意象为主导的诗性思维,改变了传统长诗、史诗比较单一的外部的、以讲述故事歌唱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从而转向现代的多元的隐匿的、以表现人与生物的生存状态、内心世界和生命体验的叙述方式,在长诗叙述方式上作出了成功的探索。
其次,创造了象征性的典型意象。“漂木”是一个物性、人性与神性三位一体的意象。它是木头,前生为树、有根,曾青枝绿叶;今生失根、无叶,失去身份归属,能在水上漂浮,这是物性。它能发现(有眼睛)、能说话、能做梦,有心跳、有呼吸、有痛苦、有故乡,有爱恨情仇,这是人性。它又是一个“漂泊的魂魄”、“先验的木头”,能够到处漂泊、审视事物、洞察人性,搜寻“神性的声音”,这是神性。这种三位一体的意象,在诗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意象。艾克诺认为:“二十世纪的知识追寻是一种放逐。”即是一种精神的放逐,诗人、作家和思想者,为了保护心灵的一方净土,或对某种乌托邦的寻求,自己选择放逐的命运,而不纯粹是由于外力的不可抗拒的逼迫。但无论是他人放逐还是自我放逐,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远离了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园,从而产生语言、文化、种族、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从个人来看,“漂木”可说是诗人洛夫一生漂泊命运的隐喻和象征;从整体来看,人类或许是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放逐到地球上,至今仍在浩瀚无比的宇宙中漂泊的生物,那么,“漂木”也是整个人类漂泊命运的象征。
第三,在诗艺和思想上熔铸古今中外。长诗不像短诗那样可以骤然爆发的灵感取胜,而需要深厚的思想底蕴、宏观的宇宙视野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洛夫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曾熟读研习佛教、道家、儒家的著作,同时又受到西方尼采哲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等的影响,诗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去广采博收,融会贯通,并作为形而上的思考在长诗中艺术地呈现出来。从诗学师承关系来看,洛夫既有中国古典诗学的底蕴,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养分。他的诗中,有屈原对现实的忧愤、理想的追求和内心的孤独;有陶渊明的隐居情怀、田园意识;有王维山水诗的空明、澄净和禅趣;有李白的天然飘逸、浪漫雄奇;有杜甫的沉郁悲悯、忧国忧民;有李贺的冷峭怪僻、梦幻色彩;有李商隐的深情绵邈、朦胧感伤;有苏轼的旷达渊博、理趣超迈。同时,还能隐约看到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瓦雷里、里尔克、卡夫卡的影响。举凡老子、庄子、孔子、佛祖、基督、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康德、罗丹、柴可夫斯基、巴哈,及以上所引的哲人、诗人,或以人物形象出现在诗中,或化用和引用他们的名言诗句,还经意不经意地活用《圣经》《金刚经》和中外名著中的典故。值得指出的是,洛夫继承中外诗学,不是标签式的引用罗列,而是一种熔铸式的脱胎换骨的创新,在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土壤上生成一种现代的解构,创造出新的意象和意境。下面试举几例。
例一:
昨日的豪情
犹如黄河之水
奔流尚未到海便只剩下涓滴
君不见
早晨镜中的青丝
一到晚上便成了一把失血的韭菜
例二:
向被情欲伤害的天使致敬
明镜亦非台
红尘的趣味何其多元
上网和上床同样叫人发疯
例三:
我很满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现状
即使沦为废墟
也不能颠覆我那温驯的梦
例一化用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在“黄河之水”前面冠以“昨日的豪情”,还没有奔流到海就只剩下“涓滴”,暗指豪情逐渐消失。李白“朝如青丝暮成雪”隐喻时光易逝、人生短暂,到洛夫这里变成了“失血的韭菜”,除包含原句的意思外还增添了新的含义:“失血”意味着韭菜枯萎灰白;收割“韭菜”时用刀割下茎叶,根部留在土中,等下次长出来后再割,隐喻人的不断被割的命运,从而在古典的土壤之上创造出新的现代意象。另外,韭菜的收割方式,同头发的不断被剪极其相似,读来忍俊不住。
例二中“天使”都被情欲伤害,意味着世道衰落、情欲泛滥。接下来插入一句“明镜亦非台”,原为六祖慧能所作的偈中的诗句,印证佛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即世界上一切有形体的事物或现象都是虚幻不真实的,万事皆空,诸法空相,明镜当然也是如此,用在这里极具反讽意味。后两句承接第一句的意思,红尘中的凡夫俗子追求享乐,与佛教修行者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是对“明镜亦非台”的解构,实为对消费时代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讽刺批判。
例三是长诗第四章《向废墟致敬》的结尾,与开头“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果然是那预期的样子/片瓦无存”相呼应。“滴水不剩”、“片瓦无存”意为虚空,是佛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诗意呈现。洛夫在苦难经历中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宿命的无奈”,对生命、死亡、存在的意义有所顿悟,意识到“空虚有时也是一种充盈”,甚至要“向废墟致敬”,以一种淡泊祥和、悲悯宽恕的心态观照生命苦难和悲惨世界,即使“沦为废墟”仍然葆有“温驯的梦”,进入一种心无滞碍的澄明境界。
《漂木》在诗歌表现手法和技巧上堪称集大成之作,举凡暗示、隐喻、象征、通感、双关、谐音、用典、变形、跳跃、拼贴、反讽、矛盾修辞、自由联想、意象叠加、词性活用、无理而妙、反常合道、虚实交替、蒙太奇组接、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等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技巧,均信手拈来,运用得炉火纯青,臻于化境。
《漂木》是一座蕴藏丰富的诗学宝库,其珍贵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还有待人们深入开发和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批准号:11&ZD111)。[作者简介]
熊国华(1955—),男,湖北黄陂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收稿日期]
2014-12-10[中图分类号]
I1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15)09-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