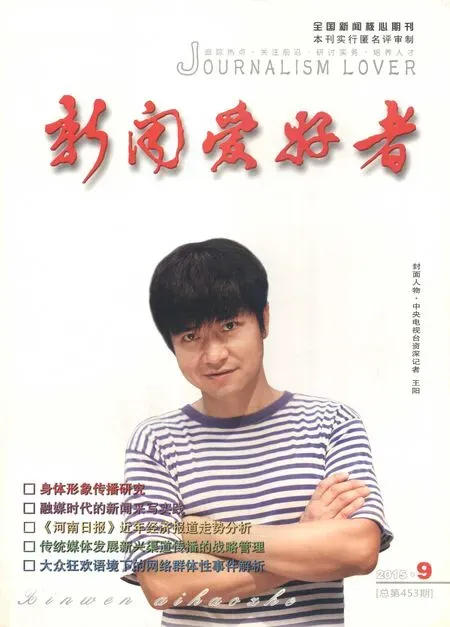论媒介记忆活跃与凝固的尺度和张力
2015-03-01邵鹏
□邵鹏
论媒介记忆活跃与凝固的尺度和张力
□邵鹏
媒介是一个不停述说的体系,是记忆在这一体系中从活跃到凝固、再从凝固到活跃的反复不断地激活和唤醒的过程。媒介记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核心与载体,既需要存储久远,也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传播、聚合和分享。传播要素的聚合与发力,无疑会使整个传播过程充满活力与能量,使记忆更加饱满。时间是记忆的磨刀石,会消磨记忆,带来遗忘,而阻滞遗忘、强化记忆的利器是适度的重复和再现,让媒介记忆的活跃与凝固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尺度和张力。如何科学合理地重复和再现记忆,从中找到最佳的路径,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也是需要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媒介记忆;文化记忆;遗忘;重复与再现
媒介是一个不停述说的体系。报纸每天固定出版,广播电视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网络媒体一刻不停地随时更新。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记忆工具,信息在媒介的空间中是嘈杂和流动的,就如同一个不停播放的大喇叭,它的声音无休无止,从不停歇,却无法真正使记忆得到静止与凝固,这有违我们对于记忆特别是历史记忆的传统想象。在传统想象中,铭文、竹简、图书、报纸、杂志等媒介的记忆是固化的、物化的,甚至是凝固不动和一成不变的。韩愈说:“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答张籍书》)魏裔介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琼瑶佩语》)他们都认为,口头传播过耳不留,而书写传播则流传久远。声音如风过枫林,听到它却抓不住它,而图书馆里的报刊书籍却可供人们随时查阅,博物馆中的历代书画也可让我们尽情观赏,使得凝固的记忆在新的语境中再次活跃起来。
即便人类大脑的记忆如同“一张可以随时擦拭的白纸,没有记忆负担,写了即抹,抹了又写,每次都是最新最刺激的信息,缺少有保留价值的东西”[1],但是,当一段留存的记忆在大脑中重新活跃的时候,激活的既是回忆也是叙述的改造和重构,因为“只有叙述无休无止,回忆才将保持活跃”[2]。如果一段回忆长期得不到个体或媒介叙述的激活,始终处于尘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这段记忆正在逐渐走向遗忘与消逝,回忆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吃力,最终无法再被人们提及。因此,记忆在媒介空间中的积淀和延续,是一段记忆在这个“喋喋不休”的媒介讲述体系中从活跃到凝固、再从凝固到活跃的反复不断地激活和唤醒的过程。
那么,什么样的记忆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激活和唤醒?什么样的记忆能够在媒介空间中被延续和传承?又有哪些记忆会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消逝在媒体和社会的喧嚣声中或另一段记忆之后?
一、“万众瞩目”:媒介聚合下的记忆
回溯人类的记忆史,在缺乏文字符号的口述记忆中,记忆仅是存留于器官中的鲜活回忆,是经验或道听途说。在口述记忆的空间中,社会群体成员间的相互讲述、讨论和节日、庆典、仪式所创造出的交流空间等形成了鲜活的记忆,并最终形成了社会成员间的共享记忆。这种口述记忆“随着时间产生,又随着时间消逝,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它的载体产生和消逝。当将记忆具体化的载体死亡之后,它将要让位于新的记忆”[3]。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心记脑存”的肉身记忆,显然“既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亦不能保证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4]。因此,没有文字符号的口述记忆必然是短暂的、凌乱的和琐碎的,并且充满了各种个体经验框架下的信息加工与删节。
文字符号所固化的媒介记忆,不仅可以让人们“反复阅读、慢慢译解那些超越时空来自远方的信息或早已逝去的人留下的信息,并用它来保存和继承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不必费尽脑汁去铭记”[5]。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记忆拥有相对连续、具体、固定的符号形式,具有普遍性的书写、编译、演示和识读系统,使文字记忆能从原本的散乱易失变得越来越精致、系统和逻辑严密。只要这些文字符号所组成的记忆单位成为媒介,或保存起来,放在存贮库和数据库之中,就可以被随时随地检索、提取和调阅,那些曾经的过往、琐碎的细节甚至无足轻重的轶事趣闻都可以在适当时机再次成为人类记忆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
文字符号给予记忆的是时间上的久远和空间上的广阔,人们无须再为记忆耗费更多精力。它改变了人类记忆的肉体形式与思维的基本面向,使得记忆能够从时空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字符号所固化的记忆就是不朽,尤其是当人类进入到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大众传播时代,即便是那些精心撰写、妥善保管的信息也会为信息的汪洋大海所吞没或为人们所忽视和遗忘。
媒介记忆是人类一切记忆的核心与载体,既需要存储久远,也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传播、聚合和分享。媒介对于记忆的影响不同于文字符号,尤其是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技术成了记忆传承与延续的决定性因素。聚合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记忆机制。媒介对记忆的聚合,其实就是对传播过程的梳理和整合,有助于形成具有统一媒介话语风格的记忆体系,而传播要素的聚合与发力,无疑会使整个传播过程充满活力与能量,使记忆更加饱满。
(一)媒介对记忆的聚合是对受众的聚合
没有媒介,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和全人类的记忆共享,媒介使得记忆突破了个人和群体的界限,使记忆的延续与传承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中被实现。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名言,也是全人类记忆中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在阿姆斯特朗登月的那个瞬间,电视画面通过卫星传送到了49个国家,7.2亿电视观众共同见证了这一刻,这是在1969年。媒介技术最大程度地使受众可以分享和感受一段原本不属于自己或者说曾经完全不可能拥有的记忆体验。这便是媒介所营造出的记忆,它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声画一体犹如身临其境般的现场体验。尤其是电视媒介在对于那些震撼性体验的呈现上,声音画面将全球观众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万众瞩目”的记忆。正如学者丹·吉摩尔在《草根媒介》一书中所阐述的:“我们对那天可怕的记忆多半来自电视:飞机猛然撞上世贸中心,爆出火球,人从高空掉落,从塔上跳下来,整个建筑结构倒塌。”[6]那些现场的人用摄像机将他们所亲历的恐怖场景拍摄下来,电视、网络、广播,所有的媒介都开始行动起来,将全世界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塑造着每一个媒介参与者的记忆,于是媒介令全球的受众在这一天拥有了相同的记忆,“9·11事件”和“反恐”成为媒介聚合下的全球话语。
媒介对于人的聚合其实也是一种记忆的塑造。没有大众媒介,人类不可能产生如此高度一致的社会记忆和态度行为。媒介决定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甚至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我们往往全然不知。记忆的传承与延续,形成了在媒介权力与话语之下的记忆体系,而个体的体验与思考在记忆的空间越发式微,逐渐为体系性的媒介记忆所取代。
(二)媒介对记忆的聚合是媒介本身的聚合
在缤纷的媒介世界中,媒介不仅将每一个受众个体卷入到媒介的话语之中,也将不同的媒介卷入到相同的话语系统当中。
在传播技术与媒介市场化的推动下,社会环境中的媒介丰富而多样,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空间中充斥着数不胜数的媒介企业,而在这样看似繁荣而炫目的媒介空间中,记忆的内容却并不是无边界的,甚至当某些极为强势的记忆出现时,所有媒介聚合在一起形成了道格拉斯·凯尔纳笔下的“媒介奇观”,它就如同中心舞台上镭射灯光聚焦下的女模特,在那一刻周围一片漆黑,仅此一处光亮供所有受众和媒体追逐。在凯尔纳看来,“流行文化的文本吸引了大多数受众的注意力,凝聚了他们的想象力,成为记录当代社会品位、希望、恐惧和幻想的晴雨表”[7]。这显然是无处不在的商业力量不遗余力吸引人们眼球的结果。同样,超级杯、奥运会、奥斯卡都可以被称为一场场万众瞩目的媒体奇观。
媒体奇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媒介的聚合,那些镭射灯下的事件被所有媒体关注,长时间连篇累牍的报道,喋喋不休的各种观点、评论,甚至此后漫长时间中这些记忆依然被不断反复激活。在凯尔纳看来,这一切的背后是商业利益、文化霸权、政治操弄,甚至是恐怖分子“在全球媒体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用恐怖奇观的壮观场面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将恐怖分子的政治意图戏剧化,同时达到具体的政治目的”[8]。
在这样的媒介奇观中,那些与奇观相伴的镭射灯下的记忆得到了传承,而那些灯光之外的记忆却因此变得出奇安静。
(三)媒介对记忆的聚合是记忆信息的聚合
记忆本身是流动的过程,即便记忆的开始仅仅是闪光灯下的一个瞬间,但当这个瞬间不断在我们的脑海中被回忆、被讲述的时候,回忆者与叙述者便开始重塑这个瞬间,通过不断地加工以便于我们将这一记忆储存起来。“记忆会逐渐沿用叙事的结构,包括在哪里发生的,谁告诉我的,都有谁在场,我是如何反应的,而这些都是一个被人讲烂了的故事的要素”[9]。
媒介在社会中恰恰担负着这样一个回忆者与叙述者的角色,媒介通过“滔滔不绝”无休无止的叙述将原本闪光灯式的记忆瞬间通过局部的重建和阐释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记忆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众多媒介与受众都卷入其中,就如同所有的叙述者一样,为了记住那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和事件,他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对记忆的瞬间展开回顾和讨论,而这个回顾和讨论的过程就是媒介对于记忆信息聚合的过程。
在记忆信息聚合的过程中,不同媒介对同一个事件展开言说,恰如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一个媒介,当进行言说的主体在表述一个内容时,同时也平行地做出了一个对自身的表述,而在言说中的主体一般很少能对这个媒介的表述进行反思,并且从来也不能有意识地对这种表述进行控制”[10]。而“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个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11]。瞬间的记忆在媒介的空间中被反复地回顾和讨论,零散的信息在反复言说中被拼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的完整故事。而每一次记忆在媒介空间中被再一次言说时,它既是媒介对记忆信息的重新唤醒,也是媒介对过往记忆信息的重新叠加,我们永远不可能恢复到记忆最初的状态,但在记忆信息的不断聚合中,媒介使记忆避免了被遗忘的厄运,变得比其他记忆更加经久不衰。
二、“喋喋不休”:媒介重复下的记忆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敌人。在时间面前一切记忆都终将被遗忘,即便被固化为文字抑或任何“高保真”的数字记忆,也无法阻止记忆的最终流失。记忆的延续与否并不在于记忆以何种方式存储,文字尽管可以固化记忆,但无人阅读的文字同样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遗忘,图像、影像也是如此。物质固化的记忆并非绝对的永恒。时间是记忆的磨刀石,它会消磨记忆,带来遗忘。
遗忘是人类记忆的天敌。“我们识记过的所有内容,如果顺其自然,随着时间的消逝都会被逐渐遗忘”[12]。在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的研究当中,记忆被搁置时间越久,遗忘就越多,而形成记忆并与遗忘进行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他以音节组作为人们学习记忆的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发现,“同样的识记材料,诵读次数越多,记忆得就越牢”[13],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分散的重复肯定会形成更好的记忆效果。也就是说,重复是对固有记忆的再次激活,并且强化和延续记忆,正如法国学者亨利·柏格森所说:“重复根本不会促使第一种记忆向第二种记忆转变;重复仅仅是利用越来越多的运动,那种运动延续第一种记忆。”[14]
我们可以确信,重复使得个体的记忆得以强化和延续,而在群体和社会层面的重复似乎也拥有相同的功能。我们的群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是有延续性和可识别性的,它保证了群体和社会的独特性与持久性。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群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依赖的是交际的传承。代际之间口口相传的是不断重复了数千年的英雄传说;同代人之间不断对共同经历展开交流和讨论也是记忆在群体中的重复、强化与聚合;社会行动者的纪念活动、法定假日、庆典仪式更是一种制度化的重复,以强化保持共同记忆的持久性。
在对记忆的研究中,媒介的物质性使得人们更多强调媒介作为记忆的载体在保存记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记忆从鲜活的生命载体跨越到文字符号固化的媒介载体时,记忆的积累和传承模式被彻底改变了。恰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指出的:复制使产品大批量销入市场,打破了原作的即时即地性,也使原作实际存在的时间长短摆脱了人的控制。[15]也就是说,媒介空间中的复制使得原本的记忆可以被大批量地重复、可以被随时重复,且记忆的实际存在被延续、被强化。
媒介的重复与复制并不相同,本雅明将媒介技术称为机械复制,“在文献领域中造成巨大变化的是印刷,即对文字的机械复制”[16]。照相、摄影则是对形象和声音的机械复制,但是机械复制的酷似物与摹本都无法拥有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和永久性。媒介重复则不存在原作的问题,或者说大量高度一致的机械性重复使得媒介空间中的原作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一无二性与永久性。印刷对于名著经典无差别的机械复制、CD对于音乐作品的高精度复制,使得受众完全没有必要像追求艺术品一样去追求对原作的耳闻目睹。而电影更是不存在所谓的原作,它是以大量复制销售为目的的媒介生产。
(一)媒介的机械性重复
媒介重复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根据媒介重复的一致性程度或重复性质不同,大致将媒介的重复方式分为机械性重复、叠加性重复与混杂性重复三种不同的类型展开分析。
媒介的机械性重复可以被视为一种无差别的复制,相同的图案在媒体中反复出现,相同的歌曲和影片被经常性地重复播放,以及书籍被一再翻印。这种机械性重复意味着媒介空间中记忆被重新激活的同时并不改变原有记忆本身,重复的记忆与原有的记忆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对于个人而言,“我们记忆的绝大部分都与我们生活的事件和细节有关,而其基本要素就是具有时间性,因此不可能具备被重复的能力”[17]。媒介记忆中的绝大部分也不具备被重复的能力,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决定了大多数媒介空间中固化的信息很快会走向遗忘,而能够获得机械性重复的记忆则是权力、宗教、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极少部分。譬如,媒介空间中国歌与国旗的反复出现显然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宗教类书籍的机械性重复是宗教一致性的重要保证,文化经典上的机械性重复对于人类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有着独特的价值。同时,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企业的商标广告也可以长期统一地反复呈现。可见,机械性重复往往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努力实现的结果,而影响因素一旦消失则这种刻意的重复也会随之消失,与之相关的记忆便逐渐走向遗忘。
(二)媒介的叠加性重复
机械性重复保证了记忆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要脱离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将记忆变成可以独立复制的段落。而叠加性重复则是一种线性的、发展的重复,记忆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是连续的,一段记忆在媒介空间中被重复是因为其与当下的记忆产生了叠加,在过去与现在的交叉联系中记忆的重复出现了新的认识与创造。
对于叠加性重复,我们可以以媒介中历史记忆的重复作为对象进行阐释。历史本身可以视为早已被文字符号所固化的尘封旧事,本质上已经成为不容被篡改和重新杜撰的共识,那么记忆重复的意义就必须是当下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可以存在于三个层面:(1)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于国家、民族和自我的全面认识。我们通过编撰系统化的历史教材对历史记忆进行重复,在这当中历史必然是客观的,但它服务于我们当下的需求。(2)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中未被发现的事实真相。譬如,历史文物大发现、历史谜案被破解、历史内幕被揭开,总之新发现、新认识、新观点都可以帮助已经休眠的历史记忆重新复活。(3)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现在的认识,解决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重复某段历史对于现在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譬如,我们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重复的是战争的历史记忆,叠加的是我们对当下和平的珍视。媒介中文化记忆的传承也是如此,不断重复的民俗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是过往记忆与当下的叠加,它留住了传统却又加入了今天的“注脚”。
(三)媒介的混杂性重复
混杂性重复是指不同媒介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对同一记忆内容的重复。从一致性的衡量标准来说,讲述主体的复杂性使得混杂性重复不仅是凌乱的和非线性的,而且可能是与记忆本身严重背离的重复。事实上,在媒介混杂性重复的过程中,我们对哪一段记忆可能在媒介中被反复演绎无从知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记忆和它原本的模样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混杂性重复激活了一段沉睡的记忆,却也可能混淆了这段记忆。
在大众文化领域中这种混杂性重复最为典型,小说、影视剧从各种角度对记忆展开重复,“文化记忆在这种环境下失去了固定的轮廓而变得模糊。不是保存,而是更新;不是回忆,而是发明,这逐渐成为文化行为的新要求”[18]。以影视剧创作为例,香港导演徐克从1991年开始以每年一部的节奏,连续拍摄了6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一举将黄飞鸿这位一百多年前广东佛山的街头艺人捧成了国际文化名人。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黄飞鸿尚且可以如此,那些历史悠久的著名人物就更加能成为影视剧作品重复的焦点。以近年来流行于华语影坛的武则天题材为例,从1976年开始该题材被中国的影视人在电视剧中重复了36次,从1939年开始在电影中呈现了5次,其中的历史价值很难评估,但武则天确实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唯一的也是最为传奇的女皇帝。
混杂性重复确实可以赋予那些几近被遗忘的记忆以新的活力,让那些鲜为人知的记忆变得耳熟能详。混杂性重复在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上让记忆始终保持“新鲜”,善于接纳和融入新的文化,但记忆的本真也在一次次的重复中丧失殆尽。
三、“过去重现”:媒介构建下的记忆
时光倒流,记忆回转,在媒介无休止的叙述空间中,记忆是可以被随时重现的,甚至可以说媒介中的一切文本都是经过媒介重现的当下或过去,都是媒介记录下的时代与社会,但并不是说一切媒介空间中的文本都是媒介记忆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并不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将媒介文本视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我们所记忆的过去,不过是立足现实对过去的重建,回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现在的需要、利益和期待”[19]。对于个体而言,记忆是当下的,是社会的,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各种利益诉求。对于群体和社会而言,记忆同样也无法脱离当下的时空界限,我们之所以去记忆、去回忆都有其当下的特殊意义,或是为了反思过去启示未来,或是为了总结经验寻找方向,甚至借古讽今娱乐世人,记忆总是带着一种时代的烙印。媒介记忆也是如此,记忆要在媒介空间中传承延续,就必须对记忆展开媒介化的重新建构,形成符合媒介与受众需求的文本形态。“从物质性角度来说,文本是制作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媒体技术产物,或者是银幕上的形象。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符号代表的是媒介所再现的东西,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想法,它们并不是事实本身”[20]。这种在媒介空间中构建形成的具有明显“虚幻性”与“虚假性”的记忆文本,要得到社会记忆层面的认同,并被视为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档案,就需将文本经过媒介化的加工使之具有劝服性,营造出它们与真实之间的关联。
媒介化的文本要完成真实性的构建,让受众对媒介空间中重建的过去形成一种群体记忆的认同感,需要从文本媒介化的各种策略和技巧上共同施加影响。只有适当的策略才能使重现获得真实感,使受众能够在媒介的记忆中找到与自身记忆的关联,与当下现实社会形成对应,并最终产生认同。
(一)媒介“重现”的类型分野
人们显然不是将媒介空间中所有的“过去重现”都作为档案来认真对待的。尤其是那些虚构的影视剧作品中对于过去的重现,它完全可以根据制作者客观条件和受众现实需求对过去的记忆展开杜撰和篡改,无需为此担负任何责任。对于受众而言,影视剧中的真实与虚构是不需要去区分的,或者说不应该有人期待影视剧担负起历史教育与记忆传承的使命和职责。当我们将影视剧称为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一类型的文本所追求的就不再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再现,而是屏幕空间中的艺术效果,以及与受众之间的共鸣。
但另一些类型的文本则不同,媒介直接告诉受众这些类型的文本所再现的就是客观事实,无须再作辨别和判断。譬如报刊中的新闻报道、电视中的新闻时事类节目、网络新闻门户的主要内容等。新闻报道是一种将客观真实视为生命的文本类型,要求此类型内容的从业者将客观性视为职责所在,一旦出现失实报道将直接危及从业者的职业操守与媒介机构长期建立的信誉和威信。
除了新闻类文本,纪录片也是一种将真实视为生命的媒介文本,并将“非虚构作为纪录片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再退了”[21]。纪录片的制作者们也在试图“完全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记录和拍摄,力争把最客观、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还原给观众,给观众带来最强烈的‘真实感’”[22]。更为重要的是和新闻报道一样,很少有人去质疑纪录片所重现文本的真实性,人们下意识地认为那些画面、声音和文字便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事、物、景的逼真再现。
媒介文本上的类型区分为媒介记忆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在充满多样化文本的媒介空间中,受众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分野,知道哪些“重现”是可以被认真对待并相互言说的,而哪些又仅仅是媒介空间中的“昙花一现”。
(二)媒介“重现”的技术奇观
媒介空间中“过去重现”常常演化成为一场令人瞠目的技术奇观,电脑和摄影技术的革新使得人们可以运用“动画”“搬演”“再现”的方式呈现那些原本不曾拥有的记忆。
在2010年美国历史频道推出的12集史诗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中,人们震惊地发现,影片中大量运用了电脑CG(计算机动画)和好莱坞式的表演技巧,营造出了一种阿凡达式的视觉效果。影片中电脑CG制作的画面,让人们可以从高空俯视城市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可以直视子弹缓慢飞行射中敌人穿透身体时的震撼,甚至近距离直观感受草原上牛群奔走、大海中舰队航行、空中如云的战机。这显然已经超越了所有历史亲历者的真实记忆,媒介所重现的现实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本身。好莱坞式的表演技巧通过人物搬演,将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在银幕上重现,通过纪实手法让观众身临其境般地感受1817年爱尔兰工人大卫·吉尔罗伊(DavidGilroy)如何使用炸药开凿伊利运河,1869年17岁的中国劳工洪雷沃(HungLeiwo)如何在挖掘铁路隧道的爆炸中幸存,1911年凯特·韦纳(Kate Weiner)在纽约衬衫工厂工作并逃离火海等场景。《美国:我们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纪录片不仅可以重现历史,更可以像剧情片一样再现历史故事的过程、情节,甚至通过动作分解、定格、升格等方式重现和聚焦历史的细节。
纷繁复杂的影视效果让人们对“过去重现”产生迷惑。电脑三维可以制作出泰坦尼克号触礁沉没的整个过程,可以还原“9·11”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细节,甚至可以再现侏罗纪时代中恐龙捕食的场景,而变幻莫测的灯光和震撼的声音效果更加强化了重现的“逼真”。影视中搬演的运用则直接像故事片一样找来演员虚构情节和对白,让还原的历史故事更具视听效果。当然,这些重现可以是制作者小心翼翼的欺骗,也可以是制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共谋”,人们明确地知道这是在用虚构的手段还原真相,而不会去追究它是否欺骗了自己。
(三)媒介“重现”的叙事法则
“过去重现”并不一定是媒介技术上的介入,实际上仅凭文字符号和合理的叙事技巧就可以实现对过往的再现。“所谓读者的‘文本体验’就是参与这种‘现实’的创造过程。不同的叙事模式为文本读者创造出了一种对现实的‘幻象’”[23]。“在读书时,我们会有一种被拉入作者世界的感觉;在朋友给我们讲故事时,我们会本能地进行呼应;在看电影时,我们会认同影片中的主角。我们的思维会在不同的地方游移,会模拟出故事的场景”[24]。人们在叙述的文本中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并且更加确信文本中所重现的过往,而叙事的策略与方法则成为媒介记忆传承的重要途径。不同的叙事可以给予读者完全不同的感受,第一人称的自传体使人们更能相信故事是真实存在的,时间、地点、动机、原因和结果这些叙事的基本元素也被利用于劝服受众使之创造出一种“现实”[25]。而受众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观念则成为叙事中“真相”的佐证,过往重现与现实生活之间呼应就成为叙事者与受众之间共同构建一种“叙事性真实”的基础。
媒介叙事往往就是对现实生活经验与观念的模仿,我们也将现实世界作为“标尺”来衡量媒介叙事的真实性。叙事者与受众对于当下的经验和观念则成为过往重现的叙事成规。譬如:我们习惯接受事情按照从原因到发生、经过再到结果的方式去发展;认为生活中惯常的就是出现冲突、矛盾、问题,进而分析情况,最终冲突、矛盾、问题得到解决的推进模式;期待叙事中出现正义与邪恶、英雄与小人、胜利与失败这样强烈的二元对立式的冲突。正如法国学者高概所说:“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26]
[1]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0.
[2]帕特里夏·法拉,卡拉琳·帕特森.记忆[M].户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11.
[3]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
[4]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6.
[5]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7.
[6]丹·吉摩尔.草根媒介[M].陈建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6.
[7]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9.
[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96.
[9]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风景[M].张朝霞,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59.
[10]鲍里斯·格罗伊斯.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M].张芸,刘振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59.
[1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0.
[12]赫尔曼·艾宾浩斯.记忆的奥秘[M].王迪菲,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98.
[13]赫尔曼·艾宾浩斯.记忆的奥秘[M].王迪菲,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6.
[14]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7.
[15]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10.
[16]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5.
[17]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6.
[18]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9.
[19]莫里斯·哈布瓦茨.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20]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61.
[21]常启云,肖邓华.浅谈纪录片的真实性[J].新闻世界,2009(6).
[22]王春霞.规范与界定探索与追问——也谈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J].中国电视,2008(11).
[23]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
[24]奇普·希思.粘住[M].雷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09.
[25]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55.
[26]高概.语言符号学[M].王东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学系)
编校:张红玲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媒介作为人类记忆的研究——以媒介记忆理论为视角”(14JDCB01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