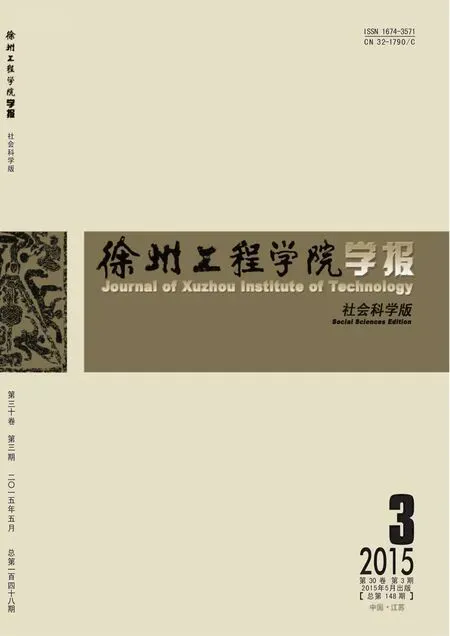“使天主之教 无远不行”——北京西洋传教士与朝鲜士人的交往心态
2015-02-28韩东
韩 东
(韩国汉阳大学 人文学院,韩国 首尔 133791)
“使天主之教 无远不行”
——北京西洋传教士与朝鲜士人的交往心态
韩东
(韩国汉阳大学 人文学院,韩国 首尔133791)
摘要:18世纪发生在北京天主堂里的西洋传教士与朝鲜士人的“邂逅”,虽说是“天缘”,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貌合神离”。这些西洋传教士虽然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然而朝鲜士人并不买账,对于尊崇儒教的朝鲜士人来说,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都是“异端”,所以西洋传教士即使接待朝鲜士人,却没能让朝鲜士人真正理解与接受天主教。同时随着在交谈中朝鲜士人的“无礼”与“无识”问题的显现,原本“欲出朝鲜”的西洋传教士感到了失望,并渐渐疏远朝鲜士人而闭门不见了。
关键词:天主教;传教士;朝鲜士人;心态;传教
158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到达广东肇庆后不久刻印了《山海舆地全图》,这幅依照西洋绘画以及地理知识而绘制的世界地图给当时中国士人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颠覆了他们心目中“世界”的面貌[1]44-62,其中也包括改变了中国士人对“西洋”世界的认知。进入17世纪,得助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北京后对世界地理与地图的传播,中国士人开始把“西洋”与“欧洲”联系起来。而朝鲜士人对“西洋”的认知也得助于当时“朝贡体系”下的使节派遣,朝鲜使节在北京城中见到了西方耶稣会传教士,通过与这些传教士的谈话,以及作为礼物而接受的书籍与世界地图,朝鲜士人才开始真正打开了认知“西洋”的大门[2]122-124。
进入17世纪,朝鲜士人虽说对于“西洋”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18世纪末期以前的朝鲜士人来说,西方的天主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并不是那么清楚,用葛兆光教授的话说,那些西洋传教士只不过是一些“邻居家的陌生人”[3]。但是,对于天主教自身的不了解,却并没有影响朝鲜士人与传教士的往来,来到中国的朝鲜士人都会乐此不彼地去天主堂拜访这些并不熟悉的“陌生人”,而这些传教士也总是会友善,甚至热情地接待朝鲜士人的来访并赠送礼物,在北京的天主堂里,他们仿佛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比如1720年,朝鲜士人李器之在玉河馆拜见传教士苏霖就感叹到:“吾居天地之极东,君居天地之极西,今此会面,岂非天缘?”传教士苏霖也自叹彼此“相见恨晚”[4]304。由此看来,对天主教的陌生并没有疏远朝鲜士人与西洋传教士的心理距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朝鲜士人与西洋传教士在天主堂的“邂逅”呢?
1645年日本德川幕府为搜捕天主教徒,提出了希望能够进入朝鲜国土自行搜捕,且朝鲜方面也必须派人搜捕并随时向日本汇报情况的无理要求[5]149,当然最终遭到了朝鲜方面的拒绝。葛兆光教授认为:“日本严厉禁教捕人这件事情,倒让朝鲜人知道了西洋国和天主教进入日本后的命运,这些一直铭记丰臣秀吉入侵之辱的朝鲜人,反而对那些被倭酋追捕的耶稣之党,产生本来并没有的同情。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使者到北京来,都要好奇地专程看看这个天主教,究竟是什么模样?”[3]3葛教授的这种推测能够从一个侧面解释朝鲜士人出于好奇而频繁造访天主堂的现象,但是似乎无法解答耶稣会传教士热情接待朝鲜士人的心态。因为朝鲜士人与传教士的天主堂“邂逅”,不仅仅是朝鲜士人好奇心的“一厢情愿”,也包含了传教士的“热忱相待”,那么北京天主堂里的传教士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展开与朝鲜士人的交流的呢?
通过翻看《燕行录》中朝鲜士人所记录的与传教士的笔谈资料,可以确定的是西洋传教士热情接待朝鲜访客绝不是因为他们“热情好客”的民风,而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企图。本文撰写的目的,便是阐述西洋传教士在北京天主堂与朝鲜士人的交流心态。
1784年,朝鲜人李承熏在北京天主堂接受了葛神父(一说梁神父)的洗礼,被赐教名“伯多禄”,随后他返回朝鲜创立天主教会,进行传教。由于朝鲜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是在没有耶稣会传教士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导致了朝鲜人不得不自己充当上帝的使者——神父,他们的洗礼活动不得不由教友代替,因此朝鲜的传教活动既不正规也不成体系。加之1773年罗马教皇解散中国耶稣会,天主教放弃原来的“补儒论”传教主张,进而转为与儒家对抗,走上严守天主教义的道路。受此影响,朝鲜的天主教与传统的儒教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朝鲜政府对天主教徒进行了多次的打击。在这种背景下,受朝鲜教众的要求,中国苏州人周文谟奉北京主教汤士选之命,混入朝鲜朝贡使团,进入朝鲜开始传教[3]8-9。纵观朝鲜天主教传播的历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朝鲜的天主教传播是在朝鲜人自己的主导下完成的,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传教“自觉”,而西洋传教士对于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播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积极主动。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在中国传教的P.de.Halde神父在其《中国纪事》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最近,从朝鲜来与我们见面的人,通过汉文笔谈,对我们有所了解。但是在朝鲜不曾宣传过天主教,尽管朝鲜人中也并不是没有在北京受过洗礼的,但是,在朝鲜的长期传教,却需要清朝皇帝的批准,得到这种许可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雍正二年(1724年)礼部发布禁教令,中国的教会刚刚全部瓦解以后更是如此。只是天主有不可思议之奇迹,如果中国可以基督教化,那么像朝鲜、满洲这样文化上追随和尊重中国的国家,无疑在几年间就会效仿中国。[3]5
在这段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一是,当时天主教在清朝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限制;二是,耶稣会并非不想在朝鲜传教,只不过他们认为应该先让中国天主教化,如此一来,朝鲜自然也就会效仿中国,信奉天主教。因此,对于18世纪前期的西洋传教士来说,即使对待天主教在朝鲜传播的方式趋于“保守”,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希望天主教义广播朝鲜半岛,关于这一点不妨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1720年朝鲜人李器之踏上了燕行之路,9月27日在北京的天主堂里拜见了苏霖、戴进贤、张安多等西洋传教士。对于当时的见面场景,他曾在《一庵燕记》中这样记述到:
余求见西洋画,出示画像七簇……余请得一二丈,苏、戴二人,各出他小画二三丈赠之。其中小锦片塗墨,而空人形,若阴刻印本者然。画作女人抱子状,欲与而还置用,甚有吝惜意。余问其故,答此是天母之像,若慢屑待之,与受皆不好云。余曰:“天主之教,若行于东国,是亦诸公之功,天主之像,流布何害?”三人皆以为君言极是,遂与之。[4]302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发现当李器之希望得到天主教圣物圣母像时,耶稣会传教士因担心朝鲜人“若慢屑待之,与受皆不好”而显得“有吝惜意”。这样的回答是符合当时朝鲜认识天主教的现状以及北京的西洋传教士对待天主教在朝鲜传播的态度的。然而当李器之无意中说到如果能让这些图画在朝鲜流传,说不定能让天主教在朝鲜传播时,苏霖等人方才“恍然大悟”,旋即把圣母像赠送给了李器之。应该说李器之说这番话时,只是出于对西洋事物的好奇而促使对天主教圣母像产生了兴趣,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天主教为何物,也不清楚天主教的传播会对朝鲜产生什么影响。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月之后的10月28日,当朝鲜人郑泰贤与西洋传教士汤尚贤再次会面时,他们的谈话内容就明显充斥着天主教徒的传教企图。
汤尚贤言于郑泰贤曰:“吾们欲出往朝鲜,作天主堂,使天主之教,无远不行,可乎?”盖问海路,亦有意也。郑泰贤答:“此系于我国朝廷,非我们所可遥度。但此处皇上能许诸先生出去乎?”答:“我们元不受官于此处,但为行教以来,行止随意,大西洋,小西洋,中国,外国,无处不可住。皇上亦不照管我辈之来去矣。”[4]370
汤尚贤虽说夸大了传教士在清朝“行止随意”的权利,但是很显然这里他有了“欲出往朝鲜”,传播天主教的想法,并且有意地试探朝鲜士人对于传教士前往朝鲜传教的态度。其实通过翻看朝鲜人与北京天主堂传教士的笔谈记录,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洋传教士欲往朝鲜传教的企图,比如对于自己与朝鲜人在北京天主堂的见面,传教士解释到:“此番幸会,俱有天主深意,我们人类,俱系天主所生,四海尽属弟兄。相去数万里,亦弟兄也。”[4]370他们对天主教的传播就这样从与朝鲜人的见面伊始便开始了。又如西洋传教士因深谙朝鲜尊儒排佛的背景,所以当朝鲜人询问“西洋亦尊尚孔夫子否”时,西洋传教士竟会谎称说到:“亦尊敬”,又问“斥佛乎”时,还会爽快地答道:“斥。”[6]880再如为了夸示天主教传播的普及以及受到清朝皇帝的信奉,传教士费隐也曾放言到:“中国奉天主教者甚多,咸以顺理存心,皇上万几之绩,俱亦顺理,莫非崇奉天主。”[4]337另外当面对朝鲜士人对天主教的疑惑时,那些西洋的传教士也会很巧妙地运用儒家经典来开释,朝鲜人洪大容与西洋传教士刘松龄关于天主教的对话就是这样。
余(洪大容)问:“天主之学,与三教并行于中国,独吾东方无传,愿闻其略。” 刘(刘松龄)曰:“天主之学,理甚奇奥,不知尊驾欲知何端?” 余曰:“儒尚五教,佛尚空寂,老尚清净,愿问天主所尚。” 答:“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 余曰:“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答:“孔子所云郊祀之礼,所以事上帝耶,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曰:“《诗经》注,不言上帝之主宰耶?”[7]236-237
这里刘松龄便是运用儒家孔子与《诗经》来解释天主教上帝的含义,他的解释虽有牵强的嫌疑,但是对于崇尚儒家思想的朝鲜士人来说,无疑能够拉近与天主教的距离,从心理上减少对天主教的排斥情绪。西洋传教士就是通过这些谈话中的“铺垫”,让朝鲜士人认为天主教“讲道理与《中庸》《大学》有同处”[8]217,进而让朝鲜士人产生“盖其对越上帝,勉复性初,似与吾儒法门,无甚异同,不可与黄老之清净,瞿昙之寂灭同日而论。又未尝绝伦背理,以塞忠孝之途,海内之诵羲文周孔之言者,孰不乐闻”[9]461的感叹。除此之外,为了拉近与朝鲜士人的关系,增加好感,西洋的传教士们在与朝鲜人会谈结束时都会赠送一些稀有的西洋器物,当然,在这些赠送的礼品中自然也少不了有关天主教的汉译书籍,这些西洋器物与书籍赠送也都是出于传教目的[10]26,31,464。
当然这其中最能说明西洋传教士有欲出朝鲜传教企图的无疑是他们针对朝鲜地理与路程的探问,如他们在与朝鲜人的笔谈中会谈到:“贵邦建都何地,从何等地名来此,乞指明路程。”[4]377毕竟要开展传教活动,首要任务便是能够顺利进入朝鲜,所以在《燕行录》资料中可以发现不少西洋传教士探问朝鲜路程的内容。比如下面的两个例子:
曰:“贵国亦有船到中国来否?”曰:“只有一带鸭绿水,一苇可杭,西洋渡几里海路?”曰:“约五六万里,鸭绿水出海口否?”曰:“环东土皆海也,唯自义州距北京,左夹渤海而来,直路则唯有一衣带水而已。”[6]879-880
且问:“自登莱往朝鲜,海路多少如何?”答:“不能详知,而不过二三千里。”问:“有舟楫往来者乎?”答:“山东渔採人,多往来朝鲜海边。”问:“山东海亦多渔採处,何以往朝鲜?”答:“山东海无海参,朝鲜海中,海参甚大,故多往渔採。”其人但首肯而已。[4]370
无论是朝鲜半岛的鸭绿江,还是山东半岛的渤海湾,如果由海路进入朝鲜,这些地方的航线都是必须要弄清楚的,西洋传教士对这些路程的详细探问无疑是在为日后进入朝鲜传教进行探路。这里有趣的是,对于西洋传教士欲往朝鲜传教的心思,朝鲜士人也有所察觉,然而他们看待这件事情的视角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朝鲜人曾说到:“前此西洋人,虽不明言东出,而每问我们路程,多有欲往之意。盖其人品虽诡异,而甚高洁,有厌薄此处胡俗之意,见我国人衣冠文物,有艳慕之色。”[4]370这里朝鲜士人显然是站在了“华夷观”的“高度”来看问题了,这也反映了明清交替后,朝鲜国内的“朝鲜中华思想”在士人中的渗透是多么的有力与普遍。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天主堂的传教士们是怀揣着“使天主之教,无远不行”的朝鲜传教企图与愿望的。
可是话说到这里就不禁要问了,既然西洋传教士是如此的“渴望”进入朝鲜传教,那么最终为什么没有派西洋神职人员进入朝鲜呢?这里就涉及到清王朝与朝鲜当局对天主教传播的限制,虽然从康熙到乾隆,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传教多少都有限制,但是传教士的活动仍相对自由,而到嘉庆十年(1805年)以后,传教士的活动就受到了全面而严厉的限制。而朝鲜对天主教的全面打击也是纯祖即位(1801年)以后,即大体都在19世纪以后[3]8-11。然外部的环境即使会影响到传教士进入朝鲜的态度,但绝不是动摇其进入朝鲜决心的深层原因。朝鲜人严璹在《燕行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有刘松龄者,年过七十,见为钦天监正。日昨见译人,先通未见,意松龄以今日为约,且言人多则当弊,三使各率一两人为宜云,今日三房上下人尽随出及至,则松龄称病不出见。”[11]240李德懋在其《入燕记》中也记述到当自己希望观览天主堂的“仪器之阁”时,守者要么“托以主人不在”、要么谎称“堂近年失火,今新创而乐亦焚坏”而不许其登览的事情。北京天主堂里的传教士对待朝鲜士人的拜访一向热情,往常都会主动把那些“西洋景”主动拿出来让人欣赏,赠送之物也不在少数,为何对于朝鲜士人会出现“概不接待”的局面呢?对于这种现象似乎可以在朝鲜人洪大容的如下话语中找到答案。
惟东俗骄傲,尚夸诈,待之多不以礼,或受馈而无以为报,又从性无识者,往往吸烟唾涕于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洁性,近来以来,洋人盖厌之,求见必拒之,见亦不以情接也。[7]229-230
洪大容认为西洋传教士拒见的原因在于朝鲜人“吸烟唾涕”“摩弄器物”的“无礼”与“无识”。西洋传教士真的是因为无法接受朝鲜人的“文明卫生”问题,才疏远他们吗?通过翻看传教士与朝鲜士人的交谈记录,可以发现朝鲜人有的提问确属“无礼”与“无识”,但绝不是文明卫生习惯那么简单。比如,朝鲜人对西洋传教士的“婚姻”问题就很感兴趣。当他们与西洋传教士寒暄一阵之后,便会问到“携眷否”[6]862、“诸位在西洋时,有妻子乎”[4]356,西洋传教士往往会尴尬地回答到:“修道人,元来与童子一样,我们并无妻子。”[4]356朝鲜人郑光忠对于西洋传教士曾有过这样的记述,他说:“(传教士)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慕中国之言语文章者,去国离亲,来仕中国,有终身不归者云。”[12]59简言之,对于朝鲜士人来说,西洋传教士的生活是“案无鱼肉室无妻”[13]197。由于朝鲜士人并不清楚天主教义中神父不能娶妻的规定,总是以儒家的思维习惯来询问传教士的婚姻问题,这些提问对于恪守天主教义的传教士来说无疑是“无礼”的。
同时,虽说早在明末清初之际,朝鲜士人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汉译西学书籍[14]199-204,而且当时的西学书籍在两班士大夫阶层中流传比较普遍,安鼎福(1712-1791)就曾说到:“西洋书自宣庙末年已来于东,名卿硕儒无人不见”[15]372,但是那时的士大夫仅把西学书籍“视之如诸子道佛之属,以备书室之玩,而所取者只象纬句股之术而已”[15]372。可见朝鲜士人对西学书籍接触虽较早,但是仅仅局限于西洋的科学技术,而对于西洋的天主教却并不了解。所以,18世纪末期以前的朝鲜士人与传教士关于天主教的对话,也是充斥着对教义的“无识”。即使传教士通过使用儒家的名人与经典来阐释天主教的内涵,拉近了天主教与信奉儒家思想的朝鲜士人的心理距离,但是朝鲜士人仍然对于传教士所说的天主教感到非常疑惑。比如朝鲜人刘拓基就曾表达过“天主教者,未知昉于何年代,而自云只奉天无伪,斥老佛为外道云。书肆亦未闻有此书,未审其宗旨法门果如何也”[16]97的疑问,由于不理解天主教的实质,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传教士“其说荒惑不可测”[17]81。
另外因为对传教士的话产生了疑问,朝鲜士人便根据自己的思想与认知准则去“解读”天主教,比如朝鲜人徐浩修便认为天主教“其屏嗜欲、灭伦理、似佛氏,薔精气、住聪明,似道家”[18]542。与传教士交流过的朴趾源也认为天主教“自谓穷原溯本之学,然立志过高为说偏巧,不知返归於矫天诬人之刻,而自陷于悖义伤伦之臼也”[19]310。由此看来,朝鲜士人并不买传教士“热情接待”的账,哪怕是在传教士对天主教进行“儒家式”的包装之后,他们仍然认为天主教与佛家、道家无异。当然对于朝鲜士人对天主教的这种误读,西洋传教士也会与其展开辩论,同时也会感到“不爽”,比如朝鲜人白景炫与周神父的谈话便是这样。
周先书曰:“天下有儒释道三教,而道者,人之死生中一件也。 在中土崇奉之极,故方今天下皆尊尚之。贵邦亦有闻知否?” 翼卿答书曰:“天主道学之高明,曾所闻之,而但不知微妙之理何居?” 周曰:“为此道者,清净无欲,与物无竞,然后能造乎微妙之境。则虽死犹生,如蝉之蜕,精神脱出行骸之外,虽千万岁,长存不灭。知此理者,生不恶死矣。” 翼卿曰:“君之所谓道者,无乃仙乎?仙贵虚灵,佛尚寂灭,仙佛皆吾道之歧也。行吾道,则歧无所不通,生死蝉蜕之说,终近於不经,故圣人不言之耳。” 周怅然不悦。[20]80
或许是朝鲜士人“独尊儒术”的原因,对于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都比较排斥,所以,尽管传教士把天主教说的那么高尚,朝鲜士人仍然会认为“大抵西洋人之学,辟佛郭如,而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 然亦一异端云”[21]286-287。对于西洋传教士尊奉的天主教,朝鲜士人却看作是“异端”,以此可推想当西洋传教士面对朝鲜士人把天主教与佛家、道家相提并论,与其展开讨论时,在这些传教士的眼中,朝鲜人对天主是多么的“无知”。如果说“婚姻”问题还只让西洋传教士们感到尴尬,那么朝鲜人对“天主”的“误读”与“批判”,显然会点燃传教士的“愤怒”。所以从朝鲜士人与西洋传教士谈话中表现出来的“无礼”与“无识”,我们可以推测到传教士对于朝鲜士人的“失望”,这或许才是后来传教士拒见朝鲜人的真正“内幕”,也是北京的传教士为何一直没有派传教士去朝鲜的原因。
18世纪,发生在北京天主堂里的西洋传教士与朝鲜士人的“邂逅”,现在看来双方都是怀揣着各自的“需求”而来的,朝鲜士人是出于对异邦人物的好奇,而那些西洋传教士们却是基于传教的企图。所以,虽说他们的邂逅被标榜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4]378,但是他们的这种“热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貌合神离”。这些西洋传教士们虽然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但是朝鲜士人并不买账,对于尊崇儒教的朝鲜士人来说,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都是“异端”,所以西洋传教士们即使热情接待了朝鲜士人,但是却没能让朝鲜士人真正理解与接受天主教。同时随着在交谈中朝鲜士人的“无礼”与“无识”问题的显现,原本“欲出朝鲜”的西洋传教士们开始了失望的旅程,并渐渐疏远朝鲜士人,开始闭门不见了。
参考文献:
[1]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M]//王元化.学术集林:卷16.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卢大焕.朝鲜后期的西学输入与西器受容论 [J].震檀学报,1997(83).
[3]葛兆光.邻居家的陌生人[J].中国文化研究,2006(3).
[4]李器之.一庵燕记[M]//燕行录选集补遗:上.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2000.
[5]成以性.燕行日记[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18.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6]李商凤.北辕录 [M]//燕行录选集补遗:上.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2000.
[7]金景善.燕辕直指[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71.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8]李宜万.家山全书农隐遗稿 [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30.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9]李颐命.书牍·疎斋集:卷11[M]//韩国文集丛刊(172).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6.
[10]李元淳.朝鲜西学史研究[M].一志社,1986.
[11]严璹.燕行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40.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12]郑光忠.燕行日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61.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13]赵尚絅.燕槎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37.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14]赵珖.朝鲜后期西学书的受容与普及[J].民族文化研究,2006(44).
[15]安鼎福.杂著·天学考[M]//顺庵丛书:上.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0.
[16]刘拓基.知守斋燕行录[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38.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17]南泰齐.椒蔗录:第1册[M].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18]徐浩修.热河纪游[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51.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19]朴趾源.热河日记[M]//韩国文集丛刊(252).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2000.
[20]白景炫.燕行录[M]//燕行录选集补遗:中.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2000.
[21]金舜协.燕行日记[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卷38.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责任编辑蒋成德)
"No Matter How Far it is, the Doctrine of God Can Reach":
the Contact Mentalities Between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Korean Scholars in Beijing
HAN D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133791,South Korea)
Abstract:In the 18th century in Beijing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Western Catholic missionaries and Korean Scholars was thought to be "predestination",but it's quite dubious.Although these western missionaries clothed Catholic in a "Confucian" coat,the Korean scholars still thought it as a "heresy",for the Korean scholars only respected Confucianism rather than any other ideologies.Therefore even if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warmly received the Korean scholars, they still failed to make them tru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Catholicism.Moreover,the rudeness and ignorance the Korean scholars displayed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made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felt so disappointed that they alienated them since then.
Key words:Catholicism; missionaries; Korean scholars; mentality; missionary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3-0064-05
作者简介:韩东(1988- ),男,四川广元人,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域外汉文学、中韩比较文学、东亚历史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