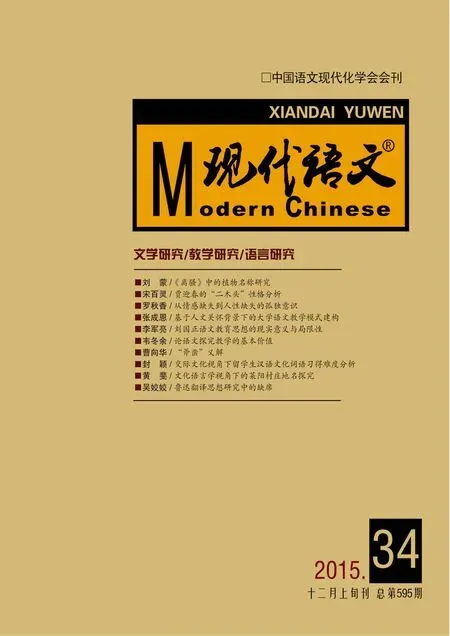奇情与奇趣——凌濛初和李渔婚恋题材拟话本的审美异同
2015-02-28于新未王引萍
○于新未 王引萍
奇情与奇趣——凌濛初和李渔婚恋题材拟话本的审美异同
○于新未王引萍
摘要:凌濛初和李渔的拟话本都具有“奇”的审美特点,但二人对“奇”又有不同的阐释与追求。凌濛初重视产生“奇”的情感,李渔则重视因“奇”而产生的趣味。凌濛初的“奇情”和晚明文人风尚息息相关,李渔的“奇趣”则在看似不合时宜的欢乐中隐藏了明清易代的悲哀。
关键词:凌濛初李渔奇情奇趣
“奇”是明清之际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之一,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尚奇倾向。作为独立创作拟话本的代表,凌濛初和李渔都在婚恋题材的拟话本中表现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新颖、别致的特点,凌濛初的拟话本集以“拍案惊奇”为名,李渔也有“情事不奇不传”之语。但二人对“奇”的理解和表现有着明显的不同,凌濛初的作品偏向“奇情”,“奇”是感情迸发的结果;李渔的作品侧重“奇趣”,“奇”是产生“趣”的手段。从“奇情”到“奇趣”的转变体现出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
一、凌濛初拟话本中的“奇情”
凌濛初的作品在“奇”的表象下隐含着对“情”的追求,主人公在情感的支配下做出一系列的奇行异举,感情漩涡中的男女往往为了追求情感的圆满奋不顾身,不仅可以为爱轻生死,甚至可以打破生死、人鬼的界限。
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同佥公子拜住在花园外,看到荡秋千的宣徽小姐速哥失里,两人定下婚约。但不久同佥家破人亡,只剩下拜住一人。速哥的母亲看不起拜住,要把她另许他人。速哥不愿抛弃拜住,缢死在轿中,停尸清安寺,拜住前往哭祭,速哥听到哭声苏醒,和拜住逃亡上都。这种重情感、轻生死的奇行女子给“二拍”增添了人情与人性的光彩。《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中,吴兴娘虽然已经死去,但以魂灵的方式来完成情感的追求,也甚为奇特。吴兴娘和崔兴哥比邻而居,同岁而生,以金钗定为夫妇。崔家在外宦游十五年未归,吴母欲将兴娘别嫁,兴娘惊忧而死。后崔生回乡完婚,兴娘的魂灵幻化成庆娘的外形,与崔生相处一年,后又促成崔生和庆娘的婚姻,虽然期望崔生不忘自己,但二人婚后兴娘就不再显灵干涉。不忘旧情,死后魂归已是奇事,一年时间完宿愿,然后就此放手,再不搅扰更是一种奇情。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但“二拍”中也有不少痴情的男子。《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中名妓苏盼奴与赵不敏相好,赵家贫,盼奴资助其读书。后赵不敏授官司户,却因名妓难以除籍不能迎娶盼奴,抑郁而终,盼奴也在同一天命赴黄泉。功成名就不弃发妻的男子已属少见,不忘妓妇情深,发语“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关,岂是闲事”[1](P274),并因此而死的男子当真是奇之又奇了。《莽儿郎惊散莺燕 㑇梅香认合玉蟾蜍》中凤生和杨素梅,情定玉蟾蜍。可惜分别被以外家名义定下嫁娶,不料四个异姓名却是一双有情人,两人分别以他姓论嫁娶,仍然是一对夫妻,也是奇异的缘分。凤生不为才貌双全、富贵无边的冯家甥女动心,认定情投意合的杨素梅更是少见的奇情。“二拍”中有此“奇情”的男子不在少数,表现出作者对平等爱情的赞扬,在爱情中,男性和女性一样要有真心的付出和勇敢的坚持,不能见异思迁或者胆怯逃避。
凌濛初笔下的奇情故事多是建立在青年男女双方一定的感情基础之上的,且其笔下多恋爱故事,侧重表现欢爱中的男女克服重重困难,抱着不能在现世结为夫妻,就要在阴间再相会的决心,做出一系列的奇行异举。这种“奇情”的背后是对人合理欲望的追求,以及对自由与爱情的颂扬,这和晚明时期肯定人情人欲,相对开放、自由的风气是分不开的。可惜凌濛初去世的同一年,明朝也灭亡了李渔的拟话本创作集中在清朝初定时期,经历了明清易鼎的战乱之痛,李渔的作品呈现出另一种气象。
二、李渔拟话本中的“奇趣”
李渔饱尝明清易鼎战乱之痛,清初文坛又被朝廷严密控制,他对自由、平等情感的追求相对减弱,侧重发掘因“奇”而产生的趣味。李渔的拟话本中也有很多奇特的婚恋故事,它们大多是些轻松有趣的婚姻故事,作者希望他的小说可以带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些许快乐。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渔侧重用新颖奇特的题材增加作品的趣味性。《男孟母教合三迁》和《萃雅楼》都是选择文学作品中较为少见的同性恋情题材进行发挥,前者改男做女,后者三男欢爱,在同类作品中情节也属奇特少见。《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男男女女竟然要开设班次,传授降服异性的本领,也真是新奇有趣。在较为常见的题材中,李渔也擅长利用新奇的道具推动情节的发展:《夏宜楼》中瞿吉人借用西洋传来的望远镜成就了和娴娴的婚事;《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则借用《占花魁》一出新戏,带出了另一个妓女和嫖客的故事,虽然老套,但是因为有新素材的融入,而有了新奇有趣的特点。李渔的作品虽然有刻意求“奇”之嫌,但能以“奇”生“趣”,也是其匠心独运之处。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流传广泛,李渔打破常规,偏让男女主角极不般配,以求推陈出新,博人一笑。《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外号“阙不全”的阙里侯生得眼花面疤,手秃足跷,鼻见酒糟,发色沉香,口吃背驼,嘴歪眼斜,可谓是奇形怪状极矣,但就是这么一个绝丑男子偏偏娶了三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为了巴结丽人做出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举动;《拂云楼》里才貌双全、立志要娶个绝色的裴七郎却娶到了面黑牙乌,肌糙指粗的封氏女,以致在路上相逢,裴七郎竟然怕人嘲笑而藏于人后。极美的妻子配了极丑的丈夫,或者极美的丈夫娶了极丑的妻子,视觉上的冲击感以及双方磨合中的种种冲突让人忍俊不禁。
最重要的是李渔拟话本的结尾通常是妥协式的美满,男女主角互相磨合、忍让,最后皆大欢喜,而不是像凌濛初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对心中的目标不懈追求。且李渔的拟话本多婚姻少恋情,似乎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婚姻在没有成为定局之前不妨多方谋求,就像《夏宜楼》中的瞿吉人看中娴娴小姐,就千方百计谋求,不惜使用欺骗、恐吓等手段;或者像《合影楼》中的珍生,撒娇耍赖,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一旦成为定局,不如委曲求全,争取在逆境里找到办法善待自我,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三位美人自知无法摆脱要与阙里侯共度一生的命运后,只好想出每个房里放两张床,中间点上大把的熏香遮盖阙里侯身上异味的主意来改善自身处境;《鹤归楼》更是通过对两对夫妻对待情感的不同方式形成的不同后果进行对比,表现了作者不和命运做无谓的抗争的思想以及顺应时势以求自保的人生哲学。这种妥协式的美满,可以说是在乱世中求快活的唯一可行手段。
三、从奇情到奇趣转变的原因
凌濛初和李渔的婚恋题材拟话本都追求“奇”的审美效果,但在具体表现上又有“奇情”和“奇趣”的不同侧重。这种审美倾向的同中有异与他们处身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一)“尚奇”——一以贯之的原因
凌濛初和李渔的婚恋题材拟话本虽有“奇情”和“奇趣”之别,但“尚奇”倾向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种“奇”不同于“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多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2](P1),偶有涉及神怪灵异,也是顺情理而为。在这一点上,二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晚明商业气息浓重,人们普遍好货好色,物欲横流引起竞争之风,只有新奇、能调动人们好奇心的产品才能独占鳌头。这些产品不仅包括华服美食,美妾姣童,也包括广为流行的文学作品。“市民读者的尚新尚奇的阅读需求,同样也引起白话短篇小说作家的关注”[3](P81),“二拍”为凌濛初应书商之邀而作,李渔的创作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作品本是为了广泛流传而生,自然会主动迎合潮流。
但“尚奇”不仅是作者自觉追求商业利益的表现,也是他们个性觉醒之后对思想独裁抵触与不合作的表现。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不仅国内各区域间交流加强,西方思想也传入国内,传统思想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统治者极端注重思想控制,采取种种措施以期读书人能够回归到“三纲五常”的传统道路上来。凌、李二人都出身于商业家庭,受商人思维影响较深,在求奇求变和求中庸之间更偏向前者。二人都放弃了科举,而专心于通俗文学创作和书籍刊刻、书坊经营。既然放弃了中规中矩的科举道路和千人一面的科考文章,用“奇”来彰显对朝廷思想独裁的不满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他们这种“庸常之奇”的文学观念受到“王学左派”的极大影响,与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及李贽的“新奇正在于平常”是一脉相承的。但明末和清初毕竟不是同一个朝代,不同的生存环境使二人向不同的方向偏离出各自的特点。
(二)情感因素下降的原因
从明末到清初,情的分量在世人心中是不断下降的。明朝帝王自万历始,多不理朝政,导致政事荒废。这使得明朝末年党争激烈,官场腐败,民不聊生,但也让明朝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出现裂痕,不同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得以生长,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大行其道,士人倾向于反观内心,重视自我的体悟。当时的文坛掀起一股重视情感、赞扬情感、解放情感的潮流。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情教”观等都对凌濛初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但是晚明黑暗的政治格局使文人缺乏进身的途径和信心,一部分文人将内心不好的一面也借心学发泄出来,滋生懈怠、懒惰的情绪,甚至以享乐、纵欲为追求。明亡之后,人们把明亡的原因归咎于心学流弊造成的士风颓丧,针对心学返归内心的感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进行了批判,因心学而滋养生的各种情感观念也偃旗息鼓。士林风气从崇尚个人心性的解放,转换为对时代变更的关注与反思,倡导经世致用,个人的情感追求让位于对家国天下的思考。吴毓华说:“到了晚明,戏曲美学关于情的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激烈动荡,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之下,不断地增加了理学的成分。这种趋势,到了清初就形成了由情向理的一种反复。”[4](P98)拟话本创作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处于凌濛初和李渔之间的拟话本创作大多走的是宣扬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的路子。但“二拍”早在在崇祯初年就已刊印发行,这时明王朝的穷途末路虽已注定,但大规模的战乱尚未波及江浙,不论读者还是作者心态都是较为平和的,尚能够在较为自由、平静的氛围中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与婚姻。
李渔的拟话本创作集中在清朝建立以后。明清易鼎之际,战争的惨烈和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以及由此带来的衰败凋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存境遇。生存尚不能保障,亡国破家的痛楚和移风易俗的悲哀也未得到平复,人们何来心思追求情爱的自由与满足?政局稳定之后,清廷注重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尤其着力于等级制度的重建和维护,平等、自由的思想被抹杀,基于人性自由、人格平等而产生的情爱观念不再是时代的主流,婚姻制度在晚明偶然流露出的一缕光明被抹杀,重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森严壁垒。
(三)趣味因素上升的原因
李渔擅长运用新奇的题材选择与情节处理方式以及妥协式的美满结尾带给读者趣味性的阅读体验。这种趣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清易鼎之际为求生存的辛酸选择。明亡后,文人有的力图恢复,如顾炎武、屈大均;有的投奔新朝,如钱谦益、吴伟业;李渔则选择了卖文为生,和前朝今朝都保持距离。作为一个纯粹依赖作品生存的文人,他必须要贴近市场,兼顾更多人的阅读兴趣才能养家糊口。李渔的读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达官贵人正在匡定秩序,不一定能容忍情感对规则的破坏,而平民百姓朝不保夕,显然对情感的追求也无能为力,作为生活中必备的调味品——“趣”就成了彼此之间最好的结合点。李渔就是凭借着其作品的趣味性在达官贵人和清初严密的文网之间游走的。
更重要的是李渔希图通过作品的趣味性来给苦难的生活增加一些欣喜。他认为“人情畏谈而喜笑”,明确表示其写作目的是“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经历战乱和易代之痛后,李渔尤其注重生活的“欢喜”。他曾以诗“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国。纵便难久长,亦且娱朝乐。一刻离苦恼,吾责亦云塞”[5](P25)注释这种写作目的和人生态度。他的拟话本作品不涉及易鼎之痛,对欢喜的过分追求和对现状的极力容忍显得不合时宜。这种欢喜和容忍的风格可以说是有点明哲保身的,但考虑到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就不忍对他苛责。明亡之前,李渔的生活是相对安定富裕的,而易代之际残酷的战争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了他的内心世界,使他形成了谨慎保守、逆来顺受的个性。这种“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的个性化审美理想,可以说是对曾经离乱的自己和世人的一种心理补偿和身处乱世的悲切愿望。他只是希望能平安欢喜地走完一生,并能够把这种欢喜传达给读者,使饱经离乱的世人能够对平安喜乐的欢喜缘分还保持一份憧憬。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李渔婚恋作品的创作风格。
综上可知,作家的审美理想是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明朝后期,社会思想相对开放,合理的人情人欲得到肯定,人们对美好的情感有着普遍的向往和追求,生逢其时的凌濛初在拟话本中对这一时代风尚有着良好的把握,其婚恋作品表现出明显崇尚“奇情”的倾向。李渔虽然也受到开明情感观念的影响,但国家战乱、人民离丧必然导致他对情感的追求相对弱化,清朝对封建秩序的重组和加强,进一步挤压了情感的生存空间。由此,李渔在保持明代以来“尚奇”的审美追求的同时,注重开发其中的趣味性,使他的作品向“奇趣”的审美追求转变,希望用欢喜带给一代生活苦难的人民些许慰藉。同时,也应该看到,对作品情感内涵的忽视,不仅源于李渔个人认知的欠缺,更是时代思想沉闷的必然结果。
注释:
[1]凌濛初:《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2]凌濛初:《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王言锋:《市民尚奇心理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题材的选择》,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第81页。
[4]吴毓华:《情的观念在晚明的异变》,戏剧艺术,1993年,第4期,第98页。
[5]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参考文献:
[1]朱海燕.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变迁[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2]刘保昌.夜雨江湖:李渔传[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0.
[3]郭英德,过常宝.明人奇情[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徐定宝.凌濛初生命历程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5]傅承洲.凌濛初的尚奇观与“二拍”之奇[J].北方论丛,2006,(6).
(于新未,王引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750021)
基金项目:(文章系北方民族大学2015年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奇情与奇趣——凌濛初和李渔婚恋题材拟话本的审美异同”[项目编号:2015-YJ-WS-028]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