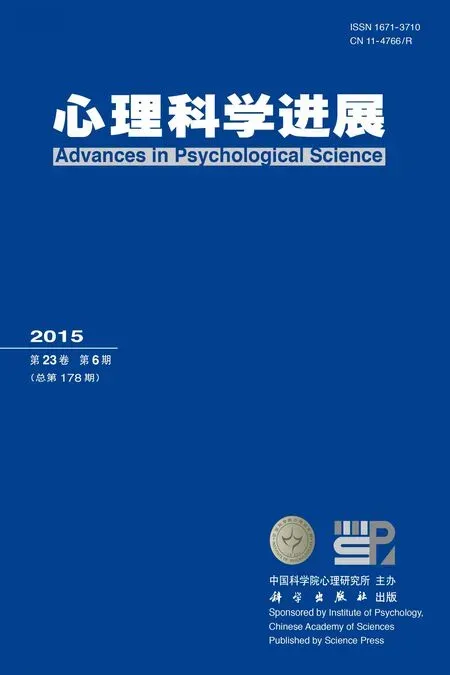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
2015-02-27刘程浩徐富明史燕伟
刘程浩 徐富明 王 伟 李 燕 史燕伟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1 引言
Tversky和Kahneman(1983)指出在概率判断中,如果将两个合取项组成的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那么就会产生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用数学表达就是:P(A∧B)≥P(A)or P(B),因为根据集合关系,元素A∧B∈集合{A,B},所以 P(A∧B)≤P(A)or P(B),显然合取谬误违反了这一规则。而合取谬误还包括一种特殊的情况:双重合取谬误,即P(A∧B)≥P(A)and P(B)。
合取谬误的典型情景有“Linda”任务以及单词频率估计任务。在“Linda”任务中,Linda被描述为“一位单身、外向,年龄为31岁的女性。在大学期间,她主修哲学,十分关注种族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而且曾参加过反核游行”。实验中,要求估计两种陈述中哪一种更有可能发生: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T);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同时她还是一名女权主义者(T&F)。而在单词频率估计任务中,要求被试估计两种包含7个字符的单词形式哪一种含有更多的单词:形式一为“_____n_”;形式二为“____i n g”。在这些情景中,被试往往认为合取事件(T&F或ing形式的单词)的概率更大,产生合取谬误。
一般来说产生合取谬误的概率判断是错误的,但错误的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是否就一定是谬误?
Tversky和Kahneman(1983)认为错误的判断可以称为谬误需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一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二是这种错误是观念上的而非字面上或技能上的;三是判断者应该已知正确答案或者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获得正确的答案。而Wolford,Taylor和Beck(1990)认为错误的判断是否可以称为谬误取决于任务的情景。他们将决策的情景分为未知情景和已知情景:未知情景指描述的情景尚未发生,对未知事件的概率判断只需依据标准的合取规则即可,这种情形下,违反合取规则的错误判断可以称为谬误;但在已知情景,描述的情景已经发生,对已知事件的概率判断就转化为求条件概率的大小,即求合取事件是否更符合描述的情景,因此尽管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这种判断过程符合概率的标准理论,所以这种情形下的错误判断并不能称为谬误。但如果判断者将未知的情形误解为已知的情形,将合取事件的判断转化为求条件事件的判断,那么这种错误判断也是合取谬误。
从以上研究分析可以看出,评定合取谬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在Wolford等(1990)研究中,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取决于任务情景,但决策者是否能够有效地区分已知和未知的任务情景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而且后续的研究证实,对于一些描述情形,例如用于研究合取谬误的经典任务情景难以进行分类(Wolf,1991),因此这种错误的判断可能并不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但是二者在其它两项标准上的看法较为一致:一是这种错误并不是由于缺乏计算或理解能力造成的,而是主观上的认识偏差造成;二是如果能够提供事件间的清晰的逻辑或数学关系,那么决策者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其本身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但由于受任务情景及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依据其它线索进行判断。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研究者主要针对合取谬误标准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作为一种判断和决策的偏差现象,必须达到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才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在相关的情景任务中,确实存在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而且这一现象在概率判断中是很普遍的,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2 心理机制
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目前解释合取谬误的理论主要包括因果模型理论、惊奇理论、确认理论、加权平均模型理论以及“齐当别”理论等。
2.1 因果模型理论
Tversky和Kahneman(1983)将任务情景分为两类:M→A和A→B,在不同的情景中分别建立相应的因果模型进行分析。
2.1.1 M→A因果模型
经典的合取谬误情景由三个部分组成:因果模型M、一个基本的目标事件B以及一个增加的事件A。例如在Linda任务中,M为Linda的个体描述,事件B为她是一名银行出纳员,事件A为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而事件B不是M的代表性结果,事件A为M的代表性结果,所以在概率判断中建立了M与A之间因果联系而不是M与B之间的联系。该理论认为,被试对事件的发生概率的判断正是基于这种因果关系的建立,如果建立了因果联系,那么就会对相关事件发生概率给予高估,由于合取事件A∧B包含了事件A,所以也会建立合取事件A∧B与M的因果联系而不是合取项B与M的因果联系,从而导致合取事件A∧B的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B的概率估计。
2.1.2 A→B因果模型
关于A→B模式的任务情景为:在一项包含了英国所有年龄和职业的成年男性的代表性样本的健康调查中,F先生是随机从这个样本中挑选出来的,现在由你判断以下哪种情形更有可能发生:a)F先生有一种以上的心脏病;b)F先生年龄超过55岁并且他有一种以上的心脏病。
Tversky和Kahneman认为,尽管在A→B模式下,A、B都不是因果模型M的代表性结果,但是如果事件A与事件B之间存在因果或者正性相关关系,那么对于条件概率P(A/B)或P(B/A)来说,其发生概率就会大于P(A)和P(B),同时由于这些关系的存在,被试对合取事件A∧B的发生概率的判断会转化为求条件概率的判断,所以合取事件A∧B的概率估计要大于任一合取项的概率(A、B)估计,从而导致双重合取谬误。而且合取谬误率(合取谬误的频率)与这些条件关系的强弱有关,即如果合取项间的因果关系更强时,那么被试在概率判断中就更有可能出现合取谬误。
其实,不论是将任务情景分为M→A还是A→B模式来解释,都是通过建立相应的因果模型来进行分析,而在对应的因果联系建立时都是依据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 heuristic)对信息进行处理。在M→A模式下,关于个体的描述性信息M是个体为类型A的代表性描述,因此更有可能将个体判断为类型A;在A→B模式下,合取事件A∧B包含了事件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因此是事件的代表性发展过程,所以合取事件的发生可能性被估计的更高。由此可见,如果判断者采用代表性启发式而非标准的概率理论和合取规则对信息进行分析来估计事件的发生概率,那么就会产生合取谬误。
2.2 惊奇理论
针对Tversky和Kahneman(1983)因果模型理论中采用A→B模式解释一些合取谬误的现象,Fisk和Pidgeon(1998)首次提出用潜在惊奇理论(potential surprise theory)也可以解释这类现象。该理论认为事件的发生概率可以用惊奇值(surprise values)来表示。惊奇值代表了事件发生时我们可能感受到的惊奇程度,而惊奇值与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应,一般来说,越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带给人们的惊奇感(值)越小。
在合取事件的判断中,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基于事件B和事件A两者概率中较小的值,即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受概率较小的组成事件的影响更大,受概率较大的组成事件的影响较小。而单一事件的估计概率不仅仅取决于自身而且受其他事件的发生的影响,如果事件A、B呈正性关系,那么在事件B发生的条件下,事件A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并导致合取谬误,但如果事件A与B无关,那么就不太可能产生合取谬误。
例如,在Fisk和Pidgeon(1998)的研究中,要求判断以下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A.某人患有两种以上心脏疾病;B.某人年龄超过50岁;A∧B.某人年龄超过50岁,该个体患两种以上的心脏疾病。若事件A与B无关,而且设定A的概率值较小,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基于事件A的概率,但是A的发生概率较低,所以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会低于B而且不大于A,此时就不会产生合取谬误。但在本任务中判断合取事件A∧B的发生概率时,该个体年龄超过50岁,那么其患心脏病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即A与B呈正相关时,条件事件A/B的发生概率大于事件A的发生概率。这种情况下,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基于条件事件A/B的概率和事件B的概率中较小的值,如果事件B的概率小于A/B的概率但大于事件A的概率,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会基于事件B的概率而大于事件A的概率,从而导致合取谬误。
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并没有明确在条件事件A/B的概率小于事件B概率的情况下以及在事件B的概率小于条件事件A/B的概率时,事件B的概率小于事件A概率的情况下,是否也会产生合取谬误。而根据惊奇理论的假设可以推知,如果条件事件A/B的概率小于事件B的概率,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会基于条件事件A/B的概率,由于条件事件A/B的概率大于事件A的概率,所以也会导致合取谬误。但是,如果事件B的概率小于条件事件A/B的概率,事件B的概率又小于事件A的概率,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会基于事件B的概率从而小于事件A的概率,此时就不会产生合取谬误。
此外,虽然针对KT的任务情境分类M→A,惊奇理论认为若A和B之间存在正性关系时,将提高事件A作为描述性信息的代表性的结果程度,即在A和B之间存在正性关系时,合取谬误率大于A与B无关时的谬误率。但是不能解释在M→A情形下为何会出现合取谬误,在M→A情形中,描述性信息M是类型A的代表性描述,而A与B无关,可以认为M与A也是正性关系,因此A的概率会因为描述性信息M而增大,在M→A模式中,A的发生概率要高于B,所以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会基于事件B的概率而不大于事件A的概率,此时不能认定产生了合取谬误,而且在M→A模式下,A与B无关,根据惊奇理论此时也不会产生合取谬误。但是因果模型理论从启发式思想出发解释了M→A模式下为何会出现合取谬误,所以惊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
2.3 确认理论
确认理论(confirmation theory,CFT)来源于贝叶斯归纳确认逻辑,即证据(evidence)影响事件发生的可信度。在数学意义上就是如果证据支持事件的发生,那么该事件的条件概率就大于其本身的概率, 即 P(A/e)≥P(A)。Crupi,Fitelson 和Tentori(2008)认为在经典的合取谬误情境满足三个条件:(1)e与A呈负性关系;(2)即使A存在,e与B也呈正性关系;(3)A与B呈微弱的负性关系。而在这些条件下,事件的条件概率关系为:P(A∧B/e)≤P(A/e)、P(A∧B/e)≤P(B/e)。
确认理论认为合取事件(A∧B)得到e的确认使其条件概率较先验概率(或本有的概率)增加更多,而合取项的概率增加额很小或者没有。在概率判断中,被试并不比较合取事件的概率或条件概率的大小,而是根据确认性进行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如果用C表示确认度,那么合取事件的确认度C1=P(A∧B/e)–P(A∧B),合取项的确认度 C2=P(B/e)–P(B)、C3=P(A/e)–P(A),由于e与A呈负性关系,e并不支持A的发生,所以P(A/e)=P(A),所以C3=0,但是e支持B的发生,所以P(B/e)>P(B)、P(A∧B/e)>P(A∧B),那么C1>0,C1>C3进而产生合取谬误。然而,由于合取项B的确认度C2也大于0,无法比较C1与C2的大小关系,所以该理论无法解释一些双重合取谬误的现象。另外,如果任务情景中没有证据e或证据e属于中立性信息,即无法对任何事件的发生提供支持,那么合取事件和合取项的确认度都同为0,此时这一理论就会失去解释力。
与确认理论类似的还有支持理论(support theory)(Tversky&Koehler,2004),该理论认为对事件主观概率的判断就是判断对特定假设的支持度,即证据e支持事件发生的程度。他们用条件概率不等式说明合取谬误是这一不等式的一个极端情况:由条件概率的一般不等式 P(A/e)≤P(A∧B/e)+P(A∧¬B/e),其中¬B表示事件B的互补事件,存在极端情况P(A/e)≤P(A∧B/e),此时的判断即为合取谬误。支持理论假定P(A∧¬B/e)的判断趋于0时,才会出现合取谬误,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条件下这一条件概率仍趋于0,所以这一理论的解释力不太稳定。
针对CFT的解释力,Schupbach(2012)研究认为CFT用来解释合取谬误时相关的任务情景中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并不是判断中出现合取谬误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一些情景中尽管没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但仍旧出现合取谬误,而在一些情景中尽管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却没有出现合取谬误。所以Schupbach认为,这些条件和合取谬误间即使存在因果联系也是很微弱的,因此任何的确认理论在解释合取谬误时都是无力的。对此,Tentori和 Crupi(2012b)认为Schupbach对用确认理论解释合取谬误的理解不太准确:确认理论用来解释合取谬误时,并没有指出这三个条件是产生合取谬误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这三个条件或者说是特征只是经典的合取谬误情景的主要特点。而且Schupbach在实验中采用的任务情形都与经典的合取谬误情景有出入,因此这些不同意见并不能说明确认理论无法解释经典的合取谬误现象。他们根据对Schupbach的实验情景的再研究,发现证据e对合取事件的确认度是合取谬误率的严格增函数,再次验证确认理论的解释力。
此外,Shogenji(2012)研究认为,确认理论或者支持理论不能解释双重合取谬误,而且只能解释合取谬误为何会发生,并不能很好地拟合某些实验数据,因此提出了采用合理性取向加工(justificationoriented process)来解释这一现象。合理性取向加工能很好体现认知双目的(dual-goal of cognition)性,即增加正确的信念并减少错误的信念:正确的信念的增加正相关于信息的数量,即如果事件包含的信息越多,就会增加正确的信念,同时事件包含信息越多说明其较为特殊,因此其先验概率越小;错误的信念的减少负相关于条件概率的大小,即如果描述性信息使事件的发生得到确认,那么其条件概率就越高,就会减少错误的信念。在合取事件的判断中,对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转化为事件的合理性程度的判断,而合理性程度J(h,e)是条件概率P(h/e)和先验概率P(h)的复合函数,J(h,e)=F(P(h/e))–G(P(h)),合取事件的信息数量多,就会增加对其的正确信念,同时减少其先验概率,而且描述性信息使合取事件的条件概率增加,又减少了对其的错误信念,二者共同导致合取事件的合理性程度大于任一合取项的合理性程度,进而产生了合取谬误。
合理性取向加工的思想认为事件发生的合理性程度同样是条件概率和先验概率相减的结果,这与确认度的计算方法一致,但该思想不仅仅考虑证据e对事件发生的支持度的影响,而且同时分析事件本身的先验概率,因此可以解释双重合取谬误的现象,但它同样受制于证据e的出现与否以及与事件的关系。所以,尽管这种思想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了确认理论,但仍旧存在一定的限制。
2.4 加权平均模型理论
加权平均模型(weighted averaging model)是指人们在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上,并不是根据合取概率或者条件概率等进行比较,而是依据对多个合取项的概率进行简单的加权平均。Tversky和Kahneman(1983)认为这种均等化加工(averaging process)可能导致合取谬误,甚至是双重合取谬误,尤其是在一些合取项的发生可能性为数字形式时。
Fantino,Kulik,Stolarz-Fantino和Wright(1997)认为如果合取谬误确实是因为人们在判断时采用均等化加工的结果,那么就有以下结论:(1)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可以由合取项的发生概率估计得出;(2)合取项的主观发生可能性越不一致,合取谬误率就越高。而且这些推论已得到Gavanski和Roskos-Ewoldson(1991)实验的支持: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相较于两个合取项发生概率都很高或很低时,两个合取项的发生概率中一个很高而另一个很低时,合取谬误率更高。Fantino等人(1997)在实验中通过比较被试对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与乘法、加法以及平均模型的拟合度,发现被试的判断与平均模型有更好的拟合结果,说明合取谬误的产生正是由于被试在概率判断中采用加权平均模型计算的结果。其中该模型的数学表达为:R=C+∑Wi·Si/∑Wi, 其中 Si表示合取项 i发生的可能性,Wi为合取项i对应的权重,C为常数项,表示被试一致的基线回应,R表示合取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但是Tentori,Crupi和Russo(2013)采用条件概率下的加权平均模型分析这一模型的解释力时,发现不一致的结论。他们将Fantino等人(1997)的模型改进为:P(A∧B/e)=w·P(A/e)+(1?w)·P(B/e)。实验中设定合取项A发生可能性低,合取项B可以得到证据e的确认,但发生可能性不太大,而¬B得不到e的确认,但却有更大的发生概率,而加权平均模式假设增加的合取项使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增加从而导致合取谬误,那么在合取项为B和¬B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合取谬误。但实验结果表明只有在合取项为B的条件下,也就是只有合取项能够得到证据e的确认时才出现合取谬误。因此,他们认为合取谬误的发生不是因为增加的合取项使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增加,而是证据e使合取事件得到确认的结果,所以他们支持确认理论,并不支持加权平均模型理论。
但是在Tentori等人(2013)的实验中,合取项¬B发生可能性的主观估计的任务情景与合取事件概率判断的情景并不一致,因此对¬B的主观概率估计可能会因情景不同而产生变化,如果在合取事件判断的情景中,¬B的发生可能性被重新估计而变小,那么A与¬B的主观概率差别并不大,根据加权平均模型理论,此时合取谬误率会很低,而且在Tentori等人(2013)此条件下的实验中,并不是没有出现合取谬误,只是合取事件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的差异不显著,所以两种理论下实验的结果可能是一致的。而且在运用加权平均模型进行概率判断时,对合取项概率的主观估计也有可能是根据证据e的支持性进行的判断,所以加权平均模型也有可能在具体加工中运用到确认理论的相关规则。由此看来,二者可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互借鉴性。
2.5 “齐当别”理论
The 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Li,2004)认为在涉及多结果维度的多种选择时决策者“齐同”选项之间一个或多个差异较小的可能结果维度后,将差异较大的一个可能结果维度作为最后决策的判断依据。刘立秋和陆勇(2007)认为如果建立在语义理解错误的假设上,可以用该理论来解释合取谬误。
例如,在Linda任务中,存在两个结果维度,合取项T在两维度上的结果同为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同理,合取项F在两维度上的结果同为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而合取事件T&F在两维度上的结果为:Linda为一名银行出纳员,Linda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在判断合取事件的概率时,即比较合取事件和合取项在两个维度上的结果的概率,如果Linda是一名女权主义者的概率大于她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的概率或者Linda是一名银行出纳员的概率大于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的概率,那么齐同合取事件和合取项在两维度上的共同结果之后,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就会大于任一合取项的概率估计,此时就会产生合取谬误。但如果两个维度上的结果概率等同,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就等同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此时就不会产生合取谬误。
2.6 其它理论和思想
一些研究认为,合取谬误的典型任务情景中常出现“and”、“probability”等具有多义和模糊意义的词语,而这些语义的多样性可能会导致合取谬误。
例如,Bonini,Tentori和Osherson(2004)认为,如果判断者将“probability”理解为“plausibility(似真性)、believability(可信性)、legitimation(合理性)”而不是标准的数学意义,那么就会将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产生谬误。但Moro(2009)研究发现,在未出现“probability”的任务中,仍出现错误的判断,说明这种语义上的错误理解并不是导致合取谬误的原因。而Dulany 和 Hilton(1991)认为在经典的“Linda”问题中,如果将合取项B理解为B∧¬F,即合取项B和合取项F的互补事件组成的合取事件,由于该任务情景中相关的人物描述支持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所以P(F)>P(¬F),那么合取事件B∧F的发生概率就大于B,进而导致合取谬误。但Bonini等人(2004)在实验中通过比较B和B∧¬F条件下被试的判断,排除了这种误解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并不支持Dulany和Hilton的观点。此外,在Hertwig,Benz和Krauss(2008)的研究中指出,如果“and”被理解为代表一种时序关系和因果关系时,那么事件的判断就会被理解为条件概率而非合取事件概率的判断,如果“and”被理解为集合的并而非交时,事件的判断就会被理解为析取事件而非合取事件的判断,而这些情况下的判断都会出现“合取事件”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概率估计的错误。但Moro(2009)在排除了包含多种含义的“and”任务情境的研究中,仍发现被试出现错误的判断,而且Tentori和Crupi(2012a)研究也证实,尽管被试将“and”正确理解为“合取”关系,但仍旧出现错误判断,说明并不是因为对任务的无法理解导致的判断错误。
从上述的研究看出,这些解释都是从语义理解错误的观点出发来对合取谬误进行解释,但大都存在对立的研究结论和分析,可能是这些不同的语义(“and”、“probability”、“单一合取项”)对判断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导致这种不一致的结论。
合取谬误实际上也可以用基线比例忽略(base rate neglect)来解释,基线比例忽略是指在事件的判断中忽略相关事件统计学上的信息,而只关注当前呈现的案例信息,从而造成判断和决策偏差的一种现象(Pennycook,Trippas,Handley,&Thompson,2014)。因为单一事件的概率大于复合事件的概率可以认为是一种暗含的基线比例信息,但被试忽略这一信息,只注意到描述呈现的代表性信息或采用其它一些有偏差的合取事件概率估计的方法,从而产生合取谬误。
此外,Franco(2009)提出采用量子论形式主义(quantum formalism)来解释合取谬误。该思想认为人们在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中产生的合取谬误的大小并不一致,采用传统的心理机制很难在量化的水平上对谬误率的差异进行解释,而采用量子论的形式可以将判断者的具体的概率估计过程量化,从而清楚地分析这种谬误率差异的原因。Franco认为人们在概率判断中产生合取谬误是由于干扰效应(interference effect)的存在,具体来说就是在事件判断中除了依据相关事件的概率信息外,判断者的主观因素也会对这些概率值进行一些调整,并产生一定的干扰项,导致相应的概率判断出现偏差,而且由于这些干扰项的主观产生性,所以不同的决策者偏差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从上述合取谬误心理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理论间存在某些共同之处:例如因果模型和惊奇理论都强调合取项之间存在的因果(正性)关系对合取事件判断的影响;而确认理论和加权平均模型都认为描述性信息(证据e)对合取项和合取事件判断概率的影响,而且正如前文分析所述,运用加权平均模型进行概率判断时,对合取项概率的主观估计也有可能是根据证据e的支持性进行的判断,所以加权平均模型也有可能在具体加工中运用到确认理论的相关规则。由此看来,二者可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另外,加权平均模型和“齐当别”理论都认为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与所有的合取项发生的概率密切相关(相加或比较)。此外,不论是合取项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还是证据e对事件发生的支持性关系,都强调判断任务中所呈现的信息间的联系对合取事件判断的影响。
而这些理论间的差异也很多,如因果模型认为合取项间因果关系更强时,合取谬误率更大(Tversky&Kahneman,1983),但惊奇理论认为合取谬误的大小与正性关系的强弱并无关系(Fisk&Pidgeon,1998),而且惊奇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合取谬误的所有情形;而确认理论根据合取项和合取事件确认度大小的比较判断合取谬误的产生与否,而确认度是事件自身条件概率与原有概率的差异,但加权平均模型依据合取事件的条件概率与合取项条件概率的大小比较判断合取谬误产生与否,二者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加权平均模型与“齐当别”理论的差异在于合取事件概率的判断,前者关注合取项发生概率之和,后者关注的其实是合取项在两个结果维度上概率的差异。
3 影响因素
尽管有众多的理论或思想来解释合取谬误,但这些理论多少都存在一些不足或局限,因此需要对影响合取谬误的一些因素进行探讨,以便于充分揭示这一现象。
3.1 频率效应
Gigerenzer(1996)认为从生态有效性(ecological validity)上讲,用于研究合取谬误的任务情景中信息呈现的方式以及要求回应的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实际中并不常见。实际任务情景中,信息多以频率的形式出现,而实验中的信息多以概率或比率等人为的形式呈现,因此在实验情景中观测到的合取谬误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实际的判断中。而且他们认为概率形式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被准确认知,通过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实验任务以频率形式呈现,合取谬误率会显著减少。但是Tentori,Bonini和Osherson(2004)研究发现,尽管在任务情景以及任务要求中的信息均以频率形式呈现,但合取谬误率与概率形式的信息呈现条件下并无显著差别,而且Erceg和Galić(2014)研究认为,尽管频率形式的信息可以显著减少在赌博任务中过度自信,但对于相应的合取谬误率没有影响。
对此矛盾,Wedell和Moro(2008)认为在相关的实验情景中,可能无法排除回应方式(response formats)的调节作用,例如要求对事件的发生可能性进行估计还是对合取事件和合取项的发生可能性进行选择或排序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回应方式对合取谬误的影响已得到许多实验的支持(Tversky&Kahneman,1983)。Wedell和Moro通过实验发现,无论回应模式是可能性估计还是可能性大小选择时,均无显著的频率效应。但是无论是在频率形式还是概率形式的信息条件下,回应方式对谬误率的影响显著,当回应方式为可能性估计时,合取谬误相对于可能性大小选择时更低一些。
3.2 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Bovens和Hartman(2003)认为合取项和合取事件的概率判断依据的是两个不同的信息来源,有时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完全可靠的,而且任务情景中的描述性信息影响这些来源的可靠性,由于可靠性的不同,判断者会给予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概率估计,一般来说高可靠性来源的事件的概率估计更高,如果描述性信息能够提高合取事件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而无法改变合取项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那么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就会高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产生合取谬误。
Hartman和Meijs(2012)深入分析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影响作用,他们认为不仅仅描述信息会影响合取项和合取事件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而且描述性信息本身的可靠性也是不稳定的。研究中,他们采用“Walter the banker”的任务情形,在此情形中关于Walter的人格描述是由他人转述的,而这些描述可以分为三类:H1,Walter今年31岁,是一位直率的、聪明的,并且拥有医学和哲学背景的人;H2,Walter在一家银行工作;H3,Walter在Leuven参加了一次关于认识论的正式会议,其中H2和H1、H3分别是负性关系,而H1和H3是正性关系。他们通过数学计算模型发现,三项合取事件S11={H1,H2,H3}相对于两项合取事件S1={H1,H2},其合取项间一致性的增加值是转述者可信度r(0~1)的增函数,而合取项间的一致性越高,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越大,如果转述者越为可信,那么S11的概率估计也更大于S1,而且只要满足r>0.5,S11的概率就大于S1的概率。可以看出,转述者的可信度不仅能决定合取谬误的产生(r>0.5),而且能够影响其谬误的大小。例如在Linda任务中,关于Linda的人格描述是由实验者(转述者)提供的,因此被试会认为其可信性r接近于1,所以合取事件的概率估计大于合取项的概率估计。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概率判断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为这是由于对实验者充分信任的结果。
但是Jarvstad和Hahn(2011)研究表明,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与合取谬误率的高低无关。他们猜想可能是因为被试对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不够敏感,或者描述性信息对合取事件的代表性不受其本身可靠性的影响,以致没有出现这种效应,但他们并不排除其它来源可靠性的影响作用。
3.3 金钱刺激
在Tversky和Kahneman(1983)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当在实验任务中给予金钱的刺激时,即对正确的回答给予一定的奖励,那么合取谬误率会显著减少。而在Zizzo,Stolarz-Fantino,Wen和Fantino(2000)的研究中,在实验中加入了任务情景的复杂性这一变量,发现只有在简单的任务情景中,金钱的刺激才能有效地减少合取谬误。如果任务情景过于复杂,被试可能无法对任务准确认知,大都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引起天花板效应从而导致金钱刺激的作用消失。而且Devetag,Ceccacci和De Salvo(2013)在研究网络社交情形下的合取谬误现象中发现,即使在金钱刺激的条件下,个体会因为公共关注的关系而产生名誉顾虑(reputation concerns),会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前后一致,从而使金钱刺激的效应减小。然而在Charness,Karni和Levin(2010)的研究中,发现金钱刺激的作用很稳定,无论判断中是否存在人际交流,均发现中等的金钱刺激可以有效地减少概率判断中的合取谬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任务情境不能被被试准确地认知,那么即使被试拥有一定的合取规则知识也无法利用,那么金钱的刺激就无法提高概率估计的正确率。在Charness等人的实验中可能控制了情景复杂性,所以其实验结果与Tversky和Kahneman(1983)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认为在简单任务情景的条件下,金钱的刺激对合取谬误的影响是稳定的。
3.4 训练效应
Agnoli和Krantz(1989)研究发现如果给予被试一个短期的统计知识的训练,包括一些合取项之间的关系的解释,那么合取谬误就会显著减少。但是Stolarz-Fantino,Fantino和Kulik(1996)研究认为,如同一些学习过沉没成本效应的学生更有可能表现出该效应一样,经过概率训练的被试也更有可能表现出合取谬误,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尽管受过相关的概率训练,但仍表现出较高的合取谬误率。但是关于这种解释,显然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何会出现训练的反效应。
对于一般的概率知识的训练无法减少合取谬误的现象,Moutier和 Houdé(2003)研究认为,合取谬误并不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概率或逻辑计算的能力造成的,而是无法阻止启发式加工导致的,所以概率知识的训练并不能减少合取谬误。因此,要使训练产生效果,需要进行启发式阻止的训练,他们的实验结果支持这一猜想。而Cassotti和Moutier(2010)深入分析启发式阻止训练在减少合取谬误上的作用,他们认为情绪唤醒在启发式阻止的训练中有重要作用。如果在启发式阻止的训练中,被试的相关情绪唤醒较困难,那么对启发式的监控的敏感性就会降低,从而无法有效阻止启发式,即使进行启发式阻止的训练,也不会产生效果。
一般来说,情绪多于非理性的加工有关,而且情绪的唤醒是快速的,要早于理性加工,因此对非理性加工的阻止训练,应该与情绪唤醒联系起来。否则即使进行了非理性加工的阻止训练,情绪的影响也会减弱这种训练作用,致使训练作用消失。
3.5 个体差异
Rogers,Davis和Fisk(2009)研究发现,个体的统计知识水平在合取谬误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具有高统计知识的个体产生合取谬误的概率更低。但是后续的研究(Rogers,Fisk,&Wiltshire,2011)指出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并不显著。但这两项研究都认为超常信念者(paranormal believers)更倾向于产生合取谬误,但他们就超常信念者更倾向于产生合取谬误的原因存在分歧,超常信念者是指一些难于理解概率和随机性的个体。Marks(2000)认为超常信念者由于先前期望的原因倾向于认为随机事件(或合取项)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导致合取事件的发生概率估计过高,而且Rogers等人(2009)认为超常信念者可能对合取事件的惊奇值赋值较低,因此对其发生的概率估计偏高。但是Rogers等人(2011)却认为超常信念者更容易发生合取谬误并不是上述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语义理解错误或者启发式运用的不同的原因。
此外,Feeney,Shafto和Dunning(2007)研究认为,个体间存在推理方式的差异,在合取谬误的任务情景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推理方式:因果推理(causal reasoning)和类别强化推理(category reinforcement reasoning)。如果被试采用因果推理,那么更有可能产生合取谬误,但如果被试采用类别强化推理,那么在合取谬误率上存在认知能力的调节作用,而低认知能力的个体更有可能产生合取谬误,但高认知能力的个体不容易产生合取谬误。同时,可以得出认知能力与合取谬误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相关,同样受个体的推理方式的影响。
Morsanyi,Handley和 Evans(2010)通过比较自我中心主义(autism)的青少年和其他同龄人在同一任务中的合取谬误率,发现二者存在差异: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青少年产生合取谬误的概率较低。对此,他们分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主要有:自我中心主义的青少年对合取规则更敏感;他们与社会交际较少,缺乏社会性推理能力;缺乏对任务全面性特征的敏感性。实验研究排除前两种原因,即支持自我中心主义的青少年的合取谬误率较低是因为不能对任务的特征进行充分建构导致的。
3.6 情景的社会化
Gigerenzer(1996)从生态有效性分析,认为用于研究合取谬误的任务情景在现实中并不常见,因此对这种现象在实际中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但是Davies,Anderson和Little(2011)的研究认为,现实中更多的存在社会化任务情景,而且这种社会化任务可能会加剧这种谬误率的出现。如果情景更多是关于个体及其归属的问题,那么对合取事件和合取项的选择不再是一种集合关系的比较的结果,而是一种搜寻-确认问题(search-and-identity problem),即一切为了减少事件的不确定性为主。如果描述信息能够使合取事件的不确定性减少,但对合取项的不确定性无影响,就会选择合取事件,产生合取谬误。
3.7 其它影响因素
此外,Charness等(2010)研究发现如果允许个体向团体其它成员咨询,那么合取谬误率会显著降低;而Nilsson和Andersson(2010)在足球赌博的任务情景中发现,如果两支球队赢率差异较大,个体更倾向于投注两支球队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赢率较低的球队,但在两支球队取胜概率都很低的情况下则不存在这种偏好;Nilsson,Rieskamp和Jenny(2013)发现如果在概率判断中增加记忆负荷将会使合取谬误率显著增加。
4 研究展望
针对合取谬误现象的解释机制众多,但并未达成一致,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需要从合取谬误的心理机制、其实际应用性及其理性与否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4.1 逆转合取谬误
逆转合取谬误(The inverse conjunction fallacy)是判断合取事件为真的概率小于合取项为真的概率,或 P(M∧N is r)
在合取谬误和逆转合取谬误的任务中,要求判断的合取项和合取事件概率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上述的逆转合取谬误情景中,合取项为M、N,而实际判断的却是M为r、N为r的概率,如果将逆转合取谬误中合取项定义为M为r、N为r,那么根据集合关系的分析:整个集合为真其实是集合的交为真和集合的补集为真的合取事件,所以整个集合为真的概率要小于集合的交为真的概率,所以这种理解下相关的判断也可以称为合取谬误。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用解释合取谬误的理论来分析逆转合取谬误,揭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机制。
在逆转合取谬误的任务情景中,一般并不出现描述性的信息。因此,Jönsson和Assarsson(2013)认为Shogenji(2012)用于研究合取谬误的合理性取向加工思想并不能用来解释逆转合取谬误,他们采用一些替代的信息作为描述信息或是证据e来进行分析:将被试依据的背景知识作为证据e;从要求判断的事件中抽出一定的共同信息作为证据e;以及将判断的事件相互作为证据e。这些思想的提出可以为解释合取谬误提供一定的研究方法,Tversky和kahneman(1983)将合取谬误的任务情形分为M→A和A→B两种模式,在A→B模式下,任务中并没有出现描述性信息来作为证据e,但如果采用替代的方法来提供证据e,那么同样可以采用M→A模型的建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解释。此外,作为解释合取谬误的经典理论,确认理论只能解释存在描述性信息的任务情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就会增加确认理论的解释力。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合取谬误和逆转合取谬误的共同的心理机制的研究,以及采用研究逆转合取谬误的思想来完善一些合取谬误的解释理论,以便于更深层次、更全面地揭示合取谬误。
4.2 实际应用
通过对合取谬误的心理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应用到相关研究的结论和观点。例如因果模型的解释启示我们不能相当然认为两个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事件可能只是存在相关关系,也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关系就认为其发生可能性更大,启发式思维虽然较为经济,但有时却产生很大的偏差,应该慎用;而频率效应启示我们更容易加工频率形式的信息,可以在日常的决策情景中尽量使用频率形式呈现相关的概率等数字信息;而对金钱的刺激以及训练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由于在日常的决策中,经常涉及金钱等利益的刺激,而这样的刺激很容易唤起情绪的注意,所以在日常判断中,可能不自觉的进行了这种联合情绪的启发式阻止训练和强化,进而减少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启示我们在日常决策中可以加入能够引起情绪波动的刺激;而团体效应提醒我们,做决策前应该听取周围人的意见,而不是一意孤行。所以,尽管合取谬误是一种比较稳固的现象,但我们仍旧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和方法减少这种判断偏差。
4.3 谬误与非理性
在概率判断中产生合取谬误是否就一定是非理性的?根据Hartman和Meijs(2012)的研究,合取谬误的产生是由于充分信任提供信息的实验者的原因,但这种完全信任不能够说明人类的决策就是非理性的。而徐英瑾(2014)从生态有效性、有限合理性以及社会合理性角度为违反合取规则的判断并不是谬误提供辩护,研究认为在判断中采用直觉性的思维,例如启发式思维体现生态有效性和人类认知的有限理性,并采用支持理论和确认理论的思想指出在现实中,判断者原有的知识或者已知的背景信息能为合取事件的判断提供支持,因此导致的对合取事件的偏好符合社会合理性。所以,这样的概率判断符合进化论的思想,属于人类认知过程必要的阶段,并不能说明这类认知就是非理性的。
此外,违反合取规则会导致错误,但是在一些任务情景中,缺少必要的概率条件无法采用合取规则和标准的概率理论进行判断,此时决策者会采用替代策略进行判断,尽管有时这些策略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但根据理性(rationality)的定义:对所拥有的信念的一致性程度(Aristidou,2013),而且理性并不等同于符合标准理论。如果决策者并无其它的策略可选而坚持当前的策略,那么就不能认定是非理性的表现。
而且Aristidou认为用来解释合取谬误的理论并不是人类行为的最好解释,研究人类的行为不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理论,而是寻找合适的理论来更好解释人类的行为,在实际的判断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干扰(noisy)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所以人类会采用模糊推理模型(fuzzy reasoning model),并不是采用标准的概率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人类在某些条件下的决策行为。von Sydow(2011)也认为标准的概率理论并不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合理的理论,人类在现实判断中会将各种干扰考虑在内而采用基于干扰逻辑关系的贝叶斯归纳逻辑模式,这种判断模式能很好解释人类的概率判断行为。
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对合取谬误的任务情景进行分析,划分为结构良好的任务情景和结构不良的任务情景,而结构良好的任务情景具备必要的概率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判断可以用理性和非理性区分。此外,还应该从进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根源进行分析和探讨。
刘立秋,陆勇.(2007).Linda问题:“齐当别”抉择模型的解释.心理科学进展,15(5),735–742.
徐英瑾.(2014).从演化论角度为 “合取谬误”祛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110–118.
Agnoli,F.,&Krantz,D.H.(1989).Suppressing natural heuristics by formal instruction:the case of the conjunction fallacy.Cognitive Psychology,21(4),515–550.
Aristidou,M.(2013).Irrationality re-Examined:A few comments on the conjunction fallacy.Open Journal of Philosophy,3(2),329–336.
Bonini,N.,Tentori,K.,&Osherson,D.(2004).A different conjunction fallacy.Mind&Language,19(2),199–210.
Bovens,L.,&Hartmann,S.(2003).Bayesian epistemology.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ssotti,M.,&Moutier,S.(2010).How to explain receptivity to conjunction-fallacy inhibition training:Evidence from the Iowa Gambling Task.Brain and Cognition,72(3),378–384.
Charness,G.,Karni,E.,&Levin,D.(2010).On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New experimental evidence regarding Linda.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68(2),551–556.
Connolly,A.C.,Fodor,J.A.,Gleitman,L.R.,&Gleitman,H.(2007).Why stereotypesdon’teven makegood defaults.Cognition,103(1),1–22.
Crupi,V.,Fitelson,B.,&Tentori,K.(2008).Probability,confirmation,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Thinking&Reasoning,14(2),182–199.
Davies,J.B.,Anderson,A.,&Little,D.(2011).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so-called conjunction fallacy.Current Psychology,30(3),245–257.
Devetag,G.,Ceccacci,F.,& De Salvo,P.(2013).Do reputation concerns make behavioral biases disappear?the conjunction fallacy on Facebook and mechanical Turk.Cognitive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Laboratory,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Trento,Italia.
Dulany,D.E.,& Hilton,D.J.(1991).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conscious representation,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Social Cognition,9(1),85–110.
Erceg,N.,&Galić,Z.(2014).Overconfidence bias and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edicting outcomes of football matche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42,52–62.
Fantino,E.,Kulik,J.,Stolarz-Fantino,S.,&Wright,W.(1997).The conjunction fallacy:A test of averaging hypotheses.Psychonomic Bulletin&Review,4(1),96–101.
Feeney,A.,Shafto,P.,&Dunning,D.(2007).Who is susceptible to conjunction fallaciesin category-based induction?.Psychonomic Bulletin&Review,14(5),884–889.
Fisk,J.E.,&Pidgeon,N.(1998).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potential surprise,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tion A:Huma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51(3),655–681.
Franco,R.(2009).The conjunction fallacy and interference effect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53(5),415–422.
Gavanski,I.,&Roskos-Ewoldsen,D.R.(1991).Representativeness and conjoint probabilit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61(2),181–194.
Gigerenzer,G.(1996).On narrow norms and vague heuristics:A reply to Kahneman and Tversky.Psychological Review,103(3),592–596.
Hartmann,S.,&Meijs,W.(2012).Walter the banker:The conjunction fallacy reconsidered.Synthese,184(1),73–87.
Hertwig,R.,Benz,B.,&Krauss,S.(2008).The conjunction fallacy and the many meanings ofand.Cognition,108(3),740–753.
Jarvstad,A.,&Hahn,U.(2011).Source reliability 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Cognitive Science,35(4),682–711.
Jönsson,M.L.,&Assarsson,E.(2013).Shogenji’s measure of justification and the inverse conjunction fallacy.Synthese,190(15),3075–3085.
Li,S.(2004).Equate-to-differentiate approach:An application in binary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12(3),269–294.
Marks,D.F.(2000).The psychology of the psychic(2nd Ed.).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Moro,R.(2009).On the nature of the conjunction fallacy.Synthese,171(1),1–24.
Morsanyi,K.,Handley,S.J.,&Evans,S.B.T.(2010).Decontextualised minds:Adolescents with autism are less susceptible to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than typically developing adolescents.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40(11),1378–1388.
Moutier,S.,&Houdé,O.(2003).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and conjunction fallacy inhibition training.Thinking&Reasoning,9(3),185–201.
Nilsson,H.,&Andersson,P.(2010).Making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appear possible:Effects of conjunction fallacies in evaluations of bets on football games.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1(2),172–180.
Nilsson,H.,Rieskamp,J.,&Jenny,M.A.(2012).Exploring the overestimation of conjunctive probabilities.Frontiers in Psychology,4,101–112.
Pennycook,G.,Trippas,D.,Handley,S.J.,&Thompson,V.A.(2014).Base rates:Both neglected and intuitiv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40(2),544–554.
Rogers,P.,Davis,T.,&Fisk,J.(2009).Paranormal belief and susceptibility to the conjunction fallacy.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3(4),524–542.
Rogers,P.,Fisk,J.E.,&Wiltshire,D.(2011).Paranormal belief 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Controlling for temporal relatedness and potential surprise differentials in component events.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5(5),692–702.
Schupbach,J.N.(2012).Is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tied to probabilistic confirmation?.Synthese,184(1),13–27.
Shogenji,T.(2012).The degree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 and the conjunction fallacy.Synthese,184(1),29–48.
Stolarz-Fantino,S.,Fantino,E.,&Kulik,J.(1996).The conjunction fallacy:Differential incidence as a function of descriptive frames and educational context.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21(2),208–218.
Tentori,K.,Bonini,N.,&Osherson,D.(2004).The conjunction fallacy:A misunderstanding about conjunction?.Cognitive Science,28(3),467–477.
Tentori,K.,&Crupi,V.(2012a).On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and the meaning ofand,yet again:A reply to Hertwig,Benz,and Krauss(2008).Cognition,122(2),123–134.
Tentori,K.,&Crupi,V.(2012b).How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s tied to probabilistic confirmation:Some remarks on Schupbach(2009).Synthese,184(1),3–12.
Tentori,K.,Crupi,V.,&Russo,S.(2013).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onjunction fallacy:probability versus inductive confirm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142(1),235–255.
Tversky,A.,&Kahneman,D.(1983).Extensional versus intuitive reasoning:the conjunction fallacy in probability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90(4),293–315.
Tversky,A.,&Koehler,D.J.(2004).Support theory:a nonext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e probability.Preference,Belief,and Similarity–Selected Writings Amos Tversky.MIT Press,Cambridge,MA,329–376.
von Sydow,M.(2011).The Bayesian logic of frequency-based conjunction fallacie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55(2),119–139.
Wedell,D.H.,& Moro,R.(2008).Testing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conjunction fallacy:Effects of response mode,conceptual focus,and problem type.Cognition,107(1),105–136.
Wolford,G.,Taylor,H.A.,&Beck,J.R.(1990).The conjunction fallacy?.Memory&Cognition,18(1),47–53.
Wolf,K.(1991).The schoolteachers'portfolio:Issues in design,implementation,and evaluation.Phi Delta Kappan,73(2),129–136.
Zizzo,D.J.,Stolarz-Fantino,S.,Wen,J.L.,&Fantino,E.(2000).A violation of the monotonicity axiom: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conjunction fallacy.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41(3),263–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