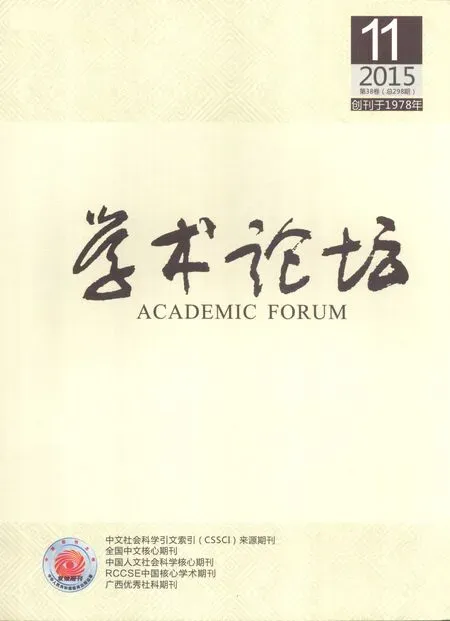老庄与现代纯诗
2015-02-26雷文学
成 杰,雷文学
作为破除传统、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现代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诗歌作为现代文学的“排头兵”,在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走在最前列,因而相较小说、散文和戏剧而言,诗歌更为深刻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 但诗歌作为所有文学中最具潜在精神的形式,它必定也最内在地体现了本民族的思想传统,正如艾略特所说:“没有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传统。 ”[1](P87)作为我们民族文学中最值得骄傲的古代诗歌, 曾受到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成就古诗辉煌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庄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现代诗歌。 在关于诗的本质、诗人修养、诗人思维方式、审美追求等四个方面,老庄思想均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现代纯诗论者。
一、反功利、天地一体的现代纯诗观
活跃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月、象征、现代诗派是对初期白话诗和功利诗派的反动而出现的。在黑云压城的旧中国现代社会,诗歌和其他一切文艺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担当起启蒙、救亡的社会使命。 但过分的功利性造成对诗美的伤害,使得诗歌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初期白话诗粗糙的形式也令诗坛失望。 在这种形势下,纯诗观应运而生。
现代纯诗主要以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为代表,但它的萌发远早于新月、象征派,也不止于现代派。 我们从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里提出的文学“无用之用”说,五四诗坛郭沫若和周作人对功利的批判,宗白华等人充满意境美的小诗创作,再到20 世纪40 年代中后期以“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为特征的“九叶诗派”,都可以听到这种纯诗观辽远的呼唤和回响。 几乎可以说,对“纯诗”的追求伴随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每一个步伐。
“新月派”是第一个成功地为新诗制定游戏规则的诗歌流派,它以主张格律闻名于诗坛,其纲领性的宣言首要的一条就是“本质的醇正”,作品要做到像“无瑕疵的白玉,和不断锻炼的纯钢”[1](P148),显示了他们对纯粹诗意的追求。 这种追求的前提也是破除诗歌的功利目的。 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主张把“善”从诗歌中剔除,以为使人向善只是道德家、政治家、哲学家等的目标[2](P126)。这是破除社会的功利目的。 闻一多更从“史”的角度清除诗歌中形形色色的功利观:“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 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3](P356)这种对“纯粹”诗意的追求,不但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形式上。 诗人们对格律的追求,也是为了加强这种诗意的纯粹, 如陈梦加说:“限创或约束,反而常常给我们情绪伸张的方便。 ‘紧凑’所造就的利益,是有限中想见到无限。 诗的暗示,捡拾了要遗漏的。 ”[1](P149)徐志摩也说:“音节的本身还得起原于真纯的‘诗感’。 ”[1](P133)新月派诸人均留学欧美,这种纯粹诗观是学习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影响的产物。 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他们相信这种纯粹“在东方一条最横蛮最美丽的长河”[1](P146),他们这种反功利、对纯正诗感的追求显然受到老庄的影响。 除庄子的“无用之用”论外,庄子追求人性之纯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他们。庄子从其自然人性观出发,反对种种社会规范对人性的伤害, 视仁义和种种对外在功名的追求为道德上的“骈拇枝指”,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4](P244)。这种反外在功名的纯美人性和反外在功利的纯正诗感在逻辑上的关系一目了然。
纯诗观由穆木天、王独清等象征派诗人正式提出,目的是反拨早期白话诗创作的粗糙。 穆木天主张:“我们的要求是‘纯粹’诗歌。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 我们要求是‘诗的世界’。 ”[1](P94)王独清起而响应:“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 我觉得有倡poesie pure 的必要。”[1](P106)他们提出要纯粹的诗的世界,以与散文的世界相区别。 他们认为,散文是说明的,而诗是暗示的。 他们的策略是,强化文字的音乐和图画的功能,用文字刻画形象,用声律强化这种形象,以暗示出一个纯粹的诗的世界。 “纯诗能在形体元素即‘音乐’和‘色彩’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暗示力。 ”[5](P95)这种策略宗白华已经注意到了:“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 ’”[1](P29)穆木天明确主张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1](P98),王独清则用一个公式来表达:(情+力)+(音+色)=诗[1](P104),表现了他们共同的信念。
他们要达到何种“诗的世界”呢? 穆木天说:“诗要暗示出内生命的深秘。 ”“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是诗的本能。 ”[1](P99)穆木天等人显然对诗有超过诗艺本身的哲学追求, 他们以此开拓诗的境界。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哲学精神源自何处。 穆木天深受保尔·瓦雷里的影响:“这个世界被封闭在我们内心”,“纯诗世界”是与现实完全绝缘的。 但是,也正如穆木天所认识到的,“象征是对于另一个‘永远的’世界的暗示”[2](P231)。 这个世界即是西方以意志冲动为特征的形而上世界,是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另一个精神世界。 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中国自然哲学显然不是这样一种哲学背景,穆木天等人要想用象征手法“暗示”出这样一个西方式的超验世界不太现实(这需要更为充足的历史条件),其作品也没有显示出此种暗示。 那么,他们纯诗的世界唯一的可能就是来自于本民族老庄的自然哲学。 这一点被稍晚的现代派诗论家梁宗岱道出。
梁宗岱是不遗余力在中国推广象征主义的理论家, 他是从象征主义来理解纯诗的:“这纯诗的运动,其实就是象征主义的后身。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的形体的元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而超出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 ”[6](P80)可以看出,纯诗的目的是要超越我们的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境界,这正是用老庄思想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诗学理想(“吾游心于物之初”)[4](P306)。 梁宗岱坚持认为,中外诗学中“绝对”“纯粹”的诗艺,和“绝对”“纯粹”的道的本原,其实是一回事。 当然,在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梁宗岱还来不及辨别中外哲学精神之异,他只是注意到二者之同;而理解这种“同”,他只能运用潜藏在自己潜意识中的民族哲学——实际就是道家哲学。 梁宗岱对象征所达到的境界这样理解:“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6](P62)“恰如春花落尽瓣瓣的红英才能结成累累的果实,我们正因为这放弃而获得更大的生命,因为忘记了自我的存在而获得更真实的存在。 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引用到这上面是再恰当不过的。 ”[6](P63)可以看出,这其中内在的精神是道家哲学的天地一体、万物齐一的观念。 事实上,梁宗岱打出的是西方诗学的旗号,而他的思想实质和思维方式体现的却是民族的道家哲学——万物本性的同一给他提供了象征诗学的哲学依据。
可见,没有真正西方哲学精神支撑的中国现代诗学,往往只能回到本民族的哲学。 中国现代诗人并非不注重西方宗教哲学思想的学习,但要想在短期内进入另一种异质文化的核心——形而上学,则显然并非易事。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对西方宗教哲学的学习往往不同程度地停留在较浅的层次。 所以鲁迅批判章太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是高妙的幻想[7](P69),批判的正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里貌习宗教以为己用的不可能, 也暗示了真正的哲学宗教精神不易得。 因而,中国现代诗学对传统精神的回归成为必然。
二、强调宇宙意识和自然观念的人格修养
注重人格的修养是中国诗人的传统,所谓“诗品出于人品”。 现代诗人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宗白华认为要作好诗就需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做诗人人格的涵养……一方面要作诗底艺术的训练。”[1](P29)如何进行人格修养?纯诗论者重在两个方面: 培养宇宙意识 (实际是哲学意识);在自然中活动。
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认识到民族哲学的不足。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大有逊色”[8](P8)。 哲学诗歌往往相通,哲学的状况必会影响诗歌的品质。在中西诗学大碰撞的时代氛围下, 中国诗论家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 胡适认为“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9](P68)。 朱光潜认为中国诗不能达到深广之境界,原因是“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操的淡薄”[10](P91)。西方象征派、现代派诸诗人如波特莱尔、魏尔伦、艾略特、瓦雷里等人本身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他们的诗歌也因为哲学意识的渗入而具有博大幽深的境界。 受他们影响的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人和诗论家纷纷强调要加强诗人的哲学修养,或称之为“宇宙意识”。
闻一多对宇宙意识的关注在现代诗人中是突出的。 在《宫体诗的自赎》中,他认为,诗人“悟得宇宙意识”,才能创作出最佳的作品。 而所谓“宇宙意识”,也就是“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3](P19-20)。这种道家式的“永恒”意识闻一多主要是通过对庄子的研究而获得的。 他曾精心校释《庄子》内篇,还写有探讨庄子思想的论文《庄子》和《道教的精神》。 在主要探讨庄子文学色彩的论文《庄子》中,闻一多明显对庄子的思想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 ”[3](P282)闻一多向往庄子“道”的境界,他把庄子的追求“道”看成游子思归,其中不难看出他本人的大宇宙回归意识。他钦慕《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原因就在于这首诗“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3](P21)。这种意识也浸透在他的诗歌如《奇迹》《李白之死》《剑匣》里。
“宇宙” 一词在宗白华的诗学中也频频出现。他的“艺术境界”就是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11](P2)。 艺术关系到宇宙境界和自我心灵,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三者乃是养成健全的诗人人格的必由之途[1](P31)。这当中,“哲理研究”处于首位。他的“哲理研究”是以庄子和禅宗为主的,而禅宗正是老庄思想改造过的中国佛教。 影响宗白华艺术观的主要还是庄子, 他反复强调庄子最具艺术天才,“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11](P9), 认为中国艺术意境的创造“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11](P10)。
康白情的诗人修养观与宗白华接近,他认为:“诗是主情的文学;诗人就是宇宙的情人。 那么要作诗,就不可不善养情。 ”[1](P43)他把诗人称作“宇宙的情人”,那么他的“养情”养的就不是一己之情,而是与宇宙相关的“大情”了。 中国首部新诗史的作者张秀中注意到了他们的诗人修养理论,并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哲理的研究”。 他反对一些人把诗歌和哲理对立的态度,认为哲学和诗歌相通,“全是以透视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使命”,“没有一位大诗人,不是同时又是一位很渊博的深致的哲学家的”[12](P27);并引用湖畔诗人古列利支的话说:“哲学者不是歌的诗人, 诗人是歌的哲学者”[12](P27),因而强调诗人要“要穷究宇宙奥蕴”[12](P27)。
中国现代诗人哲学意识的觉醒是受西方哲学刺激的结果,但最终回归到民族的自然哲学。 纯诗论者纷纷强调诗人要有“宇宙意识”,要注重“哲理研究”,实际上是用现代哲学术语表达的对古老哲学的信仰。
“在自然中活动” 是现代诗人加强人格修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老子、庄子在创造他们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时,把“自然”置于至高的地位,所谓“道法自然”。 自然的含义是“自然而然”,不能等同于作为物质世界的“自然界”,而是与“人为”相对的哲学范畴。 但老庄的这一自然观为中国诗人的“回归大自然”提供了哲学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老庄虽然倡导自然, 但并没有倡导过回到自然隐居,没有直接赞美过作为山林平原等的“自然界”。很多学者引用庄子的“山林欤! 皋壤欤! 使我欣欣然而乐欤”证明庄子赞美过大自然,其实不对。实际是庄子“拟世人赞叹山林、 平原可供游玩的快乐”[4](P335),批评世人不能超越哀乐,“直为物逆旅耳”[4](P336), 将上述引言当成庄子赞美大自然是断章取义的结果。道家的自然范畴与“大自然”的结合,成为中国人回归自然的哲学依据是魏晋时候的事[10](P88)。魏晋老庄思想的复兴不仅极大开拓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更引起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极大兴趣。 心物的相互发现、相互映射、相互表征渐渐形成中国诗歌独具民族特色的意境美,为中国古诗的辉煌作出巨大贡献。
“自然”对诗学的重要意义也受到现代诗论家的注意。 孙作云意识到“东方的诗是以自然为生命”[1](P229)。强调向自然学习、在自然中锻炼诗人的人格成为纯诗派诗论家的共识。 对这个问题注意最早又论述得最充分的当数宗白华。 在《新诗略谈》里,他认为“诗人最大的职务就是表写人性与自然”[1](P30-31),所以,要养成诗人人格,除“读书穷理外”,最重要的是两种活动,第一就是“在自然中活动”。 为什么诗人要在自然中活动、培养自己的人格? 宗白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第一,自然是“诗境诗意”的范本,他认为“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感觉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声的乐谱”[11](P21), 而花草的精神和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 所以在自然中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 第二, 自然是构成意境的重要元素, 认为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 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11](P21)。 宗白华对“意境”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对自然在诗境中的重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 故特别强调诗人在自然中修养人格; 他自己的创作经验也印证了自然人格的重要性——因与自然的相通而获得创作心境, 如他介绍《流云小诗》的创作心境时说:“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条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 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 ”[11](P177)
宗白华的理论受到后来诗论家的重视。 康白情在谈到“养情”的方法时,认为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件事就是“在自然中活动”,原因是作诗所必须的感兴“就是诗人底心灵和自然底神秘互相接触时,感应而成的”[1](P48),强调“人心”和“自然”的接触时才能生“感兴”;并在论述时引用了上述宗白华自然是“诗意诗境的范本”的原话,表明他和宗白华的一致。 这种一致在新诗史论家张秀中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更强调“作诗就要靠感兴;感兴就是诗人的心灵和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的时候感应而成的,所以欲使感兴常生,就不能不常接触自然。 ……自然是一切艺术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陶炼厂了”。 “诗人最大的职务,就是表写自然与人性。”[12](P29)这些几乎就是康白情、宗白华的原话了。
三、冥合自然的比兴思维
从创作手法上讲,“象征”可谓是中国现代诗坛从西方引进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象征是西方象征派、现代派最重要的手法,因而尤其受到中国现代纯诗论者的关注,他们在思考这一外来品时,多以中国传统诗歌艺术手法与之类比。 这种类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西诗学共同的艺术规律,但同时也陷入某种理论误区。 这在初期的文化交流中是可以理解的。 在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现代纯诗对象征的某种误读实则是在创作手法掩盖下深层诗学思维方式的不同——象征和中国传统的赋、比、兴,表面上看是艺术手法,深层看则是艺术思维方式。
周作人很早就注意到“象征”,以为这一来自国外的手法就是中国的旧手法“兴”,而兴“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是象征”[13](P222-223)。 朱自清也认为“暗示”是这一派诗作的生命,而暗示就是“含蓄”,就是“曲”,也就是传统的“比”“兴”[14](P171-172)。 在《说鱼》中,闻一多也将象征与古典诗歌的“兴”“象”相等同。 朱光潜则认为:“所谓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 ……象征最大的用处,就是把具体的事物来代替抽象的概念……象征的定义可以说是:‘寓理于象。 ’”(《谈美》)梁宗岱不同意朱光潜的观点,认为他把文艺上的“象征”和修辞学上的“比”混为一谈,他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6](P54)。宗白华也认为 “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 (比兴的)手法才能传神写照”[11](P116)。 从上述可以看出,如果忽略理论家在细节上的分歧, 则他们实际上均认同象征等同于“比”“兴”。 但这种认同失之笼统,没有细辨象征与比兴不同的精神分野, 没有细辨“比”“兴”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实际。
作为《诗经》“六义”的两个要素,“比”“兴”最初只是创作手法,为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服务,在作品中只占有局部地位,正如朱熹所说:“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诗集传》)刘勰的看法也是同样的意思:“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 ”“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理以比事。 ”(《文心雕龙·比兴》)但这种状况不是不变的。 到了魏晋,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儒家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自两汉之间从印度传入的佛家思想开始兴盛,传统的道家思想也借此复兴,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中国诗学精神发生深刻变化。 《诗经》时代作为比兴之物,只是与诗人主观情志有某种微妙关联的外物,与情志还是两种不同的“物”,其与情志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目了然。但自晋宋以来,随着山水诗的出现和发展,自然景物的描写不仅在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且逐渐“人化”,与诗人的主观情志相融合,使情与景逐渐成为合二而一的东西。 钟嵘从理论上这样解释“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诗品序》)他看出了情景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微妙神奇的诗学效果,这就改变了“将‘兴’仅视为表现手法的旧谈,从而涉及到艺术的根本特征”[15](P163)。 周作人等人将象征视作“兴”,显然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与《诗经》时代的“兴”已大不相同。 因为正如梁宗岱所说,象征应用于作品的整体,关系到作品的整体意义,这一点就类似于钟嵘的“兴”的功能。 所以,只有联系魏晋时代的思想背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梁宗岱等人将象征等同于“兴”。
梁宗岱等人虽然看出象征与“兴”的共同点,但显然还没有看出它们的不同。象征与比兴由不同的文化孕育,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与精神走向。
从哲学上讲,象征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诗人对世界人生的超验觉悟;而中国哲学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超验的世界,中国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共同本性,表达的只是对自然的体悟,因而“‘兴’的本质是诗人一瞬间返回‘天人合一’状态的微妙体验”[16](P30)。
从思维机制上讲,“‘兴’的启动须‘致虚极,守静笃’,‘涤除玄览’,以平和宁静的心灵观照大千世界;‘象征’ 的思维却充满了亢奋和宗教化的迷狂”[16](P30-31)。
从技术操作上说, 象征和比兴都暗示出一个精神世界, 但象征所暗示的精神已经舍弃了所用来象征的物象,目的在另一个世界,尽管这用来象征的物本身仍具有自己独立的美;而“兴”所暗示的精神就在于物本身,在自然本身,物和人构成不二的世界。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比兴的哲学依据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庄子·齐物论》)的道家哲学,中国现代纯诗论者所谈及的象征,实际上是传统的比兴思维。 他们的诗学取道西方的象征主义又间接地回到老庄哲学冥合自然的思维方式。
四、对意境美的追求
随着五四草创期新诗创作阶段的结束,中国新诗何去何从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向西方诗歌学习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将目光投向传统诗学。 卞之琳以为, 在白话新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之后,就应当接通我国诗歌的传统和文化遗产[17](P64)。这些文化遗产如“性灵、神韵、意境等等重新成了人们自觉追求的目标”[16](P20)。比如,胡适就非常赞赏温庭筠、姜白石等人的诗词意境。 宗白华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新诗:“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1](P29)废名认为:“现代诗是温、李这一派的发展”[16](P87),表明现代诗对温、李诗歌意境美的继承。朱湘坚持“无论自由诗,还是有韵诗,都应该注重‘意境’的创造”[2](P178)。孙作云则认为“中国的现代派诗……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意境”[1](P227)。
意境作为古诗的核心范畴,其产生与老庄思想息息相关。 在晋宋之际,已经产生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有意境美的诗歌,而意境理论也相应在南朝萌芽如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并随着后来唐诗创作的繁荣而出现并走向成熟。意境产生的哲学背景是包含老庄哲学复兴在内的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的兴盛。 意境产生的哲学基础正是老庄哲学。 两汉之交的佛学东渐也在魏晋南北朝时影响了意境的诞生,那正是民族哲学改造外来佛学的结果。 学界倾向于认为意境理论的思想渊源是老庄哲学:“意境说是以老子美学 (以及庄子美学)为基础的。 离开老、庄美学,不可能把握‘意境’的美学本质。 ”[18](P276)“意境就是庄子游心哲学的美学实现。”[19](P24)具体说,老庄哲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意境的产生:
第一,“道”论是意境理论的哲学基石。 在老庄看来,“道”不仅是“万物之宗”,而且贯穿于宇宙万物。 万物都是“道”的体现,因而本质上并无差别;人也和万物一样,只是宇宙之一员,同于万物。 “庄周化蝶”的寓言暗示人与物不分即“物化”的境界,这种境界正是意境的两个要素“意”和“境”(或曰“情”和“物”)交融不分的哲学依据,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
第二,“言意之辨”启示意境的操作机制。 由于“道”本身虚实难辨,老庄均认为用语言把“道”说清楚是不可能的,所以老子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56 章》;庄子也认为“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4](P199)。作为这一矛盾的解决,庄子提出著名的“筌蹄之喻”,强调“得意忘言”。 言意之间的矛盾使得老庄不过分看重言而强调对言后之意的把握,这给古诗创作以启示。 中国古诗创作强调要超越文字,传达出文字背后的丰富意蕴,所谓“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吸收。
第三,有无虚实之论启示意境虚实相生审美效果的创造。 在老子看来,“无”本是“道”的特性,甚至可等同于道。 “无”并非没有价值,只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比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11 章》)。 所以他强调“有无相成,虚实相生”。 庄子同样认为“无”之中大有深意:“视乎冥冥,听乎无声。 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 ”[4](P162)这种有无相生相成的特性其实就是一种高妙的艺术,中国画的“计白当黑”、音乐的“此处无声胜有声”正体现了这种艺术奥妙。 王夫之评古诗“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认为其“墨气所射,四表无穷”,即是诗歌当中这种艺术胜境的体现,所谓“无字处皆其意”(《董斋诗话·诗绎》)。 这种境界一直被历代诗论家津津乐道,严羽所谓“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司空图所谓“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均表达了这种理想。
在老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意境的这三个特点同样为现代诗人所认可。 诸多理论家注意到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或融合,宗白华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11](P3),意境不是纯客观地、机械地描摹自然,而在于主体的心性,即他引用米芾的话所言“心匠自得为高”[11](P6),“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11](P5)。 朱光潜的看法类似:“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 ”“‘即景生情,即情生景’。 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 ”[11](P5)梁宗岱这样论象征:“所谓象征,只是情景的配合,所谓‘即景生情,即情生景’而已。 ”[6](P56)“象征之道也可以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 ”[6](P59)这实际上是用西方理论术语道出了中国意境的特征。 对丰富而含蓄意蕴的追求也是现代诗人追求的目标。 宗白华要借意境“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20](P70)。 梁宗岱认为象征有两个特性,其二就是“含蓄或无限”[6](P57)。 同样,对超越具体形象的艺术幻境的追求,现代诗人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宗白华的意境就是要“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以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20](P70)。
这样,老庄思想通过意境这一中介又把传统文化的乳汁输给了现代诗人。
[1] 杨匡汉,刘富春.中国现代诗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2] 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4] 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6] 梁宗岱.梁宗岱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7]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6.
[9] 龙泉明,邹建军.中国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10] 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11] 宗白华.艺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2] 草川未雨(张秀中).中国新诗的昨日今日和明日[M].上海:上海书店,1985.
[13] 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14]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4)[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5] 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6] 李怡.中国现代诗学与古典诗歌传统[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7] 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2.
[18]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9] 薛富兴.意境: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理想[ J].文艺研究,1998,(1).
[20]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