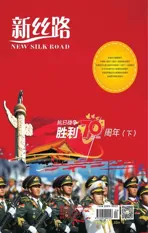从田小娥与白灵的形象分析陈忠实男尊女卑思想
2015-02-25常翠岩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常翠岩(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从田小娥与白灵的形象分析陈忠实男尊女卑思想
常翠岩(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7)
陈忠实的一部《白鹿原》,被作者自己誉为可以在棺木中当“砖头”来枕的作品,其中各种形象都深入人心,而《白鹿原》中以田小娥为代表的众多女性形象尤其令我辈唏嘘!无论是被称为“荡妇”的田小娥还是白鹿化身的白灵。作者笔下这两位命运截然不同的女性,却反映了男性作者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本文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西蒙·波伏娃的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作者在作品中这两位女性形象塑造中的男尊女卑思想。
集体无意识;“魔鬼”;“天使”;男尊女卑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里,陈忠实坦诚自己是读着厚厚的县志,在四、五个卷本里看到贞妇烈女的名字和事迹,“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躁姓氏的耐心。”,于是在叹惋这些女性的悲哀中,陈忠实有了逆反心理,给与县志上后来连真实姓名也无,甚至在大同小异的守寡故事里,贞节牌坊下的密密麻麻的名字注目礼,而且恶毒的涌现了一个从民间故事和笑话里听取的荡妇淫娃中塑造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着反抗着的形象——田小娥形象的写作意念。作者从创作的本源上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被迫的,反传统的道德的“荡妇”,以突出对县志里女性命运的抗议,以表达自己对父权统治下的女性命运的同情!那么作为一名男性作家,给与女性这样的同情与悲悯,已经很人道了,或者说塑造田小娥本身就带有很明显的女性解放的意味,可是笔者在田小娥的命运中,却只能看出男性作者集体无意识下流露的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西蒙·波伏娃说在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只有两种特征:温柔、聪明、正义、牺牲自我、无欲无求、完全依赖男人而活的母亲形象的“天使”和追求自由、反抗、自私、顺从自己心里欲望的“魔鬼”。田小娥就是作为男性作家眼中的“魔鬼”的形象。而白灵就是“天使”!
一.“魔鬼”形象的田小娥
田小娥,被父亲送去将军村的郭举人家里充当小妾。她的悲惨命运也是由此开始。在郭举人家里,她是“泡枣的工具”。一个月一次有大房在窗口偷听的夫妻之事,并且家里洗衣做饭都得做,另外她的重要作用甚至不是传宗接代,这样一个大部分封建家庭女性的悲剧命运——生育的工具,而是“泡枣的工具”,为了给郭举人延年益寿的工具,这就为她后来的反叛,甚至为她后来成为“荡妇”,埋下了伏笔。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女子却地位如此低下,也没有文化。她父亲虽然是个秀才,但是对她的教育也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不具备成为“天使”的可能性,而却具有“荡妇”的潜质。她能反抗的资本只有自己的身体。
1.美貌。书中写到田小娥的美。是通过白嘉轩“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我看了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趁早丢开,免得后悔。”鹿三已经按捺不住“你嘉轩叔说的全是实话好话!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通过这两位白鹿原上的最有仁义道德的“君子”的评价,还通过鹿冷氏的嫉妒衬托出,田小娥的美貌。不守妇道,和黑娃在一起使得黑娃不能光明正大的进入祠堂,从鹿三这些人来看,美貌的田小娥就是“魔鬼”。而后来鹿子霖上了她的床,也是因为她美貌。成功勾引白孝文,把他从白鹿两家的族长变成了抛弃妻子和沿街乞讨的败家子,也是因为她的美貌。她就是一典型的“红颜祸水”的“魔鬼”。
2.性。是性让田小娥选择了黑娃,也让黑娃上了田小娥的床。两人之间要说爱情,实在是牵强。鹿子霖利用性,让田小娥相信自己会帮她让黑娃回来,所以心甘情愿的成为鹿子霖手中的工具。后来她成功勾引了白孝文,也是因为性。她在白鹿原里的大部分生活都和“性”相关,被迫或者她主动,因为和她发生“性”,相关的人都是道德被谴责的一方,而她更是万夫所指!所以田小娥死了以后,黑娃后来和白孝文握手言和,可以重新进入祠堂,白孝文当了县长。没有她这个魔鬼,黑娃和白孝文还是白鹿原上大家尊重的人物。
3.“厉鬼”。作者让田小娥死后鬼魂不散,附身鹿三,诉说自己的不幸,"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捧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任谁读到这里,都不能不为田小娥不幸的悲剧而动容,这是作者比窦娥的夏雨雪,血染白练,大旱三年更冤屈的诉说。看看作为白鹿原仁义典范的白嘉轩的回答"你是个坏东西,我处治你我不后悔。你活着是个坏种,你死了也不是个好鬼。你立刀把我整死,我跟你到阴家去打中。阎王要是说你这个婊子在阳世拉汉卖身做得对,我上刀山我下油锅我连眼都不眨!"在男尊女卑的思想模式里,女性的欲望的正常需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成为“荡妇”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死后还要被造的塔镇住,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一个从封建大家庭出走的小妾的“魔鬼”形象,就是所有男性作家潜意识身体向往而理智下会排斥的女性形象。而作者正是通过白嘉轩,来完成对田小娥的这个魔鬼的愤恨和诅咒,以及镇压。
二.“天使”形象的白灵
白灵,白嘉轩唯一的女娃,从小被白嘉轩宠溺的女孩。所以她没有经历缠脚的痛苦,却可以进入西安学习,可以在父亲把她锁在家里以后逃婚,甚至自己给婆家写信退婚,这样一个美丽、聪明、大胆、执拗的女子,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叛逆者,却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多次选择中,选择了革命、崇高、正义,而对于自身幸福和快乐无欲无求。
1.革命者的形象。
与田小娥不同,白灵一开始就有更多自主的权利,还有一向严苛的儒家卫道士白嘉轩的疼爱,所以白灵人性得以正常成长,而且叛逆的方面更多,她不用用传统女性唯一的武器——身体去反抗周围的不公,她得天独厚的有很多美好的品质,最后不惜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彻底与家庭决裂,走向革命。与旧恋人决裂走向革命。一个可以向国名党高官抛砸砖头的女革命者,她的形象比较高大,比较有气魄。具备了“天使”的天分!
2.牺牲自我。
白灵与鹿兆海青梅竹马,相知相爱,最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道路上的选择中分道扬镳。这是她在爱情和革命中,牺牲了爱情,选择了革命,这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做到的。给鹿兆鹏打掩护,扮假夫妻,对于革命领导人的崇拜,对于革命事业的投入,最后真的成了鹿兆海的妻子,这是她又一次的牺牲,牺牲自己的贞洁与名誉,选择了崇高。她在延安革命内部的“清洗”中,正义与妥协中,她选择正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她成为了烈士!烈士的死,又代表着新的革命的孕育。表面看来她死于偶发事件,但是封建制度对于自己的叛逆者从来不心慈手软,革命内部的“大清洗”本身就是封建势力的另一个表现而已。另外在男性社会里这样一个可以和男性平等的女性形象就是死在自己为之奋斗的革命的内部“清洗”之中,从这点来说,很多人比较认同作者是对革命的思考,也是加深对现实的批判意味!但是从男尊女卑这点来分析的话,可以看出作者骨子里的对于“天使”般女性定义,如果没有牺牲,如果没有高尚,如果没有悲剧,何来“天使”!
3.“白鹿”的化身。
白灵生的时候的吉兆;“……临进厦屋门时,头顶有一声清脆的鸟叫,她从容地回过头瞥了一眼,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
白灵死的时候的托梦;“……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我答应了一声,就惊醒来了……”
白鹿原,是作者笔下人物生活的场景,也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而白鹿原的得名是一只精灵——“白鹿”。作者把农耕社会里的土地的形象,那种熔铸在血液与灵魂里的精神,赋予一只活波跳跃的精灵里,而让白灵成为白鹿原上“白鹿”的一个代表。(当然神乎其神的朱先生也被作为白鹿原上的“白鹿”的化身。)而白灵作为白鹿原上成长起来的女英雄,作者赋予了这样一个不凡的诞生和死亡。她不是传统意义上一味温顺的作为丈夫附属品的“天使”,作者让白灵不同于传统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中会注重家庭,而让白灵选择了革命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放弃爱情,放弃家庭,放弃名誉,视死如归,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一个男性作家笔下的理想的“天使”的形象。
三.从女性主义和集体无意识的范畴看陈忠实的男尊女卑思想。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指出文艺作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自觉意识的控制,而常常受到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的影响。
所以在陈忠实努力为田小娥鸣冤的同时,他自己无可遏抑的把她又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一个会无意就毁掉黑娃和白孝文的人,甚至会阴魂不散,会夺人性命的,为自己报复整个白鹿原,而不是逆来顺受的面部不清的小妾,受气包,或者一般的荡妇淫娃。在“黄土”文化中孕育出的陈忠实,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由于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会不自觉的就把笔下的女性分为两类,“魔鬼”和“天使”。尽管陈忠实是“对抗”县志里的贞女烈妇写下田小娥,这个被男人作为没有人的属性,只有肉体的存在,让很多男人都会轻易得到又不忠于任何男人的形象,正是作者潜意识里对女性的一种认识,既然不是贞洁的“天使”、必然是“魔鬼”!
西蒙·波伏娃认为“每一位作家描绘女性的时候,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就会流露出来。在女性形象上,经常不由自主的暴露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梦想之间的裂隙。”,“男性作家都以独有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集体神话:将女人等同于完全的肉体,男人的肉体从母亲的体内出生,又在情人的怀抱中得以重生。这样,女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在于她体现了自然:血的峡谷、盛放的玫瑰、海中的妖女、山中的灵魅,男人视她们为沃土、元气、事物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掌管诗歌,成为人世和彼岸天国的桥梁;……她明确注定的被限制的存在,她正是以被动性成为和平与和谐的代表,如果她们拒绝这一角色,就会成为“祈祷的螳螂”,食人女妖。……”
田小娥的悲惨命运的一开始,在封建的妻妾制度里,她只是一个“工具”的“物”的存在。和黑娃在一起,是因为“性”,是田小娥作为“肉体”的存在。那么她在后面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她就是被作者设定为贞洁牌坊的对立面,一个“荡妇淫娃”!尽管作者也写了田小娥的无辜、她的善良、她的无奈和困境,但是不受男人掌控(背着郭举人和黑娃偷情),甚至想要掌控男人(变成厉鬼附身鹿三,让白鹿原瘟疫横行),她在世人和作者的眼里就是一个“魔鬼”。即使不是自己选择成为魔鬼,但是她就是一个需要被挫骨扬灰,被造塔镇压的“魔鬼”!
白灵的形象,是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女英雄、几乎是完美的形象,但是相对于田小娥来说,这个形象缺乏生气,甚至不丰满,但是“天使”的光环是作者以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另外一种认识:作为书中仁义和父权代表的白嘉轩的女儿,她聪明伶俐,敢于反抗;作为书中革命领导人的夫权的行驶者鹿兆鹏的妻子,她顺从配合,乐于牺牲;作为书中革命事业的一份子,她又坚持正义和视死如归。
具有史诗风格的《白鹿原》半个世纪的书写中,革命者的形象,尤其女性革命者的形象,有激情、有大是大非的判断力、有无私的付出,这样一个革命者的人物形象,使得白灵成为作者笔下女性的另外一个标签,母亲般的“天使”!
在《白鹿原》这篇连作者自己都意外畅销这么久的书中,作者竭力去表达对女性的关怀和对女性悲剧的怜悯,可是这份人道关怀里依然有着男性俯视女性的视角,依然带着男性作家集体无意识特有的男尊女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就是就是通过田小娥这个“魔鬼”和白灵这个“天使”的形象表现出来的!
[1]《白鹿原》,陈忠实,2008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陈忠实,2010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3]《第二性》,西蒙·波伏娃,西苑出版社,2004年5月。
[4]《心理学与文学》,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
常翠岩,1977年11月出生,新疆伊宁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在职研究生,西安培华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