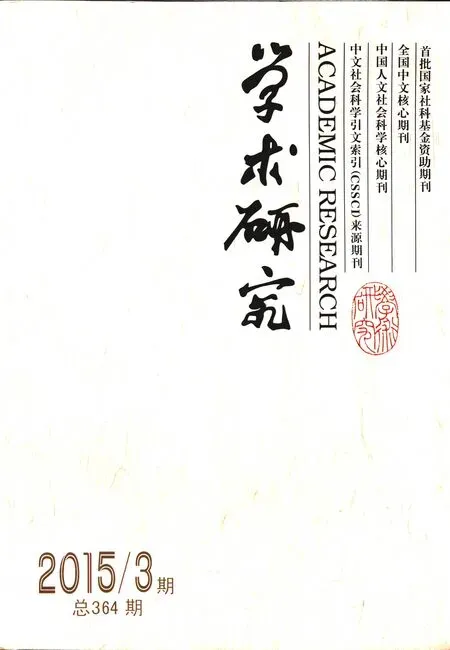《文心雕龙·辨骚》“博徒”正诂
2015-02-25杨德春
杨德春
学海酌蠡
《文心雕龙·辨骚》“博徒”正诂
杨德春
此前多以贬义解诂 《辨骚》之 “博徒”,如吴林伯 《〈文心雕龙〉义疏》:“则 ‘博徒’为贱人,本篇引申为下品。‘英杰’,卓越也。”陆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释曰:“博徒:赌徒,这里指贱者。”此亦明显以博徒为贬义。周振甫对博徒之解释一以贯之,《文心雕龙注释》:“指屈原赋尚存三代的体制,已杂战国风气,不是雅颂的正统继承者,”《文心雕龙全译》《文心雕龙选译》亦以博徒为 “赌徒,微贱者。”王运熙、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博徒:此处指低贱之人。”亦明显以博徒为贬义。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博徒人之贱者。”张立斋 《文心雕龙注订》订补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所注博徒云:“《史记·信陵君传》:‘公子闻赵有处七 (杨德春按:此七当为士之误。)毛公,藏於博徒。’立斋按:此谓比之 《雅》《颂》,固逊之如博徒,于辞赋则崇之如英杰也。”[1]云楚辞比 《雅》《颂》固逊之如博徒,此与范文澜释博徒为人之贱者同以博徒为贬义。或偶有以 “博徒”为褒义者,如李金坤说:“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 ‘博徒’和 ‘异乎经典’之 ‘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2]赵仲邑则说:“拿它来和 《雅》、《颂》相比,它当然是个浪子;但和后来的辞赋相比,它却是个俊杰。”[3]而罗剑波认为:“在刘勰看来,《楚辞》是有 ‘变’于经书,而不是要比经书低微、逊色。”[4]
综观此前对 “博徒”之解诂,其一,或褒或贬,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其二,未能察觉 “博徒”词义自《史记》后之细微变化。其三,未能根据 《辨骚》文意以定 “博徒”之具体涵义。故循此三点而进,庶几得 《辨骚》“博徒”正诂。东汉崔骃有 《博徒论》,已残缺不全,《太平御览》则有: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脚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5]
《博徒论》不是问答赋作,更非杂赋,明言 “乃谓曰”,而非 “乃问曰”。 “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不是问句,而是感叹句,意为:你受天命怎么如此之薄啊!你禀性怎么如此不纯啊!若 “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是问句,所问为天命本性。性命为孔子所罕言,崔骃焉能以天命本性问之于农夫?农夫又焉能回答?可见,崔骃 《博徒论》之文章结构绝非问答体。崔骃 《博徒论》已明言是论而非赋,历来标 “论”者均为议论,如王沈 《释时论》、鲁褒 《钱神论》,敦煌文献之 《茶酒论》亦当如是。又 《北堂书钞》:“燕臛羊残,炙雁煮凫,鸡寒狗热,重案满盈。” “适逢长吏,膏卫东显,抚绥下车,但到酒罏烂燂。”[6]从以上片段看,博徒乃待长吏访贤之隐者,《博徒论》之博徒既然是隐于博徒之贤者,则博徒绝非嘲笑农夫之劳苦憔悴、自吹悠闲自得。贤人高士感叹农夫 “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是对农夫之同情、对统治者和天命论之嘲讽。其主题不过是待长吏访贤隐者,不可隐于农夫或可隐于博徒而已。
《太平御览》第1695页:“崔骃 《七依》曰:‘紫唇素齿,雪白玉晖。’”据 《后汉书·崔骃列传》,崔骃 “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崔氏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实际上是隐于典籍中。 “骃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骃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谓崔骃急于出仕,不待访而
自薄候宪。 “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崔骃之人生轨迹正是先隐后仕、以隐求仕。可见,《博徒论》中之博徒形象正是崔骃以自嘲描绘的自我形象,而农夫形象则非作者自嘲的自我形象。故 《博徒论》中之博徒介于褒、贬义之间,实属中性词。此博徒仍为英才,但并非正途出身之英才,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曲线英才,或曰浪子英雄。 《文心雕龙·辨骚》之 “博徒”也当作如是观。
若以 “博徒”词义自 《史记》后之变化解诂 《辨骚》之 “博徒”可得正解。 《史记》:“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閒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魏公子常闻此博徒为贤人,而不与其游,因其不求士也。又如 《史记》:“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7]袁盎认为,剧孟虽为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余乘,此博徒必有过人之处。剧孟实为浪子英雄。 《史记集解》释博徒:“如淳曰:‘博荡之徒。’或曰博戏之徒。”此为博徒之原义。自 《史记》行世,博徒词义出现了去贬化倾向,但未变为褒义,而是介于褒贬之间的中性词,新义为隐于博徒之贤人或英雄。沈约 《宋书》王微与江湛书曰:“赏剧孟于博徒,拔卜式于刍牧。”[8]博徒与刍牧地位并为低下,但王道鸿鬯,于博徒之中赏剧孟,于刍牧之中拔卜式,此博徒实属中性之词。赏剧孟于博徒,此博徒仍为英才,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曲线英才,或曰浪子英雄,虽为浪子而终成英雄。
计有功 《唐诗纪事》:“适性落拓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9]高适性落拓不拘小节,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此为曲线为官之路。如此则隐迹博徒之博徒,虽为浪子而终成英雄。李白 《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赵俗爱长剑,文儒少逢迎,闲从博徒游,帐饮雪朝酲。”[10]盛赞赵俗爱长剑、赵之文儒少逢迎而闲从博徒游。此博徒亦为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曲线英才。这些都是 《史记》行世后博徒词义发生微妙变化之典型例证。据此可确解 《辨骚》“博徒”文意。 《文心雕龙·辨骚》云:“固知 《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
《辨骚》以楚辞具备 “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事,此四事同于风雅。楚辞亦具备 “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 四事,此四事异乎经典。楚辞与经典之异同各占一半,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此由楚辞有同于风雅之四事而来。而风杂于战国,此由楚辞有异乎经典之四事来。接言楚辞乃雅颂之博徒,此博徒不可能完全是贬义或完全为褒义。故不可作简单化、极端化、模式化之解释,以博徒为贱人而引申为下品或与英杰解相对照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此博徒既然与辞赋之英杰相对言,与英杰形成正反对照,此为古人行文对比之法,可为一说。但古人亦有互文之法,英杰自然是英才,博徒实为曲线英才,此亦可为一说。
刘勰 《文心雕龙》以原道、徵圣、宗经为为文之本,原道、徵圣、宗经三者三位一体,宗经也就实现了原道、徵圣。楚辞四事宗经、四事未宗经,虽与完全宗经者有别,但自然也与完全不宗经者迥异,实乃曲线宗经,不失为经典之变相继承者。故宗经之浪子英雄即为 《辨骚》“博徒”之确诂。据王利器 《文心雕龙校证》,《文心雕龙·知音》也用了“博徒”一词:“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 ‘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此说楼君卿不过是个夸夸其谈之人,随便说话就被讥诮,文人学士更不能妄谈,故此处 “博徒”一词绝不是褒扬之词。 《知音》“博徒”是用 “博徒”之原始义,而 《辨骚》“博徒”是用 “博徒”之新变义,《知音》之 “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 《辨骚》之 “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
[1]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2]李金坤:《〈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48页。
[4]罗剑波:《〈文心雕龙·辨骚〉“博徒”再诠》,《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5]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64页。
[6]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594、595页。
[7]《史记·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82、2744页。
[8]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5页。
[9]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10]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6
A
1000-7326(2015)03-0157-02
杨德春,邯郸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河北 邯郸,05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