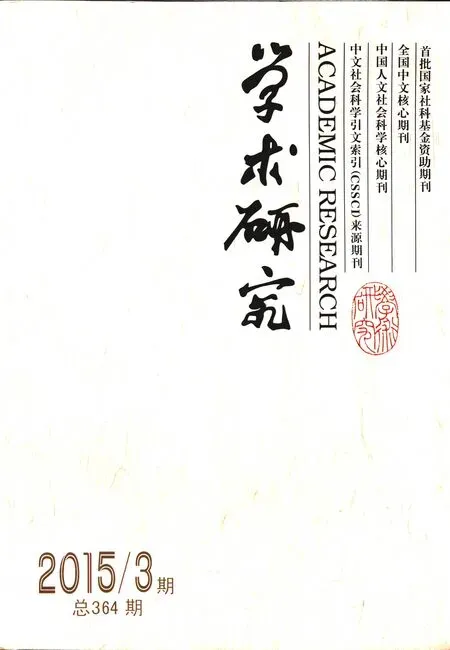美国进步时代的腐败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5-02-25颜昌武
颜昌武 罗 凯
美国进步时代的腐败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颜昌武 罗 凯
政党分肥制、社会对腐败的高容忍度、金钱腐蚀政治、政府职能扩张,构成了美国进步时代前夜腐败高发的主要原因。进步人士为有效治理腐败,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限制掠夺之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二是重新唤醒公民责任感,以公民权利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美国进步时代的腐败治理,给当下中国最有力的启示在于:腐败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理的,但必须深刻认识当前中国反腐工作的特殊性与艰巨性,尤其需要凝练广泛的社会共识,依赖广泛的公众参与,在不触动政治体制根基的前提下,推进技术层面的政府改革。
进步时代 腐败治理 政党分肥制 公众参与
透明国际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美国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9位。[1]事实上,美国多年来稳居全球腐败水平最低国家的前10%之列。[2]但历史不容回避,进步时代前夜的美国也曾有过一段极其不光彩的腐败史,特别是格兰特总统当政的八年 (1869—1877年),被公认为美国 “史上最腐败的八年”。从腐败肆虐到跻身最清廉国家之列,美国人民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这一成功转型对今天的中国又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
一、腐败横行的年代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腐败可谓无处不在。从腐败的主体来看,政党、政府、国会,无一置身度外。在那个党权 (party-government)时代,政党势力、政府权力和大企业利益三位一体地勾结在一起。作为 “政党分肥制”的直接后果,政府职位成了党争胜利者的 “盛宴”。长期控制权力的共和党尤其擅长 “腐败交易”的游戏,它一方面依靠选民的支持攫取政权,另一方面以政治恩惠笼络选民的忠诚。国会也深陷其中,1878—1880年,包括前联邦参议员多尔西在内的一批官员,借助抬高邮价、增加无价值的服务等手段诈取联邦邮政部数百万美元,史称 “星号邮路案”。军队也不能幸免于腐败丑闻:海军部利用签订军舰制造合同的机会侵吞几十万赃款,陆军部则大量出售西部地区的皮货贸易特权。人们就此感叹:“把1870—1895年这二十五年间国会、司法机构和行政部门的全部人员名单查阅一下就会
发现,几乎尽是一些声誉败坏的人物。”[3]
从腐败的层级来看,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抑或是市政府,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腐败交易”。进步时代的领袖级知识分子威尔逊 (Woodrow Wilson)指出,随处可见 “市政府的污浊气氛、州政府当局的幕后交易,以及在华盛顿政府中屡见不鲜的杂乱无章、人浮于事和贪污腐化”。[4]
在联邦层面,当格兰特 (Ulysses Grant)出任总统时,人们期待这位在南北战争中屡建奇功的英雄也能在政坛再创奇迹,但事与愿违,总统近乎灾难性地大搞裙带关系,令民众失望不已。所谓 “一人当政,鸡犬升天”,在格兰特的内阁中,竟然有多人是总统的亲友或总统夫人的亲戚。[5]他选拔的三任财政部长,一任不合法,一任是贪污犯,一任是行贿受贿能手。这位昔日战功卓著的英雄,堕落为美国历史上最受诟病的总统之一。在逃税漏税的 “威士忌集团案”(theWhisky Ring incidents)中,财政部主要官员和总统的私人秘书成为涉案者,后者参与密谋并通风报信,但却得到格兰特总统的庇护而逍遥法外。在 “莫比利尔信用丑闻”(the Credit Mobiler)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把股票赠予政府官员以影响立法,格兰特总统的副手科尔法克斯 (Schuyler Colfax)也牵连其中。[6]这两大丑闻,集中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腐败程度。
在州政府层面,最常见的腐败形式是权钱交易和政治欺诈。据1905年一份由法国人绘制的美国政治地图表明,在当时的45个州中,25个州完全腐败,13个州特别腐败,只有6个州政治清明,没有腐败。[7]在密苏里、新泽西、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州议会和州政府的关键职位都控制在铁路垄断集团手中。宾夕法尼亚州也不遑多让,共和党党魁卡梅伦竟然公开拍卖立法。[8]
市政府更是腐败的重灾区。市民为搭建凉棚而想占用一部分人行道,就得向有权颁发许可证的官员行贿;有的官员将提供给救济院的食品拿回自己的餐桌上享用;有的官员则将市里的公共资产拿去放债,并将利息装入自己腰包。扒粪者斯蒂芬斯在其名篇 《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中,讲述了1898年至1900年间,圣路易斯市在市长齐根海因的管理下,“贿赂是如何发展成为市政府惟一实在的业务的”。[9]独圣路易斯市如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因腐败蔓延而蒙羞。梅尼斯对美国纽约、波士顿等15个大城市腐败情况的研究表明:在1850年前,几乎没有腐败;在1850年到1880年这一时期,腐败开始上升;在1880年到1930年期间,腐败一直处于一个较高水平;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各种改革,腐败才开始下降。[10]
二、腐败因何高发
一个宣称以弘扬民主价值为使命的国家,何以深陷腐败泥潭呢?罪魁祸首当属顶层制度设计的偏差,“政党分肥制”主导下的政府不可能廉洁高效。所谓政党分肥制,是一种依据党派关系分配政府公职的制度,大选获胜的政党通过任命公职报答该党的积极支持者,其最能显示 “分肥”的地方在于:公职的任命不以能力高低为准,而是以效忠程度为据。
在效忠者众多而政府职位有限的情况下,无论总统候选人还是效忠者都苦不堪言。对效忠者而言,光喊口号表忠心远远不够,最后拼的还是银子,银子花得多,就意味着效忠程度高。银子花多了,自然要找机会回本。政府职位因此成了发财致富的捷径。对总统候选人来说,要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就须无节制地给效忠者们开出各种空头支票,承诺给他们所期待的政府职位。任人唯 “财”的政党分肥制促成了权钱交易,出钱购买官职的事例随处可见,各级政府最终沦为无能者的天堂和特权惬意竞逐的场所。恩格斯就此深刻地批评道:“正是在美国……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11]
如果说 “政党分肥制”是这一时期腐败高发的制度性诱因,那么,美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当属腐败高发最为直接的原因。依据亨廷顿的说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可能与急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
Can cross-boundury marketing save the domestic brands? 12 44
密切的关系,“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它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12]具体到进步时代的美国来说,它正经历着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急速转型。借鉴亨廷顿的观点,我们认为,上个世纪之交美国易发高发腐败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转型时期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时期,进步时代前夜的美国社会对腐败有着较高的容忍度。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普遍表现出对道德腐化和政治腐败的司空见惯。
在官场,官员们信奉 “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因而对腐败有相当高的容忍度。麦克伊 (Drew McCoy)在其名著 《难以捉摸的共和国》(The Elusive Republic)中辩护说,美国许多经济发展远景的实施,必须依靠公司来推动;如果共和党人抨击公司是腐败工具,就难以推动自己和选民渴望的经济发展。[13]位于官场金字塔最顶端的格兰特总统与第一夫人,对腐败有着惊人的宽容。当总统秘书巴布科克在著名的 “威士忌集团案”中狼狈不堪时,格兰特竟出具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而第一夫人则认为,总统对国家的贡献理应使他们的小家庭享受 “体面”生活,当然这种 “体面”生活离不开有钱商人的 “昂贵献礼”。
在民间,公众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且道德观沦丧。一个不顾个人道德的社会,不会对官员们的腐败行为感到激愤,反而对腐败现象习以为常。如斯蒂芬斯所指,“人民并不是无辜的”,“祸害美国人民的弊政,是由美国人民自己造成的”。[14]历史学家莫里森 (Samuel Morison)等则感叹:“几乎到处存在着旧有道德标准的崩溃,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正直诚实已从社会生活中消失。”[15]
第二,在社会转型时期,新兴的利益群体急于在利益重构的版图上攻城掠地,或无视官场的腐败习气,或主动凭借手中的金元为腐败大厦添砖加瓦。
对新兴的大企业来说,它们控制着经济资源,并试图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难免催生 “财富收买权力”之风。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公共资源,比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商人们则聚敛了大量财富。凭借手中的金元,商人疯狂 “收购”官员手中的公共资源。在银弹的攻击下,官员纷纷沦为商人的俘虏,从而使后者逃脱了本应履行的赔偿责任,而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却无从保障。
急速的城市化产生了大批移民。对这些移民来说,能否通过选举这一权力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至关重要,而官员们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在他们眼中,效忠于代表自身利益的某个人所带来的实惠,远高于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所带来的实惠。官员们抓住新移民的这一软肋,转而以就业机会、住房或公民证等为诱饵收买新移民,以便维持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在新移民对政治腐败的默许甚至纵容下,一些原本无党性的组织迅速演化成政党分肥的操作机器。比如,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 (Tammany Hall),之所以从一个慈善机构蜕变为影响最大的政治机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大批爱尔兰移民的加入。
三、进步人士如何治理腐败
政党分肥制、社会对腐败的高容忍度、金钱腐蚀政治、政府职能扩张,构成了进步时代前夜腐败高发的四大原因。要根治腐败,也必须针对这四大病灶开出药方。总起来说,美国人开出的药方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掠夺之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二是重新唤醒公民责任感,以公民权利遏制公共权力的滥用。
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进步人士首先纠编顶层制度设计,以功绩制代替号称 “腐败之源”的政党分肥制。1881年,加尔菲尔德总统遇刺身亡,加快了废除政党分肥制的进程。1883年1月,在参议员彭德尔顿的倡导下,美国国会通过了 《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文官制度的法令》,即 《彭德尔顿法》,确定以 “功绩制”代替 “政党分肥制”,明确了竞争考试、职务常任与政治中立三项原则。此后,克利夫兰总统、麦金利总统、老罗斯福总统先后颁布法令或发布命令,为现代文官制度在美国的确立做出了接力棒式的努力。
功绩制的确立极大地遏制了公职人员的腐败。其一,功绩制要求公共服务去政治化,要求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削弱了政治机器对文官的控制,从而减少了文官为政党服务而滋生的腐败。其二,公职人员的选择依据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取,这使得道德败坏、投机钻营之流很难混入文官队伍,在源头上减少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其三,在功绩制下,公职人员任期受到严格保障,这使得原来那种每一次政府选举就换一次血的情况不再发生,不仅保证了政府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也使公职人员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不容易卷入腐败行为。
明确划分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事责,强化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及监控力度,是抑制腐败蔓延的有效手段。在进步时代,美国联邦政府在影响甚至控制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食品和药业竞争以及各州间贸易等方面的权力急剧膨胀,最终取代州和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管制者。
明确划分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亦能减少政府设租的空间。政府限制市场和资源的准入,是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减少腐败的产生,进步人士实施了一系列釜底抽薪式的改革举措,即还权于社会,将原本一些被禁止或限制的活动合法化,杜绝了商人寻租的念头。比如在美国实行禁酒的1919年至1933年间,非法生产和兜售酒类猖獗一时,执法官员的贪贿之风也愈演愈烈。而当政府最终解除该禁令后,相应的腐败现象也就销声匿迹了。
进步人士坚定地认为,公民应该对腐败承担起道德责任,哪里的公民羸弱无能,哪里就会腐败蔓延。只要唤醒人们沉睡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就能有效地遏制腐败。
19世纪末,美国媒介在财政上逐步摆脱对政治机器的依附,独立性日益增强。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人视自己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专事揭露各种腐败丑闻和黑幕的写作,从而揿起了声势浩大的黑幕揭发运动。以著名的扒粪者斯蒂芬斯为例,“为了唤醒一个明显无羞耻的公民的自豪”,他在 《麦克卢尔》杂志上一连发表了6篇文章,逐个揭露了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的政治腐败情况,1904年,这些文章以 《城市之耻》为名结集出版。斯蒂芬斯一再声明: “我的特殊工作,就是要揭批美国政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腐败分子及政治不公现象。”[17]
斯蒂芬斯等人所主导的黑幕揭发运动,不仅披露了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督促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对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特别是社会良知与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他们的调查和文章,全社会都意识到了腐败的严重与危害。他们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批判,也会导致政治家竞选败北、引发检察机构进一步调查介入,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道德法制来保证公职人员的独立和公正。就抑制腐败的效果而言,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有时比严酷法律的作用更为显著。
恢复公民精神,除了占领舆论高地,还必须通过各种政治改革让公民重新获得自己曾让渡的权力,从狡猾的政治机器统治集团手中夺回提名、选举候选人以及参与决策的权力。为此,进步人士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扩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改革举措包括直选议员,赋予妇女以选举权,普及动议权、公民投票权和罢免权,以及推进地方自治修正案和地方特许权运动等。通过这些赋权于公民的政治改革,进步人士有效地削弱了政府机器在对付人民时所拥有的绝对优势,从而推动了一个清廉高效政府的来临。
四、中国能从美国学什么
美国进步时代的腐败治理虽是 “他乡的故事”,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目的自然不在于弄清美国那个时期发生了什么,而是希望与进步时代的美国有着颇多 “似曾相识”之处的当下中国也能走进属于自己的 “进步时代”。虽然中美两国在基本国情、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但美国进步时代的腐败治理仍然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腐败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理的,但必须深刻认识当前中国反腐工作的特殊性与艰巨性。美国人虽然也一度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甚至束手无策,但他们通过自身的不断探索,最终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蔓延,为二战前后美国的迅速崛起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今天,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路上,同样横卧着腐败这只拦路虎。美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勇于查找腐败的原因,对症下药,是完全能够打垮腐败这只老虎的。虽然美国的高发期主要处于进步时代的前夜,但美国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美国反腐方面的相关制度仍处于持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这也告诉我们,反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科学研判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要加深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
无论当下的中国与进步时代的美国看起来多么相识,但两国之间巨大的差异不能视而不见。一定意义上,两国之间的改革在方向上迥然有别。比如,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美国是从极端自由化的情况下检讨政府过去放任自流的做法。美国的经验表明,腐败的有效治理,有赖于强有力的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今天的中国,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同样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尤其是要划清政府的边界。不同于美国的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政府强而市场弱的困境,不仅需要谨防膨胀的市场力量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更迫切需要政府以 “壮士断腕”之勇气,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第二,腐败治理的成效有赖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就没有有效的腐败治理。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社会,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步时代是一个价值观念分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利益分化与冲突的时代。能否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冲突中寻求共识,考验着每一个进步人士的政治智慧;能否将蜂拥进城的农民和新移民培植成具有良好公民精神、能够充当政府合作伙伴的公民,是进步时代的又一大考验。令后来者感到庆幸的是,美国反腐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一个基本理念,即对民主价值的认同与坚守,他们医治侵害美国制度的一切弊端的灵药妙方,也是依赖于增加民主。同样令人庆幸的是,美国社会各阶层都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出现了问题,进而展开了各种自组织活动并推动政府致力于腐败问题的解决。说到底,公民的呼声,公民的行动,才是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根本力量。
中国的公众在反腐败方面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首先应当从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国情出必发,但无论如何,公众监督应当建设成为腐败治理的一个有效环节。美国人自建国以来,骨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他们警惕政府,担心公权力被滥用。我们则怀持 “有困难、找政府”的期待,因而迫切需要培植能够充当政府之合作伙伴的社会力量,尤其需要将公民个体与社会组织培育成为与市场和政府相抗衡的第三方力量。特别是在今天的 “自媒体”时代,一些公众热衷于网络反腐,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热情,我们应当加以积极保护和引导,充分发挥好公众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反腐败的外部环境,建立起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第三,在不触动政治体制根基的前提下,技术层面的改革也能有效地推进腐败治理。到19世纪末,美国人发现,即使是民选的政府,也同样可能腐败横行、问题丛生。如何促使政府更好地对公众负责呢?进步人士发现,仅仅增加公民投票权并从道德上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员予以谴责,并不能实现持久的改善。要使持久的改善成为现实,从技术层面入手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鉴于此,进步人士从管住“钱袋子”入手,通过对政府及其官员实施 “非暴力的制度控制”,逐步确立起现代预算体系,从而将“美国梦”坐实到可操作的层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进步时代所取得的成效来看,预算改革不单是
一种提升政府经济和效益的技术改革,也是一种重塑美国治理结构的政治改革。
在进步人士看来,“民主并不是一项旨在吸引大量旁观者的运动”,要想不成为民主运动的局外人,要想为民主大厦添砖加瓦,就应该想办法对政府中发生的事情多一些了解。了解政府有很多方式,但没有哪种方式比编制一份合理的预算更加全面和更加有效。因为预算是政府的血液,是政府正在做什么或打算做什么的财政反映,通过预算,人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政府过去的情况、当前的状况和将来的计划,而且明确设定了责任和控制方式。通过引入和借助公众力量,预算改革不经意地重塑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
[1]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4年12月3日发布的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 (CPI)排行榜,http:// www.transparency.org/cpi2014,2015年1月28日可访问。
[2]格莱泽、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王兆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页。
[3]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4页。
[4]Woodrow 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June 2,1887,pp.481-506.
[5]特贝尔、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7页。
[6]博伦斯、施曼特:《美国政治腐败》,吴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18页。
[7]Arthur Ekirch,Progressivism in America,Littlehampton Book Services Ltd,1974,p.108;转引自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4页。
[8][15]莫里森、康马杰、洛伊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15、1014页。
[9][14]斯蒂芬斯:《美国粪:城市的耻辱》,朱晓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54,1、7页。
[10]梅尼斯:《限制掠夺之手:1880—1930年美国城市中的腐败与增长》,格莱泽、戈尔丁主编:《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胡家勇、王兆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5-108页。
[11]恩格斯:《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页。
[1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4页。
[13]Drew 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1600-1775,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16]廷德尔、施:《美国史》第3卷 ,宫齐等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630页。
[17]斯蒂芬斯:《耙粪者自述》,朱晓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责任编辑:王雨磊
D771
A
1000-7326(2015)03-0060-0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12YJC810030)的阶段性成果。
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暨南大学应急管理中心副教授;罗凯,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广东 广州,51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