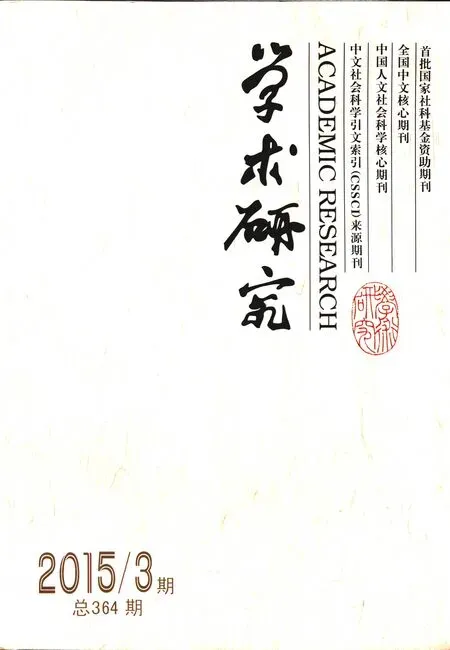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
2015-02-25干春松
干春松
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
干春松
中国思想在1840年之后,进入典范转移阶段。然而在现代学科制度形成之前,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对中国原有的概念注入新的观念和内容的方式来融合新知,这一点从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观念 “仁”的重新理解可以看出。通过将平等、公正等价值输入,儒家的思想有了新的面向。
康有为 仁 平等 公正
中国思想的近代转型从制度层面来看是直接引入西方的学科制度,即在新设立的大学里采用西方的学科制度来取代原先中国的 “四部之学”。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是否以哲学科来取代经学科的争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经学被纳入现代学科体系中,它亦只能以众多学科之一的身份来进行知识性传授,而不再是 “真理”性的宣示。
与制度性的转变不同,概念和思维方式的传入则是潜移默化和缓慢的,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引入新的概念;二是通过翻译建构新的概念,比如唯物、唯心这些我们目前常用的概念,都是经由日本人的翻译而传入,并成为汉语学术术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就是充实丰富原有的概念,比如 “国”,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国”的含义有了重要的转变。
哲学和思想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观念史或概念的发展史,这种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和不甚明显的。但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是文化冲突和融合比较丰富的时期,观念的变化就会十分激烈。比如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传统中国的有无概念,在王弼的解释系统中,被赋予本体和现象的意味。而宋明时期对于本体和功夫的讨论,也受到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旧概念被输入新内容的现象,冯友兰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叫 “旧瓶装新酒”。他说:中古哲学以依傍远古哲学,所以是 “旧瓶装新酒”。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 “新酒”不多,或新酒不够 “新”。 “在西洋哲学史中,自柏拉图亚力士多德等,建立哲学系统,为其上古哲学之中坚。至中古哲学,则多在此诸系统中打转身者。其中古哲学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新成分,其时哲学家亦非不常有新见。然即此等新成分与新见,亦皆依傍古代哲学诸系统,以古代哲学所用之术语表出之。语谓旧瓶不能装新酒,西洋
中古哲学中,并非全无新酒,不过因其新酒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古代哲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亦能容受之。”但近代以后,因为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很强,出现了许多新的名词,已不是旧的框架所能容纳,所以就不能再采用旧瓶新酒的方法。 “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变,新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其哲学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术语,亦多新造。盖至近古,新酒甚多又甚新,故旧瓶不能容受,旧瓶破而新瓶代兴。由此言之,在西洋哲学史中,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也。”[1]
冯友兰强调其 “新理学”体系是 “接着讲”,而不是 “照着讲”,那就是说,他是采用了理学 “旧瓶”而装进去了许多新的内容。他在比较自己的作品和金岳霖的 《论道》的时候,认为金先生的著作才是 “新瓶装新酒”。 “当我南岳写 《新理学》的时候,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的,不过他不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2]
冯友兰和金岳霖进行学术创作的阶段,现代学科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然而冯友兰的区分对处于转折阶段的1840年到1911年期间的学术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一是那个时期的学术创作者并非是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和学者甚或其他身份的综合体。比如康有为和章太炎都主要是政治人物,学术创作经常会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二是那个时期人们往往更多地受传统的学术范式的影响,对西方思想的了解比较表面。所以,在后来学者的评论中,他们的思想经常会受到批评,比如顾颉刚、钱穆对章太炎和康有为基于经学的立场来进行学术讨论的方式提出过批评。冯友兰也是如此。他说:“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廖平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经学之间瓶破而哲学史上之经学时期亦终点。”[3]显然,经学和现代学科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分歧,因此冯友兰对康有为、廖平要以经学范围西学的做法提出批评的确是一种典范转移的明确表达。然而具体到儒家而言,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是知识和信仰融为一体的,如果完全以现代学科将之转变为知识化的体系,那么其信仰的成分便被消解。也就是说,知识化的儒学并不再是传统儒学的发展,而是其变种,因为借助于知识化的表达,儒家的价值理念便难以落实。而康有为和廖平,试图以经学化解西学的努力,一个不容忽视的立场是,他们试图借助西学来充实儒学的信仰,而非将之知识化。因此,冯友兰对康有为和廖平的批评可能并不是十分有针对性的。
在康有为自身的思路里,他了解现代学科发展的趋势,然而他亦同时要考虑学科化之后,儒家的信仰如何传承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所以,康有为提出了以建立孔教会来解决信仰问题的方法。①对知识和信仰的分途的讨论可参阅干春松:《知识和信仰的分途:近代社会变革中儒家的知识化和宗教化的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而从知识化的角度看,经学固然是一种难以承受的 “旧瓶”,然而经学所具有的一些内容却也并非是简单的知识化所能处理的,因此,回顾学科未定型时期的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哲学形成的曲折性,更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本文以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概念 “仁”的重新定义和思考来分析这种曲折性和复杂性。
“仁”是儒家最为核心的观念,孔子突破传统礼学对仁说的局限,“坚持 ‘仁者爱人’的精义,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确立了仁学的伦理学立场。”[4]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仁的不同解释可以视为儒家观念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孔子因人立教,不断阐发仁的不同侧面,我们从中亦可以了解。首先,仁是一种道德通感能力,孔子通过对忠恕之道的解释,强调对他人处境和感受的体察,并以此来引导自己的行动,反省自己的意志。其次,仁亦是一种德目,并构成与其他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并列或融摄关系。②“仁”对于儒家道德理论和伦理体系的架构作用可参看黄惠英:《儒家伦理与道德 “理论”》,黄惠英:《儒家伦理:体与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39-46页。比如 《论
语·八佾》中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那就是表明仁对于礼的基础性意义。就此而言,仁对于其他的道德行为构成一种意义生成的作用,也成为一般道德行为的境界性标识。比如 《论语·阳货》中孔子说能够做到 “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的人,就达到仁者的境界。
对于仁的通感、扩充面,由孟子所发展,“孟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把仁规定为人的本性,把恻隐规定为人之本体的情感发用……恻隐之心之人的开端和基点,故称端。把恻隐之心加以扩充,便是仁的完成。”[5]并由此提出 “仁者无不爱”的儒家价值理想。除了孔子和孟子之外,孔门后学和荀子等都从各个角度对仁学有所阐发,由此,后世的儒者,都是通过对仁的观念的新诠来发挥、发展儒家义理。按照陈来的说法,到宋明时期,道学家将宇宙论和道德论连接,并认为朱熹的思想中,除了理学之外,亦应肯定其仁学的贡献。 “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突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6]
1840年以来,儒学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家,一方面继承儒家的经学传统,另一方面则试图回应西方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乃至价值观上的挑战。所以,他们反本开新,构建新的经学解释系统,从反思性的角度探索西方的资源和中国本土传统结合的可能性。康有为对仁的阐发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而展开的。
虽然,许多学者多从谭嗣同的 《仁学》为开端讨论现代仁学的发轫,但无论是思考的丰富性还是复杂性,康有为的仁论无疑更有讨论的空间。正如梁启超所说:谭嗣同的仁学,主要是光大康有为的宗旨,[7]其基本格局是在康有为理论上的扩展,因此,康有为的 “仁”观念的变迁更有案例性的价值。
第一:仁为本
康有为说,六经各有所守,然而要了解孔子之道,则莫如 《春秋》,因为孔子为万世制法之精义,全存于 《春秋》,而 《春秋》之精义,并不在其事与其文,而在于其 “义”。在康有为眼里的儒学发展史中,董仲舒和何休因为对春秋学的发展贡献甚大,所以他甚至认为董仲舒要比孟子和荀子更为重要。具体地说,康有为是通过 《春秋繁露》来理解孔子和孟子的仁学,甚至人性论的思想的,他还编写了 《春秋董氏学》来梳理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中,亦最重 “仁”,认为仁是天的 “意志”,所以 “明王道重仁而爱人”,认为仁是 《春秋》之宗旨。
俞序得 《春秋》之本,有数义焉,以仁为天心,孔子疾时世之不仁,故作 《春秋》,明王道重仁而爱人,思患而豫防,反覆于仁不仁之间,此 《春秋》全书之旨也。 《春秋》体天之微,虽知难读,董子明其讬之行事,以明其空言,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一国以容天下,而后知素王改制,一统天下,春秋乃可读。[8]
对于 “仁”的解释,孔子本人就极为多样。孟子则往往将仁与其他德行或者政治措施结合起来,发展出仁义、仁政等观念,而康有为则更为接受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中的解释:
何谓仁?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事也。如此者谓之仁。[9]
康有为评论道:这篇对仁的解释最为 “详博”。既点明了仁者爱人,又有伦序之大本,并涉及仁人之行为方式,《春秋繁露》的重要注释者苏舆也认为后世谈论仁很少出此范围。[10]
康有为的仁本论基本上是沿着董仲舒的理路形成并展开的。他在解释 《论语·学而》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的时候,就贯通了 《必仁且智》中对仁的概括和 《王道通三》中对 “天仁”论的思想,然后加以发挥。他说:
孟子述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老子以天地、圣人为不仁,孔子以天人为仁,故孔子立教,一切皆以仁为本。山川、草木、昆虫、鸟兽,莫不一统。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大同之世,不
独亲其亲,子其子,老有终,壮有用,幼有长,鳏寡、孤独、废疾皆有养,仁之至也。然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类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则乾父坤母,众生同胞,故孔子以仁体之;自类之本言之,则父母生养,兄弟同气,故孔子以孝弟事之。此章为拨乱世立义。[11]
关于康有为从三世说来解释仁的层次性的问题后文会有所展开,在这段话中,康有为认为仁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意义所在。虽然事物各有分类,但儒家以仁体之,所以建构一套以仁为基础的博爱思想。
儒家之仁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反求诸身,二是推而扩充之,永无止境。康有为在解释 《论语》中,“我欲仁,斯仁至矣”一语时说:“仁者,人也。受人于天。而仁为性之德、爱之理,即己即仁,非有二也。近莫近于此矣。故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反求诸身,当前即是。而学者望而未见,或诿为远,永无至仁之地,实无欲仁之心耳。”[12]
相比于反身而诚一面,康有为更为看重推扩义,所以他尤其致力于阐发孟子的将不忍人之心推扩到事事物物的推恩思想。他认为:孟子之道只有一,一者仁也,这是孟子思想的第一义。他将孟子看做孔门的龙树、保罗,是因为他认为孟子是深通 《春秋》三世之大义,有本于内,而专重扩充,传孔子之大道。孟子之不忍人之心,道出了圣人之用心。 “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新,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人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13]①在 《南海师承记》中,康有为就明确地说:“孟子仁字专在扩充。”并说,施于天下之同饥同溺,所以发井田之制。 《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50页。
与1840年后刚刚接受西学的思想家一样,他们喜欢借助物理概念来解释某种本体性存在的事务,这里康有为亦将 “电”“以太”和 “仁”相并列以说明仁的源始性和动力源,认为人道之仁爱和文明就是要把这种作为仁呈现的不忍人之心推扩开来。有不忍人之心则有不忍人之政,康有为认为中国传统专制的残酷非根源于儒家,而是老子的 “不仁”之道,“孔子以仁为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传之,由拨乱至于太平,仁之至,则人人自立而大同。老子以不仁为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韩非传之,故以刑名法术督责钳制,而中国二千年受其酷毒。”[14]所以要摆脱专制就是要回到儒家的不忍人之政。康有为在 《孟子微》中说:
仁者博爱,己欲立而立人,必思所以安乐之,无使一夫之失所,然必当有仁政,乃能达其仁心。[15]这就是说,如果是仁者的政治,必基于仁者之心,从而必有以民为本的措施。
第二:仁与博爱、平等
以爱释仁,将仁的推扩视为爱的体现乃是孔子论人之关键,亦是儒家人本主义最坚实的基础。康有为在解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段话时说:“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16]很显然,康有为的博爱论仁受到了董仲舒和韩愈的影响,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爱。”[17]后来韩愈在 《原道》一文中,则认为博爱是仁之 “定名”。
因为肯定仁是博爱的,故而康有为极为肯定管仲之事功,他在解释为什么孔子会肯定管仲是 “仁人”这个儒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时指出,孔子之意即是肯定了仁是博爱。他说:“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孟子之卑管仲,乃为传孔教言之,有为而言也。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岂知孔子之道,内外本末并举,而无所偏遗者哉。”[18]②康有为之离开朱九江,意味着他对宋学义理的评价。他说:“宋人讲义理不及董子。董子以天心为主。”还说:“朱子解 《中庸》仍是空口说过,未曾打入实处讲。”他比较推崇周敦颐和王阳明。 《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 3 1、2 3 2页。在文中,他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并不一定准确,不过,他是反对只知修
身,贬低事功的倾向的。因此,他说仁的最高境界是博爱,而人的最高境界则是为 “天民”。
在万国竞逐世界格局中,康有为认为民族国家之建构乃不得不然,不过他依然推崇超越身家国家而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并将这样的人称为 “天民”。 “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一般之人 “只养一身,或养一家,或营一职,甚者一身之中仅养一体。盖觉性极小。”如果能知天民的责任,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对天下之为难就会思考如何拯救。因此,天民的责任,“一在觉民,一在救民。”[19]
基于觉民和救民的使命感,康有为认为忠恕之道中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的精神更符合仁的本质。他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说: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由不属己也。愚尝论之,天地万物,同资始于乾元,本为一气,及变化而各正性命,但为异形。如大海之分为一沤,沤性亦为海性,一沤之与众沤,异沤而无异海也。但推行有次,故亲亲而后仁民,仁民而后爱物。孔子以理则民物无殊,而类则民物有异。其生逢据乱,只能救命,未暇救物,故即身推恩,随处立达,皆至人而止。此非仁之志,亦仁之一方,而今可行者也。仁者,二人相人偶,故就己与人言之。立达者,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诸心加诸彼,故推恩可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皆从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出。孟子专言扩充,真的孔子之传者也。孔子言仁至多,不易体会,此章最明,学者可留意焉。[20]
他也是以大海之众沤和海水的比喻来说明一体和各类事物之间的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并认为要从事物的差异中看到其一致性,这样才能将仁爱之心推扩出去。他由此认为孟子的良知扩充最符合孔子之仁的意思。
博爱的基础是万物平等、众生平等,康有为认为古今圣人的聪敏才智只在爱其人类,更有甚是只爱一国之民,欺凌别国,这是背乎公理,是 “爱德之羞”。[21]而这种博爱体现在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则是反对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康有为将孟子视为发明民权观念者,所以提倡汤武革命,不能容忍一人肆于民之上。他解释孟子用 “平世”而不用 “治世”的原因,是孟子 “明平政治义,天生人本平等,故孔子患不均。 《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 《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世。盖以平为第一义耳。平政者,行人人平等之政。”[22]①陈来说:“儒家的平等观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不与近代西方完全一致,他不是个人主义的平等,也不完全是基于权利的平等,它包含甚广,如民族平等。而且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比较,它更突出的是经济的分配平等,其平等观接近于社会主义。” 陈来:《仁学本体论》,第441页。所以在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中,他用公平、文明、权利和平等等现代的观念来重新定义 “仁”。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立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意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23]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康有为试图将现代价值和仁学相结合的努力,以及以现代民主、平等、公平的价值理想来丰富孔子的仁学思想的追求,他认为这些现代价值是仁的价值在不同时代的表现,符合孔子所定的三世不同法的原则。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一度是民权自由的倡导者,只是那时他的民权和议会
思想主要目的是 “上下通”,即让最高统治者能够准确详细地了解民情,而不是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权和自由。民国成立之后,康有为发现民权和自由对传统的秩序造成了摧毁性的影响,因此,他反而后悔曾经提倡民权,转而强调 “国权”,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民权和自由便无从谈起。①梁启超在 《南海康先生传》中说:“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则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的确,要了解康有为的思想,首先要理解其糅合公羊三世和进化论所建构的历史观。康有为将这样的思想贯穿于其论说的几乎所有的方面,即使平等和博爱也是如此。
博爱固然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然物之不齐物之情,如何在博爱和差等之爱中找到平衡,是由博爱论发端之处就已经形成的问题。董仲舒就反对 “爱而不别”,认为那是一种仁而不智的行为。[24]康有为亦认为仁有差等,他在 《孟子微》中通过解释 《孟子·尽心上》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段话的时候,他将差等之爱和普遍之爱分置于不同的 “世”中。他说按照孔子的三世之法,拨乱世的仁,行之不远,所以看重亲亲;而升平世开始爱及人类,故能仁民。到太平世,众生如一,才可能兼爱物。如此,仁依据不同的世 “进退大小”。天下万物都本天而生,尊天者,必爱同生。 “但方当乱世、升平,经营人道之位置,民未能仁,和暇及物?”[25]所以只能提倡节制以减杀机而已。
类似的说法在 《中庸注》中也可发现。在解释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之道,修道以仁”一语时,康有为根据大同小康的分期,提出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亲其亲子其子是小康之仁,而远近大小一统,则是大同之仁。 “孔子本仁,此孔子立教之本。孟子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老子以天地为不仁,故自私。孔子以天地为仁,故博爱。立三世之法,望大道之行,太平之世,则大小远近如一,山川草木,昆虫鸟兽,莫不一统。大同之治,则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务以极仁为政教之统,后世不述孔子本仁之旨,以据乱之法、小康之治为至,泥而守之,自隘其道,非仁之至,亦非孔子之意也。”[26]
康有为依据进化论,认为小康之仁要向大同之仁发展。在 《大同书》中他将这种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称为 “大仁”。②朱熹解释爱物就是 “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四书章句集注》)康有为认为即使在大同世,猎杀动物也不可避免,比如会伤害人类的猛兽和毒蛇之类。这些物种只养一些放在动物园中。不过反对以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的杀生,人类可以通过新技术做出替代肉食的食品。不过他认为物种进化有高低,天演的优胜劣败决定动物要受人的控制。康有为:《大同书》,朱维铮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第256页。他解释孟子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是 “求仁莫近”之道,并将推己及人作为太平世之仁道。 “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问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终身行,孔子告以恕。故子贡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证圣之法,太平之方,内圣外王之道,尽于是矣。”[27]
第三:仁与智
孔子论仁,常常与别的德目结合而讨论,这也成为后世儒者阐发仁的精神的常用方法,所不同的是关注点的差异。
孔子十分看重仁与知的关系,在 《卫灵公》篇中,就讨论知、仁、敬、礼之间的关系,他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这就是说,如果只有 “知”,不能辅之以仁、礼,那么就是 “为善”。
在作于1885年的 《教学通义》中,康有为列举了经典中对于儒家德行的各种说法之后,就提出德
行应与时偕行,他当时的说法是:“以仁为上,知次之,忠、和终之,刚健勇毅皆所不取。”[28]余且不论,由此可见,即使在确立今文学的立场之前,康有为其实已经十分看重 “知”的重要性了。
对于 “智”或知识能力的重视,与1840年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积弱原因的分析有关。康有为以及稍后的严复等都将开发民智作为他们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1890年之后,康有为看重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而在这部书中,亦十分看重智的重要性。在 《必仁且智》篇中,董仲舒对于智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即 “先言而后当”,就是先想清楚是非利害再有所作为。因此,仁和智在人的行为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不仁而有勇力,则反而会导向暴力,而不知之人,即使有良马,也不会驾驭。所以仁和智要结合才能有好效果。仁的意义是爱人类,而智的作用是除其害。康有为对这段话的解释是:“孔子多言仁智,孟子多言仁义。然禽兽所以异于人者,为其不智也,故莫急哉。然知而不仁,则不肯下手,如老氏之取巧;仁而不知,则慈悲舍身,如佛氏之众生平等。二言莞天下之道术矣。孔子之仁,专以爱人类为主;其智,专以除人类为先,此孔子大道之莞辖也。”[29]
在 《康子内外篇》中,康有为也提及孔子比较少以仁义对举,而是经常以仁智对举。 “上古之时,群生愚蒙,开物成务,以智为仁,其重在知;中古之后,礼文既闻持守,先以仁为智,其重在仁。此夫子所以诲学者以求仁也,此非后儒之所知也。就一人之本然而论之,则智其体,仁其用也;就人人之当然而论之,则仁其体,智其用也。”[30]①陈来认为康有为虽然以仁为体,但在德性与在价值上有时重视智超过了仁,所以 “他反对宋儒的仁统四德说,这就改变了宋儒以来人的统帅一切的地位。” 《仁学本体论》,第438页。这个结论恐怕有一些过强。统而观之,因为继承董仲舒的仁受之于天的思想,仁的地位依然突出,不过康有为提升了智的重要性,认为智超过义、礼这些传统上更为重要的德性。康有为用体用来讨论仁和智,或许是受汉人以群体和类来说明仁的意义的影响,从而区分了 “一人之本然”和 “人人之当然”。所谓 “一人之本然”乃是指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人之生存意识大于道德感,所以智具有决定性意义。而 “人人之当然”则指人的社会性存在。而儒家尤其是汉儒总是要从人的群体性存在来说明人之为人的独特性。这种区别对于康有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从应然性的立场上,仁要重于知;但在本然性的角度,智的地位尤其突出。在这样的区分中,他认为在仁义礼智信这几项儒学的核心价值中,智的地位十分特别,与孟子论人禽之别是基于仁义不同,康有为认为仁、礼、义、信这些德性别的动物也可以具备,只有智才是人与动物区分的最基本的要素。 “既乃知人道之异于禽兽,全在智。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大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31]因此他将本然性的存在作为人的初始状态,而要通过道德教化,最终达成仁道。在此点上他甚或从董仲舒的性三品倒向了荀子。与孟子的仁心非由外铄不同,康有为则肯定了知识和辨别能力对于道德观念建立的重要性,认为 “知之所及,即我仁之所及”。
在解释 《中庸》中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这段话时,他说:德性合人己内外,仁和智共同构成人类的境界。知的格局决定仁的大小。 “盖仁与智,皆吾性之德,则己与物皆性之体。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天人同气,无内外之分……凡我知之所及,即我仁之所及,即我性道之所及。其知无界,其仁无界,其性亦无界。故诚者知此,以元元为己,以天天为身,以万物为体。”[32]
在 《中庸注》中,康有为也有以知之格局决定仁之大小的说法。
故自群生之伦,无有痛痒之不知,无有痿痹之不仁。山河大地,皆吾遍现。翠竹黄花,皆我英华,遍满虚空,浑沦宙合。故轸匹夫之不被泽,念饥溺之在己,泽及草木,信孚豚鱼,皆以为成己故也。其次,仅知人类之为己,则思济太平而援自立。又其次,仅知国之为己,则思定社稷而安民生。又其次,知乡族之为己,则广睦恤而勤惇叙。又其下,知家之为己,则勤孝养而劳慈畜。若此者,各以知之大小为仁之大小,即其性道大小之差焉。然能与国为体,以家为己,尽智竭力以为
之,至死而毕焉,亦合内外知道也。[33]①在 《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对仁的层次有更为细致的划分。 “天下何者为大仁,何者为小仁?鸟兽昆虫无不爱,上上也;凡吾同类,大小远近若一,上中也;爱及四夷,上下也;爱诸夏,中上也;爱其国,中中也;爱其乡,中下也。爱旁侧,下上也;爱独身,下中也;爱身之一体,下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5页。
康有为承认不同的人因为知力之大小而决定了其境界,然而却不能认可将小仁之境视为大道,比如有人将修身寡过视为孔子之道,那就是丧失其性的狂人。其实,他所要批评的主要是自宋明理学之后只知修身而不知将之推及天地万物的一些俗儒。所以康有为提出理想的仁智关系是 “仁智双修”“以智辅仁”。
盖以孝弟发其行仁之始,以泛爱众极其行仁之终,以谨信肃其行仁之规,以亲仁熏其为仁之习,而后学文以广其智益。虽仁智双修,而始终于仁,但以智辅仁,所以养成人之德也。[34]
由此可见,在康有为的仁学体系中,智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知能辨明是非利害,所以有助于仁者安仁,进而利仁。②对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一语的解释中,康有为说:“利,贪也,知仁为有益,而欲得之也。盖人而不仁,其智昏,不能乐天知命;其性贪,不能节欲修身。久困必至于滥,久乐必至骄淫,惟仁者随遇而安,吾人而不自得。” 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 ,第402页。然而进一步可以推测的是,康有为对于智的肯定,也在于他对于近代以来竞争格局的转变,他认为现代世界国家间竞争的根本在于知识,因此他在戊戌变法和其他时期的政治改革设计中,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入手点之一。
第四:仁与勇
孔子思想中特别重视 “勇”的德行,所以将智仁勇视为三达德。当然,“勇”也经常会被人质疑。比如孔子就说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孟子也特别看重 “勇”,其强调的许多德行背后都有勇的意味,比如舍生取义,养浩然之气,均是勇字当头。孟子在 《公孙丑上》中说,勇是 “不动心”,如果目标确定,则虽千万人吾往矣。
然而,到汉代,勇这样的德性并不完全被肯定,董仲舒就认为,如果没有仁作为基础的勇,反而会对社会造成危害。③“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57页。
1840年之后,国家的积弱使得尚武和勇力再度被人们肯定。康有为亦是如此。他在解释 《论语·公冶长》中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孔子描述成要出海传教,有子路跟随,但因为没有出海的船只而作罢。 “孔子抱拨乱反正之道,太平大同之理,三世三重之法,横览中国皆不能行,私居忧叹,欲出海外。是时,大瀛海之说已通,大九洲之地已著,孔子答曾子,发明地圆,故心思海外大地,必有人种至善,可行大同太平之理者,欲择勇者同开教异域。以子路勇而好仁,故许其同行,子路果喜。可见圣贤传教救人,不惮艰远之苦志矣。从行海外,凿空创开,事本艰难,故孔子极称其勇。而是时海道未大通,无船筏可出海,欲返无舟,空深叹慕,此则圣人所无如何,故卒不果行。使当时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罗马,东渡日本以开美洲,则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道,当有一地早行之也。传教救人,宜出海外,后学当以孔子、子路为法,无惮艰远矣。”[35]
乘桴浮于海,本来是一种不满于现状的自我流放,但在康有为这里则成为心思海外大地,去大同太平之理的壮举,亦可见其奇思妙想之一斑。
康有为对于勇的肯定,还可以从他对于 《论语》中智仁勇三达德之间的关系的阐释中得到证明。他解释道:
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人之生世,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万物之事理错杂于前,而不知所从,则日在惑中;身家国天下苦恼相
缠,而不能逃去,则日在忧中,身世言行危难相触,而不能胜之,则日在惧中。惑则如盲人瞎马,夜行临池;忧则如在火坑悬崖,惧则如见毒蛇猛虎,大火怨贼。此人道之至苦,而日望圣人拯之也。圣人先救惑者以穷理明物之知,则幽室皆见光明;施忧者乐天知命之仁,则地狱皆成乐土;施惧者以浩气刚大之勇,则风雷亦能弗迷。故知、仁、勇为三达德,学者度世之妙方。[36]
康有为素有拯救天下之豪气,①二十七岁那年,他 “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其来现世,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上,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94年,第34页。因此,眼看人道之苦,必思拯救之,这样就要明万物之事理,有爱人之心,而更要有浩气刚大之勇。
康有为对曾子多有微词,认为他所编撰的 《论语》并没有将孔子的真实意图记录下来。但对 《论语·泰伯》中所记录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句话最为赞叹。康有为说:“曾子之言皆守身谨约之说,惟此章最有力,真孔子之学也。其得成就为孔学大派,皆弘毅之功,力肩孔道仁为己任也,易箦不昧,死而后已。”[37]这样的一种精神,就值得效法。
第五:仁与大同
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平等的世界就是 “大仁盎盎”的状态。他说以前人们对于仁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主要是执著于对于 “类”的认识,只知道爱同类,而不能将这种爱推扩开去。
当太古生人之始,只知自私爱其类而自保存之,苟非其类则杀绝之。故以爱类为大义,号于天下,能爱类者谓之仁,不爱类者谓之不仁;若杀异类者,则以除害防患,亦号之为仁。[38]
在康有为的 “大同”思路中,他认为人类之苦难是因为各种利益的纠缠,诸如国与国的竞争、阶级的差别、人种的差别、男女的差别,甚至家的局限、生产方式的限制,所以要救治人类之苦难,就要去除这些因为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制度所产生的阻碍人类获得幸福生活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进一步认为,人类不仅要追求自身的幸福,还不能牺牲别的物种的利益。古今人类的幸福观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这也是要破除的。由此,他甚至对传统儒家的 “爱”的秩序提出了质疑。 “孔子以祖宗为类之本,故尊父母。子女者,爱类之本也。兄弟宗族者,爱类之推也。夫妇者,爱类之交也,若使与兽交者,则不爱之矣。自此而推之,朋友者,以类之同声气而爱之也;君臣者,以类之同事势而爱之也;乡党者,以类之同居处而爱之也;为邑人、国人、世界人,以类之同居远近而为爱之厚薄也。以形体之一类为限,因而经营之,文饰之,制度之。故杀人者死,救人者赏,济人者誉,若杀他物者无罪,救济他物者无功。”[39]这样,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爱人类、保人类的历史,而不能延伸到别的物种。据此,康有为认为产生于印度的婆罗门、佛教思想更为接近 “人道至仁”的境界,因为他们的教义中,包含有爱护别的物种的思想。所以大同世界的哲学,必是戒杀的哲学。
康有为认为,孔子的哲学中,本来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所以其学说,由 “亲亲”“仁民”,必然发展到 “爱物”。虽然在物质匮乏、国与国竞争的今天,要做到超越家、国的意识,而达到 “爱物”并不现实,生活世界中,绝对不伤害别的物种也暂时做不到,但是为仁无限则是需要秉持的观念。
在他的大同设计中,有一个机构称之为 “奖仁院”,并在各地根据行政区划设立奖仁分院和奖仁局等,对于那些慈惠人士,按照他们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分别授予上仁人、大仁人、至仁人、至大仁人等不同的称号。
当太平之世,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惟智与仁而已。智以开物成务、利用前民,仁以博施济众、爱人利物,自智仁以外无以为荣。[40]
从 “大同”来阐述仁的意义,康有为旨在超越基于人类、国家和家庭、个人的限制,提出了破除人
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这一方面可以看做他对于不合理的世界秩序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于儒家和佛教思想的融合,从而在宋儒的一体之仁基础上,期待建立起一个超越一切的爱的世界。
结语
从康有为对 “仁”的观念的重新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西方思想的影响,诸如平等、正义等,也包含有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接受,他不但用 “以太”和 “电”来解释仁,还认为仁和智的关系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康有为通过对仁的思考而展开的对于传统制度和西方传入的价值体系的反思,比如对于国家与国家的侵略、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等此类问题,他以公羊三世结合进化论的历史观,说明其出现的必然性,但也以进化的思想来否定其合理性,从而为人类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这种基于经学的立场出发的理论创造试图解决儒学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复杂性。进而我们能看到超出学科范围更多的关注点。所以梁启超以 “仁”作为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充分关注了康有为仁学融汇古今的努力的。他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 ‘仁’字为惟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以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41]客观地说,与谭嗣同强调 “通”,而激烈反对纲常伦理的仁学相比,康有为的仁本论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和开放性。
笔者同意冯友兰的说法,“仁”是康有为试图使用的旧瓶,他用它装入了现代西方的许多观念,也试图由此扩展儒家价值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但笔者并不接受冯氏所做出的 “新酒”已将旧瓶撑破的判断。中西思想的不同以往经常被理解为古今之异,从这个角度看,旧瓶似乎不能容纳新酒,但是,如果从康有为的努力看,仁的观念依然存在着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它与中国文化心理的内在关联,则可以使之更能深入我们的观念系统,而为我们所接收。更进一步地说,这些旧瓶中的 “陈酒”可以成为我们反思 “新酒”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康有为、冯友兰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意义一样。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第492页。
[2]冯友兰:《冯友兰自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193页。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4][5][6][7]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5、110、46、432页。
[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页。
[9][10][17][2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8、258、319、257页。
[11][12][16][18][20][34][35][36][37]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381、432、478、492、424、383、409、453、438页。
[13][14][15][19][22][25][27]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14、415、455、417、472、415、423页。
[21][38][39][40]朱维铮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4、353、353-354、340页。
[23]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26]康有为:《中庸注》,《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79页。
[28]康有为:《教学通义》,《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6页。
[29]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1-162页。
[30][31]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08-109、108页。
[32][33]康有为:《中庸注》,《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384页。
[41]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我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责任编辑:罗 苹
B258
A
1000-7326(2015)03-0015-10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