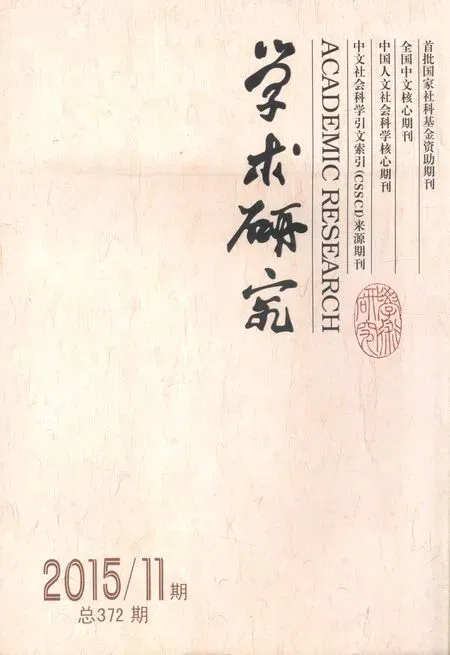龚自珍与浙西词派
2015-02-25习婷彭玉平
习婷 彭玉平
龚自珍与浙西词派
习婷彭玉平
“清空骚雅”是浙派理论之精髓,亦是清代词坛的普遍审美取向。身处嘉道词坛的龚自珍深受浸染,他以“清深”论词,是对浙西清雅观的认同。龚自珍与郭麐对袁通《捧月楼词》的评价,体现了龚自珍尊情与郭麐援情入雅的词学观念。两者关注情是嘉道词学发展趋势。郭麐的“情”以“雅”为绳尺,龚自珍之“情”多是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呐喊,是时代最强音,为固步于派中的郭麐、孙麟趾等所缺。
龚自珍郭麐《捧月楼词》孙麟趾浙西词风
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携《乐府补题》进京,将这部咏物词集广为流布,掀起了一场大唱和,以至“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1]同年,龚翔麟刊刻《浙西六家词》,标志着浙西词派的正式形成。浙西词派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于道光年间仍绵延未绝。直至清末,浙西词学仍是批评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即多有评议,嘉庆以前,浙西一派独步词坛,“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2]浙西词派清空骚雅的审美取向更积淀为清代词人对词体审美要求的普遍认同。
身处嘉道词坛的龚自珍,自觉或不自觉受浙派影响。夏承焘曾说:“但疑霄汉飞仙影,仍是江湖载酒身。”[3]认为龚自珍的词明显有竹垞《江湖载酒集》的风格。王易《词曲史》则直接将龚自珍归为浙派:“《同声集》录清人吴廷、王曦、潘曾玮、汪士进、王宪成、承龄、刘耀椿、龚自珍、庄士彦诸家词,大致以浙派朱、厉为宗,间有主张北宋者。”[4]然而,龚自珍所处的嘉道词坛正值浙派后期改革调整之时,游词、鄙词、淫词的出现,警醒了吴锡麒、郭麐等人,他们试图振衰补弊,一挽颓势,重树浙派宗风。浙派内部的反思与革新,使得板结的浙派理论出现了裂缝,其宗主地位开始动摇,浙派以外的词人能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因此词坛逐渐出现了新声。龚自珍的词学观亦是新声中的一种。
一、龚自珍与嘉道浙派词人的交游
龚自珍生于乾隆末年,而其词学活动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此时,浙派宗主朱彝尊(1629—1709)已辞世百年。浙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厉鹗(1692—1752)行年则早于龚自珍近半个世纪。二人对龚自珍的影响更多通过流传的词集以及定型的浙派理论实现,龚自珍曾熟读朱、厉二人词集,有《菩萨蛮》词注曰:“效蕃锦集。”在体式上仿效朱彝尊《蕃锦集》集句体。嘉道年间,与龚自珍同时活跃在词坛并有交流的浙派人物是吴锡麒(1746—1818)、郭麐(1767—1831)、孙麟趾(1792—1860)等人。
龚自珍与浙派后期两位核心人物吴锡麒、郭麐的交往,仅在《己亥杂诗》自注中偶然提及郭麐的画作,此外未发现只言片语。但龚、郭却有一位共同的好友吴嵩梁。龚自珍在京期间,多次同吴嵩梁等文人雅集,并诗词唱和,如:道光二年(1822),参与吴嵩梁邀集的崇效寺小集,作《一萼红》;道光三年(1823),同陈用光等人在吴嵩梁寓所举行诗会,纪念欧阳修生日;道光六年(1826),邀请吴嵩梁、姚莹等八人举行消寒第一集。而吴嵩梁深受浙西宗风浸润,对朱彝尊尤为仰慕,与郭麐关系更是密切。《灵芬馆词话》载:吾友吴兰雪嵩梁“见其‘帘外桃花红奈何。春风吹又多’之句,金荃之亚也。”[5]可见,郭麐对吴嵩梁词评价颇高。如果说龚自珍与郭麐没有直接交往,那吴嵩梁也完全可能将自己宗奉的浙西词学影响及龚自珍。更何况,龚自珍结识郭麐女婿夏宝晋。道光二年(1822)吴嵩梁在京城崇效寺举行集会,此寺与浙派宗师朱彝尊有一定关系,据光绪《顺天府志》载:“崇效寺:唐刹也,在白纸坊。……寺中旧传四季多花,游履颇盛,王士祯、朱彝尊辈俱有题咏。又有王、朱手植丁香,吴嵩梁又移植海棠于丁香左。”[6]吴嵩梁的选择固然与崇效寺“四季多花”、景色旖旎有关,但瞻仰朱彝尊等前贤的用意亦昭然可见。在这次聚会中,龚自珍结识了郭麐的女婿夏宝晋,与浙西词派的因缘自是更进一层。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又与吴嵩梁等人于清明日祭翁方纲、王昶等。而王昶曾是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因为吴嵩梁的缘故,龚自珍与浙派成员交往不可避免,只是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已。
如果说龚自珍与吴嵩梁的交往尚未能使龚自珍触及嘉道词坛浙西词派的核心,他与吴锡麒、郭麐二人似无直接过从。那么他与孙麟趾私交则应纳入考察龚自珍与浙西词派关系范畴。孙麟趾是嘉道年间承袭浙派词风的重要词人,他的词学宗尚总体不出浙派藩篱,其词学理论著作《词迳》为浙派“清空”理论的衍伸,所编《清七家词选》选厉鹗、林蕃钟、吴翌凤、吴锡麒、郭麐、汪全德、周之琦七家词,更遴选《嘉庆以来绝妙近词》,均有意仿效《词综》、《国朝词综》,仍朱、厉之旨,承浙西之绪。
孙麟趾与龚自珍年岁相仿,孙的《绝妙近词·凡例》载:“道光五年,汤雨生都督招游金陵,严问樵太史、龚定庵礼部、秦雪舫驾部以词倡和,历年既久,积词渐多”,[7]这时孙与龚当已结交,彼此诗词唱和,历年既久,关系自是密切,故后来孙麟趾将定庵词收录于所辑《嘉庆以来绝妙近词》一书。
龚自珍晚年有三首词提到了孙麟趾,其情弥深。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官去京,次年开始在江浙一带游历,访故地,会旧友,酬唱日多。如其《台城路》小序云:“同人皆诇知余近事,有以词来赆者,且促归期,良友多情,增我回肠荡气耳”,这良友中就有孙麟趾。词的上阕主要抒发龚自珍壮志难酬、凄然离京的失意,下阕则记叙了孙麟趾托寄家书的始末。孙麟趾为江苏长洲人,道光二十年(1840),龚自珍游江宁,客居江宁的孙麟趾赋词送别,并托龚自珍代寄家书,孙词《定庵将归,托寄家书,赋此送别,调金缕曲》表达了对龚自珍的安慰和劝勉,而对龚自珍结交名士高僧,有红颜知己相伴的生活极为称羡。他甚至认为龚自珍可以远离是非,从此归乡,隐居著书、镜阁偎香是福分,而想到自己仍然飘零无依、仕途无望,与家人分隔两地,不免潸然。龚自珍狷介狂傲的性格与行为多不为时人所理解和接受,孙麟趾对此却十分欣赏,因此龚自珍称此词:“增我回肠荡气”,视其为知音之赏。
总体而言,龚自珍与当时浙西词派的核心人物虽无交游迹象,但与浙派中人的关系却一直维持着。嘉道年间,浙西词派走向末期,词派本身日显松散,已不复康熙年间交游酬唱的盛况,以至一些原本浙西词派中的派系归属也呈现出模棱两可的尴尬,郭麐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龚自珍与嘉道浙西词派中人物的诸多联系,虽然促进了龚自珍与浙西词派的因缘关系,但鉴于当时浙西词学的复杂及变化迹象,曾被悬为高标的“清空醇雅”已经难以涵盖嘉道浙西词论的全部。浙派内部尚且如此,与浙派若即若离的龚自珍的词学自然更非传统浙派词学可限,而这种离合之处正昭示着清代词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二、嘉道浙派与龚自珍词学观比较
清初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在乾嘉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成员如吴锡麒、郭麐辈针对浙派词家流露的弊病提出了若干改革主张。郭麐曾被后世称为浙派殿军,他追慕竹垞,宗法南宋,曾说“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8]但他也有反思,对浙派的批判毫不留情,他的理论典型地反映出浙派后期略显复杂的格局。部分成员则依然谨守家法、承继宗风,对浙派的审美取向推崇备至,孙麟趾堪称代表。
(一)郭麐、龚自珍对《捧月楼词》的评价
作为嘉道浙派中坚人物的郭麐,其词学观念集中体现了浙西晚期词风的因变。龚自珍与郭麐词学观的异同之处,可以从两者对《捧月楼词》的评论窥见。《捧月楼词》系袁通所作,袁通是郭麐业师袁枚之子,亦是龚的好友。龚自珍曾为作《袁通长短言序》,郭麐的《灵芬馆词话》有四条提到袁通词。
龚自珍在序中首先交代了袁通词有六卷。袁通词集刻本,今存两种:一为二卷本,名《捧月楼词》,约初刻于嘉庆四年;另一种是八卷本,版心题《捧月楼绮语》,书名页题《捧月楼词》,约刻于道光间。龚自珍所见的袁通词集显然不可能是嘉庆四年就已经刊刻的二卷本。邵广铨《捧月楼绮语跋》云:其于甲戌(1814)夏游大梁,与袁通相遇于繁台之下,“握手道故后,出《捧月楼绮语》一编见示。是癸酉(1813)年手自删定者也。……以余所见兰村所为词而所存仅仅止此。”[9]此跋末署“嘉庆乙亥(1815)春初”,可知此跋系邵广铨于嘉庆乙亥(1815)为袁通癸酉(1813)手删本词集所作。今存八卷本之《捧月楼绮语》所收词作迄于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与袁通癸酉手删本并非一书。所以,龚自珍所作《袁通长短言序》,应该是为袁通癸酉手删本词集所作。而这版词集也正是郭麐细读和审定过的。
龚自珍认为袁通词的内容不仅仅限于“闺房之思、裙裾之言”的绮语艳情,而是“以阴气为倪,以怨为轨,以恨为旆,以无如何为归墟”。以阴气为端绪,由此引发酝酿为怨,暗含其中;疏泄为恨,行于文字;迂回曲折,最终归于“无如何”。“阴气”所指为何?龚自珍在《宥情》一文说:“我尝闲居,阴气沉沉而来袭心,不知何病。龚子则自求病于其心,心有脉,脉有见童年。见童年侍母侧,见母,见一灯荧然,见一砚、一几,见一仆妪,见一猫,见如是,而吾病得矣。”又“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因为阴气的存在,他回忆童年带着些许清冷的色彩。阴气于他来说是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中从心底浮现出的一种莫名情绪,是不受外界影响的自在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敏感、深刻而流露于直觉的生命体验。阴气虽与怨、恨、“无如何”为同一序列的情感,但它停留在混沌未明状态,是怨、恨的端倪。龚自珍认为词最适合抒写此种情绪,并且他往往能从词中体会到“阴气”的存在,回归到童年那时的心境。读钱枚词时如此,读袁通词亦是如此。龚自珍认为袁通善于运用词长短不一的体式特征,分别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程度的情感和意志。他说,袁通的词使得自己沉浸其中,“岂徒调夔、牙之一韵,割骚之一乘也哉”?质言之,袁通词打动自己的地方并非仅仅是韵律的流畅和寄托深远的诗骚大义,更多是蕴含于短言中的“烈”、长言中的“淫裔”,是阴气、怨、恨等真情。这种情可以无关乎家国之爱,也可以无涉于忠君之思,甚至不需要外物感发,而是无来由的喷薄欲出、不吐不快,这是他从袁通词中读出的强烈共鸣。
郭麐对袁通评价极高,他说:“同辈工词者,湘湄、二娱、甘亭、兰村诸君外,作者寥寥。”[10]但袁通并非一开始就得到了郭麐的青睐,事实上,郭麐对袁通词的评价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与袁通词风格的转化分不开。“袁兰村少时喜为侧艳之词,余尝为之序,未敢许也。后见所刻捧月楼词,居然大雅。前所见者十不存一二,因叹其竿头之日进也。”[11]按郭麐所言,袁通少时填词,多侧艳之体,郭麐对此时的袁通词不能苟同。而“后见所刻《捧月楼词》”,词体归于雅正,前所见侧艳词“十不存一二”,郭麐才对袁通词表示了赞许。他不仅细读了《捧月楼词》,并对其做了指摘。“世之论词者,多以秾丽隽永为工,灯红酒绿,脆管幺弦,往往令人倾倒,然非词之极工也。吾友兰村,少善倚声,体多侧艳,及刻捧月楼词,则一归于雅。余前既已言之矣,要起尤工者,则在于友朋离合、死生契阔之间,非近人所能仿佛。……极工言情。”[12]郭麐在此处,否认“秾丽隽永、灯红酒绿、脆管幺弦”为“词之极工”;这三个特点隐含了浙派词的审美要求:风格隽雅、辞藻华美、声律谐调。郭麐通过对《捧月楼词》的评骘,认为词之为工者在于言情。而袁通词中“友朋离合”、“死生契阔”这类的悲欢离合之情是其词最可贵之处,也是旁人难以企及、难以模仿的。这类感情的特点正在于真,惟其真挚,是以感人。
龚自珍与郭麐对袁通词的评价和体认都离不开“真情”二字,这是袁通词的特点所在,另一方面龚、郭二人对“情”的重视,并非出自偶然。龚自珍的“尊情”说自是无需多言,郭麐对袁通词的评论则是他反复强调重申的一个词学观念。郭麐学词以《花间》入门,中年开始学习南宋词而有所得。正是因为中年“忧患鲜欢”,需要以词“陶写阨塞,寄托清微”,所以南宋词进入到他的视野。他认为只要是出自“胸臆间”,即便是“无足以悦耳目”的“虫鸟之怀”,也“未易轻弃”,可见对真情真意的珍视。郭麐认同浙派远祧南宋,步武姜、张的学词途径,但他以为,学姜、张的关键不在于模仿二人安排、勾勒技巧,“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13]以姜、张为宗填词的前提应该是“胸中所欲言之意”与“不能尽言之意”,即学姜、张应以意为先,这与其学习南宋词以“陶写阨塞,寄托清微”之旨相一致。若“徒仿佛其音节,刻划其规模,浮游惝恍,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那就会“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嘒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而“胸中欲言而不能尽言之意”即性灵、寄托,这才是构成词的灵魂所在。郭麐所言的“寄托”不同于稍后兴起的常州词派所言比附诗骚的寄托,郭麐的“寄托”即“性灵”,即“情”。他说:“词家者流,其原出于国风,……然其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14]郭麐所言的情都是抒情主体个性的表现。
郭麐对性灵、真情的重视尤为可贵,但郭麐论词并没有脱离浙派宗法南宋、追求雅正的前提,他的情仍不离雅的轨范,是对雅的补充。无论是白石、玉田,还是竹垞、樊榭,郭麐都是深为服膺的,尤其认为提倡醇雅,一洗《草堂》余风的朱彝尊对清词的发展居功至伟。他对雅正词风更是情有独钟:“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于是学者莫不知祧《草堂》而宗雅词矣。樊榭从而祖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厘然一归于正。”[15]而张炎早有关于情的训诫:“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16]所以,郭麐在提到“情”的时候,也不得不更为审慎,以免流于俗艳,悖于雅正。袁通词得郭麐青眼的前提是“一归于雅”,在雅正基础上,郭麐尤为称赞了其“极工于情”的特征。郭麐所言之情是不能脱离雅的前提而独立存在的,这使得情无论是表达还是内容都要符合雅的要求。郭麐认为的雅的表达方法和形式是情“千曲万折以赴声律”、“缠绵委折,如往而复”,以致“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这是浙派理论的题中之义;而关于情的内容,虽则他多次强调“胸中之意”、“性灵”等真情,但在对袁通词的评价中,郭麐所称赞的情是“友朋离合、死生契阔”之情,而对男女艳情极为慎重,对袁通所作侧艳之词,郭麐是“不敢许也”。正因为强调情的内容,所以才需以雅相规范。龚自珍不仅对以“闺房之思、裙裾之言”为外壳的词并不如郭麐那般反感,对情的表达更是不加束缚。他说:“凡声音之性,引而为上者为道,引而为下者非道……”“声音之道”“引而为下”即以声音表达阴气、怨、恨这一类悲观消极情感,排遣心中郁结之气。龚自珍明知这样会有“沉沦陷溺之患”,仍然坚持为之,原因何在?“爰书而已”。龚自珍把词看成是陈述罪行的状词,即记录自身真实情感的工具。与郭麐等浙派词人相比,龚自珍的情,因为发端于内心深处的阴气,因此无论是内在规定还是外在束缚都更少,其表达也更为自由、真实。郭麐的重情远不如龚自珍的尊情来得彻底。
(二)孙麟趾、龚自珍对“清”的体认
作为在嘉道时期与龚自珍有着直接往还的浙派人物孙麟趾,在词学上与龚自珍有着诸多交集。孙麟趾的词学观基本承竹垞、樊榭之旨,略有补充。《词迳》是孙麟趾的重要论词著作,在此书中,孙麟趾明确提出了“作词十六字诀”,即:“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17]其中,位于首位的是“清”。“清”本是浙派词学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滥觞于张炎以“清空”评白石词,与“质实”对举。朱彝尊时期,浙派强调得更多的是“雅”,至厉鹗,“清”的词风受到关注。孙麟趾在嘉道时期,浙派改革之声四起之时,重申“清”的概念,以期坚守浙派营垒。
而在作品创作中,“命意”直接影响词之“清”风格的呈现。他说:“五采陆离,不知命意所在者,气未清也。清则眉目显,如水之鉴物无遁影,故贵清。”这里的“清”即条理清晰,达到这一要求的途径就是要“命意”明确。作词之要在立意,所以孙麟趾“清”的另一层含义即“命意明确、条理清晰”。而孙麟趾“清”的最后一层含义是针对声律而言的。“词宜清、脆、涩。包慎伯明府云:感人之速莫如声,故词别名倚声。倚声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脆矣清矣而不涩则浮。”[19]孙麟趾所言之“清”与“腻”相对,是一种明快而澹净的韵律特征。
龚自珍的诗词中也时常出现“清”字,如:“和知邦政美,淡卜主心清”、“心迹如此清,容光如此新”、“晓枕心气清,奇泪忽盈把”、“赖是小时清梦到,红墙西去即银河”等。这类“清”大致可释为无杂念的心境。又有:“不似怀人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点银钩,记清愁”、“香兰一枝恁瘦,问香兰何苦伴清吟”等,这类“清”多为“淡”意;而“美人清妙遗九州,独居云外之高楼”这里的“清”,则表示高洁的人格品质。一言以蔽之,龚自珍笔下的“清”其用意大致包含:“高洁、纯净、淡雅”这几个意义。具体语境中,语义或有所偏重,但其含义仍是相通的。“清”对于龚自珍而言,更多的是一种人格理想和境界。他对“清”的感悟和追求一方面缘于童年体验,另一方面明显受释家思想的影响。龚自珍有两次用“清深”进行诗学批评:一次是评自己的诗风:“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另一次则是以“清深”评彭甘亭:“诗人瓶水与谟觞,郁怒清深两擅长”,自注曰:“郁怒横逸,舒铁云瓶水斋之诗也,清深渊雅,彭甘亭小谟觞馆之诗也”。此外还有:“先生读书尽三藏,最喜维摩卷里多清词”。龚自珍以“清深”评价自己的诗作,针对“平易近人”而言,“清”应指不落俗套、不作凡语,使人耳目一新。而“深”则有免于浅薄,托旨遥深之意。龚自珍所言之“清”其意在于新。所以这首诗中,他紧接着说道:“本无一字是吾师”。说明龚自珍不愿拾人牙慧,而要独出机杼。因此王芑孙评其诗文“扫空凡猥”,王昙亦云“绝空一世”,后人也有评曰“新奇”。[20]
龚自珍所言清深的“清”与孙麟趾所言的“清”都有出尘脱俗寓意。这是“清”所蕴含的重要含义,也是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审美要求,然而龚自珍与孙麟趾都言“清”并非仅仅是传统批评思维的惯性使然。龚自珍在《台城路》词中以“孙楚”比拟孙麟趾,这是对孙麟趾如孙楚般漱石枕流的气度和高洁品格的赞誉。在另一首小词《谒金门·孙月坡小影》中,龚自珍更明晰地刻画了自己心目中孙麟趾的形象。词中,龚自珍说孙麟趾的真面是琴与剑,与龚自珍的箫与剑如出一辙。龚自珍在诗中多次提到自己性格中的两个极端:“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少年击剑更吹萧,剑气箫心一例消”等,他在诗词中抒写的正是这种“箫心剑气”,而龚自珍认为孙麟趾是与之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人,琴与剑正是柔情与壮志两方面。龚自珍以“清怨”来形容孙麟趾的情感,认为这种情感和品性是“禅与风怀相战”的结果。孙麟趾终身未第,蹇留客乡,落魄潦倒。但现实生活困顿、仕途经济无望,都没能消磨孙麟趾的政治理想。入世、用世理想一次次在现实中受挫,而出世遁隐的思想又植根于心中,两者矛盾不可消除,所以才有了“香奁清怨”。这既是词人对孙麟趾的认识,也是对自己的总结。
龚自珍一生也一直饱受禅与“风怀”“相战”的困扰,他曾将词集题名为《红禅词》,室名取为红禅室。“红”代表了现世的纷扰,禅则是理想的超脱。“红”与“禅”的纠葛带来的是恩怨,龚自珍认为孙麟趾的清怨也同样来自于这种纠葛,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痛苦之情之所以呈现清的面貌,还是得益于佛家思想。礼佛对龚自珍而言,即自我精神慰藉,现世无从安放的箫心剑气,在这方净土才能消歇。受佛家思想影响,龚自珍将“清”作为一种理想人格甚至人生的终极目标。
孙麟趾词学理论中“清”的概念更多的是对南宋张炎等骚雅词人理论的继承和推进,具体针对词的审美和创作的要求,但是其“清”概念中超凡脱俗的旨趣与龚自珍“清深”的内涵显然是一致的。这并不仅仅是传统批评理念的耦合,更是因为两人在性格方面相似,以及同受佛学思想影响的缘故,至少龚自珍对孙麟趾的体认是如此。但孙氏的理论始终不离浙派旨要,其“十六字诀”仍是浙派理论的重申,这些看似详尽可行的填词技巧,实质上并未能对浙派词产生新的作用。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早指出了孙氏的症结所在:“大抵今之揣摩南宋,只求清雅而已,故专以委夷妥贴为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胜人者,清矣而尤贵乎真,真则有至情;雅矣而尤贵乎醇,醇则耐寻味。”[21]谢章铤认为,“清”贵乎真情。孙氏于字句、声韵处求“清”,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龚自珍对孙麟趾的“清怨”有着清醒认识,以为这是“禅与风怀相战”的结果,将这种感情视作词的生命,遗憾的是,孙麟趾似乎尚未意识到情之于词的重要性。至少他不曾将个人人生体验与思考融入到词学批评中,因而《词迳》实则并未触及到浙派“不足于情”的真正病理,这正是孙氏难以救浙派于将衰的重要原因。
三、余论
浙派的正式形成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此时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已然巩固,并对文人实行笼络政策,开鸿学博儒科,为汉族文人提供了一条实现政治抱负和用世理想的通衢。而多数文人开始离开山林,重返仕途。朱彝尊即是一例。行年稍晚于朱彝尊的浙派成员出生于清朝,对朝廷的感情自是与前朝遗老不同。而且康乾盛世中,政局相对安定,河清海晏的社会环境与醇雅清空的审美倾向相融洽。所以浙派中期成员多作咏物词,于此锤炼作词技巧,在遣辞造境、结构篇章上费心颇多。如李良年《秋锦山房词》大部分词作都是咏物词,这在浙派词人中很常见。嘉道年间,清朝统治开始衰败。有志之士一方面困于黑暗现实和沉闷的社会环境而幽愤满胸;一方面有感于政治腐朽而寻求改革之道。这样的心态投射到文学领域则表现为,文人对自我表达的重视和对抒情主体的强调,以及对各种文体范式的改革和对新写作方法和内容的积极探求。诗学领域,既有袁枚性情论强调抒情主体,又有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等新的审美要求和创作方法;而词学领域,这两种新变都体现在了嘉道词人对浙西词派的改革,作为袁枚弟子的郭麐,将业师“性情”论援引到词学批评中,为“不足于情”的浙派开出了“援情入雅”的药方;而对形式与方法的改革则有孙麟趾的“十六字诀”以及吴中词派的声律论,更有常州词派的寄托论。所以,嘉道时期浙西词派的新变既有词派内部因素的推动,亦是时代使然。
然而,由于流派理论的惯性,无论主变的郭麐还是主因的孙麟趾,都不离浙派的雅正审美要求。“词主雅正”一度是浙派理论的精髓所在,作为师法南宋,步武浙派的后学来说,这也是不易之论。所以,雅是郭麐悬于性情的绳尺。客观来说,雅正暗合了文人儒家文化中正平和的审美理想,极容易获得共鸣。有清一代,雅正已经凝定为词坛普遍审美取向,龚自珍也莫能例外。他主“畅情”,但词并不流于叫嚣,因为他张弛有度;他讲“清深”,同样也体现了他对“清雅”观的认同。龚自珍的尊情说和郭麐的“援情入雅”都是时代氛围促成的,所以两人同时关注到情并非偶然。然而,两者对情的态度确实存在明显差异,重情程度的不同更是由于个人赋性不同。龚自珍藏于心底的阴气,同常人难以理解和企及的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无力挽救社会的痛苦,所酝酿出的情感之强烈和表达之迫切自然异于时人。他的情是个性的张扬,更是自我的宣泄,这般珍视个性和自我的思想是前卫的。这种超前的思想使之成为继袁枚之后,扛起性情大纛,抒写自我的猛将。他的赋性、思想都决定了他必然肩负这一历史重任,在清代文学史上留下一抹华光异彩。尊情、畅情观是龚自珍张扬个性、释放自我的呐喊,是龚自珍奏出的时代最强音。这既是嘉道词学发展的趋势,也是固步于派中之义的郭麐、孙麟趾等人所缺的。
[1][清]蒋景祁编:《瑶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10页。
本课中,学生借助点子图,数形结合,化解了数学信息之间的不易理解的困难,通过点子图的拼摆,让抽象的思维形象地呈现,隐藏的数量关系通过“形”的表象显露出来。学生理解了三种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加深了对每种方法思路的理解,体会到了数形结合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用数形结合策略表示题中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目的。“数形结合”可以借助简单的图形(如统计图)、符号和文字所做的示意图,促进学生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协调发展,沟通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从复杂的数量关系中凸显最本质的特征。
[3]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吴无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
[4]王易:《词曲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86页。
[5][8][10][11][12][13][14][清]郭麐:《灵芬馆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4、1530、1514、1519、1532、1524、1521页。
[6][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9页。
[7][清]孙麟趾选:《绝妙近词》,咸丰五年刻本。
[9][清]袁通:《捧月楼绮语》,光绪十一年刻本。
[15][清]郭麐:《灵芬馆全集》,《灵芬馆杂著续编》卷2,《梅边笛谱序》,清嘉道刻本。
[16][宋]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页。
[17][18][19][清]孙麟趾:《词迳》,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555、2555、2555页。
[20]《龚自珍全集》,第520页。
[21][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460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I207.23
A
1000-7326(2015)11-0136-06
习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3);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