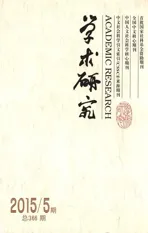晚清学堂读经与日本
2015-02-25朱贞
朱贞
晚清学堂读经与日本
朱贞
晚清教育改革,师法日本,甚至于连中国固有的经学如何安置,也部分借鉴了日本的教育经验。壬寅、癸卯学制的拟订以及清季教育宗旨的颁行,有关经学教育的规划,都能找到日本方面的影响。而来自于日本的明治汉语新词汇、教科书、教学方法和教育观念,也冲击了晚近中国的经学传承及其所维系的伦理纲常。由此带来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经学在近代中国的存在。
学堂 经学 日本
早在1906年,蔡元培就已提出,晚清各项教育制度 “多仿日本”。[1]清季壬寅、癸卯学制办法,规仿日本,学界早有讨论,并注意到清季十年变革中日本因素的影响。①美国学者任达在论述清季新政变革时,提出清季十年的变动,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桑兵进一步指出,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中国最广泛而深入的时期。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 (桑兵:《清季变政与日本》,《江汉论坛》2012年第5期)。汪婉所著的 《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与吕顺长撰写的 《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则分别探讨了晚近中国官绅赴日教育考察的具体状况。近代中西乾坤颠倒,学习欧美与日本的求强之路与传统 “礼失求诸野”的取径大不相同。晚清官绅对于在西式分科设学框架内怎样体现“中体”,即经学等固有课程如何安排的问题上,颇费思量。欧美诸国学制办法,并无经学。作为学制仿行对象的日本,对于经学进入学制和学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仔细探究。
一、晚清学制考察中的日本意见
西学分科并无经学的事实,使得部分采纳西式教育观念者主张取消经学,“喜新蔑古,乐放纵而恶闲检,惟恐经书一日不废”,[2]导致了清季在分科设学框架内如何开展传统学问一直出现争议。甲午战后,日本明治维新取得的成效让国人慨叹之余,兴起拜师念头。加之日本应对西学,本就多取材于长期受影响的中国文化,更易获得彼时国人的认同。
制定壬寅、癸卯学制,很大程度依赖于对日本学制的借鉴。清季,一些曾有赴华经历的日本教育界人士,对于晚清教育改革如何处理旧学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评议。庚子年间,曾游历中国并担任日本《教育时论》主笔的辻武雄撰写了 《支那教育改革案》,专门邮送数百册于清廷朝野上下。强调中国教育
方法必须改革,否则 “人才之盛恐未可期,富强之基亦未易望”。提及视为 “人伦之大本”的孔子之教,认为 “支那三千年之道德全系孔教所维持,是以学业修身须以孔教为主”。[3]而曾任直隶师范学堂教习的儿崎为槌,在所撰 《清国学生思想界之一般》一文中,探讨中国学生习读经书的过程、方法与效果,兼与日本教育制度作比较,认为 “要把支那四百余州、四亿人口导向文明,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拯救支那的道德,除大兴新学外别无其他”。建议中国学生抛弃 “非实用性”的经学,转向西学。[4]
儿崎为槌和辻武雄两人态度的差异,恰与明治初、中期日本教育界对待儒学的不同做法相似。江户时代,书塾与寺子屋教育大都以四书五经为主。明治初期,推行与江户时代大相迥异的教育办法,在彻底洋化的偏激主张下,提倡用西学取代中国儒学的欧化政策。甚至在1872年的太政官 《文告》中,宣告儒学不能救国,清算儒学。至1879年前后,围绕德育问题的讨论,儒学开始重新抬头。明治中期,随着东洋道德和西洋艺术口号的提出,《教育敕语》宣告恢复对儒家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注重,并推动各学校设立以传统儒学为主的修身科。在天皇主导下,日本道德之学又变成了以孔学为主。①有关明治时期儒学复活的讨论,参见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2-152、167-174页。
整体而言,庚子之后的日本教育模式,以1886年颁布的 《学校令》及之后的各项修正令为基础,确立了西式分科设学框架的日本近代学校制度。中小学的读书识字、修身等科目虽然还会出现四书五经的内容,但所学已以普及西学为主。就高等教育阶段而言,传统中国的学说除了被放进专门研究中国古典的汉学科目外,还被放入分科框架内的文学 (主要仍是汉学)、历史 (东亚历史)展开。②具体课程设置,详见日本近代教育史事典编集委员会编:《日本近代教育史事典》,平凡社,1971年,第127-128、230-242页。为了应对西式分科,井上哲次郎等人还把经学纳入了重新建构的东洋哲学文化体系。③日本教育史研究者也注意到近代明治时期西洋思想之东洋化,参见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吴家镇、戴景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7页。是以,日本设学,经学相关主要被放入哲学和汉学分科开展。
清末东渡考察日本学制者极多,对日本设学如何处理中学的做法多有留意。在考察日本大学时,姚锡光注意到日本大学校分文、法、理、工、农、医六科,文科之中,汉文属焉。[5]关赓麟具体考察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科设置,该校文科分为哲学、国文学、汉学、史学、国史学、言语学、英文学、独逸文学、佛兰西文学九科。哲学与国文学都设有汉文学科目,而汉学分经学、史学、文学等专修科,科目互有不同。[6]日本师范学校与大学类似,以汉文科讲授经学。朱绶考察日本男子高等师范,文科分为伦理、教育、国语、汉文、英语、历史、地理、哲学、理财、体操等九科。[7]王景禧考察小石川区大塚窪町高等师范学校,学科分为预科、本科、专修科,本科与专修科都列有国语汉文类,“听汉文讲师宇野哲人讲授 《左氏传》及 《老子》,学生皆极意体会。”认为日本高等学堂,仍注重汉文。[8]
部分在日华人学校,则设置了专门读经的学科。如横滨的商立中国大同小学校,由中华会馆专为教育在横滨经商的中国子弟及游学人员而设,分高等、寻常两科,课程与日本小学校略异。在高等学堂课程中,分修身、读本、史学、地理、英文、日文、理科、文学、算学、写字、绘图、体操、唱歌等项,其读本课程主要就是读四书。[9]
一些教育考察人员刻意寻找日本国内保存旧学的痕迹,以作为维护经学的依据。缪荃孙认为日本维新变法后,国中古礼相沿不废,“且于学校特设一科,所谓国粹保存主义也。”[10]批判中国新学家动诋古礼的行为。林炳章则发现,日本文部省于明治五年至十二年审定教科书,“修身杂引我六经诸子语”。日本汉学名家,亦时有人。而保存国粹、注重德育之议论,数见不鲜,“知孔教之精,亘古不可磨灭。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非浅流所能增损。”[11]
由于明治初年视儒学为无用,到 《教育敕语》颁布后重新提倡以儒学培养旧道德,日本国内对于如
何处理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极大的变迁。是以,当时日本的教育界人士,对于中国学制应如何处理经学的意见并不统一,“此邦有识者或劝暂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再复古学;或谓若废本国之学,必至国种两绝;或谓宜以渐改,不可骤革,急则必败。”[12]
罗振玉东游日本,获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告知,新式教育不可抛弃经学:“今日不可遽忘忽道德教育,将来中学校以上,必讲 《孝经》、《论语》、《孟子》,然后及群经。”[13]胡景桂考察早稻田大学,获校长大隈重信提示,中国开办教育,要把经书融入伦理教育,“宜先颁明诏,将五经、四书有关伦理者,另编读本。史鉴中易感动人心者,撮其要领,编为修身书。此非废弃经史、割裂经史也。将来专攻文科者仍责令全阅,不过藉此简易之编,以一天下之志趣,以正天下之人心。”[14]二者意见,反映了明治中期后以儒学培养道德的日本官方态度,强调经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在是否开设经学专门的问题上,已有了细致的分歧。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接触众多日本教育家,得来有关中国传统教育的论调以变革为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科教授井上哲次郎告诉吴汝纶,“教育不应时事,则无其效。孔子之教大好,然今日则见其未备”。虽然旧学不合时用,但日本的教育家大多并不赞成完全抛开经学,提出以中西兼顾为宜。尤其是从道德培养的角度出发,更要注重经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认为,“今时当路皆知西学之为急,而汉学则殆不省”,因学徒脑力有限,“姑择其急耳,然其弊则至忘己”。所以建议吴汝纶要将学堂各阶段中、西学课程合理分配,“今贵国设西学,欲汉洋两学兼修,患课程之繁,小中学、高等学校 (大学预备校)课程半汉文、半西学,而晋入大学则专修其专门学,则庶乎免偏弃之忧。”[15]曾担任文部省官员并参与制定 《教育令》的田中不二麻吕则强调课本无论大小学堂,宜行酌量。如道德不取耶稣,而取孔孟之教。[16]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高桥作卫并未与吴汝纶见面,却专门作 《与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吴君论清国教育书》,建议中国振兴学制,“宜以孔道为学生修德之基”。[17]
晚清时期的日本教育界,在中国旧学是否以及如何纳入新式学堂等问题上给予意见,其原因除了当时日本国内提出帮助同文同种的中国进行改革,分享自身学习西学的教育经验,如同大隈重信1903年在早稻田大学校友会上提到中国教育问题,“对于中国,除外交和政治以外,还可以通过同文同种的关系,对其进行扶助诱导和开发”,[18]以使中国接受东洋化后的西学,进而奠定日本在东亚思想界的话语权外,还有现实因素的考虑。1900年前后,日本国内的高等教育开始扩张,在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增设九州大学及东北大学,导致汉学科急需教师。甚至于日本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就是为了培养在新设大学中担任讲座的汉学相关教师,有研究指出,“正是在帝国大学设置分科大学并引入讲座制,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文部省为培养胜任与中国相关讲座的教授,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①谭皓:《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研究 (1871—1931)》,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9-151页。从1899年到1911年前后,除了上文提到的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外,狩野直喜、伊东忠太、冈本正文、桑原骘藏、岩谷温等几人亦先后赴华留学。这些都导致了日本国内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不能不有所留意。
二、东学影响下的晚清教育改革
曾经注重儒学后又成功师法欧美的日本,符合晚清学习西方兼能安置固有文化的需求,完成了先为弟子复为师的角色转变。从壬寅、癸卯学制的先后出台,乃至清代教育宗旨的颁布,各项有关经学教育的规制,都能找到日本因素的影响。但经学乃中国固有,并负有维系伦常的功能,清廷教育改革,势必不能依照明治维新先弃后扬的步骤进行。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依据东学建构起来的学制系统,也因个人对中西学处理意见的不同呈现差别。
日本教育界的意见,对晚清兴学产生了具体影响。在参考日本学制的基础上,一些赴日游历考察人员开始考虑如何把经学课程具体规划到学堂中去。罗振玉在参考日本学制的基础上草拟了 《学制私议》,
对于各阶段学堂经学课程的内容有了划分,主张 “将五经、四子书分配大、中、小各学校,定寻常小学第四年授 《孝经》弟子职,高等小学校授 《论语》、《曲礼》、《少仪》、《内则》,寻常中学校授 《孟子》、《大学》、《中庸》,并仿汉儒专经之例专修一经,其余诸经为高等及大学校研究科。不得荒弃,以立修身道德之基础。”[19]项文瑞在考察日本学校后,为上海闵行镇务敏学堂草拟办法,分为修身、读经 (讲解)、字课 (作文)、习字、历史、地理、算学、体操、读古文词、图画、理科、英文等项。提出读经教授以《论语》、《孟子》、《礼记》、《周礼》、《左传》五种为要,并在诵读之外,强调默写,“听毕,令默写。其益,比读更多,而班渐可齐”。[20]甚至于日本创设的一些新式学科,也开始为当时学人所注意。如罗振玉创办的 《教育世界》即添加了哲学栏目,由王国维主笔。
与日本明治教育政策先去汉学后又提倡的调整不同,中国晚清教育改革最初就已确定将经学列入学制,并加以注重。负责拟订壬寅学制的张百熙,在1902年的 《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即主张大学堂先办预备科,功课 “略仿日本之意”,以经、史隶属政、艺二科下之政科,“四书五经,……自应分年计月,垂为定课”。[21]显示其已有在分科观念下设立经学课程的主张。而在学制出台前,张百熙曾与张之洞电商学制事宜,肯定了日本学制作为仿效对象 “尤为切用”,并专门就教育内容和层级划分探讨新学制下设经学的大致办法。[22]
在如何应对西式分科的问题上,中日情形毕竟不同。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西式分科有史学可以对应。但经学既无对应,日本的汉学做法也不可行,再加上哲学一词被保皇派的梁启超大肆使用,也为清廷不喜,不可借用。因此,日本教育经验一方面提供了学制框架,另一方面以文学分科归类和以修身、伦理涵盖经学为主的道德培养就成为旧学分科借鉴的办法。
在张百熙的主持下,中国首个统一学制诞生。 《钦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壬寅学制,划分普通学堂与专门学堂的体系,并以分科设学办法对原有中学课程进行规划。但经学虽列入学堂课程,却主要以日式分科框架来处理。尤以大学分科章程展现得最为明显,仿照日本设文学科,将经学列为其下分目。在经学分科的具体设置上,显示出了对于 “参考日制”的偏重。整体反映在学制课程中,“东、西洋”学的色彩较为浓重。①这并非毫无缘由。张百熙在应新政改革上谕的奏疏以及进呈学堂章程的奏折中,显示了对于 “参考西制”的偏重。其重用的参与谋划学制章程的沈兆祉、李希圣等人,也勇于革新,使得时人谓 “北京大学堂中皆新党人物”。见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正由于壬寅学制较为趋新,引起争议。是以清廷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后,《清史稿》认为此举用意在 “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23]说明仿行日本的壬寅学制,并未能体现经学等固有学问的特殊性,也成为后续癸卯学制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与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实则主持了癸卯学制拟订的张之洞,对于壬寅学制的较大一项调整,就是增加经学比重。癸卯学制是张之洞在借鉴日本学制框架的基础上,②张之洞除了鼓励留学日本外,还曾专门委派后来拟订癸卯学制的助手陈毅赴日游历考察教育,陈毅在致那珂通世的信函中对此有记载,“仆两次东游,专为考察教育。归谒总督张公,力陈国民教育当重之旨”。李庆编注:《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将湖北办学经验与个人治学观念结合,对壬寅学制进行修订的产物。相比壬寅学制,不仅修订了中学的具体分科办法,调整增加了各类各级学堂经学课程的比重和内容,并在分科大学的规划上体现出明显的不同。与壬寅学制参照日本大学分类办法,将经学置于文学科下迥异,癸卯学制则将经学、理学放入专为中国固有学术而创设的经科大学,史学、文学则放入可以对应西学分类的文科大学。专门的经科大学,又下分周易学、尚书学、毛诗学、春秋左传学、春秋三传学、周礼学、仪礼学、礼记学、论语学、孟子学、理学11门。[24]显示了癸卯学制虽然同样沿袭来自日本的分科设学办法,却又注重凸显以经学为核心的 “中体西用”的中学分科方案。
不过,癸卯学制的做法,却又被主张沿用日式分科框架的时人视作难以理解。当时教育主张仍旧趋
新的王国维,在看过大学堂分科章程后,认为经学与文学内容联系密切,“必欲独立一科以与极有关系之文学相隔绝,此则余所不解也”。[25]不赞同将经科与文学科分列,主张废置经科,仍放入文学科下。若想显示尊经之意,则将文学科置于各分科大学之首即可。而且,日本没有设置独立的经学科目,癸卯学制各科并设,势必引起有关经学与伦理、修身共存问题的争议。舆论指出修身、伦理内容多取自四书五经大义,与读经课程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26]故当时有人提出,或将经籍大义归入修身,[27]或将修身、伦理归入读经课。[28]
由日本移植而来的分科设学办法,经过内化而最终演变成晚清的癸卯学制,将中西学共容于新式学堂。虽然在经学的保存上,癸卯学制分科并未完全按照日本模式进行,但日本教育界的经验仍然成为朝野论证学堂读经合理与否的重要依据。
官方层面,除了学制仿行外,1906年出炉的晚清教育宗旨同样表现出了对日本办法的借鉴。学部侍郎严修拟定的教育宗旨,[29]本就受到日本 《教育敕语》的影响,定为五条: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所谓 “忠君”,在于宣扬保存帝制。而 “尊孔”一说,特别引用日本历史来证明中国学堂教育保存经学的合理性,“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节,激发忠义”,得出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的结论。[30]
在野层面,对于舆论出现的经学无用论,时人同样以日本近代史事作为辩驳的论据。刘师培指出泰西敦崇考古,日本明治维新尊王大义取自春秋大义与宋明儒术,皆为 “中国学术足以效用之证也”。并认为当时欧美诸国都在研治泰东古学,日本大学也列为汉学专门,如中国自丧本国固有,将贻诮于邻封,所以主张定经学为学堂必要科目。[31]当时舆论还试图借鉴日本教育界软、硬教育的学说,论证读经的可行性。日本汉学家远藤隆吉认为江户时期令学生谙读四书五经,效果非常好,导致了明治维新时期的伟大人物多由此而出,谓为硬教育。而新时代的学校教育教材简单,又考虑开发儿童兴趣,以致养成儿童畏难苟安,谓为软教育。该说一度影响中国,认为不能仅从儿童兴趣出发注意软教育。提倡经学课程作为硬教育,对于学生能力和道德的培养有一定好处。[32]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治初期与 《教育敕语》颁布后对于儒学的态度截然不同,导致晚清国人同样标榜学习日本教育经验,却各有取舍。清季,提学使东游日本考察,即注意到日本明治中期后国内以“孔孟之学”补救学校弊端。吉林提学使吴鲁发现:“近来教育家如嘉纳、伊泽辈欲提倡孔孟之教,讲明道德,以端风化而正人心。”[33]陕西提学使刘廷琛也发现日本欧化盛时,不免弊害,赖以道德挽救,推崇孔孟备至。并认为 “日本陈迹,实足为前事之师”。[34]接受了新式教育观念的时人,则认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步入文明国家,一大原因就是明治初年从重汉学转为 “采取欧美诸国教育新法”,[35]注意到经学 “无用”的一面。赴日考察的关赓麟注意到日本维新以前,盛行汉学,其时学校课本概用中国之四子、五经,无所谓教科书,“迨西洋文物输入之顷,稍知汉学之无用,乃一变其制度”,最终 “十余年间,文明思想播于全国”。[36]相关论述,为后来的新教育家所沿用,普及教育的强国之道就变成了效仿与学习日本明治初期移植西学的取径,反对学堂读经。
三、“挟东洋自重”与经学存续
晚清学制改革,引入了西式分科设学框架,又因为仿行日本,添加了许多东学因素。就旧学而言,西式分科无法对应,日本将西学东洋化的做法成为了重要的借鉴取径。表面上看来,经学进入学制和学堂借鉴了许多日本教育界方面的经验,似乎对于晚近时期的旧学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实际造成的后果,却对经学本身延续及其维系伦常的功用都产生了冲击。①当然,除了中学外,近代中国接受的西学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东洋化后的西学,诸如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方面。至于晚近日本对于中国接受西学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不再赘述。
从日本逆输入的大量明治新汉语,动摇了晚近经学的传承。对于文字语言变革与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张之洞在拟订癸卯学制时已有注意。在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出戒用外国无谓名词,以 “存国文、端士风”,出自古人 “文以载道”之意,注意文法字义对于旧学训练的影响:“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37]张之洞提到的很多词汇,都是从日本而来的,而且数量极多,“日本逆输入的汉语新词数以千计,其中使用频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约500个。……就此而论,清季以来,中国人实际上可以说是用西思,发汉音,说日语”。①桑兵:《清季变政与日本》,《江汉论坛》2012年第5期。有学者指出,在 《学务纲要》这一规定的背后,显示了清廷在学制章程的拟订中,已注意到文法字义的转变,“且上升到危及中国学术风教存亡的高度”。②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 “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55页。而刘师培也撰文表达了同样的观感,“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致使 “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38]刘氏此话在于梳理中国文学变迁,却也说明新文体与名词的输入,已影响到中国文学本身。
从文以载道的角度出发,文字、文学的变化,会导致对于经学等固有学问的理解出现问题。宋恕提出 “愈古之书,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则又恐训诂益荒,古书将无人能读”。[39]是从经学训诂角度理解文字变迁带来的影响,认为将导致经学理解困难,出现 “无法读古书”的困境。而经学本身承担的维系伦理纲常和道德秩序的功能,也因自日本输入的西方伦理学内容受到影响。晚清学堂中伦理与修身科目的主要内容,本来多系经学所出。然而,随着翻译日文书籍的大量输入,③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籍至少在千种以上。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各种思想随之而来,修身和伦理的知识体系开始发生变化。
日本宏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曾就中国教育状况对留日学生发表演说,论述了如何于发展新教育的同时兼顾经学道德培养的问题:“中国言德育,所取者孔子经训而已。但孔子之经训,活用之则为国家文明之要素,死守之则为糟粕之陈言。趋入二十世纪文明之世界,而但取口舌间之伦理与模范上之观念,以装点门面,并不足以应无方之世。……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为教育。然其所以活用之方法,则必深明中国旧学,而又能参合近世泰西伦理道德说者,乃能分别其条理,而审定其规律。”[40]按照这种观念,过去伦理纲常与道德模范的旧学培养方式,已不适合新时期的文明社会。要活学活用中国旧学,需将中国旧学参合西方伦理道德学说,中西杂糅才能适合时代发展。就日本自身教育发展而言,这种观念是逐渐形成的。1902年,梁启超探讨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得失,专门指出其初始阶段未尝留意德育,致使 “举千年来所受儒教之精神,破坏一空,而西人伦理道德之精华,亦不能有所得”。[41]日本国内的开明派与守成者围绕1878年田中不二麻吕所拟 《教育令》和1879年井上毅起草的 《教育议》也掀起过有关道德培养的论争,核心问题即在于如何协调学习西方和保持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此后,1882年颁行的 《幼学纲要》开始明确提出来自欧美的修身伦理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东亚,要把儒家五伦道德作为教育根本。1890年的 《教育敕语》确立了 “和汉道德”的重要,宣扬以其为基础的将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杂糅在一起的道德教育体系。④参见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2-147、167-169页。虽然强调道德之说以儒家为根本,但新道德体系的建构却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西方思想的内容。
自日本借鉴而来的修身、伦理教材,添加了许多西方伦理学的内容,势必危及经学维系的传统道德体系,引起教育界的混乱。王先谦就专门提出,由于日本效法西人,致使中国引入的日本 《修身科教授法》、《伦理书》等书所载伦理,非中国所谓修身和伦理。如果以此教导中国学童,会致使 “伏无数乱机。父兄不能束其子弟,官长亦安能有其民人哉”?建议对相关书籍加以裁酌,否则 “贻误后学,流为乱阶”。[42]但自甲午以后,时人对于学习日本教育方式培养人才,进而谋求富强与进步的主观意愿加强,日本译著大受欢迎,甚至难以查禁。如元良勇次郎所撰 《中等伦理学》,由文明书局翻译出版,学部认为中西学说杂糅其中,尤多荒谬,下令查禁,“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43]
朝野竞相标榜学习日本西洋,还导致了固有学术的衡量办法也进一步外洋化,评判标准逐渐变成以东西洋为先进、中国传统为落后。所以在以东洋为师的晚清教育改革中,日本教育经验混淆了传统经学的教授办法。吴汝纶在1902年就提出了 “新旧二学,恐难两存”的忧虑,理由之一即是中西学存在差异,“西学但重讲说,不须记诵,吾学则必应倍诵温习,此不可并在一堂。”[44]癸卯学制中,官方强调读经办法借鉴外国,注重讲解,使得学堂经学教育与中国传统诵读办法出现偏离。及至宣统年间学制调整,面对经学教育出现种种问题,学部明言采纳了日本学堂对于一些学科要求熟读成诵的办法进行调整,强调多读而不成诵,不如少读而成诵,表示改良经学教育的学制调整也师法日本。忽略了记忆与背诵之学,是中国书塾教授的传统办法。1908年,各地间有塾师反对以学堂办法改良私塾,理由即有“记忆与背诵之学不可偏废”。[45]即便是对中日两国教育都很熟悉的赴华日本教习,也认为中国旧学教育,本就是 “以经典诵读入门”,早期主要凭借记忆力研习经籍。[46]学制本身,已是按照西学分科办法规划经学等中学课程。但探索固有学问的治学途径,真正理解中国学问,本应以国人为重。[47]宣统年间的学制改章,官方强调用日本学科的办法来改良经学课程,注重诵读反变成了师法自日本的教育经验,反映了近代教育转型中时人的不自信,以至于改革的思路变成以师法东西洋为进步。甚至于解读中国学问的办法也逐渐取径外国,经学教育的办法开始渗透进较多比附的内容。穿凿附会,或照搬日本讲义授受,或讲解经义比附东西学,经义授受开始脱离故往。
传统经学授受,大都是按书讲学。借鉴东学的晚清教育改革,引进了教学使用教科书的做法。山西优级师范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将日人所作 《论语类编》、《朱子孟子要略》等书直接作为教科用书。[48]个别书局采用将经书通俗化并比附东、西洋新学的读本,作为教科书出版。1905年,彪蒙书室印行《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一套,作为蒙学修身及读经科教科书。[49]该书希望借新编经学教科书宣扬西学,如 “解大学在明明德,既推到德律风之德,又绘为德律风之图;解心广体胖,既推到体操之体,又以体操为练习;解论语时习之习,绘为体操之图”。在绘图与内容上,都与前人解经办法取径迥异。并极力将西学知识融入释义,“解贱而好自专说到专制政体,非天子不议礼说到下议院权。尤与圣贤背道。”[50]解读经义比附新知的这一读经教科书,在直隶、广东等地使用极多,奉天辽阳州所属小学堂读经一科甚至皆用该读本教授。[51]学童在此基础上得来的对古代经籍的认识,自然是以西学为填充,远非经典本意。在旧学宿儒眼中,新式学堂以此教科书为教,类同外国人读中国书,表面似是,实际却非。
而学部对此很是注重,希望通过教科书的审定,去除附会之弊,端正经学教育趋向。如但焘著 《周礼政诠》,学部即批示毋庸审定,理由即是该书取日本政俗,以证 《周官》例言,“一一牵合,转不免多所傅会。如曰衣服之为学校制服,……其他解释经注处亦间有误会”。[52]上述 《绘图四书新体读本》也遭到学部查禁,认为该书 “误学童”而 “滋谬种”,通行各处严禁。[53]
在教授课程时,一些经学教习开始引入经过日本过渡而来的西方教育学理论。如德国教育学与心理学家赫尔巴特的 “五段法”教育理论,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被改用在经学教育上。所谓五段法,笼统来说,即将教学过程分为预备、提示、联想、系统与方法 (应用)五个阶段。这一教育理论,在清末民初教育思想中流传极为广泛,据俞子夷回忆,“首次大战前,小学教法主要从日本输入,而其内容与本质主要是基于五段法的一套。”晚清小学堂,多加使用。如1903年的南通师范实习小学,“五段法是常
用的”。[54]五段法与经学被逐渐联系起来,1907年,《河南教育官报》刊出了名为 《孔圣五段教授法》的文章,将中国旧学授受比附到这一教学理论上来。而一些新式小学堂的读经课程,明确标榜使用五段法。1907年的河南辉县学务调查,发现一些教员用五段教授法讲经,视学员大为赞赏,认为 “尤能推陈出新,实为各属之冠”。[55]
对于处理中国固有学问仍然 “挟洋以自重”的做法,当时的学人并非没有注意。1902年,张元济在谈及教科书问题时,就明言来自于外国的教科书不能沿用,原因即在 “取径迥别”,一些甚至与中学绝无关合。[56]1910年,章太炎提出古书的训诂文义,从中唐到明代,一代模糊一代,以前中国人自己尚不明白,外国人自更难明白,“你看那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而且日人成见已深,又不晓得中国声音,不明训诂,“几个老博士,翻腾几句文章学说,不是支离,就是汗漫。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指明由于彼时办学的不自信,才会出现办学诸事出现皆以外人判断为准的倾向。强调讲学问、施教育,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以外人品评定其贵贱。自国的人应该讲自国的学问,开展自国的教育,“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57]虽然民国时期,不乏有日本学人提出经学或失于中国而存于日本之说,①本田成之在 《支那经学史》一书结尾,提出 “像经学这一类学科,或将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的说法。见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320页。但晚清经师宿儒仍大量存在,在旧学问题上当然有自信做出点评。
但问题在于,晚清讲求西学或东学已变得流行开来,一些学人趋新的同时,又不希望抛弃旧学,以至于讲新学又附会经书作为依据。如刘尔炘所说,“西学渐盛之时,士大夫往往以讲求新学为趋时之要务,或附会经传以明所学之非外道”。[58]而学生稍窥故编,昧于择别,对于经书难免有畏难情绪。不感兴趣者,则一无所获。即便认真研读,所学也已较中国传统学问本身有所差异。这种经学教育的隐忧,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开始有所发现,并试图加以纠正。但纳入西式分科框架体系内的经学本就面目全非,晚清日本的影响又添加许多纠结,正本清源不仅难上加难,还容易贴上顽固守旧的标签,致使后人距离传统学问的本意越来越远。
[1]蔡元培:《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2-453页。
[2][21][24][30][3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4、832-835、770-814、151-153、85页。
[3][17]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193-194页。
[4][46]儿崎为槌:《清国学生思想界之一般》,《教育研究》,明治38年 (1905年)4月1日,第72-74、85页。
[5][6][7][8][9][13][15][16][19][20][36]王宝平主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81、114、638、212、222、363-367、375、238、439、170-177页。
[10][11][14]王宝平主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下),第528、556-580、608页。
[12][44]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406-407页。
[18]《大隈伯的对清教育谈》,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6-327页。
[22]《致京张冶秋尚书》,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卷249,电牍80,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45页。
[23]赵尔巽撰:《清史稿·荣庆传》卷439,列传226,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401-12402页。
[2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1906年第118、119号。
[2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1904年8月19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27]《奏定小学堂章程评议》,《时报》1904年5月22日。
[28]《上学务大臣条议》,《湖南官报》第603号,1904年3月25日,专件。
[29]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补:《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第180页。
[31][38]刘师培著、钱钟书主编、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4-105、154页。
[32]蒋维乔:《论硬教育与软教育》,《教育杂志》第5年第9期 (1913年12月10日),言论。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内政类,5470-63,缩微号:413-2481,吴鲁。
[34]《署理陕西提学使刘廷琛奏陈调查日本学务情形片》,故宫博物院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卷70,第11页。
[35]谢洪赉:《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166-170页。
[39]宋恕:《粹化学堂办法》,宋恕著、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77-378页。
[40]《日本宏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演说》,《湖南官报》第307号,1903年3月8日,论说。
[41]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新民丛报》第1期,1902年2月8日。
[42]王先谦著、梅季标点:《葵园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901-904页。
[43][4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三: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15-122页。
[45]《私塾改良难期实行》,《中外日报》1908年3月7日。
[47][57]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0、517页。
[48]罗襄:《重印论语类编孟子要略序》,《湖北文征》第1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50]《广东提学札各属禁用彪蒙书室绘图四书新体读本文》,《福建教育官报》第9期 (宣统元年三月),文牍。
[51][53]《督宪杨准学部咨禁用上海彪蒙书室教科书札饬提学司转饬遵照文》,《北洋官报》第2112册,1909年6月26日,公牍录要。
[52]《但焘呈周礼政诠毋庸审定批》,《学部官报》第137期 (1910年11月2日),审定书目。
[54]俞子夷:《现代我国小学教学法演变一斑——一个回忆简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4期。
[55]《河南教育官报》第11期,1908年1月4日,本省学务报告。
[56]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陈景磐、陈学恂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58]刘尔炘:《果斋遗言》,《刘果斋先生年谱》,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传记资料辑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6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K252
A
1000-7326(2015)05-0111-09
朱贞,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