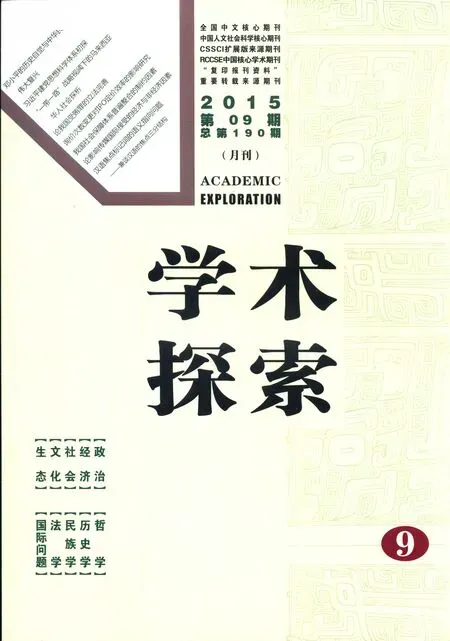论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2015-02-25曾粤兴孙本雄
曾粤兴,孙本雄
(1.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北京师范大学 刑科院,北京 100875)
论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曾粤兴1,孙本雄2
(1.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北京师范大学 刑科院,北京 100875)
受贿罪在主体、罪状表述、情节考量、刑罚体系等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受贿罪的主体应当从“身份论”转向“公务论”,更加注重公权力的廉洁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表述太过模糊、暧昧,应将其修改为基于职权或权势。财物说、财产性利益及部分非财产性利益说、利益说均存在缺陷,应将受贿对象限于财产性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除为理论及实务界徒增烦恼之外,别无他用,应予以取消。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应该以数额为主,兼顾其他情节。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缺陷,应该废除死刑、完善罚金刑及没收财产刑。
受贿罪;立法完善;贿赂犯罪;立法表述
一、受贿罪的主体应为“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
我国《刑法》第385条将受贿罪的主体局限为“国家工作人员”,体现出浓厚的官本位特征,是传统“统治型”思想的体现。但是,事实上传统的“统治型”观念不仅为腐败违法犯罪行为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温床,也为全民参与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设置了观念上的障碍。因为在“统治型”观念主导下,官员们总是以统治者自居,加之官员在经济社会分配过程中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和深化,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发展是在自己的统治与管理之下铸就的,更多是自己的功劳,自己从中获取一小部分利益也理所应当,这就是能人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囿于官本位思想,人民群众总是被看作被管理者,从而削弱了监督和揭发腐败犯罪的动力。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化,公务行为逐渐从“统治型”向“服务型”转变,随着市场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也随着公务行为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现今通过具体列举“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方式已经与政府职能调整不相适应,呈现出滞后性。况且,受贿罪的本质在于“钱权交易”,更加注重的是“公务”行为,而不是行使公务的人的具体“身份”。因而,受贿罪的主体应当从“身份论”转向“公务论”,更加注重公权力的廉洁性而不是身份的特殊性。
就受贿罪主体的条文表述而言,有学者认为应表述为“公职人员”。[1]但是,此种表达仍不理想,其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因为公职人员即从事公职的人员,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身份,而不是职务。故应将受贿罪的主体表述为“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样在实现“身份论”向“公务论”转化的同时将关注重点集中在“公务”上,体现了受贿罪的钱权交易本质;而且,在囊括了现今国家工作人员所指涉范围的同时,避开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不恰当解释的批驳,直接指向这类犯罪主体的本质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不仅包括外国人,而且也包括在国际公共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
二、完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
就现在受贿罪的立法而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成立的法定要件,但学界就是否应该保留该要件及如何理解该要件存在争论。就是否保留该要件而言,学界存在不要说和必要说的争论。前者认为,只要无正当理由收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就应当构成受贿罪。[3](P225)后者认为,受贿罪的成立要求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这是刑法学界的通说。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表述上稍有不同。即前者通过“正当理由”、遵守“国家规定”来表达后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表达的内容。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刑法理论界存在法定职权说与实际职权说的争论。前者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该依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毕竟法律、法规对公权力均具有明确的授权;后者认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读应该以实际职权为依据,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行为人所享有的职权往往较法律、法规规定的要多,如果仅以法定职权作为参考依据,那么犯罪嫌疑人就会以其利用的不是法定职权、其行为不属于权钱交易等为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不利于惩治受贿犯罪。[4]我们认为,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应该以法定职权说为参考依据。一方面,我国法制仍不健全,公权力长期缺乏明确的界限,尤其是党政合一的现实条件下,公职人员所享有的权力较法定授权宽泛得多;另一方面,受贿罪的本质在于钱权交易,不管权力是否合法,只要符合了钱权交易的条件、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即应构成犯罪,而且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也将职务上的隶属、制约关系等纳入射程,这足以说明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法定职权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表述太过模糊、暧昧,这是造成学界有学者在明确了利用职务便利的参考依据之后,还花较大篇幅论述何为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而且,这一表述中的便利到底是何种便利也不无疑问。因而,有必要对该表述予以修正。受贿罪属于钱权交易型犯罪,而现行刑法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目的在于将钱权交易这一本质表述出来,故在对这一表述进行修正时,应牢牢抓住其存在的意义与目的。权表现为职权和权势,职权包括主管、分管、经办、参与及相关职务行为(包括合法与非法),权势包括隶属、制约等。因而,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基于职权或权势。这样不仅简单明了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同时,也将权钱交易的本质予以展现出来,较为合理。
三、将“财物”修改为“财产性利益”
对于受贿罪的对象应该为何,理论上存在财物说、[5](P221)、[6]财产性利益说、[7]财产性利益及部分非财产性利益说、[8]利益说等学说的争论。[9](631)、[10]笔者赞成财产性利益说,理由如下。
第一,其他学说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财物说将受贿罪的范围限制得过窄,不利于有效打击受贿犯罪,“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司法解释中将财物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即为最好的证明;主张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受贿罪贿赂范围的观点有过于理论化的嫌疑,因为刑事立法如若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滋生司法腐败,那么再完善的刑事立法也只是空中楼阁。例如,主张受贿罪包括收受非财产性利益的论者往往赞成将性贿赂犯罪化,认为其具备了钱(利)权交易的本质,腐蚀了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与构成要件。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存在诸多缺陷。理论上认为,性贿赂一般包括三种情形:“自己出马”、“花钱培养女公关(公司职员)”、“花钱寻找女公关(职员以外性工作者)”,前两种形式难以计算财产性利益,后一种形式,相当于受贿人自己花钱找性工作者,可以计算金额。实践中,有的法院对后一种形式的性贿赂即按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受贿额。从李薇等实际发生的性贿赂案件来看,其获得的利益往往巨大甚至特别巨大,说明社会危害性更大,但目前纳入受贿罪、行贿罪处理难度过大,不仅取证困难,而且容易造成与财产性行贿犯罪处罚上的失衡,还容易导致受贿罪因涉及隐私而不公开审理,影响案件审理效果。只有在今后全面修改广义上的贿赂犯罪的前提下,才有性贿赂入罪的时机。
第二,将财物修改为财产性利益符合我国的国情,不会放纵犯罪。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攻坚克难阶段,腐败形式多种多样,社会各界均要求对腐败犯罪实行零容忍,以至于出现扩大受贿犯罪范围的呼声,但是这一扩大不是无限的,应该结合司法实践,将法律的可实施性作为法律修改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我们认为受贿罪所收受的财物应该修改为财产性利益。一方面是将现行刑法中的财物解释为财产性利益,有超越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应该及时修改刑法;另一方面,将财物修改为财产性利益,能够很好地打击新型受贿犯罪行为,不会放纵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贿行为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但是通常的受贿行为都是权钱交易,或者说能够用金钱来衡量,无论是会员卡、著作权转让还是其他权利凭证的虚假转移都是如此。而且,刑法不是治理受贿犯罪的唯一手段,我们也能通过诸如行政法规、党纪法规等来规范受贿行为。故而,采用财产性利益说不会放纵犯罪。
四、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
就“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言,学理上存在保留说与取消说的争论,取消说为多数说。笔者认为,取消说较为可取。
第一,保留说存在诸多问题。保留说存在多种看法,为论述方便,我们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主张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表明财物与职务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要素,他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是客观要件,也不是主观要件,更不是主客观统一要件,而是证明受贿人收取的财物具有贿赂性的对价[11]、[12]、[13](我们称之为对价性质说);另一类主张将“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抑或主客观统一要件(我们称之为主客观要件说)。我们认为,无论是对价性质说,还是主客观要件说,均有不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亦即上文所主张的基于职权或权势)已经表明了收取财物的贿赂性对价,无须再画蛇添足加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这一要件的添加除了为理论及实务界徒增烦恼之外,别无他用,主观说、客观说及主客观要件统一说的学说争论即为例证。主客观要件说中,无论是旧客观说的行为型理解、新客观说的许诺型理解、主观说中的动机(受贿人的心态)型理解,还是主客观统一说中的“行为+许诺”型理解都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为受贿人留下了钻法律空子的空间,且也与受贿罪的本质相违背。众所周知,受贿罪属于职务型犯罪,其所保护的客体是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可收买性),也即拿了工资等合法收入之外不该拿的财物就应构成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留下了狡辩的空间,也人为抬高了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不利于有效地治理受贿犯罪。
第二,取消说并不存在保留说所指责的所谓缺陷。对价性质说认为要件取消说只是回避“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与矛盾,无益解决司法实践的困境。[11]但是,我们认为,论者的批判只是就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而言的,其没有站在整个受贿罪的罪状表述中来分析和思考问题。我们主张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前提是借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亦即上文所主张的基于职权或权势)这一要件来展现收受财物的贿赂性,这与论者的初衷是一致的,不存在回避矛盾的问题。
第三,取消说顺应时代潮流,与国际社会惩治受贿罪的趋势相适应。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要求对贿赂犯罪抓早抓小。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观点主张扩大对受贿犯罪的打击范围,严密惩治受贿犯罪的法网,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刑事政策相契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日本、意大利等法治国家均未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作为受贿罪的成立条件。[2]
五、科学设置受贿罪的犯罪情节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受贿罪属于典型的数额型犯罪,但是唯数额论在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不足,我们主张受贿罪的立法规定应该以数额为主,兼顾其他情节,在数额的考量上,我们主张摒弃确定数额的形式,因为确定数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呈现出滞后性,就像1997年刑法将受贿罪的刑罚标准具体确定为五千、五万、十万,在公民平均收入均有明显增长的今天,这些确定性的标准显得过于不合时宜。但是,将数额与行为人的平均工资标准相联系,采用倍数制的形式规定,不仅使得受贿罪的数额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动,呈现出动态性;而且,将受贿罪的数额与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平均工资标准相联系,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量刑的均衡化。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有学者认为受贿罪的数额确定可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准来具体确定比例。我们认为,受贿犯罪通俗而言,属于官员犯罪,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则是全民标准,属于民的范畴,依照民的标准来对官吏,不具有恰当性。因此,我们主张受贿罪数额标准的确定应当参照官员的年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就具体操作而言,应当参考当地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年平均收入来确定受贿罪的刑罚适用前提,尽管不同层级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与消费层次不一,因人而异的标准表面看起来更符合实质正义,但不利于刑法的统一适用,也会给检察机关造成举证上的难度。故应该根据当地从事公务人员的年平均收入,设计相对统一的标准,以实现刑法适用的统一性。根据赵秉志教授的研究,受贿犯罪的入罪门槛应为3万元,数额较大上限为30万元。[14]3万元大致相当于基层公务员的年平均收入,30万元与基层公务人员年均收入10倍基本相当,①《各地基层公务员工资调查:多略高于当地平均工资》http://local.chinaso.com/detail/20141113/1000200003265141415876028 178537622_1.html,2015年7月10日访问。因而,我们主张将现阶段受贿罪的入罪门槛确定为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的1倍,而用“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10倍”替换现在立法所主张的数额较大标准的上限,然后在从严治理腐败犯罪理念指导下依次类推。另外,我们主张《刑法》不设置受贿罪的门槛,而是通过司法解释在细化受贿罪量刑的同时,规定受贿罪的门槛。
情节方面,因受贿犯罪形式多样化,有的受贿犯罪虽未达到上述数额,但是因为有其他恶劣情形——如索贿,也应该纳入受贿罪的射程。我们认为,从惩治和预防此类行为的发生而言,应该加大对收受贿赂之后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惩处力度。民生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其事关人民的生存、生计和生活,是刑法应该重点保护的领域,如若收受贿赂之后损害民生,在追究其受贿罪刑事责任时,应该加重处罚。正如培根所言,不法行为弄脏的不过是水流,而不公的司法弄脏的则是水源,司法人员收受贿赂之后妨害司法活动的,不仅弄脏了水流,更弄脏了水源,因而更应该严惩。就从宽方面而言,我们认为,对于受贿数额在年收入10倍以下,犯罪情节较轻的,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六、完善受贿罪的刑罚
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缺陷,笔者认为,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死刑的存在;二是罚金刑的缺失;三是没收财产刑的不合理。
就死刑而言,我们认为受贿罪不应该规定死刑,因为死刑只应该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1999年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列举的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的情况(即指立法上不应配置死刑的情形)主要有:毒品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职务上的犯罪、宗教犯罪等。”[15]受贿犯罪明显不属于上述犯罪的范畴,应取消死刑。况且,司法实践中受贿罪适用死刑的情形越来越少,废除受贿罪的死刑还有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2]但是,受贿罪最高刑只配置无期徒刑,对于严重的受贿犯罪行为,显得过于轻缓。因而,我们认为,对于个人受贿数额在年平均收入数额的100倍以上或者情节极其严重的,不得减刑、假释。
受贿罪属于贪财图利型犯罪,为其设置罚金刑,不仅能够让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树立不义之财不该取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贿犯罪的发生率,并且罚金刑的适用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方向,契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为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有必要为受贿罪增设罚金刑。《刑法修正案(九)》二审稿已经为受贿罪配置了罚金刑,这完全符合罚金刑惩治贪财图利性质犯罪的需要,不过应进一步明确罚金刑方式,否则罚金刑的适用将带来更大的随意性。我们建议采用比例制,原则上按受贿金额的25%处罚。低于该比例可能隔鞋搔痒,高于该比例可能导致难以执行。
我国刑法为受贿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这种刑罚不问财产来源、不考虑受刑人复归社会后的生活,并且“我国刑法中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体现出的陈旧、落后的财产刑观念在国际上被认为背离了没收财产的宗旨,构成对被判刑人基本人权的剥夺。由于此种,没收财产刑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刑事立法所摈弃,依据上述没收裁决提出的资产追缴请求一般会被外国所拒绝。”[16]在此背景下,我们在设置受贿罪的条文表述时有必要对受贿罪的没收财产刑予以修改,可具体表述为:“受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应予以没收。受贿犯罪所得不能追回或与合法财产无法分割的,应当没收其相应数额的合法财产。”②此处表述借鉴了黄风教授的研究成果。参见黄风:《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1期。
七、结 语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认为,受贿罪的法条设置可以表达为:“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基于其职务或权势收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是受贿罪。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犯本罪,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第一,个人受贿数额在当地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数额10倍以下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
第二,个人受贿数额在当地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数额的10倍以上30倍以下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个人受贿数额在当地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数额的30倍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个人受贿数额在当地公务人员年平均收入数额的100倍以上或者情节极其严重的,不得减刑、假释。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
受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应予以没收。受贿犯罪所得不能追回或与合法财产无法分割的,应当没收其相应数额的合法财产。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受贿危害国家安全及民生安全、妨害司法活动或者索贿的,从重处罚。”
[1]刘晓山,吴洪江.关于受贿罪主体之重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曾粤兴,周兆进.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J].中州学刊,2015,(4).
[3]李希慧.贪污贿赂罪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2004.
[4]孙国祥.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新论[J].法学论坛,2011,(6).
[5]薛进展,张铭训.贿赂犯罪慎改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8).
[6]孟庆华.贪污贿赂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
[7]孙国祥.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J].人民检察,2014,(3).
[8]高铭暄,张慧.论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J].法学杂志,2013,(12).
[9]於贤淑.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立法探析[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10]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张小霞.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重新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12]陈洪兵.论贿赂罪的职务关联性[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13]薛进展,张铭训.贿赂犯罪慎改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8).
[14]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1).
[15]赵秉志.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2).
[16]黄风.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J].法商研究,2014,(1).
On Legislative Amelioration of the Bribery Crime in China
ZENG Yue-xing1,SUN Ben-xiong2
(1.Law School,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00,Yunnan,China;2.College for Criminal Law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Many defects exist in the bribery crime of law of China and require to be improved.First,the subject of taking bribes should be shifted from“identity theory”to“public duty”,with more attention paid to the integrity of public power.The statement of“taking advantage of duty”is not exact,and should be replaced by taking bribes on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y or power.Then,the theories aboutscope of the crime of accepting bribes are notprecise either,except thatof“Accept property interest is bribery”,and the element“to seek benefit for the briber”should be abolished.Next,when talking about bribery crime,we should consider the amountof bribery first,then other plots.Finally,it is necessary to abolish the present death sentence on bribery crime,and improve the penalty of fine an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bribery;legislative perfection;bribery crime;legislative expressions
D924.392
:A
:1006-723X(2015)09-0033-05
〔责任编辑:黎 玫〕
曾粤兴,男,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
孙本雄,男,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