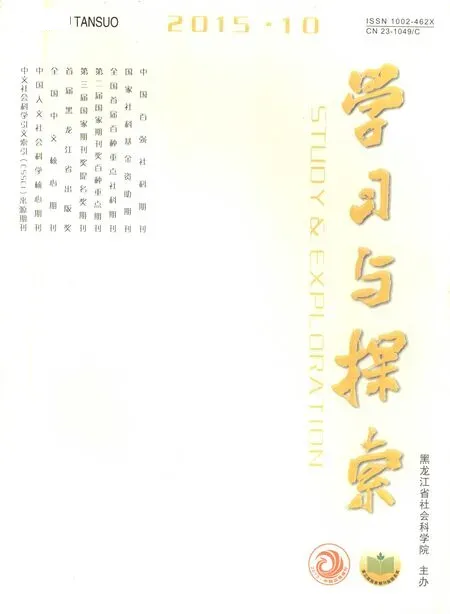元化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记事
2015-02-25蓝云
蓝 云
元化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记事
蓝 云
这些日子,再次捧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依稀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怅惘,元化先生离世已有7个年头了。仍历历在目的,是当年为先生读这本书、整理他口授的《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往事,竟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总被雨打风吹去”。
为先生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2005年的事。那年秋季,沪上《新民晚报》为先生开辟《清园谈话录》专栏,先生就让我帮他整理一些口授短文供晚报刊用。
先生虽然天生目光如炬,可是晚年一直备受视力衰退的困扰。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患过严重的眼疾。他告诉我当时医生在他眼球上打过针,还说你不用害怕,眼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里面是一包水,不会一戳就破。年过八十以后,他左眼得成了青光眼,致使失明,右眼是严重的白内障,又不敢贸然去动手术,担心唯一的微弱的视力也会失去。他懊丧,说自己是“读写俱废”。他说他是一个靠读书写作为生的人,一旦不能写作,就不知生命对自己还有什么意义。他的老师熊十力曾诗云:“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现在轮到自己了,切身体会到熊师当时的窘迫。我看他那么苦恼,就说有我啊,你告诉我,你要读什么、写什么,我都很乐意为你去做。先生无奈地看着我:是啊,你就是我的眼睛。就这样,进入新世纪后,替先生读书读报,整理他口授的文稿信函,多由我来承担,我真的成了元化的眼睛。
《清园谈话录》共有二十多篇,《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中一篇。为了这篇谈话,先生要我为他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非常希望在晚年再读一遍。他说此生他是第三次认真地去读这本书。前两次,作为一个有点激进的青年,克利斯朵夫的狂热和偏激与他发生共鸣,他非常赞赏罗曼·罗兰和他笔下的克利斯朵夫。现在他老了,对激进主义有了深刻的反思,他觉得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会有别样的感受。
这是一套不一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洋溢出先生心中对罗曼·罗兰的偏爱。他告诉我,当年他特地到沪上福州路,买了黑丝绒来装帧这套书的封面,还在封面烫金印上了书名(用鲁迅书体)。可以说,再没有其他书能得到先生如此虔敬。先生对罗曼·罗兰推崇备至。我曾告诉先生说法国作家中我最喜欢雨果,例如《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都曾深深打动我的心。先生说你应该更喜爱罗曼·罗兰,他的英雄传记不可不读,当然要读就读傅雷的译本。他还说如果有人替他写传记,他希望自己的传记是像英雄传记那种写法。他说你一定要设法找来一读。
很早以前,先生就对我说他非常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法国家庭女教师安多纳德,认为是他心中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他曾完整地给我讲述安多纳德的故事,一个把爱当作信仰的法国少女,拼命地挣钱,历尽了困苦和凌辱。她来到德国克利斯朵夫所在的那个小镇,为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为了能供她心爱的弟弟奥利维读大学。克利斯朵夫得到两张歌剧《哈姆雷特》的戏票,正好碰上一袭黑衣、神色落寞的安多纳德在剧院门口,想看戏却没票,于是他把那张多余的戏票给了安多纳德,邀请素不相识的女教师一起进包厢看了歌剧。东家却因此辞退了安多纳德。就在克利斯朵夫回家的火车途径一个小站时,恰巧与另一辆去法国的列车相遇,车窗与车窗相对着,克利斯朵夫突然认出对面车窗后正是那个因一起看戏而丢了饭碗的安多纳德,他们四目对视却来不及招呼,列车已各奔东西而去,失之交臂。再后来,在巴黎车水马龙、人流潮涌的大街上,贫病交迫的克利斯朵夫又一次看到街对面的安多纳德,他们认出了彼此,挣扎着走向对方,好不容易穿过马路,却不见了人影,永远地错失了彼此!先生说这就足够了,再多的笔墨都会显得多余,再没有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爱情。
先生暮年又想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基本上是我读他听。因为适逢时任《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来探望,想为先生尽点心,她托助手出了一些车马费,在复旦大学招募了几名学生志愿者,课余时也来为先生读书读报。这样,每天上午雷打不动由我读,下午间或由复旦学子读书报或读《约翰·克利斯朵夫》。2005年整个秋季,每天一早风雨无阻地去庆余别墅为先生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成了我和先生的必修课。通常在上午,先生会排除其他事务,盼望我的到来。到了先生那里,泡上一杯上好的绿茶,先生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枕头垫得高高的,我则拖一把藤椅,安放在先生的床边,开始读书。这套藤椅是我陪先生一起选购的,不仅造型优雅,而且坐着很惬意。四周静静的,全无车流人声的喧闹,仿佛就是我和先生在牵手克利斯朵夫。
翻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先读罗曼·罗兰的序言。先生说你先把全书四卷目录读一遍,我一本一本翻开目录依次读完后,先生要我直接读卷五《节场》与卷六《安多纳德》。我遵命先读《节场》。先生说,读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巴黎的艺术圈,克利斯朵夫在那里都碰到了什么,在那里找不到真正的“法国精神”。还说你可一定要让娇娇(我的女儿,当年在巴黎学艺术)别赶时髦,要找到真正的“法国精神”。读《节场》,读着读着,克利斯朵夫在音乐界、批评界、文艺界、上流社会不断地被排斥;读着读着,克利斯朵夫愤世嫉俗格格不入;读着读着,克利斯朵夫陷入困境贫病交迫……就这样读着,日复一日。记得有一次,读着读着突然听见先生发出“噗——”“噗——” 的鼾声。我猛地停止朗读,看着先生。先生闭着眼睛问:“怎么不读了?” “我看你睡着了。”先生仍闭着眼睛说:“我听着呢!你不要和我淘气!”我这才明白,先生有边打呼、边听克利斯朵夫的本事!
在读《安多纳德》时,先生不再闭眼,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他说他为这一卷中显现的女性美、人性美和人间的爱深深打动,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也会爱安多纳德,与我一样。读完这一卷,先生又让我从卷四《反抗》中,翻出克利斯朵夫和安多纳德所乘坐的两辆火车相向而过的一节来读,当读到“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慢慢地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灭。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地分开了”时,先生说:“停,再读一遍。”我又读了一遍,先生叫我:“拿笔录下这一段,我要用。”
先生第三次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实是在听,听觉使他感到故事时而激越时而和缓,时而像快板时而像慢板,有节奏感和乐符的跃动,宛如在听交响乐。特别是安多纳德在书中的几次出现,如同一个旋律在作品中被在不同场合反复变奏。他特地就此请教了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戴鹏海教授说先生的直觉是对的,在音乐作品中这叫“主题的再现”。先生说罗曼·罗兰是个博学的人,尤其擅长音乐,这是同时代其他著名文学巨匠也难以比肩的。
说是三读克利斯朵夫,准确地说是听克利斯朵夫,而且听的只是《节场》和《安多纳德》。其实先生对这部书的人物和情节早已烂熟于心,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不同心境、不同情景中,会给先生带来新的不吐不快之感。
先生认为这回重读和从前不同,他已不再把克利斯朵夫看作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明,也不再有那般年轻时的狂热的激情,并认为克利斯朵夫也是有缺陷的。过去先生最爱这部书的《反抗》和《节场》,对克利斯朵夫不顾一切想要去涤除艺术界多年积存的油垢,向那批用艺术以外的手段去骗取金钱、地位和名誉的文士进行挑战,那时先生对克利斯朵夫何其倾倒!觉得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成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先生联系当时文艺圈的种种,他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愤懑不平,这从他1948年所撰《论香粉铺之类》中可以管窥。针对钱钟书、张爱玲、鸳鸯蝴蝶派,他使用了类似大批判的语言:“他们干着这种勾当,居然还标榜着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大段抄录了克利斯朵夫的话——虽然克利斯朵夫的一根头发都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他当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认真读过克利斯朵夫的人,实在为这一切感到悲哀、不平和愤怒。他这样诘问:“难道一个巨人的惨痛战斗,壮烈呼声,竟可以当作香粉铺的装饰品?出卖狗皮膏药的商标?”“——难道睁着眼睛让我们的文艺变成香粉铺不成?”那时的他欲摧毁一切宛如克利斯朵夫。可是这次重读先生认识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总是对的,有时他做过头了,把值得肯定的作品和值得尊敬的前辈也一概践踏在脚下,他已然醒悟自己在当年犯了与克利斯朵夫同样的毛病。
读完这些章节,先生吩咐我拿来纸笔,说你可以记录了。他慢慢地思考着,慢慢地叙述着,我一字不漏飞快记下。往往一个上午,他说我记,不容人打扰。下午他午睡,我就回家用电脑整理成文,打印出来,第二天一早读给他听,由他口授修改意见,然后再口授新的一段。彼此配合默契效率很高,基本上每天一段,一周就完成了。直到先生认为满意了,他即刻吩咐我,立即传一份给《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严建平,2005年11月29日《清园谈话录之七》刊出;另一份传给《财经》杂志副刊,先生把标题改为《友情、亲情和爱情》。
末了,附上我为先生笔录的《清园谈话录之七——友情、爱情和亲情》及署名为方典的《论香粉铺之类》,或许对王元化学案研究有用。*因版面所限,此处略去附录两篇文章。
[责任编辑:修 磊]
2015-06-11
蓝云(1950—),女,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心高级教师,2002年起任王元化学术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