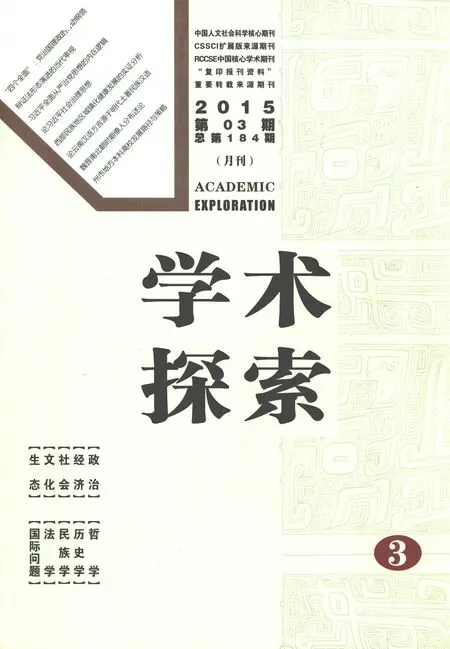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2015-02-25王朝阳
王朝阳
(商丘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王朝阳
(商丘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制度经济学;宋代;士人经商
自战国以来,官员、士人经商就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宋代犹然。关于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探索,近几十年来中外史学家已有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涵盖了相关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年代最早、影响较大的当属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1],全先生在这篇长文中认为宋代官吏经商的原因有官俸太少、商业观念的变化、商人地位的提高、政治上的腐败等原因。受时代所限,全先生对相关史料的运用现在看来并不太充分,但此文奠定了宋代官吏经商研究的基础。赵晓耕的专著《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2]从法制史的角度,通过对两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义利观念的变革、官僚体制及商人地位等方面论及了宋代官商的存在原因。程民生在《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3]一文中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及观念角度等方面对宋代官员、士人经商进行了深入的评价和思考。郭学信的《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4]认为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5]从商品经济的冲击、薪俸有限、闲官制度形成的弊端等方面论及了官员经商的原因。综合来看,宋代官员、士人营商的产生有其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等。
本文不想按部就班地逐一分析造成官员、士人经商的各种原因,因为这样容易带来人为的割裂感,不便于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实质。基于此,本文拟引进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从制度上探究分析之。
一、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及启示
诺斯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凡勃伦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总和。”[6](P34)简言之,制度是一种规则,其主要的功能是增进秩序,无论这种秩序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指人类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出来的那种制度,主要包括习俗、道德观念、思维意识及文化传统等。外在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并付诸实施的规则。它包括政治规则(或叫政治制度),经济规则(或叫经济制度)和法律契约(或叫法律制度)。
关于宋代士人经商的诱因,既有思想因素、文化因素,也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因素。如果按制度经济学来说,前者是内在制度,后者是外在制度,这恰好能用“制度”将两者连接起来,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联系就能有效地展现出来。
尤其是宋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无论是内在制度还是外在制度,与前代相比,都有一些甚至是较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在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从官员、士人经商来看,宋代的“内在制度”肯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不过,当时的以习俗、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内在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士人的行为,恐怕需要做出探讨。另外,宋代政府所制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是否对士人经商产生影响?就制度而言,宋代政府的制度供给是给士人私营商业带来促进还是阻碍作用?这都有待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也正是笔者尝试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宋代士人经商的意义及目的之所在。
二、从制度经济学看宋代士人经商
(一)内在制度的促成
1.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
义利观念从本质说属于道德层面的范畴,自先秦开始就有了蔚为壮观的义利之辩,贵义贱利奠定了传统义利观的理论基础,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代表了唐代以前广大士人对经商的基本态度。
逋及宋代,在义利观方面,则是冲破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点的桎梏,逐步转变成为义利合一的义利统一论。李觏在《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7](P326)在义利观念上,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初步挣脱了“讳言财利”的藩篱。苏洵继承了李觏的观点,在义利统一方面更是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8](P278)他充分强调了义利合一,改变了传统义利观所认为“义”“利”矛盾对立的观念的认识,内在地把二者融合到了一起。
降至南宋,永嘉学派进一步充实和完备了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其中以陈亮和叶适的思想最为突出,陈亮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9](P140)旗帜鲜明地发出了求利合理的呼声,他还说“《乾》无利,何以具四德?”[10](P1850)意思是如果没有“利”,岂有仁义道德的存在?作为功利主义学派集大成者的叶适更是把义利之辩发挥到了极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11](P324)也就是说世上不存在脱离功利的所谓道义。可见陈亮、叶适等功利学派力图打破传统的义利对立的界限,将功利提至前所未有的位置,这是自北宋以来义利统一思想的又一次延伸和强化。这不仅为宋人追逐商品利益寻求到了理论支持,更找到了与民争利的理由。浙东事功学派于内在价值观念方面促使了士人阶层私营商业的发展,宋代士人营商比例的增加与南宋事功学派不无关系。而且这种义利观念的嬗变对本末思想也带来极大的影响,并与义利观一起作为内在制度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士人阶层。
2.本末观的嬗变
北宋初年,士大夫对商业的认识有一定的转变,掀起了反对传统本末观的思潮,范仲淹与李觏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范仲淹在《四民诗·商》中写道:“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12](P25)在这里,范仲淹肯定了商人的作用,呼吁人们给予商人应有的地位。比范仲淹稍晚的李觏充分肯定了商人及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13](P149)其实,这是一种自由放任的重商思想。
如果说北宋时期士大夫的本末观有了不同于前代的特点的话,那么南宋的事功学派则进一步将这一特点发扬光大。陈亮这样说:古者官民一家,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陈亮已经委婉地表达出了农商皆本的初步理念,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这彻底改变了以往将农和商对立起来的观点,无疑是观念的一次更新!稍后的叶适则公开批判了重农抑末观点:“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这如同晴空中的一声惊雷,震撼了本末观的理论天空。
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带来商业意识的增强,商人地位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作为知识文化人的士人阶层受到意识观念的冲击是首当其冲的。
3.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
入宋以后,传统的“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撼动,官僚士大夫们已经初步认可商人的存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乐意与之交往,并有了羡慕的意味。宋代的诗人做了很多的《估客乐》之类的诗,如方回在《估客乐》里不加隐晦地描写了对商贾的向往之情:生不羡凤凰池,死不爱麒麟阁,估客乐哉真复乐。①方回:《桐江续集》卷九《估客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虽然士大夫对于商贾的生活暗生羡慕之情,但对于士大夫来讲,“他们几乎天然具有对于商人的优越感,无论是对于商人的观察还是评论,同情还是非难,大抵都有一种‘居高临下’和‘保持距离’的态度”,[14](P148)不过,面对商人阶层的地位的上升以及社会开放风气的侵袭,他们这种天然的优越感越来越少,致使部分士大夫心理失衡,这种心理上的波动摧毁了士大夫的精神堤防,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和彷徨甚至是心理煎熬,但是巨大商业利润无时无刻地诱使着他们,于是,一部分士大夫挺身而出,纷纷涉足商界,或明或暗地掀起了一股经商逐利的热潮。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现实中的士人、士大夫经商与否所带来的巨大差异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们脆弱的神经。如《桯史》记载:“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旦日,衣冠谒而请焉。”[15](P16~17)看来,这个书生对于富人甚是羡慕,从心理上已经被折服,所以才有后来的登门拜访。士子对是读书还是经商产生了犹豫的心态,士子们脆弱而又敏感的心灵受到了触动甚至是撞击,于是一部分士人走上弃儒营商或亦儒亦商的道路就在所难免了。
上述义利观念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以及心理上的诱因属于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范畴,是内在制度的变化。其中,义利观念的变迁使得君子言利求利行为,找到了道德的武器,披上了一层合乎礼义的面纱;本末观的嬗变带来了士人对商人观念的转变以及商人地位的相对提高,这对士人经商来说,是一种间接的促进作用;士人们心理方面的松动为其涉足商业提供了一种文化心理机制。这些内在制度的嬗变或多或少地减轻了士人营商的阻力,营造了一个士人阶层经商的相对宽松的氛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促使宋代士人经商行为的增多。
(二)外在制度的诱使
1.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官本位”,对一个士人来讲,一旦入仕为官,不仅仅是名声上的荣耀,更重要的是从此获取了附加在官职上的权力,以及借此得到的诸多利益。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官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士人阶层,所以官吏营商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文化机制。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官政治制度的确立期,初步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官员在政治地位等方面是历朝历代中较高的,这就使得部分官员在私营商业过程中缺少了某种程度上的顾虑,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官僚的任用制度上,宋太祖设计了独特的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它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相结合,就演变出了大量冗官,形成了一个消费力巨大的阶层,也就拥有了相当可观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激发了士大夫经商的热情。
而且这种制度造成了一大批有官无实和无官的士人逐步沉积下来,他们眼巴巴地在渴盼着那少之可怜的差遣机会,却需要付出多年的等待和经济上的压力,为了能够抓住机会,他们不惜奔走于权势之门,这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于是经商就成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这样形成了一个徘徊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经商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北宋名臣李清臣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原今之大弊,皆入仕之门杂而众也。入仕之门杂而众,故仕者日藩。有罢职而归,几涉三岁不得再调者。进未得禄仕,退失其田庐。故廉白之人,身虽挂仕版,名虽荣圣世,而无赀以继其生,盻盻焉常不得其所。上急于父母甘旨修随之养,下迫于妻孥之饘粥,则守节不笃者,或乘其间隙匮困之时,起而牟利,买贩江湖,干托郡邑,商算盈缩,秤校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为王官,退则为市人。”②[宋]李清臣《圣宋文选全集》卷二一《议官策上》。
他们往往将追求商业利润的观念带进了官场,这就给士大夫带来了模仿效应,形成了宋代士商融合的趋势。宋代官、职、差遣相分离的任官制度以及科举的改善属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属于外在制度(正式制度)的变化,这种外在制度的变迁深深地影响着宋代士人的经商行为。
2.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
(1)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宋代的土地制度是唐末五代以来土地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有宋一代以“不抑兼并”著称于史。从产权制度上来讲,进入宋代后,土地制度已经摒弃了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双重产权制度的残余,私有产权制度在宋代得到了确立。朝廷对土地买卖和土地占有持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高官要员利用“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广占良田,以至于“承平浸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16](P4164)在此基础上,官员在农业领域内经营就获得了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也在农业方面注入了更多的商业因素。可以这样说,宋代的土地政策造成的实际生活中的官员集地主、商人于一身的情形更加明显,这是两宋官员因土地经营而成为官商的一种制度诱因。
(2)专卖(禁榷)制度的诱使。专卖制度是我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特色之一。到了宋代,禁榷专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些禁榷专卖品成了宋王朝的财政支撑。政府的禁榷职能是由各级官员来完成的。因此,在缺乏制度监督,又无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官员的贪婪图利的人性会愈加膨胀,很自然就会出现以权谋私的现象。所以说商利的诱惑与官吏的特权地位使官商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重要的是,这从制度上拉近了官员和商人的距离,使得两者的勾结取利成为了可能,这样在经济领域就会出现“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的情况。所以我们说,双轨制的价格体系导致官员权力寻租,致使官员经商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官员与商贾相为表里,专卖制度下的权力和金钱在这里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官员和商人局部达到了所谓的“共赢”。
3.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
(1)立法层面上存在漏洞。应该说有宋一代对于官员私自营商的立法惩治是绵绵不绝的,但问题是这种立法缺乏一定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且前后标准不一。如《宋史》卷183载有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及此年前后的法令:“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17](P4478)
政府对官员私贩官茶的处置愈来愈轻,太平兴国二年之前,贩卖数额达到一点五贯就被处死,兴国二年变成了三贯以上才被黥面,至淳化三年则是十贯以上方被黥面,这说明了朝廷前后立法标准不一。从立法层面上来讲,对官员经商的约束越来越少,这使得官员在心理上更加有恃无恐。
除此之外,宋代制定的禁商法令本身有很多漏洞可钻。在法律条文上,朝廷仅仅禁止官僚士大夫个人的经商行为,但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对于地方官府经商并不禁止,相反还给予一定的鼓励甚至是优惠的措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有时很难断定官员是替公经商还是为己牟利,他们往往借为官府经商之名,行赢利归己之实。由此可见,宋代的法令本身并不太严密,或者说是不彻底的,存在一定的漏洞,这对官僚士大夫来讲就有了可乘之机。
(2)执法层面上,对违禁官员的处置不严,有法不依。整个宋代,朝廷对于士人阶层的优待是众所周知的。对士大夫经商的处置基本上是采取纵容的态度。苏辙言:“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18](P116)
既然政府对官吏经商的惩治在一定程度上徒有虚名,而且在营商过程中又能借助权力的护佑,那么官员何乐而不为之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的法律是“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19](P4961~4962)并且宋代官员经商案发的原因多是被人告发所致,并非朝廷主动查处,反映了朝廷在官员经商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3)在法治理念上,以“仁义”之治代替法治。宋代文官治国大行其道,更多的文人儒士进入了官僚队伍,在治国理念上更加注重儒家的教化,儒家的仁义之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表现在法制方面就是“法意人情,两不相礙”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赎屋·执同分赎屋地(吴恕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6页。、“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婚嫁·诸订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赵惟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1页。理念的盛行。儒家的仁义理念一旦渗透进了法律的范畴内,就意味着非法制因素在实践操作中虽不能说大行其道,起码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从人性上讲,注重仁义理念给判案披上了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那就是一些私营商业的不法官吏通过所谓的仁义逃脱了或者说减轻了法律的制裁。
从法律层面上看,宋代对于士大夫经商的处置,无论是立法环节上、执法环节还是法制理念上均存在着一定的疏漏,虽然朝廷对士大夫的经商惩治措施看似完备,但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姑息政策成为主流。相关律法在司法实践中大打折扣,政府对士大夫的惩治多流于形式,因此官员经商大行其道就不足为怪了。
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经商所处的外在制度(正式制度)是诱使他们投身于商海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法律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官商的产生。从政治制度看,沿袭已久的官僚体制以及宋代特殊的官、职、差遣制度,加上科举方面的因素,使得士人阶层经商有了政治制度方面的有利安排;从经济制度方面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及富有特色的禁榷专卖制度使得士大夫私营商业在经济领域中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再者,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使得朝廷对违禁士大夫的处置更多地流于形式。
三、宋代士人经商的制度经济学评介
宋代其实处在我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宋代士人阶层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从制度供给上说,无论是内在制度(非正式制度)还是外在制度(正式制度),对官员营商的制约性都是不足的。从内在制度看,人们义利观念的转变及本末观念的嬗变,使得官员对商人的看法及意识有了较大的转变,也使得士人阶层厕身其间,缺乏意识形态的羁绊;还有士人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也使得自身对商人认同感加强,心理上对财富的垂涎愈加强烈,所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士人阶层经商的盛行。从外在制度看,当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一旦和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成了宋代官(士人)、商一体的黏合剂,国家禁榷制度的强化反倒促成了士商的结合,这恐怕是朝廷所始料未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是不足的,很多制度反而促使了官员的经商行为。
宋代制约官员营商的有效性也是较低的。因为政府的很多制度,无论是制度的设计还是制度的执行层面,效用都是大打折扣的。首先,选官中的官、职、差遣制度与科举、荐举等制度相结合,演变出了大量的冗官,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制度层面上制约官员营商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和政策上的相互矛盾,也给官僚贪赃枉法及经商牟利以可乘之隙。
即使是惩治官员营商的法律机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立法环节上前后连续性不强,且有所瑕疵;执法环节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总体来说是外严内松。对官员的震慑作用并不明显,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司法制度的不健全,致使对官吏经商不能有效地制止与打击,自然使得各种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士大夫经商就会大行其道,官吏经商也就屡禁不止了。
综上所述,宋代的士人阶层大肆营商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各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官员、士人营商的产生,或者说制度本身给士人营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促使士人营商的制度安排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竞相具备,价值观念的嬗变和官文化的传统使“士人营商”有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政府官员的权力架构则为“士人营商”提供了可供操作实施的权力资源。当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士人营商”的制度安排就会进入自我增强的路径中。其实,历朝历代的士人经商都有其共性和特性,不同朝代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了不同时期士人经商的特点与原因存在着异质。无论各个朝代士人经商原因的异同点如何,但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在于制度本身。退一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且还有制度不够完善的地方,仍有官商生存的空间,又何况一千年前的宋代呢?所以说制度的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商的根本之策,而它的欠完善,又为官商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说能寻找到减少官员经商之策的话,那么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双重创新就是这种策略的必由之路。因为士大夫和普通人一样,也是“经济人”,有强烈的趋利动机,一旦给予条件,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变通法律或规则来实现自己经商赢利的目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士人经商是不可避免的,前提是:只要在一个国家内部还潜存着诱使官员经商的基因,还存在着适应于官员经商的制度安排。
宋代是一个承上启下、处于转型期的特殊朝代,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诸多问题随之而来,内在制度方面的重要表现—价值观的嬗变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行为、道德规范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属于外在制度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会作用于整个社会,并带来相关的反作用。这些冲击与作用对宋代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其余波涉及明清。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同样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如何采取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制度范畴来规范政府官员相应的官商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使之由社会发展的阻力变成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因此,宋代的官商问题对于我们的现实社会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1]全汉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赵晓耕.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程民生.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兼谈宋代商业观念的变化[J].中州学刊,1993,(2).
[4]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6);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J].天津社会科学,2008,(3).
[5]郎国华.宋代官吏营商之风的原因及危害[J].江苏商论,2003,(1).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7]李觏集(卷29)《原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苏洵,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卷九)《利者义之和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陈亮集》(卷一二)《四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六《龙川学案·龙川门人》[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汉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民诗·商》[M].范能浚编集,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13]李觏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5]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二)《富翁五贼》[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6]宋史·食货上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宋史·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五《衡论下·申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9]宋史·刑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p lor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O fficials and Scholars Engaging in Trad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 ics
WANG Chao-y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Shangqiu,476000,Henan,China)
The engagement in trade of Officials and scholars in the Song Dynasty is attributable to causes of political,economical,leg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We can discuss them in an organic theory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From the internal system,the increased business behavior among the scholar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eakening of restraint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the evolution of the fundamental and incidental values,and spiritual dither and loss of the scholars.From the external system,contributory factors that attracted the officialsand scholars to go in for business include bureaucracy,the separationmechanism of official,post and dispatch,the government land policy and themonopoly system,and the legal system thatwas seemingly harsh but loose in reality.Besides,there are deep system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officials and literati being in business.For one thing,therewere few systems that constrained thispractice;for another,the existing systems were low in validity.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e Song Dynasty;scholars'engagement in trade;causes
K061
:A
:1006-723X(2015)03-0130-06
〔责任编辑:李官〕
王朝阳,男,商丘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