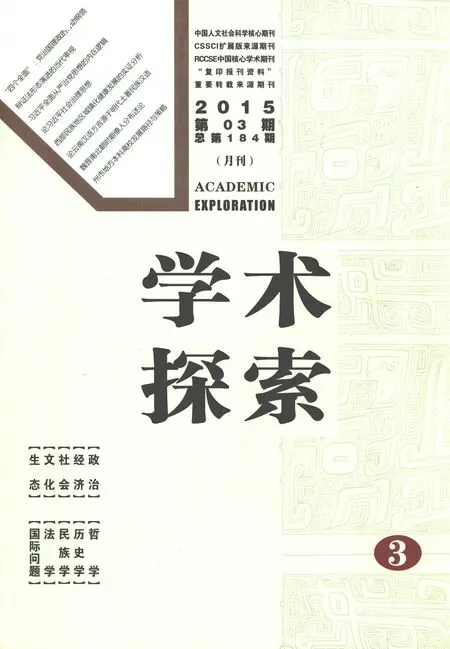近代西方人士考察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著述
——《代理领事李敦滇西北旅行报告》研究
2015-02-25梁初阳
梁初阳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近代西方人士考察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著述
——《代理领事李敦滇西北旅行报告》研究
梁初阳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晚清时期,西方人士在中国西南地区展开大规模考察活动。英国代理领事李敦活跃其中,他在云南西部地区的考察,具有拓荒性质。李敦深入调查云南地方社会情况,其考察报告涉及西南边疆社会多个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被收入《英国蓝皮书》中,于清光绪年间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该报告的中、英文版本面世以来,由于流传不广及翻译不精等问题,其参考价值未能得到充分认识,至今国内学界少有人研究和使用报告中的内容。对这部重要著作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可为今天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和云南对外开放提供有益的借鉴。
近代西方人士;李敦;云南考察报告;重要著述
云南是连接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家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近代以来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留存下大量的考察资料,在中国对外交往等领域的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目前学界对这些资料关注不够,对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英国驻腾越(今云南省腾冲县)代理领事李敦关于晚清云南西北地区的考察报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1902年11月至次年1月,李敦从云南府(今云南省昆明市)出发,对云南西北地区进行综合考察,“此次调查经过的武定、元谋、大姚、宾川等地,鲜有外国人光顾,他的调查,也算是填补了西方人在云南北部的考察盲点地区”,[1](P47)可知此次考察活动具有拓荒性质。李敦后来依据调查材料写成考察报告:Reportby Acting Consul Litton on a Journey in North-West Yunnan,被收入英国蓝皮书中。“《英国蓝皮书》是英国政府提交议会两院的外交文件,自公开刊行以来,很受各国学者的重视”,[2](P1)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李敦考察报告写成当年(1903年),即由黄文浩译成中文,名为《考察云南全省播告》,在湖北洋务译书局刊行。这份关于中国西南边疆近代社会情况考察的重要文献,虽有中、英文版本面世,却少有人知。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专注于中国西南史地之学,“多年留心者,则为纪载滇事之书。”[3](前言,P2)经数十年搜集整理,编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云南史料丛刊》等重要著作,但却未能获见此书,可知其罕见。以方先生的深厚学养和敏锐洞察,已注意到此书的重要参考价值,因不见原书而“未能确说其事”,[3](P562)进行精辟分析,实为憾事,至今仍无专文进行讨论。①关于李敦的考察报告,邓衍林在民国时期编《中国边疆图藉录》,收录了中译本的书目(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245-246页);《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丛刊》及《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转录,唯将书名误为《考察云南全省报告》。杨梅在《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及其著述》(云南大学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论文)、《晚清至民国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调研资料的编译与研究》(《清史译丛》第十辑,济南:齐鲁书社,2010版)中,简介过英文考察报告内容。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撰写背景、作者生平、内容价值及翻译流传等问题进行探讨,对了解云南近代社会历史发展,并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一、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云南考察潮
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又有越南、缅甸等藩属国作为屏障,与西方世界少有接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规定外国人士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买房、自由居住,还可到内地传教、游历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势力开始大规模进入。此时还从西方掀起一股世界性的考古、探险浪潮,与新兴的人类学研究相互影响,在此背景下,大批外国官员、商人、传教士、军人、学者、探险家涌入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之考察。19世纪末,法国通过中法战争完成对越南的占领,英国也通过第三次英缅战争吞并缅甸,西南边疆藩篱尽撤,云南成为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的滩头阵地,开始为西方人士关注并进入考察。
西方人士对云南的重视,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区位,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北部和东部分别与内陆的西藏、四川、贵州、广西等毗邻,西部和南部则与缅甸、老挝、越南诸国接壤,是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地区往来的重要通道,英、法占据缅、越后,特别看重云南的地缘优势,将其视为本国在南亚、东南亚势力范围的延伸,因此积极开拓市场,并计划修筑铁路,准备将云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列强还把云南当作进入中国的后门,认为“云南是唯一能够成为联结印度和扬子江及中国东部的锁链”,[4](P14~15)因此渴望通过云南,向中国内地的广大区域扩张势力;第三,被云南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和假想中的巨大市场所吸引,当时在西方主要是英国的工商业界流行着一个“云南神话”,认为云南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是一个蕴藏着巨大的商业财富的“黄金之国”。以英国探险家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为代表,1882年他在英国格拉斯哥商会支持下,从广州经云南到缅甸。回到英国后他出版了考察报告,并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等杂志上撰文,详述其旅途见闻,认为云南是中国西南部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积极鼓吹进入云南市场,因此可以说“商业利益是把英属印度引向中国西南边疆基本的也是原初的动力”,[5](P3)争夺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也是促使考察活动兴起的主要动因之一;第四,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各个领域的科考探察活动方兴未艾,云南在地理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中有丰富的资源,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清末在云南进行过多次考察的英国军官戴维斯所言:“云南不仅仅能引起政治家和商人的兴趣,对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来说,云南也有许多尚待发现的空白。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们,将会对那儿崇山之中广为分布的宝藏很有兴趣,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种学家来说,如此广阔的研究天地将耗尽他们毕生的精力,而且会留下许多未竟事业靠后人来完成。同时,该省的动植物资源都未得到系统调查,而这个地区还有终年不化的白雪,温和的高原以及热带雨林,都将引起博物学家的工作兴趣。”[4](P4~5)
基于上述原因,自19世纪下半期始,西方来滇调查研究的各类人员络绎不绝,掀起了一股考察的热潮。其动机不外乎殖民渗透、科学研究、争夺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等,活动具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人数多、涉及领域广的特点。考察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报告、游记、论著等珍贵资料,对今天了解近代云南社会各方面情况,有重要帮助作用;同时在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中,也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60多种比较重要的调研专著中,约有27﹪的著作是由政府官员留下的,这些著作的政治性和商业性较强”,[6](P291~292)其中就包括了李敦的云南考察报告。
二、李敦来华事迹订证
关于李敦的资料,以《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的记录较为权威:“Litton,George John Letablers(1870~1906),烈敦,利顿,乔治·约翰·莱泰布勒斯,英国人。1895年任驻华使馆翻译学生,1898~1899年任驻重庆领事。1899年在中英缅甸划界委员会任职。1900年2月在腾越二百英里的地方被土人打伤。1900年任驻腾越领事。著有《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 Report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1898)等[7](P290)”。然而这段关于李敦生平事迹及研究著述的介绍,既不完整也不尽准确,比如他的最后职务是代理领事(Acting Consul),并非领事;另本文所介绍其在云南的考察事迹及撰写的报告,介绍中也只字未提。
根据记载,李敦在重庆期间职务是领事助理,代理领事职责。作为驻华领事,搜集情报为重要职责,事实证明李敦胜任这一工作,他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旅行家,还能写像样的游记式考察报告,并附上准确的地图。1898年在重庆任职期间,他曾深入四川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一带考察,并写成《中国:川北旅行报告》一书,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游记式考察报告。他还于1899年初赶赴贵阳,处理澳洲传教士富莱明(Fleming)被杀案。在贵阳他与来华游历的英国驻印度武官文格德(A.W.S.Wingate)相遇,两人一同与贵州地方政府进行交涉。事后两人分手时,文格德描述道:“当我望着他骑马东行,在那个飘著细雨的星期天早晨,他鬈曲的棕发被雨水湿透,他那高壮的体格充满着活力。”[8](P181~182)让我们对他的形象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李敦于1899年6月到达云南思茅,同年10月被任命为思茅关的代理领事,3个月后又调到英国中缅边境使团工作。1900年中英联合勘界时,李敦等英方人员在勐董(今云南沧源县境内)遭到当地佤族的攻击,英国官员曹大林和继德理被追杀致死,李敦本人也负伤,后经中方派来的差弁、防勇竭力救护,才最终幸免于难。[9](P748)1901年11月,李敦被任命为腾越代理领事,“于南门外设立正关,会订试办章程”。[10](P33)腾越设关不久,他就借口要“与滇督面商铁路、边界事宜”,[11](P283)于次年初到云南府,此后在昆明长期逗留。1905年,英国政府派李敦代表,与迤西道尹石鸿韶会勘滇缅边界北段。李敦提出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妄图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这个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和当地各族人民的反对。在谈判过程中,片马的总管事,傈僳族人勒墨夺扒率领各寨头人,拿出清政府颁发的兵部札符及登埂土司颁发的管事头人委任状,与李敦据理相争。事后李敦带重礼亲自到勒墨夺扒家拜访,许以“东翁”头衔和1500元印洋,收买他投靠英国,出卖片马,遭到拒绝。后来石鸿韶同李敦在实际勘界中,由于腐朽无能,虽保住片马等地,却更丧失了小江以外的大片领土,最终被清政府革职查办。
李敦在云南期间,为了英印殖民政府的利益,在云南各地积极活动,获取大量地方资料,成为当时西方世界公认的“云南通”。其关于云南的一些观点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比如对晚清云南人口总数的统计,中外各机构的数据出入很大,李敦经过调查统计,认为当时云南总人口约九百多万人,西方人士以其“旅居本省多年,对本省了解颇深”,[12](P481)认为此数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李敦的结局有这样的记载:“他在腾越不畏艰险到处游历,为英国侵略势力效尽了犬马之劳,以至1905年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笔者注)要任命或提升他为正式领事,但遭到了领事界的反对,认为李敦的头脑不太正常。1906年1月李敦在一次简单外出后回到腾越领事馆,猝死在椅子上,年仅36岁,最高官阶为领事级”。[13](P112)可知李敦最后的职务只是代理领事,许多资料中将其记为领事并不准确。
三、考察报告的撰写背景、内容及参考价值
李敦的考察报告是其在1902年进驻昆明后,借从云南府返回腾越的机会,在滇西各地游历考察后依据调查材料写成。1900年“昆明教案”发生后,英、法两国夺得云南省七府的矿产开采权,共同组成隆兴公司进行开发。双方有合作也有竞争,在云南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矿产资源探查活动,“隆兴公司的查矿人员,法国政府的勘路队伍,英国驻腾冲领事烈敦等均一齐出动,纷至沓来,不绝于途,他们的足迹遍布三迤”。[14](P73)其中李敦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滇西一带,“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公元1902~1903年)间,英国驻腾越领事烈敦,曾两次到云龙秘密勘测,确知云龙矿藏丰富,便打电报给北京英国公使馆,要求向清政府租借云龙之漕涧,准备开采云龙的矿产。这个侵略计划,后来因烈敦的死亡未能实现”。[15](P76)这些资料记录李敦在云南省内活动的时间和范围,与其考察报告中记述的内容大体一致。
1902年11月16日,李敦自云南府启程,开始考察活动。通常自云南府到腾越,客商多走传统的滇缅线,即从云南府往东,经楚雄、下关、永昌(今云南保山地区)到达腾越。但他行走路线较为特别,从云南府向西北经富民、武定、元谋至大姚,再往西到宾川,在鸡足山游历考察一番后,来到大理府。在上关和下关盘桓数日后,又从大理府启程,经邓川、浪穹(今云南洱源县)、鹤庆后到达丽江。在丽江北部的雪山和金沙江一带进行一番考察后,李敦南下剑川,西至兰坪县,在营盘镇渡过澜沧江,沿江南下至云龙,再西转进入永昌府,最后渡过怒江到达腾越。他的游历路线如此曲折往返,无非是想尽可能多地搜集云南地方情报,其调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考察云南西部的商贸、交通情况,研究英国资本进入云南的可行性,为英国商品在云南市场寻找机会,并在此基础上扩大英国殖民势力在云南的存在范围。此外在考察过程中李敦还注意了解云南省内的民族分布、文化习俗、山川地理、矿藏资源等方面情况。
本着上述目的,李敦每到一地,都注意考察当地的商贸、交通、城镇、人口、物产、民族、风俗、地理等方面情况。其中商贸和交通是其关注的重点,商贸方面如新兴州(今云南玉溪市)的纺织业、白盐井(今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的盐业、下关城的商贸活动、中甸的畜牧业、云南与缅甸的骡马交易、滇西北的道路及马帮运输、滇西各地的商品流通等,都有深入调查;交通方面,李敦对于沿途所经道路,详细记录路况走向里程等,重要地点还标明海拔和纬度,报告后附有《路程表》,记录下了每段行程的英里数及准确用时,文末又附有五幅详细的考察路线图。除搜集商贸交通的情报外,李敦还关注当时云南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关于晚清云南西部各民族,他对沿途所见的汉、彝、纳西、傈僳、怒等各族人民分布情况作了记录,其中还对敏加(又称民家)进行重点考察;文化风俗方面,他对当时宾川鸡足山的寺庙香火情况着墨较多,记载了大理洱海地区的民间传说与历史遗迹,还生动描述了鹤庆当地人民的服装习俗及赶街情景;在自然地理方面,他在丽江北部的大雪山和金沙江之间详加踏勘,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再次考证了金沙江在此段的正确流向,指出了当时西方地理文献中的记录有误,另外他还发现当时英印政府所编绘的地图中,关于丽江雪山的山脉走势标注不尽准确。此外,考察报告还涉及到晚清云南的边疆治理、政治军事、对外交往等方面内容。在报告结尾处,李敦总结云南交通、经贸及民族分布情况11条,供英国政府及商人参考,他认为云南仍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其经济好坏取决于当年的鸦片和粮食的收成;云南对外贸易远逊其他省份,但滇西的边贸潜力巨大,应注意培植地方市场;云南作为骡马等牲畜的重要产地,其重要性不应被忽略;腾越和下关是滇缅贸易路线上重要地点,建议各国在两地设立商业机构;列举出滇西主要进出口货物的名目;建议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到澜沧江、怒江上游的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游历考察。
李敦的考察报告中,留存下许多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兹举数例:大理府的下关是李敦考察的重点之一,他说:“下关不仅是各地商人聚集交易的商贸中心:有从腾越过来贩卖洋货的,有从临安(云南南部)①临安府治今云南建水县。来卖布匹和买鸦片的,有从广东过来贩运鸦片的,还有来自四川、西藏、丽江的商贩,在此地以骡马、毛织品、药材、麝香交易茶、盐、糖、棉布;还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区。我估计从缅甸进口的货物,至少有一半在此地售卖。”[16](P7)李敦的这些考察记录,是关于近代云南国际国内贸易情况的重要资料;李敦一行从兰坪县的啦井镇(盐井)西行,在营盘附近渡过澜沧江,沿岸南下,“在一个叫Tsao Yao的小村宿营,这是我们离开盐井后,第一次看到华文告示”。[16](P17)其间近百公里的路程中没有见到官府张贴的华文告示,笔者在相关史志中并没看到类似记载,李敦的记录直观地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的社会政治面貌,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再如李敦一行在永昌府的猛古渡过怒江到达蛮因后,他记述一路的见闻说:“因为瘴厉肆虐——自马可·波罗描述后变得非常有名——汉人不能在怒江河谷的浮桥一带定居。而在猛古,只有在更北边30英里的地方,我们才能发现华人的聚居区”。[16](P19)在永昌府属的怒江两岸,自古就为远近闻名的重瘴区,地方志书中记载:“潞江,旧名怒江……两崖陡绝,瘴厉甚毒,夏秋不可行。”[17](P82)1910年李根源来到此地考察,他记录到:“附近江边,数十户一团之村落有六七,住民尽僰夷”。又说:“猛古寨,五户,瘴地水毒。蛮因……瘴地水毒,无人马店。”[18](P3743)李根源到此地考察已时隔7年,从记录的内容来看,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居民构成变化不大,这些记录也进一步印证了李敦考察报告内容的准确性。
李敦考察报告的重要价值在于:首先,他对近代滇西的商贸和交通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记录了云南与英国及其殖民地缅甸的商贸和交通往来情况,是今天研究近代云南对外交往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次,他在考察过程中,准确详细地记录所经之地的人文及自然面貌,对我们了解近代云南社会历史情况有极大帮助;第三,李敦经过深入调查,对晚清云南社会发展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云南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商业潜力,但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仍独立于贸易的“洪流”之外,此说法无疑给当时西方流行的“云南神话”泼了冷水。由此可见考察报告无疑是一部严肃审慎的著作,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通过对报告内容深入解读,可知此著作为李敦基于科学严谨的一手调查材料写成,记述科学准确,内容真实可信,为近代西方人士考察云南的精审之作;其中部分地区是首次有西方人士涉足考察,所以记录下的资料尤其珍贵,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参考价值。
四、对考察报告了解不够及译本存在的问题
自晚清西方人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各地进行考察,他们的活动就一直受到国内各阶层人士关注,部分参考价值较高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李敦的云南考察报告即为其中之一。报告写成当年(1903),就由湖北洋务译书局翻译刊行。此书全一册,封面题名为《英国蓝皮书:考察云南全省播告》,扉页上又题有“英国第三册蓝皮书”“西历千九百三年英领事李敦Litton考查云南全省播告”及“夏口黄文浩译”等字,书末附有五幅路线图。正文70页,约1.5万字。然查阅全书及书末附录之《云南西北路程表》和考察路线图,可知李敦行程所及,不过云南、武定、楚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等滇中及滇西数府厅州县而已,并非云南全省。事实上核对报告的英文名称,准确译名应为《代理领事李敦滇西北旅行报告》,可知中译本的名称并不准确。
长期以来,对于近代西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考察活动,海外学界一般多关注其在学术上的价值,较少考虑到在这些活动当中,还包含有西方列强在华资源的搜求及利益的争夺;而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强调其中的殖民侵略成分,却忽略了其在中国现代学术上的积极贡献。事实上将近代西人在中国边疆进行的各种考察活动视为“侵略”的观点,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盛行,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左倾”思潮在学术领域的影响,更形成了一种固有模式,将西方人的云南的探查活动简单、粗暴地扣上“殖民侵略”“间谍活动”等帽子,这一时期关于西方考察论著为数不多的翻译和介绍,也主要是为“揭露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等政治目的服务。在这种形势之下,研究者自然难于关注到这些考察活动,对我国现代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怎样的贡献;对考察后留存下来的大量资料在近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参考价值,也重视不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内对于近代西方人士考察中国边疆地区的论著,掀起一个翻译和介绍的小高潮,出版了一系列的译著,相关研究也取得明显进步。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对李敦的云南考察报告的了解和研究不够,就明显成为一种缺憾。
此局面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收录李敦考察报告的《英国蓝皮书》英文原档,在国内仅有少数几家图书馆收藏,查阅不便;二,百年前刊行的中文译本,由于时间较长,且流传不广,今已难获一见;三,由于译者对云南地方性知识的缺乏及翻译态度的随意,中译本存在译文不够畅达及内容不尽准确的问题,也影响了人们对报告内容的研究和使用。
中文译本存在的问题,除前面提及的书名翻译不准确外,还有一些重要地名的翻译错误,如大理的苍山TsangShan误译为獐山,赵州Chao Chou(今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误译为曹州、云龙州YunLung Chou(今云南省云龙县)误译为永隆州等。此外中译本中漏译、误译的现象还较为严重,如李敦在武定州(今云南省武定县)一带考察时,谈及由于云南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重要出省商道已由此地改为从昭通至四川宜宾,随后话锋一转,说道:“法国的强盗们在控制红河航线并于蒙自设立海关后,将其变为进入云南中心地带的商道,并有可能永久霸占。”[16](P1)这样一句表达了作者重要思想观点的话,中译本中竟然完全省略,让人殊不可解!再如李敦一行由白地坪(今兰坪县金顶镇)向啦井镇进发,记述沿途交通情况时说:“原来的山路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穿行,但现在不用了,著名将领杨玉科在重新占领由回民义军控制的大理城时,新修筑了一条山路,现已成为繁忙的食盐运输通道。”[16](P15)而光绪年间的中译本的译文为:“所过之处,皆崇山峻岭,土匪作乱时,有统领郭姓者,曾开新山路一条,以包抄匪之去路,现此路为盐商常往来之处。”[19](P222)对照报告原文,我们发现这段译文不单把人物的姓名弄错,且没能准确表达出原文的意思。这类问题在光绪年间的中译本中并非少数,内容本身都不准确,就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使用了。
通过对李敦考察云南报告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其内容涉及近代西南边疆社会的多个方面,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报告的英文原档罕见,中文译本又存在翻译不精及流传不广的问题,影响到人们对这份重要资料的研究和使用。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行沿边开放战略,云南省的地理区位优势凸显,只有对云南与周边国家地区交往的历史及现状深入研究,才可能为今天的开放提供有益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份重要著作重新翻译并深入研究,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杨梅.近代西方人在云南的探查活动及其著述[D].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
[2]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英]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M].李安泰,等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杨梅撰稿,贺圣达审定.晚清至民国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调研资料的编译与研究[A].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译丛(第10辑)[C].济南:齐鲁书社,2010.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英]文格德(A.W.S.W ingate).一个骑兵在中国:从北京古城到云南边境五千里壮游[M].陈君仪,译.台北:台北马可孛罗文化,2000.
[9][清]陈灿.宦滇存稿[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0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编撰.云南省志(卷十六·对外经济贸易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11]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M].昆明:1985.
[12]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7.
[13]房建昌.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J].思想战线,2003,(1).
[14]荆德新.云南各族人民收回七府矿产的胜利斗争[J].思想战线,1978,(5).
[15]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冶金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16]G.J.L.Litton.Report by Acting Consul Litton on a Journey in North-West Yunnan.[R].London:Printed By Harrison and Sons,1903.
[17][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18]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A].永昌府文征(四)[C].李根源辑,杨文虎,陆卫先.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
[19][英]李敦(G.J.L.Litton)撰,黄文浩译.英国蓝皮书:考察云南全省播告[M].湖北洋务译书局,1903.
An Im portant W riting about Expedition into the Frontier Region Of South-West China by W esterners in Modern Times——A Study of Report by Acting Consul Litton on a Journey in North-W est Yunnan
LIANG Chu-yang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esterners carried out large-scale stud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west regions of China.A-mong them,the British acting consul Litton,as a pioneer,investigated the western regions of Yunnan actively.Based on his thorough investigation,his reportwas of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because it involved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regions.Later,the reportwas included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and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Guangxu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After its publication,the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s of the writing failed to get enough attention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circulation and inaccurate translation,so up to now few domestic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and used the contents in the report.Probing into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would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of the fields concerned,and can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opening up of contemporary Yunnan.
contemporaryWesterners;Litton;investigation reportof Yunnan;important literature
K09
:A
:1006-723X(2015)03-0124-06
〔责任编辑:李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院级项目“清代对外交往研究”。
梁初阳,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云南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