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空间下女工的主体性及其实现
——基于福州SF工厂的个案研究
2015-02-24许丽娜张广利
许丽娜张广利
(1.2.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上海 200237)
生产空间下女工的主体性及其实现
——基于福州SF工厂的个案研究
许丽娜1张广利2
(1.2.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系,上海 200237)
女工;生产空间;主体性;劳动过程
生产主体性的增长有利于女工在劳动过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与资方斡旋,从而有利于女工自身利益的增长,对女工生存境况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福州SF工厂为个案,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考察了生产空间下女工的主体性状态,并通过对劳动过程中和劳动过程之外两个层面上诸多因素的考察来解释女工生产主体性状态何以形成。研究发现,女工弱势的经济地位和弱势的社会地位互相强化,使其生产主体性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它的发挥受到来自生产车间、居住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多种因素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
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关注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据他的观点,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断通过各种方法加强对劳动力的压榨,但这势必引起工人各种形式的反抗,为此
资本家就要采取相关措施实现对工人的控制。因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控制与服从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尽管马克思对劳动过程问题研究提供了主要的概念和工具,但他对于劳动者的主体性、利益、控制等基本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阐释,而这些未被具体阐释的领域也就成为后继研究者的起点[1]。随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将工人主体性带回劳动过程之中[2](P5)。他关注工人的体验,并将理论的逻辑重心放在工人是如何服从控制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女性主义等各种思潮的日益发展,学者们为进一步还原劳动者的主体性做出了努力。例如,李静君对南中国女性的研究中,关注了劳动者主体性的性别问题,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关注了有宗教等级的劳动者,翁爱华(Aihwa Ong)关注了有文化特色的劳动者[3](PP149-176)。总的来说,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劳动者的主体性一步步凸显,并且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对劳动者主体性的研究不再拘泥于阶级分析视角,而是从性别、种族、族群、性取向、民族等多个角度来探寻工人的多元化主体性,身份认同也就成为分析工人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概念[4](PP143-171)。
就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学者们从阶级、阶层、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工人主体性进行了研究[5][6][7][8][9]。同时,随着中国规模巨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形成,学者们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阶层意识做了大量的研究[10][11][12][13][14]。余晓敏、潘毅等学者还对女工的消费主体性进行了研究。
准确地说,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对此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如下:“根据我国哲学界及西方哲学近代以来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我们把人的那种永远不满足于既在的生存境遇而去不断创造新的生命价值,以获得一个更新的精神自我的行为和意识的特征,称为人的主体性。它是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人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不断得到发展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的特性。人的主体性是人性的精华,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尺度之一。”[15](P195)一直以来,主体性在哲学领域被限定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思辨之中,缺乏对人的主体性的实证研究。
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的“主体性”,更精确地讲,应该是指“主体经验”,也就是在研究中,研究者从研究对象出发,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经验,它并没有特别强调哲学意涵上的“主体性”。在劳工研究中,研究者用到的“主体性”,指的是作为个体、作为工人阶级这一群体的主体性,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身份认同、阶级意识、抗争意识等,而主体性则成为对这些具体研究内容的抽象统称。
中和上述两种对主体性的研究路向,本文一方面接受哲学上对主体性的界定,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理论中结构和行动二者关系的维度对主体性进行实证考察。
承接当前学界对工人主体性的研究,本文将聚焦女工的生产主体性①在本研究中,研究对象为女性农民工,为方便称呼,本文一致采用“女工”的称呼。。这里所强调的主体性不是通过考察阶级意识或者身份认同来体现,而是回到劳动过程以及女工的日常生活中来考察女工在生产空间中的存在状态。将行动者的主体性放在结构与行动二者的关系维度中,考察行动者面对各种结构的规制,能否积极行动而构建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对主体性考察可细化为对自主性和能力性的分析。自主性意味着当个体面对生活中影响和制约他/她的生存和发展的诸多因素时,个体能根据自身需要独立地、自由地做出选择,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等。能动性则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各种外在因素的束缚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采取策略改变自身的境遇。创造性则意味着个体能够改变客体,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有学者将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看作是主体性的不同侧面,它们表征着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和作用。
本研究即基于上述主体性的含义,考察生产空间下女工的主体性发展程度,面对生产空间中来自资方的各种结构性规制,女工们能否发展出积极的实践模式以打破资方的控制和压迫?她们如何建构主体性?所建构的主体性有何特点?是否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试图通过对
女工劳动过程之中以及劳动过程之外因素的考察来探讨生产空间之下的女工生产主体性的形成,一方面从主体性内涵以及性别角度拓展当前工人主体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女工日常生活的考察,了解她们生存发展中的各种困惑,从而探讨制约女工主体性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为提高女工生活质量,提升其自身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参考建议。
2014年2月,笔者通过招聘进入福州一家隶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的鞋厂SF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文章所使用的材料均来自笔者对SF鞋厂女工的观察和访谈。
二、个案分析:以生存为主导的主体性建构
SF鞋厂属于中外合资企业,是生产名牌NIKE运动鞋的专业代工厂。该厂现有职工4000余人,六条生产线,线上百分之八十多为女工。除少数本地人之外,女工多来自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在该厂的组织结构中,最高层为公司的董事长、正副总经理等;其次为各个车间的厂长;再次是每条生产线上的车间主任;接下来就是直接负责生产的经理和组长;最底层即为既无技术也无权力的工人。笔者进入工厂后被分配在包装组,这是鞋子出厂前的最后一个总工序,具体包括:拔楦与配鞋(把成型的鞋子从楦头上拔下来并配对)、磨胶和补胶、清洗、分配鞋垫、放置鞋垫、塞入鞋撑、整理鞋带、检测、小包装(将每双鞋子装入鞋盒)、大包装(将装有鞋子的鞋盒放入大纸箱并封箱)。笔者所从事的工作是整理鞋带,这一工序最为简单,一般新员工都会被安排从事此项工作。
该厂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女工要严格按照员工准则穿衣打扮才能进入车间,进入车间后一举一动都处在厂长、经理和组长等人的注视之下。每天早晨每条生产线一般都会召开早会,平常因各种生产状况的发生也会召开各种训导会,总之女工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制度、服从上级、服从机器。生产线劳动强度非常大,最经常的情形是女工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厕所,若去厕所必须要找组长来代班,否则自己所在工位的鞋子会不断堆积从而影响后面的进度。笔者所从事的工作整理鞋带最为简单,但几乎每天要整理近两千双鞋子,双手很快长出茧,十指骨节疼痛异常,经常在晚上睡觉期间痛醒。而其他女工也同样经历着这样的折磨,不同的工序需要用到手和胳膊的不同部位,所以尽管身体的皮肤是完好的,但是皮肤下面骨节的疼痛却在折磨着女工们,经常会听到女工抱怨“胳膊肩膀痛得抬不起来”“手连筷子都要举不起来了”等等。就薪水来讲,尽管产量非常大,根据工龄以及技术水平等因素,女工的工资级别各不相同,她们的薪水只能在2000元左右徘徊,根本无法与厂长、经理、组长等人相比。车间常年噪音严重,笔者刚进去的前两天,一天工作完毕,因噪音而导致严重的头疼。而这些女工常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工厂并没有提供任何保护措施,很多女工因此导致耳鸣等病症。此外,生产鞋底的车间则因为塑胶以及胶水加热等各种原因常年充斥着刺鼻的气味,而工厂同样没有提供保护措施。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之下,女工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这个工厂工作五年以上,有的甚至从工厂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这里工作。总的来说,工厂充分利用了女工的低成本劳动以在竞争中获胜,但工厂中存在着劳工权利受损严重、过度加班、工资低下、劳动条件恶劣等状况。
尽管如此,笔者看到的情形却是女工们卖力地投入到生产当中,她们一方面怨恨资方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在忍受着剥削,努力工作,她们的主体性表达首先基于现实的生存需求。
首先,面对生产中的各种不公,女工们惯常的做法是向主管们提出抗议。但是为了保住工作,常常根据主管的态度来采取行动,但最后往往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默默忍受不公的待遇。在笔者旁边工位的女工HP所从事的工作是将鞋垫塞入鞋子中。这道工序比较难以操作,要在鞋垫底部沾满胶的情况下将其平整地塞入鞋中不得有任何褶皱出现。HP来自四川,个子矮小,一双手也比一般人要小很多,正是这一特点使其能快速地将鞋垫塞入鞋中,而其他人做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经常一双鞋垫要塞很多次才能成功。拥有这样的优势,HP几乎无可替代,但在这个工位工作了5年之后,HP的技术等级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现处于39级,而有的新员工一入车间就能拿到30级,为此她感到非常愤怒。生产线上的
经理是一个来自江西的年轻男性,他掌握着提高工人技术等级的权力,但这位经理脾气火爆,经常大声训斥工人,HP对其存有畏惧心理。对于想提高技术等级的想法,她也只是平常通过开玩笑的方式向经理表达出来,或者通过在生产中频繁去厕所以逃避工作的方式提出抗议,而这种方式却让经理十分反感。对与自己是老乡的组长,HP就会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组长的回应通常都是沉默。对此,HP也无可奈何。在生产过程中,女工们会向组长或者经理提出各种要求,例如考虑到工作的难易程度想要调换工位、请假、提高技术等级等,但是组长或者经理奉行的准则是一切以促进生产顺利进行为重,而不是以保障女工权利为重,因此女工们的大多数要求是得不到满足的,久而久之,女工们便只能将自己的要求变成抱怨,然后再心怀抱怨地投入生产当中。
其次,组长和经理是女工们最直接的主管,他们掌握着女工能否请假、能否提高技术等级、能否在流水线上获得好的工位等诸多权力,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为了给组长和经理留下好的印象或者更进一步与他们搞好关系,女工们除了私底下抱怨,甚至不会使用磨洋工等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言的“弱者的武器”。与斯科特研究中的农民不同,女工们身处一个完善的组织之内,处于永无休止的被监视之中。车间里装有摄像头,女工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另外,整个车间的构造类似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厂长可以在车间中间部位建筑的二层上清楚地看到下面生产线上女工的一举一动,而在地面上组长和经理也在监视着女工们的工作。因此,处于如此严密监视之下的女工们,为了不被责骂,一般情况下是不敢有丝毫懈怠的,面对高强度的劳动也只能忍耐。这里的女工们都已不是刚走出乡村的小姑娘,她们都已在外打工很多年,深谙关系效用,因此很多女工在日常生活中即便不会刻意与经理、组长保持良好关系,也不会得罪经理、组长等主管,以便使自己在车间中能够顺利地工作下去。
再次,车间内部从厂长、主任到经理、组长再到女工,所有人的薪水都和产量直接挂钩,一月之内的产量越高,生产奖金也就越多,当然不同职位的人所得到的生产奖金比例是不一样的。在车间饮水处显眼地贴有告知女工这个月生产产量以及超额完成量的通知,以激励女工们努力工作。笔者在调研期间,其中一个月的生产产量较高,而依据自己的技术等级20级,生产奖金也就拿到了325元。实际上,虽然生产产量越高,生产奖金也越多,但是分配到女工手里的生产奖金是非常少的。但是如若没有每月几百块的生产奖金,女工们的薪水可能连2000元都不到。因此,为拿到每月的生产奖金,即使没有主管们的约束,女工们也会在自己的工位上一刻不闲,整个车间都笼罩在拼命赶工的氛围之中。正如布若威所揭示的,工人们玩一个游戏就会产生对其规则的同意,而玩游戏的过程以及游戏的结果使资方与劳方之间产生了一种共同利益,从而使双方的关系得到协调[16]。笔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每当有客户来到生产线上查看鞋子质量的时候,线上的女工们都会积极配合组长、经理等人将之前生产出的优质鞋子放在生产线上以供客户检查。笔者原以为女工们会在此时故意装傻,不配合,但事实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这就说明女工们在此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管理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鞋子质量不合格,管理者拿不到订单,她们自然也没有钱可以赚,因此即便平时受到管理者的压制,遭受各种不公待遇,但是面对这种情形她们还是会积极配合管理者将最好的鞋子呈现给客户。
此外,整个生产流程被分解为多个不同的工序,每个女工被固定在不同的工位上。每条生产流水线的传送带就好比一条链条,将每位女工锁在特定的位置从事某道工序,每个女工都不能逾越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安排一方面为了实现机器和人体的联结,可以提高女工的熟练程度,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权责分明。生产流程的每个工序都有对应的女工负责,如果出现生产问题可以找到每道工序的负责人,从而有利于追究责任。因此,生产流水线的设计和运转使女工们慢慢获得一种独立的个体意识,同时也使女工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将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情和面子,各自的利益将在更大程度上对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起着重大作用。在流水线上,负责清洗这道工序的共有两个
女工DY和LP,她们已共事很久,但是两人却常常为鞋子清洗数量的不同而争吵。为公平起见,她们约定各自负责靠近自己一侧的鞋子,而这就要求面前工位的女工ZL处理完她负责的工序之后,将鞋子平等分配给DY和LP。但是有时候前面工位上的女工ZL却不能做到这点,这就导致她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常常非常紧张。因此,在车间尽管生产流水线是一个由不同工序组成的以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集体性的场域,但是女工们却变得更具个体意识,她们各自在自己的工位上忙碌着,无论前面或者后面工位的女工有多忙碌,她们都不会伸手帮忙。每个人在生产流水线的锻造下变得只关注自我,同时个体也开始据此调节与别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能理直气壮地只关心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成为他人命运的旁观者。从个体角度来讲,流水线使女工获得了个体意识,但是这种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使女工之间的关系呈现碎片化,因而从群体层面上看,女工们却丧失了与资方斡旋的机会与资源,反而限制了其主体性的发展。
总的来看,在劳动过程中,女工们的主体性建构主要基于保有工作的维持生计,她们的生存理念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为了自己的利益,她们会主动和主管们搞好关系,会积极工作等,而她们也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她们也对所遭受的不公以及各种压制感到愤怒,但是为了在工厂工作下去,她们的惯常心态是“忍忍”“习惯就好了”。在调研期间,笔者认识了一位一同入厂的四川女工,她原就不打算在厂里长期干下去,只干两三个月然后就回家照顾高考的女儿,所以她常对笔者说:“有人欺负你,你就提出来,我都是提出来,反正我又不打算长期在这厂里干下去,要是想长期干下去,我自然会和周围人搞好关系。”可见,很多女工的行动选择也都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并且车间里女工的关系是非常原子化的,她们相互之间并没有结成大范围的牢固同盟,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她们都各自行动。总的来说,面对生产空间中来自资方权力的结构性限制,女工们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她们往往为了眼前的实际利益约束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限制女工生产主体性的发挥?什么因素促使女工们愿意长久依附于工厂?她们车间之外的生活体验是如何影响工厂内部的控制与反抗的?
三、女工主体性的形成
面对资方的管理和剥削,工人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抗争?工作场所的生产秩序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笔者将对生产空间、居住空间以及虚拟空间进行综合考察,从而将劳动过程之中的因素和劳动过程之外的因素结合起来以达到对影响女工生产主体性因素的更全面考察。根据在SF鞋厂的实地调查,笔者总结出在生产空间、居住空间以及虚拟空间中存在的限制女工生产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生产空间满足了女工及其家庭生活策略的安排
通过对该厂女工的访问以及附近其他工厂女工的访问,笔者发现,SF鞋厂付给女工的薪水明显要少于其他工厂,SF鞋厂女工每月薪水在2000元左右,而其他工厂特别是计件制之下的工厂女工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薪水,并且,这些小型工厂管理相对松散,工人上班无须打卡,随时可以请假,加班自愿,工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即便如此,SF鞋厂的很多女工仍然拥有5年以上的工龄,每年也不断会有新的工人进入该厂。对此,女工提供的解释有:“SF不会拖欠工资!”“SF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啊,不然我才不会耗在这里!”“在这个厂干活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老公孩子!”对于女工们来讲,每月的收入非常低,并且大部分都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如若拖欠工资,将会对她们的生活形成巨大的打击,因此SF鞋厂每月10号按时支付工资能使女工的收入比较稳定,她们宁愿赚的少一点也想按时拿到工资。在SF鞋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提供是强制性的,一旦进入该厂便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从每月薪水中扣除“两险”的费用,很多新进来的员工会因此离开,原因便是扣除“两险”之后,薪水太低。但是一旦在SF厂工作久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则会成为女工选择在此长期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在于面对恶劣的生产环境以及艰难的城市生活,很多女工的身体并不健康。她们常因医院高昂的检查费用而独自将患病的疑虑放在心中。对于养老保险,她们也希望借此保障自己年老之后的生活,因为女
SF鞋厂的另一个优势便是工作时间的安排满足了女工照顾家庭的需要。李静君在对深圳和香港两地工厂“生产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同属于一家企业的两个工厂中的女工,因其劳动力再生产依靠的因素不同——深圳女工依靠老乡网络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香港女工则依靠家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导致她们对资方的不同依赖程度,资方也据此对她们实施了不同的控制方式。深圳女工多经农村社会亲属关系入厂,其中的老乡关系和性别权力关系成为资方实施管理手段的依据。而香港女工多为主妇,“家庭职责界定了她们的身份和利益,资方对其的控制策略便从满足她们的家庭主义入手”[17]。在SF鞋厂,资方同样从家庭主义入手来实现对女工的控制。SF鞋厂女工多来自四川、江西和安徽等地,老乡关系对她们来说是重要的,但由于资方担心老乡势力干预工厂的经营管理,一般同一组之内多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女工组成。但同时大部分女工在20岁左右就已结婚,现在要么丈夫也在SF鞋厂所在城市打工,要么孩子跟随父母在此读书,资方据此在工作时间安排上充分满足了女工照顾家庭的需要,以实现对女工的控制。工厂作息时间可分为正常班和轮班制,女工可依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上正常班的女工下班后可以接孩子放学同时准备晚饭等等,而孩子年龄已大或者想赚取更多薪水,身体状况良好的女工则多选择轮班制。总的来说,SF鞋厂在保障制度、作息时间安排等多个方面满足了女工个人以及家庭的策略安排,满足了女工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从而使女工依附于SF鞋厂并长期工作下去。
另外,SF鞋厂为女工提供宿舍、食堂、运动场所等生活配套措施,同时在劳动过程之外车间内部会举行多种娱乐活动,并在各种节日对女工施以物质问候,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女工对工厂的依赖程度,使女工更加顺从,进而束缚了女工主体性的发挥。
笔者在该厂工作时就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宿舍虽然简陋,但每间宿舍配有洗衣机和空调,而这两件物品可以说是生活在南方湿热气候之下人们的必备品,这就为女工提供了很大的生活便利。同时宿舍24小时提供热水和冷水,并配有淋浴间,方便女工们洗澡。尽管很多女工因丈夫孩子都在本地而没有居住在宿舍,但她们还是充分利用了宿舍的便利条件。女工们持有工卡就可以方便地进出宿舍区,因此她们下班之后不忘拿着大号的塑料水桶到宿舍接热水以供家庭所用,同时周末她们也会将家里的衣服、床单、被罩等物品拿到宿舍机洗。甚至有女工为了节省家里的水电费,她们会专门到宿舍洗头洗澡,然后再回家,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来节省开支。而这些便利是其他工厂所不能提供的,因此工厂提供的这些生活措施充分满足了女工们实用性质的生活需要,从而将女工们紧紧拴住。
同时,各个车间每年都会举行迎新联谊会、各季度生产总结会等活动,活动会提供各种食物饮料,要求大家准备各种节目,通过这些活动,工人之间、工人与主管之间加强了互动和联系,为日常生产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外,每逢节假日以及女工生日,工厂都会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助。例如在春节、元宵、端午以及中秋等传统节日,公司会向女工分发传统特色食品。而在“五一”劳动节,工厂则会向每位员工提供120元面值的超市购物卡。再者,每位女工在入厂之时,其出生日期便被登记在册,每位女工生日之时可到工厂内的超市免费领得价值30元的物品。对于女工们来讲,她们的收入很低,她们大多持实用主义的生存态度,无论对工厂有什么不满,工厂提供的任何一点物质利益,她们都会乐意接受,就像她们所言“有总比没有好!”,并且附带在有形物品身上的还有工厂的感情投资,这在无形中增强了女工对工厂的认可。因此,工厂针对女工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仅丰富了女工们的业余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女工对工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得到
慢慢培养。
(二)居住空间中遭遇的社会排斥,增强了女工对工厂的依附
社区生活的社会排斥难以培养出女工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反而使女工更加依附于工厂,从而限制其生产主体性的发挥。SF鞋厂的女工大多已婚,为方便照顾家庭,她们往往并不住在宿舍,而在工厂附近的社区租房。同时,有些女工其孩子虽然不在身边,但是丈夫因工作性质会一周回来一次,再加上工厂宿舍管理的束缚,她们也会在附近社区长期租房居住,因此这些女工便拥有工厂宿舍和社区出租房两个住处。总的来说,大部分女工是与当地人混住在一起的。但当地人对女工们及其家庭往往持有根深蒂固的社会排斥,女工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
就当地人和女工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基本上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若彼此认识,见面会礼貌地打招呼,仅此而已。对地方社会而言,女工是外来者,她们冲击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引起当地人的紧张和不适。特别是这些女工都来自四川、江西、安徽等较贫困的地区,当地人似乎天然地看不起这些贫困的女工,他们潜意识里都含有一种对女工们的歧视。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很多产品、技术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特点,而扬州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并不能故步自封,积极对发展模式进行创新,实现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目的。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发挥“三微一端”的作用,扩大扬州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宣传的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不仅如此,当地部门还要联合网络平台、电视频道等,拍摄扬州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宣传片、微电影等,加深人们对扬州运河的认识,并通过中华儿女对传统文化的情结,实现旅游宣传,进而弥补传统宣传方式的不足。在这一基础上,扬州运河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模式,得到了本质的创新,对于其日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地人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从很穷的农村来,是来这里讨饭的,他们好像觉得是他们赏给我们饭吃一样!”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比他们低一等。他们这边的人都太看重钱,你有钱,就看得起你!你没钱,就看不起你!”
“我在这边呆了快十年了,也认识不少当地人,和他们关系一般吧,他们当地人表面上对你很客气,但要是牵扯到具体的问题上,他们一点情面也不讲的。所以我也不想和他们深交,没人情味。和房东算是比较熟悉了,但也就是见面打招呼,交房租、水电费的时候随便说几句,住这么近,也没和他们一家一起吃过饭什么的。我也都是和我同事、老乡玩,和她们在一起比较自在。”
总的来说,当地人与女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社会距离,当地人对女工们持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而女工因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弱势往往自卑、敏感,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上具有被动性。这就导致两个群体的交流互动非常少,社会距离拉大,他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房东与房客等日常的工具性关系而难以发展出情感性的互动。
就社区生活来讲,女工面对的社会排斥主要源于因户籍不同而享有的不同待遇。很多女工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多年,甚至连春节期间都不会回老家,但就是因为户籍问题,她们在当地从来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完全被排斥在当地发展事务之外。而社区内开展的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女工们也不在被邀请之列,她们完全被当作外来者。当地人的孩子可以正常入学,但在访谈中了解到,很多女工的孩子入学并不顺利,要么得缴纳额外的费用,要么需动用私人关系,如此孩子才可进入学校读书。对女工而言,她们无法获得社区提供的生殖健康服务,笔者工作的生产线上,很多女工堕胎多次,并经受多种妇科病的折磨。相比于当地居民,这些女工们只享有非常低的公共服务水平,明显的待遇差别使女工难以形成对社区的归属感,她们只把社区当作一个住处,而不是一个家。相比之下,工厂反而提供给女工更多的归属感,很多女工都将“回宿舍”称作“回家”,可见工厂为女工提供了更多的认同感。
由于无法对社区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在客观上使女工顺应工厂的各种控制策略,进而依附于工厂,而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必然限制女工们主体性的发挥。
(三)虚拟网络空间对女工产生的心理代偿和自我规训,间接阻碍了其主体性的发挥
虚拟网络成为女工们获取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途径,它对女工产生了心理代偿和自我规训的双重作用,对虚拟网络的使用使女工慢慢忘却了现实世界的种种艰辛,在潜移默化之中安于现状,从而间接阻碍了其主体性的发挥。
在这里之所以对网络的作用加以强调,主要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生活是女工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女工产生的作用不可小觑。下面是SF鞋厂女工的一天:CX每天早上8点上班,7点被闹钟吵醒,一边打开手机通过网络听歌曲,一边再睡会儿。躺到7点半左右,匆匆忙忙洗漱,然后再一边听音乐一边简单地吃点早饭,在上班打卡结束
的最后一分钟冲进车间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工作期间,通过手机QQ、微信等聊天工具保持“在线”状态,去卫生间的时候,会故意磨蹭,一边偷懒,一边和网友聊几句。中午下班之后,仅有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CX手机也不离手,下午6点下班之后,CX会在宿舍偷偷煮饭,吃完之后,会和关系较好的姐妹一起闲聊,大家都随身带着手机,讨论各自的网友,一起娱乐。朋友们散去之后,CX洗漱之后便躺下,再在被窝里和网友聊天,或者看网络小说,晚上12点左右便睡去,这就是CX的一天。她的一天代表了大多数SF鞋厂女工的生活状态,即便是有孩子在身边、有兼职要做的女工,手机对她们同样不可缺少,就像她们所言:“和同事整天在一起也没那么多话可说,大家各自上上网挺好的。”对于她们来说,每天在工厂一刻不停地至少工作8个小时,完全服从于机器,几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生产过程被机器大规模地分解,女工们只需不断重复一个个简单的毫无技术可言的动作。不仅如此,女工们的身体、意志和行为在工厂都经受着同质化的重塑,她们被限制在生产线上,毫无主导性,因此,这样工作一天结束后,人便会竭力渴求吃、喝、玩、乐等各种生理满足,而价格便宜又便利的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便很好地满足了女工们的娱乐需求。
以下内容摘自SF工厂女工的QQ空间。
“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的,我们相爱也不是为了生气的。用心付出的东西一旦无法挽回,也不用再怨什么,悔什么。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
“现在的我,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一切都好,真的,都很好。”
“人生苦短,若花草凋落,一路坎坷,一季花凉,遍地忧伤;人生美丽,若四季常青,顺风顺水,惊艳岁月,一路高歌。可谁的人生又能顺风顺水得以圆满?谁的人生没有缺憾全是美丽的花园……”
对这些心灵鸡汤式语句的转发和阅读是女工们试图利用网络文化来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表现,它是一种女工应对日常生活挫折的平衡机制。但是这种平衡机制在平衡女工生活挫折的同时,也规训了女工的自我,在潜移默化之中解除了女工的抗争意识。但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女工来讲,她们的媒介素养水平有限,再加上现实生活的艰辛,容易在利用网络满足娱乐需求的同时迷失自我,甚至失去对现实生活的判断,进而被网络文化左右,陷入网络世界而无法自拔。
四、结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人完全依赖他所在的单位,缺少独立性,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动听从安排,主体性严重缺乏。对于SF鞋厂的女工们来说,她们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拥有选择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她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选择合适的就业机会,双方都可以通过谈判协调各自的权利与利益。但事实上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女工,其主体性发展处于一种较低的层次上。从农村到城市,物理距离的拉长使传统的亲属网络无法对女工形成约束的同时也无法对其起到保护和支持作用。女工不得不独自面对资本的剥削,她们的主体性生长就始于此。为了适应工厂的生活,她们在日常实践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行为模式,而这个过程即为其主体性的生长过程。在理想情况下,在女工们认识到自己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之后,她们将通过有组织的合作,或者借助直接的抗争行动,或者借助工会、法律以及政府与资方进行谈判,从而拿到合理的薪水,进而与资方建立一种合作互利的平等关系。但现实是,女工在日常生产中仅仅会采取诸如咒骂、忍耐而非激烈的方式来对抗资本的压迫,将主体性一再压制,从而使其发展处于较低的层面上。
对于工厂而言,它的主要目标是获取高额利润,为此一方面要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加大生产量,资方目的在于压制女工主体性以顺利获得利润。而对于女工来讲,基于她们的生存及生计以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提供给她们的机会少,选择范围有限。而SF鞋厂则是不多的优质机会之一,它管理相对规范,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且提供简单的福利,从而在劳方和资方的关系中,使资方获得对于劳方的权力。同时,SF鞋厂的各种控制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工对工厂的依附程度,再加上女工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弱势地位,
这就迫使女工在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时不得不与资本“握手言和”,以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资源,这也就导致女工在与资方的互动情境中,无法发展出高层次的主体性以化解各种结构性的规制,进而使其更加顺从于资本的控制,形成了与资方之间例行化的依附与自主关系。
女工们生产主体性的增长有利于女工在劳动过程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与资方斡旋,从而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增长,对女工生存境况的改善具有重大作用。但本研究发现,女工弱势的经济地位和弱势的社会地位互相强化,使其生产主体性处于较低层次并具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它的发挥受到来自劳动过程和劳动过程之外的多种因素的限制,而要改善女工的这种被动处境,则需要双管齐下,市场和社会都需要做出改变。
[1]Lee,C.K..Gender and the Social China Miracle: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2]Burawoy,M..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London:Verso,1985.
[3]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2).
[4]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
[5]徐小洪.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问题研究[J].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6,(1).
[6]刘爱玉.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6).
[7]赵炜.国有企业职工阶层意识研究:对一家国有企业阶层关系的调查与分析[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5).
[8]佟新.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失业危机”对工人的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2,(6).
[9]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1).
[10]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
[11]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12]潘泽泉.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以农民工社会分类问题为例[J].社会,2007,(4).
[13]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7,(2).
[14]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15]王坤庆.精神与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教育反思与建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6][美]迈克尔·布若威著,李荣荣译.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7]李静君.劳工与性别:西方学界对中国的分析[EB/OL].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2/1600.html.2008-12-02.
责任编辑:玉静
XU Li-na1ZHANG Guang-li2
(1.2.Department of Sociology,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female migrant workers;production space;subjectivity;labor proc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subjectivity in labor process,they increasingly found it easier to be proactive in their negotiation with their employers,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of respect for their interes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conditions.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Factory SF in Fuzhou,this paper adopts Burawoy's labor process theory in an examination of female migrants workers'subjectivity in the production space,in order to explain the factors in and outside of the labor process that help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vulner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reinforce each other,which makes them tend to adopt a strong pragmatic approach to exert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labor process.And that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subjectivity is constrained by the limited space they have in the workshop and their living quarters.
C913.2
:A
:1004-2563(2015)02-003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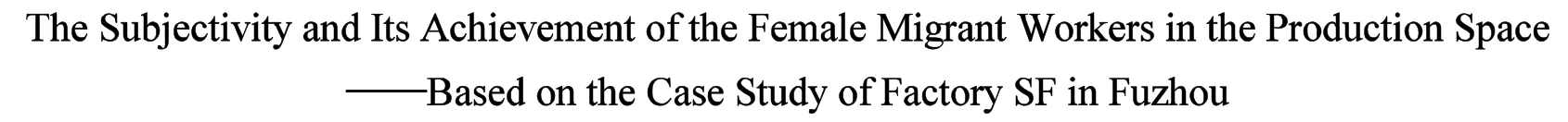
1.许丽娜(1987-),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2.张广利(1963-),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