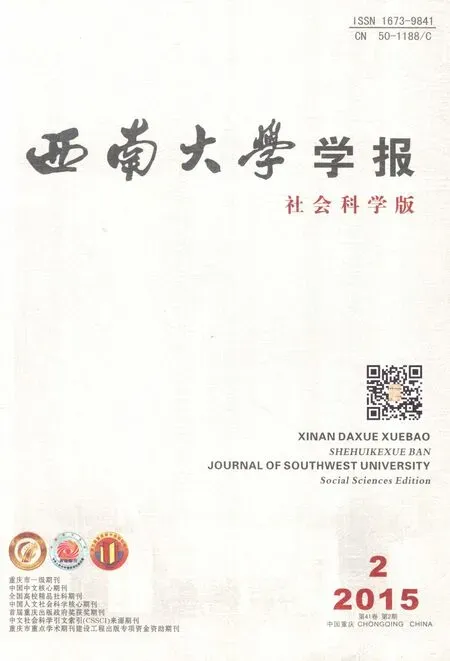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
——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2015-02-24田澍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
——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田 澍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武宗绝嗣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一危机是正德君臣懈怠、乱政的集中反映。在这一危机中,除武宗外,首辅杨廷和是另一关键性人物。在武宗生前,杨廷和对群臣上疏劝谏预立皇储漠不关心,没有对武宗形成强大压力,使解决危机丧失了最佳时机。在武宗死后,杨廷和自作主张,选立武宗堂弟朱厚熜为君,直接造成了武宗绝子。但当世宗继位后,他削足适履,违背遗诏,想当然地提出要让武宗堂弟变成武宗亲弟,试图通过改换皇帝的父母为其造成的武宗绝子弥补遗憾,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来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杨廷和不得要领,胡乱作为,大搞一言堂,要么隐忍,要么张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政治危机时拙劣表现的典型代表。
明武宗;明世宗;杨廷和;绝嗣危机;武宗遗旨;大礼议
明武宗绝嗣是明朝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如何应对这一涉及王朝根本的政治危机,是考量当时各种势力政治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武宗绝嗣危机中,作为内阁代表的首辅杨廷和的表现是最值得关注的。在已往的研究中,学界极少有人以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理性地审视杨廷和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言行,仅仅以其“大礼”主张来就事论事,使对杨廷和的研究难以取得真正进展。鉴于此,特立此题,以武宗绝嗣危机处理的视野来考察杨廷和的应对策略的得失。
一、杨廷和在选立储嗣的呼吁中无所作为
在研究因武宗绝嗣而引发的政治纷争中,学界大多以“大礼议”来笼统地概述这一现象。事实上,以“大礼议”来代替“绝嗣危机”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们两者之间不是对等关系,“大礼议”作为武宗绝嗣危机中的一个争端,不可能涵盖“绝嗣危机”的全部内容。换言之,“大礼议”只是“绝嗣危机”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部内容,所以,用“绝嗣危机”表述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情势更为妥当。该危机是考察正德、嘉靖之际人事变动和政治走向的一条主线。
储君为“天下大本,国家治乱攸系”[1]卷133,正德十一年正月庚子。武宗绝嗣局面的出现,是正德政治极不正常的集中反映,是正德时期君臣败政的典型表现,更是君臣关系极不和谐的必然结局。作为称帝多年且届成人的武宗,一直无有子嗣,成为正德时期最大的政治隐患。一些敢于担当的朝臣深为忧虑,纷纷站出来明确要求武宗效法宋仁宗,从同宗中选择一位,暂时立为皇储,先作教养,以备不测。如正德九年(1514),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要求武宗“讲求我朝留亲王之意,参考宋仁宗育宗室之典,以固根本”[1]卷111,正德九年四月丁巳。不久,广东道御史王光亦言:“皇上嗣登大宝已及十载,皇储之位尚虚,天下之心安得不忧?而上天之戒亦岂虚示也哉?伏望念创业之艰,重天下之本,择宗室之贤者一人,选正直之臣辅导预养之,待皇上诞育,仍遣归藩,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1]卷119,正德九年十二月己巳。但对此类建议,武宗当成耳边风,一概不理。武宗拒绝效法宋仁宗,使选立储嗣久拖不决,直至暴卒,直接造成了皇位的空缺,形成了空前的绝嗣危机[2]。
在绝嗣危机形成过程中,于正德七年(1512)底担任首辅的杨廷和(正德十年三月至十二年十一月丁忧)可以说毫无作为。正德十五年(1520),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范永銮疏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之情不通,近年以来,廷臣或请罢游幸,或请建储君,或请亲君子远小人,惟冀圣心感悟,悔往图新,奈何日月之光逾远,纶綍之音不闻!诸臣论列,得入御览与否,不可得而知也。间有批答,多假乎左右,而内阁之臣无与,臣恐一日祸作,陛下置天下于何所邪”?[1]卷190,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庚戌范永銮对武宗荒嬉和拒绝选立皇储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君臣阻隔和内阁无所作为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毫无疑问,武宗应承担绝嗣危机的全部责任。但如是说并不意味着阁臣就可以置身事外。范永銮等一批朝臣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拖延解决绝嗣危机的严重危害。当绝嗣危机真正到来时,说明范永銮等人并非是杞人忧天。令人不解的是,在形成绝嗣危机的过程中,首辅杨廷和等阁臣大都装聋作哑,尸位素餐,很难像范永銮等朝臣那样强谏武宗预立皇储。可以说,在绝嗣危机的潜伏期和爆发期,杨廷和等阁臣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出现,他们像旁观者一样隔岸观火,出奇地冷静和从容!据《明史·杨廷和传》载: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他既不采取一切措施抢救武宗,又不趁机说服武宗解决皇储,其态度冷漠和举止怪异是明代历史上独有的,这与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的张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武宗暴亡,由他亲自选立嗣君的所有努力正式宣告结束。绝嗣危机如同此前谏言朝臣所担心的那样降临。在三月十三日晚,在豹房中的武宗病危,身边只有太监陈敬和苏进二人,在如此关键时期,后宫和阁臣亦无法面见武宗,武宗也无意向他们交待后事。这既是武宗荒谬绝伦的最后,也是最集中的反映,更是杨廷和等阁臣被武宗视为无有和影响政局能力达到冰点的最好说明。换言之,在武宗弥留之际,阁臣如同废物,被皇帝和宦官抛弃在一边,连顾命大臣的身份也未获得,足以说明武宗内阁的困境和无能。武宗和太监最后向外界传出的指令是:“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1]卷190,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此语是否为武宗临终所言,而无两位太监的矫伪,难以判断。假使为真,从中可以看出,到最后一刻,武宗也没有指定何人为皇位继承人,而只是为自己揽责,为其他人开脱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正德乱政的全部责任。这样的遗言,无论太监,还是阁臣,都是求之不得的,符合各自在后武宗时代的政治利益,完全撇清各自与正德乱政的关系而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武宗也无意解决皇储如此重大的事情,而只是一味地为其他人洗刷清白,自己独自承担全部坏政的责任,这是非常离奇的现象!
二、杨廷和断送了武宗选嗣的最后机会
当绝嗣危机真正降临时,如何有效控制局面,防止出现灾难性后果,是考察朝臣,特别是密勿重臣处理危机能力的重要指标。此时,再纠缠于谁为该危机负责,已为情势所不容,当务之急是解决现实问题,尽可能地将危机中的不确定性排除,使危机的解决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三月十四日,毫不知情的杨廷和等人正在内阁等待武宗钦定殿试题目,以便组织考试,但他们未等到武宗批复,却等到惊人的“驾崩”消息,杨廷和也与众人一样,“惊悸失措”。不过,在惊恐之余,杨廷和“私念危急时天下事须吾辈当之,惊悸何为”?[3]尽管在武宗生前,杨廷和未能促成立储之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廷和也在私下盘算此事,并考虑合适人选。前述他以“伦序”暗示太监就是明证。所以,在死讯传来之际,杨廷和不与众阁臣讨论,便脱口而出:“请众太监启太后,取兴长子来继承大统,莫说错了话”。[3]按照杨廷和的记载,在他说出兴世子朱厚熜之前,还未正式接到武宗遗言,他第一时间得到武宗暴亡消息是送殿试试题的太监传来的。他刚说完此言,“魏司礼英等八人及谷大用、张永、张锐同至阁中,魏手持一纸授廷和,乃大行皇帝遗命……臣廷和、臣储、臣冕、臣纪举哀叩头讫,臣廷和即扬言:‘且不必哭,亦且不必发哀’,遂取《皇明祖训》示诸司礼曰:大行皇帝未有后,当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奉迎兴长子来即皇帝位,兵部选法,伦序相承,正是如此”[3]。也就是说,杨廷和决定选立“兴长子”不是按照武宗遗言行事的。《明武宗实录》对此没有说明。《明史·杨廷和传》也含混其辞,不记谷大用到阁之前杨廷和的主张,并言“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事实上是杨廷和不让他们多嘴。《明史·世宗本纪》也语焉不详,认为“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使不明真相者如云里雾里。倒是《国榷》的记载大致符合实际,认为“大学士杨廷和等定议”[4]后才禀告张太后。可见,在正德时一直隐忍的杨廷和在此危难之际,能够依据《皇明祖训》的相关精神,按照“伦序”原则,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确定皇位继承人,应该说是一种创新。在这一特殊时刻,杨廷和采取了非常举措,用无缝对接的行政手段在一天之内完成了选君、颁诏、派员迎取等重大步骤,这一切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参与者只有阁臣和几位太监。在这一重大决策过程中,他们之间没有展开讨论,是杨廷和以命令的口吻来宣布自己的决定的。从选君和解决危局的角度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依武宗遗诏而言,在选定新君时,杨廷和应与张太后共同“议处”,而不是杨廷和一人决定后强迫张太后顺从。所以说,在选定“兴世子”时,内阁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特别是没有听取张太后的意见。但在后来的“大礼议”中,杨廷和的追随者非说世宗是由张太后决定的,如吏部左侍郎何孟春所言:“今日神器必归真主,虽皇祖之训,先帝之遗诏,固圣母之意也”。[5]卷41,嘉靖三年七月乙卯这完全是为了支持杨廷和而罔顾事实。毋庸置疑,在决定新君人选时,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讨论,更没有与张太后沟通。杨廷和不让讨论,既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好处是在选君时减少阻力,避免引发歧义而使选君流产;不足是对后续问题考虑不周,将产生更大的麻烦。
新君是选出来了,但武宗绝嗣危机并未解决。对“伦序”的理解可有多种观点,但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武宗绝嗣之事,而不仅仅是选择新的皇位继承人。但是,自从杨廷和提出不容讨论的“兴长子来即皇位”后,杨廷和自觉或不自觉地葬送了为武宗续嗣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就是说,是明武宗亲自断送了续嗣权,是杨廷和亲自葬送了为武宗续嗣的最后机会。因为真要在武宗绝嗣之后选择新君,就必须按“伦序”在孝宗之孙、武宗之侄中选定,而不是在宪宗之孙、孝宗之侄中选定。从孝宗之侄中选定新君必然意味着武宗的断嗣。而杨廷和选定“兴长子”继承皇位与武宗生前朝臣要求预选武宗之侄为储君的要求完全相背。快刀斩乱麻的杨廷和在成功选定新君的同时,事实上在制造着更大的麻烦,暂时的平静和顺畅并不意味着绝嗣危机的真正解决。
杨廷和选定新君的意志最后通过武宗遗旨而正式确定,成为不能更改的法律文书。事实上,武宗遗旨不是武宗意志的体现,而是武宗死后杨廷和意志的体现。张太后没有参与讨论,碍于情势只得顺从杨廷和的意见。武宗遗旨的内容是:“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1]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同时又发了一通张太后懿旨:“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1]需要指出的是,遗旨和懿旨中的“弥留”或“寝疾弥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武宗死后杨廷和个人在作决策。但不管如何,通过向天下颁示的遗旨和懿旨,“兴长子”完全取得了称帝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一旦公开,便意味着武宗绝嗣真正变成了现实,而幕后唯一的推手就是杨廷和。
《明史》的作者在杨廷和等人的传记中就武宗死后皇位空缺时对其作为评论道:“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6]这一评论仅仅从维护政局的平稳过渡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从武宗绝嗣危机角度来考察并不确切,是一种短视性的溢美之词,完全无视杨廷和在武宗死后绝嗣危机中的主要责任。杨廷和选定“兴长子”,就意味着武宗彻底绝嗣。可见在绝嗣危机中的最后时刻,杨廷和也照样没有表现出特异才能而找出两全其美的对策,人们不应用选定新君来掩盖绝嗣危机,或忽略绝嗣危机,更不能掩盖杨廷和的责任。
在完全不考虑武宗续嗣的前提下,来选择新君是杨廷和在最后一个关键节点所做出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有极大风险性的。由于武宗暴亡,各种势力在惊恐中同意了杨廷和的主张,杨廷和也在严密封锁消息中暂时获得了主动权。这一特殊情势对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似乎得心应手,可以我行我素。但就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来说,一言堂并非上策。在危机处理初期,主事者要有包容之心,在适当范围之内征求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是必需的。如果压制不同意见,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以非常时期的非常需要为名,拒绝听取不同意见,必将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后果。
三、杨廷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是绝嗣危机的余波
选择“兴长子”并没有解决武宗绝嗣危机,而是正式宣告武宗彻底绝嗣,这完全是杨廷和个人的决定,他要有勇气承担这一历史责任。按照选择新君之日的诏旨和杨廷和的说法,选立“兴长子”是来当皇帝的,而不是给孝宗当儿子来的。这是必须明确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念。无视这一点,就不可能理性考察世宗即位后所出现的与武宗绝嗣危机的任何争论。
选定“兴世子”之后,杨廷和有了充裕时间来认真面对和思考武宗绝嗣的问题。在选立新君时,杨廷和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未能把选君与解决武宗绝嗣统一起来,反而使该危机进一步加重,在最后关键时刻直接造成了武宗的绝嗣。杨廷和在发现问题后,自然要想法弥补,那就是要把“兴长子”改变成孝宗之子。因为作为武宗堂弟的“兴长子”,怎么改也不可能变成武宗之侄或武宗之子,只有硬着头皮迫使他变成孝宗之子,使孝宗一系通过“兴长子”而得以继承而不绝,这是杨廷和在发现漏洞之后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能否实现,却不是由杨廷和个人所能掌控的。也就是说,在新君即位之后,杨廷和已无任何权势可言,他左右不了政局,也左右不了皇帝。
前已述及,“兴长子”合法称帝的唯一依据就是武宗遗旨。虽然这份遗旨是由杨廷和等人打着武宗的旗号向天下颁示的,但一经公布,任何人都必须遵循。大多数研究者不明武宗绝嗣危机的发展路径,转移视线和话题,以杨廷和的是非为是非,要用“大宗”来重塑世宗称帝的合法性依据。
张太后懿旨中有“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告示。像能否改换皇帝父母这样的大事,杨廷和要像一个多月前一人指定“兴世子”称帝那样来决定,要把自己个人的意图变成朝廷的政策,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极度无知的表现。但是,杨廷和还沉浸在无君的特殊时期,当新帝登基后,他还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称帝后,当世宗要议定其父尊号时,杨廷和依然像武宗暴亡后那样,拿出汉宋事例命令礼部毛澄:“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6]世宗要礼部议定其父兴献王的尊号,而杨廷和却越位指令礼部改换皇帝的父母,并且连称谓都已想好。不难看出,杨廷和早有准备,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和“周密”。这是他自己想好的危机处理预案,也是他自认为绝对有把握的危机管控方案,他不与皇帝沟通,背着皇帝要豁出来单干,从一言堂的第一个漏洞向第二个漏洞转移。杨廷和的这一表露和越位充分说明他的狂妄自大,根本不把新君放在眼中,缺乏基本的行政能力。如果他是精明务实和遵守规则的阁臣,自己不应在第一时间插手此事,而是先让礼部组织廷议,听取不同意见,再探求各方能够接受的方案。但杨廷和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违背议事程序,将自己置于绝境之中。在未与皇帝沟通的情况下要强迫当朝皇帝改换父母,使世宗无地自容,这不是在皇帝即位后一位精明政治家的理性选择和应当行为。“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是杨廷和最无知的表现,表面上好像是说给朝臣听的,实际上是说给世宗听的。按照这一指令,世宗也不得有异议,否则,也在“斩杀”之列。世宗对杨廷和的“冒犯”,在入京时就已不满。当时杨廷和要让世宗按皇太子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但世宗明确告诉他们:“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然而,杨廷和自恃“拥立”之功,自以为是,不予让步,仍要求世宗按照皇太子礼入居,又被世宗拒绝。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张太后出面调停,否定了杨廷和的主张。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杨廷和彻底失败。但第一回合的预演并未给杨廷和以清醒的警示,他仍不死心,准备再找机会迫使世宗就范,以便挟持世宗,形成强臣弱君的局面。“当斩”之说就是杨廷和使出的又一杀手锏,主要是针对世宗的。人们应该明白,杨廷和没有任何权力和资格发布这样的命令!在中国古代,恐怕人们找不到第二份这样公开恫吓和威胁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的斩杀之令。杨廷和这一急不可耐的命令,事实上反映出了他对自己当初选择“兴长子”的极度懊悔和焦虑,更反映出他在冷静之后认识到自己在武宗绝嗣危机中的巨大失职。他试图要以飞蛾扑火式的精神把世宗变成孝宗之子,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能量。正是杨廷和一手点燃了火药味十足的大礼议,故大礼议是政治事件,而绝不是简单的仪礼性争论。但杨廷和自此再不可能像选君那样在完全封闭的真空中决策,他自己一言堂的决策没有任何授权,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条件保障,他的提议必须经过公开的讨论,而这一讨论是他无法也无力独自操纵的。对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哪有不让争论的道理?哪有把反对者视为“小人”的道理?哪有“斩杀”反对者的道理?从杨廷和要斩杀反对者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已知道讨论结果的不妙,暴露了自己的心虚。当世宗即位后,杨廷和的政治生态已完全发生了变化,但他仍然沉浸在武宗死后的皇位空缺时期,仍想享受无君时期的权力快乐。他无视现实政治的巨大变化,完全忘记了作为阁臣的自己是君主的附庸,自不量力,要依靠过时的孝宗皇权向新君挑战。杨廷和无视廷议程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将一己之意强加于皇帝和群臣之上,不容议论,完全是乱政行为。在杨廷和的高压和恐吓下,依附于杨廷和的朝臣利用自己的一点点知识极力迎合杨廷和,用一些奇谈怪论挑战世宗的合法性。如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等人把世宗继统不继嗣看作是商代夏、周代商的王朝断裂,言:“自家天下以来,气脉相承,未有继绝不继嗣者。若云只要帝王之统不绝,不必继嗣,则如汤之于桀,夏之统不绝;武王於纣,殷之统不绝,皆谓之继统可也。皇上奉先帝遗诏入继大统,而谓之不必继嗣,彼欲皇上比于汤、武也,将宜先帝于何地也”![5]卷41,嘉靖三年七月甲子
当皇位空缺时,杨廷和可以利用非常时机的借口而无视懿旨“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约定,向外发号施令,但当世宗即位后,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自己必须回到阁臣应有的角色。像让当朝皇帝改换父母这样的大事、难事,杨廷和还想唱独角戏,自作主张,并想再次获得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当世宗以“兴长子”身份真正称帝后,武宗绝嗣危机应该画上句号,杨廷和必须迅速转换立场和角色,利用“拥立”之功与新帝建立新型关系,以有所作为于世宗新政。但杨廷和在这个时候又把弥补武宗绝嗣危机的缺憾视为自己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标,要让新任皇帝为该危机负责,把武宗绝嗣危机转嫁于世宗,试图把世宗拉进该危机的漩涡之中。然而,世宗并非等闲之辈,更不是任人摆布的弱智之君。世宗自从接到武宗遗旨,就能看明白自己称帝之后仍然是兴献王的儿子,不会因意外得到皇位而改为别人的儿子,即他不会拿皇位换父母。在世宗看来,这是做人的基本尊严。否则,他不会跑到北京自投罗网,唯利是图,甘当他人之子,让天下之人耻笑。在讨论武宗绝嗣危机以及大礼议时,武宗遗旨是世宗称帝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杨廷和试图移花接木,转移视线,用隐蔽手段将世宗改换成孝宗之子是徒劳的。大礼议中的纷争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明了。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派展示给世人的是:即使他们引经据典,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甚至虚晃着“程朱”的旗号,都不可能达到目的。用所谓的“大宗”取代武宗遗旨而将世宗引入到武宗绝嗣危机中的企图只是杨廷和的一厢情愿,不可能像选君那样简单粗暴地命令他人,特别是使世宗完全接受更不可能。
大礼议最终的结果是彻底否定了杨廷和的主张,完全按照武宗遗旨确定了世宗与兴献王朱祐杬的父子关系,这是没有悬念的结局。嘉靖三年(1524),世宗钦定大礼议,此举具有标志性意义,武宗绝嗣危机最终由世宗划上句号。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清洗,标志着武宗绝嗣危机的真正结束,这是武宗君臣在选立储君问题上不作为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造成武宗绝嗣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武宗和杨廷和等人直接造成了武宗的绝子和孝宗的绝孙,而杨廷和要把这一责任转嫁给世宗的图谋未能得逞,通过公开讨论的大礼议纠正了杨廷和的错误主张,正视武宗绝嗣,最终承认武宗绝嗣,该危机便以确定世宗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君临天下而彻底结束。至于当时部分臣民和后来的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和争论不休的礼仪和礼制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不应与世宗能否改换父母混为一谈,因为对“争考”与“争庙”等的争议完全不是同一性质和同一层面的问题。
大礼议是武宗绝嗣危机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是武宗生前预立皇储和杨廷和在新君继位前后大搞一言堂的总爆发,其结果是使延续十多年的武宗绝嗣危机得以最后解决。这是大礼议最核心和最显著的政治功能,但长期被学界漠视。
四、杨廷和应对武宗绝嗣危机的教训
从武宗绝嗣危机的整个过程来看,杨廷和始终没有找到万全的应对之策,该危机是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处理失败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危机初期的不作为
在危机潜伏期,敏锐的朝臣不断上疏,要求武宗效法宋仁宗预立皇储,但武宗一再错失良机。在这一时期,杨廷和等阁臣也漠不关心,使危机处理失去最佳时机。可以看出,此时的君主和阁臣视立储为儿戏,集中反映着正德时期朝臣特别是阁臣的懈怠和政治乱象,使绝嗣危机在渐变中日益复杂。
当武宗在豹房弥留之际,他仍与宦官鬼混在一起,未能像其父孝宗那样将阁臣召至榻前交代后事,杨廷和等人也未能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那样成为顾命大臣,使武宗自己亲自解决绝嗣危机失去了最后机遇期。在武宗本人未能亲自解决皇嗣之后,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掌握在杨廷和等阁臣手中。当武宗去世之后,内阁暂时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前台,作为首辅和在阁资历最深的杨廷和理应在这一关键时期尊重武宗生前朝臣要求效法宋仁宗预立皇储的建议,从武宗侄子辈中按“伦序”选立嗣君,亦可有效化解危机。但杨廷和并未顺应朝臣的共识和要求,却从武宗同辈中选立,并不让争议。此举从选君继统来讲是可取的,但从解决武宗绝嗣危机的角度来说是不可取的。杨廷和此举其实是对长期以来要求武宗续嗣主张的极大蔑视,说明杨廷和并不认同朝臣的主张,这从另一方面揭示武宗生前杨廷和为何对朝臣续嗣主张冷漠的原因。当杨廷和决定由武宗堂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皇位时,就正式宣告了武宗的绝嗣。
(二)危机到来时的乱作为
在按杨廷和之意快速选定新君之后,杨廷和才意识到武宗绝嗣的严重性,但收回成命已不可能。此时的杨廷和已没有在选君时的担当意识,而是要自毁形象,自绝于世宗,盘算着要依靠自己虚弱的力量将“兴世子”改变成孝宗之子,要尽可能地减轻自己的责任。武宗绝嗣已被杨廷和彻底断绝,但他动员一切力量要把朱厚熜变成孝宗之子,要把朱厚熜变成武宗亲弟。只有如此,杨廷和才能向天下有个交待,向张太后有个交待,也向自己最后造成的武宗绝嗣有个交待。既然世宗和武宗同为一个父亲,那就是亲兄弟,既使武宗绝嗣也能勉强说得过去。这是杨廷和的如意算盘。可惜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能否实现,显然不是由杨廷和一人说了算。换言之,选君时,杨廷和说了算,但要皇帝改换父母时,杨廷和说了不算。
长期以来,学界对大礼议的研究存在巨大误区和许多盲区,即无视武宗绝嗣危机,仅仅认为大礼议就是对兴献王尊号的争论,研究大礼议只从讨论世宗之父的尊号来孤立、片面地展开,而没有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理性地认知大礼议。笔者之所以坚持认为大礼议就是对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就是要改变这一认知模式,揭示大礼议的核心和本质问题。只有洞悉武宗绝嗣危机的演变,并以该危机为主线,才能真正理解大礼议的真实面目。离开武宗绝嗣危机,就不可能理性地认知大礼议。而杨廷和试图用改换世宗父母的作法来弥补自己决策的巨大缺陷,又使自己身陷深渊,无力自拔,直至彻底失败。换言之,杨廷和要世宗改换父母,犹如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成功,是一个最愚蠢和最幼稚的政治选择,其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和自取灭亡。从整个危机演变的关键环节来看,杨廷和始终定位不准,胡乱作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加严重,最后以自己的完败而告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过高地估计了此时杨廷和的能量,有意或无意地把杨廷和当成此时的支柱。事实上,杨廷和根本无力完成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企图。人们不应该忘记,杨廷和在正德十五年(1520)连要求武宗主持正常的殿试的能力都没有,致使该次殿试延迟至下一年,而且是由世宗即位后补试的,成为明朝和科举史上的一大奇闻怪事。
(三)新君时的路径错选
在世宗入京时的第一次较量失败以后,杨廷和并没有认清形势,立即改弦易辙,而是一意孤行,决意与世宗对抗到底。杨廷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也就意味着他完全选择了与世宗对抗而无法回旋的不归之路。他未能抓住“拥立”世宗的历史机遇而换得新君的好感与信赖,最终葬身于武宗绝嗣危机之中,成为武宗绝嗣危机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是杨廷和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不是世宗打败了杨廷和,更不是张璁打败了杨廷和。那种过分强调世宗用皇权镇压杨廷和,以及张璁“迎合”世宗而击败了杨廷和,完全是一种肤浅乃至错误的认识!杨廷和在武宗绝嗣危机中的表现,集中反映了他无力应对政局巨变的大潮,没有能力抓住政治机遇,他的应对失误使自己和追随他的人一并成为武宗绝嗣危机的最终受害者。在选立世宗后,他又选择了忠于孝宗的路线,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行为,绝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的作法。在杨廷和选立新君之后,再不可能有兼顾两者利益的万全之策,侵害当朝皇帝的利益而要成全已逝皇帝的利益,这是一个危险极大的选择。这个选择如果碰上一位昏庸和见利忘义的皇帝,也许能够迫使其就范。但如遇上稍明事理的皇帝,肯定不会成功。不幸的是,杨廷和恰恰碰到的是后者。杨廷和因此成为“三输”型的政治人物:他未能为武宗续嗣,也未能为孝宗再变出一个儿子,更未能换得世宗的尊重和好感。杨廷和不可能一方面造成武宗绝嗣,另一方面又要忠于孝宗;也不可能一方面与世宗水火不容,另一方面又要有为于新政。他选择了忠于前朝,就必然为新朝所不容。故他们被世宗通过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顺势清洗是当时政治的需要,完全符合世宗的政治利益,也完全符合明朝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自掘坟墓而被世宗清除政坛的过程。正是杨廷和逆势而行,故被世宗遗弃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世宗生长于湖北,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也对社会风气有深刻的感受,完全不同于生于后宫、教于深宫的皇储。如果说后者是温室中成长的话,那么世宗就是在大自然中接受阳光成长的,他知道临民做君的道理,更知道不能因为意外得到皇位而随意改换父母,抛弃自己的至亲,否则,无有脸面立于万民之上!在大礼议中,世宗就是要依据武宗遗旨得到自己应有的名分,维护自己父母的合法权益,成为万民的榜样。他说:“人君能尽伦理以立于上,万姓化于下,伦序明而人道备,福将自至。”[5]卷81,嘉靖六年十月丙寅世宗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赢得了胜利。杨廷和无视现实而削足适履,拿过时的旧礼来压迫世宗就范,实践证明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从危机处理角度来说是完全失败的,是一部典型的反面教材,其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和汲取。
[1]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2]田澍.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07-110.
[3]视草余录[M].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M]//国榷·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89.
[5]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6]张廷玉.杨廷和传[M]//明史·卷190.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张颖超
K248
A
1673-9841(2015)02-0139-07
10.13718/j.cnki.xdsk.2015.02.018
2014-08-10
田澍,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