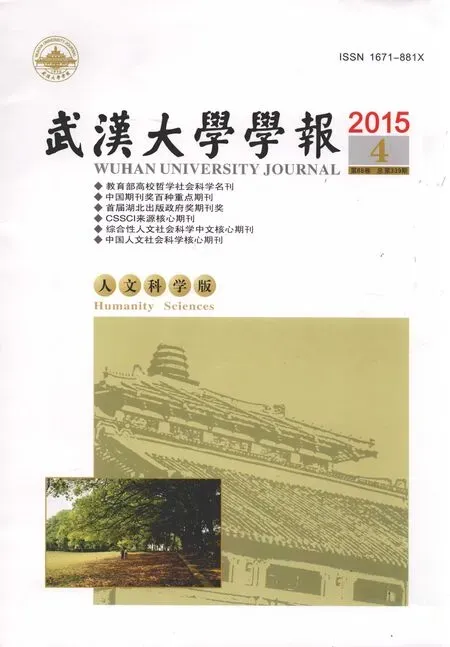“丽则”: 扬雄赋论与汉赋嬗变
2015-02-23刘冠君
车 瑞 刘冠君
“丽则”: 扬雄赋论与汉赋嬗变
车瑞刘冠君
摘要:以“丽则”说为代表的扬雄赋论,对汉赋的创作与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层面成为汉赋走向自觉的重要理论指标。“丽则”说与汉赋自觉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扬雄认识到“丽”乃汉赋的本质特征,并且将弘丽确定为大赋的文体特性;二是扬雄反思并批判汉赋之“丽淫”,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创作规范;三是汉大赋虽努力适应“丽则”思想而未能实现,从而表现出汉赋体制的惰性;四是后来抒情小赋的出现呼应了“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美学主张,既在另外一条路径上实现了汉赋体制的转变,同时也表现出理论影响创作的滞后规律。
关键词:扬雄; 丽则; 赋体; 嬗变 “丽”者,“弘丽”之谓也。“丽”之一字,乃是扬雄赋论的。无论是扬雄早期创作的模拟风旨,如名作《甘泉》《羽猎》等,还是他晚年悔赋之憬然而悟,明确表态“壮夫不为”等,无不围绕“丽”字立论。“丽”之内涵,不仅打着扬雄之前文学思想的鲜明印记,还带有大汉王朝宏伟壮丽的文学风貌,这些都是赋所以独立成体与区别其他文学样式的决定性因素。“丽”作为汉赋审美特性的提出,蕴含着扬雄对赋体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洞察,也呈现出扬雄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整体思考。
一、 弘丽:本质的体认与深化
在扬雄之前,“丽”作为审美概念已经进入赋的批评领域。面对众多文人对赋的责难,汉宣帝回护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829页。随后,围绕“大者与古诗同义”之说,展开了对赋所表达内容的探讨,将赋的意义与诗三百所代表的价值规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汉宣帝将赋体的价值提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尊体的表现,而尊体正是文体自觉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一随口应答,成为扬雄赋论展开之先声。“辩丽可喜”则是对赋的宽容与怜爱,与古诗同义乃是对赋体的理想期许,但并非所有的赋都能达到这种境界;而赋之小者虽未达到这一高度,却拥有“辩丽”的审美特色。“辩丽”之所以可喜,乃是因为:辩通之于声调流畅,韵律动人;丽通之于文辞华美,富艳悦目。扬雄后来对赋的尊尚与贬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遵循着宣帝开创的这两条路径。
在“丽”的概念进入赋论之前,它的本义为偶俪,之后又引申出附丽、连缀等义,再进一步引申出美丽的含义。在宣帝之前,作为美丽之义的“丽”已经大量出现,开始时多用来形容容貌与屋宇,后来用到音乐欣赏方面,如《淮南子·原道训》:“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淮南子》,陈广忠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45页。用其来形容音乐的美妙,乃是“丽”作为批评术语进入赋论的桥梁,所以才会有宣帝的言论。扬雄的赋作也多次用其美丽之义,如《羽猎赋》云:“丽哉神圣,处于玄宫。”*《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542页。“未皇苑囿之丽,遊猎之靡也。”*《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553页。用“丽”形容宫殿与苑囿风貌。大量美丽之“丽”在其他领域中被使用,是“丽”进入赋体文学批评的重要契机,而汉宣帝的无心栽柳,则成为其进入赋论的开始。扬雄正是从此背景下,将此字纳入了赋体批评之中,并将之作为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重点论证。
扬雄生长于相如辞赋之乡,成年于武宣盛世之后,辞赋的繁华方兴未艾。一方面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模式的形成,另一方面时主如汉成帝热衷于辞赋铺夸,扬雄好辞赋便在时代氛围之下成为自然而然之事。《扬雄传》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515页。对相如赋的推崇与模拟是扬雄辞赋创作的开始,而他所取法的是相如赋的“弘丽温雅”——“温雅”姑且不论,而相如的“弘丽”确是一种代表着汉代盛世气象的博大之丽,即“弘丽”:从大赋规模之弘到描述心胸之弘,由铺排文辞之丽到描绘内容之丽,都成为扬雄取法的内容。相如赋具有这种气象,才使得《西京杂记》中会出现托名相如的“赋迹”、“赋心”之说,也使得扬雄能够拥有足够的资源在《河东》《甘泉》《羽猎》《长杨》四赋中实现模拟与创新的有效融合。扬雄在与刘歆的书信中说自己:“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林贞爱:《扬雄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沉博绝丽”就是对“弘丽”内涵的注解,在博大的基础上加之以深沉,而又将“丽”的要求推到了极致。我们反过来看,有理由相信班固所说的“弘丽”或是从扬雄自述的“沉博绝丽”中而来,而班氏在词汇提炼的过程中,丢失了一部分扬雄对“丽”的狂热追求以及重视赋之内涵深沉的创作倾向。前者是扬雄前期尚丽赋论之典型代表,而后者正是扬雄后期赋论转变的种子,从对形式文辞的强调转而更为重视内容,更为重视赋的教化作用。扬雄在理论上对“丽”的强调,充分体现于自己的创作实践。
无论是“弘丽”还是“沉博绝丽”,都是汉大赋根本特征的本质表述,标志着扬雄早期关注的重点在于汉大赋,而且是对于司马相如创作传统的继承发扬。扬雄对于“丽”的认识在后期得到进一步深化,但是对于“丽”乃赋之本质的看法却始终未曾改变,他虽然会以有用无用来衡量,却还是能够在提出新的创作标准时,仍然坚持“丽”的传统要求,从他对于“丽则”、“丽淫”的辩析就可看出,无论是诗人之赋还是辞人之赋,都在“丽”的笼罩之下,将“丽”作为赋体的本质特征,也就更加清楚明白。两百余年后,在文学全面自觉的时代,曹丕《典论·论文》在概述诗赋的特点时,还对此遥遥呼应说:“诗赋欲丽。”如果说“丽”还是诗赋共有,那么“弘丽”与“沉博绝丽”则是大赋所独有,是扬雄对于大赋深刻体认之后的不易定论。
扬雄对于赋的认识并未止于“丽”之一面,而且随着后期思想的转变,对于赋的思考也开始发生变化,从偏重艺术风格转而更重思想内容,从对文体本质特征的认识,转向了大赋本体价值的探索。
二、 丽则:扬雄的反思与重铸
扬雄晚年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日趋严峻,心中忧惧日深。他开始思考赋的本体价值,鉴于之前所献大赋欲谏反讽的弊端,于是发表了悔赋言论。《扬雄传》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3575页。扬雄认为赋想要讽谏,必然铺排联类,使文辞丽靡之极,铺扬张厉,纵横恣肆,虽然会想方设法地表达主旨,结果却不惬人意,劝而不止,反而变本加厉,难以收到讽谏的效果。如此一来,丽靡之辞的存在价值就成了问题。
扬雄“尚丽”有一个历时的发展过程,即前期的崇尚“绝丽”、“弘丽”,到后期对“丽”进行反思,从赋的功用角度切入来批判对“丽”的单纯崇尚。这一过程与他对赋体文学的认识紧密相关,标志着他对赋的重视从艺术层面转移到了本体层面,艺术形式让位于理性主旨。一方面体现了赋在当时势力之大,文体自觉性之高,对艺术美的追求之切,以至于引起了正统文教观念的对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以功用价值来衡量文学的观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还要等到魏晋才会大量出现。
扬雄的转变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并非简单赋体观念的变化。扬雄文学思想由早年“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到后期“女恶丹华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的悔赋之变,“只是交战于他思想中的矛盾的表面,而其深层,则无疑是双重主旨,如同交响乐中两个主旋律(文以载道与文道玄览)在扬雄意识中的反复出现”*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这一方面作为道、儒矛盾在扬雄身上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表现出自然之道与伦理之道的交融,伦理之道占据了上风,因此他便以“正”来规范赋,以取代以相如为代表的汉赋旧范式,以创造有益于教化的新规则,于是“丽则”说的提出也就自然而然了。扬雄《法言·吾子》说: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雄:《法言》,韩敬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3页。
“淫”本为过甚之意,子曰“郑声淫”,《书》曰“罔淫于乐”*陈戍国:《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13页。,都是形容音乐过甚,破坏了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与中正不颇的平衡状态。这表现于赋论,即扬雄少时所好之“绝丽”,后期所批评的“闳侈钜衍”,故而对于文采铺张的过分追求,影响到了赋作内容的表达与现实作用的发挥。扬雄批评景差、宋玉等人的作品为辞人之赋,将之作为“丽以则”的反面典型加以否定。
“则”本是定差等的界划标准,即评判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如刘熙载比较了《扬雄传》说相如赋“宏温雅丽”与扬雄的“丽以则”,指出“则与雅无异旨也”*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5页。;再如《左传·隐公十一年》传“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77页。,以经、则对举,可以看出二者意义相似,指一种稳固的评判标准。扬雄以“则”论赋,就是为赋的创作确立一个正确标准;而这一标准的内涵,其实就是儒家经典“诗三百”的雅正思想,这从孔子对待郑、卫之音的态度即可看出。许结说:“从大的文学传统来讲,赋的传统独立性是不强的,是受到诗的影响,而构成了‘以诗代赋’的批评传统,我们对赋的批评就带着这样的印记,诗歌批评的印记,包括早期赋家自己的批评也是如此,如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都是这样一个传统。”*许结、潘务正:《赋学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88页。下面我们看下扬雄《法言》与“丽则”说相近的三条论述:
“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扬雄:《法言》,韩敬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9页。
第一条将淫辞与法度相对,指出淫辞是文章大害,关键就是破坏法度。这里的法度就是“则”。第二条,将雅、郑并举,也就是则、淫对举,中正乃是遵循法度的表现与结果,同时也是儒家构建理想社会范式与个人行为模式的重要标准。第三条辨析事、辞,“伉”有质直之义,而“赋”则涉及扬雄批评辞人之赋的特点“淫”,即辞藻过盛。“事、辞称则经”,既可以理解为事、辞相称的就是经典,也可以理解为达到了经典所代表的理想境界,亦即“丽则”规范。
扬雄提出丽则、丽淫说是想用经学理想规范漫衍不归的赋,以期将这种文学样式纳入儒学庞大的教化体系之中。他的“丽则”概念表达就是“中正”标准,就是文与质的完美结合,他把儒家文质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推衍到了赋论领域。而这种新规范的提出,也正是汉赋自觉的重要标志,它开始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向某个理想标杆靠近,不断地调和自身与这个理想之间的矛盾,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正是在这一取法的过程中,改变了之前混沌的存在状态,成为自我体认的有意识的主体。
可以说,汉赋在规范之下的自觉,一是应答了理论的指导,赋作向理论要求的高度靠近,产生部分积极的变化;二是面对理论的指导,显现出强大的自主性,并未顺从评论家的指挥棒立即行动,而是沿着原来的轨道和惯性继续滑行,只有到了新的时代,依靠多种因素的作用,才能出现根本性转变。
三、 自觉:大赋的遵从与背反
扬雄“丽则”说提出之后,反应最为迅速的当属班固。班固与扬雄时代相近,而生活环境却大不相同——一个是西汉乱局,一个是东汉新政;一个是礼崩乐坏,一个是经学重建。生时寂寞的扬雄,“丽则”赋论恰好适应了东汉前期的社会形势,班固成为他的第一个追随者。“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6页。班固完全赞同扬雄的观点,并以此为标准评价扬雄早期作品,将之与宋玉等人比较,视为辞人之赋的代表。班固认为,“扬子悔之”是关键一环,他认识到了扬雄前后思想的变化,并由此将扬雄赋论与赋作区别开来。班固一开始就接受了扬雄的“丽则”说,将诗人之赋与“丽则”作为创作标准,在《两都赋》中出现了与西京大赋不同的地方。不过,这种变化是微小的,而且集中体现在颂扬上,继续发挥汉赋“美”的功能,直接导致劝谀,而非讽谏。《东都赋》毫不吝惜赞扬之笔,从王莽之乱一路说起,将汉朝光辉历史细细道来,赞颂力度比《文王》《公刘》诸篇颂周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明帝更是称颂备至:班固作品发出“盛哉乎斯世”的感慨,恰可作为此赋的中心点题,更遑论之后的《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了!
班固的赞颂在张衡的《东京赋》中变本加厉,张赋对东汉制度的颂扬不遗余力,其有别于班赋的地方在于对礼的重视,张衡借安处先生之口批评曰:“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宜其陋今而荣古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3页。“礼”就是《东京赋》的中心,这与扬、马赋作对于山川、器物等穷奢极丽的铺陈已有不同,扬、马的传统被他集中地留在了《西京赋》中,留在了被批判的凭虚公子口中。延续班、张的颂扬之路,到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登峰造极,其延续《诗经》进行颂扬的目的明确体现在《序》中:“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宜,匪赋匪颂,将何述焉?”*《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09页。赋的结尾(乱辞)云:“栋宇已来,未之有兮。神之营之,瑞我汉室,永不朽兮。”*《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18页。充分表明作者对大汉王朝的归属感和身为此强大王朝子民的荣耀感。不过,王延寿没有从东汉新建的宫殿中找出一个吟咏对象,反而是对西汉遗留下来的一个王国宫殿情有独钟,将之作为大汉声威的代表,正可看出东汉人对西汉旧梦的迷恋,也间接地看出时人对于危机渐起的东汉王朝满怀忧虑。颂扬一路也在东汉王朝日渐混乱的形势下由盛转衰,汉赋的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扬雄“丽则”说的尊从与背反集中体现于一人身上,那就是赞成扬雄最力的班固。他的《两都赋序》表现出对汉赋的不同观点,认为武宣盛世的众多赋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页。,某种意义上否定了扬雄对这些赋作“丽以淫”的评价。而观乎班固的《两都赋》,却是“宣上德”者多,而“抒下情”者近乎无,所谓的讽喻更是难得一见。号称有讽谏之意的《二京赋》,尽管张衡精心构思,着笔用力,讽谏效果却微乎其微。
由此看来,大赋已是积重难返,想要用大赋来讽谏,只能是不免于劝。赋家讽谏之心虽在,但所用的体制仍是扬、马旧式,故讽谏效果自然不佳。汉大赋的这种尴尬处境,集中体现了正统文学理想与赋体文学自身倾向之间的矛盾。在古典标准与自身规律的冲突交融之中,汉赋取得了自身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并不体现于汉大赋,即使左思的《三都赋》也不过篇幅加长,铺陈增丽而已。汉赋真正发生变化,由铺陈大赋到抒情小赋转变,是由班彪的《北征赋》开启的。
四、 转变:小赋的形成与开拓
在《北征赋》之前,扬雄的《解嘲》运用大赋的体制来抒写心中抑郁,已经有了转变的痕迹。所谓“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为卿相,夕失势为匹夫”*林贞爱:《扬雄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127页。,言辞大胆犀利,已非《子虚》《甘泉》诸大赋可比,已有赵壹《刺世嫉邪赋》的雏形。扬雄后期的赋作与学术论著,改变了前期弘丽的风格,增加了沉博的内容,模拟经典的行为与愤世嫉俗的批判,都表明他开始向自己所提出的丽则标准靠近。
《北征赋》是两汉之交出现的佳作,采用骚、散两种句式,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蕴含了一些近乎诗人之义的因素,由一己遭际上升到对社会现实的感伤,正与《黍离》等篇立意相类。班彪以行迹为线索,触目所见,有感而发:“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阨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黍离之悲、身世之感,全部都凝聚在一唱三叹、盘桓郁结之中。至于“风猋发以飘飖兮,谷水漼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皚皚。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霑衣”*《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9页。,无论写景还是抒情,都已经向诗歌靠近,而且比诗经、楚辞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不但成为汉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过渡,也可看做诗歌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彪女班昭《东征赋》也有类似特点,只是情感要单薄得多。紧接着就是张衡的转变,《归田赋》拓展了二班赋作的写景抒情因素,从外在的讽谏颂扬转向个人情怀的抒发,抒情小赋也就在转变中形成,汉赋的转型至此真正获得了实现。
抒情小赋实现了扬雄“丽以则”的审美理想,而其途径便是赋的诗化。从隐微一面来看,抒情小赋与三百篇血缘更近,而非汉人用伦理教化标榜的“诗经”;从艺术形式与成就看,比它脱胎的母体更加成熟;从体制看,长期以来持续发展的骚体赋,无论结构方法还是抒情基调,乃至句型都是骚体模式。这不仅体现于骚、散结合的《北征赋》,而且《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式的句子,也是《离骚》句式去掉“兮”字的结果。“从《二京赋》到《归田赋》,暗示了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递转,这一递转的意义就在于把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带入赋中,并由此开拓了赋的题材与意趣,从而有可能与辞人之赋构成某种张力,打破其创作上的固定思路与格局,刺激其再度发展。”*曹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载《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第45页。所以,看待这种递转,不能仅仅将目光集中在汉赋体制的变化,更要关注赋家日益浓重的主体意识。在由重功用转而重愉悦、由体国经业转而抒发穷愁的过程中,“丽则”说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跨过扬、马模式,将赋重新引回了诗骚传统,固持了赋体的文学艺术特性,是文学自觉主旋律的时代和弦。
美、刺是汉代诗学最为重视的两端,“丽则”说所指向的诗人之赋正是通过这两端表现出来,它的意义不仅吸引汉赋向美、刺靠近,而且指引着后世赋家超越了汉儒,转而注重诗之本义,创作旨归由教化转向抒情,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描绘转向内心表达。从创作实践看,由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蜕变,由辞人之赋到诗人之赋的转折,呼应了扬雄的“丽则”说,是创作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同时“丽则”说也对汉赋体制的固定与成熟发挥了正面作用。
●作者地址:车瑞,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Email:cherui1103@163.com。
刘冠君,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YJC751125)
●责任编辑:何坤翁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