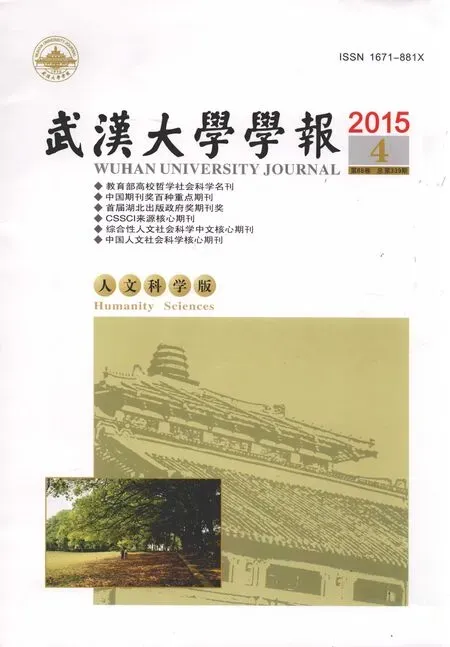从《溪山琴况》之“和”况探究二胡演奏的立美、审美活动
2015-02-23向清全
宋 晶 向清全
从《溪山琴况》之“和”况探究二胡演奏的立美、审美活动
宋晶向清全
摘要:中国古代七弦琴演奏及琴乐美学专著《溪山琴况》中提到“和”是古代琴乐重要的审美范畴。笔者在“和”这一审美范畴下,从音乐创作、表演、传播三个角度出发,探讨二胡演奏中真实与再创造、弦与指、指与韵、音与意之间的关系,从而丰富二胡演奏的立美、审美活动。
关键词:二胡; 《溪山琴况》; 立美; 审美
二胡由最初原型“奚琴”发展到现在已有千余年历史,是中国标志性的民族乐器。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大力挖掘民间艺人的艺术珍宝,使二胡演奏艺术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一批批二胡演奏家层出不穷,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经典的二胡音乐作品。
任何音乐作品都要经历创作、表演、欣赏三个过程,二胡音乐作品也不例外。“音乐表演是音乐存在的活化机制。无论在何种音乐行为方式中,音乐表演都使整个音乐处于激活状态……在记谱法产生之后,或者在一度、二度创作已分工明确的音乐活动中,音乐表演经常作为中介结构,在音乐活动诸环节中扮演着连结作品的创作与接受的重要角色。”*参见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397页。可见,记谱法产生之后,静态的二胡作品只是作曲家谱写在纸上的可视性音符,只有通过二胡演奏者进行二度创造,才能对可视性音符进行诠释,让欣赏者进行艺术鉴赏。二胡的演奏对于乐曲的诠释、解读起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探讨二胡演奏中所要达到的立美、审美追求十分必要。
“和”是中华文明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音乐最高的审美追求,即实现音乐美的前提是将对立的音与音之间相互调和统一,构成和谐的关系,使人在感官上达到音韵协调和畅的一种音乐美学思想。《溪山琴况》为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瀛所著,是一部系统论述七弦琴表演艺术理论和琴乐美学的专著。在该书中提出的24况中,“和”是重要的审美范畴,并在该范畴下探讨了“音”、“弦”、“指”、“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已具有琴乐演奏技艺美学的理论意义。由此可见,《溪山琴况》虽是论述七弦琴表演艺术理论和琴乐美学的专著,但其所蕴含的琴乐演奏的技艺美学和琴乐美学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器乐的演奏中的立美、审美活动。因此,笔者试图借鉴《溪山琴况》关于琴乐演奏中“和”的审美范畴,并结合演奏实践,探讨二胡演奏中的立美、审美追求。
一、 真实与再创造相“和”
《溪山琴况》对真实、再创造这两个概念虽无提及,但笔者认为它们对于二胡演奏十分重要。因此,这里试图在《溪山琴况》中重要审美范畴“和”的概念框架下探讨两者关系,以得出二胡演奏中所要遵循的真实与再创造相“和”的审美、立美原则。所谓真实与再创造相“和”,笔者主要是从乐谱和演奏者关系的角度进行阐释。真实是二胡演奏中“二度创作”的基础,是对二胡音乐作品本身的忠实再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把乐谱作为最基本的依据进行分析,同时还要了解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和创作背景,甚至是作者创作时的意识形态。以二胡曲《二泉映月》为例,如只根据曲名了解或只简单依据谱面所示意的东西进行诠释,就很容易把该曲误解为描绘无锡美景的音乐,带着这种思想情绪曲演奏该曲,无疑是对华彦钧(阿炳)先生创作意图的误读。由此,我们不但要对乐谱进行研读,还要了解创作此曲时,华彦钧(阿炳)先生食不果腹、穷困潦倒的生活背景,这样才能较为精确地把握住该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做到对作品意图的真实再现。然而,二胡演奏作为二度创造,演奏者若只有理智分析,对乐谱进行忠实显现,则显然不够。“作曲家写成的乐谱形式的作品虽然内涵着立美主体的审美情感、想象、体验,并将这些抽象为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但无论多详尽的乐谱,都无法非常精确地记录事物运动的内在精神,非常确切地体现人类感情运动的细致变化、以及感情性质与感情色彩的微妙差异,符号难以完全展现作曲家的生动的精神创造。”*参见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第397页。长期扎根民间,与民间艺人交流,我们会发现,在一次民俗活动中,大多数执乐者并不需要乐谱,甚至很多民间艺人并不识谱,但他们却能完整地演奏一首首乐曲。音乐旋律“活态的”存活在民间艺人脑中,采风工作者将他们所演奏的乐曲忠实地记录下来,形成可视性乐谱,而可视性乐谱虽能记录下每一个音符,却很难书写下连接音与音之间的细微情感。可见,对于民间乐曲的记录我们常常只关注到“标本式”乐谱的记录与保存,忽略了民间艺人们的情感与构曲思维,而构曲思维却是民间艺人能够演奏出千变万化的乐曲的关键。此外,二胡曲谱经一次次的流传,资深演奏家的修改,又可能使得曲谱本身的完善性和精确性有所降低。因此,乐谱呈现给我们的可能只是一个示意信的草图,但乐谱的存在又为演奏者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发挥的空间。
由于可视性乐谱有自身的特点和缺陷,二胡演奏中需要再创造成为必然。因此,再创造是决定二胡“二度创作”的价值的关键。“乐谱潜在的东西需要挖掘,无法记录的东西需要丰富,其结构的开放性质、未完成状态需要表演的再创造来完善,这些恰恰为表演的再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参见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第397页。要做到创作中不改变作曲者的意图,并且使作品得到升华,这就取决于演奏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刘天华所作的《良宵》(除夕小唱)为许多二胡演奏者所喜爱,笔者翻阅了刘天华女儿刘育和所著的《刘天华创作曲集》(2005年修订版)曲集发现,刘天华二胡曲《良宵》的谱例上并没有泛音的标记。多数谱例上在演奏提示中写到“如演奏两遍,则第一遍结尾速度不变,第二遍结尾时再渐慢,并可在末尾加一内弦泛音结束。”*参见杨长安:《二胡独奏曲精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可见,乐曲演奏的遍数以及结束的泛音可能是后人按照乐曲表现需要所加入的。但从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中来看,泛音是他并不排斥且较为推崇并想极力引进的一种演奏技法。所以笔者认为,泛音的加入并没有破坏刘天华这首乐曲的表达。它的加入更能表现人们经过一个欢乐的除夕,渐渐进入梦乡,笼罩在大雪中的整个世界又渐渐恢复平静的意境,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和回味,反而增强了乐曲的美感和结束感。这就是典型的表演艺术家用演奏技巧延展音乐表现力的表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胡的演奏中,在客观理性地研究作品的同时,表演者的演奏个性必须与创作者的创造个性相结合,对乐曲无法记录的内在精神情感进行深挖,在不改变创作者本义的同时发挥创造性,对作曲家的审美情感进行补充,做到真实与再创造相“和”。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演奏的艺术使命,揭示作品的内在魅力并使之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二、 弦指相“和”、指韵相“和”
弦指相“和”、指韵相“和”,是笔者借鉴《溪山琴况》之“和”况中所提到的——“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曰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琴乐演奏的两个审美命题“弦与指合”、“指与音合”,总结归纳而来。“弦与指合”是指要具备娴熟精湛的演奏技术。“所谓‘指与音合’,是指在掌握纯熟的指法技艺的基础上‘细辨其吟揉以叶之,绰注以适之,轻重缓急以节之,务令婉转成韵,曲得其情’。在奏乐的音乐中,是琴曲的演奏合乎音乐的章法、句度(‘篇中有度,句中有候,字中有肯’),由此产生悦耳而富于韵味的情感音调,达到指与音的相‘和’,这也是音乐演奏中技艺美的实现。”*参见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第157页。这两点侧重于解决演奏技术上的技艺美学问题,对于二胡演奏有着很大的启发性。
(一) 弦指相“和”
表演者的演奏技术是否娴熟,这一点至关重要。人是音乐行为的主体,演奏者通过对乐器的操作,将静态的乐谱转化成鲜活的音乐,赋予作品生命和活力,同时演奏者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生存魅力。二胡与多数乐器不同,没有固定音位和品位,所以对音准的把握十分严格。对音准的把握,需要内心听觉的培养,以及长期练习下手指对音位和把位的感知与掌控。如果将作品视为一个生命体,音准则是它的骨架。因此,我们只有做到琴音相“和”后,也就是准确的把握音准,才能去追求娴熟过硬的演奏技术。二胡演奏技巧中,揉弦较难把握但又必不可少。揉弦对美化音色、表达音乐情感以及表现演奏者的激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二胡曲《良宵》(除夕小唱)是二胡学习者练习揉弦的首选曲目。流畅自如的运弓、快慢适中的速度,描绘了一幅家家热闹欢腾、世界和谐美满的场景。弹性放松的揉弦更是锦上添花,含蓄地抒发了在艺术事业上得到支持的刘天华与学生们一同过除夕,甚至是全天下人欢度除夕的那种极富满足感的、激动不已的心情。《病中吟》更是运用了“吟”的揉弦手法表现对当时整个病态社会的哀叹,表达了作曲者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走投无路的悲叹。除此之外,颤音、顿弓、抛弓都是二胡表达音乐语言的重要手法。如《战马奔腾》中运用大跳弓模仿马蹄声,运用半音阶的模进来模仿马的嘶叫声。《光明行》尾声中颤弓的运用,颤弓本身所带来的震动感与层次感,高音区颤弓所产生的明亮辉煌感,力度的强弱感交织一起,与全曲尤其是第二乐章形成强烈的对比,情绪更加激昂,如沉睡已久的火山喷发一般,使得全曲生机勃勃,这样的点睛之笔就好似当时迷茫的人们最急需的那缕明亮辉煌的曙光。又如《第二二胡狂想曲》中运用滑音表现极富民族特色的湖南花鼓戏的韵味等等。
综上所述,琴音相“和”的基础上做到弦指相“和”是完成二胡演奏的必要前提,缺少这个前提整个二胡作品会淡然无味。但随着大量展现二胡技术性的现代作品的出现,二胡的演奏技术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有些演奏者过分追求技术,把炫耀技巧作为音乐表演的目的,演奏出来的音乐常常华而不实,缺乏艺术内涵。可见,技巧只是二胡表演必不可少的基础,它并不是音乐表现的全部内涵。因此,演奏者做到旋指相“和”的同时,需要把这些技术技巧完全融入音乐的表演中,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音乐才能使听者身临其境,感受音乐所要表达的情感。
(二) 指韵相“和”
指韵相“和”是笔者受《溪山琴况》之“和”况中“指与音合”的启发借鉴得来的。对于“指与音合”笔者已在上文中阐释,在此不予赘述。由于二胡为中国标志性的民族乐器,很多作品都是由姊妹艺术民歌、戏曲、说唱等作品演变而来,而这些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因此,指韵相“和”就是指,在弦指相“和”的基础上,二胡曲的演奏上合乎音乐作品的地方特色,达到指韵相“和”。
笔者上述提到的韵味,主要是指音乐的风格。演奏者对地方性音乐风格把握是否得当,是该作品在地方性“话语体系”中得到肯定的关键。因此,对韵味的把握在二胡演奏中不可缺少,这也是演奏者立美、审美的必要手段。二胡的作品属于器乐作品,有较多的二胡传统器乐作品来自于对民歌、戏曲、说唱等姊妹艺术的移植和改编。民歌、戏曲、说唱等艺术植根于中国广阔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歌种、剧种、曲种。这些艺术门类与地方语言密切相关,各地语言的调值走向、节奏韵律等对民歌、戏曲、说唱等艺术门类特定音乐形态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所以从语言中寻找韵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如要赋予《江南春色》、《河南小曲》、《兰花花叙事曲》等地方性色彩较强的二胡乐曲生活气息,演奏者首先要把握好乐曲的章法、句度。其次可以先身临其境感受一下江南、河南、陕北等地方的生活环境。最后,演奏者可以试图模仿江南方言、河南方言、陕北方言,并把这种对环境的感受和语言的品味以及地方音乐的特征带进二胡演奏之中。这时演奏者可以发现,一个地方的语言,对于表现一个地方音乐韵味起着重要的作用,音乐韵味的把握也是正确表现地域风格特征的重要手段。
因此,要使一首二胡曲具有基本的美感,旋指相“和”必不可少,如再对韵味把握得当,做到指韵相“和”,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就不会干瘪、怪诞,甚至脱离本地或本民族音乐的特点,这样的二胡作品富有生命力,其渲染力也将大幅提升。
三、 音意相“和”
“所谓‘音与意合’,是琴乐演奏最终要达到的审美境界。作为更进一层的审美要求,《琴况》并未停留在单纯的演奏技艺所能达到的‘曲得其情’层次上,而是追求着‘音与意合’的审美境界,提出了‘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即以演奏技艺达到精妙细微的乐音表现,来触及人内心深处最敏锐幽深的心理体验,这是从单纯的乐音运动形式中难以领会到的。”*参见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第158页。
可见,《溪山琴况》中所提到的“音与意合”,主要是在“和”的审美范畴下,探讨音乐表现与审美体验中的情感意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做到音、意相“和”,才是二胡演奏所要达到的最高审美境界。“意”可以理解为意境,它是我国传统音乐演奏中十分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意境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创作者内心的‘意’造成了一种意境空间,这种‘意’包含了创作者的人生体悟和社会思考,统领了整个曲子的基调,也使整个曲子变成了创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参见许多军:《二胡演奏中的氛围营造和意境美》,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2月第27卷第4期,第179页。如二胡曲《江南春色》中的引子,用泛音“描写”了雨后江南,春回大地,万物争妍的场景,创作者营造了一种静中有动、虚中有实的音乐意境,从而表达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而演奏者在演奏中则要把这种意境传递给听众,使之产生共鸣。由此可见,二胡作品中的情感意境是由创作者所赋予,再由演奏者传达,最后由观众接收的,立美、审美活动贯穿于创作者、演奏者、观众三种不同的参与角色之中。创作者是作品情感意境的构造者,而演奏者则是这种意境的挖掘者和中介者,把所体会到的意境传递给听众,使听众在听曲时也会感受到、并在头脑中建构一个意境。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某些景象所触动,将自己的感情融入进作品。
演奏者如何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意境忠实地表达出来?笔者认为,演奏者首先应将自己放置于创作者的文化背景之中,进行想象与体验。观众在接受音乐作品的之前,应通过各种的途径(如作品的标题、节目单中对作品的介绍、演出前舞台灯光布置等等)对音乐作品做简单了解,使作品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情感基调在大脑中产生一个基本的“轮廓”。但由于作品的标题、节目单中对作品的介绍等只是一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音乐作品的全部内涵。因此,演奏者的演奏应顺应审美体验中的情感意境,通过音响动态触动观众,让观众通过所感受到的音乐进一步“勾画”心中的意境。所以演奏者的技术是否精湛、娴熟十分关键,一个轻柔的滑音、微小的颤音或是几秒钟的气口、短暂的停顿,在这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见,一切优秀的音乐作品离不开创作者主观意境、感情的孕育,离不开演奏者对创作者主观意境、情感意境的诠释,同样也离不开听众的对情感意境的接收与反馈。所以,二胡演奏者“故欲用其意,必先练其音;练其音,而后能洽其意”。也就是说,要首先解决技术层面的立美、审美弦指相“和”、指韵相“和”,最终要用心灵去感悟和体会乐曲内在所蕴含的意境以及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感意境,并把娴熟的技术技巧与这种情感意境相互融合,“音从意转,意先乎音,音随乎意,将众妙归焉。”做到音意相“和”,使听者与创造者产生心灵对话,这才是二胡演奏最终要达到的审美境界。
四、 结语
明末虞山派著名琴家徐上瀛所著《溪山琴况》中所探究的琴乐演奏美学,对二胡以至于其他器乐演奏的立美、审美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古琴为弹弦乐器,二胡则为拉弦乐器,虽两者演奏手法不同,但在中华文明背景下长期“生存”的两件乐器,他们的审美旨趣却“不谋而合”。因此,在《溪山琴况》中所提到“和”的审美范畴下,探究二胡演奏的技艺美学与琴乐的审美美学十分必要。
一部音乐作品,要经过音乐创作、演奏、传播三个过程,这三个过程被称为“一度创作”、“二度创作”、“三度创作”,当然不同主体(创作者、演奏者、欣赏者)的立美、审美活动始终贯穿在这三个过程当中。演奏者作为“二度创作”者,三个过程中重要的中间环节,是赋予音乐作品鲜活生命力的关键。因此,演奏者在演奏中如何处理好与创作者、欣赏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由此,笔者认为,在处理二胡演奏者与作品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上,要遵循真实与再创造相“和”;在提高二胡演奏者自身演奏技艺美学素养上,应做到琴音相“和”、弦指相“和”、指韵相“和”;而在调和创作者、演奏者、欣赏者三者关系上,则要达到音意相“和”。
●作者地址:宋晶,湖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Email:231973088@qq.com。
向清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京,100101。
●基金项目:湖北师范学院校级项目(XJ201316)
●责任编辑:刘金波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Erhu Performance by Studying
the ClassicXishanWorksofQin
SongJing(Music College,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XiangQingquan(Music Department, China Conservatory)
Abstract:As an academic monograp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tring instruments,Xishan Works of Qin proposed that “harmony” is significant in aesthetic scope.Under the assumption,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reality and creation,the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melody,the playing skill and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from three different angles which were musical creation,musical performance and music spreading.
Key words:erhu; Xishan Works of Qin; Aesthetic Activities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