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与文士的重“笔”观念
2015-02-22胡政
胡 政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东魏北齐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与文士的重“笔”观念
胡 政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东魏北齐时期,随着南风的不断北传,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不少关于文笔问题的争论。总体而言,尽管不断“文”化,东魏北齐文士们普遍具有重“笔”的文学观念,他们也多从事军国文翰和实用文章的写作,注重在该类文章的创作中展示才情。这种文学观念的出现,既深受当时北方传统地域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影响,也与高氏统治者本身的文化文学素养、崇尚实际的政治理念和取士制度等紧密相关。
东魏北齐;文笔;崇实;高氏统治者
文笔之辨是南北朝时期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它涉及到对文学本质功能和范围的认识问题,南朝文人对其讨论颇多。文笔的内涵,虽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基本意义大致如下:“文”主指注重辞采的性情之作、有韵之文,“笔”主指军国文翰、碑志书记等实用性文章,多不重押韵或声律。在北朝,自十六国以后一直有重“笔”的传统。但自北魏孝文帝时代以后,随着汉族士族政治地位的提升和文化环境的宽松,文学领域的“南朝化”倾向明显。至东魏北齐时期,在文学方面,高氏统治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偏于实用,表现为文人注重章表碑志等“笔”类实用文章的写作;一是偏于“浮华”,表现为北方文人和入北的南方文人对南方文风的继承,注重“文”的创作。具有这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文人之间时有争论,表现为文笔之争。而其主要倾向,依然是注重“笔”类文章的写作。东魏北齐时期出现的这种文笔之争,是南北文风交融的体现。重“笔”的倾向,既与北方传统的地域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紧密相关,也与当时高氏统治者的文化取向和文学态度紧密相关,对此尚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东魏北齐时期的文笔之争与普遍重“笔”的文学观念
东魏北齐时期,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关于文笔方面的争论。《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载:
(魏)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邵)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其中的“唯以章表碑志自许”一句,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太平御览》卷五七八引《三国典略》作“唯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校勘记》中解释说:“按如此传,则是章表碑志之外,连作赋也同儿戏,和上文‘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之语矛盾。疑《御览》是,这里衍‘外更’二字。”[1]498-499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中也指出:“所校是。魏收这一番话意在贬抑温、邢,若据《北齐书》则文义难通。”[2]390从上下文看,确是如此。表面上,魏收的这段话中体现了他的一个文学观点,即重视“赋”这种文学性较强的“文”体,而认为章表碑志之类的“笔”类实用文章等同于“儿戏”。这种观点看似与南朝后期重文轻笔的文学观念极为相似,实则不然。魏收此言,本出于文人相轻的意气,他的真实观点并非如此。《北齐书》本传中还载有一段有名的文笔之争的事迹: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
魏收本以学当时以“笔”闻名的任昉著名,且有其朋党闻名邺下,何敢轻视此类文章?从魏收的生平事迹看,他的章表之作很多。《北齐书》本传中还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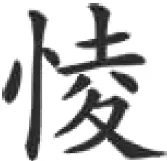
可见,自北魏后期至东魏北齐时期,魏收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军国文翰的写作,魏收的“敏速”且“工”的文才正是体现在这些文章的写作之中。对“笔”,他不能不加以重视,很难仅以“儿戏”的态度待之。细读一下,我们对魏收这段话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事实上,他并不认为“章表”为“儿戏”之作,而是“唯以章表自许”才是“儿戏”。他不反对以“章表自许”,只是不要“唯以章自许”;“章表”之作非“儿戏”,而仅仅注重或擅长于“笔”类文章的写作才是“儿戏”。他的文学主张,准确来说,应该是重“笔”之外又要重“文”。
除了魏收的这段话之外,当时的文笔之争还有多处表现,如:“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诏(李)浑与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3]1206《封子绘墓志》中评价封子绘:“加以纲罗百氏,综涉六经,雅练朝章,尤悉治典。激察之行,每有耻而弗为;雕虫小技,固壮夫之所忽。”[4]424以军国文翰见长的文士孙搴也有类似的表述:“搴学浅而行薄,邢邵尝谓之曰:‘更须读书。’搴曰:‘我精骑三千,足敌君羸卒数万。’”[1]342《颜氏家训》中记载文笔之争处颇多:《文章篇》记载颜之推的观点:“夫文章者……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同篇还载一事:“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翫,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又,《勉学篇》:“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悠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5] 237、265、167
综上所引材料可见,东魏北齐时期,关于文笔问题的讨论是比较多的,而一个基本的倾向是重“笔”,更有甚者贬低“文”类文章为“雕虫小技”、“须臾之翫”和“羸卒”,而将“笔”类文章提升到较高的地位。其中,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颜之推也表现出明显的重“笔”的倾向,“至于”一词和“行有余力,则可习之”一句足见其态度。更多士人甚至“武人俗吏”则是从“施用”的角度来看待文笔问题的。而即使重“文”者如刘逖、魏收,也不能忽视“笔”之功用,更倾向于主张二者的融合,由此也可见当时南北文学风气的不同。
事实上,在整个东魏北齐时期,很多文人的一项基本内工作就是从事实用文章、特别是军国文翰的写作。《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中列举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人:
有齐自霸图云启,广延髦俊,开四门以纳之,举八纮以掩之,邺京之下,烟霏雾集,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清河崔长儒、河间邢子明、范阳祖孝徵、乐安孙彦举、中山杜辅玄、北平阳子烈并其流也。复有范阳祖鸿勋亦参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陆卬、崔瞻、陆元规并在中书,参掌纶诰。其李广、樊逊、李德林、卢询祖、卢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独擅其美。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刘逖、魏骞亦参知诏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诏旨,其关涉军国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逊、李德林、薛道衡为中书侍郎,诸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俱是德林之笔,道衡诸人皆不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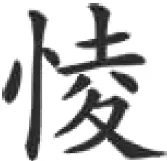
(陈元康)(天平)二年,迁司徒府记室参军,尤为府公高昂所信。……高祖闻而征焉。稍被任使,以为相府功曹参军,内掌机密。高祖经纶大业,军务烦广,元康承受意旨,甚济速用。
(赵彦深)子如言于神武,征补大丞相功曹参军,专掌机密,文翰多出其手,称为敏给。
(崔季舒)长于尺牍,有当世才具。(杨愔)朝章国命,一人而已。(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李绘)素长笔札,尤能传受,缉缀词议,简举可观。(张亮)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
另,《北史》卷四七《阳尼传附阳昭、阳静立传》记载:
(阳昭)学涉史传,尤闲案牍。为齐文襄府墨曹参军,甚见亲委,与陈元康、崔暹等参谋机密。(阳)静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词令,善尺牍。
《魏故司空公张君墓志》记载:
(张满)转仪同开府中兵参军,掌管记。文同宿构,辞并立成。[4]324
由此可见,东魏北齐时期,包括“北地三才”和阳休之、卢思道、薛道衡、李德林在内的有名文士和陈元康、祖珽、崔季舒、杨愔、赵彦深等能够受到统治阶层重用的汉族士人皆长于“笔”的写作,这说明当时的文学领域中确实存在着一股重实用文章的风气。《颜氏家训·教子》中还记载了北齐的一个士大夫教授儿子书疏、鲜卑语和弹琵琶。他教授后两样是为了“伏事公卿”[5]21,而教授书疏则显然是因为受到了当时这种重“笔”风气的影响。
东魏北齐时期文人重“笔”的观念还表现在他们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很注重对其进行文学性修饰和描写。上文所引《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中载崔因为作文“率直”而遭到魏收的嗤笑,说明至少北魏末年开始北朝文人就已经较为注重在公文中展示文采了。至东魏北齐时期,在齐梁文风的影响下,文士们更加重视对南朝文学技术的学习和模仿,在“笔”类文体的写作上也是如此,魏收与其同道即是如此。此外,北人学习徐陵的作品也极为重视其“笔”。尹义尚《与徐仆射书》:“如军书愈疾之制,碑文妙绝之词,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6] 96-97从“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两句中我们不难体会东魏北齐文人普遍对于南方“笔”类文章的重视和热情。
东魏北齐文人们还将“笔”类文章作为展示自己文学水平的一个重要载体。如:
(杨)遵彦即命德林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大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卬。卬云:“已大见其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制作,乃涓浍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与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师此人,以为模楷。”[7]1194
北齐时期亦有宴会上作实用文章者:
李祖勋尝宴文士,显祖使小黄门敕祖勋曰:“茹茹既破,何故无贺表?”使者伫立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1]320-321
显然,当时文人已经将实用文翰和诗赋一样当作展示自己的文才的载体,“以为模楷”尤可见时人对“笔”类文章的重视。事实上,他们这类文章在东魏北齐时期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受到南人的重视和赞赏。《朝野佥载》卷六载: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8]140
又,《酉阳杂俎》卷一二《语资》中载庾信语:
我江南才士,今日亦无。举世所推如温子升独擅邺下,尝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进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9]112
二、高氏统治者之于重“笔”文学观念的影响
影响东魏北齐时期重“笔”观念的因素很多,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因素:高欢及其后辈们代表的政治权力之于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
与北魏后期的统治者相比,高欢及其子孙的汉文化、文学素养较低。《北齐书》中称高欢是河北大族渤海高氏之后,即便如此,从其祖父以来已经三代居于怀朔,“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成为自北魏迁洛开始就逐渐被边缘化的居于北镇的胡人和胡化汉人的利益代表。从《北齐书》中《神武纪》、《外戚传》和《儒林传》中的记载看,在文化素养方面,他们真心喜欢的是胡族文化,特别是胡乐,而其自身的汉文化素养并不高。在汉文化教育方面,高欢、高澄等也注意选择汉族名儒教育子弟,但效果不佳,“徒有师傅之资,终无琢磨之实”[1]582。在汉文学素养方面,高氏统治集团成员也整体较低。政权统治者中唯后主高纬以好讽咏著称,但并无作品存世,且他对于文学的兴趣远远不及对胡乐的兴趣大。高氏子弟和外戚中,汉文化和文学素养较高的主要是高澄诸子,如高孝瑜和高孝珩,高延宗现存诗一首《经墓兴感诗》。其余诸人则多粗武淫虐之徒。
高氏诸人的汉文化和文学素养不高,汉化程度较低,这也是东魏北齐时期胡汉冲突的根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更加注重的是汉文化和文学的实用性,而对“浮夸”的清谈风气和齐梁文风并不欣赏。《北齐书》中称高欢“雅尚俭素”、“不尚绮靡”,高洋在天保元年下《正风俗诏》也提倡“反朴还淳”而不满“浮竞”、“奇”、“丽”之风[1]24、25。这些说明高演以前的统治者多崇尚简单实用而不欣赏“绮靡”、“浮竞”的趣味。他们的这种好尚也体现在文学方面,如高演读书喜欢“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1]79,高洋不满王昕的“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3]884并最终杀之。他们的这种好尚对南朝文风的传播有很大的不利影响,而对促进东魏北齐文人大量从事“笔”类实用文章和崇实的文风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东魏北齐时期重“笔”的文学观念,还与高欢、高澄、高洋、高演等人注重实务、重吏事有很大关系。从东、西分裂开始,高氏政权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从外部看,宇文氏政权一直是高氏的最大威胁,萧梁在灭亡前也与高氏政权有所摩擦;从内部看,胡汉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故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所看重者主要有二:一是武功武略,一是吏干能力。高氏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如高欢、高澄、高洋、高浚、高涣、高琛、高思宗等皆长于武功。高演以前的统治者皆长于吏事。如《北齐书》卷五十《恩倖传》云:“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贞干之臣。”《北齐书》卷四《文宣纪》中记载,高洋“雅好吏事,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北齐书》卷五《孝昭纪》中载高演“善断割,长于文理。长于政术,剖断咸尽其理,文宣叹重之。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即位之后依然如此,以致厍狄显安对他有“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的评价。《北齐书》卷四二《阳休之传》中也记载了高演向阳休之求治道的事情:“肃宗留心政道,每访休之治术。休之答以明赏罚,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为政治之先。帝深纳之。”对于高氏子弟,高洋等人也重视对其进行吏干教育。如“文法吏”宋钦道被高洋“令在东宫教太子吏事”[3]939,高润、高叡等人也皆长于吏干。
作为政权的统治者,高氏对实务能力的重视必然体现在他们对汉族士人的选择上,体现在他们的取士制度之中。
北方大族本就有重视实干的传统。“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废世务”[5]315、356实是北方大族士人的共识。东魏北齐统治者本身对于实际的世务能力也极为注重,他们对士人有同样的要求。当时的取士制度基本是门阀和才干兼重,而更为统治者注重的显然是才干。在统治集团的影响和导引下,当时士人多有实干能力,以吏干知名的士人还有很多,如阳休之、刘子翊、源师、源彪、李稚廉、封述、封询、许惇、宋世良、郎基、郎茂、崔伯谦、宋钦道、房恭懿、房彦谦、郑子翻、李朗、崔子枢、高构、李浑等。而不长于实干者则往往不受统治者重用,甚至被责罚或被杀。如《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中记载:“(刘昼)在皇建、大宁之朝,又频上书,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终不见收采。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而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进。” 又如,高洋之所以杀掉王昕,不仅仅因为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还因为他“疏诞,非济世才”[3]884。司马膺之也因为“疏简傲物”而“竟天保世,沦滞不齿”[1]241。《北齐书》卷三十一《王昕传附王晞传》:“时二人(裴泽、蔡晖)奏车驾北征后,人言阳休之、王晞数与诸人游宴,不以公事在怀。(孝昭)帝杖休之、晞胫各四十。”就连风流名士也不能“诗意地栖居”,而是要注重世务。《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记载:“(裴)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自北魏后期以来,河东裴氏多风流人物,如裴粲、裴伯茂等。裴让之本人也以风流知名:“与杨愔友善,相遇则清谈竟日。愔每云:‘此人风流警拔,裴文季为不亡矣。’”[1]465因此裴让之的话典型地说明“留情世事”已经成了当时一些士人自觉的选择。当时还有人以吏干自许、以吏干求誉,从中也可见当时风气。如源师“明辩有识悟,尤以吏事自许”[3]1032,李蔚“昆季并尚风流,长裾广袖,从容甚美,然颇涉疏放。唯蔚能自持公干理,甚有时誉”[3]1605-1606。这一时期的很多士人,如陈元康、崔季舒、崔暹、杨愔、赵彦深、祖珽等,也确实表现出很强的实干能力。尤其是杨愔和祖珽,北齐时期对稳定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士人中的一部分即为文人,他们自然也深受政治权力的导向和影响。上述长于吏干者中就多有文人。高氏所选用的文士也多从事“笔”类文章的写作工作。此外,高氏对长于“笔”类文章的文人的重视还有很多表现。如《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谈薮》: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10]1281
高欢竟然将历来文人不齿与之并列的“刀笔吏”比之为孔子,可见他对这类文人的重视到了何种地步。当然,据《北齐书》卷二四《陈元康传》,陈元康对于高氏政权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文书工作,还在于他的有辅政的实际才干。《北齐书》同卷《杜弼传》中记载,高欢不满杜弼对窦泰没有尽到劝谏之责,杜弼回答说:“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高欢听后“益怒”,也可见高氏统治者对于“刀笔吏”们的重视。又如孙搴:
会高祖西讨,登风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请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1]341
祖珽甚至还因“笔”才免罪:
未及科,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散参相府。[1]515
高澄也看重这类文人。侯景叛乱后,高澄看到侯景的报书,“问谁为作。或曰:‘其行台郎王伟。’王曰:‘伟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1]36这件事情和后来武则天读到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而感叹宰相失人比较类似。
综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高氏统治者的文化文学素养、崇实的政治态度和取士制度对于推动东魏北齐时期文人重视“笔”类文章写作的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5]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3.
[6] (清)严可均.全北齐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唐)魏征,令狐德棻等[M].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 (唐)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责任编辑:石长平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he Rulers and Practical Concept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HU Z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with the continuous spreading of southern style to the north, many arguments about writing appeared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Overall, despite the continuous culture turning, scholars generally had practical literary concept. They also engaged in militarism Wenhan and practical article writing, focusing on display talent in the creation of such articles. This literary concep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nd literary in the North at that time and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Gao rulers’ cultural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dvocating practical things and system of selecting scholars.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writing; advocating practical things; Gao rulers
2014-09-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朝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进程的历史解读”(11CZW027)。
胡政(1978—),男,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I206
A
1671-9824(2015)04-006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