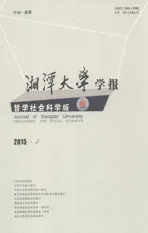哈耶克法治主义自由观的认识进路*
2015-02-22李建华牛磊
李建华,牛磊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哈耶克法治主义自由观的认识进路*
李建华,牛磊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哈耶克的自由秩序理论体系经过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积极自由概念的确立更是使其理念无限趋近于洛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自由”的自由主义观点。哈耶克法治主义自由观的认识进路中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法律之治是法律的基本属性;其次,法治的根本原则乃是普遍利益;最后,形式合法则是法治当前的最大危险。
关键词:哈耶克;积极自由;法律之治;普遍利益;形式合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2014年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将法治作为全会唯一的研究主题,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如何将法治不断引向深入的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社会的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要勇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全世界古往今来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实施有益的拿来主义,才能够更好地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我们认为,在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与法治理念的发展脉络中,英国思想家哈耶克将法治与自由相结合的法治主义自由观在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借鉴。当然,我们在借鉴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并保持高度警惕。
在哈耶克的自由秩序理论体系中,如果说自由是该秩序的正当性前提与追求的目标,平等是自由秩序的合法性基础,那么法治便是自由秩序的重要保障机制。诚如哈耶克所论及的那样,民主政治绝不是无限的政府。民主政府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对个人自由加以切实的保障。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大多数个体的理性水平与社会认知程度相较于少数精英而言往往差一些,他们最为看重也最容易被吸引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或者是情绪激昂的民族情感。这两个方面也是最容易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进而使得民主的决策结果偏离民主机制建立的初衷。要使得民主走出放纵的泥沼,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言找到恰当的“中点”,法治的方式恐怕是目前较好的一个选择。
一、法律至上:哈耶克自由思想的渊源
当历史从古罗马共和国法治到罗马帝国再到欧洲中世纪时,由于官员权限的逐渐不受控制以及民众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民众开始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开始追求权利的意识不断觉醒,并从自发逐渐转向自觉的斗争。或许正是基于此,哈耶克论述到,个人自由最初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尤其是在英国。按照美国学者伯尔曼的总结,[1]48英国的法律至上的自由传统起源于广大民众自《自由大宪章》签署之后形成的法治理念,即法律如果不植根于社会,只会变得机械而又专横。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正是由于英国较多地保留了中世纪普遍盛行的有关法律至上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其他地方或国家则因君主专制主义的兴起而遭到了摧毁——英国才得以开创自由的现代法治进程。
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英国的中世纪发展历程至少告诉了世人两个层面的观点:第一,在中世纪国王并没有权力去创制或者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废除或者违反法律,国王能做的是宣布或者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者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现存法律的种种滥用。而市民、骑士和贵族组成的国会的职能也是根据自身的理性与掌握的知识,来判定国王提出的法令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也并非是去创造法律。第二,英国国会制度的建立与长期推行逐渐引发了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守夜人政府即有限政府的概念,从而避免了英国类似于法国和德国走向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之路。直到1640年在议会停开多年之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从而引发了英国长达四十多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英国议会的长远和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革命之前的维多利亚专制时代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在革命之后依然得到了整体性的存在并作为英国君主立宪的主体保持到现在。
洛克所著的《政府论》对于英国的法律至上理念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哈耶克认为,洛克在其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所关注的虽说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目的这类问题,然而他所关注的实质问题却是权力,即不论是谁在实施这样的权力,如何才能够避免堕落成专断的权力,等等。与其他人不同,洛克不承认任何主权者的权力。在洛克看来,如果我们把主权交给一个人,那么这就是君主制;在他死后把主权交给他的子嗣或者选定的继承人,这就是君主世袭制。如果把主权交给少数选出来的人和他们的子嗣或者继承人,那么这就是寡头政体。[2]117不管将主权交给谁,都将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专断性权力的滋生。即使是将主权交给人民所掌管的议会,也需要将主权进行有效地分割,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加以分立和互相监督,才能够有效保证原本保障全体民众自由的制度不会因短视、狂热或其他的因素而成为堕落的专制权力。因为一旦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三种权力中的任何两个加以勾结,那么这个社会的统治就不会再是法律的统治而是赤裸裸的人的统治,这就违背了洛克所倡导的“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的观点。一百多年后,大卫·休谟在他所著的《英国史》一书中,再次总结了英国的“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当时在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政府,或在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的政府,都是与某种专断权力相伴随存在的,而这些权力则掌握在某些行政官员手中。因此,在此之前,人们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如果不采用其他手段而只凭一般性及刚性的法律和衡平原则,能否达到那种完美的境况。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至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种权力去摧毁自由。结果,在废除星座法院这一事件中,议会发现,严格遵循法律的原则虽会导致某些不便,但是因捍卫此原则所获裨益足以超过那些微小的不便。据此,英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他们的先辈,牢记他们的成就,因为是他们历经无数次的抗争后,最终确立起了这一崇高的原则。
与人治相比,法治显然对于平等和自由的保护能起到更好的作用。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社会的群居生活与动物相比,遵循着某些规则去行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这些规则逐渐从无意识的习惯发展为较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又从清楚明确的陈述发展成为更加一般性的陈述。这个自生自发状态下发展而来的一般性陈述,也即是一般性的行为规则。[3]184而这个规则的基础便是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人的统治相比,法律的统治显然更为确当。第一,一切机构和官员的任务便是解释和监督法律的执行。第二,规则的另外一层属性便是“一般性”;换言之,规则只能够关注所有人的行为的规范与平等自由的实现,而不能着眼于特殊群体乃至个体。第三,仅仅具有形式合法性,而缺乏应有的实质合法性则是当前法治最大的缺陷,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何谓法治。
二、法律之治:法治的基本属性
法治首先是法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法治的首要观点,亦是法治的基本属性。不过这里面似乎仍然有一些问题并非讨论得很清楚,比如何谓法律。在当代世界的民主政治中,法律被定义为立法机构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通过的规范和限制个体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对于这个定义中的缺陷我们已经很清楚。多数同意下通过的一般性行为规则即法律是否就构成了让少数强制性遵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反之如果这样的法律与少数个体的利益是不一致或是相冲突的,那么这样的法律之下的统治便不能够称之为法治,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之一。因此少数服从多数的立法原则应该是有界限而非是无限制的,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立法的范围界定问题。按照汉密尔顿在对美国的宪政体制向纽约州人们进行解释的时候所谈论的观点,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不仅是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保护一部分社会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在不同阶级的公民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而要解决少数个体利益无法得到公平保护的问题,汉密尔顿给出的解决办法之一便是“不受多数人约束,也就是不受社会本身约束的团体中形成一中意愿”。[4]266如果套用哈耶克的观点,便是法律的设立与颁布实施的正当性来源并非是多数个体的意愿,而必须是所有个体必须共同遵循的某些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甚至是高于一般性的法律。
其次,这些法律的制定与讨论的过程中,广大民众的角色究竟是积极参与还是简单地进行投票选择。如果只是后者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这些法律不是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御民之术,而这显然已经远远偏离了法治的轨道了。我们发现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中国抑或是西方国家,统治者以人民的名义颁布实施的法律在实质上变成了限制人民自由的一个利器。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如果民众不能够参与法律的制定与讨论,那么民众就感觉不到这是他们的法律,而仅仅是统治者的法律。不过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在一些实际情况中,由于立法活动的专业性质,很多法律往往并非是民众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甚至并非是整个立法机构的决定,而仅仅是立法机构的某个相关组成部分的成员的意愿和专业知识的表达。这种情况下所颁布实施的法律显然并不能够代表整个立法机构的意愿,更遑论全体民众的利益诉求。这种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趋势和不良倾向也是需要我们去加以关注的。
最后,法律自身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本身所要遵循的原则问题。按照19世纪法学家萨维尼的理论,法律实施是否能够充分保障和实现自由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最主要原则。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获得一个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的界限,然而此种界限的确立又须依凭某种规则,而这种规则便是法律。如果按照哈耶克所批判的“极端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人民的幸福应当是最高的法律”。从表面上看,该观点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但其真正要表达的乃是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法律制定的最高标准。换言之,应该是一种普遍意义上而非特殊意义上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法律并非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在长久以来的发展和探索过程中逐渐发现和确立的,因此法律自身的合法性来源应当是正式的法律出现之前、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自然法和习惯法等。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说,这些法律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无人知晓他们出现于何时。[5]8在这种法律秩序中,法律不是中央机构自觉、不断地进行制定和修改的事物,也可能偶有立法,但是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社群的行为模式和规范、社会习俗及道德观念发展而来。而且,在这种法律秩序中,习惯法无须由法学家进行自觉、系统、持续不断地理性审视。对习惯法的尊重完全不存在异议。我们认为,之所以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中央立法机构对习惯法的尊重“不容置疑”,更关键的地方在于人类本身并不能够创设或者建构法律,而是在长期的发展和试错过程中逐步“发现”的,再加之长期的实践和检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普遍利益:法治的根本原则
如前文所述,民主体制之下少数服从多数制定与颁布法律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范围同样不是无限的。民主下的法治的界限便是法律对普遍利益而非特殊利益的关注。反之,如果法治关注的是特殊利益,那么不但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会致使法治沦为多数个体强制少数以维护其利益诉求甚至是少数个体企图达成垄断目的而搪塞公众的挡箭牌。基于此,我们认为普遍利益不但是法治的根本原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制的有限政府的重要因素。诚如哈耶克所论及的那样,宪政意指有限政府。但是,对于宪政的诸项传统论式所做的解释,却使人们有可能把这些宪政论式与一种民主观调和起来。依照这种民主观,宪政乃是指一种多数意志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有不受限制的政府形式,一种使全知全能的政府成为可能的宪法究竟还具有什么作用呢?难迫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运转而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由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论调始终是否定性意义基础上的,因此对于法治和宪政的理解同样是出于否定性的价值层面。他所发出的连续性疑问其实是指出了当前人们对于法治根本原则的含糊不清甚至是有意无意地误解,不再将政府关注普遍利益、制定一般性行为规则当做法治的合法性来源。如果从现实层面分析,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经引起很多不同解读的开篇语或许能够给我们当下的混乱做一个注解:所谓法律指的是“由事物本性产生的各种必然联系”。萨拜因对此分析道,孟德斯鸠这一笼而统之的论式涵括了他一直未能澄清的含糊不清之点。在物理学中,一种“必然关系”只是诸多物体行为的一致性。在社会学中,法是理应得到遵守但却常常被人违反的人之行为的规则或者规范。[6]208可见,法治的存在,既说明了人类行为规则经常遭受违背的尴尬现实,更表明了通过法治的形式来让全体公民遵循法律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法治的话,人类的正当行为规则有沦为形式主义的危险,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相不干预对方自由的情形也将不复存在。
毋庸置疑,要实现自生自发秩序,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所有个体都必须无条件遵循的正当行为准则指导下的法律与法治就必须始终关注所有个体而非部分个体的自由,才能够避免法治的权力与机制的设置不会沦为专断性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哈耶克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下对于普遍利益或者共同利益的理解一直处于不明确的状态,甚至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当前,很多个体对于普遍利益的理解便是所有个体利益总和。哈耶克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普遍利益不可能是所有个体凌乱而独特的利益的总和。哈耶克的这一观点与卢梭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认为民主体制所要保障和实现的是公益而非众意。他认为公益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是以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为依归;众意则是所有公民个体利益的简单之和,往往着眼于私人利益。公益与众意的从属关系乃是当所有个体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除外,众意剩下的部分便是公益。[7]35不过,哈耶克与卢梭的公益论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对于究竟何谓公共利益,卢梭的观点接近唯理主义的特点,强调人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与辨别众意与公益的区别以及相互间的换算关系,尤其是如何实现公益。但是哈耶克的普遍利益论却是基于否定性自由和自生自发秩序的基础上,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知道什么是普遍利益,“道理很简单,因为作为决定因素的哪些情势,绝不是政府或任何其他人所可能完全知道的”[8]2。其次,尽管卢梭和哈耶克对于公民个体都并非是绝对的信任,但是出发点却是不同的。卢梭认为公益达成需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民之间彼此不能够有任何形式的勾结,这样才能够在彼此的特定利益之间寻找到公益的支点。但是如果一旦公民之间出现了勾结,那么派别的出现不可避免,某个或者某些派别通过一些手段将本集团的利益变成了公益,但是该集团利益相对个体而言固然是公益,可是相对于全体民众而言无疑又是众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尽管伴随着民众的勾结,众意最终达成公益的分歧减少了,但是可能达成的最终结果却是更加偏离了公益本身。与卢梭的反派别论相比,哈耶克之所以对民众的信任是有限的,乃是因为所有个体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他们并不能够完全清醒的知道自己利益诉求的全部内容。但是哈耶克接着说道,正是对于未来结果的无知,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就那些作为实现多种目的之共同工具的规则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哈耶克还分析了普遍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只要集体利益中集体的数量小于社会所有的个体之和,那么这种集体利益同样不能够等同于共同利益或者普遍利益。换言之,该语境下的集体利益其实就是特殊利益的另一个形式而已。对于集体利益的满足其实是对普遍利益的破坏。在现实实践中,其实立法机构通过的任何普遍意义上的行为规则都不可能真正让所有人都受益。因此,只有当不同的集体利益达成一种平衡,才是真正普遍利益的实现。
四、形式合法:法治的最大危险
在当前国际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浪潮的汹涌之下,绝大多数国家先后通过革命或者改革的方式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或者至少从形式上建立了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权形式。不管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抑或是英国式的议会主权制度,无不高举主权在民的大旗,倡导民主选举与多数决策的模式,宣称以法律作为行政行为的唯一原则和指导方针。
不过,通过对上述几种形式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法治的理念与实践在相当多国家中的实施中仅仅是完成了第一个层面即形式合法的论证与建构,而对实质合法或者程序合法性的建设显得踯躅不前或者苍白无力。所谓形式合法,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权组织或者权力运行模式在形式上符合了法治的要求,通过一系列的宪法和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宣称该国家已经实现了宪政的阶段和执政模式。殊不知,仅仅依靠形式合法性其实是当前法治建设中的最大危险。借用哈耶克的观点,二战结束之后,17、18世纪以来兴起的消极国家形式即守夜人政府的理念伴随着政府职能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则是积极国家的形式,即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强制力的主要功能已经不再是限制和束缚个体的自由实现,而是个体自由赖以实现的重要制度保证。此外,原本在自生自发秩序中处于独立地位、承担着率先“发现”认知社会的创新能力并带领其他个体一同走向自由和幸福生活重任的思想和意见领袖大部分却被政府雇用,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府按照自身意愿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建构相关制度的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以民众为主导的选举和投票制度是否依然能够真正表达和反映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比较悲观的情况是民众将变成政府支配下的木偶,尽管依然处在对于未来的无知状态,但是他们对于未来的认知道路可能就此被政府及其领导下的意见领袖所垄断,导致平等和自由的丧失。换言之,恰恰是所谓的民主和法治体制埋葬了其原本要保卫的自由与平等。正如卢梭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企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让全体人们授予政府可以随意按照政府自身的意愿立法的权力,那么这样的民主体制还是民主的吗?这样的法治对于个人自由而言还有什么真实意义呢?连阿克顿勋爵都在感慨:人们一旦假设,绝对权力因出于民意便会同宪法规定的自由一般合法,那么这种观点就会……遮天蔽日,使残暴横行于天下。[3]295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阐述绝对权力即便是出于民意的全体同意,依然会使其堕落成专断性的强制力,并非出于对民意的不信任,而恰恰是看到了很多个体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往往会将自身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或者短期效益放在首位,从而与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去甚远的客观现实。因此,如果要使得法治真正成为自由的重要保障机制,首要的一点便是要遏制将形式合法当做法治的全部内容,换言之,要对形式合法基础上的法律的制定模式加以限制,规定其边界。不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施以法律限制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它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迟到会丧失。那么,为了实现普遍利益即全体个体的平等与自由,我们现在的选择便是依靠政府能够公正执法,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而实施真正的法治。不过,这样的可行性显然是不高的。毕竟,在形式合法的法治社会中政府明显处于优势状态而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期望政府能够公平执法无疑是一个伦理学的难题。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公正是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常常被当做是德性之首,比星辰更让人尊敬。他甚至引用谚语说道,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9]130可见,在亚氏看来,公正是个体伦理道德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许多人能够对自己运用其德性,但是对他人的行为却没有德性。他引用了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比阿斯的名言:公职将能表明一个人的品质,来论证处于政权中的公职人员能够正确运动其德性尤其是公正的德性来处理一切与民众的平等与自由相关事务时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公正所促进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善。
或许依然会有少数政府官员会就此反驳,认为尽管他们的政权仅仅具有形式合法,但是他们所有的法律与法治措施都是为了保障和促进所有个体的平等与自由。即他们认为自己做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守法的公正,对他人的善。但是政治学的公理告诉我们,目的并不能够证明手段为正当。即就算政府立法的目标果真如他们所言是为了保障和充分实现个体的平等与自由,但是如果采取的措施是不合法的,那么最终即使是达到了原有的目标,却依然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毕竟,以破坏法治的措施来达致法治的目标,最终将会摧毁法治自身。诚如哈耶克所论及的那样: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3]281因此,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除了形式合法之外,我们还应该通过有效规范的制度来限制政府的立法与行政活动,从而获得实质合法性,使平等与自由始终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与指南。
不难发现,哈耶克所提出的法律之治为法治的根本以及公共利益为法治的普遍原则等观点都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指导方针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尤其是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建设的升级版十六字原则,修正了传统法治建设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隐患,提出法律的制定必须以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诚如四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治国之前提。只有立良法、行善治,才能够避免走入误区,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M].姚建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刘晓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3][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4][美]汉密尔顿,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 [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格马克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立早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about Hayek’s Conception of the Freedom under the Rule of Law
LI Jian-hua,NIU Lei*(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Hayek’s theory of free order in the system experiences a long evolutionary proces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freedom,makes his ideas close to Locke’s“where there is no rule of law,there would be no freedom”liberal views.Hayek’s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of the freedom includes three aspects.Firstly,the governance of law is the basic attribute of law.Secondly,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common interests.Third,the legal of form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Hayek; positive and freedom; rule of law; common interests;the legal form
基金项目:湖南社会科学基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路径研究”(编号: 14YBB0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公共伦理学研究;牛磊(1983-),男,安徽亳州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5-02-06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 04-0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