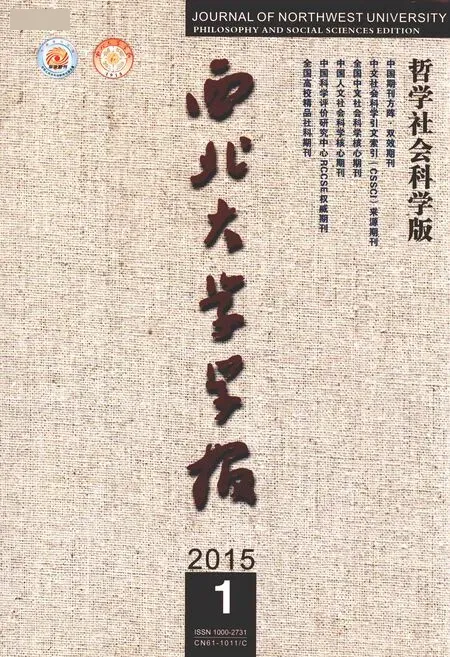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2015-02-21王子今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历史研究·“长安与丝绸之路”笔谈】
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西周王朝和东周秦国以至后来的秦王朝,都曾经在关中中部即今陕西西安附近地区设置行政中心。西周都城丰镐和秦都咸阳,在早期中西交通的开创事业中均曾据于重要的地位。
西周中期周穆王时代,史传这位君王曾向西北远行,创造了黄河流域居民开拓联络西方的交通道路的历史记录。《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2](P1357)。《竹书纪年》也有周穆王西征的明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卷五《秦本纪》和卷四三《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1](P175,1179)。晋武帝时,有人在汲郡盗掘战国时期魏王的陵墓,从中得到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获古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伯夭担任向导,从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友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纪念,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的事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周穆王西巡行程的终极,大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有的学者甚至推测,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经在欧洲中部留下了足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通常被看作信史,而关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曾经将其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将其列入“别史类”或者“传记类”中。大致都看作历史记载。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不过,许多学者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录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因此认为内容基本可信。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对于《穆天子传》中“天子西征至于玄池”的文句,刘师培解释说,“玄池即今咸海”,即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他又判断:“下文苦山、黄鼠山均在其西,今咸海以西,波斯国界也。”[3](P546)顾实对于穆天子西征路线有较为具体的说明。他推定周穆王西至甘肃,入青海,登昆仑,走于阗,登帕米尔山,至兴都库什山,又经撒马尔罕等地,进入位于今伊朗境内的西王母之邦。又行历高加索山,北入欧洲大平原。在波兰休居三月,大猎而还。顾实认为,通过穆天子西行路线,可以认识上古时代亚欧两大陆东西交通之孔道已经初步形成的事实[4](P175,244)。这当然只是一种意见。但是西周时期黄河中游地区交通西方的尝试,确实有历史遗迹可寻。云塘西周骨器制作遗址就曾出土过骆驼骨骼。位于丰镐的张家坡墓地出土玉器数量众多,玉质优异,制作精美,据检测,多为透闪石软玉,其材料来自多个产地。上村岭M2009出土的724件(组)玉器,经鉴定,大部分为新疆和田玉。由此可见,当时玉器东来的道路应当是畅通的。大致正是在周穆王时代前后,随葬车马与主墓分开,整车随马埋葬,舆后埋殉葬人的传统葬俗发生了变化,改变为将随葬的车辆拆散,将轮、轴、辕、衡、舆等部件陈放在主墓内,而将驾车马匹另行挖坑埋葬的形式[5](P193,187,75)。这种葬俗可能更突出地表现了墓主和车辆的密切关系。这些历史迹象,或许也与周穆王时代崇尚出行的风习有关。
作为周穆王西行出发点的宗周,可以看作前张骞时代中西交通线路的起点。
司马迁笔下为周穆王驾车的造父,是秦人的先祖。作为秦人在交通史上活跃表现之标志性符号的造父,后来以“御官”身份,姓名用以命名天上星座*《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一》:“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90页。。有意思的是,传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写到西王母告诉周穆王其国度与周王朝的空间距离:“咸阳去此四十六万里。”[6](卷六六下)这里不说“宗周”或者“丰镐”而说“咸阳”,是因为秦都咸阳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商鞅变法,秦自雍迁都咸阳,确定了在关中中心方位领导农耕发展和东向进军的优胜条件,也同时继承了丰镐王气。秦人与西北民族有密切的交往,于是东方人以为“秦与戎翟同俗”[1](《魏世家》,P1857),因而“夷翟遇之”[1](《秦本纪》,P202)。秦墓出土的“铲脚袋足鬲”,有学者即认为体现了“西北地区文化因素”[7](P138),战国中期以后出现并成为墓葬形制主流的洞室墓,也被判定“并不是秦文化的固有因素”,“可能是秦人吸收其他古文化的结果”[8](P308)。其渊源大致来自西北甘青高原。源自更遥远地方的文化因素对秦文化风格的影响,突出表现于黄金制品在墓葬中的发现。马家塬墓地埋葬车马的特殊装饰,也显示了从未见于中原文化遗存的审美意识和制作工艺。有学者指出,“马家塬墓地中的金珠及金器中的掐丝、镶嵌等工艺更可能源自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马家塬墓地出现的戴尖顶帽的人物形象,表明在战国时期这一地区不仅和欧亚草原中部、西部及西亚存在技术和工艺上的交流,还可能有人员的交往。”[9][10](P28)至于秦文化对遥远的西北方向的影响,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织锦刺绣,其风格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史载西汉时匈奴人使役“秦人”,颜师古解释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11](《匈奴传上》,P3782)其实,匈奴人使用的“秦人”称谓,应当理解为秦人经营西北,与草原民族交往的历史记忆的遗存。有的学者认为,“CHINA”的词源,应与“秦”的对外影响有关*薛福成《出使日记》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皆‘秦’之音译”,“揆其由来,当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林剑鸣则认为“很有可能”“在秦穆公时期,戎、狄的流徙,使‘秦’成为域外诸民族对中国的称呼”。《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50-51页。。实现统一之后的秦王朝对西北方向的特别关注,还表现在“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于是“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11](《五行志下》,P1472)。“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成为咸阳宫的重要景观*参看王子今:《秦始皇造铸“金人十二”之谜》,《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秦自雍迁都咸阳之后,咸阳继承了丰镐的作用,承担了联系中西交通的主导责任。此后,汉唐长安也同样是在这一地区,建设了表现出充沛的进取精神和能动力量的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 刘师培.穆天子传补释[M]∥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4] 顾实编.穆天子传西征讲疏[M].北京:中国书店,1990.
[5] 张长寿,殷玮璋.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 陶宗仪.说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8] 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9]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J].考古与文物,2013,(6).
[10]王辉.马家塬战国墓地综述[M]∥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K21
A
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05
2014-12-10
【主持人语】 汉武帝时期,张骞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域,被誉为“凿空之举”。通往西域之路的打通,有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学者李希霍芬将这条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但事实上,中外大量文献与考古资料证实,早在商周至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与中亚乃至更远的西方有着贸易往来。商周遗址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和胡人形象、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的丝织物与金属器物等即为例证。
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欧亚草原、南亚、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之间商品贸易、民族迁徙和思想、文化传播之路,也是沟通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桥梁。而在此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的长安,毫无疑问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本期特约四篇专家笔谈,从不同角度对周秦汉唐时期的长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疏理,以此推动丝绸之路研究的拓宽与深化。
主持人 王子今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