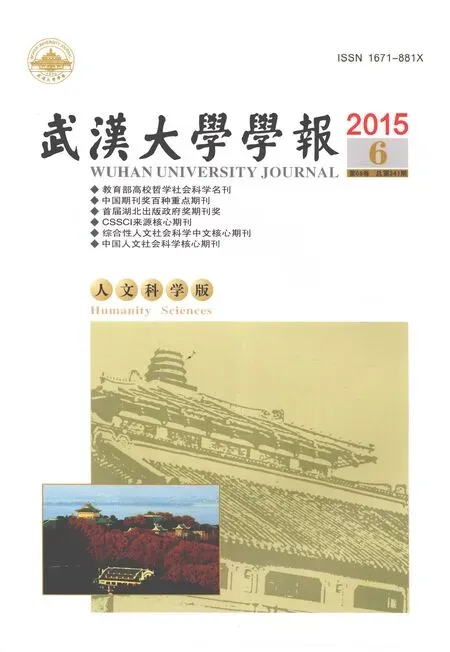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迟暮鸟语》: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2015-02-21郭雯
郭 雯
《迟暮鸟语》: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郭雯
摘要:科幻小说《迟暮鸟语》将故事背景置于生态系统毁灭后的末日时代,萨姆纳一家为了拯救人类开始进行克隆人实验,以促进人口增长。然而,千人一面的克隆人不仅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而且颠覆了传统家庭伦理,缺乏创造力、想象力、认知力等人性特征。小说围绕克隆人伦理道德的丧失、生态退化、个体身份诉求等主题,探讨了人类科学选择的潜在伦理问题。小说揭示出:人类必须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维护人性尊严,否则,任何违背自然规律和理性意志的科学选择必将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甚至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
关键词:《迟暮鸟语》; 克隆人; 科学选择; 生态伦理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克隆人逐渐成为科幻小说的一大题材。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即无性繁殖的人。美国女作家凯特·威廉(Kate Wilhelm)的《迟暮鸟语》(WhereLatetheSweetBirdsSang,1976)荣获了1977年雨果奖最佳小说奖。该小说的题目源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中的一句:“Bare ruined choirs,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意思是“荒芜的歌场,曾是鸟儿啁啾的地方”。这一荒凉的意象正是人类遭遇生态危机后奄奄一息的写照。为了拯救物种,人类开始制造克隆人,然而克隆人的出现却使人类进入了另一个生态伦理困境。克隆人千人一面,代际之间可以发生乱伦,女性沦为生育工具;更可怕的是,克隆人失去了宝贵的人性,只能依靠上世纪祖辈留下的科技信息与资源生存,活着成了其存在唯一的意义。此时,年轻的一代人急需恢复传统伦理秩序,他们带领克隆人走上重建生态家园的道路。
作者为何塑造与人类外形相似,却又难以确定其人类身份的克隆人形象?克隆叙事的目的何在?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视角多样,并且主要集中于西方学界。费丽拉在她的克隆人科幻文学专著中以本雅明的“光晕说”和鲍德里亚的“类像说”,批判了打破自然规律的克隆人,指出只有重建人类社会才能避免伦理恐慌。*参见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I Am The Other: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London:Praeger Publishers,2005,pp.151~161.霍夫曼认为威廉将克隆题材聚焦于社会问题而非道德启示,“未来由科学家统治的社会令人恐惧”*Marcia R.Hoffman.“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Book Review)”,in Library Journal,1975,100,p.2176.。威廉姆斯以乌托邦中的家庭与婚姻关系探讨小说中“人人属于彼此”的观念,认为“人造子宫是达到平等的手段”*Lynn F.Williams.“Everyone Belongs to Everyone Else: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Recent American Utopias 1965-1985”,in Utopian Studies,1987,p.128.。巴尔也将人工生殖作为推理性小说的母题,指出这种技术以“女性作为生育者,可满足同性伴侣想要孩子的愿望”,然而史蒂文斯认为“这种母题作为小说的隐喻,与现实中女权斗争者所采取的技术并不相同”*Carol D.Stevens.“Methodologically Questionable”,i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1990,17(2),p.281.史蒂文斯对巴尔(Marleen S.Barr)的著作 Alien to Femininity:Speculative Fi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中关于《迟暮鸟语》的女性主义的论述进行批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女性主义视角,或是乌托邦的社会与政治隐喻,小说作为典型的“软科幻”,在科技外壳之下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和谐生态与伦理秩序的维护。笔者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重点以克隆人的身份和群体伦理异化为出发点,探索小说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中的生态伦理思考与人文关怀。
一、 克隆人:科学选择的伦理困惑
人类正在经历“科学选择”阶段。从宏观上看,“科学选择”是人类选择的一种过程和状态,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逻辑发展;从微观上看,它是人类面对科学技术时做出的具体选择行为*关于科学选择的概念,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迟暮鸟语》描写的正是人类做出的科学选择与后果。小说开篇便描写了全球性的灾难场景:污染扩散、核实验、核泄漏、人口增长率为零、全球四分之一的地区陷入饥荒与瘟疫、无法净化饮用水、植物枯萎、大气层被破坏、全球经济陷入谷底。生态环境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人类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对自然的肆意开采破坏了自然生态,使人类饱受痛苦,仅存的萨姆纳(Sumner)一家感叹道:“我们改变了我们头顶上大气层的光化反应,却无法适应其增强的放射性,以至于无法生存”*凯特·威廉:《迟暮鸟语》,李克勤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2页。。于是,他们肩负起用科学改变人类命运的使命,选择了一片未被摧毁、与世隔绝的山谷,进行人与动物的克隆。萨姆纳家族成员、第一代基因贡献者戴维(David)致力于克隆人研究,希冀通过克隆人交配繁衍后代。可见,科学选择具有双向性,人类主动地认知科学、运用技术;同时,克隆人是被选择的产物,是被动的科学选择的结果。
工具理性正在被异化,自诩为地球主人的人类开始成为被改造的客体。克隆人的身份由代号作为标记,从某种意义来说,每一代都是一个人,其由分割的细胞与碎片构成,而这种科学选择的结果随着“戴-Ⅰ,克-Ⅰ,西-Ⅰ,沃-Ⅰ”的出现,注定带来新型生态灾难和伦理困境。戴维看见“戴-Ⅳ,他自己……他转过身,沉思着这些男孩的未来。都是同样的年龄。叔伯,父亲,祖父,全都是一个年龄。他开始觉得头疼了”。“头疼”表明他意识到科学选择的隐患:人类可以选择生物科学进行基因复制,甚至可以脱离“原作”,对“摹本”进行重复叠加。当爱人西莉亚的克隆人出现在戴维面前时,他顿时出现幻觉:他把西莉亚-Ⅲ当作妻子,西-Ⅰ和西-Ⅱ当作双胞胎女儿,“每次看到她时,眼中的影像总是西莉亚,这一点让他心口隐隐作痛”。幻觉和痛苦源于相似性带来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混乱。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后,又肆意更改了进化历程,改写了自然规律,动摇了人类的根基。一个个“摹本”之间消解了生物差异性,人沦为复制技术之下的“类像”。
千篇一律的科学选择产物使小说弥漫着恐怖感和怪异感,产生了“暗恐”效果*详见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Uncanny,trans.by David Mclintock,New York:Penguin Group,2003,pp.123~134.“暗恐”(uncanny)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关键词是“重复”(repetition)、“复影”(double)和“压抑的复现”(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其德语原文是“unheimlich”,基本意义表示陌生的、非家的、令人不适的、令人害怕的,但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即本应隐秘的东西却显露出来,朝着“熟悉的”意思发展。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反义词:“heimlich”表示熟悉的、友好的、似家的、舒适的,同时也表示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暗恐”本身就是一个语义含混的词语,“暗恐属于恐惧的一个种类,会回到以前认识的某事,回到早已熟悉的事物”。本文目前主要引用国内通用译法,即童明教授翻译的“暗恐”。关于“暗恐”译法可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暗”字旨在突出uncanny词义中“隐秘的”、“压抑的”、“秘密的”意思,但uncanny绝非仅表示“恐惧”。另外,关于“双重性”(double)的翻译还参考了童明教授的译法“复影”,参见童明:《暗恐/非家幻觉》,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6~116页。。“暗恐”虽然最早是心理分析的术语,但是如今已被运用于文学、艺术、建筑、文化等领域,表示似曾相识、熟悉而陌生、或者不确定性引发的恐怖或怪异感。克隆人的脸庞“既熟悉又陌生,既了如指掌又难以捉摸”,这一描写透露了戴维的心理“暗恐”,身份不明的克隆人群体加强了他的伦理困惑:这一个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谁?“这群人个个都是你,不同生长阶段的你。这种感觉真有点瘆人”。人类一直对另一个自己抱有某种恐惧心理,它重复了死亡母题,增强了恐怖感。小说中希尔达当初“用绳子勒死了那个一天比一天更像她的小女孩”,实际上杀死了令自己恐惧的“复影”,因为“复影”导致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当叔父沃尔特的克隆体沃-Ⅰ说话时,“这个声音实在太像沃尔特,戴维不觉心中一凛,泛起一股寒意。也许是恐惧”。可见,恐惧和不安取代了戴维以前平静的生活,他触景生情,以往属于自然人的文明象征——浆果、黑莓、焰火、古老的国庆节都历历在目。然而人类与大自然相处和谐,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规律的平衡被打破,如今突破常规的克隆人与自然界格格不入。
除了生理上的相似以外,克隆人群体的心理也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失去属于自己的个性——也就是形成自我的特性。“心灵感应”在小说第一部分的I代克隆人中已经展露无遗,而在第二部分的第二代克隆人群体描写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大家可以共同感受到一个人的欢乐、疼痛或恐惧。主人公茉莉在未出现自我意识之前,曾经感叹从前那些世纪的人类会“因为孤独而发疯。他们从来没有体会过兄弟姐妹像一个人时所带来的安慰: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心愿、欲望和欢乐”。可是她逐渐发现无法区分的整体,“一模一样,完全是一个东西”。齐泽克认为“真正的焦虑并非由于身体的复影,而是对独特灵魂的复制”*Slavoj Zizek.“Of Cells and Selves”,in The Zizek Reader,Oxford:Blackwell,2000,p.316.,当人类的外形与心理一模一样时,不仅形成完美世界的多样性彻底消失,而且个体将困惑于何为个性,为何要有个性,如何构成个性。
作者将多样性的覆灭用一种幽默与讽刺的笔法表达出来。当被选出的克隆人们踏上寻找信息的征程后,其中两个克隆人由于脱离了群体,变得抑郁痛苦,甚至开始服用镇定剂等精神疾患的药品,因为“丧失理智是对集体的威胁,同一支的兄弟姐妹们将感受到与患者相同的痛苦”。有学者曾对双胞胎进行研究,认为除了基因相同以外,还有许多方面超出了生理性,包括性格、习惯和行为也会有许多相似性*参见John Haran,Jenny Kitzinger,et al.“Human Cloning”,in Human Cloning in Media:From Science Fiction to Science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68.。 而克隆人群体的描写借用了现实中双胞胎的相似性,再经过加工变形,形成了科幻小说独到的、异于人类常态的新奇性,让读者领悟到人类的多样性也是构成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二、 伦理混乱与人性的呐喊
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克隆人所遭遇的伦理困惑,主要体现在伦理身份模糊所造成的伦理混乱上;而小说在呈现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以克隆人的视角发出了对人性的呐喊。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认为,“对于虚构事迹的事实性报道所产生的效果是对抗一套常规体系——包含着呈现新的标准体系的观点或世界景观。”*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6页。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认为,每一个伦理环境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则,而不同伦理身份的人在他所处的伦理环境中也要按照其身份做出伦理选择。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克隆人群体形成了自己的伦理环境,而新型伦理环境也有它自身的伦理规则和秩序。克隆人群体突出“集体主义”,他们奉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政策,并且可以随意性交。他们厌恶个性、排斥并孤立与众不同的个体,只要有人违反“集体主义”而一意孤行,就会被遣送至隔离区,不必在乎他的死活。传统的恋爱、家庭、婚育、友谊都不被允许存在,而所谓的兄弟姐妹之情仅仅是为了维护基因的完美性,存活是唯一的目的。可见,这些陌生化的夸张手法旨在彰显克隆人群体伦理的荒谬性。克隆人逐渐失去了传统的、人类独有的伦理意识和善恶观念,在这个新型的伦理环境中,整个生态系统内部正在逐渐崩溃。
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克隆人打破了人类原有的伦理禁忌,代际之间可以发生性乱:“他们奉行男女乱交。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受鼓励的,因为无法预计他们中有多少人有生育能力,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多大比例……乱交是最正常不过的,但仅限于他们之间”。克隆人群体脱离了家庭道德与责任的束缚,伦理环境与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他们可以像牲口一样随意交配,并且认同这样的行为。乱伦本是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乱伦禁忌也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然而,固定的父母在世界末日已毫无意义,传统家庭不复存在,并且由于缺乏明确的伦理身份,对于克隆人来说并不存在自然人社会中的乱伦。克隆人之间的交配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的族内婚姻,这是历史的倒退。
作者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未来科学选择时代进行预见,对生态灾难之下的社会伦理进行观照。女性克隆人沦为男性克隆人的玩偶和生育工具,女人只要不在经期,就可以被任何一个克隆群体中的男性交媾,性爱与吃饭睡觉一样,是完全脱离灵与肉结合的兽性原欲。她们被强迫服用催眠药或兴奋剂,以形成心理定势,接受作为生育者的伦理身份。如果怀孕,她们就会被送到生育者片区,并举行“哀悼逝者”的聚会。于是,心理创伤不仅出现在老一辈身上,对于二代和三代克隆人、尤其女性克隆人也存在心理问题。被隔离的生育者们离开了集体,“她们一辈子离不开药物,还要接受心理辅导,形成心理定势,这样才能接受那种生活”。“服药”主要是对其心理与意识可产生麻醉作用,让其失去理智、无法进行伦理选择。
由于缺乏伦理观念和伦理意识,曾经珍贵的理性、道德、创造力、精神、尊严等人性因子已不复存在。克隆人群体改变了道德“向善”的传统意义,克隆人的道德只服务于自己的族群,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向善与仁爱。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在自然人与克隆人同时遇到困境时,他们只救助克隆人。这种狭隘的“集体主义”来源于人类的“科学选择”,不仅抹杀了个体的个性诉求,而且销毁了人类真善美的道德观念,科技开始驾驭操纵人类伦理,并且改写了人的意义。当戴维与老辈们被克隆人群体排斥时,他们已经预见到了克隆人不再是人:“克隆人!并不完全是人类。克隆体”。“克隆体”实际上指出了被物化的克隆人不仅改变了人的本体论,而且不再具有伦理属性这一根本特征。“他们中间仍然可以称为人类的那一部分势必渐渐枯竭。他们要摧毁的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人性,是把人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本质的东西,是人类几千年进化所得的文明成果。
可见,克隆人群体人性的消解主要体现在理性意志的退化上,价值理性随着工具理性膨胀而缺失,这才是使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动摇的根源。叔父沃尔特临死之前对戴维呐喊道:“阻止他们,戴维。看在上帝的份上,阻止他们!”这个呐喊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呐喊,是人类希望解救自己,阻止退化与消亡的潜在危险。
“哈哈,阿巴说谎,你从来没有坐过船。”同学们大笑。“我……当然坐过船。”阿巴有些不服气,“我有一张永远有效的贝壳船票,可以乘坐大船。我带你们去看。”这时候的阿巴,完全忘记了自己对韩贝的承诺,只想证明自己。
原本为了挽救生态灾难的科学选择却带来了其他严重的问题:人性消解、传统的伦理观念荡然无存、两性关系改变、人际关系破坏。生活的意义在于“交配”,依靠前人留下的科技就足以生存,不必懂得如何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大自然、融入大自然。克隆人沦为被科技奴役的机器,他们缺乏幻想能力与概括能力,“九岁或十岁以下的孩子们无法辨识线条画,无法写出哪怕最简单的故事,无法从个别事例中总结出一般性规律、并运用到其他事例中去”。克隆人的精神危机使他们陷入对现有物质基础的过度依赖,丧失了主体性和劳动力。这一致命缺陷印证了鲍德里亚对克隆技术的嘲讽,克隆人只是“一个部分,他无须具备想象力再去生产自己,就像蚯蚓往往并不需要土壤”*Jean Baudrillard.“Clone Story”,in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by S.F.Glas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65.。等待人类的不仅是自然生态之网的破裂,还有人与人的社会之网以及人与自我的精神之网的破裂。
作者将个人的精神生态融入自然生态,关注科技、生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正如鲁枢元教授对“自然生态圈”、“社会生态圈”与“精神生态圈”*有关精神生态的论述,参见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1~93页。鲁枢元教授认为,精神生态学主要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它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以及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三个层面的思考。克隆人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自然规律,使人类变为造物主实践“人造人”,而且精神危机使生态问题上升到更为严重的伦理问题。人属于生态系统,并被自然赋予灵性,通过发挥理性来改善自身和大自然,然而,自然与生态不仅包括资源,人的伦理、情感、道德、信仰缺失会使人与自然陷入更为严峻的对抗中。对人性的回归,精神的追求,对自然的维护,以及对“人”的重新认识已迫在眉睫。
三、 寻根之旅的身份重构
世界末日并非地球的毁灭,而是人(human)不再是人(person),没有创造力的人类注定会亲手摧毁历史文明。不过小说并未刻画一个世纪末的图景,而是通过马克的寻根之旅与身份重构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克隆人与自然人所希望的未来。人类不仅是生物性躯体,而且是与他人维系的社会存在,更应认识自我、从自我迷失中解救出来,重新获得伦理意识和精神世界。戴维曾经说过“高等动物必须以交配繁殖的手段延续后代,否则便会灭绝。繁殖的能力潜伏在基因里,这东西有记忆,能自我修复”,这句话为整部小说埋下伏笔。这里的“基因”是指整个人类的基因,“记忆”隐喻了人性的延续和历史的召唤,“修复”预示着后代即将有克隆人个体逐渐脱离残酷的环境,找回遗失已久的一切自然的东西,包括遵守自然规律、发现大自然的美好、找到自我的存在感以及恢复最宝贵的人性。
重建家园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一代的肩上,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活力的象征,克隆人即将踏上回归人类的征程。第二代克隆人茉莉(Molly)和巴恩(Ben)是少数拥有自我意识的克隆人,他们的孩子马克(Mark)身体里流淌着他们叛逆的血液,他的“根”来自人类遥远的过去,由一代代陌生人的基因转化而来,“结果是,他不像河谷里的任何一个人”。克隆人虽是无根的产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但是作为“异类”的马克对于人生起源的困惑一直存在,他的探险之旅就是“寻根”的象征。“寻根”意味着回归,回归绝非倒退,而是寻找人与自然最初的有机和谐的状态。沿途中那些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与残垣断壁为他提供了“过去”的线索,寻找过去也就意味着寻找人类本真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的姓名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具有特殊寓意,其英文(Mark)包含痕迹、记号、目标等意义。马克从小生长在祖辈世代居住的农场老宅里,这里的书籍记载着祖辈们关于生活的所有奇特的东西,而克隆人群体却不会触碰它们。他喜欢从阅读中攫取精神的力量、获得对人性的认知。母亲茉莉凭借其艺术天分将所见所闻所想全用绘画记录下来,这种用艺术来表达个体情感与生活体验的天赋也遗传给了马克,他热爱雕塑,擅长捏泥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因子的光辉。
“寻根”之旅标志着具有伦理意识和自我精神的克隆人个体逐渐脱离没有意义的“类像”,开启了自然人身份的重构之路。可以说,马克的成长过程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为其今后的身份重构打下了基础。在身份诉求之路与探险的旅途中,马克开始体验自然人的本能与自由意志,他爱上了克隆人洛丝,并在性爱中放纵自我,渴求灵与肉的结合。但是,麻木的洛丝却只保持着“生育者”的身份,履行着生育工具的义务,并没有奉献真正的爱情与情感,这也加深了马克对克隆人群体的憎恶,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对摧毁克隆人群体、建立新社会的信念。同时,马克面临着伦理两难,他既是集体的一份子,又急于改变整个群体、创造新的未来:“要破坏他们眼下的完美生活,他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他们的敌人”,这是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他的伦理选择。他将克隆人的生活比作一座金字塔,最为讽刺的是,“有了科技,河谷的生活才能支撑到现在,但维持现状却让人们不思进取,于是,当金字塔开始倾斜时,任何复兴机会都将被彻底葬送”。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克隆人群体过于依赖前人的科技,他们寻找信息与物资,却从未思考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精神的匮乏和伦理的丧失正在加速克隆人社会的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注重大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描写,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融为一体,加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小说中的“树”与“森林”是反复运用的意象,它们与克隆人的身份重构有着密切关系,具有象征意义。树木和森林贯穿着人类生存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陆地上的人类祖祖辈辈都离不开树木的养分与依靠。森林具有灵性,人类也具有灵性,人类祖祖辈辈在改造大自然的劳动中认识了自己,发展了自我。马克就是大自然之子,他具有渴望回归自然的冲动,第三部分一开始就是茉莉与儿子马克倾听来自大自然的声音。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内心的悄悄话,成为另一个自我的象征,在大自然的魅力中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而克隆人群体永远无法体会到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树木和森林在马克的梦中出现,带领他寻找妈妈,唤醒最可贵的亲情。同时,树木和森林又在现实中让马克觉得可怕而危险,森林沉默着,寂然无声,马克在寂静中聆听自己的心声,让他在寂寞孤独中发现个体的存在、学会在冥思中体验生命,找到自我。
虽然探险沿途环境恶化、地势险峻,大自然的生态早已遭受破坏,城市建筑一片废墟,然而树木的根须努力在下面街道的钢筋水泥中寻找养分,在世界末日中此情此景更富有生命力,让人憧憬未来。一棵白色橡树始终贯穿小说,它默默地见证着世间沧海桑田,它见过居住在河谷上的印第安人,见过第一批拜仁殖民者,见过自然人与克隆人的兴衰,直到最后克隆人灭亡,它仍旧岿然屹立。在灾难面前,所有的生命都陷入危机。时间流逝,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存在,人类只有重新认识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才能认识自我、获得新生。因此,对大自然的描写是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克隆人的身份诉求与家园重建的主题相对应,也与“迟暮鸟语”的意境遥相呼应。
世界末日之时就是人类重生之时。在重大灾难面前,人类的伦理选择若是为了使整个人类完整生存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向善的伦理选择。少数具有自我意识的克隆人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维护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观念,为人类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未来。年轻的一代再次组建探险队寻找物资与信息,在这支队伍中,马克成为领军人物,他俨然边疆传奇中的英雄,带领小分队一路向东。最终,马克带走了几名克隆女孩,与受过训练的新生代克隆人一起开始人类种族繁衍计划。这次的繁衍与前几代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与自然紧密依存,穿过森林找到了新的家园。在这个新纪年中,任何人的酸甜苦辣都属于他自己,每一个孩子都与众不同,新新人类通过劳动创造新生活,生物多样性与人性正在复苏。
四、 结语
《迟暮鸟语》的故事绝非仅仅构想一个基于强大基因技术的克隆人群体——被相似性和心灵感应紧密团结的集体。小说从虚拟的伦理环境中探讨真正的人类伦理道德应该如何实践、和谐的生态系统应当如何维护。小说在“客观”呈现克隆人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其可能对自然人社会自身带来的伦理困惑与混乱的同时,试图从女性主义和生态伦理的视角,描绘出一种可能的希望。作者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相结合,勾勒出世界末日中摇摇欲坠的生命,也逐渐突出了作品的主题。自人类有了“人”的意识以来,伦理意识便须臾不可剥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将如此。科学选择必须要有伦理意识的介入,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自居,将理性异化、将人物化。只有从内部解救生态问题,首先拯救人类灵魂,才有可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作者地址:郭雯,苏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Email:ainna520@sohu.com。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SJB55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WWC001)
●责任编辑:刘金波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6.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