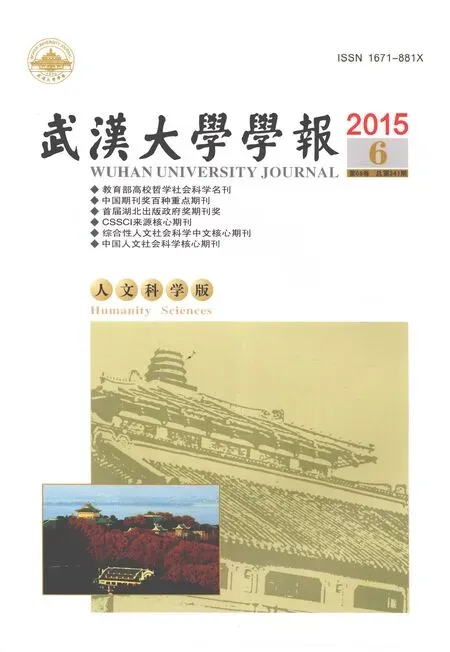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建构与运用
2015-02-21周光庆
周光庆
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建构与运用
周光庆
摘要:与300年来一些学者的估计不足相反,朱熹确实建构起了新的《四书》语言诠释方法论,成为其《四书》诠释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创立语言诠释方法论时,既有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即“义理从文字中迸出”、指向性即“正欲以语道”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又有对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即“循序而渐进焉”、立足语境法即“各随本文意看”、循环反复法即“终而复始,通贯浃洽”等具体性方法的建构,并努力使这两方面融合成为语言诠释方法论的整体,以应用于《四书》诠释的实际,获得了《四书》诠释史上开创性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展。
关键词:朱熹; 语言诠释方法论; 《四书集注》
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主干意识——儒学思想——发展到宋代,便以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态呈现;而理学理论形成以天理论为主体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朱熹《四书集注》的问世。可是,一部24万字的儒家“四书”诠释著作,何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发挥如此深远的历史作用呢?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他创建的包括语言诠释方法论在内的诠释方法论的正确与成功。然而,自清代以来的300多年里,学者们论说《四书集注》时往往对其诠释方法论中的语言诠释方法及其成就评价不足,甚至存在着许多误解;以致到了现在,还是很少看到专门研究朱熹《四书集注》语言诠释方法论的学术成果问世。但事实上,朱熹经过“四十余年理会”,确实建构起了新的语言诠释方法论;而且,既有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指向性等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又有对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立足语境法、循环反复法等具体性方法的建构,并努力使二者融合为方法论的整体,主要应用于《四书》诠释的实际,获得了《四书》诠释史上的开创性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展,因而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和研究。
一、 探讨语言诠释的根本性:“义理从文字中迸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哲人学者就开始了对于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之关系、语言在人的理解与诠释活动中重大作用的研究。他们不仅提出了“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等著名命题,而且在诠释文化经典语言的同时开展了一场历时200多年的“名实之辨”。这就为中国语言哲学和诠释学的形成发展开拓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使中国语言哲学和诠释学以其独特的风格能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朱熹当然很好地继承了这些学术精神和学术遗产,然而他又清醒地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为陋矣。然或乃徒颂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辗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朱文公文集》卷75之《中庸集解序》*本文引用的《朱文公文集》,均载于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以下不另注。)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其要害都在于对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和指向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朱熹在自觉地承担起儒家使命并将其转化为诠释儒家经典的动力和目标时,大力探讨语言诠释在经典诠释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论述其语言诠释所固有的根本性和指向性。
在探讨语言诠释的根本性时,朱熹提出的第一个重要论点是“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
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晓……则道理自逐旋分明。(《朱子语类》第2913页*本文凡是引用朱子语录,皆采自宋儒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不另注。)
圣贤形之于言,所以发其意。(《朱子语类》第256页)
圣人说话,开口见心,必不只说半截,藏着半截。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须立说别生枝蔓。唯能认得圣人句中之意,乃善。(《朱子语类》第435页)
朱熹的这一重要论点有难能可贵的深刻性:第一,它指出,圣人之心、圣人之意,是“形之于言”的。这里的亮点是“形之于言”一语,它所强调的是圣人的心意是凭借语言而成“形”的,是通过语言以表征的,是运用语言来表达的。第二,它昭告,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一个“即”字,就明白而有力地彰显出了一种深厚的理论意蕴,即圣人心意与文本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显现的关系,文本语言是圣人心意的表现性存在。第三,它进而揭示,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这就意味着,圣人之心凝聚了对于天下之理的全面认识,天下之理与文本语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存在与显现的关系,文本语言同样是天下之理的表现性存在。第四,以前面三点为依据,它特别强调,学者必因圣人之言以求圣人之心,因圣人之心以悟天地之理,使道理自逐旋分明。显然,这里所概括与强调的,既是经典诠释的必由之路和基本规律,也是语言诠释的根本性。综观以上四点,学者应该可以领悟到:圣人之心、天下之理的真实存在,正是在它们的语言建构与表达中才变得可以理解;因此语言诠释具有不可不格外重视的根本性。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语言诠释,就不可能真正诠释好经典从而体验到圣人之心、天下之理。对此,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眼光来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就不难领略到它作为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关于语言诠释的根本性,朱熹提出的又一重要论点是“义理从文字中迸出”:
吾道之所寄,不越语言文字之间。(《中庸章句序》)
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朱子语类》第173页)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朱子语类》第179页)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朱子语类》第187页)
读圣人言语,读时研穷子细,认得这言语中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见理而不见圣人言语。(《朱子语类》第187页)
朱熹已经启示人们,天下之理与文本语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存在与显现的关系,文本语言同样是天下之理的表现性存在。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强调,“吾道之所寄,不越语言文字之间”,“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义理既蕴含于文字深处,又能从文字中迸出,这对于读书人而言有着多么大的感召力!然而,义理并不会自己从文字中迸出,得有一个前提性条件,那就是读书人面对经典必须首先认真进行语言诠释,着意玩味,读得通贯。尽管义理既广大、又深远、有时还很抽象,但是读书人如能“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还告诉人们:“读圣人言语,读时研穷子细,认得这言语中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见理而不见圣人言语。”这似乎与著名的“得意忘言”论有些相近,但是它仍然突出着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就是读书人必须“读时研穷子细,认得这言语中有一个道理在里面分明”。这也就是说,他还在继续证明着语言诠释的根本性。
二、 揭示语言诠释的指向性:“正欲以语道耳”
在探讨语言诠释之根本性的同时,朱熹又揭示出语言诠释在经典诠释中的指向性,确立了语言诠释应该指向的基本目的与实际目标。这不仅因为他对二者是同样高度重视的,而且也因为二者本来就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就经典诠释而言,语言诠释之根本性总是表现为语言诠释的指向性,语言诠释之所以能够具有指向性,是由于语言诠释本来就具有根本性,二者永远相互发明。所以朱熹进一步反复强调:
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求之自浅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远,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渐经历,审熟详明,而无躐等空言之弊驯致其极,然后吾心得正,天地圣人之心不外是焉。(《朱文公文集》卷42,《答石子重》)
天下自有一个道理在,若大路然。圣人之言,便是一个引路底。(《朱子语类》第2756页)
解释文义,使各有指归,正欲以语道耳。不然,则解释文义将何为邪?(《朱文公文集》卷42,《答胡广仲》)
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朱文公文集》卷81,《书中庸后》)
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朱文公文集》卷31,《答敬夫孟子说疑义》)
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朱子语类》第437页)
按照朱熹的论述,经典文本之语言诠释的指向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经典之语言诠释指向天地之理,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诠释经典而体悟和建构天理论。这是因为,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意,圣人之心意即天地之理,而学者必因圣人之言以求圣人之心意,因圣人之心意以体悟天地之理。如果没有可靠的语言诠释,学者也就不可能有对圣人之心、天地之理的正确体悟与建构。第二,经典之语言诠释指向学者本身,基本目的是为了激励和引导学者追求天理的意趣。如果说圣人之言是一个引路的,那么对圣人之言的诠释同样也是一个引路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最好的语言诠释应该能够激发学者体悟天地之理的意趣,指点学者体悟天地之理的途径,促使学者通过语言诠释体悟天地之理。第三,正是因为经典之语言诠释具有指向天地之理、指向学者本身的指向性,所以朱熹再往前跨出一步,指出:解说圣贤之言,亦即进行语言诠释,就有必要、也有可能时时以义理相接去,使语言诠释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相交融,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反之,如果不是在正确的语言诠释之中,也就谈不到以义理相接去,因为渠成而后才能水到。
为了使广大学人都能认识到语言诠释在经典诠释中的根本性和指向性,朱熹还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众多弟子中更多地予以强调或宣讲,力图以此与之共勉。譬如,理学阵营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敬夫),倾注心力著有《孟子说》,对于其中《尽心上》之“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反身而至于诚,则心与理一。”而朱熹则在《答敬夫孟子说疑义》里为之仔细剖析:
按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窃恐当如张子之说,以“行无不慊于心”解之,乃有落著。兼“乐莫大焉”,便是“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实有味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
即使是对于地位相当的朋友,朱熹也是如此直接地提出中肯的批评,这既彰显了当时理学领袖们的风范,也说明了所论问题的重要。他首先指明,张栻的解语只是赞咏之语,缺乏充分的语言诠释。要知道,“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他接着说明,由于缺乏应有的语言诠释,由于未能发挥语言诠释的指向性,所以其解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他进而建议,这里应该引用张载的“行无不慊于心”以解之,这样便能使语言诠释真正落到实处。他最后强调,如果诠释经典而无充分的语言诠释,且不能发挥语言诠释的根本性和指向性,那只是悬空说过罢了,便与禅家无以异矣,如此则何以能够避免他们的错误并实现对于他们的超越。
三、 建构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循序而渐进焉”
通过朱熹的努力,语言诠释在经典诠释中的根本性和指向性已经完全彰显了。可是,在宋代许多学人“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辗转相迷”的情势下,在实际上极为复杂的语言诠释工作中,如何才能全面发挥并突出语言诠释的最大效用呢?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仍然满足于一般的“训诂模式”,而要开拓新的途径,找到具体而适当的语言诠释方法。否则,这一切都会落空。为此,朱熹首先着眼于语言诠释的全局,探讨其一般程序,从而建构起了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先看他的论述:
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朱文公文集》卷56,《答陈师德》)
(解经)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朱文公文集》卷31,《答敬夫孟子说疑义》)
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而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朱文公文集》卷74,《读书之要》)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朱子语类》第162页)
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朱子语类》第173页)
不若且依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之自然贯通。(《朱子语类》第183页)
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绎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辈讲解,更第二番读过。(《朱子语类》第189页)
透过以上的论述不难体会到,朱熹早已深切地感知,语言诠释的主要对象是经典的语言,在经典语言系统内部:词语组合成为句子,并在句子中发挥作用;句子组合成为段落,并在段落中发挥作用;段落组合成为篇章,并在篇章中发挥作用;篇章组合成为文本,而文本则自有文势语脉,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正是有鉴于此,他这才反复强调“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必须做到“循序而渐进焉”、“详密有序”。
朱熹反复强调的“循序”和“详密有序”,实际上又包含着三个层次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概括言之:诠释经典,应该先释字义、次释文义;应该逐字、逐句、逐段理会,然后推本而索言之。这里的“先”与“后”就体现了“次序”和“循序”,它要求“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第二个层次是深入言之:紧扣句子以训释词语意义,亦即“字求其训”;紧扣段落以解释句子意义,亦即“句索其旨”;“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绎玩味”;就这样,逐层“推捱”,“久之自然贯通”。第三个层次是展开言之:语言诠释绝对不能孤立进行,必须与体验诠释结合起来,“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这就显示出了语言诠释详密有序法特有的系统性特征。
应该说,这种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一旦运用得好确实又能引导学者“循序而渐进”,直到“自然贯通”、“意定理明”的最佳境界。限于篇幅,仅看一例: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通观这一则注文,它最大特色在于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
第一,它是先释字(词)义以字(词)求其训。其对于字(词)义的解释,既不离其本义或所用义项,又紧扣它在特定句子中显示出来的意蕴,因而准确、深刻,还能引人入胜。即以对几个关键性动词的解释而论,将“志”解释为“心之所之”、将“游”解释为“玩物适情”、将“据”解释为“执守”、将“依”解释为“不违”就是如此。特别是对于“游”的解释,学者如果能够静心玩味,不仅可以获得准确的认识,而且能够产生适当的联想,仿佛随之渐入那“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的佳境。
第二,它是次释句义以句索其旨。其对于句义的解释,既以对词语的解释为基础,又将句子置于段落之中,而且总是与体验诠释结合起来,因而正确、丰满,使人受到启发与引导。例如对“据于德”一句的解释:它既是以对词语“据”与“道”的解释为基础,又是将该句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系列之中,然后还与体验诠释结合起来,这才展现该句的主旨:“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可是这“而有日新之功矣”一层意思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一层意思既来自他本于原句的内在逻辑进行的推理,又来自他的体验,是朱熹就全句推本而索言之以得来的。
四、 建构语言诠释的立足语境法:“各随本文意看”
详密有序以进行语言诠释之方法,主要是针对经典言语系统内部的。然而,经典言语,无论就其整个系统而言,还是就其各种要素而言,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都是必然与环境互动并受其制约与影响的。为此,朱熹又建构起了立足语境法,主要是着眼于言语各种要素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分析和解释各种言语要素尤其是语词的准确意义。先看他的理论论述:
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朱子语类》第192页)
问:“一般字,却有浅深轻重,如何看?”曰:“当看上下文。”(《朱子语类》第193页)
大凡理会义理,须先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所归,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虽曰贯通,而浑然之中所谓粲然者,初未尝乱也。(《朱文公文集》卷42,《答石子重》)
圣贤说出来底言语,自有语脉,安顿得各有所在,须玩索其旨。(《朱子语类》第194页)
子张谓“执德不弘”,人多以宽大训“弘”字,大无意味,如何接连得“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文义相贯。盖“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横渠谓:“义理,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所可得也。”此语最佳。(《朱子语类》第194页)
朱熹反复强调的是,凡读书,“当看上下文”,“须看上下文意”,“各随本文意看”,应该把握住它本有的“语脉”,由此准确地把握好一个词意义的浅深轻重,而“不可(脱离上下文或语脉)泥著一字”。而他所谓的“上下文”、“上下文意”、“本文意”或“语脉”,都是指在交谈过程中特定言语要素出现的环境,大致相当于今人所说的“语境”。他的实际观点是,诠释经典言语要立足特定语境,从语境与言语的互动关系中分析和解释各种言语要素尤其是语词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将各种言语要素意义的浅深轻重准确地阐述出来。这是因为,特定语境对于在其中出现的各种言语要素尤其是特定语词,既有排除歧义而使其意义单一明确的作用,又有补衬意义而使之深厚丰满并且进而传达言外之意的作用。
为了对立足语境的语言诠释方法进行说明,朱熹自己还特别谈到两个实例。其一,《论语·子张》记载:“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对于在这一语境里出现的语词“弘”,人们大都训释为“宽大”;朱熹却认为,这种解释“大无意味”,因为它不能着眼于特定语境而接连得“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以使文义相贯。其实,这里的“弘”还有“深沉重厚之意”,而这个意义,正是特定语境补衬出来的。由此可见,必须立足特定语境以探究特定语词所表达的意义。其二,《论语》有云:“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而《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儒家倡导的“仁”与“智”呢?简单地说,首先必须认识“一般字,(进入特定语境之后)却有浅深轻重”之不同的道理;接着应该立足特定语境以探究特定语词所表达的意义,亦即“须是各随本文意看”。这样一来就不难明白,在《论语》语境中出现的“仁”与“智”,与在《中庸》语境中出现的“仁”与“智”,其意义既有浅深轻重的差别又有相同相通的共性。最后将其合而观之,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与“智”。这个实例进而可以说明,诠释《四书》经典,首先必须立足特定语境以探究特定语词所表达的意义,然后应该站得更高,着眼于更大的语境,将同一语词在不同小语境中表达出来的几个意义,置于更大的语境亦即儒学的语境之中,使之相互补充、相互发明。这样就能更好地引导人们对于特定语词所表达的儒学观念获得一种既准确又全面的认识。
然而,从经典诠释的历史实践来看,运用立足语境法的实际困难和实际情形,要比以上所论述的复杂得多。因为:第一,就语境本身而言,有小语境,即上下文或文本结构;有大语境,即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两种语境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而所谓立足语境,是既要立足小语境,也要立足大语境。第二,就文本写作而言,有的文本的相关章节,明白而周详地交待或显示了语境,只待诠释者去体认;有的文本的相关章节,则缺乏对于语境之足够的交待或显示,则有待于诠释者的考求。朱熹正是在这种种考验面前发展了自己创建的立足语境之语言诠释方法。请看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正如钱穆先生早已指出的:“从来读《论语》的,对此章不知发生过几多疑辨。直到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掀起‘打到孔家店’的浪潮,有人把此章编了‘子见南子’的话剧,在孔子家乡曲阜某中学演出,引起了全国报章喧传注意。可见读《论语》,不能不注意到此章。”*钱穆:《孔子与论语》,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8页。此章之所以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难以理解,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它的大语境、小语境以探究孔子讲话的真实用意——可是《论语》原文却又恰恰缺乏对于特定语境之足够的交待。面对这种情况,朱熹作出的诠释是:
《论语集注》: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矢,誓也;所,誓辞也,如云“所不与崔、庆者”之类。否,谓不合于礼、不由其道也。厌,弃绝也。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朱熹的这一诠释,重点正在通过考据而补写出了特定的大语境。首先,他交待了:“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接着,他说明了:“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然后,他点出了:“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于是,孔子那一番话的特定语境,包括小语境和大语境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其真实意义也就不难理解。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朱熹是如何通过考据而补写语境的,是如何通过补写语境而立足语境的,是如何通过立足语境而进行语言诠释的,是如何通过语言诠释而阐发义理的,是如何通过阐发义理而彰显孔子之为人的。这是立足语境之语言诠释方法的成功。
五、 建构语言诠释的循环反复法:“终而复始,通贯浃洽”
在经典文本语言系统里,词语组合成为句子,句子组合成为段落,段落组合成为篇章,篇章组合成为文本;它们分层装置,形成了各种层次的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形成了文本内在的逻辑结构和“召唤结构”。所以,进行经典语言的诠释,不仅要从词语到句子、从句子到段落、从段落到篇章、从篇章到文本而详密有序,并且还要反过来从文本到篇章、从篇章到段落、从段落到句子、从句子到词语而循环反复。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利用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对此,古代和近代的东西方哲人学者,都在长期的经典诠释实践中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并且由此出发建构起相应的经典诠释方法。在西方,自《圣经》诠释学发生时期开始,就逐步建构并完善起来的“解释学循环”方法论就是著名的典型;在东方,朱熹创建的循环反复法就是闪亮的典范。且看他的论述: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混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朱子语类》第163页)
读书是格物一事。今且须逐段仔细玩味,反来复去,或一日,或两日,只看一段,则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都到。(《朱子语类》第167页)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元有缝罅,如合(盒)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混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牵古人意来凑。(《朱子语类》第184页)
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绎玩味。(《朱子语类》第189页)
学者观书……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朱子语类》第191页)
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浃洽。(《朱子文集》卷52,答吴伯丰)
大凡为学有两样: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寻个道理凑合将去,得到上面极处,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见得个大体,却自此而观事物,见其莫不有个当然之理,此所谓自大本而推之达道也。(《朱子语类》第2762页)
朱熹揭示了语言诠释循环反复法的原理。第一,他率先指出:经典文本的语言绝不是混沦物事,而总是由字(词)组成句,由句组成段,由段组成篇,它们分层装置,一重又一重,互联互动,却又有缝罅,有相穿纽处,如同充满机关的合(盒)子相似。诠释者应该去抉开,却不能硬去凿;巧妙抉开的主要方法就是循环反复。第二,他特别强调:诠释经典言语系统,在操作上要兼顾两个方面,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循环反复。而所谓自下面做上去就是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基础;所谓自上面做下来就是先见得个“大体”,在初步把握住了大体意向之后再反过来重新观察字、句、段,将把握大体意向作为解析字句意义的参照。这两个方面要相互结合,令其通贯浃洽。第三,他着意启示学者:诠释经典言语,既要自下面做上去,又要自上面做下来,而且还必须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直到通贯浃洽。这就是全面的循环反复法,能够开创语言诠释的新局面。请看他创造的一个实例:
《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集注》:恶,平声。公孙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所以异于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长而能然,而孟子又详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尽心知性,于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气,即所谓体之充者。本自浩然,失养故馁,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盖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与此正相反。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
通看这则注文,学者有如深入堂奥,见到了一片新的境界。它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公孙丑复问孟子之不动心……而孟子又详告之以其故也”。这是引导学者先见得个全章大体意向,在初步把握住了大体意向之后再反过来重新观察本段字、句意义。其作用有二:一是说明全章大体意向,点出其中既有公孙丑复问的要素,更有告子之学的要素,以便读者在熟悉了大体意向之后再反过来重新探究孟子语意;二是贯通全章文意,令语意联属,使得孟子的这一言论与上文相关处的逻辑联系彰显出来,以便读者以其大体意向为参照而循环反复,更加全面地发掘本处字、句、段的深意。
第二段是“知言者……惟孟子为善养之以复其初也”。特点有二:一是诠释深刻,能够引导读者透过语词发掘其深处的哲学思想。譬如,从“知言”,说到“尽心知性”,说到“究极其理”,最后归结为“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足以启人神思。二是既自下面做上去,由释词而释句,由释句而释段;又自上面做下来,把握大体意向之后更为准确地诠释“知言”、“浩然”等词语,乃至通看本章血脉。这正是诠释深刻的根本原因。即如,为什么有必要从“知言”说到“尽心知性”呢?就因为本章前面引用了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言论,就因为本章前面孟子说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这些正是循环反复的诠释成果。
第三段是“盖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这一段是在循环反复之中进行小结,借小结之力又进行更大领域的循环反复,既使阐发出来的哲学思想更为丰厚完整,也使其有所提升,并且站立人格高处将孟子之学与告子之学明确地区分开来。
最后,再将这三段贯通起来以整体考察这则注文,我们就能看到语言诠释循环反复法的逻辑力量和诠释效用。由于它是对详密有序法的新发展,因而更能有力地“自大本而推之达道也”。
本文的研究表明,哲人朱熹感受到时代的召唤,勇于探索新的途径,有力地论证了语言诠释在经典诠释中特有的根本性和指向性,有效地创建了语言诠释的详密有序法、立足语境法和循环反复法,使之融合为语言诠释方法论的整体,并以之与其他诠释方法论密切配合,从而使《四书》诠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使中国哲学诠释学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朱熹建构的语言诠释方法论的主要亮点!
●作者地址:周光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Email:zhgqf2009@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37)
●责任编辑:涂文迁


Construction &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onSishuJizhu(四书集注) of Zhu Xi
ZhouGuangqing(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three hundred years,the scholars always ignored th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suggested by Zhu Xi or underestimated its achievement.Actually,Zhu Xi indeed constructed the new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about Sishu, which becam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on Sishu presented by him.Furthermore,when he created th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he not only discussed the theory questions about the fundamentality and directivit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but also constructed the concrete method of language interpretation,such as the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in order,the method of being established in context,the method of repetition and circulation.He tried to mix both sides,in order to apply to the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Sishu and gained the groundbreaking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 Sishu,furthermore,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cal hermeneutics in China.
Key words:Zhu Xi;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Sishu Jizhu(四书集注)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