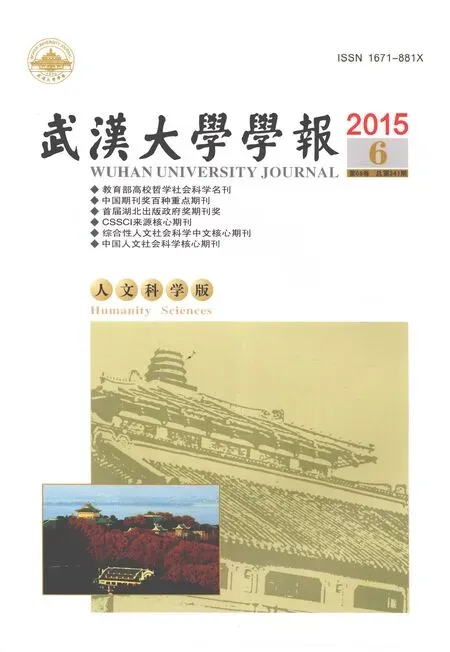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2015-02-21孙杰娜朱宾忠
孙杰娜 朱宾忠
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
孙杰娜朱宾忠
摘要: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交叉地带,当代美国医生作家把医学目视内转到自身,通过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三种叙事类型表达对医学话语规训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其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内省性。在文学空间里,他们质疑并解构指定其社会角色的规定性话语,在演绎新的自我的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文学表现促使新的社会期待的产生。
关键词:医学目视; 医生作家; 叙事类型; 当代美国 除了关于失误的自我反思,自白叙事的另一个为医生的无能感。现代医学虽发达,但不是无所不能。理查德·谢尔泽在其故事集《心灵的确切位置》(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Soul)中写道:
文学与医学的联系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神话里司掌文艺和医药的阿波罗。文学史上也不乏契诃夫及威廉姆斯之类的医生作家。然而医生作家(Physician Writers)作为一个新兴的书写群体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些医生作家,如外科医生理查德·谢尔泽(Richard Selzer)、心理医生塞缪尔·申(Samuel Shem)、内科医生亚伯拉罕·佛吉斯(Abraham Verghese)等,一边行医救人,一边以叙事的方式,如回忆录、诗歌和小说的书写,再现关于疾痛的切身经历。他们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边缘地带自由大胆表达对医学话语规训下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或许比起他们的前辈契诃夫和威廉姆斯等,这些作家在文坛上的印记并不深刻,也许不会久留。但是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频频高调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得不引起重视。医生作家群体的出现和不断壮大推动了文学与医学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发展。传统文学与医学的研究着眼于“文学中的医学”,主要对文学作品中与医疗相关的叙事进行隐喻式解读。当代医生的书写突出了“医学中的文学”,使文学成为医生表达诉求的有效和安全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代生物医学重科技、重理性和轻人文、轻情感的狭隘理念。
一、 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兴起
当代文学与医学的结合既是文学积极参与时代中心话题,逐步回归大众视野的表现,又是医学界为解决自身发展危机而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可以说,两者的结合,既是文学的自觉,更是医学的自觉。众多人文医学学者,如霍尔德·布鲁迪(Howard Brody)*Howard Brody.Stories of Sick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瑞塔· 莎隆(Rita Charon)*Rita Charon.Narrative Medicine:Honoring the Stories of Ill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和阿瑟·弗兰克(Arthur Frank)*Arthur Frank.Letting Stories Breathe:A Socio-Narrat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等认为文学和医学的结合能带来现代生物医学所缺失的人文关怀,并抵制知识权力对人性及身体的控制。人文医学学者特伦斯·侯尔特(Terrence Holt)和苏珊娜·波利尔(Suzanne Poirier)认为医生通过叙事曝光其生存状况,有效揭露权力规训下人的身不由己。菲利斯·奥尔(Felice Aull)和布莱德利·路易斯(Bradley Lewis)则把医生作家比喻为赛义德理论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以医生诗人杰克·库里亨(Jack Coulehan)和医生作家亚伯拉罕· 佛吉斯等为例,奥尔和路易斯指出这些作家通过书写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向外界展示一个个不完美但更真实的自我,从而改写医学体制中技术和理性至上的传统理念*Felice Aull,Bradley Lewis.“Medical Intellectuals:Resisting Medical Orientalism”,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2004,25 (2),p.98.。医生书写一开始便肩负着抵制原有医学话语霸权的责任。
医学话语无所不在的权力通过医学目视(the medical gaze)体现出来。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中,追溯临床医学如何从古典分类医学和症状医学发展而来,构建医学目视的相关理论。古典分类医学强调疾病的超验本质,认为患者的身体遮蔽了其超验性,患者的身体因此得不到正视。随后的症状医学一反古典医学的做法,开始关注病患身体,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个时候的医生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可见的症状,对于身体内部的奥秘所知甚少。而临床医学借助尸体解剖技术而提高了身体以及死亡的可见性,医学目视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体内部。医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并逐步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当权者规范个体行为及监视公共空间的工具。随着医学目视得到行政权力的支持,医生的目视,“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目视,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97~98页。医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消极的存在,而是具有干预能力,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如强行把某些病人隔离开来,或者介入个人的私生活(如吃什么,怎么吃等等)。很多以往被认为最正常不过的身体行为或生理现象,如怀孕和更年期等,现在都早已经被过度医学化了(medicalized)。
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壮大,病患身体乃至整个社会被现代医学的目视牢牢捕获并受到多种权力机制的约束。在医患关系中,由于医者的医学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带来的权力,医者相对来说属于比较强势的一方,他是言说者、观看者和监视者,而病患则处于被言说、被观看和被监视的语言视觉暴力中。现有的研究偏向于强调医学霸权对患者的规训作用,医者往往被当成实践其权力的工具。当代医生书写的大量出现更好地展现了医疗场景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并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权力网中重新探讨医者的身份地位。医者这种强势地位的建立与其职业化过程分不开。通过长期高强度的重复训练,现代医疗体制旨在按照其固有的职业理念把一个个普通学生培养为独立自主和客观理性的医者。其实,古今中外,医生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正面形象无不带着浓重的英雄色彩。这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的美好愿望,也是医学话语霸权一直追求的目标。在理想化了的职业目标的激励下,人文的关怀、情感的表达往往被贴上无能和低效的标签,而高效率的行动、客观理性的态度则受到热捧。受这种隐秘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职业化过程中的医学生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压抑自己的正常情感表达,以期让自己成为集体想象中的那个英雄人物。但是这种培养模式扭曲了医学关怀人间疾苦的终极目标,使医者成了对付疾病的工具,并直接导致了人文关怀在医疗场景中的缺失。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叙事学相关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发展以及现代生物医学的弊端逐步显现,医学界把目光投向文学,希望文学的介入能使在职业化过程中被剥离掉的感情回归到医疗场景中。医生作家希望通过颠覆医者的完美英雄形象抵制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作用,从而为冷冰冰的现代生物医学带来一丝温情和发展的契机。
通过书写,当代医生作家实际上把医学目视内转到自身,从一个多维的角度回顾工作状态中的自我,因而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内省性。这是医生作家对自我多重身份的自省,也是其以局内人视角对现代生物医学的反思。医生书写的内省性在具体作品中通常以几种常见的叙事类型呈现出来。在疾病叙事(Illness Narratives)*在一般情况下,狭义的疾病叙事指患者或者其家属朋友通过虚构或者非虚构叙事再现关于疾病的切身经历。广义的疾病叙事也可以包括一般作家创作的关于疾病的叙事。研究领域,著名学者阿瑟·弗兰克在其《受伤的说书人》(TheWoundedStoryteller)*Arthur Frank.The Wounded Storyteller:Body,Illness,and Eth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一书中,依照常见的主题把疾病叙事分为恢复型(Restitution Narratives)、错乱型(Chaos Narratives)和追索型(Quest Narratives)。弗兰克关于疾病叙事的研究为医生书写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为了更好地从全局上把握医生书写,笔者把医生书写归纳为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三种。
二、 医生书写之自白叙事
特伦斯·侯尔特(Terrence Holt)在评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时指出,“考虑到医学界现在所呈现给大众的,医学话语体系的主流基调似乎充满忏悔之意。”*Terrence E.Holt.“Narrative Medicine and Negative Capability”,Literature and Medicine,2004,23(2),p.318.的确,自白叙事是最常见的叙事类型,几乎所有医生书写都或多或少透露出作者的忏悔之意。这些医生作家自我揭短、自我反思,这也是医生书写被称为医生揭秘文学(Physician Unmasking Literature)的缘故之一。自白叙事颠覆了传统医学话语霸权苦心营造的神圣的医生形象,从局内人的角度,把医生在病痛和死亡面前的无能之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同时细致展现了理想身份与现实间的断裂层以及处在这中间的人的无奈,乃至绝望。大多数自白叙事的前身为发表于相关医学报刊或大众读物上的个人反思,后来才慢慢成集出版。如大卫·希尔菲克尔(David Hilfiker)的《疗伤录》(HealingtheWounds)*David Hilfiker.Healing the Wounds:A Physician Looks at His Work.Omaha:Creighton University Press,1998.和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阿图医生第一季》(Complication)*Atul Gawande.Complications:A Surgeon’s Notes on an Imperfect Science.New York:Picador,2002.和《阿图医生第二季》(Better)*Atul Gawande.Better:A Surgeon’s Notes on Performance.New York:Picador,2007.葛文德的这两个作品均已被译为中文,标题如文中所示。的一些篇章,一开始便出现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纽约客》等刊物中。自白叙事通常由一个个短小精悍、主题明确和反思性强的小故事组成, 每个小故事都可独立成篇。
自白叙事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从内部解构医生的完美形象。医生不是无所不能,更甚的是,医生也有失手的时候。希尔菲克尔在1978年发表了一篇被学界称为“令人震惊”的文章*Nancy Berlinger.“Broken Stories:Patients,Families,and Clinicians after Medical Errors”,Literature and Medicine,2003,22 (2),p.235.。文中,他详细描述了由于种种原因,误打活胎的经历。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字里行间,他把医学目视从病人身上内转到自身,他直面的是一个一直存在却一直得不到正视的问题——医疗失误。他指出,“现代医学对医生有着完美无缺的期望。”*David Hilfiker.Healing the Wounds,p.58.除了失误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这个严重的后果,失误也有损医生完美的英雄形象,因此失误属于不可言说的秘密。但是不得不承认,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人们不愿意正视罢了。
希尔菲克尔一文打破了医学界的宁静,众医生作家纷纷以独特的书写形式向大众展示一个个并不完美但更真实的医者形象。葛文德在其书中通过描述亲身经历,反思传统医疗话语对失误的不包容以及对人性的抑制等问题。哈佛医学院教授杰罗米·格鲁普曼(Jerome Groopman)在其《医生是怎么思考的》(HowDoctorsThink)*Jerome Groopman.How Doctors Think.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7.一书中以大量实例为证,从认知过程等分析医生出现失误的原因及其必然性。他把医学界中一直得不到正视的问题提升到一个理论层面,把医学的不确定性和医生的能力所限展现于大众面前,颠覆了多年以来存在于集体想象中和医学体制中的完美形象。
如果知道自己所做的只是干涉同胞的生活,所行的善充其量也只能和所犯的过相抵,在生死边缘间叱咤风云一辈子的医生们可能会对医学失去信仰之心。但是,他至少可以继续假装无所畏惧,假装死神不会降临,只要人们信奉他的权威。然后,当病人都离去后,他便把自己关在黑幽幽的办公室中捏一把冷汗。*Richard Selzer.“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Soul”,in Selzer,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Soul.New York:Picador,2001,p.18.
谢尔泽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活于理想化职业形象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形象。他笔下的医生大多为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所困。其短篇小说《怜悯之心》(“Mercy”)*Richard Selzer.“Mercy”,in Selzer,The Doctor Stories.New York:Picador,1998,pp.142-146.的叙事者便是一个好例子。故事中,叙事者的医学目视由当前转向多年以前的自己,他回忆曾经为解除癌症患者剧痛而实施安乐死的经历。谢尔泽感兴趣的不是安乐死的伦理问题,而是妄自尊大的医者在死亡和神秘莫测的人体面前的惊慌失措。年轻医生信誓旦旦地对家属承诺可以让病人通过安乐死从剧痛中解脱。最先,他注射致死剂量的吗啡,但病人不死。这促使他有了掐死病人的冲动。然而就在他与病人接触的一瞬间,他和病人有了连为一体的感觉:“我手上的脉搏在他的脖子上跳动,而他脖子上的脉搏撞击着我的手。”*Richard Selzer.“Mercy”,p.145.除去了医疗器具的干涉,最本真的人与人的联系出现了。故事的叙事者面对的不仅是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更让他震惊的是病人在注射大量吗啡后仍不死的强大生命力。而让他最终惊慌失措地逃出病房的是他与病人肉体接触那一刹那间所感受到的震撼力。这是一场垂危的病体与强大到有点自大的医学的较量。叙事者最终的惶恐不安和强烈的无能感透露了医学的有限性,也瓦解了多年建立起来的无所不能的英雄医生形象。医生自白叙事在文学与医学构成的自由空间里,把医者置身于医学目视的视觉暴力中,剖析自身缺陷,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断层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虽然弥漫着体制中人的身不由己,它展现出来更多的是新一代医者的自觉意识以及与传统决裂的欲望和走下神坛的勇气。
三、 医生书写之成长叙事
除了自白叙事,另一个常见的叙事类型为成长叙事。 如果说在自白叙事中,医生作家自我揭短,那么在成长叙事里,他们所做的就是找回职业化过程中所失去的为传统医学话语霸权所摒弃的一切。该类叙事的主人公通常有着强烈的迷失感,而叙事过程也就是找回自我并得以成长的不断尝试的过程。这类成长叙事跟弗兰克的追索型疾病叙事(Quest Narratives)有共通之处。在其《受伤的说书人》中,弗兰克指出,“追索型叙事讲述作者如何寻找更好地接受和处理生病这一事实”, 并在人生计划被疾病打乱的情况下,作者重新建构新的自我和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Arthur Frank.The Wounded Storyteller,p.117.。在医生作家的成长叙事中,作者要追寻的是对自我多重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建构,他必须在客观理智的医者和有血有肉的苦难见证人这两个主要身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叙事通常以医者在日以继夜见证并亲密接触病痛死亡之后的焦虑感和无能感开头,往往涉及叙事者的个人生活经历。长期频繁见证死亡以及自身经历使这些医者见识到生命的脆弱。而书写则让他们自由地抒发对生命的感慨以及对自我的追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追寻以后,叙事者一般能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医生作家迈克尔·斯坦恩(Michael Stein)的小说《白色生活》(TheWhiteLife)*Michael Stein.The White Life.Sag Harbor:The Permanent Press,1998.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主人公凯夫医生(Dr.Cave)少年亡父,他一直对父亲老凯夫之死耿耿于怀,认为其主治医生格雷斯尔(Gresser)有不作为而导致其父亲死亡的嫌疑,尽管后者多次澄清是其父亲自己决定终止治疗的。在行医过程中,凯夫医生遇到一个性格跟他父亲很相似的病人蒂图斯(Dittus)——他们一样“固执、独立、率真、还有点不爱惜自己的身体”*Michael Stein.The White Life,p.130.。蒂图斯在治疗过程中的种种不合作以及最终的拒绝治疗,使凯夫医生处于当年格雷斯尔的位置。
蒂图斯的出现以及他与老凯夫跨越时空的交集,使凯夫医生看到了医学话语权力的规训作用。医学话语权力的实施,不仅需要塑造出富于行动力的医者,更需要一批批温顺的病患。只有严格遵从医嘱、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才是所谓的好病人,才符合集体想象对病患角色的期待。生病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体或生理事件,在现代医学强有力的规训下,它早已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乃至政治事件。病人的不配合既是对病患角色的抵制,又是对医学权威的冒犯,是医疗话语系统中不受欢迎的逆反因子。这也是凯夫医生对其父亲拒绝治疗的事实难以接受的根本原因。英雄儿子希望有英雄般的与病魔斗争到底的父亲。当理想中的父亲与现实中的父亲不相称时,凯夫医生下意识地回避现实。蒂图斯的出现迫使他不得不去思考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对医学权力的拥护和实施使他以及千千万万的医者,习惯于把病人抽象化、简单化和病态化为某种病症或症候,而看不到病服下有血有肉的“人”。凯夫医生写道,“在病历上写下‘胸痛’这一简单的描述动作就像是用了显微镜,它让我看到扩大了的形式和形状,也突出了重点。”*Michael Stein.The White Life,p.35.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显微镜的目镜一样,它也遮挡了我看到更多东西的可能性。”*Michael Stein.The White Life,p.35.对症状的简单高效的描述使医生对病情了如指掌,但同时也引导着医生只关注这一点而忽略更重要的东西,如情感的沟通、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等。最终,当凯夫医生同意蒂图斯出院请求的时候,他也放下了自己对医学权力的执着,对老凯夫之死也有了释然之心,对生命的可能性更有了敬畏之心。
成长叙事中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艾滋病专家皮特·秀林(Peter Selwyn)的回忆录SurvivingtheFall。*Peter Selwyn.Surviving the Fall:The Personal Journey of an AIDS Docto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这也是一个与父亲死亡有关的故事。秀林父亲在其幼年时便自杀身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自杀在几十年前的美国社会乃至今天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懦弱的行为,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污名(stigma)的行为。老秀林的自杀给整个家庭带来莫大的耻辱,并被当成家族秘密而讳莫如深。作为艾滋病医生的秀林,看到艾滋病患者被大众污名化以及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跟艾滋病一样,自杀是一种既给死者又给生者带来污名的行为,它被耻辱、内疚和秘密的色彩所笼罩。”*Peter Selwyn.Surviving the Fall,p.xix.两者都属于不可言说的秘密。但是一味地不言说,一味地遮挡只是一种幼稚的自欺欺人行为,伤口依旧在那黑暗之处淌着鲜血。秀林的成长正是通过对艾滋病及病人的言说,对自己在行医过程中面对生生死死的点点滴滴感悟和思绪的整理以及最终对家族羞于告人的过往历史的公开化中获得的。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只有坦然回首了,反思了,才可能获得前进的动力,才有新的自我的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成长叙事并不都是以大团圆结局。谢尔泽在其《给年轻外科医生的信之二》(“Letter to a Young Surgeon II”)一文中把外科医生称为一直在“探寻身体奥秘”的“追梦人。”*Richard Selzer.“Letter to a Young Surgeon II”,in Selzer,Letters to a Young Docto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pp.51~53.在谢尔泽的故事中,主人公时不时获得顿悟,但是其追索永无止境。因此,其短篇小说一般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结局,更不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完整的感觉。他在接受采访时曾分析了短篇小说和外科手术的众多相似之处,同时他也强调两者的不同:“手术伤口最终需要愈合,但作者的伤口不能愈合。”*Peter Josyph.“Wounded with Wonder:A Talk with Richard Selzer”,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90,27(3),p.322.谢尔泽认为医生在行医过程中接触了太多伤痛苦难,在移情作用下自己也伤痕累累,但他同时也认为这种伤痕为医生作家反思和书写创造了条件,是其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医生作家的成长叙事实际上也是对职业化以及后来行医过程中所遭受的体制暴力的言说,并在这种言说中,实现自我的觉醒。
四、 医生书写之他者叙事
除了自白叙事、成长叙事,第三种常见的叙事类型为他者叙事。菲利斯·奥尔(Felice Aull)和布莱德利·路易斯(Bradley Lewis)在赛义德知识分子理论的关照下,指出在传统医学话语体系中,有这样一类特殊而又高产的作家,他们“要么是地域上要么是文化上的流放者”*Felice Aull,Bradley Lewis.“Medical Intellectuals:Resisting Medical Orientalism”,p.99.。 这些医生作家背景一般比较特殊,他们有的是同性恋者,有的来自少数族裔群体,或者两者皆是。因为种族、性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医生作家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成为行走在各种文化边缘的“他者”。如古巴裔医生作家拉斐尔·坎普(Rafael Campo)同时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在相对开放的美国社会,医生作家独特的背景也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另外,有些作家如印度裔医生作家佛吉斯、女同性恋作家凯特·斯坎那尔(Kate Scannell)及坎普从事的是带有社会污名(stigma)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艾滋病人所遭受的社会污名化让这些医生作家联系到自身的特殊背景以及自己为融入主流社会而做的种种努力。但是正是这些医生作家承担起了医疗系统中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通过讲述在文化或地域的他乡追寻归属感的他者故事,这些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医生作家真实反映了边缘群体的生存境况。正如坎普在其散文集《康复之诗》(ThePoetryofHealing)中所说,“作为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我曾经幻想我的白大褂可以掩盖、甚至漂白我那不是白色的皮肤;我还幻想医学术语可以有力驳斥质疑我的第一语言的所有问题。”*Rafael Campo.The Poetry of Healing:A Doctor’s Education in Empathy,Identity,and Desi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p.18.但是他后来的行医经历一步步打破了他儿时的憧憬,也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以及千万艾滋病患者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他者地位。
跟坎普很相似的另一位艾滋病医生作家是佛吉斯。其回忆录《我的国家》*Abraham Verghese.My Own Count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便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外国医学生(International Medical Graduate)在异域他乡的美国构筑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故事。佛吉斯的异域背景给他的职业生涯打上不光彩的烙印,他在美国求职过程中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最终只能选择本土医学生所不屑的传染病科,并来到美国南方一个保守的小镇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与艾滋病人尤其是当地的男同性恋患者接触过程中,佛吉斯为这些人的边缘地位以及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所触动。对自身种族“他者”(the ethnic other)角色的焦虑感驱使他把自己和这些边缘人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使他得到病人的信任,并为他积累了事业发展的资本。但是佛吉斯梦寐以求的是进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去,而不是成为边缘社群的一员。同时,自己身边病人的大量死亡也迫使着佛吉斯另寻出路。正是通过《我的国家》的书写,佛吉斯真实地把这种矛盾的心态、尴尬的处境和对前途的迷茫生动地展现出来。他的书写不仅仅为失声的艾滋病人,尤其是男同性恋患者呐喊,同时也为跟他一样在文化边缘上苦苦挣扎的被主流社会排斥的他者诉说。
佛吉斯便是凭着《我的国家》进入到畅销作家行列,该回忆录后来还被拍成电影。的确,相对于之前两类叙事类型,他者叙事的阐释空间和在读书界及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也比较大。他者叙事以医疗事件为切入口,在性别和种族等政治话语构成的大网络中讨论医疗体制的权力运作以及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对这种话语霸权的抵制。他者叙事本身关注的话题决定了它可以更好地走进大众视野。
五、 小结
需要指出的是,自白叙事、成长叙事和他者叙事这几类常见叙事类型之间也有重叠,有的叙事同时拥有这三种叙事类型的特点,如《我的国家》等。这三种叙事类型虽然形式各异、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表达了当代富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作家对自己利用医学权力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忏悔之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职业化以及行医过程中失去的自我的哀悼之情。正是在文学与医学的边缘地带的深刻内省以及书写,医生作家抵抗了传统医学话语权力的规训,并开始了构建新的自我的征程。
通过医学目视的内转,医生作家获得对生命和人性的顿悟,实现自我意识觉醒,而书写则为这个艰难的内省过程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然而,作为体制中人以及现代医学体制某种意义上的受益者,医生作家的自我书写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毕竟他们把一些所谓的行业秘密公诸众,这对医生的上帝形象是一个颠覆,也可能增加大众的不信任感。但是这种躁动是整个社会重新面对一个长久以来被完美化了的职业形象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从理想回归现实之痛。医生书写的意义在于其敢于向权力说真话以及自发走下神坛的勇气。通过对规定性话语进行楔入式解构,医生作家书写向外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讲述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尝试着建构富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新的自我。可以说,当代医生叙事正是以书写的方式为改变规训性话语控制下的人的生存状况所采取的一种创造性措施。
●作者地址:孙杰娜,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朱宾忠,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herrbnzhngzhu@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WW009);教育部第48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责任编辑:何坤翁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