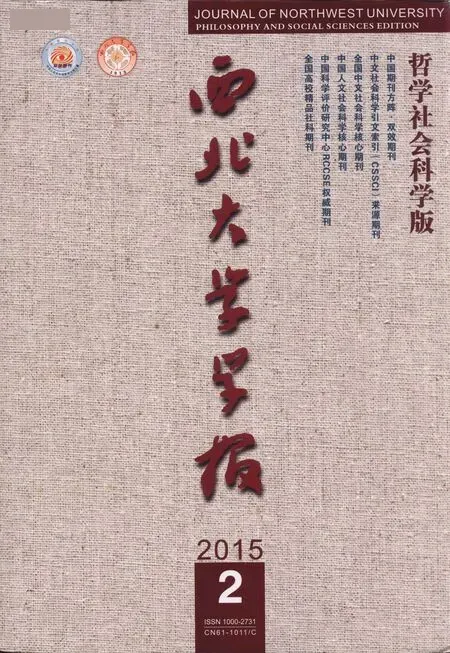古籍目录史部学术源流与古代史学嬗变的历史路向
2015-02-21赵涛
赵 涛
(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开封 475001)
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认为目录学与学术史理应结合起来,以收“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1](卷1《互著》P966)之效。古籍目录与古代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古籍目录著录历代典籍,能够反映历代典籍的流传、存亡状况,并推衍古代学术源流、叙列学术短长;另一方面古籍目录的类目和大小序及提要等要素,能够反映历代思想文化和学术旨趣,因此古籍目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颇具规模的学术史。本文通过对古籍目录史部源流的研究,分别梳理古籍目录史部类目、大小序、提要三要素的历史形成过程,以期勾列出古代史学学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趋向,进而揭示古籍目录史部对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
一
中国历代古籍目录分类法从六分法始,历经五分、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分类法,至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一统天下,经历了较长的嬗变过程。与其他分类法相比,四部分类法影响深远,居于古代图书分类正统地位,体现了儒家的图书价值观念。代表历史典籍的史部,也有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历史典籍的分类,源于西汉末刘歆《七略》,它是古籍目录六分法的肇始。《七略》类目分六大类,“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2](卷30《艺文志》P1715)《七略》分类中,历史典籍未能独立成类,没有专立史略,所著录史书如《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基本上附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其他如《高祖传》《孝文传》等著录于诸子略儒家类;《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著录于数术略历谱类。与其他类目相比,《七略》中著录《六艺略》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三十二篇;《诸子略》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历史书籍仅三十四家,一千三百八十四篇。从数量上看,史类典籍不占优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先秦至西汉史学尚不发达,历史书籍数量不多,历史典籍还不足以与其他类目相抗衡;另一方面汉代经学繁盛,在学术领域占统治地位,导致一些学术依附于经学、与经学相混,史学就呈现这种态势。其实,史学与经学的这种关系,源于《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曾以此为教材教授弟子。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定为一尊,儒家典籍上升为经,《春秋》列入六经。由于《春秋》本是史书,且未发展到体裁多样、类目完备的地步,故《七略》将史书附于春秋类,或者将一部分史书列入诸子略、数术略。《七略》对历史书籍的归类,反映了先秦至汉代史学学术状况,以及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水平。
魏晋南北朝在古籍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东汉以来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加之自汉代儒学崛起后,经学日趋繁琐,并与谶纬相混,使经学走向神学化,失去了生命力。农民起义、群雄乱争结束了汉朝的统治,也打破了经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学术文化在这一阶段出现此消彼长、纷繁多彩的局面。目录学随之呈现出复杂状况,一方面以《七略》为代表的两汉图书分类法逐渐不适应学术思想的发展,四部分类法在酝酿、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分类法不尽合理,目录分类法有复旧的趋势,但最终确定了四分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史部目录也必然随着目录学和史学学术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此期史学有了很大发展,私人修史风气很盛,历史书籍已具备多种形式和体裁。据《隋书·经籍志》载,此期所存史部书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三十四部,一千三百八十四篇的数量相比,部数是后者的二十四倍,篇卷数是后者的九倍。
魏晋时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体系中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晋秘书监荀勖依据魏秘书郎郑默《中经》,更著《新簿》,创设四部分类法。荀勖在《中经新簿》中“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3](卷39《荀勖传》P1154),分图书为甲、乙、丙、丁四部。荀勖未立各部名称,只是以甲、乙、丙、丁区分四部,性质相当于经、子、史、集。其中丙部为史学类,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自荀氏始将史书从经部析出,史部书籍正式单独为一类。由于晋以前的诗赋作品有所佚失,历史和文学两类书籍数量少于甲、乙二部,为均衡四部书籍数量,荀勖将包括经、史等各类典籍的汲冢书附入丁部(即文学类),将属于类书的皇览簿归入丙部(即历史类)。这一分类法等于承认了史学是学术中的一个独立门类,表明史学取得了足以与经学、诸子学、文学并举的地位。至东晋,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依《中经新簿》将群书“以类相从,分作四部”[3](卷92《李充传》P2391),因荀勖四部之法,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将荀勖经、子、史、集之次序易为经、史、子、集。至此,以经、史、子、集为次序的四部分类法遂一定而不可移易,史称“秘阁以为永制”[3](卷92《李充传》P2391)。虽然史学此时已独立成类,但在荀勖的分类中仅位居第三,且一部分史书归入集部,一部分属于集部的书籍划入史部。而且李充因其数量少未能再分细目,只是以甲、乙、丙、丁部次。可以说,尽管此时历史学术发展仅仅是从自发、被束缚的状态向自觉、独立发展的开始,但它毕竟开创了史学自主发展新时代。
虽说四部分类法在魏晋发生发展,但受《七略》六分法影响的分类法并未消弭。自晋至隋,以《七略》为代表的分类法一再出现,与四分法并行。如南朝宋秘书丞王俭的《七志》以及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等,就在《七略》分类法基础上有所发展。虽然王氏《七志》和阮氏《七录》未占据目录分类法的主流,但这两种目录对史籍的分类确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王俭在编成《元徽四部书目》之后,“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4](卷46《序下》P1678)。《七志》分类,基本沿袭《七略》,只是在个别地方有所不同。其分群书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其中《七志》的经典志与《七略》的六艺略内容相同,包括六艺、小学及史书。王俭处身于史学兴盛时代,目睹目录中设立史部的先例,他本人也参与政府四部书目编目工作,却“祖述刘氏,亦步亦趋”[5](P155),循《七略》旧规,将史记、杂传并入经典,足见其“志在复古,书本九篇,强分七部,以六朝之著述,合西汉之门类,削趾适履,势所不行”[5](P161)。阮孝绪“斟酌王、刘”[6](卷66《七录序》P736),参考《七略》和《七志》,吸取目录学的新成果如五部目录《文德殿书目》等,以一人之力编成《七录》。《七录》分七部:“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7](卷32《经籍一》P907)其中纪传录为史学类。史部离经而独立虽始于荀勖,但细目的厘定却始于阮孝绪,后来《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分小类的名称,基本参考《七录》而稍加变通。《七录》纪传录对后世历史典籍类目分类影响很大,史学此时独立成类已经不容置疑,并按照自身内在理路向前发展。
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总结魏晋以来图书分类法,沿用荀勖、李充等开创的四分法,将群书分四部,正式冠以经、史、子、集,标志着自荀勖所创的粗疏的四分法走向成熟,自此终结了魏晋以来古籍分类相互竞争的局面,开始了以四部分类法为正统的新阶段。《隋书·经籍志》中的史学典籍分类所引起的变化,可说是根本性的:它把《七录》中的纪传录改为史,确立为四部中的史部;其史部中的类目也是在《七录》纪传录基础上进行细分,分群书为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此后的宋、元、明、清历代目录中史部类目大都遵循《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类,只是有所增益。如后晋刘昫等编撰的《旧唐书·经籍志》,分类与《隋书·经籍志》大体相同,其史部只是略有变更;宋人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与《旧唐书·经籍志》基本相同。至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则博采众家分类法之长,将四部分类法推向高峰,其史部为十五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下又根据书籍的性质、数量、年代等具体情况再分为属。《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概貌性地展示了中国史学之源流,较完备地总结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史学发展。
代表史学典籍的史部在古籍目录分类演进中,从最初分散历史典籍于目录各类之中,逐渐发展到专门集中于史部,真实反映了历代史学变迁的轨迹,也表现出目录学家对史学发展变化的客观认识过程。
二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目录史部类目的历史嬗变中,其学术源流在目录史部大序、小序中也得以凸显。古籍目录中的大序、小序,肇始于刘歆《七略》中的辑略。刘歆首开撰写目录大序、小序,使得目录不仅著录典籍,还能考辨学术源流,具有了学术史的价值。后人对此推崇并起而效法,使古籍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世代传承。历代王朝不断更迭,史学学术也随着时代发展演进,每一时代目录学家对史学学术的看法也发生着变化。古籍目录史部中大序、小序对这些变化有着鲜明的反映。
中国历代都重视历史,史学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特殊的地位,《隋书·经籍志》就认为:“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7](卷33《经籍二》P956)但在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权威的儒家对《春秋》的看法,影响着史学学术思想观念,也影响着目录学家对史部学术源流的看法和态度。
春秋至汉初,礼乐崩坏,诸子勃兴,百家争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发展了西周以来由贵族垄断的学术文化。至汉代,儒家思想又汲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营养,逐步完善起来。汉武帝时期,国家在政治上达到高度统一,与此相适应,在思想上也提出了统一要求。汉武帝接受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儒家确立了独尊地位,儒家经典成为法定的官方学术。此期由于代表儒家的经学的深入影响,也由于史学本身不发达,处于附庸、从属经学的地位。从汉代人对《春秋》以及有关历史著作的看法中,就能看出史学地位在当时之低。《春秋》本是春秋时各诸侯国国史通用的名称,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墨子·明鬼》经常使用“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燕之《春秋》”之称[8](卷8《明鬼下》P331-333)。但汉代却流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司马迁就认为:“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9](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7)事实上,《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孔子并没有作《春秋》,至多是为教授学生,做过整理或解说的工作。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春秋》与其他儒家典籍被列为经典,经过经学家的穿凿附会、阐发微言大义,《春秋》成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治世之书[10](卷6《滕文公章句下》P155)。司马迁不是经学家,但作为史学家,其说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反映了汉代人对《春秋》的看法。《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序认为:“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2](卷30《艺文志》P1715)强调《春秋》是经,《左传》也只是解经之“传”,历史著作是为经学服务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东汉以来社会政治思想的冲击,儒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学术思想界在此期出现新的变化,史学也渐进觉醒,开始挣脱经学的束缚,显出自觉独立发展的趋向。《隋书·经籍志》在唐代初期修成,但实际上反映了东汉至隋这一历史阶段图书典籍的留存状况及其学术源流。《隋书·经籍志》不仅奠定了古籍目录分类的基础,也发扬了《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在每一类后都撰写一篇序,叙述其源流。其中史部有一篇总序、十三篇小序。史部总序认为:“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也。”[7](卷33《经籍二》P992)总序叙说史官所应具备的学识、才能以及所担负的职责,较之前代单纯的“左史记言、右史记行”说,要深刻得多。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序比较,此时史学已经脱离了经学,发展成为种类完备、有着独立体系的学术门类。在史官的人选问题上,也有了特定的、多方面的要求,以适应史学发展之需要。其古史类序认为:“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7](卷33《经籍二》P959)汉献帝命荀悦依《春秋左传》体例作《汉纪》,于是一度沉寂的编年体史书复出。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发掘的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史记,体例如《春秋》。此后,一些学者们认为,《春秋》之编年体才是古史之正法,故多依其体例修史。古史类序叙述了魏晋以后,编年体史书再度盛行的历史过程,源流清楚,特点突出。其他类目的小序,如职官、刑法、地理、谱系等,无不源流清晰,有各自鲜明的类别特点,各类之间绝无含混。《隋书·经籍志》的小序,对每一类史书的起源、性质、特点等概括准确,对当时史籍的学术流别也有全面的概貌描述,表明古代史学至此已经走向成熟,史学已经脱离经学,成为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一门学术。此后唐、宋、元、明,无论官修目录还是私人藏书目,其史部大、小序中的史学观念更加纯粹,史学思想发展越来越趋于理性。
清编《四库全书总目》对史学的看法,基本上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观念一脉相承,但也有新的发展。其史部总序认为:“首曰《正史》,大纲也。”[11](卷45《史部总序》P397)对史学的认识,较诸《隋书·经籍志》达到了新的高度。首提正史作“大纲”,是因为在古代历史书籍中,正史的地位最尊贵,它们反映各个朝代的正统历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通过帝王将相、臣僚勋贵的纪、传,反映历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军事行动,是古代社会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体现了古代社会的正统史观。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记》,就有了正史。司马迁以后,仿纪传体的史书代有续作,相沿不绝。古代史籍中的所谓二十四史,就是古代由官方明确认可的正史。《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史学思想进行总结式的概括,表明其史学认识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
但是,儒家的历史观念,毕竟对史学产生了很深影响,以致史学始终没有走出经学的阴影。《汉书·艺文志》所谓“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2](卷30《艺文志》P1715);《隋书·经籍志》所谓“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7](卷33《经籍二》P992)等等,无一不从儒家立场阐发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亦同样强调历史“资考证”的作用,并以经与传的关系,说明史学与经学的关系、正史与其他类别史书的关系,尤其强调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11](卷45《史部总序》P397);对正史之外的其他史书之所以“兼收博采,列目分编”,是由于“有裨于正史”,可资考证,因此才“择而存之”[11](卷45《史部总序》P397)。归根结底,认为历史还是为经学服务的。
古籍目录史部大序、小序在其不同时代的发展中,能够概述史学学术,考述史学源流,论述史学高下,理析出古代史学学术从经学附庸到独立门户、从自发状态向自觉发展的历史发展流变过程,可谓简明的古代史学史纲要。
三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与变迁的轨迹还在目录史部的提要中得到显现。古籍目录提要也称为叙录、书录、解题,源于西汉末刘向的《别录》。刘向每校一书,便撰写一篇叙录,目的是辨析校书中之讹谬,叙述作者生平行事,概括一书大意。《别录》开创的叙录方式,被后人起而效法并有所发展。提要内容涉及古代典籍的各个方面,与所处时代史学思潮及目录学家的史学观念密切相关。对同一部史书来说,不同时代的学者尤其目录学家评价它时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而其提要最能反映出历代史学思想的异同。限于篇幅,在此仅以巨著《史记》为例以见其状。
汉时《史记》没有固定书名,初始名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传”,也叫“太史公”。而“史记”原是史籍的类称,如《汉书》记载:“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2](卷62《司马迁传》P1715)“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2](卷33《经籍二》P2737)等等。汉以后至唐初,学界将《史记》称太史公书,也称史记,同时对其他史书亦称史记。唐初官修《隋书》正式将其定名为《史记》,标志其得到官方认可并确立了史学权威地位。《隋书·经籍志》载:“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7](卷33《经籍二》P953)在官修史书中首次将《史记》与《汉书》并列,从此《史记》之名正式确立。从西汉《史记》产生到唐代初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过程后,《史记》才有了正式名称和与其相配的地位。
目录学家余嘉锡认为:“叙录之体,源于书叙。”[5](P38)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略如刘向、刘歆父子所作书录,从中可以看出汉时对史学的看法。其自序曰:“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9](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5)这是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临终之时的嘱子之语。司马迁先人在虞夏之世就以天官之职显名于当时,到了周代,仍掌斯事,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但司马父子仍忧心“废天子之史文”,认为史书应“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9](卷130《太史公自序》P3297)。然而在汉代,统治者认为《史记》离经叛道,蛊惑人心,一直没有给予公正评价,以致学界不敢为之作注。东汉时朝廷要求对《史记》进行删节和续补,诏杨终“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12](卷47《杨终传》P1599)。所以尽管西汉时刘向、扬雄等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2](卷62《司马迁传》P2738),但因司马迁著书“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2](卷62《司马迁传》P2738),所以《史记》仍被指责为对抗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
魏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削弱,史学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走向自觉发展道路,受此影响,此期对司马迁和《史记》有了一些积极的评价。如晋代学者华峤曰:“迁文直而事核。”[12](卷40《班固传》P1386)张辅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3](卷60《张辅传》P1640)。他们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虽然很高,但依然没有认识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事实上,在魏晋时期,学界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任何一家都会这样评骘。如刘勰评价陈寿:“陈寿三志,文质辨洽。”[13](P171)西晋人评价华峤:“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3](卷44《李峤传》P1264)评价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3](卷82《干宝传》P2150)总之,魏晋时期学人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唐初依然是这种状况:“《史记》传者甚微。”[7](卷33《经籍二》P957)“汉晋名贤未知见重。”[14](卷首《序》P2)至中唐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学界才对《史记》给予高度重视,作出积极评价。
宋时,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对《史记》评介才与前代有了明显区别。针对班固对司马迁的讥评,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认为:“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15](卷5《史记》P176)否定了包括班固在内汉代人对司马迁和《史记》的错误看法。稍后与晁公武同时代的目录学家陈振孙,对《史记》给予肯定和褒扬:“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皆前未有其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16](卷4《史记》P97)宋时众多理学家对儒学进行阐述、完善,形成了理学思想,对社会各个方面均有深刻影响,其史学观念和思想也对史学批判取向影响极大。与晁、陈二氏同时代的朱熹对司马迁评价极高,认为秦汉间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其文尚“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而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17](卷70《读唐志》P1281),肯定司马迁作《史记》于史实“无妄作”,“《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18](卷139《论文上》P3298)集理学思想大成的朱熹如此评价司马迁与《史记》,无疑渗透着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宋元及以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声望日隆,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籍源源不断出现。至清时,《四库全书总目》分别对各个时期关于《史记》的观点、结论进行缜密辨析,对汉代以下《史记》的整理、研究作了全面总结。关于对汉、宋时期对《史记》不同看法,《四库全书总目》辨析说:“《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免牴牾。”[11](卷45《史记疑问》P400)此说符合历史事实。又认为:“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之凿。而订讹砭漏,所得为多。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牾。”[11](卷45《读史记十表》P400)这是以清代汉学的立场、观点,考察汉、宋对《史记》的研究状况,对《史记》作出的总结性评价,其结论烙有清代的学术印记。
由此可见,古籍目录史部的提要不但能使我们了解一部史学著作的流变过程、著述内容、作者生平及人品学风等情况,还能使我们一睹不同时代史学观点、思潮之风貌。
结 论
史学这门传统学科的发展与变迁,与古籍目录史部发展密不可分。二者的关系可以从目录史部类目、大小序、提要的流变中觅其踪迹。古籍目录史部分类,随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产生发展而流变。《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的确立,是目录分类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史部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类目划分标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史学的自主发展。同时,古籍目录史部的大序、小序也反映着古代史学学术发展变化,显现了古代史学从经学附庸到自觉发展的历史过程,彰显了史学发展的活力。古籍目录史部提要也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学术的思想倾向和史学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转折的。当然,古籍目录史部与古代史学这种互动关系,也折射出以儒家为正统地位的学术思想和等级观念,必然要维护古代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
[1]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萧统.文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5.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吴毓江.墨子校注[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孟子.孟子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司马贞.史记索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朱熹.朱文公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8]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