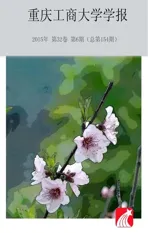《三国演义》成书与传播的接受史解读**
2015-02-21张红波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400031
张红波(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400031)
《三国演义》成书与传播的接受史解读*
*
张红波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重庆400031)
摘 要:《三国演义》的解读往往伴随着种种疑虑与困惑。困惑的根源在于作品本身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通常表现为作者意图与“内视点”之间的分歧。分歧的来源一部分出自于作者的疏漏,更多情况是由于作者的不得已而为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三国演义》“世代累积型”成书方式、版本演变、评点本的主观导向及其他文学样式对民众《三国演义》印象形成的重大影响等因素。作品文本及解读过程中“众声喧哗”局面的出现正是《三国演义》成为经典的一个缘由。在“众声喧哗”的背后其实一直也蕴藏着作者与传播者价值建构的努力。
关键词:《三国演义》;儒道精神;人物评价;价值建构
在面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时,除了“尊刘抑曹”等少数已经形成共识且不易更改的阅读体验外,很多读者都会存在大致相同的疑惑。传统话语语境中的人物评价与自身的阅读体验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甚至可能会出现两种看法完全相反的现象。如对曹操、宋江的评价,对刘备的看法,对诸葛亮与关羽的评价,对李逵的认识态度等。与此相比更为致命的是,对于作品思想倾向的评价同样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如对《水浒传》主题的归纳就存在着“忠义说”与“诲盗说”等尖锐对立的认识。这种差异的出现甚至说是必然的。这既来自于时代风尚的变异所导致的认识差异,更重要的,其实是作品本身话语体系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给读者带来的阅读自由度所导致的。
作品本身话语体系的模糊性现象长久以来都被不少文学批评家所关注。20世纪初期,俄国的巴赫金已经提出了所谓“对话”和“复调”的理论。他认为:“在一部作品中能够并行不悖地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各自都得到鲜明的表现而绝不划一,这一点是小说、散文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1]266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更是能够最明显地体现这一特点。这种类型的语言表现类型多样。在我看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作品中惯常用的所谓后世文人的诗词;二是作者本身描写的笔墨中显露出的倾向性意见;三是作品中其他人物的语言。借助这些语言,作者可以和作品中的叙述人保持某种距离,增加作品本身倾向的模糊性,从而给读者以更加广阔的解读空间与自由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距离甚至是区别小说成功和成熟与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准绳。巴赫金也指出,对话特质并非单纯表现为作品中人物的对话,而是指“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互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4-5。这种不同而又相互独立的声音和意识就是所谓的“众声喧哗”。与后世个人独创型小说不同的是,《三国演义》等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众声喧哗”多数并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甚至更多情况下可以看成是作者创作过程中所出现的疏漏和不得已而为之所导致的。这里的作者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小说的创作者如罗贯中等人,也包括版本差异的制造者以及其他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扮演者。
我们可以先从文本的解读去理解《三国演义》的模糊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道思想的交锋及其倾向的模糊性。《三国演义》以大量的笔墨渲染及歌颂了以刘备和诸葛亮为代表的积极进取型的道路。这种笔墨破坏了全书的叙事节奏,同样也赢得了一种美感,以及史书平实庄重叙事所不具备的崇高感。即便如此,作者并非全然沉浸于儒家思想中,他利用一些不甚容易察觉的事件来消解儒家的神圣与绝对的优越感。这点在代表世俗权力抗衡的魏蜀吴三方均有体现。曹操平定汉中,大败孙权,个人权势与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此时,左慈却在轻描淡写中戏弄了权势煊赫的曹丞相,而曹操却对其无可奈何。如果说,左慈更多的是用一种宗教启发式的方式戏弄与启迪曹操放弃世俗权力的话,那么,于吉与孙策间的较量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博弈。在世俗的层面,于吉无疑是处于下风的。他作为江东的道士,隶属于孙策的政权。即便众多大臣百姓为之求情,并且已经完成孙策布置的祈雨任务,他依旧难逃被杀的命运。但在超越世俗的宗教层面,孙策却是最终的失败者。于吉利用冤魂不散的方式纠缠着孙策,激怒孙策,导致其最终英年早逝。与其说是于吉的鬼魂作祟,倒不如看做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借助这种方式赢得儒道的平衡。并非站在所谓正义对立方的魏吴的君主才会受此戏弄,如果仅仅如此,道家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与儒家并无二致。何况站在历史的时空中去评价,魏蜀吴本身并无高下正邪之分。刘备一贯的为国为民方针,匡复大汉的口号至少在他不顾一切地讨伐吴国的时候已经失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经丧失理智,骄傲蛮横的刘备,他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众臣的劝谏,执意伐吴。隐者李意用先知的方式警示刘备,用一种故意傲慢的方式消解了世俗的权力。刘备虽然不相信,但最终的结局却宣告了李意的胜利,也宣告了作品叙事中对世俗权力的又一次解构。综观《三国演义》,儒道交锋并无明显的胜利者,更多的是取得了一种平衡。
儒道思想的交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出世与入世之争,这种争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隐性的,但在某些环节却是异常强烈的。其实,整部作品所透视出来的“人命”与“天数”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出世与入世的哲理化体现。当然,这种悲剧性的结局更多是建立在作者先入为主的情感取向上的,而作者的这种情感取向又来源于世代累积型成书方式的材料取舍等因素。在作品中,这种抗争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更明确地说,是体现在对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的态度上。作为《三国演义》重点渲染的一条主线,刘备“三顾茅庐”在整个作品体系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长达四五回的篇幅中,作者完成了理想君臣模式的塑造,基本完成了刘备、诸葛亮形象的塑造,预示了后文发展的方向。从作者的叙事态度上着眼,诸葛亮的出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些描写的同时,作者利用“内视点”,消融了几乎众口一词的和谐性。作品首先借司马徽之口说出了“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解了诸葛亮出山的价值。同时,作者不断地利用描写在强化着入世与出世的斗争。在刘备访诸葛亮的过程中,他先后遇到了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二人一方面高唱“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境。但同时,二人却以“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为理由极力推辞刘备的聘任。在元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及明传奇《草庐记》等作品中,诸葛亮以远游而躲避刘备的寻访,原因就是算准了刘备无帝王之命,这固然是民间叙事的套路,但多少却说明了诸葛亮出于功利心理在考量着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不仅仅是诸葛亮,即便是刘备自己也曾无意中表达出对隐遁山林的闲逸生活方式的向往。他跃马过檀溪之后,遇到了悠然自在的牧童。其实,檀溪的两头本身就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入世与出世所遭遇的不同处境。玄德深沉的一声“吾不如也”的叹息多少就能表达出作者的倾向。
其二,《三国演义》更为明显的“模糊性”表现在人物的评价体系上。为了凸显诸葛亮“古今第一贤相”的形象,作者不惜更改陈寿《三国志》中对其“短于将略”的评判,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无往而不胜的“近乎妖人”的形象。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利用其他的情节描写来消解诸葛亮的神性,以保持描写的平衡。诚然,诸葛亮似乎可以玩弄周瑜、曹操于股掌之中,可以屡次打败司马懿,但最终还是奈何不了司马懿,究其一生也无法完成攻取中原,匡复大汉的重任。这其中固然原因众多,作者未尝不是在利用这种结局消解诸葛亮的神性,以达到作品整体美学风格的一致。另外识人的失败也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诸葛亮的神性,马谡与魏延,这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给诸葛亮带来了很多不利的评价声音。作品本身就用“后人有诗曰”:“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来表现刘备与诸葛亮在识人方面的高下比较,也隐晦地表明了对诸葛亮的批评。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众声喧哗”的状况。
刘备的形象塑造也存在着这种问题,刘备是时所公认的“仁者”,作者以陶谦三让徐州、带领百姓过江、不取荆州等情节来烘托他的仁义。同时,作者也不忘用其欺骗刘璋、借荆州而赖着不归还等情节来消解这种仁义。并且作者在作品里面也在用他者的话语来消解刘备的仁义,从曹操的谋臣荀、郭嘉等人到东吴的张昭、周瑜等人,再到刘璋的部下黄权、张任、王累等人,无一不提到刘备表面仁义,实则为枭雄行径的看法。此外,在攻取西蜀的过程中,刘备曾与谋臣庞统起过一次冲突。庞统以“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来反驳刘备的看法,虽然最终君臣和好,但无疑却是从内部消解了刘备的“仁义”。何况刘备曾从事事与曹操相反方可取天下之论告诫庞统,这就更使人相信刘备的种种仁义之举不过是谋取天下的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从谏如流,是刘备与诸葛亮关系存在的一个基础,但到了后面,他为报仇,置诸葛亮、赵云的意见于不顾,一意孤行,结果使得积蓄了数十年的蜀中精锐消亡殆尽,更使得他一直所追求的“复汉”大业如镜中月、水中花,永远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并最终为晋朝一统三国埋下了伏笔。
在《三国演义》中,争议最大的人物形象莫过于曹操,暂且撇开后世对曹操形象的争论不提,单纯从作品本身中去看,模糊性也是非常大的。对比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清初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就能看到内中很多变化的印迹,这点在后文再详述。我们从排斥贬低曹操最为明显的毛本入手,同样能感受到“众声喧哗”的局面。作品通过大量事例在强化曹操的奸诈,同时还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言辞衬托着这个印象,“后人诗曰”就多是此等倾向。但作者同时也通过很多事件在模糊着我们的看法,且以曹操征伐马超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情感特征来分析。曹操在此次战役中最初极为狼狈,“割须弃袍”,这点被后世的文人屡次提起,津津乐道。如元杂剧《阳平关五马破曹》等,明末清初传奇《青虹啸》等,还有京剧作品《反西凉》(一名《割须弃袍》),川剧《战潼关》等,都是以此为背景的。但《三国演义》中的描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描写曹操失败之惨,另外一方面终南山隐士娄子伯却为曹操出谋划策,渭南县令丁斐解围,杨阜母亲大骂马超为贼,要儿子相助曹丞相破贼。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文章的情感取向。此外,曹操征伐徐州时,发誓灭城,借灭火与救火之名诛杀300余官员等,这都是曹操争霸过程中的罪证;在另外的场合他却告诉老百姓躲上山,免得被兵士抓住修筑工事,又体现了他爱民的一面。他者如割发代首,败境中大笑,原本也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文本的此类描写只会加重价值判断的模糊性。
对历史人物称谓的选择是史书“春秋笔法”的一个表现。同类人物的不同称谓原本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取舍。陈寿《三国志》对于魏蜀吴三国的立场固然可以从篇幅、感情等方面入手去分析,所谓魏武帝、先主、孙权等称谓中也足以表达其历史立场。作为与史书纠缠不清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继承了这些表现方式。还是以曹操为分析对象,作为作品大力谴责的对象,我们在文本中多处能看到“曹瞒、奸贼”等字样。如陈琳以檄文方式痛骂,祢衡击鼓痛斥,吉平、董承、耿纪等人当面怒斥,此外孙吴、蜀汉集团的君臣们也均以奸雄、国贼等身份视曹操,这些构成了作品对曹操的基本情感取向。但即便如此,文本还是留下了很多貌似疏漏的情节。单纯以谴责立场最为坚定明显的毛评本《三国演义》目录为例,提及曹操的目录称谓及次数如下:曹孟德(孟德),6次;曹操,15次;贼、阿瞒,7次。曹孟德似乎尚带有尊重之味,一如刘玄德之称谓;曹操是最为平实的称谓,于中并未渗入太多感情色彩;阿瞒或(国)贼称谓是坚定的反对立场,但这些称谓也并未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这大致就能见出作者较为含混或者说是不好处理的矛盾态度,在文本的“诗曰”等方式中同样也能看出这些痕迹。“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等闲施设神仙术,点悟曹瞒不转头”,前者喟叹曹操无法识破司马家潜在的威胁,后者微讽曹操权欲熏心,不能自拔。“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谋壮志又图南”,这种表述方式是不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理性叙事。“曹公钦义烈,特与建孤坟”,此类则为明显的赞扬立场。三个层面均有不同的描写,从而构成了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评价体系。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中的后人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把这种矛盾的评价集中于一首诗中,更加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模糊性的特点。
人物评价的模糊性不仅仅单纯地表现在对曹操等人的看法不同,它涉及的是作者价值体系的混乱或者游移。尤其是作为毛宗岗话语体系中的“僭国”集团的代表,无论是嘉靖本抑或是毛评本,情感倾向体现的模糊本身就表明了作者想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情感绝非我们原本想象的那般简单,不是决绝的“非此即彼”“此是彼非”的二维对抗。这同时就提示着学者或读者切忌“望文生义”地得出想当然的结论。
以上是文本“模糊性”表现较为明显的几个例子,隐性或半显性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何况,文本“众声喧哗”的局面只是《三国演义》阅读或研究的一个方面。解读《三国演义》,从成书年代、作者身份及生平、作品思想倾向到人物评价,无一不存在着争辩与分歧。在我看来,“众声喧哗”局面的出现与以下几种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必须注意《三国演义》“世代累积型”的成书方式的特点。胡适曾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2]269并且又说道,“《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2]270这类言语在《三国演义》早就被确定为经典作品的年代听起来显得特别刺耳。胡适先生的判断中不无偏颇之处,这与他本人的文学观有很大关系;但他的话却道出了《三国演义》成书的一大特点:世代累积型的成书方式。虽然罗贯中对《三国演义》成书居功至伟,但却不能忽略之前的众多贡献者。这点对《三国演义》“众声喧哗”局面的出现影响非常大。三国事迹在流传的过程中,一直是在史传与传说的双重形态下发生演变的。到了宋代,三国进入说书人的视域,并因为故事形态的丰富性和传奇色彩迅速成为当时说书界的显题,众家纷说“三国”忙。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故事出现多种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存和佚失的元代以及元明之际的三国杂剧,数量达60余种。以前学界多认为杂剧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实则不然,此60余种三国杂剧所展示的三国故事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纷纭复杂的遗产面前,罗贯中能够综合利用,并使之成为一部风格基本统一、情感取向较为明朗、在史传与文学之间相对妥当的历史演义小说,这已经足够说明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组织能力。但这种纷繁复杂的材料也成为《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的大负担。上文分析的那些“模糊性”基本就出自于捏合各种材料时的疏漏。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些模糊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行为。应该说,是三国故事形态的“众声喧哗”影响了罗贯中的判断,而罗贯中处理的这些瑕疵或者说疏漏又成为后人理解方式多样化的另一个源头。
其次,必须关注《三国演义》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演变。分析研究明清小说,尤其是世代累积型小说,必须关注他们的特殊属性。明清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小说根本无所谓版权的说法,这就导致书坊主完全可以依据市场的需求对小说内容进行更改。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商品,市场是唯一的诉求。在版本演变的过程中,《三国演义》文本的差异性表现得还是比较明显的。且以李卓吾先生订《新刻全像三国志》(古吴德聚文枢堂同梓)[3]本与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做比较,后者第一回卷首有杨慎《临江仙》,这点世所共知,但在前者文本中并不能找到这首词。另外,毛本第一回开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者文本中也不见。治《三国演义》者均不会对这些添加的文字视而不见,因为这牵涉到作品主题思想的概括及作者的情感取向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如全书结尾的古风。后者最末一句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而前者则为“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虽然只有几个字之别,但后者的历史幻灭感是前者理性叙事所不具备的。日本学者中川渝先生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4]103-127这只是中川渝先生找出分析的一些例子,而此类例子远远不止十一个。《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些方面学者多有论述,不必重复。正是因为版本演变的复杂性,所以出现很多后人纠结不清的问题。牵涉到对作品主题的解读,更牵涉到对作品人物解读的问题。譬如刘备白帝城殒命后,孙夫人是否投江而死。在文本中书写与否对孙夫人的形象解读是大为不同的。同样面临这种评价问题的还有曹后面对曹丕篡政时的反应,夏侯令之女面对政权更迭时的毁容行为。虽然这些交代的文字也就几百字的篇幅,但在版本演变的过程中添加与否本身就表明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无疑就导致了读者的“众声喧哗”。在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过程中,很多学者以“小字注”等方式来推论小说成书的年代,这种研究方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流行,但最终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与《三国演义》文本的复杂性相比,这些小字注的来源、作者的身份,流变过程中的处理方式也都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作品的不确定性。
再次,必须注意到明清小说传播中,评点本的注释与评点在流传过程中渗入文本并成为其中一个部分的独特性。文人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点方式会加剧文本意义本身的模糊性,并进而导致“众声喧哗”局面的出现。与版本演变相比更能体现明清小说独特性的则是其评点,严格意义上说,评点是隶属于版本演变的一个方面,但评点无疑具有更为明晰的独立意义。谭帆先生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5]86-99一书中把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类型归纳为“文人型”“书商型”和“综合型”三种。这种归纳基本吻合古代小说评点的面貌,在《三国演义》的评点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三国演义》的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6]与清代刊本相比,明代刊本在评点学的意义上更为显著。明代刊本的早期多属于书商型。书商为了打开销路,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促销。如上文提到的“小字注”问题,既是属于版本流变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书商型”评点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多以音注、插入图像、注释人名等方式存在。在流变的过程中,这些音注等可能会掺入正文,最终成为正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些小字注有时候是会影响到文本解读的。
在“文人型”的评点中,托名李卓吾评点本的存在就导致了《三国演义》文本解读的多义性。《三国演义》文人评点大致有托名李卓吾(叶昼)、托名钟惺、毛宗岗、李渔几种。这些评点本中,后三者基本上只存在着细节的差异,但前者的评价方式却迥然不同。前者的评论思路与晚明时代狂禅习气及评点者个人气质息息相关,也使得文本解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几百年以来,众人多津津乐道于刘备的“三顾茅庐”,积极探讨其中的隐含意义。而李贽却独树一帜,他评道:“孔明装腔,玄德作势,一对空头。不如张翼德,果然老实也。”(《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刘封在关羽危难之际不伸出援手,导致关羽兵败被擒身亡,后被刘备处死。李贽的评论为:“刘封忠义,玄德不知而杀之,罪犹可原,孔明知而杀之,罪不容诛矣。更将言语文饰,真是小人之过也必文。”(《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此类言辞在他的评点本中比比皆是,这样就解构了所谓“仁义”等作者着力塑造的崇高感。与其他评点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局面,从而更加导致读者价值取向的混乱性。
与其他版本相比较,毛纶、毛宗岗评点本具备价值建构的意义,理应属于综合型的序列。毛氏对《三国演义》的贡献绝对不应该单纯以版本演变过程中的一环视之。觚斋《觚斋漫笔》云:“《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7]437觚斋的这种说法依然没有完全概括出毛氏之于《三国演义》的贡献。如果说罗贯中完成了三国故事的第一次大融合,并且最终写就了《三国演义》这部杰出的演义小说,那么,毛氏父子就基本消弭了《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依旧众说纷纭的局面。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改造之功几乎可以视之为小说的第二次创造。毛氏评点本成为有清300余年《三国演义》最为流行的版本,并且一直流行至今,这本身就是对其功劳的最大肯定。毛氏父子力图建构自己的三国图谱。这种建构包括强化“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歌颂以刘备为代表的“仁政”,谱写心中“明君贤臣良将”的理想君臣模式等。而这种旨归的着力点包括删除大量立场相悖的“后人有诗曰”等。如此,则阅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氏评本《三国演义》就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两种文本本身就存在着“模糊性”,导致读者“众声喧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其他文学样式对民众《三国演义》印象形成的影响因素。《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三国故事形态多以此为准,但小说绝非三国故事流传的唯一形态。在《三国演义》极为流行的明清时代,依然存在着故事形态相异的其他传播方式。如戏曲与说唱文学,如明成化说唱词话本《花关索传》等。清人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说道:“盖自《三国志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8]54如上文所述,曹操之奸在小说本身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所谓“白脸的曹操,红脸的关公”等说法,均来自于戏曲,尤其是乾隆年间开始兴盛的京剧,以及各种地方戏。与《三国演义》渐趋统一的风格及故事形态相比,戏曲中的故事形态更加多样化,这点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明清时代的三国戏曲中,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方式依旧存在着众多“转世托生”说的形态。如清代徐石麟的杂剧《大转轮》,就把三国时代的人物与楚汉争霸时的人物对应,从因果报应的角度去阐明三国时代的恩怨纷争,这就接续了《三国志平话》等处理方式。屠隆的《昙花记》、范希哲的《补天记》等作品局部也有此类转世处理。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多数使用的是“泛三国”的概念,他们对于三国事件的解读并非完全出自于《三国演义》本身,而是把所有此类都纳入分析理解的范围,从而得出自己关于“三国”的印象。现在,《三国演义》更是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而翻拍的前提是改编、颠覆,并结合时代因素对三国故事进行重释性叙述,而观众有权利根据这些叙述重新建构自己的三国故事系统,这样就使得现代读者眼中的《三国演义》更为复杂化。
故事形态本身的多样性导致理解方式的多样性。三国故事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有所谓史传与传奇之别。而在元明时代,因为关注者更多,所以形态更为复杂化。周兆新先生《元明时代三国故事的多种形态》[9]301-346一文很明晰地梳理了这些形态。《三国演义》的成书,代表着罗贯中对三国故事的第一次真正的价值建构,居功厥伟,奠定了三国故事的讨论研究基础。在之后的几百年内,众多文人以及书商力图对《三国演义》进行自己的价值建构,而严格意义上的建构应该说只有到毛宗岗手里才真正实现。但这种实现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时代发生变化,三国故事形态依旧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并且同样的形态在不同的时代也能解读出新的时代命题。封建时代对关羽的崇拜,导致了某些事件评价上的高度一致性。而时至今日,因为语境的重大变化,那些一致又演变成了“众声喧哗”。
“众声喧哗”的场面并不损害《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相反,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开放性、流动性的特点造就了一部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从广义层面说,任何一个对三国故事进行阐述的作者甚至传播者都在试图进行着价值建构。但如果我们要把这种建构放在整个三国故事的产生与传播的视域中考虑,那么罗贯中与毛氏父子才实现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价值建构。
[参考文献]
[1]巴赫金,白春仁.巴赫金全集[M].顾金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出版集团,2006.
[3]矶部彰,编.费守斋《新刻京本全像演义三国志》の研究と资料[M].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ァ研究センタ。
[4]中川渝.《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M]∥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沈伯俊.《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新进展[M]∥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第二辑,2004.
[7]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8]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校:朱德东)
Understanding of Accepting History for the Writ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hree Kingdoms
ZHANG Hong-bo
(Chinese Department,Sichu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Abstract:The understanding of Three Kingdoms always accompanies suspicion and perplexity,the root for the suspicion and perplex-ity lies in fuzziness of this novel and this kind of fuzziness usually show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thor intention and“inner visual point”.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ce partially comes from author oversight and mostly results from author having no choice.This situation originates from such factors as intergeneration-style writing of Three Kingdoms,version evolution,subjective intention for its review,its masses'impression and so on.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of Three Kingdoms,it is the situation of many opinions on it that is the reason for Three Kingdom to become a classical novel.Behind the many opinions,there has been the hard work for value construction by the author and disseminators.
Key words:Three Kingdoms;Confucianism spirit;figure evaluation;value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张红波(1982—),男,江西九江人;四川外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7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5.06.015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6-0106-07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