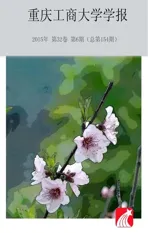对全知的自觉控制与可靠叙述的张力——以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例*
2015-02-21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朱 斌,魏 珊(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对全知的自觉控制与可靠叙述的张力
——以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例*
朱 斌,魏 珊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70)
摘 要: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凭借其全知全能,常对人事物象进行过多的直接评价,往往导致作品意义世界过分清晰。成功的可靠叙述者,常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在清晰中注入必要的含混,最终促成可靠与不可靠的矛盾统一,从而有效强化其叙述张力。
关键词:可靠叙述;自觉限知;叙述张力;少数民族小说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指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178。他的意思是:叙述者对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背离、差异与对立,意味着其叙述的不可靠;相反,叙述者对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趋同、接近或一致,则意味着其叙述的可靠。赵毅衡曾做过切合布斯本意的阐释:“如果这个隐指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与叙述者表明的价值观不同,叙述者就成为不可靠的”[2]69。其言外之意是:如果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叙述者一致,那叙述者就成为可靠的了。因此,可靠叙述者意图倾向与作者一致,似乎是作者进行叙述,他们常置身于故事之外讲故事。“因为他们不出现在故事中,因为他们占据相对于故事较高的叙述权威的地位”,“获得了常被称为‘全知’的特质”[3]171。这样,他们常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往往代表作者对人事物象进行直接而可靠的评论,如里蒙-凯南所说:“可靠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
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3]180。
一
然而,小说的可靠叙述者,一直存在一个普遍缺陷:“可靠叙述者因为全知全能,所以他常给读者过多指引,小说的意义世界往往就毫无遮拦,他拥有直接评论的权威,所以往往过度发挥,说教味过浓,甚至粗暴生硬,让人难以忍受”[4]。这不但使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缺乏必要的鲜活生动性,而且还使作品意义世界缺乏必要的朦胧蕴藉性。读者往往无法摆脱其无处不在的“权威意志”,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必产生自我的判断与感悟,只需被动接受其全知观点,被动听从其权威说教即可。这就拒斥读者对文本做必要的想象与填充,拒斥读者的个性化解读,从而割断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
所以,可靠叙述者凭借其全知全能,常直接对人事物象进行可靠判断,喜欢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难以给读者留下回味余地和想象空间。这在我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往往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评判功能,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意识形态议论侵吞故事的正常叙述。因此,在当时的小说中,可靠叙述者直接的意识形态议论泛滥成灾,完全沦落为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从而将其对直接介入权利的滥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形成了高度模式化的可靠叙述规范:往往以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对人事物象作意识形态提升,赋予它们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明确标志。
仅以敖德斯尔(蒙古族)的小说为例。其《金色的波浪》叙述到:“这男人就是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小伙子孟根乌拉。……他在七年多的部队生活中,不仅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熏陶,还学会了许多科学文化知识”[5]88。这是可靠叙述者对人物进行的意识形态提升。而其《打“狼”的故事》则叙述到:“巍峨的大青山呵,……像一排全副武装的英雄,举起那巨大的双臂,迎接着胜利归来的草原战士!”[5]175这则是可靠叙述者对自然物象进行的意识形态提升。其《一枝被踩伤的幼苗》则叙述到:“在那十年动乱的岁月里,夫妻离婚、父子决裂、兄弟之间害怕接触、亲友之间害怕来往,这种种不正常现象难道还少吗?在那场大风暴中,有多少个像乌恩奇的父亲那样的无辜群众,白白断送了宝贵的生命”[5]309。这则是可靠叙述者对事件进行的意识形态提升。
这样,小说的意图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意图——就过分清晰而明显。小说叙述者的话语,就代表了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意识形态的声音便好像神谕,控制了一切。于是,除了高亢的意识形态声音,我们根本听不见可靠叙述者的个性化声音,叙述者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因此,在意识形态的高音压制下,叙述者其实名存实亡,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为了保证意识形态主题的鲜明,当时的可靠叙述者还常直接对读者进行关于人物、事件的意识形态阐释,以防止读者阅读理解上歧义的产生。因此,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含义,早被可靠叙述者直接点明了——直接做了明确无误的意识形态阐释,读者的理解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读者就成为一个被动的接收器。
可靠叙述者这种对全知权利的滥用,还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人物也泯灭了个性,成了作者的傀儡和传声筒,因而缺乏自我个性化的声音与话语。其根源在于,作者凭借可靠叙述权威,毫不给予人物必要的尊重,因而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硬塞给了笔下人物,这就违背了人物话语与人物性格的同一性规律。因此,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往往有着同样的观点,讲着同样的道理,说着同样的话语。譬如,在居玛德里·马曼(哈萨克族)的《彩虹下》中,沙布尔阿勒老汉表达了对社会腐败的不满:“究竟是谁在破坏森林,谁在非法利用土地,谁在污染环境,谁在践踏法律,谁在以乱收费不仅富了自己的口袋,而且还满足情妇的需要,又是谁在暗地里勾结起来贪污受贿,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买官卖官”[6]508。阿斯哈尔老汉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有极少数贪婪的人却无法无天,在短短的几年里,通过各种手段,混进社会要害部门,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而且也严重地坑害了老百姓”[6]498。一位司机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们(指警察,笔者注)从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中捞取好处,……他们勾结一些臭名昭著的倒卖木材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乡村的小偷贩运牲畜和药材”[6]505。
这些人物话语,其实都是作者价值观和态度倾向的可靠代言,因而与可靠叙述者的话语完全一致。这是可靠叙述者滥用其可靠权威的必然结果:统一了不同人物观念和话语风格。于是,人物便丧失了自我个性与声音,而成了作者及其代言人——可靠叙述者——的传声筒,作品总体的话语风格就变得极其单一。詹姆斯·费伦将这种现象称为“面具叙述”:人物被可靠叙述者“用作一个面具,隐含作者就是通过这个面具说话的。即是说,一个叙述者的人物可能是功能性的,甚至于充当隐含作者的替身,隐含作者通过这个替身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7]84。这样,作品的意义世界就过于清晰,就失去了咀嚼回味的余地。
这就破坏了优秀小说叙述者话语与诸多人物话语之间所应有的对话性、双声性或复调性,也破坏了叙述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所应维持的必要张力,就成为失败的可靠叙述。巴赫金曾明确指出:一个小说家,如果“对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语言所具有的天然的双声性及内在的对话性充耳不闻,那么他永远不会理解、也不能实现小说体裁的潜力和任务”[8]113。当代许多小说就如此,往往忽视了叙述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的双声性、对话性,也就忽视了不同话语形式之间的必要张力,而把作者的话语硬塞进了不同人物的喉咙,强迫人物充当作者及其代言人——可靠叙述者——的简单传声筒。这样,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话语的“内在分野”便不复存在,人物的个性和生命亦不复存在。
这是当代小说可靠叙述的常见病象,许多作品都感染上了这病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据此,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应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以在清晰中注入必要含混,在透明中融入必要朦胧,在可靠叙述中融入巧妙遮蔽,最终促成可靠与不可靠的矛盾统一。可见,其叙述张力的生成机制,是可靠介入中融入不可靠的遮蔽和含混,最常见的方式是:可靠叙述者通过自觉限制其可靠权威,尤其是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促成其可靠倾向的含混化。因此,成功的可靠叙述者,总会在其全知叙事中自觉地“反全知”,故意限制其全知全能,甚至故意变得极其“无知”,以增强其叙事的含蓄性和朦胧性,给读者留下必要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从而有效强化其叙述张力。
二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表现为故意留下诸多“省略”,形成富有意味的叙述“空白”,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梁志玲(壮族)《暗流》中的叙述者,就常自觉地限制其“全知全能”,故意留下了诸多有意味的省略与空白。譬如,叙述者在小说开篇叙述了三个场景:其一,一个男人拉着一位梳羊角辫的小姑娘的手过铁轨;其二,那个男人同一个年轻女人闹别扭;其三,那个年轻女人送梳羊角辫的小姑娘上学。据此我们知道:那个男人是梳羊角辫的小姑娘的父亲,而那个女人则是小姑娘的母亲[9]。
但这里的叙述,却留下了明显的省略与空白,也就巧妙地设置了诸多悬疑。比如,那个梳羊角辫的小姑娘是谁?她叫什么名字?她父母姓甚名谁?是什么身份?他们究竟怎么啦?按理,叙述者是全知的,对这些问题都一清二楚,因而完全可以将它们和盘托出,毫无遮拦地告诉读者,但他偏偏没有这么做,故意不说,这就是对“全知全能”的自觉限制,故意留下了诸多叙述“空白”,平添了几分含混与朦胧。其叙述便张力蕴藉,有了耐人回味的余地。直到后来,叙述者才弥补了上述诸多空白,断断续续告诉我们:那小姑娘叫索妮,她爸爸叫索俊,是一位水电工,她妈妈叫李菊,是铁路职工食堂的临时工,她爸抛弃了她们母女,跟一位叫胡丽的女人结婚了。
叙述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而故意留下叙述空白,这在该篇小说的其他地方也存在。比如,索妮初中毕业填考中专志愿时,叙述者告诉我们:母亲李菊要求索妮填铁路运输学校,索妮沉默着就是不填,李菊轻轻说了一句“你填铁路那个学校,他会帮你的”,索妮假装没有听见,她知道那个他是谁[9]。但那个他究竟是谁呢?叙述者在此并没有明确说出来,这也留下了一个耐人回味的叙述空白。虽然没有明说,但聪明的读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却不难知道:那个他就是索妮母亲的情人——铁路段的领导王大段长。再如,叙述者讲述索妮上中专的情况时,叙述道:有人写了匿名信到校方,揭露了黄老师和潘老师的有伤风化。但写匿名信的人究竟是谁呢?在此,叙述者也没有明确告诉读者,因而也留下了一个叙述空白,从而形成了一个悬念。直到很久以后,叙述者才填补上这个空白,告诉我们:“很多年前,索妮戴上手套,捏起笔,写了一封信,匿名的,揭露了黄老师和潘老师的私情”[9]。
在另一处,叙述者叙述道:那一次一个男人看到索妮穿过枕木区,目不转睛。那天他尾随她摸清了她上班的地方。这个男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想干什么?对此,叙述者也没有进行明确叙述,也留下了空白与悬疑。直到后来,叙述者才告诉我们:这个男人叫范难,是一家银行的领导,他凭自己的身份把索妮调入银行,把她发展成了其情人。这样,叙述者在其叙述中多次自觉“反全知”,常故意留下诸多省略和空白,故意为其叙述增添几分含混和朦胧,从而有效克服了可靠叙述的常见缺陷:过分透明。这就促成了清晰与含混的对立统一,也促成了可靠叙述与必要遮蔽的有机一体,因而是有助于叙述张力的生成的。
这种可靠叙述者自觉的“反全知”,在小说中往往还表现为故意采用诸多揣测与不确定语气,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赵剑平(仡佬族)的《小镇无街灯》,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可靠叙述,但我们看其这几处叙述:“从黑鸦坎嫁上街来的新媳妇梦碧不会明白——也许还有一些人也不会明白”;“人们还在等待着,谛听着,似乎有一点事情就要发生”;“仿佛只是眨眼工夫,那拨年轻人就跳趴了,跳散了”;“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事情正酝酿着呢?”[10]这些叙述,采用了“也许”“似乎”“仿佛”以及“是不是”等明显不确定的语气,形成了明显的揣测语句。而可靠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他怎么能如此频繁地使用不确定的揣测语气呢?这是一种语误吗?不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叙述策略,是可靠叙述者对其“全知全能”的自觉限制:故意说得不肯定。
我们再看几处更明显的地方。譬如:“砣子像一截木头桩子那样一动不动地竖在阶沿上,仿佛什么都明白,又什么都不明白”[10]。按理说,可靠叙述者是有权力知晓人物内在情感心理的,因此,砣子心理究竟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应予以明确叙述,但叙述者对此偏偏含糊其辞,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仿佛又什么都不明白,因而对其情感心理并没有进行明确叙述,这就留下了几分朦胧。再看:“余警官想起什么似的,又回过头来,像是说给砣子听,又像是说给别的人听,高声大气地吼着……”[10]这里,叙述者也采用了不确定语气,也故作不知。其实,可靠叙述者完全可以明确告诉读者:余警官究竟是不是想起了什么,究竟是说给砣子听,还是说给别人听,抑或是既说给砣子听又说给别人听。但他偏偏不明说,其叙述就有了几分含混与模糊。因此,可靠叙述者的这种不确定叙述,其实也是一种巧妙的“反全知”,它使得“全知”与“限知”、可靠与含混既矛盾又一体,因而也有效强化了叙述张力。
三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还表现为故意转化为客观视角(即外聚焦视角)以形成客观叙述,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在赵剑平(仡佬族)的《小镇无街灯》中,可靠叙述者往往就自觉限制自己的“全知”,常转换为一种客观视角,不对其所叙述的人事物象作主观评价,也不涉及所叙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只进行近乎客观的戏剧化展示。因此,小说中的许多片段,单独看,极像戏剧的剧本片段,主要由人物对白构成,而叙述者的叙述,则只像舞台提示一般,极其简略。我们看:
“一夫一妻制”是哪样说的?
“你说说,”妇联主任来了一些兴味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一个人管一个人,”砣子说,“一个人用一个人。”
“作为朴素的理解嘛,”王么姐说,“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那么我犯哪样政策?”砣子说,“人家用过,我就是不能用……”
妇联主任愣了愣,尴尬地笑了笑,站起来走了。[10]
这里,原本全知的可靠叙述者,对人物保持沉默,拒绝对其进行直接的评论,只是客观地记录其外在的言行,而毫不涉及其内在的情感心理,因而成为典型的客观视角。这使其叙述带上了客观、冷静的风格:既没有强烈的情感抒发,也没有明确的思想表达,既没有对人物进行主观评价,又没有涉及其主观的情感心理。但叙述者保持客观,不对人物进行主观评价,却并非不要其主观倾向,而是使其主观倾向隐蔽化、含混化了。具体地说,叙述者的主观评价,是以人物偏激的“自我暴露”细节为“客观对应物”的,从而巧妙而可靠地暗示了出来。因此,我们从砣子对“一夫一妻制”明显偏激的理解,不难感受到叙述者对他的主观态度:批判其狭隘、偏颇与荒唐可笑。
这样,客观呈现中其实有着巧妙的主观倾向暗示,全知叙述中又融入了客观的限制视角,这就促成了客观与主观之间、全知与“反全知”的矛盾统一,也就有效增强了可靠叙述的叙述张力。因此,在当代小说中,可靠叙述者采用客观视角进行客观叙述,也是其自觉限制“全知全能”而进行“反全知”的一种有效方式。于是,叙述者原本有权利进行主观评价却常常自觉限制,保持客观,故意不评,可靠介入因此就含混化了,其可靠叙述也就有了几分含混和遮蔽,因而张力蕴藉,意味深长。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还表现为故意借助人物的限知视角,形成限知叙述,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在肖勤(仡佬族)的小说《暖》中,可靠叙述者在很多时候虽然保留着自己的叙述声音,但却放弃了自己全知的视角,而灵动地采用人物的有限视角,进行观察和感知,从而缩小了自己的叙述范围。其有时采用的是村主任周好土的限知视角,如:“村主任周好土让躲不开的太阳晒得眼冒金花,……眼角扫见小等被背筐压弯得只留个头了,赶紧走上去搭手接下筐”[11]。有时,又换用村小老师庆生的限知视角,如:“院子外有什么声响,窸窸窣窣的,是狗或猫或人的脚步?庆生心惊胆战地从窗棂往外左右张望——院子里静悄悄的,明亮的月光均匀地洒在院坝里,把院坝变成了一面清亮的镜子,老黑在空牛棚边缩着头睡觉”[11]。这破坏了可靠叙述者“全知”视角的单一性,叙述因此变得摇曳多姿,拓展出广阔的张力空间。
然而,其视角的转换又并非是随意而任性的,主要集中在主人公小等身上,因此,叙述者主要借用的是小等的限知视角。比如:有她对往事的回忆,有她对庆生老师的良好感知,更多的,是她对疯了的奶奶的害怕与恐惧。这个重点人物的限知视角,既是叙述者的意图中心之所在,又是一种强大的统一力量,它使流转的视角有了一种清晰而连贯的脉络感,因而并不杂乱无章。就像九曲黄河,虽曲折扭转,左奔右突,但总是从高往低、由西向东,一路奔流而去。而且,变换的人物限知视角,又总与可靠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交织在一起,终究是在“全知”视角下的“限知”,因而促成了全知与限知的矛盾统一,从而也有助于叙述张力的强化。
综上所述,对当代小说的可靠叙述者而言,通过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能有效强化其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和遮蔽,从而能有效强化其叙述张力。据此,小说可靠叙述者其叙述张力的生成机制,主要就是促成其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机制。从理论上讲,文学张力“是差异因素有机统一或矛盾因素融合一体而导致的动态性或戏剧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体魅力或总体效果的超常性”[12]。促成诸多矛盾因素有机一体,这是艺术张力生成的关键,而可靠叙述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就如此,它促成了诸多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存在于全知与限知之间,显露与遮蔽之间,清晰与含混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但终归表现为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有机一体。强化的亦此亦彼思维,是艺术张力生成的独特思维,而可靠叙述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也如此,它正体现了这种强化了的亦此亦彼思维:越是全知,越要限知;越是主观倾向,越要客观暗示;越是可靠叙述,越要不可靠遮蔽;越是清晰显露,越要朦胧含混;越是直接介入,越要巧妙隐退。
所以,对小说的可靠叙述者而言,单有可靠评价与介入,而没有巧妙而必要的含混和遮蔽,必然会导致其失败,也必然会导致其叙述张力的匮乏。因此,成功的可靠叙述者,其直接是可靠的,但又总存在巧妙而必要的含混和遮蔽,终归促成了可靠与不可靠的有机一体。可见,一味的可靠叙述,只会导致过分的清晰、透明与敞亮,像块透明的平板玻璃,这常是各种功利文学、党派文学用以诱人的诡计,其实是可靠叙述的敌人,是谋害叙述张力的元凶,只能导致可靠叙述的审美贫血。因此,以此寻求读者的喜爱和留恋,只会事与愿违,导致读者的抛弃和走失。这是当代小说在可靠叙述方面长期探索积累而成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因而值得今天的小说家们认真吸取。
[参考文献]
[1]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3]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4]朱斌.反讽张力与小说审美空间的拓展[J].山西师大学报,2014(5).
[5]敖德斯尔.敖德斯尔短篇小说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6]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中篇小说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7]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梁志玲.暗流[J].民族文学,2012(5).
[10]赵剑平.小镇无街灯[J].山花,1990(6).
[11]肖勤.暖[J].民族文学,2012(10).
[12]朱斌.论文学张力的性质[J].燕山大学学报,2013(3).
(责任编校:朱德东)
The Conscious Control of Omniscient and the Reliable Narrative Tension
——Taking Modern Ethnic Novel for Example
ZHU Bin,WEI S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orthwestern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Reliable narrators often make too much direct evaluation of persons and phenomena as omniscient,which often makes the significance world of works too clear.Successful reliable narrators often consciously limit their omniscience so as to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narrative tension by adding necessary ambiguity into clarity and finally by making the contradiction and unity of reliability and non-reliability.
Key words:reliable narration;consciously limited knowledge;narrative tension;minority novels
[作者简介]朱斌(1968—),男,四川仁寿人;文学博士,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魏珊(1991—),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与审美转化研究”(11BZW127);西北师大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当代民族小说的张力形式研究”(SKQNGG12004)
*[收稿日期]2015-07-17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5.06.014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06-0100-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I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