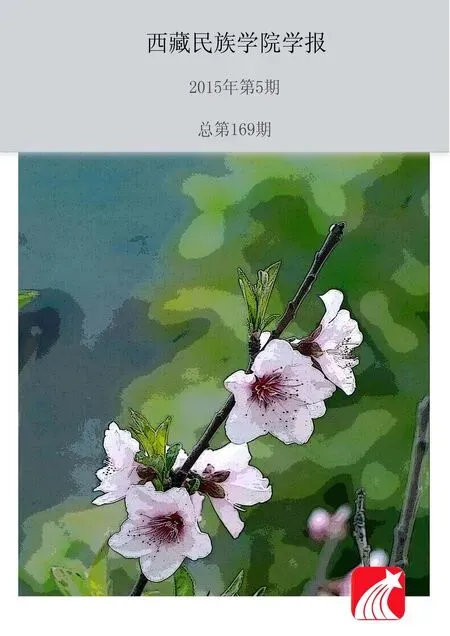吐蕃时期主要立法思想分析
2015-02-21张辉
张辉
(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吐蕃时期主要立法思想分析
张辉
(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法律体系及内在特点的形成,受地域环境、社会心态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发现社会主要矛盾,并顺应社会发展环境,做出合理的立法决策。吐蕃时期主体立法思想,对苯教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持续反思,并积极推动佛教思想与吐蕃社会的融合,佛教的普及加速了吐蕃社会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转变。在立法思想转变过程中,法律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出现,并带动了社会主体制度如经济、行政和司法制度的确立,对藏族文明的进步和西藏封建农奴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藏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吐蕃;法律;立法思想
松赞干布继位赞普后,为稳定社会,积极对外拓展,建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吐蕃王朝。为稳固政权、打击犯罪活动,实现国泰民安,吐蕃进行了持续的、富有成效的立法活动,松赞干布、芒松芒赞和赤松德赞时期的立法活动成为这一序列的代表。通过不断的努力,吐蕃形成了以“吐蕃基础三十六制”为基础的,较完备且特色鲜明的古代法律体系,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法律部门。持续的立法活动对吐蕃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藏民族文明的极大发展,保证了吐蕃王朝两百多年稳定和坚强的政局。
一、吐蕃时期的法律特点
吐蕃时期的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如诸法合体、君权神授、特权维护,刑罚残酷,大量原始习惯法痕迹等,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区、民族和时代特点。笔者认为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法律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出现
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藏文,使成文法的出现成为可能。吐蕃王朝时期通过几次立法高潮,制定了成文法。成文法逐渐取代习惯法和其他法律形式的地位,成为西藏地区法律形式转变的一次深刻改革,对本地区后续的法律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立法的社会性
立法体系着眼社会实践,法律体系既有法典、施政措施,也规定了执法标志、装饰类别和奖励处罚等内容。绝大多数条文面向社会基本关系的调整,通过法律对度量衡的标准和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做出详细规定。内容上通俗易懂,易为社会了解和接受,因此能在吐蕃社会迅速普及,符合法制建设初期的立法特点。
(三)执法的指引作用
法律除规定执法的强制性外,还着重强调执法的指引作用,如突出表现对有功者的奖赏和社会荣誉,对落后者的惩治和精神惩罚,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军事的重视。在这种法律特点的影响下,迅速确立了“灭敌援亲”思想,保证了社会稳定和对外扩展。
(四)法律直接反映了宗教思想的转变
从“基础制”的内容上看,虽然包含了大量的原始苯教思想,但其思想来源已受到佛教的“十善法”的根本性影响,“善”作为其后立法思想的灵魂,对法律内容影响深刻且坚决。吐蕃立法思想和法律实践中均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也深刻体现出两种主导宗教思想的转换和融合。
(五)法律调整军政关系一体化特点突出
吐蕃政权凸显的军事政权性质,决定了其法律制度在行政和军事关系调整中的一致性。从行政区划、官员性质、行政管理等都可以看出吐蕃法律特别是行政管理法律制度大多是围绕着军事活动呈现的。行政奖惩、人员管理、征收税费粮草大都以军事准备为调整目标。
二、从立法进程看吐蕃立法思想演变
从一般意义而言,法律体系及其特点的形成有地域、环境、社会现状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但决定因素还在于统治者是否发现并顺应了社会发展环境,做出合理的立法决策。吐蕃政权的建立、发展和强大与其立法活动密切关联,而其中立法思想的合理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吐蕃政权成立初期时立法思想
吐蕃政权建立初期虽然完成了形式的统一,但政权内、外部均面临严峻形势,尤其是内部由于各部落思想和规范的不统一,使政令无法畅通。对此吐蕃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如《贤者喜宴》中就有记载:(松赞干布)招集百姓说道:“往昔,因无法律以至众小邦离散。况且,若无法律则犯罪猖獗,我之众属民亦将沦于苦难之中,故此,应当制定法律。”[1](P6)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立法思想,也成为吐蕃法律总的立法思想:统一社会思想、稳固政权;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较之前社会有了明显转变,主要体现在重视对统一的成文法的制定,以及所依据哲学思想的转变等方面。
1、通过制定成文法,统一社会思想,指导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德乌教法源流》中这样记载:“以王之敕谕作为议商之原则,以集体之言论作为商议之友。”因此,吐蕃的基本法制是王和臣民集体智慧的产物,有朴素的民主立法观念。这种思想直接挑战了秘密法制度,避免了立法权和司法权被部落贵族、宗教首领分散,通过立法确立了赞普的至高地位,保证了法律和社会思想的统一,从而维护政权的统一。《法律二十条》的颁布开吐蕃成文立法之先河,内容上通俗易懂,绝大多数的条文是调整世俗之事(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在吐蕃社会迅速普及。通过法律对经济领域的度量衡的标准和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做了详细规定,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生活,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再如,吸收和改造了习惯法中的赔命价制度,从而代替了原始的血亲复仇,极大地缓和了部落间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
2、为保证赞普的绝对统治地位,开始依据佛教哲学理论建立法律体系。史书称自松赞干布赞普迎娶了两位信奉佛教的公主,即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之后,深受她们的信仰影响,进而接受了佛教。笔者认为在这之前①,苯教的巫师和握有实权的贵族控制神权,并利用神权蚕食王权,威胁赞普的地位。统一政权建立后,赞普希望通过神的代言人,并且是天人间唯一的受命者的身份,建立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苯教万物皆有神灵的教义在现实世界里体现为分散独立,不相归属,这显然与赞普所希望政权统一及王室在统一政权中至高地位的要求相悖,需要有一种新的统一的哲学体
系作指导。佛教传播者认为赞普是当然的最高统治者,首尊王族,次为贵族。这种主张,符合赞普集权的需要。佛教的“善”也符合了吐蕃统一政权建立初期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因此,变换哲学理论体系不单单是首脑的个人信仰问题。根据佛教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嫉妒、不忿恨、不愚痴、不谎话、不巧辩、不挑拨、不恶骂)的精神,用新创造的藏文制定的《法律二十条》于公元629年颁布,在吐蕃全境施行,为以后的吐蕃统一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3、灭敌援亲思想保证了吐蕃政权内部稳定和对外扩展。吐蕃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军队中的褒奖和惩罚制度,《贤者喜宴》记载:“不对英雄赏赐虎皮战袍,无法显英雄的威武;要把狐狸的尾巴套在懦夫的头上进行谴责,不然无法区分英雄和懦夫;对施恶者不加以提醒,他们永远不知自己所错;对犯罪者不予以刑罚,以后无法区分善与恶。”[2](P104)在《人教十六法》通过报父母恩、利济相邻、追踪上流,追认旧恩等来教化臣民,化解内部矛盾,促进内部稳定,为对外扩张筑牢基础。
这期间,吐蕃法律体系初步框架得以建立,社会管理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但这一时期的法律往往源于佛教戒律,着眼于建立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大多是面向社会做出的原则性、概括性及方向性规定,缺少具体操作规范和基本程序。
(二)吐蕃政权全盛时期的立法思想
吐蕃王朝走向全盛,通常是指芒松芒赞至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本文也以此为据。这一时期随着吐蕃社会进一步发展,吐蕃王朝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大,吐蕃内部,吐蕃与占领区的社会矛盾凸显,其中由于法律理念和法律差异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如何完善法律,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化解矛盾,维护统一政权利益成为立法的主要关注点。而不断加强的外部交往,使吐蕃王朝的立法技术更加成熟,从建立法制到完善法制的过程中立法思想也发生了一些调整。
1、完善法律体系,确立民法(公民守则)的基本原则,强调统治阶级的守法意识。《吐蕃三律》(《狩猎伤人赔偿律》、《纵犬伤人赔偿律》、《盗窃追偿律》三部法律),被看作是吐蕃王朝时期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采取“诸法合体的形式,既有刑事方面的规范,又有民事方面的规范;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的内容;外部结构上采用唐朝的律令形式”[3](P16)。众多学者认为,《吐蕃基础三十六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于松赞干布时期,完善当是在赤松德赞时期,除了立法形式的完善,这一时期已逐渐将具有吐蕃社会自身特点的阶级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法制化。此外赤松德赞时期制定的《没庐氏小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对社会礼节的指导;《狩猎伤人赔偿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残卷》对死刑犯财产的处理;此外还有《婚姻离异法》、《受诬辩冤法》等,虽然有些无法律条文考证,但已说明当时立法涉及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这一阶段,统治阶级非常重视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强调统治阶级的守法意识,注意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例如《三喜法》中就出现赞普执法前提是赞普自己应先成为法律的维护者等较先进的法律思想。
2、巩固以宗教教义、伦理道德规范为引导的立法方式。这一时期正式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的重要地位。首先,体现在建寺译经。吐蕃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就在这一时期兴建;大力推动佛经的翻译和普及,先后颁行两次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其次,提高僧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从三户养僧制发展到七户养僧制。第三,立法明确佛教在吐蕃社会的突出地位。主要表现在诏令全民奉行佛法,设“僧相”开僧人参政先河,制定《佛教大法》,并以盟誓方式巩固佛教地位。这一时期佛教真正得以广泛传播并使之趋向大众化。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精神贯穿吐蕃法律,如废除死刑及部分体刑,使吐蕃法律更加趋向文明。
3、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并继承了松赞干布时期的基本法律思想。但随着吐蕃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发现法律制定初期以法律原则为主,标准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开始积极借鉴先进地区,特别是唐朝的法律,加大了对初期立法的补充和细化,如惩罚性规范可操作性,《医疗赔偿命价标准法》就兼有实体和诉讼内容,对前期法律中医疗费赔偿,赔命价制度执行过
程中的标准模糊,执行混乱的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使赔偿标准明确具体,参照性增强。这一时期成为吐蕃法律由戒律性向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九双木简”成为部分案件关键环节的程序性解决方案,对吐蕃社会产生了深刻和广泛影响。
4、深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据《松赞干布遗训》载:“制法的目的是维护王族的利益”,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和人身特权不受侵犯。如《盗窃赔偿律》对盗窃统治阶级财产的人严加惩处“为首者诛”,并根据被盗人的社会地位确立赔偿标准,如盗窃王室的财物要按被盗财物的百倍进行赔偿,而盗窃平民的财物只需按被盗财物的八倍赔偿。《五部遗教》中则记载,偷盗寺院财物的按被盗财物的八十倍赔偿。敦煌出土的文书P.T. 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中的惩处类别和标准也是以当事人的身份高低来判断,如等级低的人,射杀尚伦和玉、金、银告身的上层人士要处死刑;射杀一般民众只要赔偿一百两即可。而《贤者喜宴》记载:“判断真伪对于诸富豪不羞辱,只稍加审判。”[2](P105)明显体现了司法特权。还有上文提到的赔命价制度,似乎法律赋予各阶层此项权利,但这仅限于同等级的人。《狩猎伤人赔偿律》规定:“若被大藏以下,平民百姓以上之人因狩猎而射死,将致害人处死,并赶走其子媳,没收其奴户、库物、牲畜。若受伤则将致害人处死”。[4](P12-13)对于经济实力低下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高额的赔命价意味着这种权利在事实上是无法享受的,因此,实质上赔命价制度是贵族阶层规避法律制裁而确定的特权法。
5、在占领地区实行军政一体的公法模式,推行包括司法权在内的王权的高度统一。法律明确规定一切事务均归吐蕃赞普的领域内,并受其所派军队和委任的各级行政官员的管理和节制,任何由赞普委派的官员都有执行法律的权力,确保了吐蕃王法至高无上的效力。同时,由于吐蕃占领的地区幅员辽阔,经济、民族、社会生活呈多元化格局,强行推行吐蕃王朝法律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因此,在司法制度的选择上,吐蕃统治者采用了因地制宜的开明思想,不仅启用当地人管理当地人,而且也允许其按照当地的传统法律调处纷争,不易其俗。这种立法思想对占领区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本部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持续吸收、利用习惯法的立法思想
由习惯法内容发展为法典的内容,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全部接收,如命价赔偿制度,最初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后来被历代法典毫无保留地吸收和应用。习惯法中的肉刑也是吐蕃法典的一大特色。二是有选择的接收,如盗窃案件的追赔制度以及原始宗教中的“神断”、“天罚”等内容。三是在习惯法某些内容的基础上,经加工整理后在成文法中出现,如有关处理奸淫、抢劫及民间纠纷的规定等。
此外,盟誓作为吐蕃时期典型的社会现象,是吐蕃法律的重要法渊,成为调整吐蕃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吐蕃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盟誓也是一种习惯法。
在吐蕃立法中,原始习惯的痕迹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立法初期,在比较成熟的《吐蕃三律》中也存在“外部结构上虽采唐朝的律令形式,但内容中很多规范是从部落习惯发展而来,又具有很强的原始习惯法的特征”[3](P16)。这说明,吐蕃时期原始习惯法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性。吐蕃统治者通过成文法律吸收习惯法,存在把法制建设和吐蕃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的立法思想。
吐蕃法律对特权阶级利益的极力维护,加剧了贫富分化。由于大力倡导佛教,佛教势力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又掺杂了宗教矛盾。不断的武力扩张,大量的消耗了吐蕃本土的人力物力,被占领地区的社会生产活动被严重干扰,当地人民的生命财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吐蕃王朝各地反抗不断。吐蕃统一政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推行的毁佛灭法,成了导火索,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吐蕃政权自此分裂,青藏高原进入分散割据时期。
吐蕃时期主体立法思想对苯教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持续反思,并积极推动佛教思想与吐蕃社会的融合,而且佛教的普及加速了吐蕃社会基本价值观
和人生观的转变。在立法思想转变过程中,法律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出现,并带动了政权主体制度如经济、行政和司法制度的确立,并出现了朴素的民主法制和社会法制思想。对藏族文明的进步,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建立和发展均产生了长远影响,即使在今天民族法制建设中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因此,吐蕃时期的立法思想在整个西藏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注 释]
①有关的苯教史书和《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这样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护持国政。”转引自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册),甘肃教育出版社,第505页。
[1]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
[2]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王尧,陈践译著.敦煌吐蕃文献选[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侯 明]
[校 对 陈鹏辉]
D929
A
1003-8388(2015)05-0024-05
2015-04-28
张辉(1975-),男,陕西周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法制与经济。
本文系西藏民族大学一般项目“吐蕃王朝与周边主要法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项目号:15myy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