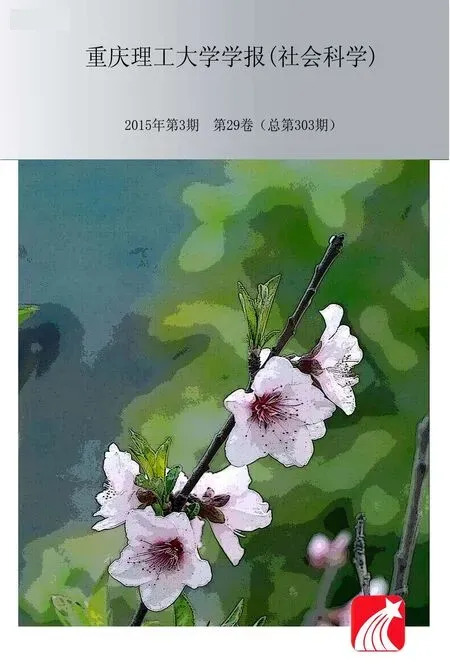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之维
2015-02-20李勇强
李勇强
(第三军医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重庆 400038)
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以自然向人而生与人向自然复归的双重意涵为核心旨趣,秉持自然对人的根源命义与自然向人的生成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实践的道路;实践活动的历史也就是自然向人生成与人不断自然化、向自然复归的辩证耦合的历史。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贬低为天生的利己主义者,对利益的追逐成了人的唯一圭臬,关爱自然只是衍生的道德义务,这既无法保护自然,也难以真正实现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掌控自然”的反叛,生态中心主义把人降格为“吃喝自然”的饮食男女,以此论证人与自然的一致性。遗憾的是沦为生物链条上普通环节的人还是难以合理、充分地实现对自然的关爱和保护。超越自然宰制人和人主宰自然的“暴力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双重意涵为枢轴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准确把握“人”这一生态文明理论的元哲学问题,从“人学”这一维提供了建构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现实路径。
一、人向自然复归与自然向人而生: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的双重意涵
秉承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双重意涵,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主张: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人必须植根于自然这一母体,依靠自然而生成与发展,呵护自然,走进自然和向自然复归就成了人之为人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作为人的存在,实践活动开启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构成了人走进自然与自然向人生成的现实基础和平台。
作为生命存在物,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只有凭借感性、现实的自然对象,才能生成、确证、表现和充实自己生命的本质力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67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休斯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将之指称为“生存包含原则”,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2]139-14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当人们“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177。即是说,创造环境的人同时在环境中被塑造。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坚持人的生成的自然根基,更秉承自然向人的生成。诚然,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的存在物,但人更是“能动的”“人的”自然存在物。对人而言,自然对其具有先在的根源性,但对现实的人而言,自然也必须向人而生——从抽象的自然走向现实的“人类学的自然”。针对费尔巴哈的荒野自然与黑格尔绝对观念异化的想象的自然,马克思精当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他的胡子、血液、肉体的本性,不是栖居于世界以外的东西,甚至“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87。
有学者正确地看到,劳动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过程,“不仅包括人改造自然这一‘由自然到人的过程’,而且还包括自然穿过人又重归于自己的‘由人到自然的过程’”[5]。正是以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架起了人向自然的走进与复归和自然向人生成的桥梁和中介。一方面,借由感性对象性活动对世界自在性的否定,使自在自然转变成“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即通过实践把天然自然提升到现实的人的世界。自然只是人的生存前提或基础,并非天然的处于“在手”状态,要将这一前提或基础转变为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诗意的栖居之地,必须从“人的尺度”出发,物趋近于人——在“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中去拓展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通过对象性实践积极介入自然,人类才能从“吃喝自然”的饮食男女转变为真正的人,在实践中凸显人的创造本性。人之为人,就在于建基于自然之上的能动创造性,这种特殊的能动本质必然要求实践变革自然的原有状貌,而变革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有环境的某种“影响”或“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92。另一方面,实践作为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不是封闭于人类自身的自娱自乐的“画圈之旅”,而是人与自然辩证互动的对立统一,在自然向人的生成中人也向自然走进与复归。我们的肉身之躯和思维着的头脑都存在于自然之中,离开了自然这个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也如水中月、镜中花。人要不至成为悬在半空的无根存在,就必须在实践中保护自然这个人的“无机的身体”。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要从“物的尺度”出发,听从关爱自然的呐喊,使需要和享受失去利己主义性质,要尊重自然中任何一个“种”;人趋近于物——认识自然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先在性,要在与自然的辩证对话与交流中自觉地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体认。这一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也就是基于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人走进、复归到自然与自然向人生成的双重互动过程。
二、利己人与自然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的双重意涵,人类中心主义以利己主义规定人、进而规定自然;生态中心主义则把人降格为生物链条上的普通一环与荒野之物,二者的形而上学对立撕裂和肢解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如此一来,也难以切中现实的环境问题,真正实现对自然的保护和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的统一。
(一)利己主义的人: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学旨归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其他存在物只是被动的机械客体,缘于人的情感、愿望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高贵性,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服务于人的利益和人为自然立法就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圭臬。近几十年,伴随高度紧张并日趋尖锐的环境问题和生态主义的无情挞伐,人类中心主义从对自然的“强式控制”走向了主张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并举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内核厘定人类利益的正当、适度与否,反对将利益个体化和绝对化,秉承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这一价值关照的中心,主张科学、合理、适度开发自然并保护自然。在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看来,生态环境问题不应由人类中心主义负责,真正该对如今的生态和人类社会环境危机负全责的应该是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我们可以并且应该超越的是那种以机械论自然观为基础的特殊的人类中心主义[6]。澳大利亚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帕斯莫尔就认为细菌和人不属于同一个共同体,既无伦理上的责任,也无伦理上的义务,人类恢复的只是相对于人来说的生态平衡,对自然的关爱呵护只是出于保护人类自身整体和长远利益从人类伦理的链条中衍生出的道德义务,因为只有合理科学利用和保护自然才能更好地固守人类的利益。我们看到,面对悬于人类头上的环境恶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类中心主义在自身的演进中改变了对待自然的偏激主张,对其骄横与狂妄态度作了“减值”处理;但问题的关键是,利益作为其核心诉求,进而规定人、规定自然的实质并无本质上的变化,这一运思理路至少面临两方面的困境。
其一,以利益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能真正保护自然吗?虽然弱式的人类中心主义一再强调其理论的基本症候和旨归是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基于此,关爱与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但问题的关键是,以利益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裹挟、控制与操作自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利益这一强大的基础逻辑仍然隐匿其中。笔者以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不是“以人为尺度”的问题,而是利益作为无意识的巨人成了人的本质规定,其他一切都是围绕利益这个圆心的“半径和扇面”。当利益被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中心位置,虽有理性护航,但对利益孜孜不倦追逐的人只能是利己主义的生物人[7]。这样,当人被利益这一生物必然性所支配与绑架,呵护自然甚或多大程度去呵护自然的标准只能是“利己主义”这一人的非本质规定了。如此一来,无论人们多么的贤明、宽容,甚或仁慈,若是离开了金钱、利益的考量,都难以有充分的动机去关爱自然;就算看到自然资源的耗损,勉强去承认自然艺术诗意的、美学的一面,但缘于利益的深层次牵绊,也难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压制住掠夺与浸淫自然的原始的生物冲动,也难以自觉地维护自然神圣的平衡,终归自然还是难以逃脱沦入让人予取予求的臣属领地的厄运。
其二,以利益为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能真正达及人类整体与长远利益的美好愿景吗?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宣称超越了“强式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类贪欲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诉求的是作为“类主体”的人的整体与长远利益。但是要真正规约人类的行为,占据道德的制高点,避免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割裂,只有立足于私有制、国家、阶级的消灭,然而在今天,这些都还存在于现实的“彼岸世界”中。实际上,抽象名义的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而缘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和相互抗争性,从实实在在的特殊利益与短期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处理环境问题,到是随处可见。恰如有学者看得精准,“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现实中无法贯彻,而是必然地衍生为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8]80,进而堕落为一种代表西方资本主义逻辑、为西方意识形态辩护的政治修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等问题上的诸多推诿、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实施的强烈阻扰、哈丁化解“公有地悲剧”的“救生艇伦理”等等,就是其生动的表征。在他们伦理关怀的疆域内从来就没有弱势的芸芸众生的立锥之地,到是经常看到他们拿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大旗封闭弱势者的声音,掩盖资源分配的不透明性。
(二)自然主义的人:生态中心主义的荒野之物
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人的愤懑,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借助还原主义把人降格为“吃喝自然”的饮食男女,以论证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指出:“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9]195这样,当人转变为生物链条上的普通环节,由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其中的普通一员、承担起普通公民角色的时候,也就能真正保护自然。罗尔斯顿也指出:“根据数学化的关于物质的微观物理学得出的形而上学将会使人越来越显得渺小,最终变成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10]4因此,人类没有理由不把自身的行为融入于自然之中。在深层生态学眼里,自然大系统是囊括一切的“无缝之网”,人、非人类生物、大地、岩石、土壤、河流、空气等等都是这一无缝之网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纽结。据此,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福克斯特别强调:“宇宙不是自身独立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实际上也不存在什么分界线,而所有的整体是由它们的关系组成的。……若是我们看到了界线,就没有深层生态意识。”[11]255-256我们看到,生态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单纯的反动或倒转”,将人降格为自然之物以论证人类关爱自然的应然性,好似化解了人与自然对立的难题,实际上远非如此。这一论证路径至少也面临两方面的困境:
困境一:人能还原为自然吗?诚然,人与自然有诸多类似之处,恩格斯甚至说过:“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12]551-552但同时,为了避免把人等同于普通动植物的愚蠢之举,恩格斯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作出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的。……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12]382-383生态中心主义似乎只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生物同一性,而忽视了人与自然之物的质性差异,这实际上是把人等同于蜗牛(当然,二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粗浅之见。试想,我们真的能够从人类这个复杂精妙的存在体中剥离出纯粹肉体甚或纯无机物的存在吗?即使这样,分离出来的纯肉体或无机之物还是人吗?生态中心主义一再强调要反对操作自然的近代形而上学思维,但是这样一种将人还原分解的生物思维又何尝没有蜕变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呢?①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形而上学“隐性逻辑”的具体论述,可参看拙文:《拒斥或遗继: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魅影》,《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6期。如此一来,由于对人与自然同质、同构性的偏爱,本来表征人之内质规定的活动也就沦为了动物式的本能活动。无怪乎,有学者大声疾呼“要高度评价使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因素,保护并强化这些因素,抵制那些反人类的因素”[13]。
困境二:退一步讲,即使人能还原为自然,但是沦为生物链条上的普通环节或自然界普通一员的人还能保护自然吗?一位生物学家深刻地洞察到:“生物链是生物之间赖以生存的联系发生之一,不知上帝是否一开始对一部分生命有所歧视,另一部分有所偏爱,很多植物是动物的美餐,而很多动物是另一些动物(肉食)的佳肴,如果要回到那样的自然,我想谁也不想成为人家腹中之食,相反是把人家食之腹中。”[14]16实际上,“人是生态系统的普通一员”只不过是用含混性的语言规避了本应严肃思考的环境问题,他们忘记了环境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了人这个现实的基点是不可能化解生态危局的。对于这种将人还原、定位于自然共同体中的“单边主义”的运思方式,我国生态伦理学者郑慧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自然共同体中,人所遵从的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都是那种纯粹的或有机体的自然规定性,“人与自然或所有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达尔文说的那种纯粹的生存竞争的演化关系”[15]。如此一来,在自然共同体之下,人对自然具有伦理关系的结论就不可能必然得出。可以看出,封闭于生物学境域内勘察与诠释人对自然界的伦理态度只能是一种囿于生物主义的癫狂与迷乱,这只会导致自然荒野的无人化和环境问题化解的责任虚位。这样,纵有关爱自然的豪言壮语,也难有对当代生态问题的真正言说,更别说有实实在在、落地生根的具体举措了。
三、人与自然互动的双重意涵:生态文明理论建构与创新的人学之维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理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支撑。囿于“自然人”与“利己人”的形而上学割裂与对峙,西方生态伦理厘定的人学基准是难以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供强大后盾与理论支撑的。为此,跳出旧有的运思理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的双重意涵为枢轴,从“人学”这一维正确把握“人”这一元哲学问题,就成了建构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现实路径。
一方面,基于人与自然的辩证互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拒斥将人与自然等同的生态中心主义,以暖融融的“人的”生态学代替冰冷的“纯粹科学”的生态学。诚然,大地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根基与承载者,我们要实现人与世间万物的多元共生,但这不是消解人的主体性[16]。生态优先绝不能误读和错估为蚂蚁、艾滋病毒比人类还重要,授予非人自然以特权,走向厌世主义。其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与强调,而在于这种主体性的无限膨胀。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人之主体地位的保留与否,而是人类作为主体是否恰当地运用了主体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7]。这种生态文明理论也绝不是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否定。实践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方式,恩格斯把“动物最多是收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看成是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也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是,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7,人类正是借由实践才得以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向迈进。生态中心主义似乎忘记了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必须以自己的实践行动改变原生态世界的简单道理。有学者还认为:“只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以人为中心,人类就必然倾向于把自身利益和地方、民族、国家等局部利益置于生态整体利益之上,必然倾向于为自己的物欲、私利和危害自然的行经寻找种种自我欺骗的理由和借口,生态危机也就必然随之而来,并且越来越紧迫。”[18]不可否认,这种隐忧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此类观点混淆了以人为本与以人的利益为本的不同特质。事实上,离开以人为本或是人的生活目的,生态系统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是纯粹的自然运动而已。反对以人的利益为本并不能放弃对“以人为本”的执着与坚守。
另一方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夸张式的自我阿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对人与自然博弈的非合作性的自觉矫正中牵引人的生存状态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之境。以利己主义为核心取向的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用物化的短期意识与物化的近视行为来互相拱卫与相互印证,这既无法担当保护自然的重任,也无法实现人类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基于人与自然互动与耦合的双重意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主张:人之为人,不是利己主义的生物式存在,自觉地关爱、体悟自然是人向自然复归走进,并跃升到自由全面发展之境的必然要求。固然,人首先要“活着”,不过仅仅局限于此只能是“非真理”的不错。恰如清华大学卢风教授敏锐地看到的:“只有当我们能重新做人时,我们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19]411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是要反思和追寻“做人”或“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利益或物质根基对于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是把人与自然物区分开来的质性规定[20]。以利益决定人对自然的关爱,这就把人降低为了生物的层面,而没有看到人与动物的根本界限。正如马克思认为的,如果把“吃、喝、生殖”等等机能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成为人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就只能是动物的机能[4]55,由此产生的需要也只是“非人的”“粗陋的”动物需要。如此一来,扬弃动物式的“利己主义”生存范式、反对“无止境的生产=完全的幸福”的“自掘坟墓”式的信条、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之为人的本性转变就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必然诉求与遵循。这也明确地提示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为理论枢轴,创建人们的新的生存方式[21],在“发展”中促“环境”,在“环境”中谋“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正和博弈和共生共荣。
综上,凭借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这一中介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秉持自然向人生成与人向自然辩证复归的双重意涵。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理念,立足当代中国的生态实践,在对人与自然零和博弈的自觉矫正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牵引人类在生态逻辑与人学逻辑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微妙的平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人学观双重意涵的创新和拓展,也是对当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理论自觉与积极应答。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英]乔纳斯·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韩立新.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与环境保护思想[J].哲学研究,2002(2):6-13,79.
[6]陆树程,崔昆.论人类中心论的本质[J].伦理学研究,2011(2):88-93,141.
[7]李勇强,孙道进.生态伦理证成的困境及其现实路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7):73-77.
[8]雷毅.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1]Warwick Fox.Deep Ecology:A New Philosophy of Our Time?[C]//EnvironmentalEthics,An Anthology,Blackwell,200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美]墨迪 W H.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J].章建刚,译.哲学译丛,1999(2):12-18,26.
[14]杨焕明.关于唐善教授《自然与人为》的回应[M]//乐黛云,[法]李比雄.跨文化对话(5).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5]郑慧子.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2):1-4,13.
[16]杨雨婷.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12):86-90.
[17]丰子义.生态文明的人学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10(7):5-10.
[18]王诺.“生态整体主义”辩[J].读书,2004(2):25-33.
[19]卢风.启蒙之后[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20]王亚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5-18.
[21]张学书.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