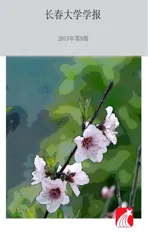钱钟书论“才与学”
2015-02-20陈颖
钱钟书论“才与学”
陈颖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钱钟书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论话语中,独具慧眼地拈出了“才而不学”与“才须学也”这来自两极的理论言说,并以宏阔现代的眼光对这一对理论话语进行会通与创化,有效地激活并提升了“才与学”的传统文论命题,为我们探寻文学创作主体条件的深层理论奥义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创作规律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与启示。
关键词:钱钟书;才;学
收稿日期:2015-04-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
作者简介:陈颖(1974-),女(满族),辽宁大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批评理论及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
英国诗人彭斯认为,人只有作为“他者”而“被看”,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才能以别样的眼光来审察自己。钱钟书的文学研究正如同彭斯的“他者”之镜,他总是力图以“陌生化”“外在”的眼光,从“非我”的新鲜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将古今中西的文学理论“捉置一处”,在异质理论话语之间不断汲取各种理论营养,在此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理论自身的运化与提升,从而在文学本体论、创作规律论及文本批评论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颇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对文学创作主体条件的理论探寻中,钱先生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论话语中,独具慧眼地拈出了“才而不学”与“才须学也”这来自两极、具有差异性的理论言说,并以宏阔现代的眼光与视阈,对这一对理论话语进行会通与创化,提出了“艺之成败,系乎才也”“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兼采为味”“化而相忘”等精见卓识,进而有效地激活了“才与学”的传统文论命题,为我们探寻文学创作的主体条件的深层理论奥义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创作规律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与启示。
1两种声音:“才而不学”与“才须学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重视创作主体的先天禀赋和特殊才能,有很多关于“艺贵有才”的论说。如东汉王充《论衡·佚文》“文辞美恶,足以观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宋濂《刘兵部诗集序》“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与此相应,西方文论也向来强调创作主体的特殊才能和智慧。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主张“诗灵神授”,把诗人视为神的喉舌或代言人,认为“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并非凭借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1]。尔后,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诗灵神授”说逐渐为张扬主体性的“天才”论所取代,把天生的秉赋才能视为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言:“天才是天生的心灵禀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制定法规。”[2]
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作家确实需要与众不同的能力和才情。但创作主体之“才”,是否仅仅来自某种先天的素质,它与后天之“学”有无关联呢?
围绕着这一“才与学”的问题,中西方的文学理论研究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才而不学”与“才须学也”。前者强调天分,认为创作才能有赖于作家的先天秉赋。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命笔”;赵翼《论诗》“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等等。后者则侧重学力,他们认为,创作才能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更需要后天的积学磨练。如《荀子·劝学》篇曰“真积力久则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功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减。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
钱钟书将前人这些有关“才”与“学”的见识捉置一处,平等对话。作为“主持人”,他并没有固守一家之见而作正误判别,而是尊重各家观点,执二持中,融贯综核,吮英咀华,进而全面深入地解析了主体才能与知识学养之间的关系。
2一场对话:“性灵说”与“妙悟说”
在《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内蕴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对话精神。这种对话,不是在言说方式上采取“你问我答”的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在具体的理论阐解中注重不同思想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补,注重消解主客对待及坚执主义,力主“和而不同”。在理论著述中,钱先生往往围绕着某一论题,将古今中西的不同时代文化语境下的相关理论话语钩连到一起,在彼此思想的相参互补中展开理论的多元对话,仿佛是在举行一场“狂欢化”式的畅谈会。可以说,“对话”不仅是钱先生文学思想生成的特有语境,也成为他的文学研究范式中所内蕴着的核心精神。
有关“才与学”问题的理论探讨,正是在一场场“对话”活动中展开的。这一话题,首先是以钱先生审视袁枚的“性灵”与“人力”相互关系的诗学见解时引发的。
袁枚论诗主“性灵”,在他看来,“诗是性情,近取诸身足矣”(《诗话补遗》卷一),“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随园诗话》卷六)。但他在强调创作主体“天分”的同时,也认识到后天的“学力”与“人力”在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性,认为“人力未及,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人工求之”(《随园诗话》卷四)。尽管袁枚将“性灵”与“人力”并举,但他对前者的过分强调,留给后世读者的是只重前者之“天机凑合”,忘却后者之“学力成熟”的偏颇认识,进而使他们将创作看成是一件“任心可扬”的方便事,以为“信手写便能词达,信口说便能意宣”。基于此,钱钟书指出,从客观效果上看,《随园诗话》一书“无补诗心,却添诗胆”,鼓舞了一班自恃有天分者创作出“粗浮浅率”的作品来[3]205。
在指陈了袁说的流弊之后,钱钟书进一步指出,袁枚的“性灵说”虽在强调创作主体灵心慧性的同时,认识到了后天的“学力”与“人力”的重要性,但其将“性灵”与“学问”对举,甚至称“学荒翻得性灵出”,这就在客观上将“才”与“学”机械地对立起来,不免有割裂之弊。相比之下,严羽《沧浪诗话》中的“妙悟”说就显得更为圆通:“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对于此说,前人多有论及,且毁誉参半。这些批评见解多数“不解沧浪之旨”,未能跳离门户之见,极少持平之论。钱钟书则以他一贯的“变易不居”的辩证运思方式,从更高的理论角度对严氏之说作了取心析骨式的阐发与丰富。他说:
严沧浪《诗辨》曰:“诗有别才非书,别学非理,而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曰“别才”,则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也;曰“读书穷理以极其至”,则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见诗中“解悟”,已不能舍思学而不顾;至于“证悟”,正自思学中来,下学以臻上达,超思与学,而不能捐思废学。犹夫欲越深涧,非足踏实地,得所凭藉,不能跃至彼岸;顾若步步而行,趾不离地,及岸尽裹足,惟有盈盈隔水,默默相望而已。[3]99
严羽“借禅以为喻”,把佛学术语“妙悟”运用于文学批评。他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创作者要以“妙悟”为“当行”和“本色”,应能够善于凭借内在的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文学艺术之奥妙,默会领略“诗家之三昧”。从现代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严氏之“妙悟”,实际上指的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犹如学禅悟佛一样的认识上的飞跃,主体以此来领悟诗的兴趣及艺术特质。
钱钟书颇为激赏严羽对“悟”的解读。他认为,文学创作确实如同学禅悟佛一样,需要作家具备特殊的艺术悟性。无论是灵感的获取还是想象的激发,都有赖于主体之“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这种“悟”,可分为“速悟”与“迟误”两个不同的层次:“悟有迟速,系乎根之利钝、境之顺逆,犹夫得火有难易,系乎火具之良楛、风气之燥湿。速悟待思学为之后,迟悟更赖思学为之先。”[3]98在他看来,创作主体所具有的不同的天赋秉性、成长环境造就了自身“悟”的渐顿迟速,就像引火工具的优劣、周围空气的燥湿等条件影响了取火之难易快慢一样。同时,除了天分与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无论是“顿悟”还是“渐悟”,又都与主体后天的思学相关联:“顿悟”,先“悟”后“思”,是“因悟而修”“以修承悟”的“解悟”,亦即沧浪之“别才”;“渐悟”,先“思”后“悟”,是“因修而悟”“自思学中来”的“证悟”,亦即沧浪之“读书穷理以极其至”。也就是说,对于创作主体而言,仅仅具有先天的悟性还不行,悟性还需后天思学的陶养。总之,悟与思学对于作家创作才能的形成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徒有悟而无思学,就不能脚踏实地、有所凭借,难以成功地跃至艺术的彼岸;徒有思学而无悟,就会亦步亦趋、循规蹈矩,也只能无奈地隔岸而望了。
由此看来,钱钟书是肯定天才的。他颇为赞赏颜之推《家训》中“为学士亦足为人,非天才勿强命笔”的言说,认为“为学者”与“为文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先天不足,而后者则必须具备先天的秉赋才情不可。如不具备而勉强操笔,则徒劳费功。不过,他对天才的理解并不拘囿于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而是强调后天思学的相辅之功。在他看来,“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也”[3]40。也就是说,一方面,文学创作是需要天才的,创作主体的才情如果先天不备,后天怎么磨砺雕琢也无用;另一方面,才与学是相辅以成的,创作主体的先天材质具备以后,还需要辅之以后天功夫,以后天之“学”来促成可塑之“材”转化为创作之“才”,即“相质因材”。因此,在他看来,所谓创作天分,并不仅仅指主体先天的秉赋才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显现为主体是否具有善于通过后天思学来藏拙补缺、扬长避短的能力:“窃以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3]97
3学化于才:“兼采为味”与“化而相忘”
在“才与学”问题的探讨中,钱钟书并没有止步于对“性灵说”及“妙悟说”的对话性阐发,而是以宏阔现代的理论眼光对这些理论话语进行会通与创化,进而提升出自己对“学化于才”问题的理论识见,提出了“兼采为味”、“化而相忘”等精见卓识。
可塑之“材”怎样才能通过后天努力转化为创作之“才”呢?钱钟书认为:“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3]98。也就是说,创作才能的获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作家在自身天赋资禀的基础上,经过后天长久艰辛地学习磨练得来的,是在不断地读书与实践、学(博采)与思(力索)中获得的。其中,后天的通学博采是培养创作才能的主要途径。前人有很多以蜜蜂采蜜来喻后天之学的论说。如张璠《易集解序》“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暄素有章,甘逾本质”[4]。钱钟书对此类说法颇为认同,并且身体力行,努力成为一只“以兼采为味”的“蜜蜂”。他通过后天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融化百家,具有了匠心独运、自成一味的艺术才能,进而在创作与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当然,通学博采只是后天之“学”的途径之一,生活实践对于创作才能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早年的钱钟书对这一问题颇不以为然,但他后来逐渐走出了原来的认识误区,越来越重视生活实践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如在《宋诗选注·序》中,他就对宋诗作者严重脱离生活、“资书以为诗”的通病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5]
除此之外,创作才能的获取也离不开主体不断的艺术实践和技能训练。“技术功夫,习物能应;真积力久,学化于才,熟而能巧。专恃技巧不成大家,非大师不须技巧也,更非若须技巧即不成大家也。”[3]211创作主体如果不谙技巧,就会使作品成为“不词之文”[3]211。
然而,生活经验与知识学问的积累本身并不是创作才能,创作主体还需要进一步将这些经验与学问巧妙地“内化”,使“学”化于“才”。钱钟书说:
记闻固足汩没性灵,若《阳明传习录》卷下所谓“学而成癖”者,然培养性灵,亦非此莫属。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人己古新之界,盖超越而两忘之。故不仅发肤心性为“我”,即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应我需、牵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有。[3]206
他认为,对于不善读书的人而言,学识记闻难免会窒塞湮没他的创作性灵,正如王阳明所说的“学而成癖”。而真正优秀的作家,并不仅仅是“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他“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6]229,能将平日读书识闻中所获取的外部经验与知识学问沉浸滋养在自己的心血里,使之成长为自身机体中的神经和脉络,“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6]78。这样,才能陶冶孕育出充沛不竭的审美情思,进而在创作中“神光顿朗,心葩忽发”。
钱钟书不但将创作主体之“才与学”的关系阐释殆尽,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较严羽等前辈论者更为周匝全面的创作才能认识。他说,“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3]39也就是说,文学创作虽然肇始于作家对世间万物的生命情感体验,但是,文学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它要求主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和性情本身不能直接进入作品,而需要对其加以艺术的升华与转化,使之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审美情感体验。同时,文学又是一种讲究“诗艺”的艺术形式,它要求创作主体能够娴熟巧妙地驾驭语言文字,能够运用恰当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既把孕育而成的审美情感体验完美地表达出来,又创作出符合“诗艺”的艺术审美原则与规范的文学文本。这样看来,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主体内在禀有的艺术审美才能,这种才能贯穿于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发现、创作动机、想象构思、文辞物化等各个环节,涉及到古人所说的悟、情、灵、学、识、力、法等多方面因素,体现为一种综合性的审美鉴赏和创造能力,而非沧浪之“妙悟”或随园之“性灵”所能涵盖。
综观《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我们看到,钱钟书的文学研究往往从文本细节出发,将处于不同历史文化时空语境中的理论阐说一一请出,在相互比较、互证、合观、连类中,力图消解理论之间的樊篱与沟壑,打破既有视域下的古今之界与中西之别。这一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克服了中西文学思想难于“对话”的话语困境,为我们深入思索如何激活本土文论话语资源,如何建构起一套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中国式”的文论话语,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与启发。可以说,他的文学研究改变了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一直以来较为封闭、单一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1世纪学术研究向开放与多元性方向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其无论对于我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还是当下的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8.
[2]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52-153.
[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50-1251.
[5]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14.
[6]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
责任编辑:柳克
Ch’ienChung-shu’sViewof“TalentandLearning”
CHENYing
(CollegeofLiterature,DalianUniversity,Dalian116622,China)
Abstract:Ch’ien Chung-shu’s found the different theories about “talent and learning” in the multitude of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s,and he carried out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in his 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rt,which effectively activated and promoted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proposition about “talent and learning”, not only opening up a new way for searching deep theoretical meaning of literature creation conditions,but also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of creation rules.
Keywords:Ch'ien Chung-shu's;talent;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