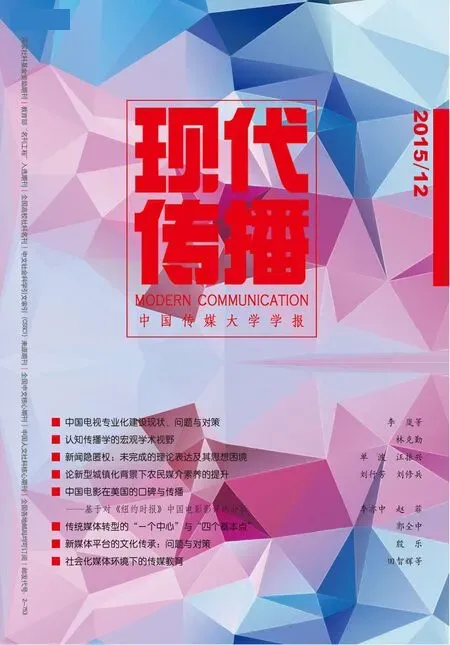新闻隐匿权:未完成的理论表达及其思想困境
2015-02-20汪振兴
■ 单 波 汪振兴
新闻隐匿权:未完成的理论表达及其思想困境
■ 单 波汪振兴
本文梳理了“新闻隐匿权”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以及这一概念的法理表达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在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新闻隐匿权从提出直至今日,并非完全都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其对新闻自由的促进作用也令人存疑。各界围绕这一概念的种种争论,也揭示出新闻隐匿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性控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
新闻隐匿权;新闻自由;新闻法;公共利益
新闻隐匿权,或称新闻记者的拒证权,在英文原文中译为“journalist’s privilege”或“newsman’s privilege”,是指对媒体及其从业人员享有未经消息提供者的许可不向外界披露消息来源的特权(privilege),包括新闻媒体可以拒绝法院要求出庭作证、公开消息来源以及对资料不受搜查与扣押的请求权①。新闻隐匿权在美国并不算是一个新概念。有学者发现,早在1722年,富兰克林的兄弟就因为拒绝交代匿名信源而被关押一个月②。1848年的纽金特案③是第一起有记载的关于新闻隐匿权的案件,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或争论④。但之后的160多年,围绕新闻隐匿权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歇,折射出新闻隐匿权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和思想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上重要隐匿权判例的分析,来梳理隐匿权发展的历史,并揭示这一理论中所蕴含的思想矛盾与困境。
一、托尔案:新闻自由的限度与权衡
在纽金特案结束110年以后,新闻隐匿权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节点。1958年,《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娱乐记者托尔(Marie Torre)在报道中称,女演员嘉兰(Judy Garland)自称“自己胖的过分”⑤。嘉兰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对托尔提起诉讼,并要求其供出提供诽谤信息的信源。⑥托尔拒绝了这一请求,她认为法院不应迫使她交出匿名信源,否则即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⑦,因为“这限制了信息自由地流向报道者和公众”⑧。
这是记者第一次以第一修正案作为武器,来主张自己的隐匿权。在此前的所有案件中,记者和律师都仅在职业道德范畴,至多是在普通法范围内,寻求关于隐匿权的支撑,而且从未得到过承认⑨。托尔一开始也是以职业道德的理由来寻求隐匿权支撑,因为实际上提供给她信息的信源并没有提出匿名要求。在基于职业道德和州立法的辩护被法官驳回后,律师随后辩称,记者的隐匿权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和实践…以及公众利益”和“宪法基础”⑩。《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主编和发行人里德(Ogden Reid)也开始将隐匿权与宪法中所规定的新闻自由联系起来,并强调,“不披露信源的特权”深深影响着“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而这正是托尔所说的记者“赖以生存的东西”。因此,提出隐匿特权的直接理由,就是为了避免记者和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受到制约。托尔方面认为,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事关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因此坚持不肯交代信源。其辩护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即如果信源不能信任记者,就会停止向媒体提供信息,媒体也因而无法将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公众。此外,除了要保护媒体可以畅通地获取信息,托尔认为法院也应当保证“公众获得自由而不受限制的信息”(11)这一公共利益。托尔方面的辩护,实际上是在努力将自己所主张的隐匿特权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隐匿特权是一种专属于新闻媒体和记者的利益,信息的自由流动则是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托尔方面将这两种利益结合起来,认为出于新闻自由这一公共利益的目的,就必须对新闻媒体的隐匿权加以保护。此时,隐匿权成为一种手段,而问题在于,在使用这一权利时,如何证明新闻媒体和记者怀有正当目的?更何况,即使怀有正当的目的,也未必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嘉兰方面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托尔的报道根本与公共利益无关。因为涉案报道仅是一桩娱乐事件,并不涉及监督政府、贪腐或其他公权力事件,难以与公共利益扯上关系。况且,嘉兰也并没有谋求对托尔的报道进行事先审查或阻碍其发表,仅要求其在发表后提供信源而已。嘉兰方面认为,记者即使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延伸到托尔身上,嘉兰的律师在法庭辩护中称,“如果要让一位娱乐专栏作家免于担责的话,也太离谱了。”(12)
但嘉兰的这一说法并未得到重视,不仅斯图尔特法官未考虑这一点,此后大部分学者对托尔案的讨论也都忽视了该案所涉新闻报道的具体性质。实际上,尽管托尔辩称自己应当享有与所有严肃记者一样的权利,但托尔的报道根本与媒体监督政府的“看门狗(Watch Dog)”角色无关,所传递的信息也仅是针对明星个人的娱乐信息,与公众利益毫无干系,甚至有以新闻作为工具谋取私人利益的嫌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托尔真的能以保护新闻自由的目的作为挡箭牌,来主张隐匿特权吗?
显然,时任联邦第六巡回法院法官的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并不在意这一疑问,他关注的是公正审判的重要性。斯图尔特在衡量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时,认为作证义务毫无疑问会在某些时候伤害到新闻自由,但这是新闻自由为了总体的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必要牺牲。而且该案对新闻自由所产生的损害相对而言并不大,由此产生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是可以通过公正审判所带来的公共利益来弥补的。因此,法院在最终的判决书中写道,新闻自由“对于一个自由社会而言是珍贵且至关重要的,但却并非绝对的。”由此看来,新闻自由也是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用来权衡社会利益冲突的一种手段:新闻自由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某种不可触碰的绝对权利,而是对某种必须保护的核心利益的修辞。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同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判决的结果应基于对二者的价值均衡,而不是用某一种利益完全压倒另一种利益。判决书中斯图尔特法官的观点随后被大量媒体引用:
“新闻自由,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靠着勇气所赢得的,是自由社会的基础。但是公正审判和探寻真相的力量,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础。目击者有作证义务的这一传统,几乎和保护新闻自由一样,同样深刻地扎根于我们的历史之中。”(13)
但为了避免新闻自由的核心利益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斯图尔特也对托尔案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14):
“必须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所处理的案件,并不是在利用法律程序强迫记者披露他全部的信源,也不是在寻求与案件未必相关或未必重要的信源。此案的上诉人所要求披露的信源,是深入到原告所涉案件的核心的。因此我们才认为根据宪法,记者并没有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
也就是说,该案的结果并不适用于那些强迫记者披露与案件核心 “未必相关”(doubtful relevance)的信息的案件。也就是说,对记者进行不怀好意的骚扰,或者强迫其披露与案件无关的信息的行为,会被认为是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规定。
在此案中,法官最终判定,嘉兰所寻求的信息合理正当,对此信息有强烈而迫切的需求,且无法通过其他手段获得,而托尔所掌握的信息与原告嘉兰的诉求直接相关,即“深入案件核心”,并且此前无先例承认记者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的特权,因此,判定托尔应当披露信源。托尔拒绝了这一请求,随后被以“藐视法庭”罪判处10天监禁。
尽管托尔最终败诉,但斯图尔特法官已经很明显地表露出了对于隐匿权的认同,这在此前的所有案件中都是没有过的。记者拒绝披露信源的这一权利,第一次在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权衡中被考量。而在此后影响深远的布莱兹伯格案中,斯图尔特法官的观点更进一步,更偏向于保护隐匿特权而非公正审判。
因此,虽然输了官司,但《纽约先驱论坛报》主编里德(Ogden Reid)认为这是新闻界的一场胜利,将这一判决结果称为对公众利益的一种延伸(15)。如他所言,这是法院第一次认真考虑记者所主张的隐匿权,也是法院第一次承认,强迫记者披露信源是对新闻界获取信息能力的损害,是对新闻自由的损害。
与《纽约先驱论坛报》态度不同的是,各大新闻媒体并没有表现对隐匿权的热衷。在托尔案结束后,媒体普遍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结果的认同,以及对寻求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反省。《纽约时报》的评论《正义和自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没有哪项自由权利是完全绝对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没有哪件事是黑白分明的”,“许多由宪法所保障的权利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华盛顿邮报》则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同社会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冲突,发表了题为 《权利体系》(Galaxy of Rights)的评论,向世人指出,“当两项重要原则相撞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所说的自由的本质,并不是对某一项绝对权利的简单陈述,而是要在一个复杂的权利体系中妥善处理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16)。媒体界在新闻评论中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即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也并非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必须在与其他社会利益权衡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丹尼尔·贝尔曾说,“任何一种价值观——不管是自由还是正义——在被当做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并被严格运用的时候,会导致过度。没有一种单一价值观能满足内在冲突的各种目标,甚至当大部分人希望目标各不相容时也是如此。所以必须明白在解决这些不相容的努力中要放弃些什么。”(17)正如丹尼尔所言,不同的社会价值之间无法等同,也经常难以相容,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即使是像以赛亚·柏林一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自由是一种价值,平等或公正或正义也是一种价值,二者既不等同,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联系。在实践中,互相冲突的规则或原则必须有一些做出让步,“如果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那么,就没有这样的原则”(18)。在新闻自由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也必须找到现实的折衷方法。
除了这一共识之外,托尔案更重要的是展现了隐匿权问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是新闻自由应当如何与其他社会利益进行权衡?尽管斯图尔特大法官给出了隐匿权官司中的第一个平衡杠杆,即记者所掌握的证据是否“深入案件核心”,但仅靠这一标准显然不足以在复杂的权利体系中做出合适的平衡。
二是托尔案中有意无意被忽视的问题,即如何让新闻自由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娱乐八卦或一己私利服务,沦为记者的“特权”?
二、1960年代的争论:威权的侵入与媒体独立性危机
伴随着托尔案的结束,美国社会进入风起云涌、令人百感交集的1960年代。在深陷越战泥潭的同时,国内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各类社会问题接连涌现,社会矛盾激化。职业的特殊性,使得新闻记者与各种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异见者的联系迅速增多,因而掌握了大量甚至连政府都无法获得的消息。政府和立法者因而经常要求那些已经与“颠覆组织”的领导或普通成员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记者协助调查,这种协助有时候是自愿的,但更多时候是被强迫的。随着“新左翼”(New Left)分子的增多,来自政府和司法机构的威胁越来越强,记者受到传唤、被强迫披露信源的事件迅速增多,因而抗议之声也越来越大(19)。
1968年,一些新左翼分子和极端人士在芝加哥举行了大游行,包括NBC、《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等全国性的大媒体,都对该游行中传达出的反对越战和抗议现任政府的主张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这些报道引火烧身,导致美国政府在两个方面对新闻媒体施加了巨大压力。先是时任美国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抨击了美国媒体,并要求他们 “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客观性”(20)。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更为棘手,美国司法部门对媒体和记者手上所掌握的信息源兴趣骤增:1970年,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的米歇尔(John Mitchell)甚至公开表达了利用新闻媒体所掌握的信息来调查极端分子和抗议活动的急切愿望(21)。新闻界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即使司法部长在几天后再次发表讲话,希望能够“消除误解”,但新闻界无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政府的强力威胁。有学者将这种传唤称作是政府强力部门利用的“恐吓和骚扰的武器”,CBS将其称为“对媒体的狩猎证”,NBC则将对媒体的传唤称为“一种被宪法的自我限制理论所禁止的事物”(22)。在政府和媒体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CBS记者弗里恩德利(Fred Friendly)说出了新闻界对自身独立地位不保的忧虑(23):
针对新闻记者的传唤实际上是将记者当做一群搜遍全国的治安小组,利用记者对抗异议。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公诉人将记者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并且“将法院的传唤权当成了他们自己工作的代替品”。
弗里恩德利的言论迅速被新闻媒体传遍全国。记者们声称,政府实际上是在利用媒体获取新闻的能力来为自己的调查服务,将记者当成了特工,如果记者与政府合作,就会从根本上毁掉新闻业。因此,记者们希望法院能够建立承认记者隐匿特权的“盾牌法”(Shield Law),避免媒体独立地位的丧失(24)。
但在国家安全的考虑下,反对记者享有隐匿特权的声音同样强大。一位评论嘉宾也在CBS的节目中警告说,媒体不应该停止反思自己的问题,而应该“邀请政府进家门”。在众多反对声浪中,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戈德斯坦(Abraham Goldstein)的评论发人深省(25):
“任何允许隐瞒信息的许可,很显然都带有这样一种风险,即犯罪行为无法被发现或裁决,或者被告的无辜无法得以证明…今天,被保护的信息可能关乎‘黑豹党’和‘争取民主学生协会’。而明天,就可能涉及到掩盖公共官员或公司总裁腐败或滥用权力的信息。”
戈德斯坦随后还与两位支持记者隐匿权但理由不同的杂志主编进行了访谈,认为无论是为了保护“普通人”远离大政府的强权,还是为了将宪法自由带给更多人(甚至包括反政府革命者),他们所声称的所谓新闻记者的道德公约中的自相矛盾都是很明显的:如果将某信息提供给政府,一家报纸的编辑方针可以得到更好地实现(如惩罚或关押“不爱国的”市民),那么报纸也承认这时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特权。如果在紧急状况(如谋杀或国家安全)时就接受传唤供出信源,也相当于承认了隐匿权并非不可质疑。因此,隐匿权似乎只在新闻媒介自己受到威胁,而不是公众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被拿出来主张,只是在新闻机构在个人层面不想再忍受传唤的时候,拿出来使用的一个挡箭牌而已,是为了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个人利益,而并非公共利益。
尽管外界对媒体声称具有隐匿特权的说法有诸多质疑,但媒体强大的舆论力量最终仍占据了上风。1970年10月,司法部长为了缓和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声明以后司法部的调查将遵循以下五条原则:1.在每起案件传唤记者之前,都考虑限制新闻自由所可能带来的公众利益损失。2.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来从非媒体渠道获得信息。3.当准备进行传唤时,事先与媒体进行沟通。4.如果沟通失败,除非有总检察长的命令,否则不得传唤记者。5.所寻求的信息必须是至关重要,且无法从非媒体渠道获取,或是出于紧急情况以及其他非常规情形时(26)。
伴随着1960年代末的抗议,新闻界终于迎来了第一起记者隐匿权得到法院正式承认的案件(27),即1970年的考德威尔案。《纽约时报》的记者考德威尔(Caldwell)报道了加州黑豹党的新闻,并在随后的案件调查中被要求出庭作证。但考德威尔不单拒绝回答关于他报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甚至声称即使在陪审团面前露面,也会损害他与黑豹党秘密信源之间的关系,进而违反他所享有的第一修正案权利(28)。考德威尔所主张的特权被联邦第九巡回法庭所接受,该法院为新闻隐匿权的使用添加了一条新的判断标准:除非政府能够“明确的证明对记者的证据具有不可替代的、强烈的、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需求”,否则不能强求考德威尔出庭作证,从而在国家利益和新闻自由之间设置了一个权衡点。
在以记者胜诉而告终的考德威尔案后,新闻界人士对获得隐匿特权的期待也迅速升温,学界也将考德威尔案与沙利文案相提并论,认为该案实际上是延续了沙利文案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原则,扩展了记者的权利,保障了信息的自由流动。“既然考德威尔的请求已经被最高法所承认,那么看起来记者已经可以超越隐匿特权这一领域,寻求其他被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新闻自由权利了。”(29)但紧接而来的布莱兹伯格案似乎证明,这种认识实在是太乐观了。
三、布莱兹伯格案:思想的争鸣与现实的困境
1972年,布莱兹伯格案(30)使联邦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该案被认为是新闻隐匿权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关于隐匿权案例的判决。美国联邦法院对于该案的最终判决是:
“第一修正案并没有使记者免于这样一项义务,即所有公民都必须对大陪审团的传唤作出回应并回答与犯罪调查相关的问题。因此,修正案并没有授予他这样一项宪法隐匿特权,同意他可以隐瞒关于大陪审团正在调查的犯罪行为的事实,或隐瞒关于此的信源或证据。”
上面的判决意见,也就是以怀特(Byron White)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派所持有的意见,即记者根本不享有任何基于第一修正案的特权。多数派法官尽管承认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给予了保障,但却更注重大陪审团进行公正审判的利益,认为新闻自由为了公正审判而进行一些牺牲完全可以接受。但除了在两种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外,拒绝承认隐匿特权的多数派法官还提出了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多数派法官认为,尚没有明确清晰的经验性证据证明,如果记者在法庭上交代了信源,就会损害“信息的自由传播”这一公共利益。这实际上是对隐匿特权和新闻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质疑。以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为代表的少数派法官则从更为理论化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认为根据常识和已有的经验,完全可以推断出强迫记者作证会损害信息的自由流动。他们认为,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自由”,而且“在可预见的怀疑之外,从不要求任何实质性证据来证明出版自由可能遭到妨害”(31)。
第二个原因是,多数派法官认为记者在某些情况下之所以拒绝交代信息和信源,是因为他们自己参与了犯罪行为,或是想保护参与了犯罪行为的信源,新闻隐匿权因而成为一种“企图逃避犯罪起诉的产物”,在法庭眼中,这种行为即使是在第一修正案的名义下,也是不可被原谅的(32)。这一怀疑似乎意味着法官对媒体一再呼吁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一个完全独立的媒体的确可以监督政府,但是谁又来监督享有新闻隐匿权的媒体和记者呢?
多数派法官最有力的反对理由则是第三点:如果承认新闻隐匿权特权的话,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实践和理论上的困难”。这源自于一种对“特权”的怀疑。第一修正案真的赋予了记者以“特权”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承认新闻自由重要性的同时,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如果在所有案件中都赋予记者绝对的隐匿信源特权,就会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即记者所享有的权利是高于普通公众和个人的,甚至意味着记者不必负担所有普通公民都必须承担的义务。这真的是第一修正案的初衷所在吗?新闻自由是一项受到宪法保障的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难道记者能够比公民享有更高的自由吗?
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对于第一修正案的解读:“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在这里,speech和press究竟是对“个人(individual)”这一主体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还是强调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保护主体,即“公众(言论)”(public(speech))和“媒体机构”(institutional press)呢?有学者认为,制定第一修正案的初衷,是为了保证言论能对政府产生监督作用,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当时的传播机构还不甚发达,媒体机构向来也没有得到过高于个人层面的保护(33)。实际上,从托尔案开始至今,无论各地方法院和联邦巡回法庭如何认定,美国最高法院始终认为,媒体并没有高于普通公众的特权。
布莱兹伯格案的判决书中称,如果隐匿特权只能由记者享有,那就势必会在法理和操作层面产生困难,即必须界定什么人可以被称为是“记者”,但这本身就与最高法所坚持的传统相悖:“我们的传统认为,新闻自由是属于每个人的,无论是使用复写纸、油蜡纸来制作小册子的人,还是在大都市里使用最先进排版技术的大出版商,都同等地享有这一权利”(34)。因此,几乎所有扮演传递信息角色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记者。在此之外,还要界定这个“记者”在某起案件中是否有免于作证的特权,如判定在该起案件中政府是否对记者的证据具有“强烈的需求”。让下级法院针对每一起案件都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并作出合适的判决,超出了它们的能力,也给下级法院增加了不该有的负担。因此,该案最终的判决书中写道,“最高法院不愿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目标,来进行一场既漫长又艰难的跋涉。”(35)
但多数派法官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隐匿权,他们同时也提出了一种例外情况,即如果大陪审团认为,要求记者交代秘密信息或信源是出于骚扰记者的目的,或意图破坏记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时,记者可以不出庭作证:
“如果记者被传唤,并要求提供与调查的案件仅有微弱或遥远关系的信息,或者他有理由认为他的证词所牵涉到的信源并没有被交代的必要,那么他也应当拥有向法庭提议撤销作证和保护信源的渠道。”
颇富戏剧性的是,曾经主审托尔案的斯图尔特法官,彼时已经从联邦巡回法庭法官升任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布莱兹伯格案中,曾有媒体从业经历的斯图尔特法官放大了其在托尔案中表现出的对新闻自由的支持态度,坚定地支持媒体记者享有隐匿特权,与包括布伦南、马歇尔大法官在内的三位法官一起,成为此案中持有异议的少数派法官(36)。他们认为,记者应当享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受制约的特权。
斯图尔特法官显然更看重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重要性。他认为,强迫记者作证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损害“肯定会在某些敏感而充满争议的特定类型事务中体现出来”。“信息的自由流动”对于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行是一种决定性的要素,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保护那些秘密的信源。因为如果缺乏对隐匿特权的保护,就会阻碍记者“采集、分析和刊载新闻”,这有可能造成记者不愿意尽全力去调查敏感事务,因而损害新闻内容,进而导致公众无法从媒体处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削弱民主社会的基础。
持有异议的法官们认为,需要衡量的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利益,绝不是记者个人的利益,而是一种公共利益,即公众能否获得信息并因此对“通过自由流动的信息做出民主的决策”作出贡献。当然,考虑到法院能否做出公正审判也是很重要的公众利益,异议法官所主张的只是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记者是否应当获得这种特权。为了解决多数派法官提出的实践困难,斯图尔特法官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判断原则,即著名的“三步检验法”。如果要强迫记者交代信源和秘密信息,就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一是有相当理由确信记者所掌握的信息与被诉事实、行为有明显关联性;
2.二是要证明其所寻求的信息不能通过其他对第一修正案损害较小的渠道获得;
3.三是要证明该信息中包含政府迫切需求和压倒一切的利益。
然而斯图尔特大法官所持的意见最终并未被接受,新闻隐匿权仍然未能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怀揣着对媒体丧失独立性的深深忧虑,斯图尔特大法官在最终的判决书上写到:
“法院在此案中最终判决,当记者被大陪审团传唤时,并没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的特权来保护自己的信源。法院因此是在邀请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用威权来削弱媒体一以贯之的独立地位,是要将记者的专业行为变成政府的调查工具。这一决定不仅削弱了受到宪法保护的媒体的社会作用,也将在长远范围内造成弊大于利的结果。”
直到布莱兹伯格案结束,媒体所主张的新闻隐匿权仍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让隐匿权所保证的新闻自由成为一项公共权利而不是记者私利?如何让隐匿权为公共利益所服务?
四、后布莱兹伯格案时代:隐匿权的重生与扩展
布莱兹伯格案彻底否定了绝对的新闻隐匿权存在的可能性,也成为了此后新闻隐匿权案件最重要的援引判例之一。但正如在布莱兹伯格案中九位大法官之间的巨大分裂一样,不同的下级法院在援引此案时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实际上,各级法院似乎受以斯图尔特法官为代表的意见影响更深,多认为记者拥有受限制的隐匿特权。为了实现这种隐匿特权,法院又在“三步检验法”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的判定标准。
在1972年的贝克案(Baker v.F&F Investment Co.)中,原告要求记者阿尔弗雷德·鲍克(Alfred Balk)披露匿名信源,但未获支持。事情起因于鲍克在1962年的报道《大亨的忏悔》(Confession of a Block-Buster)中指出,芝加哥的一位房地产投机商利用种种手段恐吓白人房主低价卖出房屋,然后再将这些房屋高价卖给黑人(37)。之后贝克(Charlene Baker)等人对房地产公司:F&F投资公司(F&F INVESTMENT COMPANY)提起了诉讼,并将鲍克的文章列为了证据,要求鲍克供出文章中的匿名信源。但主审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认为,原告无法证明鲍克是唯一可得的信源,也无法证明披露鲍克的匿名信源对保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判定鲍克的匿名信源并未“深入案件核心”,无需披露(38)。1972年,美国最高法也拒绝对这一决定做出复审。第二巡回法庭在此案中援引了布莱兹伯格案作为判例,认为布莱兹伯格案的判决也承认了记者的第一修正案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高于作证义务的,而该案与布莱兹伯格案不同的是,这是一起民事案件。因此,“法院必须认识到,与强迫记者披露其秘密信源所带来的个人利益相比,记者不披露其秘密信源所涉及到的公共利益常常要大得多。”也就是说,第二巡回法庭认为记者的隐匿特权关涉到公众利益,而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均为个人私利,遵循公共利益高于个人私利的原则,记者在民事案件中可以享有隐匿特权(39)。
多数派法官在最终判决中留下的小小缺口被越撕越大,新闻隐匿权的未来竟有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之意。该案之后,除了第六巡回法庭以外,其余十二个联邦巡回法庭都在各类判例中承认记者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受限制特权,这似乎更像是在遵循斯图尔特大法官而不是鲍威尔的意见。第六巡回法庭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在一起案件的大陪审团会议记录(Grand Jury Proceedings)中写到,如果将鲍威尔大法官的意见当做是对斯图尔特法官的支持,那无异于是在采用少数派的意见来代替多数派的意见(40)。
但无论如何,新闻隐匿权如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记者领域,就难以被称之为一项公共权利,也不得不让人怀疑隐匿权究竟是在为公共利益还是记者私利所服务。无论对第一修正案做何解读,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即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绝不是属于某个特定机构或某些特定个人的,如果要对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新闻自由权利按照职业进行不同划分的话,本身就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所内涵的原则,即不偏爱某一种特定的言论或某些人的言论,或压制其他言论。
更何况,界定何人属于“记者”的标准难以制定。在布莱兹伯格案中,多数派法官就指出,在美国传统中,“孤独的小册子作者”和“大都市的报纸出版商”一样,都受到第一修正案中的出版自由条款的保护。“几乎所有扮演传递信息角色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记者”。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模式从以媒体和专业记者为中心的单一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普通人为核心的多点状模式。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社会实际状况上考察,都应对新闻隐匿权的适用主体细加考量:一方面保证对匿名信源的保护能够作用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要保证这种权利不仅属于狭义的新闻媒体和记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级法院继续提出更为细致的标准和原则,试图对新闻隐匿权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规范和控制。
在1987年的范·布罗(Von Bulow)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认为,虽然主张隐匿权的被告是一位记者,但由于其搜集信息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写作,而不是为了向公众传播这些信息,因而不能获得隐匿特权的保护。第二巡回法院在此案中提出了一种判断标准,即无论主张隐匿权的人是不是记者,都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即他所参与的必须是新闻采集过程,其采集信息的初始目的必须是为了传播信息。这一此后被称为范·布罗标准的判断方法后来得到了广泛采用。这一判断标准实际上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基于第一修正案的隐匿权如果存在,其所保护的也只能是公共利益,而不是私利。为了公共利益起见,只有当隐匿特权的使用能够使得流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总量增加时,才可算为正当。
1993年,第九巡回法庭在肖恩案(Shoen v.Shoen)中,认为作家罗纳德·沃特金斯(Ronald Watkins)可以主张隐匿特权。因为罗纳德·沃特金斯虽然不是记者,但却是“一位致力于写作时事和争议事件的调查作家”,他获取信息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向公众传播(41)。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媒体之所以成为媒体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42)。这一判例标志着新闻隐匿权的主体不再局限于狭义的媒体和记者。
这两起案件的判决结果联合确立了一个新的复杂原则:一个人能否声称自己为享有隐匿特权的记者,取决于他在一开始采集信息时的意图;只要一个人参与了采集和传播新闻的活动,即使他不是某个媒体机构的成员,也可以声称自己具有隐匿特权(43)。这一原则的操作,无疑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也更具难度。
“记者”的身份由此得到了扩展:并不仅是指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只要参与了新闻调查活动,采集了新闻,并且目的是为了向社会传播这一新闻,就可以被认定为记者。初始目的必须是为了向社会扩散这项新闻,意味着隐匿权无法成为媒体或记者的私人武器,而是只有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一公共利益,才有资格享受这一特权。作为一项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新闻隐匿权的主体开始从新闻机构成员向全体公民扩展。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判断标准继续扩展。2004年,格雷迪(Jason O Grady)在其个人博客上披露了苹果的新产品计划,随后遭到苹果公司起诉,要求其披露消息源。2006年,美国第六巡回法庭判决苹果公司败诉,理由是该博客同样属于新闻媒体的一种,只要作者发现具有报道价值的信息,即使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编辑汇总,而仅是将信息原文公布在网站上,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在博客上发布信息是一种报道行为,应当与传统媒体获得同样的保护(44)。
这一判决又扩张了媒体机构的范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新的判定原则: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定义应当从其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和角色出发,认定某机构是否属于媒体,要看这一机构“做了什么”,而不是看该机构“是什么”。即应当从其发布的内容,而不是组织的形式上来判定(45)。
五、结语
至今为止,关于新闻隐匿权的争论仍未止息,法律地位也极不稳定:联邦最高法院从没承认过记者拥有隐匿特权;美国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第六巡回法院不承认有隐匿特权,二、三、四、九巡回法院认为至少在民事案件中隐匿特权应得到承认,一、五巡回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完全不承认隐匿特权;在美国的50个州中的3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颁布了保护新闻记者隐匿权的 “盾牌法”(Shield Law)(46)。而即使是在这些法院中,不同时间对新闻隐匿权的承认程度也时紧时松,难以捉摸。回首从托尔案到至今的发展历史,新闻隐匿权始终是一个处于矛盾中的无法完成的理论表达。
在托尔案中,新闻界为了保证自己获取信息的能力,借着新闻自由的名义,提出了新闻隐匿权的理论。自此以后,为了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媒体、法院、学界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原则与限制,希望通过完美控制的手段来达成目标。时至今日,与托尔案时期相比,新闻隐匿权的内涵扩大了许多,加诸其上的各类准则也日趋繁杂,但很难说新闻自由本身因此获得舒张。新闻自由和新闻隐匿权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已经模糊不清。这似乎正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察:为了达到某一价值,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反而导致手段本身成为了目的,成为了套在人身上的牢笼(47)。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对新闻隐匿权的规范和控制越来越多,所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个新的控制手段未必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倒时常会诱发新的争论与矛盾。与此同时,媒体和公民所享有的新闻自由本身却未能扩张。
在新闻隐匿权的发展过程中透露出这样的一种倾向:对完美控制的追求,和对理性主义的崇拜。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种倾向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一以贯之的自制、谨慎、简朴的清教徒思想。也正是凭借着理性精神这种现代性文化的驱动,资本主义才实现了巨大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基于理性主义的现代性产生了与追求反叛和自由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断裂,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主义逐渐走向终结,理性的发展不再意味着自由会随之增长(48)。因此,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在论述自由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应该怀着对计划和社会控制技术的恐惧,才能获取到真正的自由(49)。
理性追求完美的控制,并没有解决新闻隐匿权这一理论的困境。为了避免获取新闻的能力受限而采取的种种控制手段,并没能带来自由的增加,反而诱发了更多控制手段的出现。一剂控制的药方无论能不能治愈旧的疾病,却总是会带来新的问题。对完美控制的不断追求,固然完善了新闻隐匿权作为一项自由权利的内涵,却也正是这一理论始终无法完成表达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 简海燕:《媒体消息隐匿权初探》,《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②⑨ Monk C C.Evidentiary Privilege for Journalists'Sources:Theory and Statutory Protection.Mo.L.Rev.,1986,51:1.
③ 1848年,美国和墨西哥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参议院正与墨西哥秘密协商一份停战协定。然而该协定以及其他一些秘密文件却被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通讯员John Nugent提前获得,并发回编辑部。盛怒之下的参议院要求John Nugent交出消息来源,但遭到了John Nugent的拒绝。随后,John Nugent申请人身保护令失败,以“藐视国会”罪被捕入狱。
④ Berger L L.Shielding the Unmedia:Using the Process of Journalism to Protect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 in an Infinite Universe of Publication.Hous.L.Rev.,2002,39:1371.
⑤ Marie Torre.Judy Tosses a Monkey Wrench.N.Y.HERALD TRIB.,Jan.10,1957,at 3-3.
⑥ Neubauer M.Newsman's Privilege after Branzburg:The Case for a Federal Shield Law.The.UCLA L.Rev.,1976,24:160.
⑦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⑧ Fargo A L.Reconsidering the Federal Journalist's Privilege for Non-Confidential Information:Gonzales v.NBC.Cardozo Arts&Ent.LJ,2001,19:355.
⑩(11)(12)(13)(15)(16)Bates S.Garland v.Torre and the Birth of Reporter's Privilege.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2010,15(2):91-128.
(14)Berger L L.Shielding the Unmedia:Using the Process of Journalism to Protect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 in an Infinite Universe of Publication.Hous.L.Rev.,2002,39:1371.
(17)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8页。
(18)以塞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19)Osborn J E.Reporter's Confidentiality Privilege:Updat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fter a Decade of Subpoenas.The.Colum.Hum.Rts.L.Rev.,1985,17:57.
(20)(22)(23)(25)(26)Buser P J.Newsman's Privilege: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gainst Government Subpoenas.The.Louis ULJ,1970,15:181.
(21)Neubauer M.Newsman's Privilege after Branzburg:The Case for a Federal Shield Law.The.UCLA L.Rev.,1976,24:160.
(24)Osborn J E.Reporter's Confidentiality Privilege:Updat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fter a Decade of Subpoenas.The.Colum.Hum.Rts.L.Rev.,1985,17:57.
(27)Nelson H L.Newsmen's Privilege against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Sources and Information.The.Vand.L.Rev.,1970,24:667.
(28)Berger L L.Shielding the Unmedia:Using the Process of Journalism to Protect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 in an Infinite Universe of Publication.Hous.L.Rev.,2002,39:1371.
(29)Nelson H L.Newsmen's Privilege against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Sources and Information.The.Vand.L.Rev.,1970,24:667.
(30)美国学界经常提起的Branzburg案实际上不光是一起案件,而是三起案件的统称。这三起案件中其中一起为Branzburg v.Hayes,另一起案件同样涉及到Branzburg,与前一案联合起诉。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72年。第三起案件则是Caldwell v.United States,发生在1970年,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因此并不在本部分所讨论的范围之内。本部分仅讨论Branzburg v.Hayes一案。
(31)(32)Porter J M.Not Just Every Man:Revisiting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 against Compelled 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Sources.Ind.LJ,2007,82:549.(33)Alexander L B.Looking Out for the Watchdogs:A Legislative Proposal Limiting the Newsgathering Privilege to Journalists in the Greatest Need of Protection for Sources and Information.Yale Law&Policy Review,2002:97-136.
(34)(35)布莱兹伯格案判决书,Branzburg,408 U.S.at 679-80。
(36)九人大法官中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大法官提出了单独异议。他比斯图尔特法官等人更进一步,认为应当享有基于第一修正案的绝对特权。即除非记者本人参与了犯罪,否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拒绝作证或拒绝在大陪审团面前出现。然而道格拉斯的意见在案件审判时和案件审判以后,都并未得到过多考虑,主要的争论仍集中在记者是否应享有受约制特权上。
(37)美国《周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1962年7月14-21日,Confessions of a Block-Buster。
(38)贝克案判决书,Charles and Charlene BAKER et al v.F&F INVESTMENT COMPANY et al.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Seventh Circuit。
(39)(40)Fargo A L.Reconsidering the Federal Journalist's Privilege for Non-Confidential Information:Gonzales v.NBC.Cardozo Arts&Ent.LJ,2001,19:355.
(41)Baker K L.Are Oliver and Tom Clancy Journalists-Determining Who Has Standing to Claim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Wash.L.Rev.,1994,69:739.
(42)Berger L L.Shielding the Unmedia:Using the Process of Journalism to Protect the Journalist's Privilege in an Infinite Universe of Publication.Hous.L.Rev.,2002,39:1371.
(43)Alexander L B.Looking Out for the Watchdogs:A Legislative Proposal Limiting the Newsgathering Privilege to Journalists in the Greatest Need of Protection for Sources and Information.Yale Law&Policy Review,2002:97-136.
(44)Toland C J.Internet Journalism and the Reporter's Privilege:Providing Protection for Online Periodicals.U.Kan.L.Rev.,2008,57:461.
(45)Garry P M.Scrambling for protection:The new media and the first amendment.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1994.
(46)美国“新闻自由记者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rcfp.org/privilege,数据截至2014年9月。
(47)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48)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9)以塞亚·伯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作者单波系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学者;汪振兴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