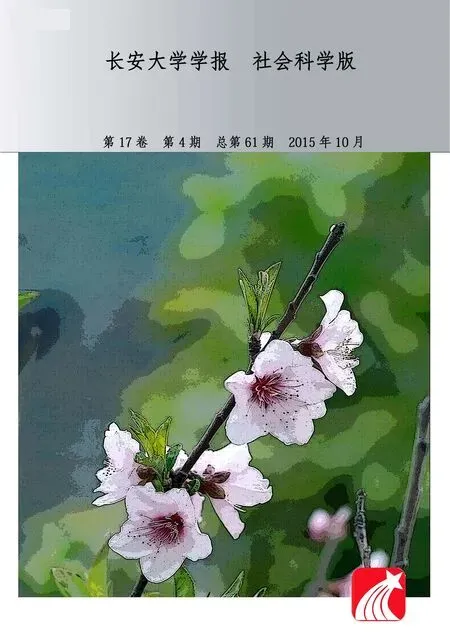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2015-02-20梁桂芳
梁桂芳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梁桂芳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关键词:宋代;美学;尊杜传统;杜甫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一次巨大转型,热烈开放、自信闳放的大唐精神逐渐被理性内敛、淡雅幽邃的宋代美学所取代。这一转型酝酿于中晚唐,拓展于北宋前期。宋初,革故鼎新,文化界亟需典范,有唐巨擘诸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乃至“姚贾”等,均被作为“候选人”重新加以审视,而只有杜甫,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及地负海涵、千汇万状的作品契合了宋代文化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宋调的不祧之祖。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曾指出:“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引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1]作为前代遗存的文化因子,宋人在将杜甫奉为表率的同时,也对其重新加以考量和改造。宋代审美中的杜甫,其诸多侧面或被强化、变异,或被淡化、摈弃,最终定格为承载其时代精神的美学范式。
一、凌云健笔意纵横——刚健的美学底蕴
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替。53年间,易八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伦理纲常,特别是君臣一纲,遭到严重破坏。为重整伦常,统治者大倡儒家学说,旌表了大量忠孝节义之士,甚至包括政敌,如在赵匡胤登基时为后周死难的韩通等。士大夫们也以此为契机试图复兴儒学,重新建构理想的审美人格。
在儒家伦常、仁义学说影响下,宋代美学首先呈现出一种道德化的审美形态,推崇至刚至坚的人格之美,即具有忠义精神和道德上自觉、自律的楷模。宋人审视过很多“典范”,如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但只有杜甫完全满足这一需求。杜甫传承了先秦以来士人重节操的品质,不仅忠君爱民、富有使命感,而且其廷争、弃官、不赴召,终漂泊以死等,更是以实践的品格,体现出儒家士人的刚健精神。杜甫具有相当的牺牲精神和自律品质。他自己是:“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劝勉朋友亦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写《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诗婉言谢绝别人送的一床锦褥,颇显安贫若素、守志不移品质。明人沈周《题杜子美像》感叹说:“贫莫容身道自尊,先生肝胆照乾坤。”杜诗是对士人知识阶层“道尊于势”高尚品格的生动阐释。
宋代士人正面接受、强化了杜甫的刚健人格精神,士风丕变。杜甫在宋代美学中的最初定格就是“一饭未尝忘君”[2]、“蔼然有忠义之气”[3]的忠爱形象,终成就“诗圣”之说。宋人以杜甫精神自我砥砺,认为操守和气节比金钱、权位乃至生命更值得珍视。苏轼《马正卿守节》载:“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4]《秋雨叹》是杜甫于天宝十三载(754)所作,感叹秋雨伤稼害农,而奸臣弄权,蒙蔽天听,表现出穷且益坚的精神,马正卿因受杜诗感发而守节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杜甫精神更是迸射出耀目光彩。爱国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肘,忧愤成疾,吟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含恨而终;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写了杜甫《魏将军歌》赠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文天祥被俘在燕京狱中凡三年余,杜诗时刻陪伴着他,他作《集杜诗》凡五言绝句二百首,《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在宋人眼里,高尚的人格精神贯注于作品,也会呈现出刚健的艺术风貌,所谓“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者则发为文章者辉光”[5]。这是一种“德”性美学观。宋人最初对杜诗的体认很独特,以“雄肆豪放”谓之,实启刚健风格先声。如孙仅状杜诗风格雄峻:“其夐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噭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6],范仲淹赞石延年诗之雄奇乃“大爱杜甫,独能嗣之”[7],欧阳修言杜诗“豪放”,至张伯玉亦形容杜诗道:“诗魄躔斗室,笔力撼蓬莱。运动天枢巧,奔腾地轴摧。万蛟盘险句,千马夹雄才。”[8]
宋初,崇杜尚没有形成风尚,在当时为数未丰的评述中,“雄豪”论杜却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论调[9]。杜诗风格多样,毫无疑问以雄浑壮丽的阳刚之美为主,所谓“才力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10]。然而这不等于“雄豪”,后者更多了一些峻急粗豪之态。杜诗之所以被如此解读,实是时代使然。宋代嘉祐(1056~1063)前后,社会上有一股尚“豪”的风尚:“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11]在时代风尚的变迁中,宋人不断调整自我的美学定位,将老杜之“豪”、“健”融会、渗透于怪异、平淡、瘦硬、奇峭等风格中,使刚健逐渐沉淀为一种基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宋人逐步跳出了唐体的藩篱。以“雄豪”称杜乍看有些突兀,但实质上符合时代文化需求,是宋代审美发展的基础和必经历程。
二、才思沉潜迫中肠——典雅的美学气质
宋人早期以“雄豪”接受杜诗于美学形态有奠基之功,但也因其过于发露渐被摈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缓和、敦厚、自制的“典雅”观。正如黄庭坚所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人也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12]
《毛诗序》言诗:“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黄庭坚“诗者,人之情性也”亦由此而来,却将其他内容一概略去,单取“情性”二字,实质体现了其论诗主张的根本转变,即对诗歌批判功能的消解,将关注现实之意、愤怒嫉邪之情化为忠信笃敬之性,体现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在这一代表性观念观照下,整个两宋推崇一种典雅的中和之美。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13]
司马光不以诗著称,对杜诗之议论尤少,上引对杜甫诗艺的唯一讨论却成为宋人论杜的共识,和者甚众:“其词曲而直,其意肆而隐,虽怪奇伟丽,变态百出而一之于法度……独得古人之大体。”[14]“语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15]这也是在两宋文网渐酷、党争日盛的时局中,宋人为避诗祸而重新调整诗歌功能,从而彰显典雅、中和诗歌风貌的体现。
杜甫《进雕赋表》自言创作“沉郁顿挫”,严羽《沧浪诗话》也指出:“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沉郁”的确是杜诗重要风格之一,也是宋人以“典雅”解读杜诗的重要前提。沉郁,是儒家修养的沉淀,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一种自我克制、深沉低回的美学形态。作为一位系念家国、百姓的诗人,无论是写民生疾苦、怀友思乡,还是自己的穷愁潦倒,杜诗都深沉悲慨,蕴涵着一种厚重的感情力量。然而,杜诗是外向的,直指社会现实,多有讽喻批判之辞,非“典雅”可括。如杜甫身历玄、肃、代三朝,而对这三代皇帝都有所讽喻和批判。他抨击玄宗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其六)他揭露玄宗、杨妃奢靡生活:“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他还敢于大胆揭发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和受制于后宫张良娣的隐私:“关中小儿坏纲纪,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他的《往在》诗更是连续批评了玄宗、肃宗和代宗。
承载着鲜活现实内容的杜诗,带有强大的气势和力量,呈现雄浑郁勃之貌。然在宋人视野中,杜诗却“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忧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16],其情感抒发含蓄蕴藉,是以治心修性为根本的,其气质“典雅文华”[17]、“主优柔而不在豪放”[18],这实际是对杜诗沉郁精神的变异。如同是咏玄宗与杨妃事,唐人多有讥刺,杜甫于其事乃至杨妃姐妹淫侈生活亦深加指责,但宋人却偏离老杜源于现实、富于批判之精神,以主文谲谏、含蓄蕴藉解读之:“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19]
较之元白,杜诗自然更为蕴藉,然其讽喻之意仍很明显,以至后世王嗣奭、钱谦益诸人多番致意。但宋人却对杜诗现实精神极力回避,消解了其批判锋芒,将其叙述微婉、含蓄处放大,以期使之成为典雅敦厚的典范,贴近宋人“诗教”的审美标准。
两宋不崇怒张,不尚直露,偏取一种既格力劲健又涵蕴深厚的外柔内刚审美形态。沉郁顿挫、直面现实的杜诗,在宋代诗教观偏取下,显示出一派沉潜典雅,与其本来面目有些偏离了。
三、老树著花无丑枝——老朴的美学风貌
在后人眼里,杜甫的形象可谓清瘦老苍、穷愁潦倒,如元代绘本《子美戴笠画像》、清代张骏所摹《诗圣杜拾遗画像》及今人张大千《杜陵浣溪行吟图》、蒋兆和《杜甫像》等,杜甫莫不老瘦清癯、愁苦刚毅,而这一形象的定格受到宋代美学的极大影响。
宋人眼中的杜甫,堪称贫病老丑,绝无少年潇洒风流之态:“杜陵头白长昏昏,海图旧绣冬不温”(杨时《向和卿览余诗见赠次韵奉酬》)、“扬云倘许客载酒,杜陵安得钱买驴”(苏泂《次陆放翁韵》)、“穷杜甫,当时西游乘蹇驴”(郑清之《碧扇行》)、“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王安石《杜甫画像》);至若杜诗,宋人亦惯以“老”称之,若“少陵失意诗偏老”( 梅尧臣《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舟次芜江怀寄吴正仲》)、“句法老益练”(苏泂《夜读杜诗四十韵》)、“子美骨格老”( 徐积《还崔秀才唱和诗》)等不胜枚举。
宋代哲学融合儒、释、道,以“性、理”为中心,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理性思辨色彩浓厚的精密哲学体系,它大大激发了宋代士人的理性精神,使得宋代审美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两宋时局艰危,士人虽受到优厚待遇,但一直处于党争的漩涡中,其忧惧心态亦少有朝气,而颇呈“老”态。摈弃浮华,崇尚理性,得老境返璞归真之趣成为贯穿两宋的美学风尚。对杜甫其人其诗以“老”解读,正体现了成熟期特定的审美心态。
“老朴”言杜还是宋代文化发达背景下,对渊深学问、深刻思力的体认,是对一种质拙高古之美的刻意追求。宋人极力推崇杜诗老朴之处,特别是其后期拗体诗。据《瀛奎律髓》统计,杜甫159首七律,其中拗体19首,多见于晚年。而“江西诗派”代表人物黄庭坚有七律311首,其中拗体153首,均老朴瘦硬,把这种老健的形式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岘佣说诗》言:“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山谷学之,得其奥峭”[20],此乃宋调典型,宋诗正沿此径一路开拓。
“老朴”言杜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杜甫1 400多首诗中,“老”字出现370余次,而白首、衰年、迟暮等含有“老”意的字词更是比比皆是。然而,细究起来,宋人在强化杜甫“老朴”风貌时,其人其诗颇多变异。中唐至宋初,杜甫多以“落魄诗人”、“狂士”形象出现。杜甫自言“狂傲”:“我生性放诞”(《寄题江外草堂》),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壮游》)、“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他理想高远、自视甚高:“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藐视流俗,不屑矩矱:“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诗亦多洒脱不羁之处,从早期的《望岳》、《画鹰》至后期《百忧集行》等,均恍惚有“健如黄犊走复来”(《百忧集行》)郁勃之风,此正盛唐气象之回响。
杜甫之狂早在唐代已为人所瞩目:“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杨巨源《赠从弟茂卿》),这是对杜甫个性的褒扬。至宋,渐鲜有人提及,至新、旧《唐书》均以否定语气存杜甫之“狂”,后更以老成持重、思虑深沉目之。在宋人眼里,杜甫早已不复年少不羁、“狂傲”之态。
青春“狂傲”是杜甫性情极具个性和生命力的部分,是成就一部伟大杜诗的重要支撑,是大唐盛世开放进取文化精神的载体。然而,随着中唐至北宋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次转型,政局迁替、经济变革、文化嬗递,士人文化心态日趋收缩、内敛,不符合其审美标准的杜甫之“狂傲”被摈弃,其老成朴拙的一面则被片面放大了。
四、风微烟澹雨萧然——平淡的美学理想
平淡乃两宋重要审美范式。有宋一代,不论是文的纡徐、诗的澹荡、词的清淡,还是书法的重意、文人画的简净、瓷器的素雅等,均昭示着一种素朴韵深的美学追求。与唐代的热烈浓艳相比,平淡是宋代审美文化的新质。
平淡不是简单枯淡,实质上是一种文人化的美学观,带有浓厚的书卷气:“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若想达到这一境界,必须久经打磨,将学识涵养内化其中。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上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诗讲求锤炼和用典,被宋人目为“无一字无来处”。宋人以此作为学杜重要门径,讲究出处、故实,提倡炼字、炼意,均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带有文人雅趣。在宋人眼里,读书、用书是创作的重要手段。要具有雅人深致,“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21]是不行的。
当然,宋代平淡美的理想范型是陶渊明。一直声名隐晦的陶潜,在北宋后,被推为“屈原后杜甫前一人”[22],其影响深远。宋人杜、陶并尊,葛立方谓:“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23]张戒亦云:“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余皆不免落邪思也。”[24]陶、杜并尊之际,杜诗在宋人那里也显现出“简淡”的特质来。宋人论杜,言“张籍得其简丽”[6],其诗 “有平淡简易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25],亦非完全无据。杜诗确有平易处,其440余首怡情悦性的自适诗,大都简淡自然,用语也颇通俗流易。然宋人对老杜的“发现”不止于此,更在于挖掘出其后期诗作的“平淡而山高水深”。
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云:“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2]
欧阳修《病告中怀子华原父》谓:“狂来有意与春争,老去心情渐不能。世味唯存诗淡泊,生涯半为病侵陵。”这堪为杜甫后期心境写照。历辞官寓陇后,入蜀的杜甫虽雄心未老,然国势日衰,豪情消磨,细碎琐屑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其诗料。若《水槛遣心二首》、《秋兴八首》等,脱略奇险,工拙相半,虽无奇崛的词汇、炫目的字眼,然融合了杜甫多年的学养、历练及晚年国势艰危、孤寂漂泊等复杂感受,极耐咀嚼,表面平淡而内蕴极为深厚。杜诗风格多样,然学杜奠定宋调基础的“江西”诸人,却觑定此处下手,卓然为两宋美学典范。
杜诗整体绝不平淡,然正如美国学者萨丕尔《语言论》指出的:“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26]在宋代平淡审美理想的选择下,杜诗风貌也发生了“自由变化”,其“平淡”的意蕴日益“凸显”出来。
表面看来,平淡和“刚健”、“沉郁”、“老朴”等似乎相矛盾,实际上,它是后者发展的必然结果。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几乎都经历过由早期的豪健清雄到后期的淡婉从容。“淡极始知花更艳”,平淡美正体现了宋人外枯中腴、沉潜韬晦的文化精神。
五、陶冶村夫成新赏——世俗的美学取向
鲁迅曾指出:“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27]这话的含义丰富,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杜甫身上有更多的世俗生活气息。
老朴、典雅、平淡是文人化的审美理想,代表了宋代忌俗尚雅的文化指向。然而,宋人在雅俗之间,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呈现出“以俗为雅”、俗中求雅、亦俗亦雅乃至大俗大雅等多元化取向。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了。”[28]“小说戏剧”代表着一种世俗化的审美取向。从整个美学文化史的发展演变看,宋代处于由雅向俗倾斜、转变的重要时期。
莫砺锋曾指出:“在六朝时代,诗坛几乎成了高门贵族的专利品,诗歌题材大体上被局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狭小范围之内。”少量山水诗体现的也是“雅人深致”,“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诗人们不屑一顾的,经常写到鸡犬桑麻的陶诗在当时完全被诗坛遗忘”[29]。到唐代,虽有人开始注意到生活中的平凡题材,如王维歌咏樵夫牧童,孟浩然描绘了田园风光,但那只是诗人静谧心境的点缀,本身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有杜甫在庶族崛起、社会巨变之际,以审美的目光观照了平凡的生活,从世俗化视角为诗歌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成为引领由雅入俗的拓荒者之一。
所谓“俗”,包括内容的世俗性和形式的通俗化。杜诗笔端,包罗万象,农夫、村妇、征夫、戍卒等下层民众及其生活纤毫毕现,庶几可以尽天下之事。若其《逼仄行赠毕四曜》句云“逼仄何逼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又“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等,《杜臆》卷二谓之:“信笔写意,俗语皆诗,他人所不能到。”尽天下之情事,到他人所不能到,正成就出一代宋诗。杜诗表现,既多“当时语”,更多叙事,破体为文,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多戏题剧论,皆开通俗化先声。黄彻语:“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而宋人模之,不加拣择:“但见其粗俗耳。”[30]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杜甫是相当关键和重要的一章。他认为杜诗风格诙谐平易,其入蜀后诗更“纯是天趣,随意挥洒,不加雕饰”,杜甫晚年多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些第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中国诗的一种重要风格”[31]。
北宋喜爱李商隐的杨亿说杜甫是“村夫子”,谓其多反映卑琐的人生和情感,辞藻村俗,不够华美。然而,随着宋代美学的定型,杜诗的世俗化得到宋人的全面认可、传扬,就连理学大师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语录,也毫无例外地通俗化起来。所谓“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万丈长”(戴昺《有妄论宋唐詩体者答之》),“村夫子”正是宋代美学中杜甫形象的又一定格。
六、结语
杜甫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典范,其美学特质是多层面的。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演绎了杜甫:把杜甫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并重新塑造出一个老成朴拙、平淡清雅兼有世俗化倾向的杜甫。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在一起,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宋代美学对杜甫的多侧面解读,有的乍一看似有“误读”的成分,然而以发展、辩证的眼光来分析,又是一种合理的再“发明”。接受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不同的期待视野出发,对经典的丰富内涵做出富有时代特色的阐释,使经典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其文化价值和意义得到持续发扬,也推动了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傅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苏轼.王定国诗集叙[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99.
[3]许尹.黄陈诗注原序[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323.
[4]苏轼.东坡先生志林:卷5[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107.
[5]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6]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59.
[7]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O].北京图书馆藏宋朝刻本原大影印,1984.
[8]张伯玉.读子美集[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75.
[9]梁桂芳.“雄豪”论杜及其与宋代诗歌的流变[J].杜甫研究学刊,2004(2):48-49.
[10]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香港:中华书局,1977.
[11]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3]司马光.温公续诗话[C]//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277-278.
[14]宋谊.杜工部诗序[C]//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6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80.
[15]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黄庭坚.山谷诗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黄裳.书乐章集后[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115.
[18]魏泰.临溪隐居诗话[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117.
[19]张戒.岁寒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施补华.岘佣说诗[C]//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75.
[21]黄庭坚.与徐师川四首[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121.
[22]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3]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0[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454.
[24]张戒.岁寒堂诗话[C]//华文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465.
[2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6]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7]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N].文艺报,1956(20).
[28]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2.
[29]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0]黄彻.銎溪诗话[M].汤新祥,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1]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OpinionofDUFuinaestheticfieldofSongdynasty
LIANGGui-fang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FuzhouUniversity,Fuzhou350108,Fujian,China)
Abstract: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culture had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The aesthetes of Song dynasty reinterpreted Du Fu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The virile personality spirit and poetic style of Du Fu became the aesthetic gist of the whole time; He with gloomy temperament was reshaped as an old, simple and elegant m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secular trend of Du Fu’s poetry was also further carried forward. These seemingly disharmonious sides were integrated into a whole organically, reflecting the brilliant and colorful aesthetics of Song dynasty. The multi-dimensition acceptance of Du Fu by the aesthetics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was a reasonable reinvention restricted by the times and culture.
Key words:Song dynasty; aesthetics; tradition of revering Du Fu; Du Fu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SS002)
收稿日期:2014-07-01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119-06
作者简介:梁桂芳(1972-),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