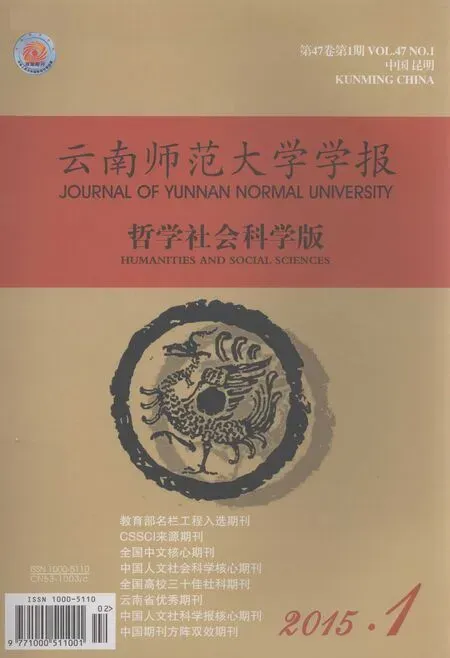论“陌生人”的宗教之维*
2015-02-14侯小纳
侯小纳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论“陌生人”的宗教之维*
侯小纳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陌生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名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随之也确定了陌生人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合法地位。陌生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人际类型,已然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陌生人”愈发备受关注,但其宗教学意蕴却鲜有论及。本文欲从宗教学角度探究“陌生人”的原初意涵,揭示其本原的神圣性特质,并围绕陌生人的神圣性及其生发开来的理论价值及意义展开讨论。
陌生人;神圣性;宗教;之维
“陌生人”作为一个知识社会学名词,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8年针对“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极具批判同时又极具现代性反思意义的问题时提出的。齐美尔把陌生人放置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进行考察,对之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与考察。他说:“只要我们感到在陌生人和我们之间存在民族的或者社会的、职业的或者普遍人性的相同,陌生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近的”。①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6.“如果说作为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是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在概念上的对立,那么‘陌生人’(Der Fremde)的社会学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界定的统一。诚然,在这里也显示出,同地域空间的关系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②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12.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陌生人”问题上来,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以及继踵其后的伍德、舒茨等学者均在没有偏离齐美尔“陌生人”理论的研究基点上,对其进行补充和扩展,但基本上是把“陌生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类型来进行研究。国内学界对于陌生人的研究鲜有涉足,目前可见的文献仅有数篇,都是从“陌生人”的社会学维度进行研究的。从宗教学角度对“陌生人”进行研究的专著、专论寥若晨星,笔者从中国知网上对“陌生人”从宗教学角度切入检索,结果竟无一篇相关研究。“陌生人”的宗教之维在于探究陌生人是相对于另一“地域集团”的未融入者,而未融入的原因正在于其所具有的宗教神圣性。弗雷泽《金枝》第十九章“禁忌的行为”中第一节及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第三章“个体与群体”中对“陌生人”从宗教学角度有过简短论述,这客观上对于本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启发作用。
一、陌生人的神圣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第三章“个体与群体”中写道:“陌生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神圣的,具备巫术——宗教性力量,并拥有超自然之仁慈或邪恶力”。③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在这里,范热内普提出了陌生人具有神圣性这一特点,而且在其他章节也对陌生人具有神圣性的原因做了说明。“神圣性之特质亦非绝对;其出现是因为特定场景之性质。某家或部落内的个体是生活在世俗界域;当开始一次征程并发现身处陌生地域时,他便进入神圣界域”。④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从引文中可以看出,“陌生人的神圣性”问题是在过渡礼仪中“地域过渡”的相关论述当中被提出的,它主要针对“为什么作为一个陌生人,在进入他方界域前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净化仪式”问题发出疑问。过渡礼仪有着很深的学术史背景,除范热内普外,特纳也对其有过深入的研究,其深化、扩展后的过渡礼仪(阈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参考、借鉴了前者的理论成果。过渡礼仪的相关理论背景使“陌生人的神圣性”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但是,除了弗雷泽在《金枝》当中的民俗材料论及陌生人在进入另一界域会带来惶恐与不安,以及范热内普《过渡礼仪》当中的相关论述外,罕见其他学者对这一学术生长点进行挖掘、阐发。在对“陌生人的神圣性”进行界定之前,首先要先弄清楚两点:一、何为陌生人;二、何为神圣。要解决这两点,其实从范根内普的引文中即可得到答案:即在于他(或她)所处的陌生地域。概而言之,“陌生人的神圣性”是指因不同的地域,在造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存在着的彼此惊惧、不安,害怕对方会带来“黑巫术”的紧张情绪。但范热内普没有向我们进一步交代清楚的是:陌生地域如何会产生神圣性?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对我们重新理解陌生人以及神圣性的概念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陌生人”一词根源于斯拉夫语,对应翻译为“Boris”,但它还有另一层意思:战门、战争或“为荣誉而奋斗”。“战门”亦是一表地点(或地域)的词,且“战门”含有争战、战事的意思,这与陌生人相见时的紧张、不适、充满敌意相符合,亦显示了“陌”的地域性特点。陌生人乍遇时的不适、紧张感,主要是由于双方均进入了“陌生地域”,相对于对方来说,彼此都是“不干净”(不洁)的,即受到了相对于另外一方的“限制力量”的钳制。因此,对“不洁物”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陌生地域的神圣性。
二、神圣的不洁物
我们总是有关于人或物的不洁的观念,这种观念有时会起到重组混乱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有时又能破坏既定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不洁物具有的这种超脱世俗的神圣功能从何而来?它是否跟陌生界域(有形或无形的)有关联?
“神圣的不洁物”的提法仍然是出现在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当中(范热内普转引自克拉塞明尼科夫所著《堪莎喀的历史与描述》第136页,同时对转引材料进行分析):
“‘他们把桦树枝拿进帐篷,其数量代表着家庭数。每人为自己的家拿一个树枝,在弯成圈后,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从里面过两次,每次从圈里出来时,他们转圈,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净化自己的错误’。从克拉塞明尼科夫的详细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桦树是堪莎喀人的神圣树,并在多数礼仪中使用。其中,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在桦树本身的意义下的直接净化作用;二是一种将人的不洁向桦树的转移,这层意思似乎体现在整个仪式中:‘待所有人被净化后,堪莎喀人走出帐篷,手持小树枝,跟随父母,经过最初通过的小门,或是较低处的口,身后跟着家里的男女亲戚。他们一出帐篷,就第二次通过桦树枝圈,然后将小树枝插在雪地上,将枝头弯向东。待将所有的东西,都扔到这个地方,掸过他们的衣服以后,他们再次回到帐篷里,但是从正常的门,不是先前用的小门’。或者说,他们将积存在自己衣服里的具有神性的不洁物掸掉,也将脱离开最重要的仪式器物”。①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
在范热内普转引克拉塞明尼科夫材料当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堪莎喀人为何要进行身体净化仪式(用桦树枝),但是可以想到,定是遭到了不洁物的“侵袭”,“他们将积存在自己衣服里的具有神性的不洁物掸掉”亦充分说明了他们要祛除掉身体里或衣服上的不洁物,已达到回归正常世俗世界的目的。但问题出现了:衣服里具有神性的不洁物是怎样沾染的?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不洁物为何具有神圣性”的问题也即迎刃而解。
关于衣服里神圣的不洁物的论述,范热内普是在论及“地域过渡”章节时谈到的。清除、过滤掉衣服里的不洁物是地域过渡礼仪的重要仪式。只有在做完了一系列的过滤仪式后,个体才能再一次生活在没有危险、诅咒的环境当中。既然是在谈到地域过渡时论及“神圣的不洁物”,那么,“神圣的不洁物”的概念一定是在谈论从一地进入另一地时所产生的——从一已知的、熟悉的界域进入到一未知的、陌生的界域。可见,“神圣的不洁物”是紧密地与陌生地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圣经·旧约全书》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②参见《旧约全书》之《出埃及记》第三章3-5节。耶和华之所以要让摩西“不要近前来”并要求脱下他的鞋子,因为摩西是不干净的,他身上沾有“神圣的不洁物”。但为什么偏偏是脱掉鞋子,而不是摘掉帽子或脱掉衣服呢?“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摩西身上沾染的不洁物说到底是因其所处的界域——相对于“圣地”而言的世俗之地。
中国古典文献当中也有关于“神圣的不洁物”的资料,屈原《渔父》及荀子《不苟》篇当中有相关描述。“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①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80.又,“非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②王先谦.荀子集解[M].长沙:岳麓书社(影印本),1996:27.为什么古人在洗过头发、身体以后要弹冠、振衣?笔者以为此举很有可能是一种净化仪式,是从一界域到另一界域的(在这里,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界域过渡)过渡礼仪,中国古代大凡遇到祭祀、节日等重大礼仪活动,参与者都必须沐浴、斋戒,以示虔诚、庄重。濯发、洗浴后的“弹冠”、“振衣”其实就是“将积存在自己衣服里的具有神性的不洁物掸掉”。且“吾闻之”句,说明早在屈原之前就已有这样的惯习,已然形成习俗。洪兴祖补注此句说:“受圣人之制也”,这就更加强了笔者的猜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两句,洪兴祖补曰:“拂土坌也,去尘秽也”。此处的“土坌”、“尘秽”亦不可以惯常的理解视之。当然,洪兴祖显然不是站在巫术、宗教的立场去作本篇的注解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发掘出它所具有的原初意蕴,且荀子《不苟》篇“人之情也”句,说明在屈原之后,这样的惯习仍然绵延不绝。仅仅“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两句已经可以与现代西方民族志材料互参,从而见出藏在这些句子中原本的宗教意蕴。
东汉的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中说:“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江南讳人不讳犬,谣俗防恶,各不同也”。③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9:970.秦汉之际,社会上主流的观念是非常忌讳直接与产妇及新生儿有任何的接触,当时整个社会的态度均保有此种观念,即使家人(限定在一定的成员)也不能随意接触新生母子,更不用说是外人了。此种习俗至今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十分盛行:产妇生完孩子后,要被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房门外挂一块红布,以警示外人不可误入。坐月子期间,除身边最为亲近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产妇的房间,否则被视为不祥(既会给不知情的探访者带来不祥,也会给产妇与新生儿带来不吉)。而且,产妇不满月是不能够串门子的,否则也会给他人带来祸端。产妇诞下新生儿本来是应该祝福、庆贺的事情(虽然在满月之后会有此类的庆贺仪式),为什么在其未满月期间,其他人都会避之唯恐不及?“以为不吉”?这正是因为产妇坐月子所居房间为“不洁”的,为神圣界域,具有神奇的魔法、巫术能量,如外人不小心沾染上,轻则会神魂颠倒,重则丢掉性命。所以“在产妇不小心因串门而给他人带来不祥时,要经由产妇家为之刷门祭宅神,即可消灾解难、化险为夷”。④任聘.民间禁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8.这实质上是一种为祛除“不洁”而进行的“净化”仪式,目的就在于祓除他域的“神圣的不洁物”。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中,也有类似的“不洁物”的情况存在,民间送丧回家途中要跨过一堆火,并且这堆火要摆在坟山与村寨路口的交叉处,火堆的作用正在于阻隔生死、阴阳两界的“神圣的不洁物”,而且此种祓除不祥的过程万不可大意,草草了之。
既然不洁物的神圣性来自于陌生地域,那么,如果单单从功能的角度把不洁物的出现所引起人们的惊异、不安说成是人们惧怕混乱的无序状态,是否会显得过多地沾染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呢?在《洁净与危险》中,玛丽·道格拉斯很有见地地沿用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理论:“正如我们已知的,污垢从本质上来讲是混乱的无序状态。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它只存在于关注者的眼中。即使我们试图避开污垢,那也不是因为怯懦惧怕,更不是因为害怕招致天怒。我们关于疾病的观念也不能解释自己在清除和躲避污垢时的行为序列。污垢冒犯秩序。去除污垢并不是一项消极活动,而是重组环境的一种积极努力”。⑤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引文中,玛丽对“污垢”的定义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不洁物”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她的这段话仍可用来论证我们的问题(玛丽从功能角度已经把洁净或不洁净的论题落实到政治-经济层面),她把“污垢”(不洁物)当作社会秩序的一种混乱、失格来理解,但却忽视了不洁物产生的另一面向:地域的向度。换句话说,玛丽的这种理论建构旨在运用于所有民族关于“不洁与禁忌”的同种分类,在讨论“污垢”的象征意蕴时,却模糊了我们寻视在最原初意义上“神圣的不洁物”所由之产生的陌生地域的思考视野。需要强调的是,每一地域相对于他方地域来说都是陌生的、神圣的,且具有神圣的交互性。
三、神圣的交互性
神圣的交互性是指陌生人彼此都会给对方带来警觉、不安,同时亦均需做祛除不洁物的净化仪式。正如上文已论述过的产妇坐月子,她被认为是“不洁”的,但同时“误入”其房间的外人也被看作是“不洁”的,会给产妇带来一定的“魔法后果”。这对于我们平时的观念——即认为神圣只是针对世俗、不洁仅会对洁净产生不祥提出挑战。
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描述异域大量相关民俗时写道:“凡外地陌生人踏上这些岛屿,必先通过岛上巫师在他们身上洒水,涂膏,并系上干枯的露兜树叶。巫师们还在四周泼水撒沙,用新鲜树叶擦拭来客和他们的船只。然后才领这些外来人去见岛上的头人……这种对于外来客人所怀的恐惧,常常在主客之间相互存在。原始未开化人踏上陌生国土时,感到自己正走进魔地,采取步骤防卫来往魔鬼及当地居民施行魔术的侵害。例如毛利人在出发往他乡之前,总要先进行一定的仪式使其旅行成为‘一般’的旅行,否则就有可能变成受禁忌的‘神圣’的旅行。”①詹·乔·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97.在接见外来陌生人时,我们常常怀有忧虑、不安的情绪。岂知此种相同的情绪亦在被接见的来访者之间普遍存在。这种在主客之间相互存在——对外来人所怀有的恐惧感说明了:神圣性不是仅指一方对另一方所施的魔法或诅咒,以期达到控制被访者、希望在被访者身上得到他们想见的应验。这种不安、焦虑、恐惧的情绪对彼一方来说具有神圣性,于此一方面观之亦如是。
无独有偶,在江绍原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一书中,亦有相关文字论述此种神圣的交互性问题。
我们知道古中国人把无论远近的出行认为一桩不寻常的事;换句话说,古人极重视出行。夫出行必有所为,然无论何所为,出田,出渔,出征,出吊聘,出亡,出游,出贸易……总是离开自己较熟悉的地方而去之较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之谓。古人,原人,儿童,乃至禽兽,对于过分新奇过分不习见的事物和地方,每生恐惧之心;此乃周知之事实,自不劳我们多费笔墨。熟悉的地方,非无危险——来自同人或敌人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然这宗危险,在何种程度内是已知的,可知的,能以应付的。陌生的地方却不同:那里不但是必有危险,这些危险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难预料,更难解除的。言语风尚族类异于我,故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虫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风狂雨,烈日严霜,社坛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远人,在僻静处,在黑暗时,伺隙而动,以捉弄我,恐吓我,伤害我,或致我于死地为莫上之乐。他们之所以如此,而且是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于我固为陌生的,可怕的,然我于他们也同样是陌生的和可怕的啊。②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5~6.
江绍原先生也讲到当进入陌生界域给己方和他方带来的惊惧与不安,此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在西非一些地区,男人久别家园,回来后同妻子会面之前,必先用特定的水沐浴并经巫师在前额上做一记号,借以消除外乡女人在他身上施行的符咒,这种符咒如不消除其魔法,还可能通过他传染给本村其他妇女。”③詹·乔·弗雷泽.金枝[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98.这说明了西非地区的男人在进入“外乡女人”的界域时,虽然会带给当地人“神圣的魔法”,但同时也会把一种近乎相同的“魔法”携带到自己故乡。所以,在他们回家之后才需要做一系列消除符咒的仪式。中国传统的“花轿迎娶”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新娘子在上花轿前,双脚是不能沾地的。“旧时,汉族、回族、满族及其他一些民族都有此习俗。据说是怕带走了娘家的福气。脚不踏地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的把轿子退到房门口,由新娘的父兄或抱或背送进花轿;有的让新娘在红缎绣鞋的外边再套上父兄的大鞋,走着上轿,上轿后再将外面的大鞋脱掉;有的在地上铺上红毡子或草席子;有的不坐轿、车,有娘家舅兄用红毯子裹住新娘,轮流背到新郎家;南方水乡婚嫁,还有隔船抛新娘的习俗。这些不沾地的习俗表明新娘由娘家到婆家是一个飞跃,跨越了一个转折,渡过了一个‘关口’。”①任聘.民间禁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42~43.新娘的“新”也正是体现在“从头到脚”这一点上。为什么新娘在进入夫家之前双脚不能沾地?正是因为此时的新娘对于夫家来说,已经具有一种“神圣的魔力”,不能沾染上娘家神圣的不洁物。同时新娘的“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也是一种祓除仪式——针对在陌生地域的夫家所做的净化礼仪。但此一方恐惧彼一方的同时,又被彼一方深深吸引——因为一方总会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进入他方地域,此种理解在根底上可以说更为原始,亦更为原初。对这一终极目的所抱有的膜拜、信仰总是偏向于神圣的一极的,它压制另一极,抹平对话和交流。我们对于神圣性的观念一直以来受这种固定思维模式的束缚,而早已忘记了无论神圣还是世俗都应该放在同一个语境里来进行界说,它们相对于彼此是互为世俗与神圣的。
四、“陌生人”的现实意义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他方界域的“陌生人”作为我们的异己者,不断涌进我们的生活世界,并形构我们部分的生活意义,提升着我们观照他者及反观自己的能力。作为他者的“陌生人”或者会慢慢地与我们打成一片,或者永远与我们保持疏离,其本身就体现为一种张力:一方面,作为另一地域集团的他者,不能够马上融入其进入的陌生集团;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不能进入”的状态,使得弥足珍贵的差异性存留了下来。“陌生人”本身就蕴含的这种“边界性”(一种陌生—熟悉状态)暗示了异己的双方进行联系的必然性,失却了联系也就无所谓陌生。“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在社会学考虑意义上是陌生的,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他们处于远与近之外,无所谓远近。”②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2.“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陌生与否的,因为它“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不与我们发生联系,亦不构成我们生活的意义。因为陌生人本身的张力,决定了其正是因为“异己的他方”而存在,对“陌生人”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对“他方界域”的关注与强调,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陌生人的当下性意义及地域性、差异性在当下社会的重要意涵。而对不同地域的强调是探讨神圣的“陌生人”现实意义的重要节点。因此,对地域(界域)的讨论将丰富我们对“陌生人”的理解。同时,对生活在已经“去圣化”世界中的我们将产生一种启发:不仅可以使我们换一种思维的角度,而且还可以发掘一种生活(生存)的向度。
中国古代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15.的说法,但这种“天下一统”的思想里面从来没有缺少地域分隔——断裂的因素。“在中国,根据古典文献,土地神不是整个大地的神祇;每一片土地都被其居住者和拥有者视为神圣的。”④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4.在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体系中,土地神的信仰是最为重要的信仰之一。但是,“土地神并不是整个大地的神灵”,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信奉的“土地”。“由于国家政权的产生和专制权的确立,也是社会两元分化,官民对立,土地神的设立也就相应分化为两大系统:官社与民社。官社即国家法定意义上的最高土地神。三代是称‘邦’、‘王社’、‘国社’。《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战国以后,社神日趋人鬼化、区域化、庸俗化。土地崇拜发展到这一阶段,自然祟拜的性质已逐渐消失,而转化为具备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信仰,人格化的倾向更为明显。”⑤唐仲蔚.试论社神的起源、功用及其演变[J].青海民族研究,2002,(3).可以看出,自三代以来,地方所祀神灵就已不是一统化的专一大神,其趋势也变得越来越“地域化”、个性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一统”的思想,但从来也不缺乏从某一地域生发的崇拜信仰。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只可能首先生活在某一地域之中,才能有完全的整体观念;从现实上来说,作为个体或群体的我们都不能逾越界限而生存——无论是生命形式上的(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从出生到死亡的历程)还是包裹在我们四周的环围。我们不会也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界限、没有神圣的地域(界域)当中,若没有地域的承载,我们将没有方向、寸步难行——因为方向的出现首先是在确定了一个立足点并以此为世界的核心(从更原始的意义上,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才是世界的中心),然后从这一点再向另外的向度不断扩展。唯当如此,新鲜的世界才会不断地向我们展开、靠近。
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可以与中国的“符节(牌)”有某种对应性,此种符节的形质有三种:玉制、铜制、竹制。中国古代的符节主要作用在于王侯命臣子出使某地时成为一种凭证,而使者在出使途中凭符节得以顺利过境,但这种具有“护照”性质的符节在原初的意义上具有宗教意义,“在玉、铜、竹三类节中,玉节的出现似要早一些。它主要用于行事之时,则是礼仪性的、象征性的,与祭祀及原始宗教有关,具有号召各联盟部落的作用,是氏族部落联盟阶段的遗风”。①郑雅坤.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J].西北大学学报,1985,(1).惜乎论者没有更多地展开论述。江绍原先生也在《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中对“出行之人”携带玉能辟邪驱灾进行过论述。可见,在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带有仪式、宗教意义的符节,它对净化陌生人进入他方界域时带来的不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净化”陌生人给我们带来的“不洁”,但正是此种“不洁”让我们在整合中看到了差异,并且让我们了解差异的能产性: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同一,也存在差异。差异性的存在能够提醒我们尊重异于自身的他者,同时生发出一种多元的思维及生活向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去圣化”的消费社会当中,自然、社会在我们眼中的神性特质逐渐淡化或已消失,在提倡“一体化”、“全球化”、“普世化价值观”的同时,不要忘了打量那个迎面而来的陌生人以及他所源出的那片地域,看看我们是否还保有着惊奇。而正当我们声嘶力竭地高喊地球村口号的时候,“陌生人”正不断地涌入我们的生活,并构成我们生活的意义,这就使“神圣的陌生人”的讨论有了现实的基础。如今的我们都被淹没在熟悉之中,忘记了陌生原初的宗教意涵。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也只是在不断地认识陌生、接触陌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害怕陌生,习惯混迹于熟悉、舒适的环境当中,当我们被迫或自愿进入陌生地域时,才能发现神圣的真正意义。在不断地追求同一、无差别的喧嚣声中,在一切都讲求熟悉、抹平差异的当下,怎样保持我们的陌生性,怀揣一颗宗教的虔诚之心,保持我们在进入他方界域时所持有的神圣、惊异、不安、甚至战栗,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讲,也体现为一方对他方的尊重。如此,整个自然、社会将渐趋于和谐的境域,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或许就近在身边。
On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the stranger”by George Simmel
HOU Xiao-na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China)
As a sociological noun,“the stranger”was firstly put forward by George Simmel,a German sociologist,and then has established its position in sociological studies.As a basic interpersonal type in modern society,“the stranger”has alread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society. Though is has received much more concern as a new academic focus,its religious implications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imitive implications of“the stranger”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to reveal its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of holiness as well as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stranger;holiness;region;dimension
C913
A
1000-5110(2015)01-0128-06
[责任编辑: 黄龙光]
侯小纳,男,新疆塔城人,云南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