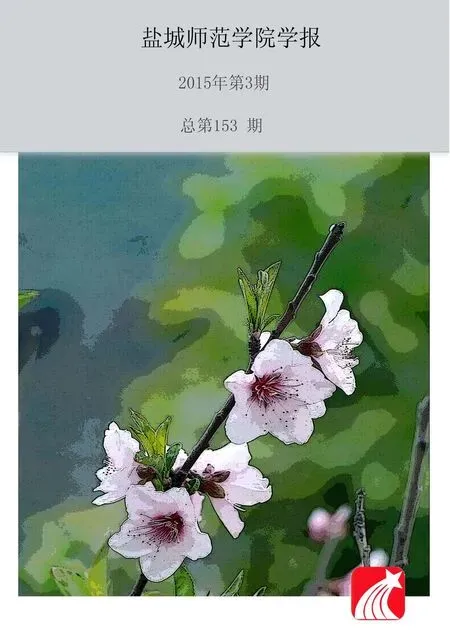国内语言理据学述略:简史、成果、论题和应用
2015-02-14李二占
李二占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国内语言理据学述略:简史、成果、论题和应用
李二占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国内的语言理据研究,历经古典阶段的萌芽产生与现代时期的停滞倒退,目前正处于给力的复兴之态。具体表现是实践方面,它已取得包括专著、词典、论文等在内的诸多成果,而理论上更形成了理据的语言类型考察等稳定的核心议题。虽然尚存在探索不够深入等缺点,但它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既有助于当代认知功能语言学范式的深化,也有利于中西兼容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建成。
理据性与像似性;理据成果;字本位;基本议题;语用理据
国内举凡现代意义上的新学科,多是在革故鼎新、中外碰撞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语言学也不例外。不过,普适性的自然科学的建立比较顺利,而像语言学这样的常被“中国”、“西方”等词语修饰的人文社会科学,往往面临共性与个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容易陷入“国际接轨”对“中国特色”的争议之中。就我国传统语言研究而言,本指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内容,然而在清末民初西学渐强、国学式微的大变局下,它走上了一条曲折的转型之路,显著标志即《马氏文通》的问世。此后,历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引进,四五十年代的初创,六七十年代的停滞,终于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复兴,呐喊出中国语言学家自己的各种声音:词组本位、三个平面、配价语法……其中,抛开印欧语眼光而扎根于汉语土壤的主要有以徐通锵为首的字本位论和以王艾录为首的汉语理据研究。这两种新兴的理论能否修成正果,自有后来历史的检验,但它们对汉语鞭辟入里的探索,则不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恰逢《汉字的国学理据》(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交稿付梓,作为编者之一的笔者遂不揣谫陋,就与“汉字理据”问题密切关联的国内语言理据研究,从背景、成果、议题、不足等方面,思考总结如下。
一、研究背景
语言符号,特别是其原型词语,当表征外物之时,会引起关于它是任意地还是有理地编码人类经验世界的猜想,并在建构自我之际,即触发能指和所指之间是否存在可论证性联系的思考。这是一个贯穿古今中外的语言探索的根本问题,决定着语言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历经古代语文学、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当代认知功能语言学等阶段。
语文学阶段,语言与哲学混沌未分,故它被统称为“词”与“物”,或“名”和“实”的问题。发端于古希腊文明的西方学界,于此形成惯例派和自然派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语言中除少数拟声词外,词的意义和形式的结合是任意的。后者坚持事物的名称由它的性质而产生,所以可以探究语言的原初动因。两种观点虽然时有较量,但总体来说,惯例派一直占据上风。中国古代学者也曾有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的类似思想,但从先秦诸子到乾嘉学派,均不同程度地关心语言的理据性,都对名实关系作出过各种论述,尤其重视字的音、形、义的理据探究,尽管未能产生严密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在前语言学时期,中西方语言文字类型的巨大差异,注定了它们研究取向的分道扬镳。西方更注重对语言进行语法的、共时的研究,而汉文化则聚焦对语言进行语义的、历史的探索。借用当代语言学术语,二者实为语言任意性与语言理据性范式之间的对峙。
现代语言学阶段,即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索绪尔(Saussure)在约定论的基础上,将该经典命题归简为“词语的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之间无必然的关系”,即著名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语言任意论影响巨大,导致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流派及代表人物,例如乔姆斯基的生物语言学,或者标准的语言学教科书,例如萨丕尔的《语言论》、霍凯特的《现代语言学教程》等,大都唯此原则是从。清末民初,中国语言研究道路新旧更替,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内嵌于其间的任意论,把语言学的天平由汉语理论偏向西语理论,以之压制我国固有的理据范式。结果是,传统的汉语理据研究因此断层,理据性的存在被严重忽视,中西语言观从而独尊任意论。本来,由古代汉语研究过渡到现代汉语研究,理据研究也应该由古代的、微观的汉字理据考证,过渡到现代词语理据研究以及理据学的创建[1],然而这一重要的过渡却被耽搁了。
当代语言学阶段,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石的语言任意论,特别是它的缺陷,得到了反思,例如雅各布森(Jakobson)认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研究的功能主义与认知转向蓬勃发展,影响渐大,例如海曼(Haiman)等学者从两方面来纠正激进语言任意论所造成的偏误。一方面,人们开始关注与索绪尔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eirce)所建立的认知符号学,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定的像似性(iconicity),表现于语音、语汇、语法、语篇等层面。另一方面,研究者重新分析了索绪尔的“相对理据性(relative motivation)”概念,用它来解释语言构式的形成动因。语言非任意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例如西方语言学界以Radden & Panther为代表的语言理据研究(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和Simone等引领的“语言文学中的像似性(iconicity in language & literature)”系列探索,均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国内语言学界从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汉语为主要语料的、特色鲜明的理据研究新潮流,例如张志毅(1990)、王寅(1999)、严辰松(2000)、王艾录(2001)、李葆嘉(2001)、赵宏(2013)等。其中,语言理据研究的发轫者是王艾录,而语言像似性研究的代表人是王寅。现在,中西语言观,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再次趋于一致:均认为理据性(含像似性)也是语言的重要属性。
二、研究成果
迄今为止的国内语言理据研究成果,大多以著作和论文的形式公诸于世。著作包括少量的理据学专著与理据词典,更多的则是涉及理据论题的专著和教材。论文有正式出版的学术期刊论文,以及仅限网络版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1.重点著作介绍
《汉语理据词典》:理据与造词与生俱来,所以它转瞬即逝,需要以语言表述的方式使之物化,形成可操作的历史性资讯。理据义的汇集是理据研究的语料与事实基础。古代的《尔雅》、《说文》、《释名》以及现代的《同源字典》等,大都以汉字或汉语单纯词为对象,而专门考释汉语复合词的理据词典一直阙如。王艾录在搜集整理一万多条汉语复合词的理据义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内首部《汉语理据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繁体字本《中文有理有据三千词》,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后又对它进行增删易改,收词3 700余条,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再版(2013)。它通过语素义、意义支点义等具体而微的手段,深入解读词语的理据。《汉语理据词典》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辞书研究》、《汉语学习》、《语文建设》等杂志,发表了林寒生、黎良军、朱于国等人的书评。
《汉语的语词理据》和《语言理据研究》(王艾录、司富珍合著)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为国内语言理据研究方面首次出版的两部专著。《汉语的语词理据》主要回答了理据是什么(概念论)、怎样探究理据(方法论)以及为什么研究理据(本体论)。以方法论为例,作者首次提出针对原生与派生词的“单体历时式考证法”和针对句段词的“分解综合式考证法”。《汉语的语词理据》被商务印书馆重印多次,引用率颇高,有王庆(2010)等发表于《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的评论。《语言理据研究》内容包括什么是理据学、理据学视角下的词语及句法理据、词语理据的研究方法、理据学的普遍意义与应用等。它创造了国内外语言理据研究领域的多个“首次”:首次把理据和内部形式区分开来;首次阐述了“理据管约论”这一关于语言任意性和理据性关系的新观点;首次提出了“语言理据学”的新概念;首次从理据、内部形式和词义三者关系的角度考察词语的意义问题。这些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以及新术语,使人耳目一新,一举奠定了作者在该领域的首创地位。它比国际上首本理据学论文集《语言理据性研究》(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2004)还早两年出版,成为国内语言理据研究的必参文献,中国知网查询到的引用率就达600次之多。《中国图书评论》、《山西大学学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了曾昭聪等人的书评,给予高度而中肯的评价。《现代外语》杂志在“稿件格式”的“专著类”下,选择该书作为范例:“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赵宏著)首先讨论语言理据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然后回顾语言理据研究史,重点探讨理据与任意性、内部形式的关系以及理据的定义和类型,最后围绕英汉词汇的单纯符号、合成符号、外来词、经济性、隐喻等多个方面,系统探究两种语言的理据机制。它是国内外首部系统对比英汉词汇的理据类型的专著,具有重要的普通语言学意义。作者曾师从潘文国,英汉语言学的素养俱佳,为近年来国内语言理据研究界的后起之秀,也是该领域内中青年学者的典型代表。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新华出版社1999年出版)为认知语言学家王寅的成名作。本书首先厘清像似性与任意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然后讨论像似性的汉语译名、定义、理据和性质,接着分析了6条句法像似性原则:距离、数量、顺序、标记、话题和句式,最后是像似性原则在文体学中的应用。作为国内第一部专论语言像似性的著作,它出版后引发了研究热潮,尤其是以郭鸿为主的语言任意论者和以王寅为首的像似论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它与王艾录等的《语言理据研究》,在时间上相距不远,遂形成合力之势。这以后,“二王”分别成为国内语言像似研究和理据研究的领军人物,是该领域里令众多中青年学者景仰的双子星座。此后,王艾录还在2002年成立了国内首个专门研究理据的学术机构——盐城师范学院语言理据研究所,而王寅主编了国内首部《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2009)。王寅为江苏盐城人,曾任职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王艾录任职于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同时,国内较早对索绪尔任意说提出系统质疑的为盐城籍的、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葆嘉。冥冥之中,江苏盐城,成为中国语言理据性和像似性研究的摇篮。
与理据相关的其他专著及教材:随着理据研究在国内学界被炒热,大量的语言学专著或教材,总会涉及这一话题,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张斌(2002/2010)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将理据义列为词语的四大附加义之一。董为光(2004)的《汉语词义发展基本类型》,把理据义作为词的一种联想意义。曹炜(2009)的《现代汉语词义学》认为,现代汉语的大多数词语是理据透明的。赵彦春(2014)的《认知语言学:批判与应用》专辟一章,论述理据与无理据之间的张力。此外,何南林等(2013)的《汉英象似性对比研究》、何爱晶(2011)的《名--动转类的转喻理据与词汇学习》、刘敬林、刘瑞明(2008)的《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吴会芹等(2011)的《词汇理据与词汇教学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探究了理据议题。
2.学术期刊论文概述
鉴于中国知网是国内最大的学术期刊论文网站,我们选择它来管窥语言理据研究论文概况。截至2015年4月26日,以“理据”为检索词,在“期刊”的类别下,分别选择“篇名”、“主题”和“关键词”,得到的结果是1 623篇、3 597篇和621篇。再以“象似性”代替“理据”,其他条件不变,得到的结果是667篇、1 387篇和1 227篇。可见,语言理据(含像似性)已是国内当代语言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学术期刊上的语言理据研究论文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无论是专业期刊如《中国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还是大学学报如《北京大学学报》、《同济大学学报》,抑或社科院系列的杂志如《中国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无论是CSSCI期刊如《中国外语》,还是普通期刊如《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几乎都发表过理据研究论文。第二,不论是知名语言学家,还是普通研究者,大都对语言理据产生兴趣。权威语言学家的高影响力论文有许国璋(1988)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张志毅(1990)的《词的理据》、沈家煊(1993)的《句法的象似性问题》、伍铁平(1994)的《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李葆嘉(1994)的《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许光烈(1994)的《汉语词的理据及其基本类型》、刘丹青等(1998)的《汉语指示词语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察》、严辰松(2000)的《语言理据探究》、王艾录(2003)的《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王寅(2003)的《象似性辩证说优于任意性支配说》、陆丙甫等(2005)的《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马庆株(2007)的《理据性:汉语语法的特点》、史有为(2008)的《语言符号的有理认知》、石毓智(2008)的《语法规律的理据》、胡壮麟(2009)的《对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之争的反思》、赵毅衡(2011)的《理据滑动: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丁尔苏(2012)的《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并行不悖》等等,不胜枚举。第三,理据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因此挂钩理据的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例如音系理据、形态理据、构词理据、词汇理据、词源理据、语义理据、语用理据、认知理据、像似理据、文化理据、模因理据、心理理据等,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国内语言理据研究已进入了活跃期。第四,来自外语界的刊物和研究者所占比例更高,他们更认同语言理据研究。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从1993年至2014年)发表语言理据论文7篇,《外国语》(从1981年2012年)发表11篇,《外语教学》(从2003年2014年)发表13篇,《外语与外语教学》(从1986年2014年)发表18篇。第五,“理据”概念的实践应用特别广泛,已成为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中最具解释力的术语。可以说,汉语理据研究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理据”一词的模因传播。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德范克主编的《ABC汉英大词典》都收录了该词,而这种收录产生的能量不可小觑。
3.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简论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代表了学界的新生力量,就像奥运会的银牌、铜牌获得者很可能升格为下一届的金牌获得者。我们将时间段设定为2000年至2015年4月26日,并以“理据”为检索词,在“博士硕士”的类别下,分别选择“题名”、“主题”和“关键词”,得到的结果是149篇、986篇和105篇。再以“象似性”代替“理据”,其他条件不变,得到的结果是150篇、292篇和244篇。分析这些结果,发现呈现出的总体特点是:选题新颖,覆盖面广,名校较多,影响很大。例如赵宏的博士论文《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2011)被下载2 833次,引用10余次;赵飞的硕士论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2005)被下载1 994次,引用数次。
三、基本论题
1.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关系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关系,萌芽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他在讨论词语构式的意义、价值、结构、变化尤其是任意性时,附带涉及了词与物之间的外部理据、词的组合聚合理据、词语理据的类型学差异、以及流俗词源理据,此后词语理据逐渐被现当代语言学关注。在Ullmann(1977)、Haiman(1985)、Lakoff(1987)等学者将“理据”作为理论分析工具而加以重新分析以后,理据性正式成为任意性的对立面,二者的关系因此构成相关研究的首要前提,被讨论得最多。总体上看,国内语言学界形成“矛盾说”、“从属说”、“分层说”和“协同说”等4派,尽管每派内部的意见也不尽一致。赞成任意性或理据性的不少学者多持矛盾说,跳不出“既然任意性指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那么其反题理据性就应该指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有自然的联系”的逻辑设置,甚至有将任意论推向“任性论”的趋势。从属说坚持语言符号主要是任意性的,而理据性只是次要的和派生的,国内认同这派观点的主要有岑运强(2006)等。分层说认为词语音义结合层主要以任意性为主,但符号组合层例如句法,则主要以像似性或理据性为主,王寅为这派的主要代表。协同说认为任意性相当于一种战略原则,它为语言符号音义的结合提供诸多可能,而理据性相当于一种战术原则,它为语言符号音义的结合提供具体而微的动因,王艾录是协同说的引领者。
我们认为任意性概念张力巨大,具有多种涵义,决不局限于狭义上的“语言符号音义之间无自然联系”的所指内容。它与理据性观念相遇、碰撞、对话,形成对立统一的交集。当然,这里还需辨清理据的隐含意义。我们认为理据由理据义和理据性构成,即理据义是赋予言语以自由的具体的类型学参数,而理据性是控制人类语言秩序的抽象的普遍原则。理据义具有多样性,此时即体现为任意性;理据义又具有管约性,此时即体现为理据性;因此从哲学的角度看,任意性更重要,但从语言的角度看,理据性更重要。可见,理据义使得任意性与理据性协同发挥作用,一起成为贯穿语言自组织系统的两条杠杆,那么抓住了词语的理据义,就等于抓住了有关任意性和理据性争辩的所有问题。
2.理据的性质、丧失与考证
理据常被定义为语言符号产生发展的动因。动因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属于认知和意念范畴,因此理据不像词音、词形那样,具有物理性。它充满虚的性质,具体包括潜隐性、历时性、民族性、聚合性、从文字性、从语言表述性等[2]。潜隐性指理据虽在词义或内部形式里留下马迹蛛丝,但多数藏于词语后面。历时性指理据表征和石化了的某时代的社会文化面貌,成为了一种历时的信息,而它造就的词语却处于共时的语言流通域,二者被越来越大的时间鸿沟阻隔。民族性指理据自产生始即打上民族思维的印记,尽管理据性质是泛语言的和普遍的。聚合性指派生、复合和句段诸词的理据,围绕根词、语素等构件而呈纵向网络状。从文字性指词的理据通过书写或隐或显,例如能指“yuánlái”写作“元来”是理据显,而写作“原来”为理据隐。从语言表述性指把意念范畴的理据,用语言表述和显化为具体的知识点,即理据义。
理据的这些性质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理据丧失。理据丧失的论题被当代认知功能语言学称为腐蚀(erosion),Fischer & Nänny(1999)、Haiman(2009)、王寅(2008)、王艾录(2008)、姚小平(2010)、赵宏(2013)等都讨论过它。我们认为,词语理据丧失有其内因和外因[2]。内因指理据的上述属性导致它自身难以显化,而外因指词语的意义支点、曲折表达和文字书写等因素对理据的干扰与磨损。考察理据丧失之因,目的是重建旧词的历史理据,使其失而复得,同时记录新词的理据,以便传之后世。
就考证而言,有些词语的理据通过词义、内部形式等或显化或保存,因而勿需考求。有些则要考释,由语言表述而成理据义,即从认知到物化。理据考证方法不一而足,例如传统汉语研究中的因声求义等。现代常用的有这么几种:一是词源追溯法,即“词的历史渊源决定或影响了词的意义,人们可以从它们的出处与其意义的关系找出词的理据”[3]。词源与理据有交集,但非同一概念,这里仅指那些包含理据信息的词源。二是词素语义挂钩法,指构词语素使用晦涩的义项,与词义连通极难;但如揭示开来,理据立刻让人恍然大悟!例如“马蜂”中的“马”为何意?原来,马在古代是六畜之首,后衍生出“大”的含义,因此“马蜂”中的“马”为“大”,类似的例子还有“马勺”等。三是内部形式展析法,即将语符的压缩的语法·语义结构,解码为易懂形式,例如“秋波”:秋水之波。
3.词和字的理据——兼谈理据论与“字本位”的关系
作为贯穿语言系统的一个变量,理据涉及语言的各单位和各层面。由于最基本的语言符号是词,因此自索绪尔始,人们在讨论语言任意性或理据性时,大都把词语作为出发点。这意味着明白了词的理据,即大体明白了语言的理据。词语,历时地看,分为原生词和继生词;从结构上说,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之别。原生词大多是单纯词而继生词主要为合成词,这种重合性对理据问题来说,得出的推论便是:如果说原生词无理据,那么单纯词也大都无理据,反之亦然;如果说继生词有理据,那么合成词也大都有理据,反之亦然。这样的认识,大致适用于索绪尔设定的“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4]51的西方语言。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西方语言文字主要是表音和他源的,失去了物质化的“形”的支撑。“形”的丧失对原生词和单纯词的影响最大,而合成词由于有了内部形式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内部形式所提供的一些用于理据考求的“蛛丝马迹”,遂被认为是相对有理可据的,尽管王艾录指出,以内部形式之有无来判定理据之有无,是犯了倒果为因的思维错误:理据决定内部形式,而不是相反。
汉语中有没有词和词组?说有易,说无难。然而如果把词定义为word的话,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单字词似乎问题不大,因为可以用一字一词的简单办法处理。二字词和多字词则存在难以区别词和非词的问题。我国语法学界长期为鸡蛋、鸭蛋、牛皮、羊皮等是词非词的问题争论不休。此类棘手的情况也反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例如第6版收“牛皮”不收“羊皮”,收“鸭蛋”不收“鸡蛋”,收“鹅毛”不收“鸡毛”……又有谁能说清楚“牛皮”、“鸭蛋”、“鹅毛”是词而“羊皮”、“鸡蛋”、“鸡毛”是词组呢?
或曰没有词哪有词典?有人以词典来证明词,这仍然经不住推敲。请看《现代汉语词典》在其前言中的首先声明“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把词和非词的东西一锅煮,这正是因无法区别词与非词而陷入困境的真实写照。其次,《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排体例是以单字为纲而以字组为目。词典凡例§1.1说:“本词典所收条目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如此以字带词、词组等的编排体例,与西语词典有着本质的区别。西语是典型的词本位语言,而汉语是典型的字本位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在事实上,倒是坚持了字本位的编排原则。
中国古代有字典,有辞典,却没有过一本词典。如今虽然有了《现代汉语词典》,但仍不敢说它是一本科学意义上的“词典”。大道至简,抛弃西语的一系列术语,比如不称词、词组而仍称汉语传统的字、字组,便可以拨去繁冗,举重若轻,直面母语,避免了多少学人精力之浪费。也许是因旁观者清之缘故,外国学者有时可以说出具有清醒认识的话。英国东方学家塞斯(A. H. Sayce)在《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三版的“语法”条目里指出:“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弄明白,除非我们不但要把欧洲语言的文法术语弃掉,而且连这一套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也弃掉。”[5]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4]51的确,在汉人的心目中,母语最基本的语义语法单位是字不是word(词、辞古人指虚字)[6]。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尔雅》、《说文》、《广韵》等中,看不到一点印欧语的词和词类的影子。《助字辩略》、《经传释词》等一系列土生土长的汉语言著作,都是以字为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乾嘉学派、马建忠、严复以及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泰斗的早期著述,都是论字而不论词的。吕先生在《语文常谈》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却相反,现成的是字。”[7]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因此在继承汉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艰苦、深入的钻研,提出字本位理论,有徐通锵、潘文国、王艾录、鲁川、孟华等人。他们认为自西学东渐以来,套用印欧语中的词、词组、句子等语法单位分析汉语的做法,是一种“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语),结果是造成20世纪汉语研究的诸多失误,因为具有语法形态的印欧语言的基本单位固然是词,但汉语编码的基本单位却是字。我们认为,汉语中的字,既是文字单位,也是语言单位,可以完全涵盖西方语言学所说的词、词组等概念。《汉字的国学理据》就是以字本位思想来贯穿全书始终的。至于有人说字的多义性是缺点,会导致术语含混,这实在是杞人忧天。例如“语言(language)”作为一个多义词,可以指人类的言语、通过言语交际的能力、一套音义结合的系统、音义结合系统的书面表达、任何交际方式等等(《韦氏新世界词典》,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可是并没有人说“语言”这个术语不能用。至于什么汉语要像英语一样分词书写的提法,什么要以拼音代替汉字的论调,更是无稽之谈。须知,汉语汉字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广大社会成员,而不是那些满脑子印欧语语法观念的人。只有下定决心立足于汉语语言事实的学者,才能力排众议,独具慧眼,为汉语研究做出实质性的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理论贡献。
理据论与字本位论同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它们都关系到语言编码的基本单位和基本原理问题,具有貌离而神合、异曲而同工之妙——理据论从字切入,字本位论从理据入手[8]。具体而言,一方面,理据论中的字本位观主要体现于以下四条:第一,理据论的领军人物王艾录也是字本位论的最早提倡者;第二,理据考证以字本位观为理论前提;第三,古往今来的汉语理据考证都围绕字而进行;第四,汉语理据考证的基本单位是字和字组。另一方面,字本位论的语言理据观主要有四点:第一,字本位论的创立者徐通锵,同时也是理据论的坚定倡导者;第二,字被重新定义为汉语中音义结合的、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第三,汉语传统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以字为基本单位,进而考求语言的组合理据;第四,字本位论明确坚持,汉语语法是对理据载体组合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规则的探索。总之,理据论者致力于探究语言符号发生发展的动因,以字为探索语言理据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字本位论者则有志于确定汉语运行的基础,认为字是汉语中最基本的音义结合的理据块。两种理论把历时与共时、语义与语法和谐相系,共同为挖掘汉语的本质特点,开辟了新的研究域。
顺便指出,字本位论还提出了“理据载体”概念[9]50-56。徐通锵认为与意义相联系的语音感知单位即理据载体,例如汉语中的可能具有意义的声和韵(我们认为至少某些声是有意义的,譬如依据戴淮清的《汉语音转学》,sh有“看见”的意思,它和韵母结合生成音近义通的词语,例如审、视、识、省、熟等),以及英语里的语素。汉语的语音感知单位与意义有自觉的理据联系,结合生成字这一基本结构单位,而英语等印欧语先通过语法化生成词缀,词缀再与词根结合并显示基本单位“词”的结构理据。徐先生还说,汉语的理据载体为成分理据,英语的叫组合理据;两类载体性质不同:有成分理据的语言一定有组合理据,但有组合理据的语言不一定有成分理据。我们觉得,理据载体概念应该加以扩展,遂尝试性地将之定义为“表现理据这一认知动因的语言单位”可以是语音、语形、语义或者由它们结合而成的词素、词、短语等。汉语的理据载体由声韵到单字再到字组,尤其是二字组;二字组上接单字,下接句法。英语的理据载体由语素到单纯词再到具有内部形式的合成词;合成词是理据研究的重点,与句法相通。
4.句法、语篇等层面的语用理据
人们倾向性地认为单纯词等原生符号是任意的,而语言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合成和组合符号才是有理据的、非任意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原生符号的理据在历史长河里丧失,失而难得;另一方面,语言的理据化机制逐渐由单纯语言符号的内部音义层,转向具有内部形式的合成符号与组合符号的外部符际层。换言之,语言系统及其理据特征发生了新的变化。语言系统出于表达精确化的需要,导致越是结构复杂的语言单位,所负载的信息量也越大,受到的理性制约也就越多。例如随着词语从单音节向多音节的变化,语言从非线性的单纯符号转向了线性的合成符号,其理据更加丰富、显化,产生了质的飞跃,不但有词与物之间的理据,音和义之间的理据,还有内部形式和理性意义之间的理据等。与此相应,理据研究不仅要关注基本语言符号的自组织规律,更要探索语言交际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语用理据性。
语用理据萌芽于索绪尔的“相对理据性”概念,即围绕合成符号而产生的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机制,例如“dix-neuf不是完全无理据的……dix-neuf则涉及整体语言内共有的字眼”,“无理据性达到顶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低到最低点的则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10]。可见,索绪尔认为复杂语言符号的产生、运用、变化等,都受制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以不是任意无序的。句段关系是显性的,而联想关系是隐性的,但借助词典编纂等手段,隐性的聚合理据可以物化、外显,例如围绕核心词“人”而形成的人名、人们、人大、人情等词语。韩礼德(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认为,内容层(语义与语法)和表达层(音系与语音)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而非任意性的[11],这里的自然性指聚合理据,即索绪尔聚合概念的具体应用,更是我们所说的语用理据。当然,当代语言学扩展了语用理据的所指范围,还包含了社会、文化、认知等任何语言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可论证性动因。国外的语用理据研究集中于句法和语篇,例如荷兰的约翰本杰明公司,先后15次出版了语言像似性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它们大多涉及语用理据。国内王艾录等著的《语言理据研究》,也用很大篇幅论述了句法理据,即语用理据。中国知网中,题名包含“语用理据”的论文也达百篇之多。这些事实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理据已演化成一个具有可造作性的理论概念,即成长为语用方法论了。
5.理据的语言类型考察——以英汉语为例
索绪尔对语言理据研究的贡献有二。一是提出了相对理据性的概念,二是把语言的分类与语言的理据结合了起来,引出了语言理据的类型学问题。例如,他说“各种语言常包含两类要素——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但是比例极不相同,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4]184-185;另外他还谈到了拉丁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汉语等的个性的理据表现。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比研究了英汉词汇的理据,例如,徐通锵(2008)的《字本位语法导论》、潘文国(2002)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王艾录等(2002)的《语言理据研究》、蔡基刚(2008)的《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尚杰(2010)的《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赵宏(2013)的《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等。
我们认为英汉理据对比主要包括词语、句法和文字三个层面。词语理据方面,第一,英语词源多涉及外来语,导致了其理据的辗转变异,而自源的汉语却有文献资料证据的有力支持。第二,英汉语最小理据载体及运行方式差异巨大。汉语最小理据载体,例如音节,以“音近义通”的方式派生孳乳出许多单纯词,人们据此认为汉语是理据性编码的语言。英语的最小理据载体,例如自由或粘着词素,它们相互结合进而“拼”出语形理据,例如doer,而语音理据则微不足道,因此无法将大量的单纯词理据化,人们遂曰英语主要以任意性编码为主。第三,汉语合成词除横向组合理据外,还有围绕某核心词而形成的明显的聚合理据,可是英语词的聚合理据数量很少。第四,英汉词语理据化的共同点,主要是合成词的理据比较透明,这种组合式的理据渐成主流,即横向组合理据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共性。句法理据方面,英语是语法厚而语汇薄的语言,汉语则是语汇厚而语法薄的语言[9]49-50。从理据视角看,英语句法理据尤其是句法像似性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词语理据研究成果不多,语义研究单薄,对单纯符号的像似性探索几乎束手无策。汉语恰恰相反,语词或字的理据研究成果很多,而语法规律的总结与探究也即句法理据的成果较少,汉语百年语法研究所获不足就是明证。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语言系统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所致,因为如果印欧语言的词语编码以任意性为主,其句法必有理据性一面,否则就意味着“任意性原则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结果将会弄得非常复杂”[4]184。同样,如果汉语的词语编码以理据性为主,那么其语法必有任意性的一面,否则语言就是僵化而机械的堆积物,更失去了生命与自由。文字理据方面,汉语是自源文字,在音形义三元构成的符号化的表意过程中,音义与形义相辅相成,而且更重视形的视觉编码作用,例如独体字的象形机制配合着音近义通的拟声原理,使得大量的单纯词得以理据化;而合体字的以形会意和形声相合,亦与合成词的理据化原理相符相契。英语为他源文字,其符号的音形义三元中,形附属于音,即形通过音的中介与义发生关联,结果是形随音转、音变形亦变,大量的理据因而遭受腐蚀湮没。不过,随着英语成为分析语,非单纯的符号也在增加,形的作用进一步得到凸显,也走上了类似于汉语的拼形表意的理据化道路。这或许是世界语言共同的发展方向,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
需要指出,语言理据与文字理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语言理据主要指音义结合的理据,具体分为语音理据和语义理据;文字理据主要指形义结合的理据,具体分为语形理据和语义理据。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语义理据,差别在于语音理据与语形理据的不同。然而,语言文字中的“形”有双重含义,既指文字之形,例如象形;又指结构之形,例如内部形式。反过来看,文字之形可与语言之形重合,例如blackboard(黑板),其语言之形包括语法结构“形+名”和语义结构“黑+板”,但是这一内部形式恰恰要借助两个文字之形black和board才能实现!这说明语言理据与文字理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汉字的理据折射的正是汉语的理据。以往研究最大的失误,就是只看到文字之形与语言之形的必“分”,而未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可“合”!
四、语言理据的应用
理据是认知功能语言学流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其概念已进入当代语言学的核心术语群,被国内外多部词典收录。同时,它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王艾录、司富珍(2002)讨论了理据在语源、造词心理、语文教学、名称、避讳、谐音、跨文化交际等领域里的应用。周荐、杨世铁认为理据对造词法、文化词汇学等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2]。我们认为要发挥理据在建设科学、理性、和谐的当代语言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对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理据便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以现代白字为例,它们出现在许多新词新语里,致使语言流通使用中的不少随意混乱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造成语言腐败;潘文国(2008)忧心于此等现象,慨然写就《危机下的中文》。譬如,国人把“祸起肃墙”写成“祸起萧墙”,把“吕脊”写成“里脊”,把“拉大旗坐虎皮”写成“拉大旗作虎皮”,一字之差使得词的语义结构完全破乱,呈现非理性、不规范之态。如果依据理据论而加以干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划工作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正能量,使规范和合理的东西胜出,最终朝着理据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前进。目前,理据应用被探讨最多的,是词语理据与汉字理据在语言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语言理据应用的一个新兴领域是词典编纂。国际上较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Swanepoel,其论文《Linguistic motivation and its lexicographical application》被中国学者李蕴真(1996)译为《语言理据性及其在词典编纂中之应用》,发表于《辞书研究》。国内提出理据词典编纂设想并付诸实施的是王艾录,他的《汉语理据词典》(1995)影响巨大。近年来,其他学者如王寅(2009)、赵彦春(2014)等,也在呼吁理据词典的编写。赵彦春在《认知词典学》(2004)、《隐喻形态研究》(2011)等著作中多有这方面的探讨。此外,我们认为国人学习英语时词汇是难点,因此迫切需要编写一本《英语理据词典》。
就理据与词典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理据与词源的关系。我们认为“词源”是笼统的说法,实际上杂合着理据、最早出处、借词等。当它仅为某词的原形式或等价语时,还不是理据;只有当它提供某词的发生缘由时,才是理据。可见,理据重在解释词语今生的认知动因,而词源偏于寻找词语前世的书面出处。然而,二者交叠重合,共性多于差异,故有学者认为,理据研究有助于词源词典和语文词典的编纂[13]。二是理据与语文词典的关系。无论是牛津系列英语词典,还是《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大都属于“词义词典”范畴,因为它们以交代词语的理性义为首务。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含有不少理据信息。例如牛津系列英语词典麾下的《简明词典》、《新牛津词典》、《词源词典》等,都标有大量词源。《牛津袖珍英语词典》第10版说:“本词典给许多单词提供了词源信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从第6版开始,以origin的字样,标注了大约200个的词源。分析这些词源,我们发现它们含有许多理据资讯,例如liner(客轮):[origin because such a ship traveled on a regular line or route(源于其沿着固定的线路行驶)]。显然,方括号里的内容既属词源,更是理据,但理据事实常被词源这一过于宽广的概念所遮蔽,因此受到严重的忽略。再如《现代汉语词典》,吕波认为第2版中有600多条对词的理据的注释[14]。我们则认为像第6版中的理据信息,可具体分为背景知识型、外来语型、隐喻型、内部形式型和释义型等五类[15]。前三类一般有专门的元语提示词,标释得比较明确。后两类基于语素或字,是理据资讯的主体,有的一目了然,有的则需推求才能激活。可惜《现汉》隐性的标注方式,导致人们容易忽视含于其中的理据,而且标注本身也存在指导目标欠明、分类标准不一等不足。总之,英汉语词典的理据信息表露虽渐成事实,但它们迫切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从而避免盲目性。
五、不足与展望
国内的语言理据研究尚处于“现在进行时”阶段,既孕育着希望,也存在有不足。不足之处,一是许多研究只集中于理据性与任意性关系的简单辨析,缺少深层的挖掘,以致限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学理困境。二是喜欢热炒理据这一概念本身,但缺乏深入钻研之耐心和理论突破之勇气,没能为理据研究提供新的思想武器。三是普通语言学视野不够,结果是论证语言任意性时,就以英语等西方语言为例;论述理据性时,却以汉语尤其是汉字的象形性为例,得出的结论因此不免偏颇。四是感想式的尝试多,而实证性的研究少,特别是不重视理据义的搜集整理,也不会充分利用英汉语词典中所隐含的理据信息。五是外语界与汉语界未形成合力,吕叔湘先生所说的“两张皮”现象依然严重。例如外语界学人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语言研究新信息,但受西方语言任意论范式的束缚,加上自身学养与所用语料的过度“洋化”,难以独立自主地深化理据研究学科;而汉语界虽有古代汉语理据研究的深厚土壤,但对国外的以“现代化”、“国际化”为标准的语言学理论有时不够熟悉,难以理直气壮地坚守理据研究阵地。
然而,随着国际语言学界对索绪尔任意论范式的突破,随着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着现代化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自信心的恢复,随着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走出去”时与西方成果“走进来”的相遇,例如最新出版的语言像似性研究国际论文集,书名即为《像似性:东方遇上西方(Iconicity:East Meets West),2015》,尤其是随着王艾录语言理据研究和王寅语言像似性研究等先期成果的引领,国内语言学界将为最终建成“语言理据学”这门隶属于认知语言学的新学科而不舍昼夜,进而与西方语言学对话、互补、共存,迎来更具包容性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曙光。
[1] 李二占.汉语理据学雏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J].同济大学学报,2013(4):110-118.
[2] 李二占.词语理据丧失原因考证[J].外国语文,2013(4):61-65.
[3] 汪榕培,王之江.英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57.
[4]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申小龙.语法差异的中西文化视角[J].北方论丛,2011(2):45-50.
[6] 王艾录.汉语语法类型管窥[C]//王艾录.现代汉语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66-274.
[7] 吕叔湘.语文常谈[M].北京:三联书店,1980:45.
[8] 李二占.字本位论与理据论深层对接关系的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3):123-128.
[9]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10] 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97-102.
[11] Halliday M A K,Matthiessen C M I M.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14:27.
[12] 周荐,杨世铁.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538.
[13] 张志毅.词的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115-131.
[14] 吕波.试析《现代汉语词典》对词的理据的注释[J].辞书研究,1996(2):11-16.
[15] 李二占.《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理据信息[J].同济大学学报,2015(1):116-124.
〔责任编辑:朱莉莉〕
H08
A
1003-6873(2015)03-0045-09
2015-01-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理据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12YJC74004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隐喻与转喻中意象图式的对比研究”(2015SJB735)。
李二占(1972-- ),男,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言理据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3.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