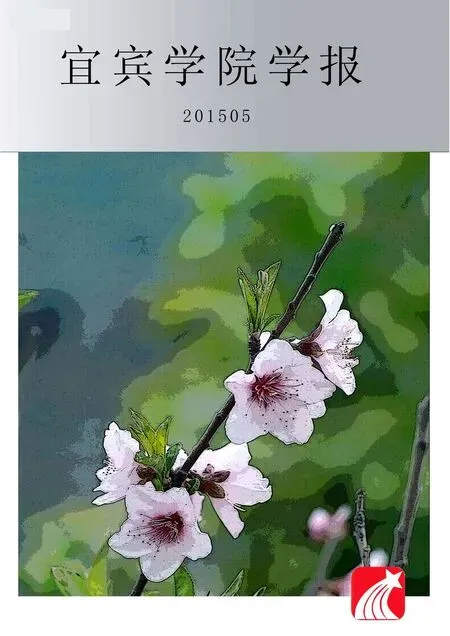过渡中的吴公馆——论《子夜》中的家族形态
2015-02-13赵静
赵 静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茅盾《子夜》中的吴公馆屹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东方巴黎上海,是上海都市文化在家族场域内的微观形态。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将吴公馆认定为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陷入了单维政治学的窠臼,意识形态化的研究遮蔽了许多可供挖掘的内涵。而纵使淡化了意识形态,取消吴公馆的阶级属性,我们发现此座公馆也无法将其划定为我们传统认定的封建大家庭之内。吴公馆无论是外延的公馆装潢还是内部的公馆家族结构都已经与《红楼梦》中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不可同日而语了。其内部家族成员已经完全跳脱了单纯依靠地租过活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的生活叙事中也已经完全容纳在现代都市场域之内,甚至公馆成员的日常行为审美方面也已经消解了几千年历史延续下来的文化哲学体系,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所以,仅仅将吴公馆定论为封建大家庭,忽视了其家族生存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认定。
实际上,公馆者,“憩足之地也”①,家庭“大众可息之地也”其主要鼎盛于民国时期,20、30年代是公馆发展的高峰期,一座座公馆不仅出现在现代都市之内,更林立于文学作品之林。到了40年代抗战时期,由于众多家庭为了躲避战火,转而向内陆挺进,一些大城市中的公馆徒留虚表,成了空壳子。以至到了1949年之后公馆开始作为公共住房,供一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临时分配居住,作为私人住宅的公馆这才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可以说,公馆在民国时期代替了府宅的生活寄托能力,并朝着单体式单元房逐步过渡,实乃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民宅过渡形态,是由封建地主庄园、府邸向当代单位住宅、商品房的过渡建筑形式。《子夜》中的吴公馆就是典型代表,其实现了对贾府为代表的古代都市私人住宅的自觉突破,开辟了新型的生活空间,产生了以往未曾出现的家族问题,并向着现代民主家庭逐步推演、转化,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过渡家族的代表。
一 现代化公馆生活
公馆一词古已有之,主要指代公家馆舍,最早见于《毛诗》,有句曰“公馆之堂涂也”②,后《毛诗注疏》中又见曰“正义曰礼有公馆私馆,公馆者公家筑为别馆以舍客也上。”③即公家建筑用以宾客居住的别馆。而后随着时代的推进、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演变,公馆在文学典籍和小说作品中的含义发生了意外地对立转向。公馆不再是公家馆舍的称谓,开始作为私人住宅出现在人们的视域范围内。在黄煜的《碧血录》中,公馆已经被冠以姓氏,作为私人住宅出现,有句“钱公馆莲花泾徐氏予往”④可考。而到了清朝,在同治年间的《从公录》中,已出现“城市村镇无论绅士兵民公馆店铺均须逐户编查”⑤一说,公馆已经开始用于称呼于私人家庭,需要按户籍编查。尤其是民国时期,在众多小说佳作之中公馆的意象更是层出不穷。
其实商品经济发展、都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变迁不仅仅是公馆作为的词语的意旨内容,其更涉及到公馆这一家族场域本身的“更新”。在子夜的开篇茅盾是这样描写这座文学中拟造出的上海吴公馆的:
但是汽车上的喇叭又是呜呜地连叫三声,最后一声拖了个长尾巴。这是暗号。前面一所大洋房的两扇乌油大铁门霍地荡开,汽车就轻轻地驶进门去。阿萱猛的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见荪甫和竹斋的汽车也衔接着进来,又看见铁门两旁站着四五个当差,其中有武装的巡捕。接着,砰——的一声,铁门就关上了。此时汽车在花园里的柏油路上走,发出细微的丝丝的声音。黑森森的树木夹在柏油路两旁,三三两两的电灯在树荫间闪烁。蓦地车又转弯,眼前一片雪亮,耀的人眼花,五开间三层楼的一座大洋房在前面了,从屋子里散射出来的无线电音乐在空中回翔,咕——的一声,汽车停下。[1]
(一)汽车
汽车缓缓驶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三层大洋房,大洋房内飘散出来悠悠绵绵的无线电音乐。汽车、洋房、无线电音乐,几个简单的词语就勾勒出吴公馆的现代奢华与时尚迷幻。公馆内外所构成的风景与汽车驶进大门前的上海都市的景致并无二致,吴公馆上上下下几乎成为上海都市的小型缩影。也难怪当汽车刚刚停下,从乡下初来上海的吴老太爷便大呼进了“魔窟”,只能用尽最后的全部生命力摇一下头,紧紧地抱着与他思维认知以及生活模式相契合的《太上感应篇》。待到他走入吴公馆,看到那不停摇晃的电灯,穿着时髦、喷着香水的各色女流,吴老太爷连仅存的游丝都已不在,脸色煞白,头晕目眩,最终一命呜呼。
吴老太爷等一众人选择的是现代化的代步工具——汽车,汽车正是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交通工具。“世界各国之进化,无不以物质文明为先导,所谓物质文明虽有赖各方面种种之发展,然扼其大要,以致政治方面而言,建设道路,整理交通。以工商业方面而言,振兴实业,开关利源,而所以收政治交通之效果,则必有物以为媒介得,所以收开关利源之效果,则必有物以利运输,诸君思之,此物何物乎,汽车是也。”⑥在当时之上海,汽车的出现已经不足为奇。根据上海历史地理志考证,上海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一条世界主义的花边。现代都市的基本设施在上海快速地逐次运行:银行于1848年传入,西式街道1856年,煤气灯1865年,电1882年,电话1881年,自来水1884年,汽车1901年和电车1908年。[2]其中汽车更是成为上流社会居民的出行必备之选,一时间上海市内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汽车作为吴老太爷首先接触到的吴公馆的现代设备,已经给吴老太爷在心理上造成了莫大的压力。这一工业文明的象征也与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从乡下进驻都市的高老太爷格格不入。
(二)公馆门里门外
而随着汽车的缓缓行驶,面对着已经完全都市化的儿女们,听着他听不懂的语言,看着那些从未见过的盛况,吴老太爷只能紧闭双眼,用自我意志来对抗这座已经“邪魔化”的都市。而当汽车停在吴公馆的院落之内,他再也无法选择性麻痹自己,从主动地选择性认同到被动都无法接受,本快要靠近死亡的边缘,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容身之所、灵魂栖居之地,他腐朽的身子已经到了入土为安的时刻。汽车流动型的进入方式给了吴老太爷选择的时间,而它一动一停的动作也让吴老太爷闪避不急,一以贯之流动的心理线条让吴老太爷的压力一增再增,以至于最终无法招架,唯有命丧黄泉。
按理说,门作为家庭出入的端口,是屋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门的开合,人的进入,置换了两种不同的空间。门是“两种状态,两个世界,已知和未知,光明和黑暗,贫富和匮乏之间的出入口。”[3]“推门”“敲门”“开门”“跨入”,不同的进入方式和不同的开门动作都会在流动中给人呈现异样的环境体验和情绪感觉。可对于吴老太爷而言,进门前后的两重环境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同时展现出上海都市的文化风光与现代表征。如果说,当汽车驶过南京路与河南路的时候,老太爷看到那“醉人”的都市风光只是颇有不适,那么来到家中,看到公馆内外与都市和谐共融的景观才是对他致命一击。家族也无法再充当都市进程的遮挡物,家族所承载的文化土壤已经无法使得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旧式人物躲避其中,安享天命。吴公馆所构成的家族场域已与都市场域合二为一,这即是对吴老太爷价值认定的完全颠覆,是对其生活理念和生活理想的双重打击。
(三)新兴的生活理念
其实不单单是汽车和吴公馆那偌大的花园式院落以及现代感十足的装饰让吴老太爷头疼不已,真正影响他判断的还是其内部成员们的都市化价值审美和日常生活理念。吴老太爷对二小姐的话语难以理解,对吴荪甫一家的吃穿用度更是无法介入,从乡下而来的他和他们早已成为两个世界的人。吴老太爷这样的感受事实上也间接证明了吴公馆内核的都市化,也就是说都市场域对于吴公馆这一家族场域的完全渗透。在吴公馆内,钢琴、沙发、电灯、电话自不必说,就连成员们的平日生活都已经无法离开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领域。林佩珊、范博文、张素素等一众青年男女去外国百货公司买高级化妆品,女子出门必喷名贵香水,穿西式洋装,去丽娃丽坦游玩赏乐。不仅吴公馆建筑本身体现着“西洋新古典主义的折中”,参考于西欧“宅邸独立于空旷之周围”的建筑理念,[4]就连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西化生活方式”,欣赏和接受着“西方物质文明”,和上海都市一样显示出“异质文化”的特色。
可以说,吴公馆内外已经无法脱离上海而独立存在,其与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发展是同步的,甚至是同体系的同构关系。茅盾大笔一挥让这座拟定的文学公馆浸淫了上海都市的光怪陆离、声光电影,甚至一开篇就安排旧式人物高老太爷扬长而去,滞留下一座完全适应都市生活、习惯于上海生活的,由年轻一辈组成的“青年公馆”。而那本该作为吴老太爷《太上感应篇》的完美继承者的四小姐也渐渐地被上海的都市感所同化,成为整个家族中最为激进的代表,勇敢地脱离家庭追求自我爱情、自由生活。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她那间象征着旧有伦理、密不透风、与世隔绝的屋子中所敞露出的窗户一般。上海都市的疾风骤雨透过窗户席卷而来,打湿、弄污了平摊在桌子上的《太上感应篇》。旧式的生活体系在吴公馆内毫无生存空间,甚至连一丝夹缝都荡然无存。在茅盾的心里,吴公馆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一座象征着“衰败”的封建家庭,为了打造“资本主义罗曼史”的恢弘历史,吴公馆作为其中的家族代表早已经蜕变为现代都市的同属性的家族空间,家族已经在社会转型期完成了新的转向。
二 经济化家族结构
吴公馆的新型变革不仅仅停留于审美方式或者生存模式,更触及到整个公馆存立的基础命脉。整个吴公馆内都市化进程最为明显的体征即为其经济化的过程。吴老太爷去世后,吴公馆操办葬礼,茅盾仅仅用一章的笔触将一个阔大的上海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从政界到军界、从买办到世家,众位人物粉墨登场。而这一章茅盾也点明了吴公馆的家族地位,其为商人家庭。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对人的身份地位有“士、农、工、商”之划分,商人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空有财富,却从未享有实权。在古代典籍记载中,商人不能“衣丝乘车”,甚至很多家庭以经商为耻,只因“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可以说,古代的统治阶级从法律和政治上控制压迫着商人的地位和尊严。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后期才有所改善,但收效甚微,甚至时至清朝雍正二年仍然有上谕明文规定:“联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汉有力田孝弟之科,而市井子孙不得仕宦,重农抑末之意……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之所能及,虽荣宠非其所慕”。⑦而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上海作为较早一批的通商口岸,更是发展出一条世界性的资产链条。当时,世界大战激战正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这样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较为宽松的道路。当时的上海,兴办实业甚至成为了时尚潮流,而那些敢于下海经商、自我创业的商人们也很好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在旦夕之间即获得巨额财富。随着政治力量对商人打击势力的减弱,这些实业家和商人们也逐渐晋身为上流阶层,成为财富和权势的象征。这也是为何这样一个商人之家能够在老太爷的丧礼上邀请到如此众多的政界名流和世家子弟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些商人、实业家对整个社会而言,虽然已经位列上层,但是其政治能力依然较为单薄。其对于现代政治的决策权和参与程度要远远低于其经济实力。加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又处多事之秋之际,这些商人的地位和身份也可以说是摇摆不定。由于其经济力量的雄厚,他们家族成为众多政治势力争相哄抢的对象,都希望其能够纳为己用。但政客唯利是图的本质和本身的懦弱性,使他们在拉拢商人的同时也时刻警惕商人的反扑和取代。故而,商人家族在外围的政治文化领域步履维艰,他们作为特有阶层的大家庭一方面巨额资产供人畏惧、垂涎;另一方面却无法与政治世家的势力比肩,处处碰壁,始终无法施展拳脚,真正参与到现代政治角逐,有时甚至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而外围的受挫也让这些商人家族认清了自己的生存现实,开始慢慢地在家族内部实行改革,以便维持其家业的安稳,并为之计深远。他们在公馆内破除了家族内部与政治政策、思想发展等一系列破旧的家族理论,引进西方先进的生活理念,以期适应社会上所宣传的政治诉求;同时也让家庭成为他们参与现代政治、继续积累财富资本的后盾,产生了家族“新质”。
一方面,近现代商人团体的出现,并没有继续固化封建地主的生活模式,而是破坏了传统的家族的宗法性,为新式的家族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和建设经费。这些经费的支出去向并没有像传统的封建家庭一般主要用于扩展土地、房产,而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都市生活的消费,都市商品消费成为家庭生计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其余一大部分则用于实业投产和投资理财。这种新型的资本再生产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农耕经济体制下小农经济的财政模式,出现了消费化的生活倾向,使得家庭内部的开支也逐渐多元化和资本化,摆脱了单一生财的门道,更多地去靠近现代经济的运作范式,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生产要求,在家族内部产生了新的生产经济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以经济作为衡量标准的商人之家,也使得掌握家庭生计命脉的成员重新取代传统家族的“家长”成为权力的代言人,并使得“经济所得”成为衡量家族内部地位排序的“新型指标”。在公馆家族中,近现代商人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公馆的家庭生计问题,为家庭生活带来更多的收益,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脚步,而且经济能力也在稳固个人“父权”的同时逐渐稀释“父权型”家族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关系形态与衡量标准。科恩在其相关研究中曾表示中国的家庭本质上为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其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婚姻或者收养的关系,并且还有共同的预算和共有财产。这样的团体以灶为单位,无论其为夫妇、父子、祖孙、叔侄、姑媳、妯娌,凡是衣食共同,就是同一家庭,与生物团体有明显区别。在以往的家庭中生产关系往往被家庭的生物性、物理性所遮蔽,不过在均已转型为商人和实业家的众公馆中经济关系被完全“凸显”,公馆成为驳杂的经济“集合体”,利益成为人们衡量任何问题的主要标准。
事实上,《子夜》展示的是吴荪甫这一民族商人创办实业的血泪史,同样也体现了他们这一家人的家庭经济史。在茅盾细致的笔法下,描绘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发展历史,更浓缩了一个家庭的微观生活。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中的同步领域,在吴公馆内家庭的收入开销始终伴随着吴荪甫开办实业的步伐。而家族中存在的新型的经济关系也消释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人伦理念,开始成为了经济实力的角逐场。经济作为基础,不仅决定了公馆内外的上层建筑,表现出家族消费特质的文化属性,更成为了话语权力、家族管理权、决策权争夺的决定因素。经济因素在家族的蔓延,给公馆这一独特群体带来前所未有的震荡,衍生出了新的家族相处规范和准则。
三 过渡化家庭内核
虽然吴公馆的生活方式已经具有了现代特征,经济化的“金字塔结构”又引发了家族内部人伦模式的革命,但是我们却不能够断定吴公馆已经改良为一座带有西方民主特性,以夫妻为主轴的现代家庭。因为在吴公馆内部虽然经济关系已经取代了伦理道德的统治地位,但是却也诱发了一系列家族问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家庭法则。吴公馆充其量仅是一座处于时代变革缝隙间的过渡家庭,虽然具有些现代表征,但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家庭的本质内核。以经济实力作为家庭政治统治基础的规则实为一种畸形的判断准则,丧失了传统人伦道德为标杆的理性的对话机制,使得整座公馆被寂寞包围。
经济关系代替传统人伦填充了吴公馆的拟政治化的功能,使得吴公馆上下依然充斥着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对于公馆的决策者来说,虽然他们不再以家族辈分论资排辈,但是作为吴公馆中掌权的吴荪甫而言,却依然对于家庭事务中的大小经纶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力。由于吴荪甫是整个公馆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谓是吴公馆上下的“衣食父母”,全家的全部开销都仰仗他一人的经商、创办实业所得。故而,在吴荪甫的心中他更多的是经济实力超群所带来的“心理暗示”。在这样一座没有父权压制的吴公馆内,吴荪甫作为兄长承担的不仅仅是家族的责任,更因为其处于财力金字塔的最顶峰而拥有了类似于“家长”的权威。虽然吴公馆内生活的男男女女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才俊,可是因为经济原因,也只能对于吴荪甫插手的事情敢怒而不敢言,有限度地自由着。而另一方面针对其余的公馆成员来说,吴公馆家族经济地位不仅仅在公馆内部给予吴荪甫一人独断的权力,更是给予整个公馆成员莫大殊荣。在城市中,公馆并非城市平常“蚁民”所能拥有,达官贵人、委员主席、军政要人、实业家、银行家才能使用此等名号。坐拥公馆就相当于掌握了城市生活的通行证,所以之后就连那些机关职员、律师、教师、医生等也要称其自家居宅为“公馆”来。⑧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人坐车忘记买票,受到售票员的嘲讽,情急之下说出自己来自某某公馆,立即壮了胆子,而听闻此话的售票员则因为其“来自公馆”而不敢再说一语,甚至连车票钱都不要了。这虽则是个传言,但是足以见得公馆威名赫赫。⑧公馆本是一个词语,其之所以威名远播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象征的权势,而这也正是众多家族喜欢将住宅命名公馆的根本原因。这些忝列公馆之中的家族成员们不仅解决了个人生计问题,同样也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公馆背后所象征的无上尊荣,而恰恰这点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形的震慑。为了享受权力,则必须要依附公馆,而一旦脱离公馆,高等的地位和莫大的权力均不复存在。故而这些公馆成员们明知自己的个人意志被剥夺,却也麻木地继续游走在公馆之内不想脱身。他们从身体和心理上都默认了公馆所构成的“家族共同体”,对一些不平等关系也习惯于逆来顺受。
这些不对等的关系当然也不存在着良性的沟通和交流。以经济因素为纲的吴公馆内部,家族成员们可以说已经无法进行深入交流。每天围绕的话题除了家族生计便是家长里短,毫无价值。在家族中,按照传统人伦体系,家族上下拥有着同样的家族理想,他们拥有着共同的判断事物的标准,“父系大家庭”是他们特有的“社会理想”[5]。当家庭内部一旦出现利益纷争之时,家族共有理想的存在则会为解决家族问题注射一剂强心针。个人利益必须避让家族利益,并为家族、君主等集体利益服务。在这样的道德教化下,家族成员有着统一的价值认定,也有着“共同生活的世界”,而“社会概念必须又与生活世界概念联系在一起,且与交往行为概念形成互补关系。”[6]换而言之,在统一家族理念的作用下,人们拥有着沟通交流的共同的信息来源和理性准则。而随着这一人伦理念的土崩瓦解,吴公馆内部又并未形成与民主社会概念相匹配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人们只能根据经济关系来选取公馆暂时的领导者。此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出于自愿,无法脱胎于真正的民主法理,又丢失了人伦体系认定下的温情脉脉的光环,亲情与血缘让位于经济利益,故而丢掉了本应有的交流、沟通的实质,在这片环境中处处表现着“话语信息的荒漠化”:
其一,信息的获取源头不统一。在吴公馆内生活着各色人等,他们有着复杂的信息来源。既有从乡下来到上海的金童玉女,他们主要接纳和传承着旧有的伦理习俗;而也有着吴荪甫这样一位时时以事业为重的男主人,他较多地关注着国家大事与经济态势,家族事务向来眼高手低;还有着受过先进教育理念熏陶但是最终妥协于家庭做起全职太太的林佩瑶,以及她只知自我玩乐的妹妹林佩珊。他们获取信息的源头不一致,有新有旧,鱼目混杂。
其二,沟通机制的不通畅造成人与人之间理解的丧失。在茅盾的笔下几乎不见吴公馆内的家族成员围坐一起促膝长谈的场景。由于房间空间之广大,总是一部分人在屋子里,另一部分人在客厅里,互相对各自谈论的事情漠不关心,更遑论出现如贾府中的怡红院夜宴群芳、中秋节赏月吃茶的场面了。虽然在吴公馆内各成员年龄相隔并不远,可是依然并没有因为年纪相仿而产生交流的欲望以及互相的理解。在他们的心中人人都为自己设定了一座别人无法攻破的围墙。我们常常可以得见林佩瑶的倚窗凭栏,追忆过往,那一片红叶所寄托的相思和怅惘是吴荪甫永远无法所及的地界;家中的顶梁柱吴荪甫也常常感叹,身为企业家的他却不能了解少年女郎、亲妹妹的复杂的心灵和感情的变化。在这些畸形的家族场域中,趋于日常的家庭对话几乎无任何实际效用,不同的话语体系与知识结构之间也无法相互渗透与融合,故而在这些成员均为充满“个性”的个体,分别彰显着不同的价值特征,而这样的过渡时代的家庭及变革间隙的时代正是他们得以存活的温床。
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公馆中唯一一个沟通畅通的便是四小姐。四小姐初来乍到,在家庭中沟通不畅,无人理解她心中所想。她爱慕范博文,却仅仅停留于梦中痴缠,唯有将自己锁在封闭的小屋之中放任自流,在《太上感应篇》中寻找安慰。张素素的到来,并与之交流使得她最终精神一振,冲破樊笼,奔向自由。她也是吴公馆中为数较少敢于反抗吴荪甫威权的一人。她深受吴荪甫不平等关系的压榨,却无法将心中郁积抒发,最终与张素素交心之后,突然顿悟生命本真的价值,渴望真正的自由生活。她将自己从水深火热的公馆泥沼中剥离,去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自我价值。她是公馆上下唯一一个解决掉“寂寞”问题的成员,成功避免了她个人爱情的悲剧以及命运的悲惨,但也仅仅止步于个人的逃离。
可以说,公馆统治者希望继续维护此种相处关系的存在,以稳固他的决定权;而被统治的家族成员则作为留守者和寄生虫,享受着“嗟来之食”所带来的安生,在公馆内墨守成规、苟延残喘。而无法忍受公馆不平等对待的个人所能够实现的能力范围也极为有限,人微言轻的他们所能带来的震动并不能撼动整个公馆的基石,也终究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生活策略和社会准则,只能够实现个人“进化的渴望”,但却无法解决整个家庭“生存的困惑”,吴公馆依然停留于扭捏的平衡之下。
所以,吴公馆不古不今,既不是纯粹传统的宗法性的,也不是纯粹近代的人权主义的,而是处于由古代宗法性家族向现代平等互助的社会团体过渡的转型状态。如同一架马车从遥远的中国传统里驶来,中途卸下些许累赘,装载上一些现代表征,扭转原来既定的方向,将时代的车轮徘徊在有限的历史时空之下,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在那样一个庞杂的历史时代之下,吴公馆被赋予了传承与开启的历史使命。它随着国家的制度、经济发展、城市化、商品化进程不停地转换着家族的身份,改变着家族的制度,推进着家族的前进。它包容着各色不同立场、相异理念的人,保守派人物、小市民、寄生者、中间人物、激进青年等。他们生活、居住在一起,一同经历着伦理观的变革,处理事务的尴尬,接受着时代的洗礼;一同面对着家族内部的松动却无能为力,产生出何去何从的空间困惑,进而一些人慢慢滋生出进化的渴望。可以说,公馆作为其家族的物化承载体,在方方面面呈现出“过渡”特质,并构成中西杂糅、新旧之交的文化概念。
结语
通过对于民国历史的回溯,对于在民国时期繁盛一时的公馆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茅盾选取公馆的真实用意,也让我们对民国时期有着公馆情结的家族的生存模式管中窥豹。其实不仅是《子夜》,在现代文学很多作品中均出现公馆这一意象,公馆成为了民国时期特定的“家”的构想。张爱玲作品中阴暗潮湿、冷风习习的白公馆和林语堂《京华烟云》中看似一派祥和的曾公馆,都成为了我们进入其文学作品重新诠释文本的新的切入点。
通过对于民国公馆的再次挖掘考证,我们拨开了公馆名称掩埋下的家族秘密,探究出当时民国时期家族内部的真正生存法则和亲子关系,也通过梳理民国时期的家族发展,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待“家”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独特意义。
注释:
① 见自《“家”与“公馆”》,《大声》,1947年第7期。
② 见自汉毛亨《毛诗》毛诗卷十二,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见自汉毛亨《毛诗注疏》附释音毛诗注(卷四),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④ 见自明黄煜《碧血 》卷上,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⑤ 见自清戴肇辰《从公 》续录卷一,清戴氏杂着本。
⑥ 见自《申报》,1921年11月27日。
⑦ 见自《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
⑧ 见自复生:《谈公馆》《十日谈》,1934年第37-47期。
[1]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3-14.
[2]唐振常.近代上海繁华录[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240.
[3]让·谢瓦利埃,阿兰·海尔布兰特.驯化地理学[M].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编译组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616.
[4]邹德农,戴路,张向炜.中国现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3-14.
[5]郑全红.中国家庭史:第五卷:民国时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68.
[6]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