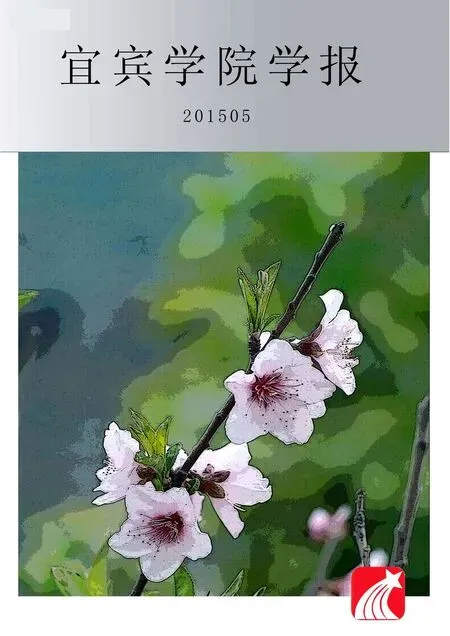是教育还是革命——论叶圣陶的个人经验与《倪焕之》的关系
2015-02-13李俊杰
李俊杰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无论给小说《倪焕之》贴上“教育小说”“革命小说”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说”等任何一个标签,都不能否认,小说的主要角色倪焕之在身份设计、心理活动以及人生轨迹上,都有叶圣陶个人经验的印记,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这样具有艺术化与抽象化的泛化描述与概括,小说内嵌着的作者叶圣陶个人的经验与人生的历程使其呈现出个人精神史的特点。
尽管收录于开明版《倪焕之》中夏丏尊的《关于〈倪焕之〉》和茅盾评论节选的《读〈倪焕之〉》①两篇评论文字对这部小说有诸如“扛鼎之作”“划一时代”这样的赞美之辞,但叶圣陶还是对这两位好友的批评性文字做了一次回应,他在1929年初版的《倪焕之》的《作者自记》中谈到:“他们两位(按:茅盾和夏丏尊)的文字里,都极精当地指摘我许多疵病。我承认这些疵病由于作者的力量不充实,我相信这些疵病超出修改的可能范围之外。现在既不将这一篇毁了重来,在机构上,这些指摘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1]285叶圣陶对于“超出修改的可能范围”的“疵病”抱有如此态度,其中的原因需从这些“疵病”本身所指向的问题去观察和分析。
夏丏尊认为小说有数处“流于空泛的疏说”,例如写“倪焕之感到幻灭每日跑酒肆”,夏丏尊特意引文进行说明“这就皈依到酒的座(笔者注:应为“坐”)下来。酒,欢快的人因了它更增欢快,寻常的人因了它得到消遣;而琐闷的人也可以因了它接近安慰与兴奋的道路”。夏丏尊认为,这段描写是“等于蛇足的东西,不十分会有表现的效果”,夏丏尊还认为,和这段一样“抽象的疏说”的,还有小说的第二十章“抽象的”叙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与整篇小说“不调和”。总之,这部小说有一些“表现技巧上的小问题”[2]276。
茅盾认为,小说第二十三章以倪焕之个人的“感念”“烘托出”工人运动的情形,而非“正面的直接描写”,这是一个“缺点”,使得“文气松懈”。作为“教育文艺”的前半部分“在全体上发生了头重脚轻的毛病”。第二十二章后半段的“回叙”“妨碍了前半的气势”。在最后一章,“金佩璋突然勇敢起来”稍显“突兀”。在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上,茅盾还提出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间的不协调。茅盾为这些问题找到的理由是连载的写作方式使得叶圣陶不能“慢慢推敲”,并且这种“枝枝节节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的“艺术上”的批评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的“时代性”问题。在“时代性”这个命题中,茅盾解释了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的方向”。他发现这部小说“寂寞”的情绪投射了“‘五四’以后弥漫在知识界中间的彷徨苦闷”,倪焕之这样“受了时代潮流的激荡而始从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的”,茅盾以为,由于倪焕之是“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能很坚实地成为推进时代的社会活力的一点滴”,本身的“幻灭”“迷惘”,使其看不到“群众”,即便是“了解革命意义”的王乐山,也没有正面“推进时代的工作”。尽管茅盾看到这些问题,但在这篇评论文章最后,他还是从文学与人情的角度肯定了这部小说,认为“在目前许多作者还是仅仅根据了一点耳食的社会科学常识或是辩证法,便自负不凡地写他们的所谓富有革命情绪的‘即兴小说’的时候,像《倪焕之》那样‘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点,该也是值得赞美的吧”。因为小说中“没有一个叫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因为“正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最终茅盾以为,像《倪焕之》这样“有目的有计划的小说”之于文坛,“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有意义的事”,甚至可以将这部小说之于“五卅”,可以看作与“五四”时期“代表时代的作品”有同等的意义。②在夏丏尊和茅盾之后对《倪焕之》这部小说进行的评价,大多是围绕着夏丏尊和茅盾(尤其是茅盾)的观点进行再阐释(有的则是质疑,如钱杏邨的评论),这两则与《倪焕之》小说“捆绑销售”的评论③,形成了各个时期各种时代语境下阐释的基点与重要的佐证。作为解释基础的这两则评论,对小说的叙述层次进行了区隔和划分,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关键词,“教育”和“革命”。无疑,这两个关键词正是这部总共三十章小说的核心,小说中“教育”一词共计出现198处,“革命”一词出现50处,从词语的频次上看,这二者的确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走向。对于这两个关键词构成的前后两个部分,大多评论文章持支持的态度,并且也大都认为倪焕之“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转向了“革命”④。本文首先探讨的问题就是由“教育”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划分”出茅盾所谓的小说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一 教育与革命:不协调中的协调
茅盾对这部小说前后两部分不协调、不均衡的观点,成就了两种主要的立论的表达模式,那就是“教育小说”“革命小说”。当然也有人将其归纳为“教育—革命小说”,这种观点在尝试弥合前后两部分不协调感的解释也远未达到这部小说真正的追求。虽然这两种阐释都是基于小说的两个核心关键词,但在“教育小说”和“革命小说”的阐释过程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解读目的。“教育小说”的阐释者主要站在“教育学”的角度,突出小说涵盖的教育知识、教育意义和教育发展史,这样既突出了特点,进入了“部分历史”,又跳出了时代语境的某些“泥潭”,获得了一定的收获。“革命小说”阐释者的历史语境则更为复杂,小说被认为是“革命小说”主要是为了说明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对于小说中片段的择取与阐释,成为了重构历史的方式,“它形象地启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倪焕之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主观上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想沿着倪焕之的道路走下去,其结局,也只能是悲观绝望,碰壁而死”[3]。本文同样认为,过去研究中“革命小说”的接受视野失去“拓新”的意义,在建立在建国后三十多年的那类“革命”语境中,贴上“革命”标签进行读解,今天看来,已然毫无再深究的价值和意义。[4]这里的“革命小说”的标签由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原因,与小说中提及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包括《倪焕之》写作之年兴起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诸多“革命”的话语立场显然是不同质的,还其本源,或对这个“革命”标签有崭新的发现。
站在“教育”角度的有所发现和站在“革命”角度的有所批判都离不开语境的阐释对这部小说的分析过程产生的影响,这两个角度,也反映出在研究过程中文本的“不协调”带来的解读契机。有台湾学者这样批评道,“整部《倪焕之》的后三分之一,乃是草率的急就章,与前三分之二相对照,显然头重脚轻”⑤。诚然,在描绘前半部分倪焕之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时候,作者以诗意的笔触,柔缓的叙事节奏描绘了他的生活,第二十章以后,叙述的节奏“仿佛”加快了。事实上这里包含着一个时间的跨度,这部小说文本描写的时间范围大约是1916年到1927年,算上借主人公回忆进行描写的辛亥革命前后,前二十章叙述的时间范围可以看成1909年到1919年这十年间倪焕之的生活状况。第二十一章表述了1920年前后倪焕之重逢王乐山,第二十二章直接跳到了1925年“五卅”运动。前二十章叙述了将近十年的状况,之后的九章内容描写了1925年到1927年倪焕之遭遇,按篇幅和描绘的时间跨度来看,事实上后半部分本用近十章写两年间的事情会更深入一些,但“头重脚轻”这种直观感受的产生,包括评价者认为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人物塑造更为得力的普遍认识,形成一种颇有趣味的观感上的矛盾。事实上这个矛盾的解答在于如何看待“教育”与“革命”这两大主题在小说中的变奏效果以及叶圣陶围绕的并非“经历”而是“心灵”的叙事风格。
从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端倪,并非是倪焕之自觉的人生追求,辛亥革命的“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带来的“新鲜强烈的力量”催生出倪焕之的“要做一点儿事”的冲动,“一面旗子”“一颗炸弹”“一支枪”的暴力冲动与光复后“随即失望了”。“感到了人生的悲哀”使倪焕之过早地感受到了“革命”并未带来理想的生活,甚至使他有了“跳下池塘去死的强烈欲望”。从“反感”开始,倪焕之当了小学教员,起初他因种种不满感到他从事的这份“教育”的工作是“堕落的”,从教三年后因一位同事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有了“严饰”“地狱”而成“天堂”的转变,认准了“教育”这项事业是实践理想的途径。[5]15-25通过开头这部分的描述,可以发现“革命”带来了倪焕之心态从高潮到低谷的一系列变化,辛亥革命以后,他的失落感甚至绝望感,恰好是被“教育”曲折地拯救了。所以小说所谓前半部分的教育主题,也缀连着一个密不可分的命题,那就是“革命”。
这里描绘的场景和叶圣陶个人的经验是匹配的,他和倪焕之一样,辛亥年中学毕业没钱升学,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6]304-305,叶圣陶还谈到过一个“朋友”曾“萌生”跳入池塘的“怅惘”,与倪焕之相似的境遇。某些学者甚至将其描述为叶圣陶个人萌生的自沉的冲动,这里面体会到了这样的情感,也罔顾了叶氏的自述。⑥叶圣陶这种失落的感情完全是个人经历的积淀。辛亥革命后,叶圣陶欢欣鼓舞,参加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抱有朴素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不妨碍国家存废的基础上主张纯粹社会主义”[7]。在日记中,他满怀激情地记载了江亢虎的“社会主义”的演说,“无贫富之阶级”“提倡社会教育”“提倡工商实业”“于是绝对的平等,绝对的自由方达”[8]。吸引叶圣陶的未必是某个宏大的“主义”,而是里面确凿的观点,其中的如“女性问题”“教育问题”的思考也一直伴随着叶圣陶,是其精神资源的起点之一。二次革命的失败,北洋政府的专制,包括江亢虎个人的命运变迁,影响了叶圣陶,让他发现了“世界的虚伪”“高悬五色之徽”,不过是“逢场作戏”[9]。从带有民族主义的“起我同胞扬轩辕,保护我自由,张我大汉魂”到“此是人间罪恶府,悲风惨日怪魔横”⑦的绝望,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前后叶圣陶的心路变迁,正是基于此点,才有了倪焕之的“在辛亥那年,曾做过美满的梦,以为增进大众福利的政治立刻就实现了。谁知道开了个新局面,只把清朝皇帝的权威分给了一般武人”[5]34。
这里并非要说明倪焕之乃是叶氏本人的自画像,而是通过叶圣陶个人的体验,再体会倪焕之这个角色塑造过程中作家构造的“镜像”之中内嵌的意义,“革命”未曾远离过倪焕之,只不过这一层“革命”的概念,包含了巨大的时间跨度和社会事件,而非某一特定观念就可解释,历经辛亥、五四、五卅、国民革命等事件的倪焕之对“革命”的理解,尤其值得重视。在小说中,“革命”是被拉长了刻度的,可谓贯穿始终,而与这种“革命”的叙述相辅相成的,就是“教育”。
叶氏借蒋冰如与倪焕之的对话,道出倪焕之最初的教育观念,“在各个人懂得了怎样做个正当的人以后”,世界会变得更具有“谅解与同情”“养成正当的人,除了教育还有什么事业能够担当?一切的希望在教育。所以他不管别的,只愿对教育尽力。”蒋冰如则从反面谈到:“教育兴了也有好多年,结果民国里会演出帝制的丑戏;这就可知以前的教育完全没有效力。办教育的若不赶快觉悟,朝新的道路走去,谁说得定不会再有第二回第三回的帝制把戏呢![5]34-75从这来看,“革命”的后续工作,或者说“革命”之后的工作,从倪焕之们的角度看须得要“教育”来完成。可见,上半部分尽管有很大篇幅叙述倪焕之的“教育理想”,但这个教育理想的出发点是“革命”。
二 革命的教育者:革命观念的发展与成型
在军阀混战包括让倪焕之有更真切感受的江浙战争的背景之下,通过王乐山的引导,倪焕之又更新了自己的教育观,“教育该有更深的根柢吧?单单培养学生处理事物应付情势的一种能力,未必便是根柢”。叶氏参加国民党的经验与文本中倪焕之的经验又产生契合,倪焕之找到了“组织”,重温了“革命”并生发出崭新的意义,分辨了“今后的革命与辛亥那一回名目虽同,而意义互异,从前是忽略了根本意义的”“如今已经捉住了那根本”“根柢到底是什么呢?同时他就发见(笔者注:应为“发现”)了教育的更深的根柢: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目前的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教育者如果不知革命,一切努力全是徒劳;而革命者不顾教育,也将空洞地少所凭借。十年以来,自己是以教育者自许的;要求得到一点实在的成绩,从今起做个革命的教育者吧。”倪焕之发现,教育的前面必须加以限定,即要做“革命的教育者”。[5]101-102
事实上,在文本中提到的1924年至1925年春,倪焕之思考了“革命的教育”,并计划奔赴上海“工作”之际,叶圣陶本人也对“革命”这一命题进行了思考。
“革命”这个词含着极广泛的意义。一切人物和行为,用“革命”这个词来形容这一部分,又用“反革命”这个词儿来形容另一部分,那就包括净了。拿治国故来说,墨守某先生的一家言,是反革命;打破家法,唯求研究对象的真际,是革命。拿行为习惯来说,拘泥礼俗,惴惴地唯恐逾越,是反革命;唯正确是求,唯意识之伸,是革命。拿社会常识来说,相信某阶级可以压制某阶级,宰割某阶级,而某阶级应该受某阶级的压制和宰割,是反革命;不相信上述的那些情形是正当的,要是当前有那些情形,就竭力反抗,竭力扑灭,是革命……反革命是以当前的状况为完美无缺的,革命是认为这些是尚待加以完善的;反革命像静定不波的湖泊,革命像包罗万象的海洋;反革命的前途像一幅白布,或者是一幅黑布,革命的前途却是真和善的国土,美的花园。⑧
这段论述说明这一时期叶圣陶对“革命”的理解,是超历史、超政治、超文学的。这一方面有“反者道之动”的古老哲思,另一方面包含着叶氏依据个人经验的清晰判断,“革命”作为精神的“根柢”断然是极端必要的,但外化为一种自我解释的名目,则是有问题的。在历史文化方面,求真的态度展现革命;在行为方面,贯彻自由意志是革命;在社会政治方面,反对专制和极权是革命。在思想上,批判精神则意味着革命。在这个解释的基础上,反观倪焕之要做“革命的教育者”,并非是“知识分子遭遇政治”的想象形态,而是保有上述的思想情态之后的自主选择。倪焕之当然不是叶圣陶,但倪焕之亦存在获得这种思想状态的可能,其身上浸润了叶圣陶的所思所想,并且这篇关于“革命文学”的探讨,比1927年蔚为壮观的“革命文学”论争早了许多。
这种可能性出现在夏丏尊批评的与整篇小说不调和的第二十章,在“抽象地”叙述“‘五四’后思想界的大势”那里。叶圣陶写到,青年们被“五四”惊醒,“知道自己锢弊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从这般自我了解开始叙述,叶氏将自己与倪焕之的“五四”进行对接,一方面这是叶圣陶自我心绪的表达,另一方面,也为解释倪焕之的人生选择与心理状况,奠定了基础。“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新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5]186-190在这里,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承接了“辛亥”以来的不安与探索的心理状态,演化着二十年代以后直至“国民革命”时期的精神脉络。在这个篇章中,叶圣陶对“五四”精神涤荡的文化、政治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的描绘,几乎可以看成是《“革命文学”》观点的精神源头。
小说在洋洋洒洒的描绘了令人激动的“五四”以后,笔锋一转,让倪焕之遭遇王乐山。按照推断和历史的一般情况的演绎,倪焕之在经历“五四”以后出现了一个人生的低潮。在小说中,叶氏将其描绘为倪焕之过了一段“隐士一般的生活”,王乐山的建议让倪焕之考虑到上海去“有组织的干”[5]198。到上海去,也就是告别乡镇,到“革命”的中心去。对于倪焕之而言,他到底是去干什么的?借王乐山的回信,可以看到,倪焕之抱着的,还是“教育”的理想。王乐山回信“所述革命与教育的关系,也颇有理由。”倪焕之琢磨,“用到‘也’字,就同上峰的批语用‘尚’字相仿,有未见十分完善的意思。”倪焕之并未介意这语言背后的不屑,到了上海,按照王乐山的安排“不失教育者的本分”,去了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在任教期,“到‘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已习惯他的新生活”[5]207-208,可是“五卅”又带给他新的认知和经验。
在这份经验上,叶圣陶和倪焕之又开始了某种暗合。发表于《文学周报》179期(另刊《小说月报》16卷7期)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和小说的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以同样的情感和相似的基调,描绘了“五卅”惨案带来的惊心动魄以及写出叶圣陶的思考。删繁就简,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文本中,同样出现了一个形象和这个形象说的一句话,“中国人不会齐心啊!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和这句话一同在响起的,还有倪焕之与“他们”那“咱们是一伙儿”的呼吁。[5]214在《倪焕之》文本中,作者藉此让倪焕之自省,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己进行批评,对“青布大褂”的劳动者加之以崇拜,在《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这种感情表述为“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按照学界的某些观点,现代文学自“五四”以后,第一次在这一方面发现知识者与劳动者的距离:知识者在革命中看到了拥有巨大的行动力量的劳动者群众。同一瞬间,知识者人物有了“自我渺小感”。[10]这一发现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被放大、凸显、利用,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思潮。
这两处文本的契合,事实上就是叶圣陶人生经验与小说创作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小说写作的背后,不仅有大历史驱动的因素,更为具体和真切的,是这一代、这一类、这一个知识分子具体的生活与思考,这也使小说塑造的“象”背后有了一个真切的对应主体。
国民革命的乡村图景,倪焕之在国民革命期间,接收学校、思忖着如何改良教育、提出乡村师范的计划,充满了激情与干劲,然而“四·一二”之后的现实又使他陷入了失望与迷惘。“王乐山”被杀,密斯殷被凌辱,作为对历史的描述与回应,作者设计了这两处情节。这两个角色引起了很多人对于其现实指涉的追问,柳亚子1929年9月27日、10月2日、10月6日、10月8日致信姜长林,询问“王乐山”是否为侯绍裘,密斯殷是谁,在1931年的《左袒集》中,柳亚子写道,“刎颈侯嬴漫怨哀,已从稗史证丰裁”,稗史指的就是《倪焕之》,另诗写道:“光轮未转骨先糜,一语深悲倪焕之。”[11]415-416可见这部小说对于柳亚子而言,其中的现实指涉带来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远比其在艺术方面获取的成就更重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叶圣陶的这部小说熔铸的个人经验,在30年代,已经感染了读者。
三 知识分子与革命
从一定意义上看,《倪焕之》的阐释史背后有个深刻的历史背景,即20世纪20年代末期知识界精神状况的转变。这一转变自20年代中期就已然出现,包括创造社在内的诸多作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向社会和革命”[12]。背后的动机不一而足,在国民革命期间倪焕之的精神历程,夹杂着兴奋与软弱、希望与绝望。最终,叶圣陶让倪焕之死于伤寒(“肠窒扶斯”)。这种因为苍蝇、蟑螂等带病菌传播的疾病,结束了倪焕之的个人理想探索之路。
夏丏尊提到的“流于空泛的疏说”和茅盾的“文气松懈”,恰好是倪焕之精神状况和现实际遇的写照,“五四”“五卅”,包括大革命失败的这些章节出现的文本裂缝,恰恰是我们进入叶圣陶精神世界的门径。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其人生历程与社会变革之际的诸多大事件有着纷繁的交叠,叶圣陶采用的回溯式的写作方式,先陈列大事件,再探究心灵史,更侧重的是心灵探索。在历史事件面前,知识分子既是启蒙者,也是被启蒙者。《倪焕之》几乎是作者对自己之前的小说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妇女与儿童、社会的边缘与底层人、乡村的教员、动荡之际的芸芸众生,在这部小说中,都得以集中的展示。在“革命”这个词的召唤下,各色人等登上舞台,逃避“革命”的蒋冰如,拥抱革命的“王乐山”,利用革命的“蒋老虎”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充满希望又收获绝望的倪焕之。有研究指出:这部小说的结构应该是倪焕之的心理活动,而不是他的外部人生历程。[13]“教育”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汇,一方面是倪焕之人生历程中不断追求、不断认知的实践理想的方式,一方面又是叶圣陶探索心灵的一种方式。茅盾对这部小说“时代性”特征的赞美,一定程度上偏离这部小说探索的方向。茅盾那种对于时代新人在不可逆转、不断进步的历史中承担宏大、庄严、广阔的历史责任,在倪焕之中,只是叙事结构中的焊点,而非主干。在这部小说中,主要展示的是“辛亥革命”后,倪焕之激动而又幻灭了,“五四来临”倪焕之激动而又幻灭了,“五卅”事件和“四·一二清党”以后,倪焕之激动而又幻灭了。在这一基础上,叶圣陶描绘的是不断寻找、不断失去,在历史变革面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却又在现实的面前被打击得粉碎的形象。倪焕之不断转换着生活的场景和生活的主题,职业的理想、爱情的理想、革命的理想,不断地破灭,“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一个个希望抓到手里,一个个失掉了;再活三十年,还是一个样!”在“命运”“循环”之中,倪焕之彻底失望。[5]270德国汉学家顾彬将其解释为倪焕之“在面对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转换中所承受的不能解脱的彷徨”。“现代性”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古国的内在基础——民族文化的整体感”[14],他的解释将这部小说的认知推向了“现代人状态”这个研究的视阈中。[4]亦有学人将叶氏的小说命名为“生存状态小说”[15],这也是在现代性的视阈中的一种发现。从个人经验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不仅呈现出了“现代人状态”,更凸显了叶圣陶个人经验与小说人物互动,开拓另一种视角。上述分析叶圣陶个人经验与小说文本中人物的精神契合,旨在点出“个人精神史”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只有分析叶氏个人的“五四经验”“五卅体验”“革命”认知,才能更为真切地理解塑造这一形象的动机和小说人物的性格发展。本文则倾向于这部小说乃是革命小说,只是这一“革命”,更偏重于个体生存角度的自我更新。
1927年末至1928年,叶圣陶逐步熟悉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送走了一批友人,把置身于危险中的茅盾“隐藏”在身边又送去了日本,期间发表了他的《蚀》三部曲,为钱杏邨、冯雪峰、夏衍等人提前预支稿费,在这个“教人徘徊的时代”创作《倪焕之》,1928年9月去往钱塘江观潮(这一细节也出现在了《倪焕之》中),在为茅盾撰写《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的广告时,叶圣陶写到,“革命的浪潮,打动古老中国的每一颗心”[11]404。叶圣陶自己也有着一颗被革命浪潮拍打着的心,它催促着温柔敦厚的他创作了《倪焕之》,从个人体验出发,以主观化、个人化的表达对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某些变化进行了历史的想象性重构。在普遍怀疑文学、走向社会革命的历史情形下,叶氏的《“革命文学”》早就表达了自己的“革命观”,站在个人的角度,亦可具有“革命”的精神,做出“革命”的行为。1927年以后,中共党组织将革命失败归咎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⑨知识青年要么走出“革命”,要么改造自己接近崭新的“革命”定义,在“革命”概念的涤荡中更新着本身的认识和判断。叶圣陶借倪焕之将“革命”理想转移到“组织”上去,理想破灭了,以说明并强调其“革命”的观念“去组织化”的思考。“组织”始终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形成了“宽泛意义上的专制”。[9]叶圣陶对“组织”的困惑,断然不是否定革命,他对“革命”本身有超高的热情,他主张的革命,不仅是通常意义中暴力的形式与政治的主张,而是一系列关于“个人”与“革命”关系的新定义、新追求,正是个人化的对“革命”的限定,使他即便在“革命文学论争”的高潮期,也未曾改变立场。1931年,叶圣陶接受夏丏尊邀请,主编《中学生》杂志,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不得不说,他始终在坚持以某种方式进行着他所谓的“革命”。在叶圣陶那里,“革命”始终不是“组织”垄断的话语,不是自我阐释的名目,对于他而言,学术上求真,坚持自由意志,反对专制和极权,就是革命。这一思想,秉承了“五四”以来的“立人”传统,是将“革命”温和化、改良化的一种努力。
诚然,作为时代的关键词,“革命”概念在不同个体的内部发展逻辑和与个人与外部社会发生的互动关系产生的“革命”的定义是不同的,在考察“革命”概念时,除了要考察它作为组织的概念、群体性的概念的含义,还应分辨这个概念的主体性特征。梁启超不仅对“革命”的广义和狭义做出了区分,还在《释革》一文中指出革命的内涵在于“迁于善”的“以仁易暴”而非“以暴易暴”,从道德上明确了革命“善”的追求⑩。鲁迅在“立人”的角度认为“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也是革命”[16]118-119。与此一脉相承,叶圣陶的“革命观”也是站在广义角度,强调完善“主体”的意义。“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关键词,不仅是政治文化的重要标识,更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一种重要的“文化”,这一文化,是在个人“具体的人生道路上极其偶然地生成和发展起来的”[17]。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文学从业者那里的言说范围,不仅是对概念史的梳理,也是对知识分子心理结构的探索。
注释:
① 夏丏尊的《关于〈倪焕之〉》,节录茅盾的《读〈倪焕之〉》,与叶圣陶的《作者自记》,均附于开明书店十三次出版的《倪焕之》前后。
② 茅盾的《读〈倪焕之〉》,原载于《文学周报》1929年第7期,引自《叶圣陶集·3》,第277-28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 1949年至1978年出版的单行本,除内容删改修订外,附录三篇均删去。
④ 唐弢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转引自《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叶圣陶研究资料》,76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⑤ 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年版,转引自《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叶圣陶研究资料》,7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⑥ 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中明确说到,“这样伤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没有”。
⑦ 叶圣陶的《大汉天声》,1911年11月18日;《送颉刚北行》,载《叶圣陶集·8》,第6页、第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⑧ 叶圣陶的《“革命文学”》,载《文学》杂志第129期,1924年7月5日作,引自《叶圣陶集·9》,第98-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⑨ 参看《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选自《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⑩ 参看张品兴、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59-76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叶圣陶.倪焕之:作者自记[M]//叶圣陶集:3.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2]夏丏尊.关于《倪焕之》[M]//叶圣陶集:3.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3]金梅.“五四”前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真实写照:读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J].文史哲,1979(3).
[4]陈思广.《倪焕之》接受的四个视野[J].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5]叶圣陶.倪焕之[M]//叶圣陶集:3.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6]叶圣陶.过去随谈[M]//叶圣陶集:5.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7]周海乐.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J].江西社会科学,1989(1).
[8]叶圣陶.辛亥革命前后日记摘抄:十五号[J].新文学史料,1983(2).
[9]邓程.叶圣陶的早期“革命”叙事[N].文艺报,2012-02-15.
[10]赵园.知识者“对人民的态度的历史”:由一个特殊方面看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2).
[11]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2]程凯.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J].文史哲,2007(3).
[13]冯鸽.现代长篇小说之知识分子心灵叙事:重读《倪焕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4]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15]阎浩岗.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J].文学评论,2003(4).
[16]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王富仁.鲁迅与革命: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读后:上[J].鲁迅研究月刊,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