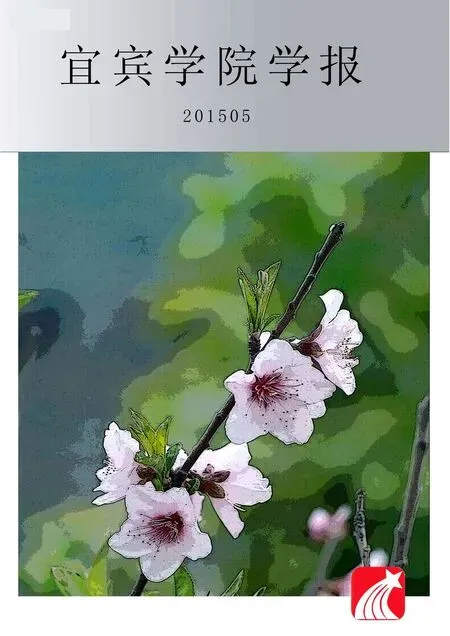唐君毅意义视域中的“我心”与“他心”
2015-02-13邵明
邵 明
(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宜宾644007)
唐君毅意义视域中的“我心”与“他心”
邵明
(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宜宾644007)
摘要:根据唐君毅先生的意义理论,意义空间最主要的扩充方式,还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相辉映、互为融摄。因为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形成、完善或不断上升超拔,都与“他心”有着几乎必然的关联:“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同情共感使得意义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不至于陷入任性的幻觉;正是双方的相互肯定共同获得超越的可能,由此而成就了一个道德人格主体;并在永恒持续的道德实践中,意义空间得以开显和澄明。唐君毅所揭示出的儒家思想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这种内在关联,成就了具有伦理特征及其价值导向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中的恒久生命力。
关键词:唐君毅;新儒学;意义;我心;他心;
唐君毅先生(1909-1978)是现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构提示我们:儒学的生命力并不决定于偶然的政治、经济等历史情境因素,而是深植于它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联之中。正是人类生存方式本身的诉求,使人与人(或“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同情共感和精神互映成为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最为重要的规范原则。因此,人或社会的伦理关系自然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核心主题,也是具有伦理特征及其价值导向的儒家思想能够不断绽放生命之花的源泉所在。唐君毅通过对意义世界的阐述,揭示出儒家思想与人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心灵在意义空间中最根本的贯通方式,就是“我心”与“他心”之间的交相辉映、互为融摄,以获得意境的超拔提升和无限生命的现实化体现,成就出自我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经验历程。
一“我心”与“他心”:意义的澄明
唐先生认为,“人的宇宙是一群精神实在,互相通过其身体动作,而照见彼此之精神的‘精神之交光相网’”。[1]118这种由“我心”和“他心”共同形成的意义世界又是在人们“当下一念”的经验历程中逐渐生成和开拓的。[2]这尽管不错,可是这样的说法还不十分准确,因为这有可能被理解为仅仅依靠一个人自己的个别行为而不必依赖他人即可完成。但是现实的经验生活表明:一方面,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最初形成是在“他心”的帮助下开始的,尽管这些“帮助”仍然离不开自身的心灵作用,即“他心”这种外在“助缘”必须通过自己的心灵作用才能够实际地导致意义生成的效果;另一方面,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完善或不断充实丰富,也与“他心”有着几乎必然的关系。这两点意味着“我心”与“他心”之间的交织互动对人的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生成和开拓,都有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详细讨论。
一方面,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最初形成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开始的。所谓他人的帮助,就是指当一个人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其父母家人,以及亲属、朋友或邻人等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对他(她)的心灵能力和意义空间的形成,有着实质性的促动作用。每个人都是在成人的教导下开始“咿呀”学语,开始学会走路、辨认物体和事情,也就是开始了一个人所谓“懂事”的过程。在这一成长过程中,长期的重复模仿和练习是不可缺少的。这看似普通生物都具有的本能习性,却并非一个完全自然化的生物生长过程,而是伴随着心灵的逐渐成熟和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尽管人在婴幼儿时期,心灵的自觉反思的意识可能是很微弱、很隐蔽的,但正是这微弱的心灵之光会随着不断的重复模仿和练习,而逐渐澄明起来,也就是逐渐形成自己的、可以无限扩展的意义空间。然后,从开始上学,直到其成人为止,一个人都处于家庭的熏陶、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的经验学习过程之中。在这一阶段,人的意义赋予能力才逐渐成熟,其意义空间才得以生成,即一个人的人格及其他(她)所面对的经验世界成形的过程(成己成物)。
在独立人格完全形成之前,也就是自己成为独立的意义赋予者之前,一个人都是处于他人的帮助之下,而始终在学习着能够独立地发挥赋予意义的能力。这些“帮助”,例如在父母家人的引导下学会走路说话、辨认事物,还有学校的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等,都内涵着该人和该家庭所处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或观念形态等因素。因此,由这些因素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传统(即“他心”的社会历史集合),对一个人独立人格的生成和完善,对一个人意义赋予能力的强弱而言,就是十分关键的了。
另一方面,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的完善或不断上升超拔,是在与“他心”的交相辉映、互为融摄下得以实现的。这里说“他心”而不说“他人”,是因为这不能指单单作为生物的他者,而是一个与己同样心灵生命存在,或者同样的一个意义赋予者。如果一个人与一个他者相遇,仅仅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生物,甚至仅作为一个无生命的存在者(物),那么就不会从中获得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对精神生命超拔的助益,而只是与一般的对象所起到的作用类似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与一个“他心”相遇,即与自己一样的具有心灵生命的存在,或与自己一样的意义赋予者,那么,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我们可以从唐君毅这段话中体悟出来:
此心灵即唯有直接遭遇另一同具此无限性之心灵,乃能得遇其真正之限制,而使其自己之心灵之扩大超升,成为真实可能。此另一无限性之心灵,初即他人之心灵。此他人之心灵非我之所能尽知,亦非我所能用手段全加以控制者。于此,人即真感其自我之心灵之为非我之心灵所限制,而人能面对此非我心灵,而接受其限制,而更求以我之无限性的心灵,与人之具无限性的心灵相贯通,人即可真得一必然的超升扩大其心灵与生活境界之道路矣。
人之知此非我之他人之我之心灵之为无限,乃在其发现他人有其独立意志,非我之意志所能加以限制之时。当我发现他人之有其独立之意志,非我之所能加以限制之时,即见其不受我之意志之限制,超越此限制,而为无限。[3]360
这段话表明,一方面,“他心”的存在及其与“我心”之间的相互确认,将使得人的意境可以无限高远而又不至于陷于完全的主观妄想之中;另一方面,道德的必要性在于,“我心”与“他心”之间恰当的伦理关系是人的精神境界得以不断超升的必要途径。要理解这两点,就需要对唐君毅上面的阐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我心”与“他心”之间的限制与超越
在唐君毅看来,“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相互限制或相互超越这两种情形。如果人与人不能处于恰当的伦理关系之中,也就不能相互肯定、承认或欣赏,而只有相互否定、怀疑或贬低,那么,“他心”就会对“我心”形成一种限制、压力或敌意,以致于最终无法和谐相处,或相互残害,或相互逃离。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无法形成。因此,“我心”与“他心”就需要能够保持一种积极的伦理关系以超越相互的限制,即能够相互肯定、承认或欣赏,而不是相互否定、怀疑或贬低。这种积极的伦理关系即是人或社会的道德性,是社会生活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
根据唐君毅的理论,对“我心”与“他心”之间相互限制或超越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论点:
首先,无限的意义赋予能力不同于可随意地赋予意义。自我的心灵具有无限的意义赋予能力,这是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内在反思都能理解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地进行意义的赋予呢?或者说,每一个“我心”是否都可以只顾及自己的意义空间而不必在意“他心”的肯定呢?毕竟,人们会疑惑:这不是从前面的说法中可以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吗?确实,就理论上而言,人们的意义赋予能力或心灵的贯通确实是不会被限制住的。可是,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意义的赋予或心灵的贯通却难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来自“他心”以及由“他心”所组成的社会。这一限制包括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的限制。例如,语言的意义根源于人们之间的约定,是在长期的经验传统中逐渐形成的;数学符号和逻辑规则也同样;还有各种意义赋予的方式(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此外,各种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方式也都形成了一定之规,等等。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与说“心灵具有无限的意义赋予能力”相互矛盾呢?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所谓“心灵具有无限的意义赋予能力”,就是指心灵是在对这些现实中的各种限制的主动掌握和主动控制之中,发挥其意义赋予能力的,而不是局限于这些限制而没有任何自由。所谓“无限的”,就是指具有破除限制能力的意思,即不可被限制住的。正是具有对这些限制的破除能力,体现了心灵或意志的自由。
其次,“他心”与普通的现实限制是有本质不同的。因为,他人心灵同样也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无限的意义赋予者,也是一个与自己一样的具有生命的心灵存在。因此,与“他心”的遭遇就是两个意义空间的相遇和碰撞,两个无限者的“对视”。对这样的“限制”,就不能再以通常的方式加以破除,不能随意地去“掌握”或“控制”。因为,那等于承认自己的心灵也可以同样被别的心灵所破除,所“掌握”或“控制”。这也是对他人心灵的贬低和蔑视,最后必将返回到自身之上,使自己成为他人心灵所贬低和蔑视的对象。因而,对他人的心灵就要采取全然不同的方式,即就像对待自己一样,给以肯定的承认。能够正面他人、面对他人的心灵,实际上也是在正面看待自己。这是自我人格的成熟标志之一,即能够从“他心”之中,反射地见到自己的心灵主体,并从而构成自我判断、自我评估、自我认识的主要方式之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他心”的肯定承认和欣赏就是恰当地超越“他心”的方式,并且,可以含摄他人的意义空间为自己意义空间的有益部分,从而使自己的意义空间获得实质性的超拔、飞跃和扬升。同样,能否恰当地对待他人的心灵,能否对他人的心灵有所助益,也是自我人格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双方的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都是在相互的承认、肯定或鼓励赞扬的情况下,得以不断提升、增强和充实扩大的,也是在双方的相互含摄之下,获得极大地超拔的。如果仅仅依靠自我的力量,而没有他人心灵的帮助,那么,自我心灵是否能够成熟,自己的意义赋予能力是否能够得到恰当地培育,都是值得怀疑的。很可能的情况是,自我的意义空间甚至都无法得以生发出来,就像人们所了解的没有受到文明开化的“野蛮人”那样。因此,他人的心灵以及由他人所组成的社会,是自我心灵或人格成熟的必要支持,也是自己的意义赋予能力和意义空间生成和不断完善的必要支持。“我心”与“他心”之间这种相互的“构成性”关系,即是人类社会本有的伦理关系。这样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道德的、正当的社会,或一个“好的”社会,反之则是一个“不好的”社会。
唐君毅从“我心”与“他心”的关系这一理念出发,得出结论说,在与他人心灵相遇的时候,如果人们不是正面地肯定他心,与他心成为相互有益的帮助,交相辉映、相互融摄,而是欲图去控制他心,使之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这种心理,就是“权力欲”。[3]361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权利欲,这也是人类社会中为什么始终不能摆脱权力之争的原因。而这也是人类社会之中对于心灵生命的自由而言最为不道德的一个因素。例如,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一旦只打算着个人的私利,就难免成为社会的敌人,因为他们出于对权力或名誉那种巨大、不可遏制的欲望,尤其是力图控制或支配他人的命运,可以随意赐予或剥夺他人的权利、名誉或尊严,可以造成他人一时的飞黄腾达或一生的痛苦。把尽可能多的“他心”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就是这种人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可以说,这样的“精英”是一个现实社会最危险的根源,也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无数灾难和痛苦的罪魁祸首,导致了对无数人类文化成果的摧残甚至毁灭。对此,我们应该时时保持警醒。
三同情共感与意义的客观性
通过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互承认肯定、鼓励或赞扬,从而使双方相互助益,这将导致双方的意义空间极大地提升。从这一点人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如果是“我心”与“他心”之间的“同情共感而互助”,那么,无论是多么平常或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会因为使相互之间的意义空间得到极大扩展,使相互的境界得到极大提升,而也变得十分重要,其价值之珍贵甚至于无法估量。
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心灵之间的“同情共感而互助”还可以使一种“客观的”视角得以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一个社会得以获得诸多共识的背景性世界观。人们一般所谓“客观的”,似乎是从单纯的外部而言的视角,而不是人的心灵的主观角度看待事物。但是,这样的“客观的”视角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幻想而已。[4]12真正的所谓“客观的”视角,首先也是人的视角之一,是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之一;其次它应该是指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确认,即各个心灵所感受到的共同的意义。尤其是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或确认,更是需要人们的感官感觉相互之间的共同确认、肯定、鼓励或赞扬。这也叫做“类观”,即人类的共同视角,或者说,获得人类共同确认的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5]147没有这一点,则任何所谓的“客观性”或“实在性”,都是不可理解的。
人之欲证某物之实在,恒取证于他人之心灵之所共知。此即见:吾人之谓一物实在,涵有此物可为一切心灵所共知之义。故若一物非一切心灵在某一情形下,所能共知,而只存在于一心灵之所知之中时,吾人亦即可由其不存在于其余心灵中之意义下,说其非客观的实在者。由此而所谓一物为客观实在之意义,即与其为一切心灵的共知之意义,不可相离。[3]369
唐先生所言即,如果只是一个人说有某物,而其他人都不承认,那么,人们似乎也只能说某物还不是真实的存在。当然,也许大部分人都错了。这种可能是有的。因此,人们还不能只根据大部分人都不承认其存在性而下判断说某物的非实在性,而只能对此存疑,以待更多的证据。但是,更多的证据也是要在绝大部分人都承认之后,才能构成有效证据。否则,如果大部分人对这些证据不能承认的话,那么,人们还是只能存疑,而不能遽下判断。当然,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人们的确只能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共同确认,而不能仅仅凭依某一个人的断言,来理解或判断各种事物,尤其是关于现实事物的存在问题。因此,如果说某一物的存在已经获得了人们的认同而知道其具有了客观实在性,那么,这也意味着它获得了大部分人的心灵的认可,不在我的心灵之内,也一定在其他人的心灵之内。或者,即使该事物外在于我,也不会外在于其他人。而这一点是人们首先必须相互承认对方的心灵生命的实在性才可以得到的。唐君毅对此补充道:
有一人与我各为一道德心灵主体,一道德人格,而互相涵摄所形成之人格世界者,则是谓有此人之最庸常之同情互助之事,即见人与我之心灵之一方互肯定为外在,而此所互肯定为外在者,又皆各分别内在于此人与我之相互对其自我之肯定之内。此一肯定,亦同时为人之各自超越其自己之自我之一超越的肯定。在此超越的肯定中,人各为一道德的主体。此主体可由其无定限的想象、理性之活动,自知其为具此无定限的意义之存在,而又各超越其自我之自为、自助之事之外,以作助人之事者。[3]371
可见,“我心”与“他心”之间的相互肯定就绝不只是一件小事,而是与每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意义空间的无限开拓和意义赋予能力的无限提升,都有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并不因其小就稍减其意义。例如,对他人观念或行为的肯定和赞同,甚至与他人见面时主动表示以简单而热情的打招呼、握手等。这样的相互肯定不是对对方的限制或操控,而是把对方视为外在于自己、又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心灵主体;进而再根据这样的肯定,使得双方都获得一种对对方的超越;并在这一超越中,自己成就为一个绝对的道德主体,具有无限的意义赋予能力和真实的生命存在。这也是“我心”与“他心”都是意义主体的必然结果。
由于意义空间通过心灵之间相互肯定的方式而获得飞跃式的提升,因此对他人的帮助或对一个社会的贡献,就不能仅以某些功利的价值去衡量,也不能单单以人们日常经验中的某种具体的幸福方式为目的,而应该以对“他心”的肯定、承认或欣赏,以帮助他人成就其道德人格为最高目标和理想。否则,如果仅仅在某一些具体的功利方面给予了人以帮助,却不去有意识地在道德人格上或在意义赋予能力上给人以帮助的话,甚至还有损于其道德人格和意义赋予能力,那么,这种帮助的价值就要降低许多,有时甚至可能反而是对人的一种危害了。[3]372
四道德实践的现实历程
道德人格的树立过程,就是一个心灵生命的道德实践,或其自觉反思不断发生的过程,也是其意义空间的开显或澄明的过程。不过,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心灵之间的感通关系并不容易得到十分清晰的认识,反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没有自觉到:这种相互的感通可以有助于自己意义空间的飞跃超升,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人格获得实质性的确立。因此,现实中的人往往是吝于给予他人以肯定、承认或欣赏的。可见,道德人格树立的过程在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是很艰难的,或者说,人的道德实践有其相当的现实阻力或限制。
对道德实践的现实阻力或限制可以有多种。除了那些来自外部自然或社会之中的阻力之外,最难以应对或超越的是来自人自身的障碍。唐君毅说:
此人之道德理想之实践历程中,所首感之问题与艰难情形,在人之从事此实践时之人格之自身。此即人之知善而不能实善善,知恶而不能实恶恶,使其良心之所知之善成真实之善之情形。此乃由于人本有只继续其原来之生活习惯或安于旧习之欲望,而停止于其原来之生活境界,与原有之德与不德之性格,或原有之道德生活境界,而不愿更求超升扩大之故。此皆可称为人之生命存在自身之堕性。[3]374
人虽然是一个具有心灵生命的存在者,可是毕竟人还有其自然生物属性的一面。因此,人就不可能完全摆脱掉其自然生物属性所带来的问题。否则,如果人是一个纯粹的心灵生命存在,那么,就与神、佛、仙或圣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人们也就不必来讨论现在的这些问题。可是,这里的问题似乎还并非如此简单,并不是像很多传统理论那样,仅仅诉诸于消除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本身也不可能)。因为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同样也是人成为意义赋予者的一个必然部分,是意义空间得以生发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人的心灵生命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一自然生物属性就不可能完全从理论上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消极因素。而且,心灵生命的上升力量也正是来自于对人自身的自然生物属性中消极因素的超越。在这些消极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唐君毅这里所说的人自身的惰性,即总是本能地希望自己停留于原有的境况之中,习于常态,不论原有的境况是有德的还是无德的,是善的还是恶的。因为这对人而言,是最为轻松而无需作任何努力的。也就是说,这将是人滑落回其原有的“无明”或本能状态的一种趋向。因此,这种心理并不会使人真的停留于原有的状况,甚至原有的状况也可能是比较善的和有德性的,而是在不经意间,使人前功尽弃,陷溺于“无明”或本能状态,其意义空间也将由此萎缩或贫乏,意境也随之低落,意义赋予能力受到削弱,从而其心灵生命也无力在各个意境之间自由地贯通。
唐先生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与“他心”的相互交织促动。如他说:“然人之形成其道德生活、道德人格,乃在其接于人、接于物之种种事中形成。人之有愧耻、立志、自信之道德心灵,不能只住于其自身之中,而须与其外之人物相接。”[3]376
这种“待人接物”可以扩展而为各种不同的人类文化活动,如理性认知、价值规范、情感审美、宗教体验等。在其中,不同人格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或欣赏(“精神之交光相网”),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心灵的陷溺和惰性,超越其所遇到的各种现实的限制,提升其意义赋予能力,开放以扩大和丰富其意义空间。此时,我们才有可能趋向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而这正是“我心”与“他心”之间的肯定承认或理解欣赏所成就的,“我们最后便归到做一切完成他人之人格之事,即所以完成我之人格;而从完成我之人格之念出发,即必要求完成他人之人格,从事应有的文化政教之活动,以帮助人完成其人格,以实现理想之人格世界。”[1]149
可见,儒家“成己成物”和对人与人之间同情共感的“仁爱”观念的强调,都基于人之作为人的生活本身的诉求。而对于动物或神佛来说似乎是没有这类要求的,也不会被赋予出成就人格的意义,因此也无所谓“道德”或“善”的观念。要而言之,以伦理观念为其特征的儒家思想与人的生存处境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正是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挖掘并阐发出这一意境,应该也正是唐君毅等现当代新儒家其“新”之为“新”的真实含义所在。
〔责任编辑:李青〕
参考文献:
[1]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邵明.论唐君毅的“当下一念”[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托马斯·内格尔.本然的观点[M].贾可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金岳霖.知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inds in Tang Junyi’s Perspective of Meaning
SHAO Ming
(SichuanThinkersResearchCenter,YibinUniversity,Yibin644007,Sichuan,China)
Abstract:The main way to broaden the meaning space, according to Tang Junyi’s theory of meaning, is that minds shine each other and mix together, because there are necessary relationship to the other minds in giving ability and meaning space their establishment, perfection, or continual enhancement: the common feelings and compassions between minds would offer objectivity to meaning instead of delusion;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cendence brings the subjective moral personality; the meaning space would be clear and open in the history of moral practice.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realistic society revealed by Tang Junyi signifies Confucianism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a lasting vitali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Tang Junyi; Neo-Confucianism; meaning; my mind; the other minds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05-0010-07
作者简介:邵明(1965-),男,黑龙江黑河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道德实践的动力机制问题研究”(14XZX019)
收稿日期:2015-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