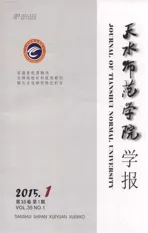关于“花儿”民族文学价值表述的思考
2015-02-12安少龙
安少龙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系,甘肃 合作 747000)
“花儿”既是西北代表性的民歌,也是西北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花儿”研究历来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音乐学与文学的角度。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持续升温,文化遗产学角度的研究也成为一大热点。不同的学科有各自关注的学术焦点,也有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径与话语表述方式,表面上看,不同学科是各说各话,互不关涉。但在话语实践层面,事实上各种学科话语是互相指涉、互有影响的。比如从文学角度对“花儿”进行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及其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的描述,无疑会成为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的重要依据;反过来,“文化遗产工程”对“花儿”从不同角度形成的多重价值判断,由此所塑造的遗产“形象”,及其所采取的种种保护措施,则不仅会影响到对于“花儿”文学价值的再表述,也会使其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对象性质悄然发生某种变化。因此,打破学科壁垒,关注不同话语的互相交集及其互相作用,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遗产工程”的实施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出现了对“花儿”的文学价值评价过高的现象。对“花儿”的文学价值不切实际的表述,会造成其“价值虚高”,进而对“花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的保护产生某种误导,导致其作为大众艺术却脱离大众,脱离自身的艺术土壤,这无论是对“花儿”的文学价值的再认识,还是对“花儿”的“非遗”保护都是有负面影响的。本文拟从“非遗”工程中对“花儿”文学价值表述的个例出发,考察“花儿”价值表述中“价值虚高”现象的成因及其背后不同话语的互相影响因素,进而思考“花儿”的文学研究路径方面的一些缺失。
一、“花儿”的民族文学属性界说
“花儿”是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北的广大地区,在汉、回、藏等多个民族中用汉语传唱的一种传统民歌。从民族属性来说,它不仅是少数民族民歌,而且是典型的多民族民歌。关于这种民歌与“文学”的关系,在20世纪后半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民间文学史著作中一般是这样安排其体例的: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歌→少数民族民间歌谣→西北“花儿”。这表明在学科上“花儿”是归属于“文学”的。其构成“文学”文本的最主要成分是被写成文字的大量歌词,其次才是其至今尚莫衷一是的“文学性”。因此也就有了以下从学科和文学性两方面的不同认识和表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向以民间口头文学为主,……少数民族文学的又一共同特征是民间文学普遍发达,……在民间文学中,民歌特别发达……”,[1]3“民间故事传说与民歌一起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长河中最汹涌的两股劲流。”[1]6“它(民间文学)是具有文艺特质的民俗,是民俗化了的文艺,它是文学、艺术、知识等的合体,而非纯文学。”[1]13“民间文学的本体不是‘文学’一词可以涵盖得了的,……总之,民间文学和纯文学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2]“民间文学不完全隶属‘文学’。它有着完全独立的形成和演进轨迹,并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文学理论’不能涵盖民间文学,解决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什么是民间文学的问题。”[3]综上所述,也就是说“花儿”在广义上是归于文学的,是被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来欣赏的,同时“花儿”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其特殊性体现在:民歌在当代既有口头文本,也有文字文本,还有多媒体文本。与作家文学不同的是,民歌不始于书写,也不止于文字,即并未被“文本”固化,文字只是民歌的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只是一种便利的保存手段,民歌并不靠文字文本存活。民歌被写在书本中,却活在生活中,它是一种活态文学,而且与其传统一脉相承。
同时,将“花儿”作为文学来研究,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一个题中之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属性,认识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性质及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逻辑起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研究范畴,包含中国古今各个民族创造的全部文学成果。”[4]9“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的文学,在内容和范畴上包括各民族的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等所有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文本。”[4]10其中,民族口头文学是多民族文学史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考察“多民族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时,我们应该同时考察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的“多”、“民族”、“文学”这几个要素,其中,“多”这个因素特别值得思考。“多民族文学”中的“多”不仅是指作为文学传承主体的民族之“多”,也不仅是指民族文学的数量和种类之“多”,更多地指由“多”带来的“多元性”,即文本的多样式、多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的特异性。而“花儿”这种民歌正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口头文学样式、形态及文化背景方面的这种特异性。
“花儿”因其形式的“特殊性”与“文本”的复杂性,给我们在文学的范畴之内提供了一条研究捷径的同时,也预伏了不少误区和难题。难题之一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史或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中,如何判断“花儿”这类文学的价值?并恰如其分地体认、保存其文本?可以说,20世纪以来大量的研究,使“花儿”的文学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认与表述,比如关于其“文学性”,在研究“花儿”中的比兴、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时,甚至有不少论者将其与《诗经》相提并论,使人们认识到“花儿”不再仅仅是“乡野酸曲”,不再仅仅是下里巴人的草根文学,而是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从文学角度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对于“花儿”的文学价值认识过低的问题。
但同样,出于某种需要对“花儿”的文学价值进行过高的判断与表述,会使之成为一个被过度建构的对象,并且因为过度建构而使其“文本”发生变异。实际的情况是,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这样的过度建构以及文本变异时有发生。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花儿”文学价值的过度表述
2003年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4年中国加入世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家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一系列国家文化政策的出台,促发了21世纪初中国声势浩大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浪潮。
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化种类繁多,但只有各民族的口头文化中有语言唱、述文本的那一部分才属于文学的一部分。“花儿”既是一种民族民间文学,而作为传统民歌,毫无疑问也是一种文化遗产。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启动以来,西北几个主要的“花儿”流传地区从省(区)到地(州)、县、市,也纷纷出台了一些规划、措施,开展了一系列自上而下对“花儿”流传地的考察、命名,还有各地自下而上不遗余力的申报、推介活动。这些活动都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之名。从过程来看,“花儿”的“保护”是地方政府将之作为文化产业“开发”、“打造”进程中的一个策略性选择。实际情形是:所谓“保护”在种种规划和口号下面往往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而“开发”、“打造”依然是大行其道,只不过现在“开发”、“打造”的,名义上不再是某某品牌和经济增长点,而是一份“文化遗产”而已,但这份“文化遗产”名目下真正被开发的还是所谓的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目标往往不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是为了拉动一个地方GDP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学术研究提供文化资源的分析与论证,并且提供知识和理论上的参考和支撑。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充当的角色,要求学术研究要有超然的品格和独立的判断力。但在实践中,在政府、学术界、文化产业开发商各自的三套话语的博弈中,学界内部的话语有时是分化的:一部分学者以现实的实际情形为参照,对许多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表示失望与担忧,对地方的“发展观”持怀疑、反思、批判的态度;另一部分学者则与地方政府及开发商的文化产业策略合谋,积极为之进行跟进式的“合理性”论证,对现状持乐观态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平息过,这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状况中有许多表征。关于前者,反思与质疑是学术的必备品格,毋庸置疑。而问题在于,后者的学术取向往往不自觉地过于迎合地方政府文化产业“开发”的意图,淡化了学术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实际就变成了对“文化遗产”文学价值的鼓吹,从而造成价值虚高,造成对于文化遗产本真价值的某种遮蔽。
试以一部将“花儿”作为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对象的“推介书”《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近年来此类著述不断面世,但论述路径大体与此书类似)。[5]在体例上,这部书引用了大量的研究资料,陈述、介绍了“花儿”的渊源、流变、民俗、“花儿”学术研究史及其成果,列举了“花儿”的流传现状,也列举了各级政府的保护、利用、发展措施等等,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一部颇为厚重的“推介书”。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花儿的价值评价”:“(花儿)近年来受到中外专家、学者、媒体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独立的学科——花儿学,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学术领域深受瞩目的一门显学。从花儿的历史渊源、艺术价值、演唱习俗、研究成果、濒危状况来说,花儿属于珍贵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是活着的《诗经》,西北的百科全书。花儿是大西北江河山川的精灵,是大西北文化艺术的奇葩,被人们赞誉为‘大西北之魂’。”[5]2……花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5]24……,“花儿真实地全方位地反映着劳动人民以往的历史足迹,是黄河文明的源头,是活生生的《诗经》。是中国音乐丰富多彩的宝藏,是活着的西北大百科全书,是中国悠久灿烂文化的骄傲,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花儿的延续传承,就是继承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体现,是时代赋与当代人的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强国的必然。”[5]107在这样的表述中,作者用大量富有诗意的文学修辞,对“花儿”的价值作了全方位的高度的评价,但显然其中的溢美之词远远多于实际论证,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过度评价。
然后是“推介书”不得不说的“花儿”的“濒危报告”:“花儿的演唱人数骤减。……20世纪80年代搞《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花儿之乡90%的各族群众能唱花儿或说花儿词的,现在约剩30%,出现断歌危机。花儿已呈强弩之末,演唱人数骤减的速度是惊人的,昔日的风景已不存在了;花儿会上花儿稀,花儿会已变成浪山会、旅游节,游山观景的人多,唱花儿的人凤毛麟角。……群众自发对唱的已屈指可数,晚上彻夜唱歌的习俗也已消失;花儿歌手后继乏人。”[5]113而书中列举的导致“花儿濒危的原因是:现代文明使花儿的原生态环境毁坏;花儿文化的性质发生变异……花儿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歌手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商品;政府、文化部门缺乏保护、引导措施……”;[5]113“花儿濒危的结果是:原生态花儿消失;外来的流行歌曲、通俗音乐及变味的花儿充斥;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民族精神泯灭。花儿的消亡,将导致地域文化消失、多民族‘共同语’的解体,其结果就是中国大西北灵魂的消亡。”[5]114再看政府的“保护、利用、发展之计划:(1)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启动,(依据是)2004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2)中国民协对相关州、县‘中国花儿之乡’的命名;(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在实施。”[5]116-117可以看出以上基本都是政策而非措施。此外,书中还简单罗列了几条学术界的“建议性保护规划”。
如果将给该书中较为分散的以上几章集中到一起,那么按照其中的核心句、段的论述的逻辑关系,就会推出以下的结论:源远流长的、被誉为“大西北之魂”的“花儿”,在“近年来中外专家、学者、媒体的高度重视”下,在政府的“保护、利用、发展之计划”正在制定或启动的过程中,正在眼睁睁地走向难以挽回的“濒危”境地,面临“消亡”的危机。对此,政府除了出台一些政策之外再也“回天乏术”,而学者们也只能提供一些大而无当的“建议性保护规划”——在学术研究的繁荣、地方政府的“大力保护”与“花儿”无可奈何的濒危状况之间存在着如此无法弥合的反差,这恐怕是连推介书的撰写者们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逻辑悖论。
显然,在上述的表述中,“花儿”的价值评价与“花儿”的濒危状况、保护措施之间是脱节的,推介书中集中呈现的“丰硕”的花儿研究成果并未从花儿流变的历史中总结出“花儿”兴衰的规律,如此之高的价值评价竟然不但无助于正确地分析“花儿”的濒危的成因,也无法为“花儿”的保护措施提供更有效、有力的学理支持。因此,对于“花儿”文化价值,类似的表述是空洞、无力的,在此价值建构背后折射出来的不过是地方政府明显的功利导向极其对学术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学者内在的文化焦虑而已。
三、“花儿”作为“文学”与“遗产”,其本真价值在于人文关怀
作为在西北多个民族中自古传唱的传统民歌,“花儿”毋庸置疑地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蕴和厚重的文化价值,在现有的认识之上,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和论证。但是,从文本出发的形态研究到所谓“民族之魂”的构建,中间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就是对“花儿”的主体即历史的、现实的传承人群的研究,忽略了“花儿”与人的日常关系。“濒危报告”强调了现代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歌唱习俗的改变,下一代在情感与生活状态上对“花儿”的“远离”,由此产生的“花儿”传承的断代危机等等,并且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现代文明”对乡村的破坏性作用。然而这是一种客位的观察,如果从主位来看呢?面对乡土社会的变迁,广大农民难道也是一味的怀旧,只有被动与无奈?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他们是怎样接受“现代文明”的?他们对“花儿”的凋敝持何种态度?谁了解过他们在当代的精神世界?“花儿”与他们的生活还有多少关系?这一系列的追问应该拷问“花儿”研究者的田野作业,其中折射出“繁荣”的“花儿”学术研究对“荒芜”的“花儿”田野的忽略,折射出学术研究中现实关注与人文关怀的缺失。
因而上述推介书对“花儿”价值的形而上的抽象的判断,就变成了一种缺乏根基的过度建构,以及因过度建构而导致的价值虚高。“花儿”是“大西北之魂”——这样的命名,诗意充盈却缺乏学理性的论述。“大西北之魂”从其主体性中被抽取、剥离出来以后就成了一个被滥用的符号,其能指与所指完全断裂,甚至能指完全被遮蔽或虚化。此种过度建构并不是基于一种文化体认、现实关怀、学术需求,而更多的基于功利化的策略性考虑。进而言之,以往学术中的“花儿”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按某种需要被“建构”出来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存活于民间、土生土长、口耳相传的“花儿”本身。
四、“花儿”研究需要价值回归于人自身
在“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推介中,学术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未来的保护过程中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正如不少学者在批评保护中的种种误区时指出的,首先要明确“保护什么”?“为谁保护”?“怎样保护”?对花儿研究而言,首先摆在面前的任务恐怕是一种必要的学术反思。近年来有不少这方面的呼吁,代表性的例如郝苏民《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6]赵宗福《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等,[7]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一个共同的方面,也是本文一直在凸现的一个中心话题,那就是“以人为本”。就“花儿”研究来说,“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指要关注、保护那些传承人,更意味着要看到“传承人”身后的广大的人群,他们才是传承主体,我们关注的目光要深入到他们生息繁衍的“田野”中去。
从上述推介书的表述来看,消失的“大西北之魂”,是指具体的传承人的减少,歌词创作的弱化,传唱之风的改变和衰减,以及其它现代艺术形式对其造成的冲击和“改造”等等。这些都是民歌形式和载体的消失,那么,这些又是如何造成的?我们由对民歌的田野、生态的考察,不难发现民间更值得关注的现实:现代化进程给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带来了太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当代社会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什么话语平台,他们传统的情感交流渠道被堵塞,于是转向消费渠道,转向物欲,并进而演变为“物欲横流”的现实。而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情感伦理的畸变。因此,讨论民歌文化空间的变迁不能无视广大农村正在发生的剧烈的变化,不能无视广大农民在文化转型中因文化的断裂、冲突而导致的迷惘、困惑、无助和焦灼,不能无视他们在社会转型中被迫或自动做出的选择,比如逃离乡土、悖弃乡村价值观与伦理、剥离民歌传承人的角色等。一种民歌的消亡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民间文化精神的消亡,这才是灾难性的,它意味着曾作为我们的文化根基的“民间”的消亡。它使我们的一切文学艺术都将变成无根的空响和喧嚣。如果我们都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当代农村,转移到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以一种更大的文化视野和人文关怀精神去进行“花儿”与人的“整体性”研究,那么我们也许才有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
五、结 语
因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化遗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民族文学”的“花儿”和作为“遗产”的“花儿”,是民族文学的价值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个共时性场域的讨论中应该同时面对的两个话题。那么两个场域的最大交叉部分,就是民歌的传承、保护路径与“遗产”的濒危、消亡现状。而两个场域冲突的焦点则在于以“保护非遗”之名进行的文学价值的过度建构。
从“花儿”到“多民族文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文化产业”,这中间其文学与文化价值经过了多重“建构”与表述,但悖论的是,与建构者的初衷相反,过度建构、过分表述导致的反而是价值的流失。那么,在民族文学的书写中该如何看待这样的被打造成“遗产”的“文学”?而这样的“建构”带给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又是怎样的话题?这些问题的倒逼,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原点,重新正视作为“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学内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且在日新月异的“开发和保护”的进程中直面现实,做出应有的学术回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切实的学术支持。
[1]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2] 刘颖.民间文学是文学吗[J].民族论坛,2006,(2):50.
[3] 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4]李晓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J].民族文学研究,2008,(4).
[5]王沛.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郝苏民.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民族文学研究,2005,(4).
[7]赵宗福.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J].民间文化论坛,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