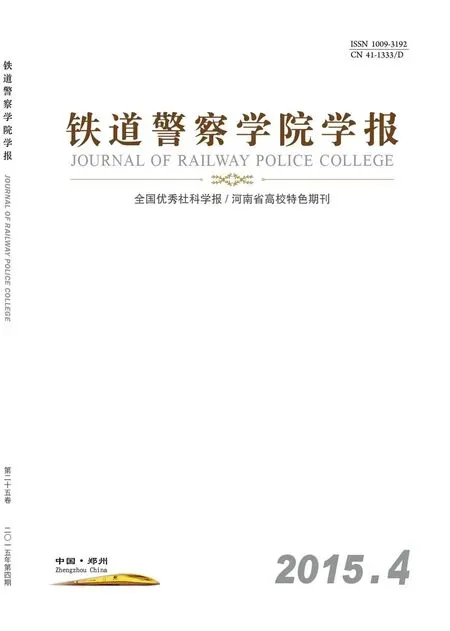被害人承诺三论——基于不同视角的分析
2015-02-12付传军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92(2015)04-0080-04
收稿日期:2015-05-20
作者简介:付传军,男,河南商丘人,河南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讲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在对刑法问题的探讨中,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考进路、不同的结论。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也是如此。本文尝试对被害人承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不同视角的分析,以期能进行新的梳理,有所发现。
由于国家对刑事追诉权的垄断,传统的刑法问题通常都是表现为“国家——犯罪人”的二元主体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国家的专门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人行使追诉权。被害人承诺作为近年来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刑法问题,它的新颖之处在于这个特定问题的主体结构模式引入了一个在其他问题中普遍受到忽视的要素——被害人,形成了“国家——犯罪人——被害人”的三元结构模式,被害人在其中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刑事追诉权的行使,具有了足够的话语权的诉讼主体。其体现了对公民自由决定权的尊重,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民权主义刑法勃兴的一个表现 [1]。
在被害人承诺中,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的介入,使得对其中许多要素的评价有了新的视角,也可以说形成了多元的评价坐标体系。对于具体问题,除了代表国家意志的刑法的最终评价外,还有被害人、行为人,以及社会一般人的评价,而后者对于前者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许多问题在被害人、行为人,以及社会一般人两两组合形成的不同视角下,可以有着不同的阐释和延展。同时,对被害人承诺正当化的法理基础,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也非常必要。
一、名称:是被害人承诺,还是权利人同意?被害人——社会一般人视角
研究被害人承诺,关于名称即有很大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来源于承诺主体(行为对象)和社会一般人的不同视角。命名为被害人承诺很明显是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即在社会一般人看来,承诺主体作为行为指向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其权益是被侵害的,所以被称为被害人,其落脚点是被侵害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这个行为就不会成为刑法中的问题。然而在承诺主体看来,自己的承诺则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故意寻求被害,行使权利的动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其落脚点却必定是实现自己的权益。
所以有学者主张应以“权利人同意”的概念替代被害人同意(承诺)的概念,“‘被害人’有时实为受益人”,“被害人的概念可以归属于权利人的概念范畴。被害人无一例外的都是相应的权利人,因此权利人同意的概念具有逻辑上的包容性,即可以合理地包容被害人同意的概念” [2]。这种主张有一定的道理,将承诺主体简单地认定为“被害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专断性,是一种个体要服从一般的思维模式。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一个视角转换的问题,如果权利人的同意已包含了全部的真理,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常态行为又为什么会成为刑法上的问题呢?承诺主体的视角当然重要,但社会的一般视角也不容忽视,毕竟社会的一般伦理判断是刑法的重要立足点,两种视角的辩证统一才是问题的全部。
因此,在笔者看来,被害人承诺作为约定俗成的名称,不妨继续沿用,毕竟尊重习惯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在沿用这个名称时要明确它的内涵:它是行使权利,但不是完全常态的行使权利,它有被侵害的结果;它是一种被侵害,有侵害结果,但它也是被害者行使权利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个问题,为其在理论上的展开奠定稳固的基础。
被害人和社会一般人的不同视角造成行为效果的不同的价值评判,而对被害人承诺行为的最终定性也是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被害人承诺研究中,根据被影响的法益的不同,这种博弈可以分为三种情形,这体现了两种评判的三种不同关系。第一种情形是以权利人(被害人)主观意志利益为法益,在这种情形中权利人(被害人)的自我决定权为唯一的法益,权利人具有完全的自主权,所以两种评判在这里是一致的,该种情况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行为,无犯罪性可言。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经妇女同意与之发生性行为,由于无违背妇女意志,也就无强奸犯罪可言。第二种情形是被害人(权利人)较轻的人身权益和客观物质利益。在这里两种评判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在被害人(权利人)看来,承诺是在正当处分自己的权益,他自己出于个人具体情况的衡量,认为这种处分符合自己的意愿,出于自己的意志,所以并不认为自己在受害,甚至在总体上认为自己是受益者;而从社会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权利人)的权益受到了侵害,认为这种侵害具有不以权利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受侵害的权益不属重大法益,社会的一般观点认为权益主体的自主决定权更为重要,所以社会的一般评判让步于权益主体的特殊评判,以后者作为评价的标准,对这种行为并不予以犯罪化。第三种情形是以生命权和重大健康权为法益。两种评判同样有重大分歧,然而因为这两种权益过于重大,在社会一般观点看来比权益主体的自主决定权更为重要,所以社会一般评判不再让步,对侵犯这两种权益的行为虽经被害人(权利人)承诺仍然认定为重大侵害,予以犯罪化处罚——个体的特殊评判必须服从于社会的一般评判。
二、对象:是承诺,还是被承诺的行为?被害人——行为人视角
除了被害人承诺的名称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和混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辨析,即该刑法问题的实体或者说是其实际考察的对象是被害人的承诺,还是行为人经被害人的承诺而为的行为。因为“现行的被害人同意理论是以一种单向性的理论视角,即仅从被害人或同意人的视角看待和研究有关的问题。这种单向性视角所造成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同意’和‘应同意之行为’的探讨混在一起” [3],所以在已有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往往把这两者混在一起都作为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将诸如行为人对‘承诺的认识’以及行为人‘基于承诺的利益侵害的范围’等本应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要素,归属到同意人同意的构成要件中来’” [4]。
在通常对被害人承诺问题的讨论中,实际上包括两个主体、两种行为。一个主体是被害人,他做出的行为是承诺,是对属于自己的权益的处分的意思表示,承诺的对象是行为人;另一个主体是行为人,他实施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行为的对象是被害人承诺的权益。这里还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聚焦于被害人,承诺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聚焦于行为人,经承诺的行为就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但这两方面在对被害人承诺问题的讨论中地位是不同的。
刑法考察的主要对象是行为人的非社会常态的行为,目的是要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被害人承诺也是如此。被害人承诺的目的性指向是行为人经承诺而为的行为,是要解决这种与犯罪构成具有密切关联的行为要不要负刑事责任,什么情况下要负刑事责任,为什么要负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行为人视角是主要视角。而被害人的承诺则是辅助性的,它是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为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服务的。“刑法虽然关注权利人的同意,但同意(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即权利人同意并非刑法的评价目标,而只是刑法对行为评价的参考。相应行为人的行为才是刑法的评价目标,才是问题的落脚点” [5]。
在讨论被害人承诺问题时,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两种视角的意识,既要从被害人的角度探讨其承诺的性质和效力以及对行为人行为的影响,又要将行为人的行为作为独立完整的刑法上的行为运用刑法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二者的关联,又要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避免概念上的错位而造成理解上的混乱。被害人和行为人是被害人承诺中的两个独立的主体,对他们的规范要求和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第三种视角的组合是行为人——社会一般人。这种情况较为简单。行为人一般并不认为自己经被害人承诺后实施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经正当授权实施的行为,甚至是一种帮助被害人的行为,然而对其行为的评判并不以其自身的认识为标准,行为人的认识在与社会一般评判的对立中,要服从于后者。不过其主观认识虽不能决定行为的性质,但会对其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根据:法益衡量还是社会相当?法益(结果)——规范(行为)视角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即被害人承诺的法理基础,众说纷纭,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法益保护作为立论的根基,侧重于从被害人承诺对法益的影响论证对其非犯罪化的根据,如法律保护放弃说、法益衡量说等。法律保护放弃说认为,当法益主体即被害人同意放弃自己能够处分的利益的时候,受保护的利益就不存在了,没有必要适用保护该法益的法律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利益的放弃);法益衡量说则强调“自己决定的自由”,认为在个人自己决定自由优越于行为所引起的法益侵害的时候,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能够被正当化。另一类则以规范要求作为立论的根基,侧重于从被害人承诺与规范要求的关系论证对其非犯罪化的根据,如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目的说认为,它是实现国家所承认的共同生活目的的合适手段;社会相当性说认为,从法律理念来看,它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 [6]。
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其实是犯罪化根据的另一面,是犯罪化根据在反面的映射,因此,讨论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必然要以犯罪化根据(违法性的本质)的理论作为参照。从上面关于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可以看出,它们对应于违法性本质的两大理论,即法益保护说和规范违反说,实际上是分别以这两种理论作为自己的根基的。
规范违反说也称为社会伦理主义,认为犯罪的本质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法益保护说也称为法益保护主义,认为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 [7]。前者也被称为形式的违法性,后者则为实质的违法性 [8]。
这两种主张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执一词,但依注重保护人们的生活利益即法益,强调法的客观属性的现代刑法观来看,法益保护主义成为主流。
然而,近年来由规范违反说衍生出的一种有力的主张认为,刑法并不是单纯地保护一定的利益,使之免受损害,所有利益都是非永恒的,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遭到损害,直至消失。“这些利益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因此是相对的,是与一定的特定的危险相联系的。……刑法的服务功能,如果的确有这种功能的话,不是笼统地保护被宣布为法益的利益,而是保护各种利益免受特定的攻击。并且,只有在关系到这种保护时,这些利益才会在法律的焦点上显现出来,成为法益”。“刑法保护的是对利益的攻击不会发生这样一种期待”。“在刑法意义上,这个利益不是作为外在的对象或者类似的东西来表现的,而是作为规范,作为有保证的期待来表现的” [9]。依照这种观点,刑法是指向人的,而不是指向物的,法益只有在相对于特定方式的危险时,它才称得上是法益。刑法的主旨在于要求利益的相关方不得以特定方式攻击利益,利益在这里体现的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总是仅仅涉及有责任的人” [10]。
其实,无论是法益侵犯,还是规范违反,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犯罪的本质,只是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分析一个行为,即行为本身和行为造成的结果。一个行为之所以被设定为犯罪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必定是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的一般的伦理规范,超出了社会能够容忍的底线,以社会难以容忍的方式损害了利益,这是社会断然不能接受的,也可以说是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从行为结果来看,这种行为必定是给社会所重视的某些利益造成了损害或者是构成了威胁,“只要不是侵害法益,或者是对法益造成了危险的行为,即便是违反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也不能作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反之亦然,“被称为犯罪的行为,仅仅对法益有侵害或危险还不够,还必须违反了社会伦理规范” [11]。“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社会的伦理规范,给法益造成侵害和威胁” [12]。“所谓犯罪,就是违反社会上的一般人当然应当遵守的社会伦理规范的、侵害法益的行为,以及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的行为” [13]。
以这种观点分析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根据,结论是很清楚的。法益衡量和社会相当是从不同的视角对被害人承诺观察的结果。从行为本身来看,承诺行为是权利人处分自己权益的行为,应承诺而为的行为是被授权帮助权利人处分自己权益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于实现人们的正常需要,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是非常必要的,是具有社会相当的行为,社会容许这种行为存在,它是在社会伦理规范之内的;从行为的结果来看,在社会一般观点看来,它虽然对一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损害确实是为了实现权利人的自主决定权这种更大的利益所必需的,损害的阴影已被这种利益实现的光芒所遮蔽,所以被正当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两种根据只是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视角,其实是并存和相互渗透的,如若损害的利益较之实现的利益更大,这种行为也就为社会所不能容忍,失去了社会相当性,不能被正当化;如果一个结果虽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但其行为方式却为社会所不能容忍,它同样不能被正当化。从对被害人承诺的正当化而言,其正当化根据正是这两种视角的统一。
综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被害人承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对于刑法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仅要选准视角,这是讨论的基础,而且要从多个视角进行展开,这样才能形成全面的、立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