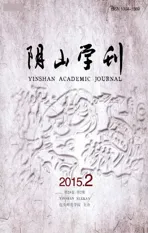文化产业的国际传播逻辑*
2015-02-12朱振明
朱 振 明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文化产业的国际传播逻辑*
朱 振 明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 100024)
中外“文化产业”概念存在差异,文化产业在跨边界传播中面对三种国际化逻辑即:意义生产与理解的格栅、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博弈、从“观念”的中介化到“物”的中介化,要走向理性的文化产业传播,需要关注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公民素质的培养以及文化产业跨边界活动的新的传播景观等议题。
文化产业;国际化逻辑;中介化
文化产业不仅是产业问题也是人类学问题。所谓产业问题,在于探讨文化活动如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所谓人类学问题,在于探讨作为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文化如何实现了跨边界的国际传播。谈到国际传播,存在着一系谱学问题。首先,国际传播是跨民族或种族边界的传播,在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而具有了全球时空和学科维度。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当我们把全媒体、民族文化产业和国际传播等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实际进入到当前的一门“显学”:全球文化产业研究。这种研究基本关注两个方面:作为产品的“意义”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符号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物质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商品政治经济学(具体毋宁说经济学)。商品政治经济学把文化产业视作一种产业活动,目的在于获取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如作为收益的利润;作为符号政治经济学,其把文化产业视作一种意义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目的之一在于增加民族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或感召力,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之后,文化与信息具有了战略性作用:不但代替物质资源成了生产的原材料,而且成了治理国家和组织社会的工具。真正的“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情:欧盟面对美国的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入侵为促使欧盟调整文化政策而提出的概念。随着全球化和全媒体传播的出现,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领域中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文化产业不仅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了民族国家博弈的工具和领域。
一、文化产业的身份:概念的扭合
在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主要涵盖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文化生产活动,如广播、电视、出版、游戏、动漫、演出等;当这种产业活动涉及文艺创作和版权时候,又被称作文化创意产业(尤其在英国),如文艺作品创作。法国学者贝尔纳·米涅区分了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别:文化产业的特征为“复制”,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则是“创造”。当“文化产业”被引入中国后,似乎所有的文化资源与活动都可被商业化,形成 “文化产业”,尤其是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旅游景点、历史名人或名地。实际上,作为“文化产业”前身的“文化工业”是一个社会批判概念,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整体论观点对“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产业的分析与批判。他们指出,对这种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文化产业的执着使消费者失去了“理性批判能力”,人类借以发展自己的科技最终成了奴役自己的工具。当美国的流行文化于上个世纪后半期大举入侵欧洲的时候,“文化产业”才被正式提出来,并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被整合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市场力量开始向传统文化领域渗透;1988年,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颁布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的概念得以确立;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1]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希望探讨“文化立国”战略,基本上这种观点所得来的启发。另外,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以及对“软实力”观点的陈述与实践。在外国的“文化产业”研究文献中,鲜有像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产业”,其“文化产业”内容主要集中于“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以及“媒介产业”,在此种意义上,以民族文化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学术界和业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贡献。实际上,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的跨边界传播都属于民族文化产业活动的范畴,因为跨边界的传播意味着不同“民族记忆”间的互动。
二、文化产业的国际化逻辑
(一)意义生产与理解的格栅
对于经济和人类学活动的“文化产业”而言,其涉及经济学和传播学规律,经济效益通过文化产品的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化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数字化媒介则是这种传播或传输的主要载体,而文化工业则是这种传播的主要表象。当前,先进的传播技术为此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对文化工业或产业而言,无论是业界或学术界,换句话,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普遍观点认为内容起着决定性作用,即“内容为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是涉及意义生产与消费的传播活动,这意味要关照文化产业所负载的内容的生产、传播、解读和消费(如使用与满足)。在一个既定的时代,一种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不是偶然的与随意的。一方面,“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媒体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2](P11)。另一方面,在每个既定历史时期,具体地,在某个既定的时空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是通过一定的理解格栅来进行的,这种格栅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那里被称作“认识型”,即某种话语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一系列的各种性质的条件使其成为可能,用更为通俗化的话说,一个时代的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尤其是生产,是通过主流思想指导方针来进行的。在表达多元化不充分的社会里,这具体表现为知识的生产由官方意志来指导,知识(与文化)生产要反映当时的具体主流思想精神,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知识的生产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我们说文化产业及其国际化是一种“人类学”特征活动,谈及人类学,这就意味“差异”,即不同民族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内容,如生活方式、思想和价值观等,谈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实际是在谈论文化的“多元性”以及跨文化传播问题。这种知识(与文化)生产的格栅成了文化工业发展的过滤器,于是,被过滤出来的东西能否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完成“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成了一种赌注,尤其当政治意识形态弥漫在文化生产活动中的时候。
文化产业的传播,尤其是跨边界传播,加速了“集体想象”或“集体记忆”的外化——既是记忆从人体里的外化,又是地方记忆超越国家或民族边界的外化。在现实世界中,对于国家或群体来说,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与对抗,作为文化重要传播渠道的文化工业成了“软实力”博弈的重要资源。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在对电视节目的研究中,提出了受众对电视节目讯息接受的三种模式:支配霸权模式、协商模式和相反模式。[3](P171~173)支配霸权模式在于展示受众接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协商模式显示了电视信息在被编码和解码时候的彼此差异;而相反模式则显示了电视受众对主流话语所“框架”出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这就是说,在文化产业的传播过程中,对内容意义的解读基本上存在着三种可能性,而这些可能也符合阐释学的“视域融合”原则。但问题是,当我们把文化产业作为意义生产的战略工具而增加“软实力”或感召力时,“支配霸权”成了最理想的模式,当然“协商模式”次之,最不希望看到的是遭遇“相反模式”。当然,霍尔这种理解是把作为文化产业具体形式的“电视传播”当作研究对象来进行的,但这种编码和解码方式可应用到其他的文化工业活动中,因为其从哲学的角度讲授了人对信息的可能接受方式。对作为情景化和制度化存在的社会活动者来说,其认知和主体化过程是与特定知识生产条件(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技术等)联系在一起,知识的生产条件越相近,知识(或文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就越容易进行,因此以文化产业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寻找与扩大“传者”和“受者”间的共同点与相似点,单纯的单向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宣传”难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二)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博弈
跨边界的文化产业活动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那里,传播的国际化具有两个维度:其一是西欧早期(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其旨在构建一个普世的民主共和国;其二是随着欧洲启蒙运动而来的普世商业思想,旨在构建一个普世的商业主义共和国。传播在两个维度上的扩展构成了现在的国际传播现实。普世的民主共和国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追求作为社会活动者的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民族文化被看作民族身份、文化创新和意义更新的源泉;普世的商业共和国更多遵循商业逻辑特征,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脱道德”的嬗变,早期具有得到道德哲学特征的古典经济学嬗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利润追求成了唯一的产业活动目的,而且经济逻辑倾向于成为管理和组织社会的唯一逻辑,作为以服务社会成员为目的的“公共物品”或“公器”的文化让位于以经济红利为目的的“商业文化”。国际传播的这两种维度及其暗含的两种逻辑成了当前对文化产业(或工业)实施分析与批判的重要内容。在当下中国,虽然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说,但后者远远走在了前者的前面。
作为经济活动,文化产业的跨边界入侵意味着一种文化工业生产方式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生长环境。在文化产业跨边界活动中,既要摆脱“第三世界主义”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又要对文化公共服务进行保护。因为,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现代面目的经济学在经济学层面上,文化工业的文化产品被看成一般商品和服务,文化产业拥有自己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的结构,而且不同产业拥有不同的逻辑,如出版逻辑、主要体现为广播电视传播正的流动逻辑、报刊印刷逻辑、以及表演和旅游逻辑;另一方面,由于商业唯一支配逻辑的工具理性功能过于强大,还需要强调了一种公共服务逻辑的回归,因为商业唯一逻辑不仅阻遏了人类作为象征动物的再生产,而且也阻碍了传播的民主化以及社会的正义。对文化产业的(合)理性批判的启发主要来自于欧洲大陆的主体哲学。自从笛卡尔实现主客体二分之后,哲学认识论成了哲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人的理性受到了尊重,合理化(例如在马克斯·韦伯)成了人类借助理性原则对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进行合理组织的过程,合理化导致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现代性及其后果”。基于科学和技术上的合理性,自20世纪以来受到了青睐,这种理性被韦伯等人称作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一种手段—目的理性,其涉及到寻找最有效的方法与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目的,不过这种合理性的特征之一是没有对目的的本身实施评估。在这里,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但手段不能为自己的目的做出有力的证明。[4](P58)于是在人们欣赏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成果的同时,我们又进入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例如污染和环境恶化、旅游资源的破坏与枯竭。
上个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对这种技术工具理性的学术性反应。社会批判理论的兴趣点之一,就是谈到这种手段—目的合理性如何利用合理性原则最终为人类自己打造了限制自由的“铁笼”。人的自由与充分发展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在批判理论那里,这种合理性成了奴役人的工具,对这种合理性的批判试图为人类、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价值观寻找“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理论中所选的对象就是单数的“文化工业”,分析和批判大众文化如何利用消费“欢愉”手段使社会成员(或消费者)失去分析与批判的能力而被“愚化”,失去“主体性”,沉浸在日常的符号消费中。这种单数的文化工业,随着大众文化兴起,被作为产业活动的“文化产业”所替代。实际上,这种商业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以及批判理论强调的支配/解放对立概念暗含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对抗,其不但折射出民族国家对经济增长的非理性追求,如对不可恢复的文化资源的破坏,而且也反映在国家对民众的治理策略中,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者被化约为纯粹的影像消费动物,失去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能力。
(三)从“观念”的中介化到“物”的中介化
文化产业活动的跨边界移动和传播体现着一种产业活动表达的变迁,即从“观念”的中介化到“物”的中介化的变迁。这种中介化的变迁实际展现一种产业活动理念的变迁。文化产业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容产业。在传统的文化产业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前),文化属于上层建筑,通过意识形态、符号、表征来实行支配与抵抗,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构成了文化产业的主要内容,而这种产业活动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换句话,在传统文化产业时期,作为内容的“观念”成了整个产业的中介化的平台,整个产业活动围绕在“观念”来进行。在美国学者斯科特·拉什看来,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工业成了一种跨越民族边界的产业活动,我们从民族文化产业时代进入到全球文化产业时代。在全球文化产业时代,文化从上层建筑中渗透出来,渗入并接管了经济技术本身,换句话,象征性(例如观念)与物质性(例如由观念物化而来的产品)具有互动关系,表征(如观念)和物(如由观念物化而来的产品)的中介化成了新的意义组织方式。简而言之,在全球文化工业背景下,在传统时代表现为表征的文化被物化,并支配着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换句话,在古典文化工业时代,中介化是靠表征(如作为内容的观念)来进行的,但到了全球文化产业时代,中介化主要是靠物来实现的,“表征的中介化”和“物中介化”成了全球文化产业的文化运作逻辑。这就是说,如果在传统的文化产业时期,文化产业的经济和意义(meaning)红利依靠了内容来实现,那么在全球文化产业时期,经济和意义的红利除了靠意义来实现外,还需要依赖由内容衍生而来的产品来实现,在这里产品衍生出了新的经济和意义红利,如遍布世界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形成了新的意义景观。
斯科特·拉什对传统文化工业到全球化文化产业的转换进行了现象学描述:“从同一到差异”、“从商品到品牌”、“从表征到物”、“从象征到真实”、“物获得生命:生命权力”、“从外延物到内涵物”、“虚拟的兴起”。[5] (P5~15)
在“从同一到差异”方面,传统文化产业的设想是,文化产品已经生产就作为一致的商品进行流动,发挥着资本积累的作用,社会活动者(或受众)被拖进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隶属于商品方法—目的理性的文化(产品)为物化或商品化,全球化文化产业则表现后福特式的差异性生产,这种差异性更多属于一个资本成功积累的方式问题,而不是抵抗问题。在“从商品到品牌”方面, 传统文化产业运作依赖的是文化的物质性商品,全球文化产业则是品牌。虽然二者都是支配与权力的源泉,但前者靠的是一致性逻辑,后者则是差异逻辑,体现了从无机性向有机性的转变,从无生命特征向有生命特征的过渡。在“从表征到物”方面,在全球文化产业时代,隶属于商品方法—目的理性的文化(产品)被物化或商品化,被物质化的文化实体在全球文化产业背景下,又成了一种新的意义的重组介质,这时的实体不再是单纯物体,而是构成了事件—物体或事件—实体,所谓事件—物体,是指该物体不简单是个物理存在,而是成了一种具有具体时空维度的情景化叙事。如当商标变成商标环境时,它就掌控了机场空间,并重新结构着百货商店、道路广告牌,城市中心;当卡通人物变成收集物和服装时,当音乐在电梯里播放时,构成了移动声音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意义不再是阐释或解释性的,而是操作性的。在“从象征到真实”方面,在象征空间中,意义的生产过程靠生产意义的结构,即通过阐释来实现,具有结构主义特征;在现实空间中,意义的生产过程靠的力量与直接性来实现,是实践性的,如由物体-事件所构建的意义,具有建构主义特征。传统文化产业占据的是象征空间,而全球文化工业则是真实空间,从象征到真实实际上是一种意义生产过程转换。在“获得生命”方面,拉什在此挪用了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认为全球产业具有自我组成,并具有产生差异性的能力,是生产性的,这不同于拥有再生产或可复制性以及机械权力的传统文化产业。在“外延物到内涵物”方面,从笛卡尔的自然物(res extensa)和思维物(res cogitans)出发,把传统文化产业生产划归为自然物,而全球文化产业生产则属于思维物。这里的“物”在传统文化产业中表现为自然物,在全球文化产业中表现为知识或智力的物(或称作知识产权)。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遭遇到的不是具意义指称结构或所指的物质性,而是被物化的所指或意义,即物化的表征。在“虚拟的兴起”方面。在全球文化产业中,媒介景观具有了思维物的特征(即具有了反思性,不是机械的再生产或复制产物),是一个多节点的体验空间,该空间具体地被表现为事件而不是物,全球文化产业就成了一种事件—物的东西,传统文化产业意义上产品或商品嬗变为一种联系不同体验的载体:事件—物体,于是物具有了中介化的作用。因此在全球文化产业背景下,文化工业系统具有了开放性特征,其开放性在于被物化的表征本身又成了不同关系与活动得以形成的中介。
三、走向理性的文化产业传播
意义生产与理解的格栅、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博弈、从“观念”的中介化到“物”的中介化。以上三个逻辑的提出来自于对当前文化产业在跨边界流动中所造成的国际传播现实的跨学科思考。文化产业的跨边界传播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产业流动,更重要是,它又是民族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元素、培养民族精神以及传播软实力的主要渠道。但在以手段—目的为特征的工具理性的驱使下,经济效益作为国家发展主要目的而得到重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来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同时为实现产业内容的跨边界传播,而无视作为意义生产与解读的情景化因素,希冀以宣传的方式把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传播出去,致使文化产业的对外传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努力实施对外传播;另一方面国际传播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促使消费者沦落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大众文化)消费”的社会活动者,另一方面试图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注意不到全球文化产业运作活动的变迁。
这三个国际化的逻辑实际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内容、效果和形式问题。走向合理的文化产业传播,似乎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议题:第一,在传播内容方面,要对意义赋予具体的意象框架,还原文化的人类学特征,使民族文化真正成为民族身份及其意义创新的依据;第二,在效果方面,文化产业在作为产业活动的同时,需要借助内容的生产来培养消费者对社会的认知和批判能力,公民意识完全的社会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在全媒体的全球化传播时代,任何隐性操作将在数字化网络的投射下变得具有可见性;第三,在形式方面,文化产业活动对社会和意义构建已从“观念的中介化”走向了“物的中介化”,“物的中介化”为文化产业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景观和传播现实:传统的、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业嬗变为一种新的、以衍生产品为中介的新的体验和意义组织方式,当然这意味出现了新的文化产业营销策略。
[1]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
[2]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M]. Paris:Gallimard, 1966.
[3]Douglas M. Kellner.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ks[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6.
[4]Val Dusek.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2006.
[5]Scott Lash.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 韩 芳〕
Internationalizing Logic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ommunication
ZHU Zhen-ming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The article not only exposes i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differences of defini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but also analyzes further three internalizing logics encountered by the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of these industries: meaning-producing and understanding grill, competition between rationalities technical and humanist, and shift from the mediation of “ideas” to that of “things”. With reference to both these three logic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ing realit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realize a rational cultural industries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subjects as content production, cultivation of citizenship, and new spectacles of cross-bord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Cultural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izing logics; Mediation
2015-02-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传播学科发展前沿研究”(11AXW003)部分研究成果。
朱振明 (1971-),男,河南南阳人,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传播、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G124
A
1004-1869(2015)02-0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