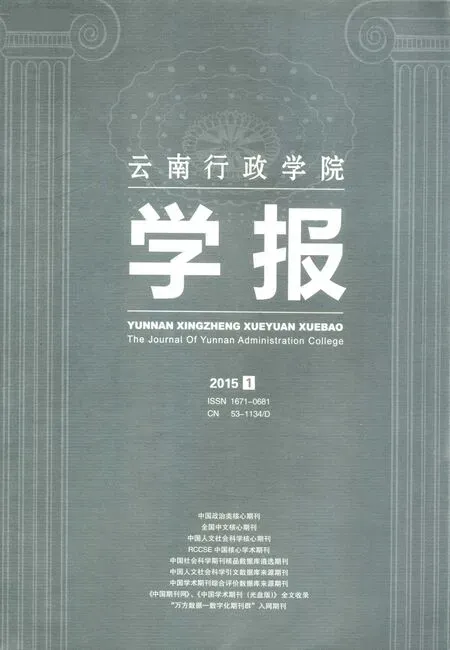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
2015-02-12何瑞文沈荣华
何瑞文,沈荣华
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
何瑞文1,沈荣华2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基础部浙江湖州,313OOO;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江苏苏州,215123)
经济繁荣的根源在哪?一般认为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诚然,制度对经济增长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无效制度的固化问题。制度可以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前者是经济繁荣的引擎,后者是经济衰败的根源。而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权力结构均衡,生成包容性制度;权力结构失衡,生成榨取性制度。因此,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制度类型决定经济兴衰。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变迁由制度漂移和关键节点共同决定。
权力结构;包容性制度;榨取性制度;经济兴衰;制度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为何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为何有的穷国能够变富,而有的富国则变穷?思想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其中,经济学界最为活跃。从亚当·斯密的市场分工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再直到道格拉斯·诺思、戴维·兰德斯、曼瑟尔·奥尔森的制度决定论,不绝于耳。另外,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战略假说、文化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以及孟德斯鸠的地理假说、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假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无知假说也不乏市场。客观地说,上述理论都不乏解释力,尤其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可以说是问鼎之作。诺思一直坚信制度是重要的,认为制度决定人类行为的激励结构,激励结构导致经济绩效的天壤之别。奥尔森则另辟蹊径,巧妙的从集体行动的视角阐释了分利集团导致国家失败的作用机理。诺思和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制度决定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是,他们却都有着明显不足。纵观诺思的制度理论,并未发现他对有效制度产生机制的有力解释,这使得他的制度理论的解释力略显沧桑乏力。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但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人远比理性人假设更为复杂,以致其国家兴衰理论根基不稳。
综上,我们发现三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现有的制度决定论无法解释有效制度如何产生以及为何有效制度没有得到普遍采纳的问题。二是政治权力作为对社会影响至深的因素,并未体现在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间,是政治权力对经济增长真的没有影响吗?无数事实恰恰证明,政治权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匪浅。第三,制度如何变迁?笔者基于权力结构、制度类型与经济兴衰的框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除了经济制度影响经济增长,还有别的因素吗?笔者认为政治权力结构对经济影响至深。第二,权力结构如何通过影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类型来影响经济兴衰?第三,制度如何变迁?
二、经济制度不足以决定经济增长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并非根本性作用。经济制度中的产权结构、市场存在和市场完善程度能够影响经济激励的结构,对经济绩效非常重要。一方面,经济制度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投资以及组织的效率,形塑了对关键经济主体的激励。另一方面,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决定了社会分配的公正性。换句话说,经济制度不仅决定“蛋糕”的大小,还决定“蛋糕”的分配。照此逻辑,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贫困的问题等价于为什么一些国家相较于另一些国家实行了更糟糕的经济制度[1][389]。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为何有些地方宁愿坚持糟糕的经济制度而放弃模仿有效的经济制度呢?这就无法有效解释为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仅在某些国家实行,其他落后国家为什么不效仿。借用奥尔森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他们也没有解释是什么阻塞了经济进步的道路。”[2]只能说明维持现状更有利,制度自动选择优化机制受到干扰,这一干扰因素无非就是政治权力。可见,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经济兴衰。
三、经济兴衰新解: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
好的经济制度本身不足以支撑起经济增长,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或缺。依据包容性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与榨取性制度,具体细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3][22-29],如表1所示。如果政治制度足够包容,那么经济制度必定不会是榨取性的,所以“包容性政治制度+榨取性经济制度”的制度模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本文仅分别讨论另外三种情况。
所谓包容性制度(inclucive institutions),就是经济上强调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分配中强调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政治上以集权提高政府效率,同时以政治多元化来制约政府专权,以此具备涵盖利益或共荣利益的制度。也就是说,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必备条件是安全的私有财产、均等的公共服务、公平的交易规则,放开市场准入,并让人们自由择业。包容性政治制度必须具备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两根支柱,缺一不可[3][23]。如果政治集权与政治多元化缺失,便沦为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榨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正好相反,榨取性经济制度限制市场准入、实行市场垄断,征收高额税收;榨取性政治制度实行专制统治,权贵垄断了政治活动。此时的制度沦为强势集团榨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一)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
包容性经济制度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包容性市场,能够提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公平竞争环境。更为重要是,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产权保护,容易形成对未来稳定的预期,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经济主体的生产和创造。其次,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即是毁灭。易言之,创新必须以牺牲一定的短期利益为代价。技术创新不仅能在经济上以新代旧,也可能在政治上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统治者只有排除对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丧失的担忧,才有勇气进行创造性破坏。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这一担忧迎刃而解。包容性经济制度通过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的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鼓励真正的创新精神,培育重大的技术创新。最后,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全民教育。技术创新对知识教育的依赖毋庸赘言。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功不可没。同时,教育能够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对加强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监督大有裨益。可以说,一旦包容性制度到位,经济增长便水到渠成。
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包容性经济与政治制度一旦形成气候,往往会形成良性循环,达到更高层次的包容性。这个良性循环通过以下机制来运行并强化:
首先,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法治逻辑。包容性政治制度的支柱之一是政治多元化。多元政治强调政治权力分配的多元化和权力必受制约。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与制约,这是法治的精髓。政治多元化及法治观念一旦建立,既能防止专制和腐败,又能创造更高程度的良性循环。
其次,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正向反馈。包容性政治制度建立在政府集权和政治多元化基础之上,通过法治手段,提供严格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夯实基础。包容性经济制度鼓励技术创新、培育创造性破坏和提供更多教育,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对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居功至伟。同时,包容性经济制度可以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繁荣打下基础。在包容性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社会权力更加分散、政治环境更加平等,使得任何集团对政府的俘获和控制更为艰难,促进包容性政治制度长期存续。只要政治制度是包容的,对于经济行为的偏离倾向,都会加以扭转,这就是正向反馈和良性循环。
最后,包容性政治制度容许新闻媒体的自由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政治多元化得到提倡,新闻媒体得到鼓励。2O世纪初,美国的新闻记者由于“喜欢揭人丑事”,被冠以“扒粪客”(muckraker)的称谓。在揭发政府官员丑闻、为政治人物反对托拉斯造势上,这些不起眼的扒粪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由媒体让有害于包容性制度的威胁曝光,鼓动社会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对包容性制度的威胁。难怪新闻媒体在西方被提升至“第四权力”的地位。
(二)榨取性政治制度、榨取性经济制度与经济衰退
榨取性经济制度导致经济衰退。榨取性经济制度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和产权保护。相反,拥有政治权力的权贵集团,出于政治替代效应的担忧,往往会抵制技术创新和操纵经济制度,并直接或间接地将社会的资源向自己转移,以使其收入最大化或最大程度的榨取租金。换句话说,权贵追求榨取性经济制度是为了更好地榨取收益。在榨取性经济制度下,制度沦为少数握有权力者的牟利的工具,如果情况得不到扭转,那么,经济将会持续的衰退[4]。
榨取性政治制度与榨取性经济制度的恶性循环。榨取性经济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彼此效力,把双方带进一个更深的反向反馈循环。榨取性制度倾向于诱致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榨取性制度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榨取性制度下,政治权力令人垂涎欲滴,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社会被推向政治动荡的格局。在榨取性制度下,制度沦为权贵谋取私利的工具,在自肥的同时又面临平民暴乱或革命的威胁。为了镇压暴乱或抵制革命,榨取性制度下的统治者必然加大榨取力度和频度以提高镇压的实力;革命的担忧降低了其统治预期,竭泽而渔式的榨取变得理性行为。当权贵们因榨取变得更加富有时,这些财富又成为下一轮榨取的基础。榨取性制度无法提供一个稳定预期,权贵忙于榨取财富,平民缺乏生产动力,长此以往,国家经济将陷入持续的恶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最终走向奔溃的边缘。
其次,榨取性经济制度与榨取性政治制度之间的恶性循环。榨取性政治制度导致榨取性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中,权力可以无往不利,可以中饱私囊,也可以无限滥用,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榨取性政治制度缺乏对利益集团分利行为的控制机制,容易建立符合少数集团利益的榨取性经济制度。反过来,榨取性经济制度为榨取性政治制度的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榨取性经济制度不断地增加分利集团的财富占比,使得它们容易通过强大的经济力量裹挟政治,推动政治制度更加具有榨取性。显然,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是合作无间并且协同推进的,但最为有害。
最后,寡头统治铁律。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认为,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如此。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更是简明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更替的舞台。榨取性制度恶性循环的逻辑与其类似:即使一套榨取性制度被推翻,新建立起来的制度也往往是榨取性的。推翻榨取性政治制度的统治者,由于在榨取性制度下制约权力的土壤浅薄,加之平民缺乏政治参与的训练,难以构成对统治者的制约,权力自身绝对不会自己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以形成对自己的制约。相反,新贵们通过建立一套榨取性经济制度榨取最大化的社会财富,借由榨取所得的财富巩固新生的统治政权。真可谓历史是会重演的——首演是悲剧,重演则是闹剧。
(三)榨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与短期增长
榨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从榨取性制度的根本逻辑来看,前提是要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当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来提供必要的可信承诺时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榨取性统治者政权稳固后,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他们会提供必要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改善每个人的收益状况,刺激生产性激励。诚如奥尔森所言,理性的独裁者将会有一种激励,因为他的利益与他的臣民的投资和贸易的增长息息相关,他会许诺永远不会没收财富或否认资产的所有权。理性的自私自利的独裁者选择了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的税率[5]。因此,不同的榨取性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政府承诺难以取信于民,连有限的成长都是痴人说梦。
榨取性制度无法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原因有三:其一,榨取者之间的内讧。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成长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容易崩溃,或者很容易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讧所摧毁。榨取式制度下掌握政治权力就意味着能够榨取巨大的财富,这刺激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结果容易导致内讧。其二,政权不稳导致短视效应。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正严明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然而建立在榨取性制度之上的统治多半难以稳固,随时存在被革命推翻或内部政变而丧失政权的风险,因此其统治行为难免鼠目寸光。这时理性的选择自然是在有限地统治期限内无限攫取、竭泽而渔,而放弃长远打算,最终将导致社会严重地两极分化。其三,生产性激励不足。当政治动荡时,榨取性制度无法提供持久的可信承诺,经济主体的劳动创造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可能创造的越多被压榨的越多。另外,政治单一化也使得平民难以在政策制定中体现自身的意志,财富分配可能面临完全由统治者说了算的困境。
综上,表1中的制度类型按由好到差排序为①优于③,③优于④,①也优于④,②是不存在的。①中的循环图示代表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的良性循环,④中的循环图示代表了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的恶性循环。③中的转化图示代表了榨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下可能存在过渡方向,既可能转化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也可能蜕化为榨取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体制。
既然包容性制度带来经济增长,制度之间也存在转化的可能,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发展出一套包容性制度,或者从榨取性制度变迁为包容性制度?可见,制度类型是固化的,不容易改变,因为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权力结构不变,制度类型很难改变。
四、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
(一)权力结构释义
政治权力由法理政治权力(de jure political power)和实际政治实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构成[6]。法理政治权力指来源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力。例如,今天美国的重要决策主要由民主党制定,这不是说民主党实力远超共和党,而是因为美国政治制度赋予了其政治权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民主党党籍)。也就是说,正式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法理政治权力。实际政治实力代表着一个集团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如果一个集团在暴力威胁、经济财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社会,那么该集团就能拥有实际政治实力。具体来讲,实际政治实力有两种途径获得:首先,它取决于该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其次,它取决于该集团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大小。集体行动的能力代表着集团威胁的可信度,经济资源的大小代表着资源分配的决定性[1][391]。奥尔森早已指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所以将关注点放在资源分配能力上较为明智。权力结构就是法理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实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情况,如果二者趋于均衡,那么权力结构就是理性的,如果二者失衡,那么权力结构就是非理性的。
(二)权力结构决定制度类型
制度类型最终取决于政治实力(political power)的对比。不同制度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但资源分配中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并无法通过承诺克服,拥有政治权力的一方无法承诺不会以权谋私。既然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制度无法通过可信承诺塑造,那么,不同群体将为自身偏好的制度展开激烈争夺,孰胜孰负取决于政治实力的大小,政治实力在较量中扮演着最终裁决者。换言之,政治实力是一个集团的政策偏好能压倒另一个集团的关键。集团的政治实力与其能够从政府政策中收益的比例正相关。权力结构就是政治权利力量的对比,如果法理政治权力完全压倒实际政治实力或者相反,那么就容易出现榨取性制度,如果二者趋于均衡,那么就容易形成包容性制度。
(三)榨取性制度也是理性选择
有些国家或地方将包容性制度束之高阁,而榨取性制度大行其道,唯一合逻辑的解释是榨取性制度符合政治精英的利益,是理性选择。
首先,经济理性导致选择榨取性制度。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的收入分配,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以一系列优越的经济制度取代糟糕的经济制度将会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可能导致某些精英或某些集团的收益情况变遭,成为经济输家(economic losers)[1][434]。当维持现状能给政治精英带来巨大租金时,经济变迁将难以进行。如果制度变迁使得政治权力遭到削弱,权贵们的收入、租金、特权都会随之下降。因此,政治精英将会对每一项经济变迁进行评估,包括评估经济后果(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和政治后果。任何会削弱精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益的变迁都会遭到否定。如果事后不能对权力和权益受损的政治精英给予足够的弥补,他们必定一开始就会以权力坚决抵制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而继续维持榨取性制度,不管制度变迁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多么有效。
其次,政治替代效应维持榨取性制度。在平等条件下,政治强势集团对优越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喜闻乐见,因为经济增长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供榨取和征税。但现实并不完全平等,因为优越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通常会侵蚀精英的优势,降低他们的政治实力,提高被替代的可能。政治替代效应是指:制度变迁或新技术的引入常常带来动荡,削弱政治当局的比较优势,这使得政治强势集团担心失去权力而抵制经济和制度变迁,即使变迁对整个社会有利可图[7]。进一步说,当精英在稳固而又存在被取代的担忧,担心经济和制度变迁可能会动摇既有体系,会壮大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会对未来政治权力构成巨大威胁时,出于对政治权力替代的担忧,不想成为政治输家(politicallosers)的权贵们将会对制度变迁百般阻挠,无论变迁对经济发展多么有利。但也有例外。处于竞争状态或高度稳固状态或外部威胁状态下的政治精英则倾向于采纳新技术。在高度政治竞争之下,精英往往乐于创新,否则就容易被取而代之。在高度稳固状态之下,当局对创新业欣然接受,因为此时不存在丧失政治权力的担忧。外部威胁通常使得当局支持创新,因为技术落后导致国家很容易遭受外国侵入。
五、制度漂移、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美好的制度和美好的生活人人都心向往之,但是,制度变迁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如何克服榨取性制度自我强化和僵化的倾向如何才能实现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和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相互作用的结果。”[3][145]无论是榨取性制度的固化还是包容性制度的起源,都是随机性的历史震荡(historical shocks)的产物。榨取性制度是历史的常态,而包容性制度只是历史的偶然。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纹路的叶子,同样也不存在两个相同制度的社会。无论制度多么类似或相近,或多或少都会在习俗、礼仪、法律等方面呈现出细微的差别。例如,有些社会承认老者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社会则没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这些差异一开始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制度漂移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换句话说,某一个点出现的小差异不一定会随着时间而变大。相反,小的差异发生,但又消失,然后又再出现,等着被下一个关键节点拉扯、放大。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同样,两个本来类似的社会也会慢慢在制度上分道扬镳。制度漂移造成的制度分歧在关键节点出现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节点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关键节点是指一个社会中崩解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时间维度上的制度差异会导致制度结果的差异,这就是政治中的时间问题。皮尔逊认为,如果两个事件或特定过程在某个历史时期同时发生或错时发生,其结果一定有所不同。“错时”就是时序(sequencing)问题,而“同时”则与时机(timing)相关。关键节点就是时机问题。时机问题就是看某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点上[8]。是发生在某个“节骨眼”(conjuncture)上还是发生在无足轻重的关头?在某个紧要关头或“节骨眼”上是否拥有某种技术或制度或重大事件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9]。在关键节点,一个重大事件或许多因素的汇聚破坏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平衡。一旦关键节点出现,那些重要的小差异便是引发极为不同反应的初始制度分歧。当然,较大的制度差异在关键节点会导致更加分歧的模式。可以说,关键节点则是历史的转折点。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不过,这种结果并非历史注定,而是偶然的。制度在这期间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相抗势力的哪一方会胜出、哪些群体能够形成有效的联盟,以及哪些领导人能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来影响事情的方向和进程。概而言之,制度变迁逻辑如下:历史带来社会细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制度漂移不断地拉扯、放大,造成制度分歧,在某个关键节点成为转折点,制度分歧彻底导致制度变迁。这当中,制度漂移是制度变迁的启动器,关键节点是制度变迁的加速器,时序是制度变迁的定位器。只有制度漂移到某个关键节点,并且发生在重要的时机上,才能诱发制度变迁。
六、结论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政党、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治理模式”[1O],关键是离不开共产党这一具有共荣利益属性的组织,这种共荣利益就是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但不可否认,中国政治制度离完全的包容性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唯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包容性制度的建设。一是加强政府集权来构建包容性制度。只有进一步加强政府集权,提高政府承诺的可信度和政府的执行力,使得政府能够在调控市场中发挥更坚实的作用,才能够为包容性制度奠定支柱。二是改善权力结构来构建包容性制度。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制约法理政治权力的肆意。包括将市民社会发育和培育相结合,同时鼓励新闻舆论监督,有效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提升公民的实际政治实力。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提高公民的社会财富,进而提高公民的实际政治实力,谋求权力结构的均衡。三是抓住机会协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犹如制度变迁,成败与否时机很重要。“习李新政”以来,不断强调在顶层设计之下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有效防止“悬浮式政治体制改革”、“碎片化政治体制改革”。上有顶层设计,下有人民呼唤,这是最好的改革良机。抓住这一改革契机,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有利于最大限度消解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成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体现,也是通往包容性制度的必由之路。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是以包容性改革的道路通向包容性增长。
[1]Acemoglu D,Johnson S,Robinson J.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A].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2OO5.
[2][美]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M].李增刚,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OO7:IV.
[3]Acemoglu D,Robinson J.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M].New York:Crown Publishers Group,2O12.
[4]Acemoglu D.Modeling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A].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Theory and App lications[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OO6:1.
[5]Olson M.Dictatorship,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3(3):569-571.
[6]Acemoglu D,Robinson J.Econom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OO6:2O-21.
[7]Acemoglu D,Robinson J.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OO6(1):2.
[8]Pierson P.Politics in Time:History,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OO4:5-6.
[9]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O14,(2):2O1.
[1O]权衡,高帆,乔兆红.复兴与增长:共容性组织推动的经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O11:272.
(责任编辑 刘强)
BO32.2
A
1671-0681(2015)01-0004-06
何瑞文(1987-),男,江西峡江人,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基础部教师,硕士;沈荣华(1948-),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
2O14-O9-2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地方服务型政府建构路径与对策研究》(批准号:O9&ZDO63);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O143O765);湖州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O14XJKY27)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