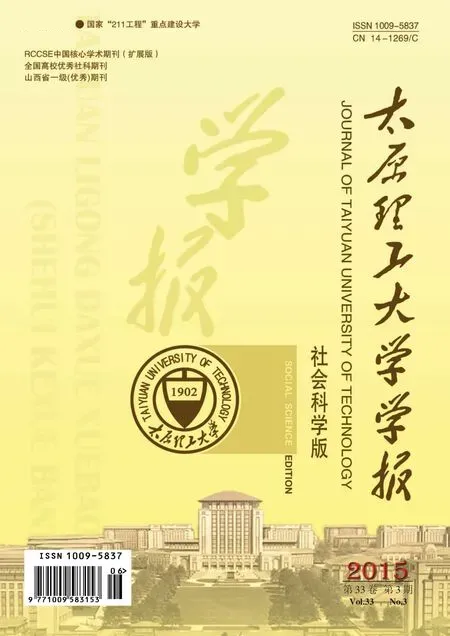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2015-02-11张洪成,苏恩明
风险社会下污染环境罪之处罚扩张问题研究
——以危险行为犯罪化为视角
张洪成,苏恩明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我国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结果本位”的传统立法观念严重制约了对当前环境风险的防范及其有效治理,难以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做出有效规制。顺应“犯罪化”、“处罚早期化”等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学习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罪进行扩张处罚,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即在《刑法》第338条的基础上增设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实现刑法对环境污染防控的前置保护。
关键词:风险社会;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犯罪化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Q2014D02);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
作者简介:张洪成(1978-),男,江苏新沂人,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刑法学;苏恩明(1993-),男,安徽宿州人,安徽财经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04-01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副产品——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诚如日本学者原田尚彦教授所述:“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是伴随着社会的高度产业化而出现的现象。环境问题,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共同的烦恼。”[1]为了有效地防治环境污染,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出重拳强化污染防治”[2]。但是,对环境的预防与治理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的健全与进步才能得以实现。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据统计2013年全国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次数为712次[3]。然而在这些污染事件中,真正受到刑法制裁的却寥寥无几。虽然刑法已经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入罪化处理,但在实践中因各种原因而以罚代刑的现象并不罕见,这种做法可以视为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但由于相关部门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过于滞后,以及刑法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过于含混等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本文拟通过相关的分析论证,来阐述刑法应扩大污染环境罪的入罪范围,将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有造成严重污染之虞的危险行为,亦纳入环境污染罪的范畴。
一、污染环境罪立法之缺陷及评析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了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要件,降低了起刑点,但是究其理念,仍然摆脱不了“结果主义”的束缚。其在对污染环境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制裁时,仍然以实际发生的重大损害结果为前提。立法的阙如必然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如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基于结果导向的思维,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却存在污染环境危险的行为,仅仅采取行政处罚的手段对其加以惩处,以致造成了“以罚代刑”的司法局面。据统计,2013年由于污染环境问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的数量为139 059起[4],而真正介入司法审判程序,并作出污染环境罪判决的案件数量仅仅有109起[5]。极高的污染环境问题的行政处罚率与极低的污染环境犯罪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我国的环境刑法并未发挥预防与惩罚污染环境犯罪的功能,污染环境罪因其自身的立法缺陷而不能实现保护环境法益的宏伟目标。
(一)结果要件的模糊性
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针对刑法第338条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了重大修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将“其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二是降低了入罪门槛,将结果要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两高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更名为“污染环境罪”。但此后,针对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罪形态在刑法理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修正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罪形态仍然是结果犯[6];还有学者认为,经过修改后的基本犯罪形态由结果犯转为了行为犯或情节犯[7];也有学者认为,修正后的基本犯罪形态应为危险犯[8]。虽然学者们各说纷纭,但是,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基本犯罪形态究竟如何确定,在实践中,则完全依赖于执法者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可见,污染环境罪在构成要件上是否要求具备特定的危害结果,本身就是立法尚未明确表述的事项。而正因这一立法的模糊性,必然引起司法适用的无所适从,故对未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对有严重污染环境危险的行为,究竟应否将其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本身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
(二)司法解释的混乱性
2013年6月8日“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既在第1条的1至4项中规定了污染环境罪抽象危险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又在第5至13项中规定了该罪结果犯的基本犯罪形态,并且适用同一档法定刑。这表明了我国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持不同的治理理念:前者坚持传统的结果主义思想;而后者顺应现代刑法理念的潮流,重视对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进行早期的预防。但对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和单纯具有侵害危险的不同危害行为,采用同一个量刑标准,本身就值得怀疑。不可否认,司法解释想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是值得肯定的,但通过这种方式是否合适,有待探讨,因为,司法解释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本身并不是法律[9]。“如果刑法本身的规定不足以惩治环境污染犯罪,可以选择修改刑法,不应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其具有刑法的效力。”[10]因此,鉴于刑法规范的特殊性与严谨性,反思我国刑事法律对于污染环境危险行为规制的缺陷,应在刑法条文中对此予以厘清。
(三)刑罚幅度不能有效鉴别行为的危害性
2013年司法解释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情形做出了规定,既概括了抽象危险犯的既遂形态,又总结了结果犯的既遂形态,并且对于两种犯罪形态均规定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法定刑之下。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并且符合第1条所列举的情形,那么无论是否造成具体的损害结果,均适用同一档法定刑,这无疑是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陈兴良教授认为,危险犯即足以使一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在实质上是因为此种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刑法将其犯罪的未遂形态在立法上规定为犯罪的既遂形态,同时又把这种犯罪本身的既遂形态在立法上规定为结果犯,这样一来在刑法中就出现了危险犯与结果犯的对应性立法[11]。这也就意味着污染环境危险犯要比结果犯的危害性稍小一些,所以两种犯罪形态的法定量刑档应当体现二者危害性的差异。然而在《解释》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两种犯罪形态之间危害性的差异,导致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畸轻畸重,不能满足公众对于法律公平的追求,降低了司法权威及其公信力,不利于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的有效预防与惩治。
笔者认为,面对现代化新型环境风险的挑战,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有关规定已经不能对其做出有效应对,相关部门必须从刑事立法入手,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立法上的治理经验,补充完善我国环境刑法方面的不足:明确污染环境罪结果要件的基本形态,将危险犯的规定合理设置在刑法规范之中;厘清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条文之间的混乱现象,解决冲突的来源;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构建罪刑阶梯结构,针对不同的犯罪形态适用不同幅度的法定刑。
二、域外相关立法经验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困扰着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国家将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摆在优先地位,“然而环境保护的成效取决于人类对环境污染与工业文明这一矛盾体的处理”[7],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因此这些国家格外注重利用刑事法律来规范污染环境的行为。为了防止污染环境实害结果所带来的严重损失,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了关于污染环境行为处罚早期化的危险犯条款,从事后惩治转变为事前预防,这更加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其中又以日本、美国的环境刑法修正的比较完善。
(一)日本的污染环境犯罪立法及评析
1970年日本制定的《公害罪法》奠定了单行环境刑法的基本模式,这部法律被称为大陆法系国家单行环境刑事立法的标杆。《公害罪法》第2条第1款规定:“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活动而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给公众的生命或者身体带来危险者,应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者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12]其规定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危险犯,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先进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对于环境的保护从源头开始,努力提高工厂、事业单位的注意义务,在引起公众的生命或健康的危险时就予以必要的刑事处罚[13],避免了环境污染的出现或扩大,从而实现了法益的提前保护,同时对环境污染也可以起到更好的预防效果,使得工厂、事业单位为了避免受到刑罚的制裁而更加严格的控制污染源的净化及其排放,有力杜绝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
(二)美国的污染环境犯罪立法及评析
美国环境犯罪在犯罪形态上可以分为危险犯与实害犯两种。只要违反行政性规定,即可视为对环境造成了危险,进而可能成为环境犯罪危险犯;而将因违反行政性规定,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他人的生命或健康处于急迫的危险状态下,即视为环境犯罪的实害犯。如《联邦水污染控制法》(Feder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第309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故意违反相关行政法规,或者有关机关签发的许可证规定的条件或限制而非法排放,导致他人处于紧迫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危险,将被定罪,处以不超过250 000美元的罚金,或者不超过15年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14]美国环境犯罪形态的区分是以“环境”作为实质标准,以“他人处于紧迫的死亡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的危险”作为“环境损害”的测量标准。其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环境刑法的伦理观,赋予环境以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人类的利益,这就为扭转“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从更高的道德角度去保护环境[15]。
日本、美国均在环境刑法中将污染环境的危险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基本形态,而当造成现实的损害结果时,则适用更重一档的法定刑。在经受了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报复之后,日本、美国更加热衷于采取刑事立法的手段来应对环境风险,这也体现了两国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的重视程度。从法律实施效果来看,这一举措在整治环境污染的问题上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且由“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预防”的环境刑事立法观念亦成为国际潮流,这些成熟的立法观念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三、我国刑法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独立犯罪化的必要性
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在应对当前环境风险的威胁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足,缺乏对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的有效规制。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有关环境立法的经验,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在刑事立法中明确规定,已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提前保护环境法益的考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个体行为对污染环境的潜在危险不可估量。如果污染环境行为一旦实施,其造成的危害结果往往不可预计。鉴于环境犯罪危害结果的严重性,近年来我国刑法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逐渐加大,然而,事后惩罚的报应思想已不足以遏制行为人犯罪动机的形成。为了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提前保护,不能再以危害结果的出现而作为刑法的制裁标准,而应将污染环境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这样就可以在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严重危害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因危害结果的出现而造成重大损害,并且对于严重侵害社会法益、具有不可挽回的侵害结果的犯罪行为,“处罚早期化”的立法观念对其进行了有效规制。
(二)风险社会下保障环境安全的基本要求
“20世纪以来,随着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刑法体系经历了重大的变迁。正统刑法理论及其研究范式面临来自刑事实践的严峻挑战。”[16]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对未来十年全球风险进行了评估,认为环境风险无论是发生概率,还是全球影响力都位居前五[17]。环境风险已经密布于当前社会之中,刑法作为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对环境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作出有效的应对。而现行刑法对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是以“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结果而启动刑罚权,这样一种事后惩罚的措施虽然能够给予实施环境污染行为人应有的惩罚,但是不利于风险社会的有效防卫,而将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能够降低频发的环境风险,阻断风险向现实损害结果转化的可能性,更加周延的保护了环境法益。
(三)有效地加强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衔接
我国对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制是以刑法典作为依据的,而环境行政法所调整的只是环境违法行为,二者对环境污染的危害性评价是一种递进的层级之分。由于在我国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规定的缺位,所以司法实践中惩治引起环境危险状态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以罚代刑”[18],这就造成了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分离,对于危险状态的规定处于真空地带,致使环境安全受到威胁而行为人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其实,即使环境行政法没有对其作出详细的规定,刑法也应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加强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有效衔接,更加完整地保护环境法益。
(四)缓解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理念冲突
司法解释是为了解决在工作实践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然而刑法第338条相关的污染环境罪并未涵摄危险犯的犯罪形态,无论是依据主观解释论还是与之相异的客观解释论似乎都不能将其通透的解释。这一方面表现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混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立法与司法的脱节,即现行刑法对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已经满足不了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行为惩治的要求。“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19],因此有必要在现行刑法的基础上增设有关污染环境危险犯的规定,以此达到立法与司法的同步,来预防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以保障法律实施的统一。
四、污染环境危险行为犯罪化之思路
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关于环境刑事立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实践需要,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在第338条污染环境罪结果犯的基本犯罪形态之前增设危险犯的相关规定,并且设置与结果犯不同的量刑档。具体规定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处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罪名的确定上,仍以“污染环境罪”来统一命名,而在刑事责任的确立上,应根据不同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区分以下三个层次:首先,环境污染罪的危险犯,若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行为,处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其次,表现为污染环境的结果犯,即如果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具体的现实侵害时,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后,表现为污染环境的结果加重犯,即如果造成污染环境的后果特别严重,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便能有效区分污染环境罪结果要件的差异性,根据不同的犯罪形态适用不同的法定刑,构建清晰合理的罪刑阶梯;并且也缓解了刑法与司法解释之间紧张的关系,为司法人员适用法律时提供便利,也为公民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融洽局面。
参考文献:
[1][日]原田尚彦.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
[2]2015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2015-03-17].人民网.
[3]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4]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3年)[EB/OL].[2015-03-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
[5]郄建荣.去年涉嫌环境犯罪移送案件数量大增以污染环境罪抓捕186人判决109件[N].法制日报,2014-06-13(006).
[6]冯军.污染环境罪若干问题探讨[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9-21.
[7]叶良芳.“零容忍”下环境污染犯罪的司法适用[J].人民司法,2014(18):9-13.
[8]林芳惠.污染环境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93-99.
[9]张明楷.简评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J].清华法学,2014(1):5-26.
[10]闫歌.在污染环境罪中设置具体危险犯的必要性[J].宜宾学院学报,2014(8):72-76.
[1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76-277.
[12]陈英慧,关凤荣.中日环境犯罪问题比较[J].河北法学,2009(12):42-45.
[13][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M].丛选功,徐道礼,孟静宜,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5.
[14]贾学胜.美国对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启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0-68.
[15]陈瑜华、王建明.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研究述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71-75.
[16]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26-140.
[17]钱小平.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J].政治与法律,2014(3):130-141.
[18]董邦俊.环境法与环境刑法衔接问题思考[J].法学论坛,2014(3):128-133.
[19][德]伽达默尔.赞美理论[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46.
A Study of the Punishment Expans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rime in the Risk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Dangerous Act
ZHANG Hong-cheng,SU En-ming
(SchoolofLaw,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ngbuAnhui233030,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legislative concept of “result-orientation” on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s criminal law has seriously restricted current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its effective governanc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gulate dangerous a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ffectively. Going with such international tid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as “criminalization” and “early punishment” and using for reference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such developed countries a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uld be expanded by our criminal law and the dangerous a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uld be criminalized. That is, the basic crime patterns of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uld be added to article 338 of the Criminal Law in order to privide advance prote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risk society; the crim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criminalization
(编辑:陈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