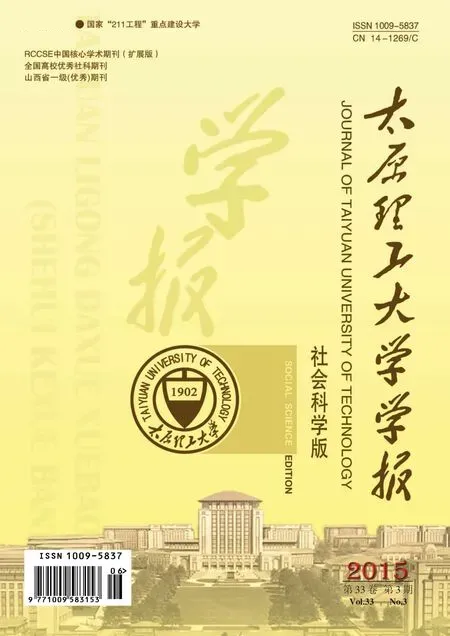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现象成因探究
2015-02-11王帅
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现象成因探究
王帅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纵观中国传统社会绵延近两千年之久的历史进程,几乎一直笼罩在大一统专制王权统治的阴霾之下,徘徊在各式各样的王朝更迭、治乱循环之间,有学者将这种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奇特现象称为“超稳定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以及政治结构之所以具备一种超强的稳定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中国所处的独特的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是这种超稳定性形成的客观条件;基于血缘宗法制度而形成的“家国同构”体制是其主要支柱;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其经济基础;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基于宗法关系之上的伦理道德精神,是为传统社会超稳定性思想文化方面的保障。
关键词:传统社会;超稳定性;家国同构;小农经济;儒家思想
收稿日期:*2015-06-09
作者简介:王帅(1987-),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12-1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其中最具特色也是最令人深思的一点在于古代皇权社会的周期性和循环性。自秦汉以降直至满清政府覆亡的两千余年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演进过程一直笼罩在大一统专制王权的阴霾之下,其间各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市井豪强、农民领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始终无法跳出分分合合、王朝治乱循环以及皇权独揽的怪圈。黄炎培对这一中国独有的奇特现象提出了著名的“兴亡周期律”定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夏曾佑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和王朝式政治格局指出:“秦以来,垂有二千余年,虽百王代兴,进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事修葺,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1]毛泽东也提出了“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样类似的观点。后世学者借用控制论的术语将此现象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超稳定性”。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超稳定性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各家各派的学说观点也是众说纷纭。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性是内涵于其基本特征之中的,是专制王权、官僚政治、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科举取士等诸多因素相互结合、关联互动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和一些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出发去深究其超稳定性的成因。综合相关学者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特征基本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国家构成方面体现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大一统帝国;政治制度层面表现为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笼罩下的科层式官僚制度与宗法制宗族制度相辅相成;社会经济层面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生产力低下、分散的小农经济;思想文化层面主要体现为“定为一尊”的儒学官学化、本土化宗教(佛教、道教等)、诸子之学,以及种种民间学说思想和各类社会亚文化相互融合影响。纵观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作为古代国家统治之本的农民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土壤,始终背负着各级官绅及地方豪强的层层盘剥,同时受制于宗法伦理等被牢固地束缚起来,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作为社会统治核心的各级士人们不敢有违君王天命,内心充溢孔孟道说,或训诂摘句,考究经典,或如履薄冰,徘徊在皇权和卫道之间,或丑态百出,一味弄权;而居于王权社会顶端的君王们更是无一不希望江山永固、延绵万年,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与惧怕人民反抗和大权旁落而无限集权,但结果却总是导致民不聊生,山河残破,君王自己身死国灭。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外在表象。通过对上述特征和表象进行研究,本文就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性的成因提出了几点思考。
一、地理方位的独特性
中外众多思想家和学者都认为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封闭性和内向循环性首要归因于中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位置所带来的影响。与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所代表的西方海洋型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是典型的东方式大陆型文明。中国大陆东濒太平洋,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极为低下的条件下,广阔而神秘的太平洋对于古人来说完全是只能臆想而无法逾越的存在,始终是古代中国人走向外部世界以及形成海洋式文明的巨大障碍;中国大陆北部和西北部气候普遍寒冷干燥,遍布着广阔的沙漠、戈壁、草原和高山;而在大陆的南部有着连绵的崇山峻岭,西南方更是有着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同时,大陆内部中原地带自古地势低缓、土壤适中、气候适宜,非常适合农业种植。这种高度封闭、海陆难渡的环境位置,以及部落聚居的农耕传统是中国古代由氏族部落争斗进而形成封建国家和传统社会政治体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法同大洋彼岸的世界进行接触,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陆内部各部族之间持续不断的血腥战争。对此刘泽华指出:“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战争中逐渐形成了暴力中心,不断将自己周围的氏族、部落联合一批,消灭一批,征服一批,逐渐形成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统治权力和这个政治统治权力能够绝对支配的稳定的地理区域。”[2]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对氏族、部落、分封诸候及其居民进行征服的过程,而这种征服一贯发生于大陆内部,没有任何来自域外海洋文明的介入。
此外,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王朝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一直伴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以及毗邻小国小邦的战争与冲突。从黄帝大战蚩尤直至满清入主中原,中华民族是中原汉民族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而成的一个大家庭,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中原汉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因周边少数民族武装的侵扰或征服而屡遭破坏;同时一些强大的中原王朝也常常用武力或文化征服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由大陆向外扩散,逐渐形成一个广义的泛中华文明圈。无论是中原王朝内部斗争还是与周边民族的冲突,都与中国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除了包围在中原王朝四周的戈壁、沙漠、高山、大洋,历代封建统治者变本加厉地筑修长城、扩大海禁,人为地限制文明空间,加之周边的少数民族和邻邦小国(如朝鲜、日本、安南等)或早就成为中国的臣属,或处在华夏文化辐射地带的亚文化地带,都没有形成高于或根本不同于华夏文明的异质文化。上述这些因素都从客观上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与封闭,从传说中的炎黄时期直至鸦片战争列强扣关,这一现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二、宗法制度联结个人、家族与国家
中国传统社会中广义的“家”这一概念涵盖了家庭、家族和宗族三个层次。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时期,古代中国的小农(诸如佃农、自耕农等)大多世代居住生活在一片固定的狭小土地上,所谓家指夫妇共同生活所组成的人群最小单位[3]。家族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放大形式,它由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构成。《白虎通义》中就说到家与族是以血缘和姻亲这两大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是“同姓从宗合族属”的一种结合,全族的共同组织、全族的男系后裔都包括在此宗体之内,为全族所共宗。族的概念突出了以血统和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关系,而宗的概念则是对一族之中尊卑与服从关系的强调。所谓宗法制度就是基于父权和族权的一种阶级统治形式。刘泽华对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的起源评论说:“古代中国,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以前的原始氏族组织和机构却仍未瓦解,它只是在功能上适应了新的需要,开始以原氏族的机构履行国家职能,即原氏族的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器。”[2]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可以看做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国家这样由无数线条编制成的巨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个人组成的家庭隶属于家族,国家是放大了的家族,作为整个国家元首的君主是全体社会宗族的总家长,故而称之为“君父”。皇族高于普通的宗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特权,族权必须仰视王权,宗族必须依附皇族,宗法血亲关系必须置身于国家的政治影响之下。反过来,家族又是国家的具体化表现,宗族族长和家族祠堂具有“准官府”的统治威慑力,国法通过家法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行使着暴力镇压职能,人们通过家法认识国法,切身感受到国家专政机器的“铁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鉴于此,陈独秀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归结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并进一步指出,“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4]。金观涛将这种现象称作“家国同构”,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发生社会整体崩溃式危机和改朝换代之时对传统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的修复功能。在专制王朝稳定之时,家国同构的体系“把国家的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5]。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社会大规模动乱只能摧毁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千万个体家庭是不可能彻底消失的。广大农民尽管深受封建皇权的剥削和压迫,然而他们在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中却是封建家长,享有自然的父权和夫权。所以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世家望族建立的王朝都自然地以宗法家长制为组织原则建立政权,宗法家族的组织原则就像细胞一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并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可以说血缘宗法制度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一切社会关系均依照宗法关系进行调整,非宗法关系也表现为宗法关系的形式。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在独立的家庭小单元中,以父亲为代表的家长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如子女、妻妾等只能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将家庭放大到宗族的层面上,其族权、族规随之自然地成为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莫大桎梏,个人只是家族的一个细胞,根本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由此推之,金字塔顶端的帝王是天下万民之大宗,君权来源于父权而又高于父权,君臣关系可以看做是父子关系的自然衍伸,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忠”与“孝”被人为地等同起来,具有了内在共通性。这种由家而国的等级从属关系被历代帝王和儒家思想家们用纲常名教的规范确定下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家天下政治社会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本位,通过纲常名教系统巩固并维系这种政治与伦理一体化的社会格局。历代统治者和卫道士们标榜着忠孝双全的道德说教,通过君权、父权和夫权将民众牢固地束缚在宗法社会的网络之中,除皇帝之外,人民无一不在这样近乎无限的约束之下仰人鼻息、战战兢兢地生活。另外,由于宗法制度是家族人伦关系的放大,亲情压过了律法,人治高于法治,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重道德、轻法律的局面,正如荀子所言“有治人而无治法”。直至今天中国人依旧重人情而轻规则,法律精神和规范意识的培养任重而道远。
三、无所不包的专制王权与小农经济的相互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被视为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这个文明的基础是那种稳定的、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劳作和消费单位,以家族作为协作与补充,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式的小农性经济[6]。这样的经济模式贯穿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史中,从未发生结构上的深层变动。而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固是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的,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强大的专制王权一方面为小农经济提供了可行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也极力限制了其进一步自由发展。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凭借暴力建立起来的专制王权要想得到长久的保持除了用军事政治手段之外,最为关键的是控制人的生存命脉,汉朝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将战国时期就逐步固定下来的大田谷作式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土地无疑是全社会的经济命脉,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所以专制国家必须实现对土地的绝对控制和支配,从而保障统治阶级的无限权力与私欲。刘泽华在论及小农经济和土地问题时提出:“封建国家始终握着最高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从来也不曾获得独立的地位和达到完整的地步。土地买卖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它始终不曾突破政治支配形态的硬壳,与自由的商品交换无法等同。”[2]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特权,普遍采取政治高压的方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对其生产进行控制和干预,限制其自由迁徙和自主择业,甚至用各种政策来干预小农的家庭形态;此外,封建统治者强加在小农头上的各种赋税徭役等盘剥方式导致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农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联系,每一个家庭都在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简单再生产,从而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力量,这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巩固自身特权的需要。
正是封建统治的残民虐政、劳民伤财导致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空前脆弱并长期处于匮乏状态,故每到王朝末期由于天灾人祸使得大量破产失业的流民就成为了历代农民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封建统治者不创造任何社会物质财富,其社会经济基础就在于小农经济所提供的一切;同时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维持依赖于人民的普遍贫困和软弱无力,正如卢梭所说,“国王的私利在于人民的软弱贫困并且永远不会抗拒”。所以封建统治者一方面要发展小农经济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另一方面又必须绞尽脑汁限制小农经济的发展并使农民普遍贫困,这样一来小农经济则必然遭到摧毁,也就同时摧毁了权力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每到王朝末期几乎都会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然而却又无法跳出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此外,封闭的小农几乎没有社会往来,在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非常容易被强权所宰割。由于农民对于土地的极度依赖性,使得其牢固地绑定在土地之上而无法产生出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工商业也几乎都是基于农业产品的加工和运销之上,官员和商人也大多热衷于求田问舍、广置地产,因此不可能出现西方工商业资产阶级这种全新的社会力量,也自然无法产生具有改天换地意义上的全面革新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萌而不发,无法向前迈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皇权与儒家思想相互交融
古代中国为世界创造了丰富的思想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首先表现为文化的世俗性色彩浓重。不论是崇尚无为的道家,推崇兼爱的墨家,还是位居显学的儒家,各派思想都与政治权力联系极为密切,注重世俗而不追求神学并将政治伦理化,这种政治伦理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对如何“治人”的思考,人性和人际关系的学说在其中的位置尤为重要。先秦诸子学说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而这些学说几乎都是为“干世主”而作的,各派各家的基本目的都是使当时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学说以实现更好的统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其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儒家学说为主,道、释等思想互补。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实际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主宰和行为规范。然而在封建统治者极力促成儒学独尊和儒学官学化的同时,其余诸子之学更多地在民间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发展及变迁,加之以佛学为代表的域外文化流入中国,这些文化相对于儒学形成了一股暗流。它们一方面与儒学互为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文化有着惊人的文化包容和同化能力,诸子异说和佛、道等宗教思想不断被儒学体系所吸纳,使得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完成了整合并具有了类似宗教的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个特点体现在儒家思想对封建皇权的维护上。儒家学说历经千年而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学是维护君权的思想理论武器,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诸子都极力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并神圣化皇权,从更高的角度维护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同时不断完善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为君主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7]。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儒家的科举制度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介于皇室和平民之间的士人阶层,其作为政治精英进入了政治生活领域。士人作为古代社会四民之首,在朝为官,在乡为绅,上可通达皇权,下可维系乡里,是沟通朝延与民间的重要纽带。
自汉武帝将儒学定于一尊之后,经过后世的不断补充完善使得儒家伦理成为了传统社会政治权威以及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几乎充斥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政治意识全部,其作用之强大足以左右民众的基本政治行为。就士大夫阶层而言,儒家思想毫无疑问地成为政治参与主体的标准并可用来控制官吏的心智和行为。就民间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将整个社会笼罩在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礼教制度之下,用泛道德教化的标准来框约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导致千百年来中国人只知位分尊卑而无法培育契约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内核正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基于宗法关系之上的伦理道德精神,君主统治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政治生活现象存在,而是融贯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王权主义是其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政治与伦理交融的社会中,实现对广土众民统治的最佳手段就在于通过伦理关系来巩固政治关系,利用父权、夫权来巩固君权,将君权、父权、夫权合为一体[8]。在漫漫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至尊,下至贩夫走卒都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下徘徊往复、裹足不前,士人们几乎全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在忠君、卫道、崇圣的界限内翻炒着一些陈旧的思维碎片。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之下,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不会出现变革性的思想和意识,所有的人都被限定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中无法取得知识上的突破进展。
五、走出超稳定的历史魔咒
中国传统社会的上述四项特征,具有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首先,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中国必然趋向一种大田谷作式的大陆性农耕文明;同时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与周边游牧民族等所谓“蛮夷”的长期征战与不断同化奠定了版图的基本格局,直到近代才有根本不同于华夏文明的西方异质文化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终结了传统社会的封闭循环套路。其次,以“家国同构”为典型特征的宗法制度是社会政治结构之基础,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极为严格、社会角色趋于固定化的社会中,个人终其一生都会受到宗法制度以及封建礼教的制约,完全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无论是身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还是芸芸众生,传统社会中的人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过,他们不过是专制社会这一庞大机器中的一个个螺丝钉,而儒家一贯追求的理想也正是一个人人各安其位、各谋其政的静态社会。第三,士人政治和官僚体制是传统社会结构的制度保障。士人毕生钻研并践行儒家思想文化,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实际是对治国安民之类帝王精神的领会,走的也正是儒家先贤所规训的修齐治平的道路;同时由于每一个士人事实上都是其所属的宗族成员之一,他们通过科举制度的层层选拔,从自己封闭的小家族中走出来帮助帝王治理天下。精于伦理教化的儒家学说则是从文化和道德双重角度稳固了家国关系中人们的从属和等级状态。历代帝王都无不格外重视儒家伦理的教化作用,而士人阶层作为古代社会实质上的文化传承者,他们对儒家经典不断做出合理的阐释和修正,把作为统治之道的儒家文明以及历代的统治思想通过文字记载、言传身教等不同方式传递给他们的继承人,从而也就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持久性。最后,相对封闭而趋于保守的小农经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赋税财源,同时这种经济模式造就的一个个顺民也为君主和官僚们创造了绝好的统治条件。
往事越千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终结了千年来传统社会兴亡勃忽的历史命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新生。思虑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全面转型变革之中,如何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建设以及发扬民主法治的精神,如何应对传统文化遗留与现代化价值理念的相互影响及中西不同文化的碰撞,如何在多元化日益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所面临的挑战。在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细致地反思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传统进行深度剖析和整合,剔除其中专制、保守、落后的因素,真正继承和吸收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优秀成果,按照新时代的要求重构民族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这是我们民族时代精神的根基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6:225.
[2]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7,4-5,62.
[3]姚伟钧.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87-92.
[4]李小林.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特征[J].殷都学刊,2009(4):136-139.
[5]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4.
[6]方钦.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J].学术研究,2010(12):79-85.
[7]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37-238.
[8]季乃礼.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宗统”与“君统”的分与合[J].天津社会科学,2000(2):72-78.
A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Super-stable Phenomen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WANG Shuai
(SchoolofPoliticalScienceandPublicAdministration,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China)
Abstract:With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had always been controlled by the unified autocratic kingship, experiencing a variety of dynastic changes and order and disorder cycle, so some scholars called this unique strange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super-stable society.” There are several deep intrinsic reasons for the super stabi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ts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relatively closed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China is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of the super stability; the “isomorphic family, clan and state” system based on the blood patriarchal system is its mainstay; the scattered small peasant economy is its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spirit of eth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patriarchal relationships and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i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guarantee of traditional super-stable society.
Key words:traditional society; super stability; isomorphic family, clan and state; the small peasant economy; Confucianism
(编辑:赵树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