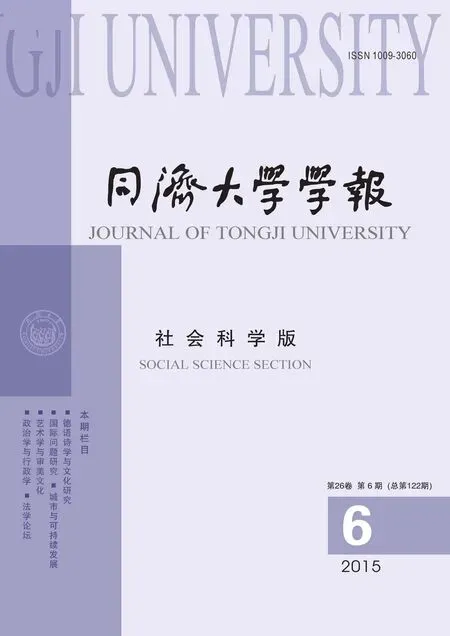雪为谁扫
——论社会治理的四项规则
2015-02-10顾俊杰
顾俊杰
(同济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092)
中国人描述道德高尚之人的标准之一是:无私,忘我,只为他人考虑。最极端的表述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中心主义和泛道德主义价值观之下的要求,其人性论的基础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论。而德治,这一自古至今为统治者所推崇且推行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形态,其根基也在于此。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通常便带有了贬义。虽然不是深刻的批评或否定,但确实对“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的做法含有一种失望的情绪和负面的判断。述说者本身,也是带有对某种现状不满之下的失望甚至颓废的情绪。一个人若如此行为,似乎就有了道德上的瑕疵,社会普遍对这种行为带有一种负面的评判。那么在我们中国,何种做法才是值得推崇的呢?
一夜北风,深雪及槛。早晨开门第一件事便是扫雪。现实与理性的做法是自己把家门口的雪扫清。但显然这不是中国社会所期待的最佳道德状态。在对好人和道德高尚之士的期待之下,“最好”的做法是,早晨起来置自家门口积雪不管,而去扫邻居家的雪。我的邻居也不扫自家门口雪,而是拿着扫把来到我家或者其他邻居家门口扫雪。邻居的邻居再去打扫其他邻居家门前的雪。如果每个环节都没有出错,每个人都拿个扫把去扫别人家门前的雪,那么这个行为最终成就了两件事情:第一,雪都扫清了;第二,每个人都成为道德高尚之人,或者至少是通常所说的好人。这个例子体现了几千年来国人对某种道德行为模式的一种推崇。中国社会也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上演着或希望上演此类故事。
这样一个圆满结局的达成,是以每个人都积极为他人扫雪,从而完成一个行为的循环之圆为前提。只要该循环链条中有一个人出了问题,比如“我今天就是想赖在被窝里不出门”,或“就是没心情去扫雪”,那最终就会有一个人家门口的雪没人扫。或者循环链条中有人存了私心,或者“为什么我卖力帮别人家扫了雪,可自家门口却没人帮着扫呢,那我也不扫了”,于是整个链条就出了问题。这里可以用“道德怨恨”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况。不管是因为自身道德高尚还是为了受到他人赞扬,当人们兴冲冲地做好事,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家门口的雪没人扫时,他一下子就会产生一种不良的情绪,会反问:为什么?凭什么?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所谓的道德怨恨,是因为“各人不扫门前雪”、“要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德背景和话语系统之下会给人一种期待,即我去做好事,别人也帮我做好事,如此形成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圆满循环系统。然而人性并不可靠,现实也不乐观,总会有自私、偷懒或刁钻之人,一旦碰上他们,这样一个道德圆圈就无法完成循环。当一个人做好事是为了期待赞扬而非自我内心道德高尚的体现,那么他必然对一个不圆满的状况产生抱怨和失望,最后会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显然,通过这种归谬,我们发现通过道德方式解决问题可能存有根本性的缺陷。“雪为谁扫”?或者“雪由谁扫”?从这里,我们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四条规则。
一、第一规则——个体权利和责任规则
每个人都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我们每个人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出发,都首先要穿暖衣吃饱饭,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进一步地,还有性爱、健康、长寿、娱乐的需求。这些基本权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谁恩赐的,而是我们每个人固有的,是根植于人性的本能。另一方面,每个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求,享受自己的权利,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想要吃饱穿暖,乃至吃好穿美,必须自己劳动,而非依靠不劳而获或别人的恩赐。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摔倒、摔伤,或防止别人在自家门前摔伤而承担责任,大雪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自己扫掉门前雪。先扫自家门前雪是最基本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他人。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世上绝大部分的事情也就解决得差不多了,因为:
第一,在经济学上,每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是最经济、最高效的。人们做自己的事情通常会用最节省的方式尽快地把事情做好,也会尽力照应好自己的利益而避免浪费。(当然其中可能会涉及把祸水往别人面前引的问题,这留待后论。)
第二,养成“自扫门前雪”的习惯就不会对他人产生依赖,个人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就不易产生奴性,个人也会比较勤劳。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关心、照顾自己的温饱、利益和福祉,尔后通过劳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需求,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三,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依赖于他人不能随意侵犯你的权利。你想要吃饱穿暖,就必须承认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我的“我”,你的“我”,他的“我”,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抽象的“我”的权利。这个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有个体独立的权利,他人也有。所以,虽然在诸多情形之下,损害别人能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当以邻为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你会发现,沟壑到处存在,最后你自己也会深陷其中。因此,你不能以邻为壑,自尊、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满足,必然最终要求你对他人的尊重,至少你不能侵犯他人与你同等的那个权利。
每个人都充分享有自己固有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社会治理的第一规则。这一规则亦可称为自由的规则。根据第一规则,我们反观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我们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期待一个仁爱、全能全智的圣王、明君,以及圣王、明君所带领着的一批贤人、清官。在今天,实际上就是对一个强大而全能的好政府的期待。民众经常问,政府能为我做什么,希望政府能解决一切问题。一旦政府没做或做不到,就不高兴,就可能会发泄,就会批评。我们的政府在民众批评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做错了。我们认为,政府的确做错了,并不是因为做得太少而是做的太多。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所以当它提供不了或者没有提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做错了。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民众与政府同样期待国家和政府能够提供一切、解决一切。这种期待正好解释了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救星意识。求圣王、明君、清官、侠客,实在不行就求观世音菩萨,总而言之,就是不求自己。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必然期待和依赖一个强大的政府。
一夜大雪过后,民众打开门发现雪统统被扫掉了,是谁扫的呢?当然是政府。然后民众就敲锣打鼓地赞扬政府,赞美领导。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对强大的好政府的期待非常危险。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希望不劳而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固然是好,但谁会为你这么做呢?当一个人只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生存时,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一旦被依赖的主体中断对你的支持,你生存的体系可能立刻崩溃。因此当你期待政府为你解决一切问题,包办一切事务,只顾着高兴地接受然后感恩,就会忽视背后的严重问题。一个政府要有能力来解决人民的福祉问题,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样样都要供给的时候,它只能做两件事情:第一是大量地占有自然与社会的财产与资源,变成所谓的公共财产与资源;第二是大幅扩展自身权力,设置庞大的运行机构。这种体制在理论上设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就是国家、政府、政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把财产、资源掌握在手里,没有无限制的权力和运行机构,国家与政府拿什么为人民谋福利呢?
问题是,当国家与政府掌握了主要的财产与资源,便产生了诸多问题。
第一,如何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当我们脱离第一规则,任由国家与政府来接手这一切时,我们得问,财产与资源的再分配、再配置中的公平如何体现?如何避免诸如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福利不平等、教育不平权、各种资源配置的巨大地域差距等不公平?
第二,如何降低国家、政府掌握社会主要财产、资源后导致的浪费与低效?通常来说,理性的人会好好看管自己的财产并加以保护。拿电视遥控器举个例子。笔者曾经看到一位老太太的一台已经旧得不行的电视机,所配备的遥控器仍然用买来时的塑料薄膜包着,因为遥控器是她的,所以她自然要好好护着。个人不会置自己的财产于风雨中而多年不顾。
第三,如何杜绝贪腐?财产与资源是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但国家和政府终究是抽象的机构。最终资源和权力的掌控,须落实到机构中的具体的人。这些人中有决策权、处置权的人,在能够完全处分、支配这些财产与资源时,会如何决定、处置呢?历史与现实给出的答案是变公为私,以公肥私,挪用贪污,腐败横行。
第四,与民争利。国家与政府掌握、利用和经营这些财产与资源,理论上总希望这些资产保值增值。但是在这样一个错误的体制之下,是不可能做成正确的事的。在错误的体制之下保值增值成为政府盈利的借口,从而与民争利,迫使国进民退。这样的治理距离第一规则也就越来越远。
所以,从古至今,当你把权利和幸福交出,期待让他人提供时,得到的恰恰是其反面——奴役!当一个国家与政府承诺为你提供幸福、创造美好生活、成为你的救星,结果就是为了给你幸福而剥夺了你的一切,最终你将一无所有。当你因为人性的懒惰,指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时,你将发现你想要消极和懒惰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当这样的社会出现之时,你就没有幸福和福祉可言,只能成为一个被奴役者。这就是违反第一规则的必然结果。自己的权利、福祉和幸福都是自己的,都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同时为了实现这些权利,每个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这才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不被奴役的人。第一规则是人类的生存、生活、生命及其延续的可靠保证,也给社会奠定了高效、公平的基石。
二、第二规则——交换与授权规则
按照第一规则,各人应当自扫门前雪。但除了门前雪,公共道路、公共区域的雪谁来扫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最好”的、最符合高道德期待的做法,依然还是要有那种雷锋式的道德模范,自家门前雪不管,先扫别家门前雪,扫完后再把公共道路的积雪也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街坊邻里们都夸赞他是多么品德高尚的人。这种高道德的期待背后隐藏的是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忽略和懒惰。话不能明说,于是就通过表彰这些道德模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崇高的目的背后有时可能隐藏着人性的黑暗。
而且,显然这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一来,公共区域的事务甚多,单纯依靠道德模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二来,根据第一规则,既然人人都要走公共道路,这部分扫雪的责任自然是我们每个人的。但是,公用区域不易精确确认,每个人都扫也不经济高效。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处理方法,即委托专门的人或设置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但是这些专门的人或设置的专门机构并不是白白提供扫雪服务的,人们需要支付费用。这既是一种交换,也是委托范围明确的授权。我出钱委托,你出力办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以致人们后来把门前雪也委托给专门的人或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专门的人或专门的机构收了费用,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扫雪训练,设计一些专门的设备,扫雪效率会更高。这样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使我们付的钱更少,得到的服务更好。而且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谈判对象是平等的。这些专门的人或专门的机构要赚钱就得好好地服务于我们,不然我们有换其他人的自由。这种平等商谈关系使价格达到一个均衡点,在我的付出和得到之间达到均衡。你压制不了我,我也压制不了你。虽然,随着社会形态与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店大欺客和垄断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与规则制定来解决的。
这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社会治理的第二规则,即交换与授权的规则。
第二规则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国家与政府。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委托给国家或政府的是什么?执行第二规则不能忘记第一规则:所有的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是我们每个人的,国家或政府本身并没有本源上的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委托给个人,而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机构,我们命之为国家、政府。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让渡哪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给国家?这可以分为“区域上的对外”和“区域上的对内”。对外,国家保障区域范围的安全,也因此建立了军队。古希腊城邦构建起来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安全。那么区域的安全由谁来保护呢?请注意这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必要时,我们可以直接履行该项责任,执戟以卫家园。但是我们也可以将该责任委托给一个国家,因此国家就有责任来维护这片地域的安全。对内,国家的任务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为了保证这一区域内(国内)人民的安全,为了维护国内公平正义的秩序,国家需要建立警察、惩罚犯罪,设置机构维护交易的安全,等等。既然我们授权委托国家做这两件事,那么我们与国家之间就需要有一份契约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份契约就是我们现在命名的宪法。这里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让渡的,是为了国家和政府机构手中有一定的权力来做我们委托的这两件事。为了做好这些事情我们还必须让渡一些经济利益,即通过缴税为政府提供履责经费。收了税,有了资源,又握有权力,便可组建国家机器、组建军队保家卫国。于是专门有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有公职人员来维护公平交易,有法庭做出符合正义的判决,惩恶扬善,定纷止争,最终维护国内公平正义的秩序。
总之,维持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秩序就是国家和政府机构所应当做的事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良好的宪法与行政法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使得整个社会政治关系处于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的秩序状态;通过良好的刑法与刑诉法等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处于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的秩序状态;通过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实施,使得社会的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处于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的秩序状态;如此等等。以财产关系为例,每个人的成功和致富是基于自身的勤奋、能力、人品和对机会的把握,或者是祖上财富的合法延续,而不是利用不公的规则与混乱的秩序把别人的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当我们进行这种交换和委托时,我们一定要明确,国家与政府本身并无立法的基础权利,立法的基础权利存在于第一规则之中,即每个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国家与政府必须遵循这种规则,即依法律行事,完成第二规则和下述第三规则赋予的职责与义务。
三、第三规则——保护弱者的规则
根据第一、第二规则,人们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设所有人都是正常、健康的人。但社会中存在老弱病残幼这些弱者。对于这些弱者,第一、第二规则中责任的承担,不能不分情形、层级而全体适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早晨开门,大雪纷飞,满山遍野都是雪。我有能力自己扫雪,也有经济能力委托别人替我扫雪,可如果邻居是老年人、孩子或残疾人,他们没有这些能力,如何处理?
如前所述,此时并不能依赖道德之士的高尚行为,指望人们的道德是一个不可靠、不系统、难持续的解决方式。但在第二规则中,我们已经组建了国家与政府。所以照顾弱者是国家和政府应做的行为,是它的受托职责。需要注意的是,照顾弱者不是国家和政府的固有责任,因为这本质上来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我们照顾这些弱者,并不是出于我们的同情心,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品德多么高尚,而是这本来就是我们人之为人的责任,是我们的天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去做则不经济、没效率,所以我们按照第二规则,把这项职责委托给国家与政府,从而构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说,政府照顾弱者并非由于它有原初的责任,而是代替我们每个人尽人之为人的责任。国家、政府不应把自己看成救世主。
基于此,我们都不应该期待受到被保护的弱者的感恩,不论是对国家、政府,还是对每个人之为人的个人。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部分利益让渡给国家与政府,最后由国家与政府统一分配给弱者,照顾弱者,让社会中的弱者也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之所在。而且,保护弱者不仅是人类每个个体的本源责任问题,也是利益问题。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和谐,比较温暖,也比较安全。保护弱者是一个社会建立公平正义秩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基础事项。其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福利而言,亦具有增益的作用。
四、第四规则——仁爱与善行的规则
如果不能遵循第一、第二、第三规则,每个人都指望着他人的爱之奉献来扫尽天下雪,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一个系统、可靠、公正、可持续的治理。但是,如果前三个规则都得以遵循且运行良好,就能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制度性保障,社会就会获得一个相对公平正义的秩序和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此情形下,仁爱与善行等道德的方式将会成为建立美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佐力。因为,鉴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及可持续性,根据第三规则提供给弱者的只能是一个保证其享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而不可能是一个优裕的生活;公平正义秩序和良好生存环境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自然性与社会性灾害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因此,仁爱与善行的规则就是不要试图以这种道德的方式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手段,放弃建立道德理想国的梦想,在第一、第二、第三规则之下,起辅助性的作用。同时,它还需遵循以下规则:
自由的规则爱之奉献或善行出于自由的选择。以捐款为例,捐与不捐,捐多捐少,自由决定,非强制,不逼迫,不绑架,无压力,甚至少有群体氛围鼓动下的从众行为。如我们现实中所时常看到的逼捐、铁公鸡榜等,都是道德中心主义及泛道德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绑架行为,违反了善行自由的规则。
慈善制度化慈善制度化的首要规则就是非政府化,国家与政府的任务在于努力践行第二、第三条规则,此其正业。慈善应交由民间来组织、运行。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可以发起、组织慈善活动,成立慈善组织。任何人,尤其是政府,不能试图垄断慈善。其次,非利益化,慈善应当与利益脱钩。任何通过慈善植入广告或宣传企事业单位影响、推销产品等行为都不能被容许。如我们时常所见,电视直播中以单位之名高举巨大支票,或通过捐款给某慈善组织,然后用此捐款购买自身产品用于捐赠等做法,都是应当禁止的行为。庄子曾说,天下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很少,而从仁义之中取利的人却很多。(《庄子·徐无鬼》)仁爱与慈善不能被利用成为一种谋利的工具,不能成为“仁术”,更不能成为诈谋之术。
论迹不论心仁爱与善行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不追问行善者的动机,而只考察其行为事迹。社会当然需要出自内在良知而自愿选择善行的道德、人品高洁之士。但任何人,只要他没有借慈善谋利,善行本身合法,都应得到正面的评价,而不必追问他的动机。据此规则,善行不以追问这个人是否道德高尚为前提,甚至都不问他曾经干过好事还是坏事。即使是作恶多端的坏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一个自己饿着肚子的逃犯看到路边黑幽幽的小手在乞讨时,将自己仅剩的干粮递了过去,这就是人性之光闪现的时刻。
仁爱与善行不倡导损己利人“损己利人才显出道德高尚”是错误的传统观念。损己利人只能是少数特殊情形下的非常人的非常行为。常态之下,不应当提倡损己以利人。损人利己为法律所不容已为常识,善行以不损己利人为前提亦应成为常识。惟其如此,慈善才能成为众人之事,可持续之事。
推食以食人,推衣以衣人,各人不扫门前雪,专管他人瓦上霜,不是所有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的,能做到者一定是极少数的圣人。普通人甚至连经常做到都不可能。但一定是有的人在有的时候能做到。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的概率很低,经常或偶尔做点好事的概率却很高。我们要提倡的就是让大家经常做好事,不要试图有那么一种理论、制度、体制或舆论迫使所有人一辈子去做好事。善行应当是圣人能做,凡夫俗子也能做;好人能做,坏人也能做;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多做也行,少做亦可。力所能及,轻松自由,无强制,非逼迫,不绑架,而不是像我们时常所见到道德模范、榜样那样苦哈哈地被架在火上烤。做好人在大多情形下应当是轻松愉快的,甚至是优雅从容的。好人不必是苦哈哈的,不必是一个个都背负着天大的责任,不必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不必感天动地。
从而,因第一、第二、第三规则得以遵循且运行良好,而使善行得以处于此等自然、自愿、自由的状态之下。社会鼓励行善做好事,但不依赖于行善做好事。亦因此,生存环境将日益变得自由轻松,社会氛围将会日趋温润和谐,社会道德水准亦将慢慢得以提升。
社会如何治理,人类一直在探索和选择。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如孔子,主张行仁义;孟子从人性善出发,主张行“仁政”。中国历代德治礼教的基点也正是在这里。儒家曾宣称上古有一个礼教大行的道德黄金时代,孔子在《礼记·礼运》曾描述过这个时代,即所谓圣王治国的大同之世。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希冀依靠哲学王之治建立正义理想国。东西方似乎都曾有过这样的理念,即世界应当由这样的人来统治,他道德高尚,天然赋有正义,既是一位圣人也是一个智者,同时又是全体子民的父母。在这样一位道德之王的治理下,每个人都成为道德高尚者,从而一国也成为道德之邦。可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证明,这个办法好像并不高明,也更不现实。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道德理想国。柏拉图最终转向了法律,认为法治才是现实、可靠且能实现正义的治理。而中国,情况似乎更糟。谭嗣同所言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形:“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仁学·二十九》)“乡愿”即伪善。而鲁迅则更是直言道德礼教吃人。但是,道德之治的失败,似乎道德本身并不需要承担多少责任。我们批判的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泛道德主义与超道德主义,是德治天下的幻像,批判的是让道德去做它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当道德无能为力之时,德治天下者就只能依靠欺骗、撒谎、瞒天过海,伪君子也由此产生。当道德老是开空头支票,甚至以诈术欺民时,人们当然会渐渐地看低、贬损道德。最终让道德蒙羞,为人们所轻污。道德应当是个人内心良知的自由选择,并非追求所谓比金杯银杯更可贵的口碑,更不是去做一些看似道德的而实际谋利甚至作恶的事情。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更为复杂,更为开放、自由的现代,依靠道德说教、欺诈、愚昧民众来治理社会,更是一条不可能达成目的的治理之道。依法治,依规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治理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