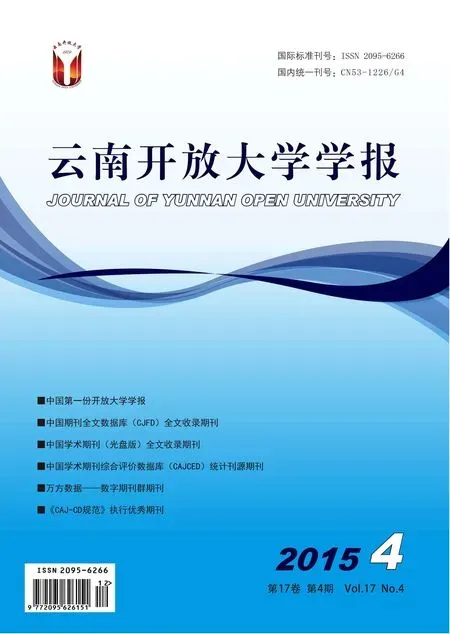浅论苗族服饰的美学思想和审美创造——基于昌宁苗族服饰造型艺术和视觉色彩的田野调查
2015-02-09蔡红燕
蔡红燕
(保山学院 学报编辑部,云南 保山678000)
美学是以审美心理出发,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服饰美学是美学的广泛意义指向服饰的对象化过程和结果。作为2006年首批入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昌宁县苗族服饰,其美学观念和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一样,与以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服饰注重自然体形的“随体之美”不同,在具有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美学观念的同时,在造型上也体现着滇西南苗族服饰所具有的个性化特征,服饰重彩、绚艳、繁密,是昌宁县苗族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一、苗族服饰造型艺术的美学思想
在审美现象学规律下,客观事物、主体结构、文化场域中建构起了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和审美场。作为服饰的主体,面对源于内在必然性而反复出现的客体物象苗族服饰时,“就会把这一对象指认为美的对象,并进而认为美是这一对象固有的性质。同时,他也形成对这一对象产生美感的心理定式。”[1]昌宁县苗族服饰以H型的“对襟披肩裙装型”盛装“十八件套”为代表,充分体现了当地苗族的审美观念。
(一)美型建构:苗族服饰造型的美学观念
1.吾型吾美:建构与解构
昌宁苗族的“对襟披肩裙装型”之美,已经被认为是这一客体的固有性质,并在主体心灵中塑型、确立与固定,美与美感已经客观化和符号化。据资料记载,苗族的“对襟披肩裙装型”的造型是从对襟裙装型服饰为基础发展过来的,苗族服饰的造型美成为具公共定义性和公认客观性的美的本质的事物被建构起来,只要不被解构,就一直不会被主观感受所简单转移。
2.天人合一:自然性与社会性
服饰美学以自然和社会为美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想。昌宁县苗族服饰将自然之美与社会之美集于一身,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现。
苗族服饰的制型之材主要原料是麻。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来看,中国最早以丝麻织物为原料的服饰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这是中国服饰的起始期[2]。当时的原始农业与纺织业,为制衣提供了最初的人工材料,用野麻加工麻缕织成麻布,用骨针、纺轮、葛藤制成衣裳。昌宁苗族所在的土皮太村、打平村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百褶裙的传说》。马克思曾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3]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的“对襟披肩裙装型”是“美用一体化”的造型。百褶裙既实用,便于人体行动;又美观,如盛开的一朵“伞花”;还皆具记述性,追溯着服饰发展的足迹。
在中国古代,血缘宗法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衣服形制确立后,人们人们都按照这种式样穿着去祀天地、祭鬼神、拜祖先。部族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得以较有秩序地进行,因而天下治。”[4]昌宁苗族服饰是抛却主流社会服装时尚与流行的常识性审美,其趋同化审美要远远大于个性化审美。苗族服饰的型式不仅标族别异,而且根据性别、年龄、婚姻、场合等方面来对具体型式加以规定。“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5]。在特定族群中的服饰穿着,既是一种伦理守德,也是一种审美心理使然。
(二)错彩镂金:苗族服饰造型的美学风格
昌宁县苗族服饰的美学风格是在特定的苗族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经济文化和苗族民间艺术文化氛围中铸就的。其中,题材要素、功能要素和文化要素是促成昌宁苗族服饰美学风格的主要要素。昌宁苗族服饰美学风格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嬗变性决定了自身形式表现上的个性定向,而稳定性无疑是昌宁苗族服饰审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昌宁苗族服饰分成日常便装、“一等盛装”、“二等盛装”3种基本型,总的来说,风格单一,不多样化。每种类型都有一定款型和样式。由于昌宁苗族服饰尤以“一等盛装”为代表,所以,现主要以此服型作为美学风格的分析对象。
1.错彩镂金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曾言,中国美学有两大风格,即“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6]。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以繁复为美。从款型上说,昌宁苗族服饰为上衣下裙,上衣对襟无扣,外套挑花女褂,百褶裙上系大围腰和小围腰,宽衣博带,层次丰富;从加工上说,绣工紧致细密,装饰考究,造型华丽,色彩绚丽,丰盛而张扬。
2.雍容端庄
昌宁苗族服饰盛装具雍容风格,更适合于隆重场合穿着。一是就质地来说,采用底色素淡、结实紧密的麻布,厚重而不飘曳;二是从款型来说,不重人体贴身效果的剪裁方式,主要靠裙、围腰的“系”来有限地突出腰身,适体的灵活度稍弱而仪式感稍强;三是昌宁苗族服饰虽重彩点缀,夸饰却不浮华,“板”而不“飘”,端庄大方。
3.闭合内敛
昌宁苗族服饰的款型将人的身体骨骼和曲线等自然状态掩藏,呈一种内敛和闭合式审美风格。在服装的三维空间中,款型中所需要的服装的结构线、装饰线,更多的是为了连缀布料而服务,没有为了重视和加强身体某一部分的肩、胸、肘、腰而特别作设计,而最能吸引人们视线的外型轮廊线,也让位于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大面积挑花。平面的单件服饰组件,联缀组合成苗族服饰穿着的立体效果,因此,具闭合内敛的同时,又在闭合中含有开化,内敛中含有炫耀。
4.动静相宜
昌宁苗族服饰兼具动态美和静态美。黑格尔曾将服饰称为“走动的建筑”。服饰造型的动态美是服饰造型附着于服饰主体的运动,由动感传达出美感的过程。
(三)从规依律:苗族服饰造型的美学法则
服饰要具有造型美,就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美学法则,来形成各种形式因素,如图案、线条、组件、形体等有规律的组合。
1.意法统一
苗族服饰造型的美学法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整体和局部。从整体上看,主要是服饰的符号意义要与适当法则相统一;从局部看,主要是视觉艺术的一些法则的表达与满足。整体上是偏向于“意”的层面,局部上是偏向于“法”的层面。
“意”是意义,“法”是法则,服饰之“意”,是昌宁苗族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创造在服饰上的反映,“法”是反映主观理解和创造在服饰上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表达。简单的说,“法”是为“意”服务的,“意”要用“法”来表达。而“意”、“法”之间的媒介,就是服饰之“型”,呈一种“意—型—法”的关系,如果再清楚的陈述,那么,就是“意:昌宁苗族服饰”——“型:对襟披肩裙装型4式”——“法:昌宁县苗族审美法则”。
2.二律皆备
昌宁苗族服饰造型的美学法则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的特征,以及昌宁苗族对于客观事物和主观世界的理解。“所谓形式美的法则不过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现实中许多美的形式的概括与反映。形式美的法则不仅来源于客观事物,而且研究这些法则是为了创造更美的事物”[7]。服饰的形式美,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服饰的型式美。
AAGCTCACTGG-3’;lncRNA BLACAT1(product length=120 bp) Forward 5’-GAATCGGACAAGGA
(1)比例与分割
昌宁苗族服饰的造型剪裁对合体要求不高,但依然是有一定比例要求的,这种比例主要是根据所穿之人的体量来确定衣、裙、袖、包头等的相关尺寸。昌宁苗族将服饰分成长袖上衣、领褂、百褶裙、大围腰、三角小围腰、腰带、飘带、披肩、绑腿、包头、绣花鞋等不同造型组件,还要用不同的布料进行分割,比如衣袖可以用若干布料拼接,即裁好后设定绣样用不同手工来合力完成。
(2)对称与均衡
昌宁苗族服饰中遍布着以服饰中心为中心点,或由点延伸为中轴线,两侧对等的对应关系。许多具体的服饰组件,比如两侧衣袖长短对应,但两边袖上花饰图案,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以均衡为美。
(3)对比与协调
昌宁苗族服饰造型上对比关系明显,组件的大与小,绣颜的明与暗、质地的麻质板结与装饰坠物的飘曳等,在对比中求协调。整件服饰图案整齐均称,但又不拘泥于某一特定构形,它能使方与圆、平与尖之间形成鲜明的反衬与对比。就整体来看,多图案、多组件、多色泽、多质地的组合又是协调的,杂而不乱,多而有序,这主要缘于有其他诸如对称、均衡、稳定、韵律等法则的相互配合。
(4)节奏与韵律
服饰上的线条和结构,是具方向感的,因此也就呈现出运动过程中连续性的、有规律的排列组合的起伏感和韵律感。昌宁苗族服饰上的刺绣最能反映这一点,那些反复、交替、连续的图案,是服饰型式上最具节奏感的跃动音符。
另外,昌宁苗族服饰造型生活装崇素朴,盛装倡华丽,除以上法则外,还具有整体与局部、繁复与简单、变化与稳定等美学法则。这些法则彼此关联,不可偏废,辩证统一。所以我们认为,昌宁苗族服饰体现出的审美范畴,二美皆备,互通途径。应该说不止是昌宁苗族服饰,两两相生,相反相谐,也是人类生命所追求的和谐状态吧!
二、苗族服饰视觉色彩的审美创造
“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他已经在自己周围创造了被称为文化的第二自然”[8]。从视觉角度看,服饰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不是款型,而是色彩。昌宁苗族将色彩作为“文化的第二自然”来加以经营,使之成为一种色彩艺术的审美创造。
(一)以美为彰:服饰色彩中的审美理想
康德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理想学说。审美理想是美学的核心问题,理想是一种无限延伸之境,注重形式,关乎人生。审美理想以人的族类生存的内在目的性为内核,获得了丰富多样的具体形态[9]。审美理想在人类共同性和多元层次性的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昌宁县苗族将对美的追求的内在目的性见诸感性形态的服饰,色彩便是民间民族服饰艺术美的具体化和物态化之一。从审美理想对审美创造的作用来看,主要是导引和内驱两方面。
1.导引:族群在色彩世界中的自我确认
昌宁苗族服饰色彩观是社会观念的产物。红、蓝、绿、黄、白“五色”,以及黑、橙、紫等色,自由的运用于服饰,是一个历经千辛的迁徒民族在服饰上摒弃等级纲常的平等宣言。苗族古歌吟:“黄河把金色披在身上,苗家是黄河的子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黄色穿在身上。”苗族古歌赋予了色彩本原意义的背后,唱咏的是一个流离失所、飘泊族群的浓浓哀伤。
杜威曾说:“由于我们常常不考虑现在而考虑过去与将来,把对过去的回忆与对将来的期望加入经验之中,这样的经验就成为完整的经验,这种完整的经验所带来的美好时期便构成了理想的美”[10]。环境封闭、远离统治阶级章采有别、差序尊卑、礼制等级服饰制度的苗族,将对历史的记忆、对祖先的情感、对土地的热爱,化成服饰上鲜艳夺目的色彩,实现苗族自我的存在感和色彩审美价值观的有机整合,“‘五色’为基”的色彩审美理想便由一种族群集体性的情感态度、审美体验所肯定的色彩观念尺度和范型模式,建构在苗族的社会实践中。
2.内驱:本质力量的感性形态对象化
在《创造的秘密》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瑞提曾说:“理想实际上在创造力当中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11]。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五色”为基,多色为辅是整个社会集团的审美关系实践活动,这些生动的色彩来源于昌宁苗族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由于不是个体化审美差异的强调而是消融,这时的色彩审美感知比审美趣味要来得广泛;由于不是短期时间断面的呈现,这时的色彩审美体验比审美趣味要来得深刻。因此,服饰色彩中的审美理想,对苗族服饰的审美创造,产生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二)主观比附:服饰色彩中的表情意义
心理学实验表明,当人置身于不同墙壁色彩的房间,即使被蒙上双眼,情绪也会出现不同波动,这时,被称为具有“非视觉的视力”,以此证明色彩能够产生与人的互动。除去表层的视觉感知,还有深层的情绪和情感的影响。由于色彩有非纯视觉的表情意义,色彩由一种知觉形式向逻辑推理方式和思想认知图式转换。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以自我的理解将大千世界的五颜六色运用于服饰,客观物象通过主观诠释以一定的形式表达着一定的内容,象征性、寓意性的比附着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和心灵世界。
1.主观映证
在昌宁苗族服饰上,色彩成为了一种观念性的阐释。有历史意义观照:黄色的黄河、红色的血战、蓝色的海浪、绿色的山涧、白色的皑雪,五色,表达着族群历史的流离;有宗教意义映证:红黄白绿四色交替的短横条纹下以桃红、绛紫、黑灰、茶褐等各色彩线缨子,是对祖先盘瓠的崇拜与追忆;有功利意义附会:昌宁县苗族在明暗、暖冷颜色间,日常中更推崇明与暖。色彩与自然、社会,包括人生的诸多方面相关联,被比附概括为吉利、喜庆和祥瑞,或趋利和避害。大红吉时、白素悲时,便是对经过引申、转义后的颜色的崇尚和忌讳。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的日子里,身着鲜艳的色泽表达着宜子益寿、招财纳福,而清寒的色泽适合于崇神奠祖、驱邪禳灾。合目的性的映证中既是主观唯我,亦有理性积极,既是生活需要,也为意愿满足。
2.多元情结
中国古代,华夏民族指“象物生时之色”为青,“晃晃日光之色”为黄、“太阳之色”为赤、“冰启时之色”为白、“晦冥之色”为黑[12],尊五色为“正色”,且黑赤青白黄“五色”还与水火木金土“五行”、北南东西中“五方”、冬夏春秋长夏“五时”、寒热风燥湿“五气”、恐喜怒忧思“五态”、智礼仁义信“五性”相关,在《黄帝内经》中,颜色甚至与人体、动植物、时节、声音、气味、数字等相对应。昌宁苗族则以“红、黄、蓝、绿、白”为五种最重要、最基本的颜色,它们是苗族先民意念中颜色的创始色。不仅如此,昌宁县苗族在“五色情结”的基础上,还有着色彩的“多元情结”。
首先,“一等盛装”作为昌宁苗族服饰的代表,建构起族群最易识别的服饰特征,服饰上是多色的斑斓并陈。其次,便于生产与生活的日常便装中有多色的拼接与刺绣,常处于服饰的某些部位,比如破袖后的一道彩饰,领口的一圈花样等。再次,昌宁县苗族服饰依年龄而有所区别,有的老年苗族妇女服饰,多取五色中的某一色泽作为主色,再以其他色辅之。
3.摄情取色
摄情取色指昌宁县苗族主要从主观印象中摄取色彩。摄情取色往往能够把握事物的原色特征,取其核心,同时加以变色处理。
日月辰昏,四时更替,斗转星移,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就取其春色之翠、夏色之粉、秋色之金、冬色之皑,不求自然物象的真实模拟,不讲空间主体的明暗透析,用色彩平面的刻画“意足不求形色似”。所以,我们能够在苗族服饰上看到绿色的蝶形图案、红色的蛙形纹饰、黑色的菱形花朵。夸张和写实、变形和变色的表现手段,是昌宁县苗族服饰民间艺术的造型和用色传统。
(三)以技为用:服饰色彩中的技法特征
昌宁县苗族服饰色彩使用以伦理化和宗教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依据,设色技巧追求视觉心理效果,用一定经验性的、主观唯我的技法特征来完成审美创造。
1.符号化
首先,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的色彩词汇是参与族群标识物积极建构的主要成分,这便使那些普遍使用的颜色具有了符号化特征;其次,昌宁县苗族服饰除布料本身色彩外,色彩还主要应用于纹饰,一方面造成色彩具有工整感;另一方面,与纹饰一起体现着符号化特征;第三,昌宁苗族服饰有基本颜色词,且多取单纯色,鲜艳、明快、热烈。与其他色彩交融使用,敷色之繁,以繁述繁,繁而不冗,变化中求统一,整体上有“满”之感,想象空间少,视觉冲击度强,这也是“盛装”能成为昌宁县苗族族群符号性标识物的原因之一。
2.程式化
汉族民间美术设色有“红配绿,丑得哭”、“红搭黄,喜煞娘”、“黄白不随肩”、“青紫不并列”等口诀。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了解到昌宁县苗族服饰在配色方面的相关说法,但在配色设色上,是有一定程式和规范的。
首先,取色齐整。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上的颜色一经取用,大至整块布料,中至某一部件,小至图案纹饰,总是整块或次第出现的,不会有单个色块、色条、色线出现就中断的情形。其次,以面分切。昌宁县苗族服饰的色彩基本依图案纹饰进行面的切割。这时的面,除去大块布料颜色外,基本是以条状进行面的色分。往往横形条状多于竖形条状,面与面,或者说是条与条之间,可以彼此拼接,但单个面或条,上面的颜色循回出现,属于同组,有意思的是,同组的色必须重复往回,但不同组的面与条,却几乎在色彩使用上没有联系,不需要一定取他组中的色彩来使用,只共同服务于服饰的整体色泽和谐即可。第三,设色不均。这里的“不均”,指的是设色用力的不平均。我们如果以“盛装”为例来解读,完全可以看出服饰色彩上以“红”作为主打色。朱红、梅红、桃红、桔红、粉红、枣红、土红、紫红、棕红、绯红、铬红、绛红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远视身着“盛装”的苗女,映入我们的眼帘便为衣饰上的一片红;还有,“黑”也不可偏废,因为黑布要与篾圈一起制作成“敢蒿”戴于头;此外,白布鞋底红鞋帮,是绣花鞋最常用的制材色彩。
3.装饰性
昌宁县苗族服饰色彩具有装饰画的色彩特征,从事物的固有色出发,重视色相、纯度和明度的对比和调和,重视平面空间中色彩的对比,不重视事物固有色、环境色和光源色的相互关系,不体现事物的三维空间透视。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多使用色彩纯净、饱和程度高的色彩来装饰衣物,在色相中,使用原色多,间色与复色少。并且用色彩明暗和深浅、色彩面积大小形成对比,通过色彩的醒目、突出效果,使之发挥色彩的特有张力,对象化地产生丰富、生动、绚丽的服饰色彩移情想象。
总之,造型艺术和视觉色彩之于苗族服饰,有着丰富的审美性,内在性质得到了延伸与拓展,对之进行现象描述与审美体悟,可以帮助我们从审美的感性外观层到文化观念层,更深地体会苗族以积极地审美创造去内化服饰审美的典型化、本质化的精神,有利于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更贴近他们的现实审美需求,开展有效的文化保护活动。
[1]张法.美的建构与解构——从美学原理中的三大问题谈起[J].晋阳学刊,2011,(6):57-62.
[2]兰宇.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特征[J].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学院,2007,(5):591-640.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论[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0.
[4]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450.
[5][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78.
[7]杨幸,甘霖.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4.
[8]高尔基.论“渺小的”及其伟大的工作[A].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71.
[9]胡家祥.论审美理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6):1-7.
[10]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226.
[11]阿瑞提.创造的秘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24-246.
[12]刘熙.释名(卷四)[M].台北:台北育民出版社,197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