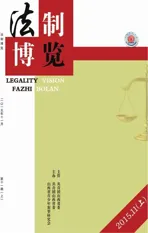完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问题的若干探讨
2015-02-07刘苏婵
刘苏婵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5
完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问题的若干探讨
刘苏婵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110035

摘要:2015年8月20日,首次由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多个政法部门针对律师工作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表示,如果无视律师的合理意见,错案发生几率就会上升,中央政法各部门要充分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将法律已规定的律师会见通信权等落实到位。笔者拟依循从理论到实践的思路,先分析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的必要性,再针对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存在的问题作出检讨和分析,最后对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提出了若干思考。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合理限制

一、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必要性
(一)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是实现有效辩护的必经途径
二战以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观念频频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公约中。具体到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最具标志性的立法体现是赋予了律师的刑事诉讼辩护权或者说是大大充实了律师的刑事诉讼辩护权。极具代表性之一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都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来准备他的自我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与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辩护关系属于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信赖关系,犯罪嫌疑人只有充分接触律师,并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才能达到有效辩护的结果。律师通过与犯罪嫌疑人接触,可以了解到侦查机关针对其开展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资讯,从而深入把握案情,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制定进一步辩护方针。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是实现刑事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地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地防范冤假错案发生。实现程序正义、司法公正,需要形成控审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的三角结构,而保持诉讼三角结构稳定的关键之一,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组成的辩护力量能够与代表国家的控诉力量对抗。如果律师的辩护权在侦查阶段不能充分发挥,控诉就会偏离它的应指方向,程序正义也将无法实现。《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题为《刑讯逼供调查报告》的文章显示,47.54%的警察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利会见当事人,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会得到一定监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会被激活。自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很多律师都反映检察机关加大了对办案机关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在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检察机关共受理律师控告办案机关阻碍刑事诉讼权利案件4109件,通知有关办案机关纠正3372件。
二、现阶段律师会见权存在的不足
(一)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受限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并未对具体的会见时间、次数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一般要求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会见两次或三次当事人,每次会见的时间也有具体的要求。超过规定的次数之后会见将不被准许,超过规定的时间也将会被打断。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今年8月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律师反映较多的问题是贿赂案件的“会见难”。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担心影响侦查、泄露案情,以“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为由,不安排律师会见,或者将律师会见时间限制在半小时之内。新刑诉法及相关规定未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作出规定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案件的复杂程度而不宜作出统一的规定,目的是让侦查机关根据具体案情作出不同决定,而非允许办案机关肆意限制会见时间和次数。
(二)“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不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具体到实践,这一规定增加了侦查人员的办案难度。首先是侦查机关的同步全程录音录像问题。刑诉法规定了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录音或者录像,并且要保持录音或录像的完整性、全程性。这与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产生了冲突,同时引发了操作层面的问题,如律师介入后,全程的录音录像是否中断、被“中断”的录音录像如何“衔接”等。其次是在监视居住期间,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可以对被监视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而当被监视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其辩护律师时,执行机关还是否可以继续进行监控、监视,法律并没有给出规定。还有,在会见不被监听时,在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出现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甚至逃跑等安全责任的归属问题。
(三)律师会见缺乏有效救济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律师救济的途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刑诉法虽然完善了律师诉讼权利遭到侵害时的救济程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失衡情况。究其根本是缺少中立的裁判者。同级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是律师权利遭到侵犯时的救济对象,而本质上其又属于侦查机关,均难以担任中立裁判者的角色。此外,法律规定的律师会见权遭到侵犯后的救济方法是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如果此时案件已侦查终结,移交起诉,这种方法对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是无法救济的。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6条规定,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检察机关违反上述规定,在未安排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的情况下就将案件移交起诉,那么即使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得到救济,但案件已经进入到审判阶段,此时的救济也只能是迟到的救济。
三、解决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问题的途径
(一)确立“眼可见而耳不可闻”原则
在完善“会见不被监听”方面,可以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眼可见而耳不得闻”原则。“眼可见而耳不得闻”即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存在保密特权,仅可以监听,而不可以耳闻其内容(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方式)。将“眼见而耳不可闻”原则运用到我国,能有效化解会见不被监听与侦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监视居住时的电子监控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能避免律师在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出现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甚至逃跑等情况。从2012年6月开始,宜春市公安局先后斥资600余万元,对看守所进行了升级改造。1月28日,宜春市看守所所长赵铁汉向《新法制报》记者介绍说,该所共建了4件律师会见室,并且安装了视频监控探头,但没有安装监听设施。办案机关可以采取宜春市公安局的做法,建立专门的律师会见室,并安装视频监控器,但是不可以有同步录音。
(二)完善会见权救济制度
从世界各国司法实践来看,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律师的执业权利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延伸。当律师的会见权遭到侵犯又缺少相应救济时,律师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无法保障。因此,当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权遭到侵犯,向检察机关提起申诉、控告时,检察机关要敢于拿出态度,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力保障权利。可以在检察机关中设立专职救济部门,其任务就是保障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权利,确保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纠正。这个专职部门要同案件的侦办部门或者案件的起诉部门分开,一旦发现侦查行为在办案过程中侵犯到律师的会见权,应及时作出强制命令,责令相关的侦查机关、看守所立即满足律师的会见要求。
(三)规范律师职业伦理
律师执业行为是否规范,不仅影响律师职业的整体形象,而且影响公众对法治的信仰、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律师职业伦理,对律师违法违规行为都有严厉的惩戒措施。例如,在2011年,美国有5916名律师因违法违规执业受到惩戒,其中有1046名律师被取消了律师资格。律师须德才兼备,并具有良好的职业伦理,才能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实现程序正义。现阶段,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在我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全国近700所法学院中,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教研室是唯一一所专门性法律职业伦理教学研究室。前不久,公安机关查处了北京锐锋律师事务所周世锋等人纠结无业游民,肆意干扰司法,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我国律师协会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呼吁我国法学院必须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其意义就是对那些即将从事律师职业的法律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通过这门法律人的“思想品德课”让他们知道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哪些职业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四、结语
2015年8月20日召开的全国律师会议上,突出的亮点就是明确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性。行文至此,笔者认为,这次全国律师会议的召开对律师权利保障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给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带来了发展的春天。法律的作用更多的时候应该是通过权利来制衡权力以维护社会的安定,而不单纯是为了保障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孟建柱.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切实规范执业行为[N].检察日报,2015.
[2]曹建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N].检察日报,2015.
[3]刘学敏,刘作凌.在押被告与律师会见通信权的保障与限制——以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为借镜[J].现代法学,2011(7).
[4]陈光中,汪海燕.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J].中国法学,2010(1).
[5]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J].现代法学,2011(9).
[6]李红.比较法视野下的律师会见权法律保障与制约——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参照[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7).
[7]宋英辉,甄贞.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沈红卫.探求刑事正当程序——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9]徐隽.律师辩护,确保公正的重要一环[N].人民日报,2015.
[10]曹建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N].检察日报,2015.
[11]高铭暄,陈光中.公检法办案标准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刘苏婵(1992-),女,满族,吉林梨树人,法学硕士,中国刑警学院刑事诉讼法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1-0016-02